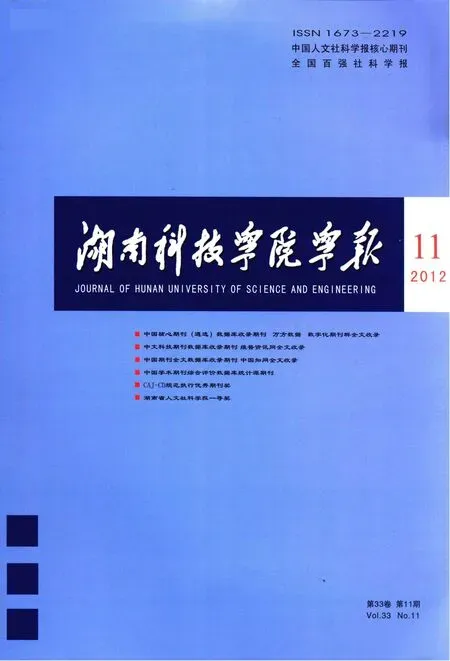论《公刘》诗中所体现的周族迁徙的文化意识
潘雁飞
(湖南科技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系,湖南 永州 425100)
一 《公刘》体现的周族迁徙的原因及路线
据丁山先生考证,周族一共十余迁,[1]著名的有五迁,一迁于豳,二迁于岐,三迁于丰,四迁于镐,五迁于洛。但在六首史诗中,大规模的迁徙主要表现在《公刘》和《緜》二诗中。前者记公刘去邰迁豳,后者记古公亶父去豳迁岐。这两次大迁徙前后相隔十世,但每一次迁徙都带来了周族命运的根本改变,周族人因此而一步步走向强大。
《公刘》全诗曰:
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餱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巘 ,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 琫容刀。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 覯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緜》全诗曰: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 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 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捄 之陾陾 ,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 鼛鼓弗胜。
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駾矣,维其喙矣!
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
《公刘》一诗记载了周民族形成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大规模迁徙。虽则周族始祖以农事受封立国,但毕竟仍还是游牧民族,而从这次迁徙后周民族则由游牧民族转变为农耕定居民族。
这次迁徙的原因,案《诗经·大雅·公刘》毛《传》曰:“公刘居于邰,而遭夏人乱,迫逐公刘。公刘乃辟中国之难,遂平西戎,而迁其民邑于豳焉。”“盖诸侯之从者十有八国焉。”[2]《史记·刘敬传》:“公刘避桀居豳。”《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公刘避夏桀于戎狄,变易风俗,民化其政。”《史记·匈奴列传》亦云:“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史记·周本纪》则说:“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脩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这些材料都无一例外地说到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夏后氏政衰,公刘是为了避桀(夏人乱)而迁徙。《毛传》《刘敬传》具言迁豳,《周本纪》只言迁徙,公刘之子庆节立国于豳。学者或以为矛盾,其实公刘迁豳已是事实,只不过到庆节时正式立国于豳而已。所谓“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应该是对《公刘》一诗的最好注脚。
关于豳地所属,旧说指今陕西旬邑和彬县一带1《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豳州新平县即汉漆县,诗豳国,公刘所邑之地也。”《汉书·地理志》云:“右扶风 栒邑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朱熹《诗集传》曰:“豳,国名,在禹贡雍州歧山之北,原隰之野。”又曰:“豳,在今 邠州三水县。”汉之漆县即今陕西之 邠县(彬县),宋之三水即今陕西之旬邑县。三家之说,影响至巨,后人多从之。,钱穆先生《西周地理考》以为公刘旧邑之豳在山西汾水一带,吕思勉先生从之。[3]笔者以前说为是。2今人齐社祥又考证豳地 “在陕甘交界、子午岭西麓南段及东南 ,今甘肃省庆阳、合水、宁县、正宁等县(北豳)及陕西省旬邑、邠 县、永寿、长武等县(南豳)。而以居南豳时间为最久。”可备一说,然范围过宽,具体城邑难定,不从。见齐社祥《公刘旧邑考》,《甘肃社会科学》2003 年第3 期。因前述载籍说“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脩后稷之业”,关于公刘是否由邰(今陕西武功县)迁豳,似乎也有了疑问。笔者以为“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当是史实,因载籍资料未明言具体地点,今人已难考实。但大致范围应在今甘肃庆阳一带。这里虽然是戎狄所属,但土地肥沃,气候湿润,是比较理想的农业耕作区域。因为夏乱不窋失其农官职务,所以不再以“后稷”官名称之。至公刘时,所居之地常为戎狄侵扰,后又还归邰地。胡承珙《毛诗后笺》云:“公刘之迁必非由戎狄而来,盖自不窋失官窜狄,公刘复兴必已还居邰地。至夏乱见迫,或以邰地逼近,故特改邑于豳,以豳邻西戎为中国不争之地。平西戎者,《正义》所谓与之交好得自安居,是也。……《传》又云:诸侯之从者十有八国。毛公所据周秦古书,尤可见公刘是避中国之乱而迁进西戎,故有诸国相从,必非由戎狄而迁矣。”[4]其论甚是。可见公刘迁豳实由邰地。
其迁豳具体路线如何?《公刘》一诗只有文学性的描述,而无具体迁徙路线:
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餱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 琫容刀。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覯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如果翻译成白话,我们更能清楚的想见其迁徙的和乐盛况:
忠厚我祖好公刘,不图安康和享受。划分疆界治田畴,仓里粮食堆得厚,包起干粮备远游。大袋小袋都装满,大家团结光荣久。佩起弓箭执戈矛,盾牌刀斧都拿好,向着前方开步走。
忠厚我祖好公刘,察看豳地谋虑周。百姓众多紧跟随,民心归顺舒畅透,没有叹息不烦忧。忽登山顶远远望,忽下平原细细瞅。身上佩带什么宝?美玉琼瑶般般有,鞘口玉饰光彩柔。
忠厚我祖好公刘,沿着溪泉岸边走,广阔原野漫凝眸。登上高冈放眼量,京师美景一望收。京师四野多肥沃,在此建都美无畴,快快去把宫室修。又说又笑喜洋洋,又笑又说乐悠悠。3徐培均译诗,见姜亮夫等编《先秦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年版,第569-570 页。
诗写公刘着手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他们将在邰地丰收的粮食装进仓库,并制成干粮,并将其一袋袋包装起来,接着拿起武器浩浩荡荡出发。他们边行进边察看边瞭望边测量,在行进中终于发现豳地土地肥沃,最适合种植、养殖,也适合采石、建房。于是决定将新的城邑建在豳地。
关于迁徙线路的记载,《史记·周本纪》露出了一些端倪:“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说公刘带领周族人顺着漆水、沮水,渡过渭水而定居于豳地而建宫室。然而还是不甚详细。这种不甚详细的特点说明了周族在制作祭祀诗时对活态型史诗的取舍特点,比较重视心灵上的崇拜和情感的抒发而不重视细密的叙述与记载。这也可以看出在文化较为发达的民族中由于对祭祀礼乐崇隆而导致活态化史诗的消解的痕迹。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说明“文献所谓公刘迁豳,不是一个点,当为一地域范围的‘面’,所迁豳的最后定点,不是一代一次完成,其间当几代周族在此‘面’上的自北而南逐步迁徙和逐步壮大”[5]。
但迁徙的史实我们至少是可以完全肯定的,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进一步证明彬县一带是周先祖的活动地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陕西长武县发现的先周文化遗址有司家河、胡家河、下孟村和碾子坡等,在彬县又有弥家河、雅店等遗址。特别是碾子坡遗址发现了大量的先周文化遗迹和遗物资料。“过去,发掘者将之分为两期,其中,早期约相当于殷墟二期,晚期相当于古公迁岐前后。现在,学者们提出碾子坡遗址还可以再细分,时代跨度可能更长。”[6]碾子坡遗址的先周文化广泛分布泾水上游,正是由这个子午岭、六盘山、陇山环抱的半封闭地域,孕育了早期的先周文化。而且碾子坡东南距今彬县不及20 公里,极有可能是周族居豳的中心城邑。
二 《公刘》所体现的周族迁徙文化意识特征
同时在《公刘》一诗中我们还发现了了几个民族迁徙的重要特征:首先,特别重视改善自身生存环境。诗中说“陟则在巘,复降在原”;“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覯于京,京师之野”。一路上以公刘为首的族人,忽登山顶远望,忽下平原细察,往看百泉交灌的大原,又越过南面的山冈,终于在边迁徙边观察中来到水源丰富、原野广阔,众所宜居的、可营造都邑的豳地。这些描写无不体现了对生存环境的重视。《毛诗正义》说:“相原地而往之百泉之间者,上已升巘观之,是登高以临下。此往百泉之间,自下而望高,且虑下湿,故往之泉处。前既升巘,今复陟冈,反覆审观之。下言‘于京斯依’,故知京是可营立都邑之处。”[2]可谓深得诗人之旨。
其次,初步具备了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山水意识。诗中还写道:“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毛诗正义》:“日影定其经界者,民居田亩,或南或东,皆须正其方面,故以日影定之。居山之脊,观其阴阳,则观其山之南北也。大名则山南为阳,山北为阴。但广谷大川,有寒有暖,寒暖不同,所宜则异,故相之也。流泉所以溉灌,故知观其浸润所及。相寒暖,视浸润,欲民择所宜而种之,逐浸润而耕之,皆所以利民富国,故公刘殷勤审之也。”[2]周族们上山岗观测日影、丈量平原和山丘、观察哪些背阴哪些朝阳,堪明水源和水的流向,然后觉得“豳居允荒”。正可以为本族人的生存和繁衍提供良好的自然环境,又在心里认识上确证这是一个天人合一、山水相拥的好地方,正好可以“度其隰原,彻田为粮。”所以决定要“于豳斯馆”。
三是有整体谋划和规划意识。全诗第一章写迁徙的准备,“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餱粮,于橐于囊”。极富于层次感;二章重点写择地与安民,“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三章重点写规划都邑乡野,“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覯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处处’,则处其居民也;‘于时庐旅’,则庐其宾众也”[7]。五章写对井田的规划,“井田的设施,适用于平坦肥美之地,如其地不平坦肥美则别为计划。平美之地作为井田,水厓下隰之地则作放养牲畜的牧地,此即谓之‘井牧其田野’,亦公刘相阴阳、观流泉,度其隰原、度其夕阳之所为”[8]。
四是以农立国的永久定居意识。其建都邑、修宫室、行祭祀(必伴随有立庙之举)、量田亩等等,都可以看出周族迁豳有一种深谋远虑,长久定居的意识。所以说“于豳斯馆”、“于时处处,于是庐旅”、“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五是迁徙时的高度统一与人心的和美融乐。全诗在具体场景和人物刻画中显示了在迁徙行动中步调高度一致,展示了当时的社会风貌,特别是周族昂扬和谐融乐的心态跃然纸上。其中“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见出整齐划一的步调,昂扬奋发的精神状态,团结一致的群体凝聚力。“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看出人心的和美。“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显现出周族这个大家族的和谐。
[1]丁山.古代神话与民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2-37.
[2]孔颖达.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影印本.
[3]吕思勉.先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1.
[4]胡承珙.毛诗后笺[M].合肥:黄山书社,1997.
[5]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485.
[6]徐良高.夏商周断代工程与先周文化研究[M].中原文物,2001,(2).
[7]范处义.诗补传[M].转引自: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53.
[8]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