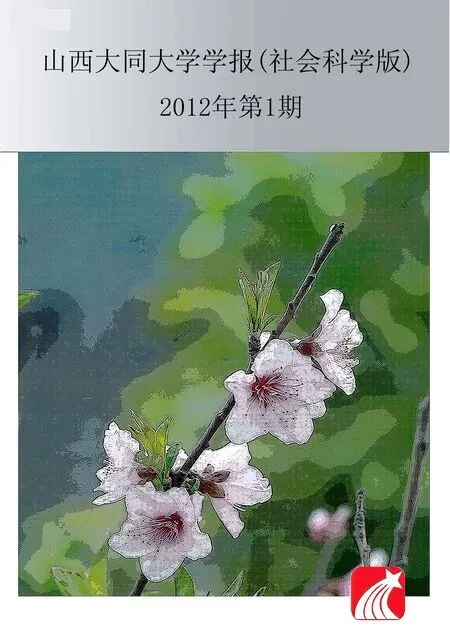权利本位: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逻辑起点
彭清燕
(吉首大学师范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权利本位: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逻辑起点
彭清燕
(吉首大学师范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权利本位是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逻辑起点。权利本位是以普遍赋权的方式通过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权利宪法化、地方法制化和具体化为中心而展开的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立法模式。作为一种法哲学观念,权利本位观表达了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应当以权利为本位或者出发点的一种价值陈述,实现了传统社会义务本位模式和权力本位模式向现代社会权利本位模式的转换,包含着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现代化的功能取向。
权利本位;少数民族;公民参与
权利本位(right based)是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逻辑起点。以普遍赋权的方式通过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权利宪法化、地方法制化和具体化为中心而展开的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立法模式,谓之为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权利本位。以权利本位思想作为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法学基础理论,其基本取向是确立了以权利和义务为分析框架搭建的法学体系中权利的核心地位。认为权利、义务、责任构成了现代法律的主观领域,权利是这一领域的核心。义务和责任均以权利为依归,以权利为导向,在逻辑和价值上以权利为其法理的前提或根据。[1]作为一种法哲学观念,权利本位观表达了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应当以权利为本位或者出发点的一种价值陈述,实现了传统社会义务本位模式和权力本位模式向现代社会权利本位模式的转换,包含着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现代化的功能取向。
一、权利本位作为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逻辑起点的基本内涵
权利本位是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逻辑起点,这一命题阐释的是个体权利何以作为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之逻辑起点,其基本内涵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权利本位观以权利为核心重构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理念是民族法制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古代社会以自然经济、宗法概念、家庭关系和专制独裁成为义务本位的经济基础、伦理基础和政治基础,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奠定了以权利为逻辑点和轴心的法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即权利的观念完全是近代理性观念的产物。[2]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法律设定义务的目的在于保障权利的实现;权利是第一性的要素,义务是第二性的要素,权利是义务存在的依据和价值。[3]在权利本位范式中,权力服务于权利,权力应以权利为界限,权力必须由权利制约。[4]权利本位作为一种全新的法学思想和文化模式,否定了义务本位和权力本位,是法哲学及法律文化的历史进步和必然。其次,权利本位观以权利为主导区分了现阶段民族地区公民参与权利与自治权力之间的轻重关系。民族地区公民参与权利作为一种个体权利,只有获得法律的确认和公权力的保障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其法律地位直接关系到整个民族法制的价值取向。虽然民族地区市场经济化已成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但是民族地区权力主导型法权结构遗存依然严重。压缩权力所占比重,扩张公民参与权利的空间,确立了权利的主导地位,增强民族成员对自治过程的介入,实际上就是推动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自治权力实现的过程,同时,权利本位思想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与承认多元利益的取向亦成为推动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最后,权利本位观以民族参与权利为主体,试图为异域的法律资源找到妥适的本土表达。我国民族地区公民参与的法制环境复杂。少数民族地区多为边(边疆)、山(山区)、寒(寒冷)、旱(干旱)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居住分散,联系不便,大大制约了民族地区公民参与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南方多数地区属于山地农耕经济文化类型,北方属于牧业经济文化类型,使各民族形成了不同的参与文化心理。且民族地区多是从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农奴制等各种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分别跨越了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传统政治文化的烙印与其它地方相比更为深厚,狭隘型和臣属型政治文化仍保持着较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的深层次意识中没有把政治参与当作自己的权利。现有的民族地区公民参与缺乏针对民族地区本土特征形成的法哲学体系或者法律理论体系。权利本位观从民族实际、民众个体、民族实践出发,深入分析不同族群的历史、命运、血缘关系、传统和习俗,理解民族的过去、现在及未来之间的相互关系,建构民族地区公民参与的理论与话语。
二、权利本位观对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理论回应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某种形式上的少数民族参与的制度安排,但是国家在计划、决策甚至具体实施许多直接涉及少数民族利益,或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发展战略或项目的过程中,却没有提供有效的少数民族的参与机制。[5]自上而下视野中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更多关注的是地域、自治机关和自治机关自治权力,其运作与发展的轴心围绕自治机关自治权力而展开,某种意义上民族区域自治法更像一部压缩型的少数民族行政法。在这个自治单元中,代表国家的自治权处于绝对的单向支配地位,代表社会个体的权利则因规定的过于抽象且流于形式而被一劳永逸地搁置起来。基于民族区域自治法关于权力和权利的配置与匡约,民族地区地方政治体系呈现出家长本位、权力崇拜的主要特征。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在自治权追求的社会同构化中被抑制,脆弱的公民参与权惧于公权力的强制性和扩张性随时可能被牺牲。忽视甚至扼杀少数民族公民参与,导致民族自治制度容量狭小而不堪重负,引发某些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的失范和崩溃。站在少数民族自治制度设计的宏大命题中,选择权利本位观作为构造原理的切入点及联结法律规则与个人行为的功能纽带,将公民参与权利融入自治权力的运行,就性质而言不只是表面上的自治机关的一方之政,而是公共权力和公民参与权利在合法状态下实现结合的高效运行机制。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权在民族区域自治中的总体地位及自治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核心问题,也是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关键环节。
权利本位范式下,自治权应当区分公民参与权利与自治机关自治权力两种维度。首先,就源流关系而言,公民参与权利是自治权力的源泉。社会契约论从自然权利出发,认为公共权力来源于“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6]“以及构成社会的人们的同意”。[4]我国宪法亦规定了一切权力源于人民。自治机关在聚居区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自治权力,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质上都来源于人民根据国家和社会管理需要做出的权力让渡。分析法学的权利哲学理论从个人和国家的权利权力关系转换视角证明了自治权力的来源。美国分析法学家霍利菲尔德把权利划分为要求权、自由权、权力权和豁免权四种类型,个人把权力权和豁免权让与国家后只享有要求权和自由权;国家在享有权力权和豁免权的前提下,负有保障公民要求权和自由权的义务。可见,权力实质上是权利的衍生形态,公民参与权利作为公民要求权和自由权的具体形式是国家保障义务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公民参与权作为整体的人民权利是自治权力赖以产生的源泉。其次,公民参与权利是自治权力运行的保障。权利本位应用于民族区域自治,就是促使公民参与权利与自治权力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结合,实现少数民族公民对自治活动的深度参与,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自治的实效。概括地说,公民参与权利对自治权力运行的保障力可分为抗衡力、支持力和监督力。抗衡力即借助公民参与权利的扩展,增强了权利对权力的抗衡度,改善双方的地位和力量对比关系,弱化行政权力的专横性,从而避免自治权力的片面性及独断性,保证其合法性、正确性和科学性;支持力即拓展少数民族公民有序、合法参与的途径,保障少数民族公民制度化参与的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性,促进自治权力和参与权利的良性交流和互动,从而有效地调解社会及民族矛盾,获取来自社会认同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支持;监督力即公民参与对自治权力的预警功能、检查监督功能和纠错功能,是制约自治权力具体的、普遍的制约方式。监督力有助于推动公共政策朝着符合人民公共利益的方向去发展,有助于保证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后,公民参与权利是自治权力的目的和归宿。行政法的任务不再限于消极保障人民不受国家过度侵害之自由,而在于要求国家必须以公平、均富、和谐、克服困窘为新的行政理念,积极提供各阶层人民生活工作上的照顾,国家应是各项给付之主体。[5]自治权力代表的是多数公民的公共利益,完全可以还原为一个个具体的公民个人利益。因而权力服务于权利,自治权力说到底是以公民参与权利作为其目的和归宿,是维护公民参与权利的重要手段。
三、权利本位观对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现实回应
我国少数民族构成成份复杂,分布范围广泛,地域面积广阔,自然环境多样,与汉民族相比,本身就存在着天然的特殊性。特别是近年来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正经历着形式、范围和深度上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解构、离心、破碎性、失衡、政府惰性、多元利益冲突以及多中心主义的特征。虽然这些变化是渐进的而不是革命性的,但是新变化与民族地区天然的特殊性黏合凸显了制度文本和制度实践的悖论,成为权力向权利转向的深刻社会资源,并推动权利本位观在治理民族地区各种方略中的渗透。
(一)权利本位观是解决民族矛盾的善治之道体制转换、结构调整、社会变革形成了民族地区的多元利益格局。利益调整触及了群众的分配、就业、医疗等具体经济利益,利益差别容易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而民族地区政府、公民和社会间的缺乏良性互动是群体性事件产生及升级的重要原因。权利本位观作为一种方法论是整体主义方法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的有机结合。宏观上权利本位观有利于对社会现象、法律精神及建构原则进行总体的把握,从而确立由一般到特殊的分析流程;微观上有利于观察底层权利主体对国家权力的回应和影响,形成由具体到抽象、个体到整体的分析思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权利本位观在解决民族矛盾上具备地方性、流变性、碎片性品格,具备了创造自治政府权力和公民参与权利良好社会结构的基本条件。从权利本位观出发,解决民族矛盾的善治之道实际上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自上而下的管理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从而建立以信任和互利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形成政府与公民社会的有效接合。此即一种善治模式,其所提出的治理理念和制度架构实质是权利本位观的具体化。为了社会和谐与善治的目标,政府应当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回应公民需求以解决“民本”问题;充分赋权于民以解决“民权”问题;保证最大限度的民众利益代表性以解决“民生”问题;通过与民间更多合作形成政府主导的多元化均衡治理格局以解决“民享”问题。[9]
(二)权利本位观体现在协商民主在民族地区的应用现阶段,我国民族地区发展的宏观背景是改革所带来的利益结构变迁及利益分化。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加之族群的区域性、多元性、混杂性,各民族及内部成员具体利益诉求各有差异。为了争取、维护和实现本民族利益诉求,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意识觉醒,使得他们愿意有意识地介入地方治理过程,民族地区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以投票为中心”的仪式性参与已远不能满足公民参与的需要,“以对话为中心”协商民主更接近实质性参与的本意,更契合民族地区多元、差异和多样化的特征。协商民主以公共利益为导向,以理性的对话和协商达成共识,实现个体正当利益的公共利益。协商民主的理性化是个体理性向公共理性的转化,压缩了公共权力个体化的生存空间,规约并限制公共权力的滥用。公民透过协商参与表达意见和利益诉求,政府透过协商回应民意,从而使政治交流从单向命令指挥走向双向交流讨论。最终,有利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从而建立起良好的政治互动关系,有利于避免政治失序状态,避免民主建设过程被打断。[10]协商民主以公民权利为出发点,通过公民的对话、讨论、辩论等手段参与决策的制度设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利本位观是协商民主的逻辑起点。协商民主中的权利本位观的关注视角是向下的,即呵护普通民众的个体利益,以普通民众的草根民主为根源,回应如何使普通民众的草根民主上升为影响政治决策的决定力量,在制度的框架内实现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建构民族地区公民参与的法律保障体系,通过公民参与行为影响民族地区决策系统,是权利本位下的协商民主的必然发挥。
(三)民族地区公法变革中的权利本位观改革后公法体系的建构试图把公共利益最大化建立在否定个体利益的基础上,这显然会导致社会发展丧失活力,最终导致公法体系的虚无主义。但是,如果改革后公法体系的重建与变革把个体利益的强调建立在否定、疏忽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则会导致社会发展失去秩序,更重要的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基础和制度规定性不相符合。[11]可以说很长一段时间内,当代中国公法体系变革是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平衡。民族地区双轨的精英集权政治金字塔结构所产生的官僚惰性,致使干群互动不足,基层社会参与到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公共决策中的机会甚少,浅表性或形式化参与难以真正参与具体决策,对个体正义的尊重及个人利益的维护远还未形成制度化。依据现代宪政精神,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服务并从属于公民的权利,公民权利在逻辑顺序上先于国家权力,在价值序列中也先于国家权力。就现阶段而言,基于公民权利的严重缺失,公法变迁的重要方向在于对公民权利的维护和捍卫。静态层面形成国家权力、公民权利与可以良性互动和平衡的法理关系与结构秩序,动态层面实现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运行机制。重视民族地区族群的内在世界,发现和使用民族群体的集体记忆、象征、神话、价值观和传统,以形成民族地区公民参与认同心理和文化共同体,才能更广泛地吸引民族公民的参与。毋庸置疑,民族地区公法变革中渗透着从公民权利出发、以公民内部眼光来凝视参与权利的权利本位观。
权利本位观并不否认权力,相对于义务而言,并不否认义务。只不过认为在权力与权利、权利与义务的体系中,权利应当占居主导地位,是民族地区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本位或者法律的出发点和重心。承认、尊重和保障民族地区公民参与权的主体地位,才能在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转型中创造一种反映少数民族的自身利益的有弹性、有活力的社会秩序。
[1]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2]庞德.法律史解释[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3]张文显.“权利本位”之语义和意义分析——兼论社会主义法是新型的权利本位法[J].中国法学,1990(4):25-34.
[4]张文显,于宁.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从阶级斗争范式到权利本位范式[J].中国法学,2001(1):63-79. [5]周勇,马丽雅.民族自治与发展: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6](英)霍布斯著,黎思复译.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7](英)洛克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8]黄锦堂.行政法的概念、性质、起源与发展[M].台北: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8.
[9]靳永翥.从“良政”走向“善治”——一种社会理论的检视[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234.
[10]张紧跟.从维权抗争到协商对话:当代中国民主建设新思路[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2):25.
[11]潘伟杰.公平正义的实现与当代中国公法变迁的方向[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5):99.
〔责任编辑 赵晓洁〕
Standard of Right:The Logic Starting Point in M inority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Legal Protection
PENG Qing-yan
(Normal College,Jishou University,Jishou Hunan,416000)
The standard of rights is the logic starting point in minority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legal protection.The standard of rights is the common empowerment way through minority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right constitution,local law and specific to launch the participation of citizens in legal protection legislation pattern.As a kind of philosophy,the standard of right view expresses minorities citizens to participate in legal protection which should be in the rightas the standard or starting point of a value statements. It realizes the traditional social obligation and power standard mode to themodern social right standard mode conversion,including the function orientation ofminority citizens participation and the law modernization.
right standard;minority;citizen participation
D903
A
2011-09-30
2011年湖南省教育厅基金项目(11C1020)
彭清燕(1970-),女,湖南龙山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刑法及民族法制。
1674-0882(2012)01-003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