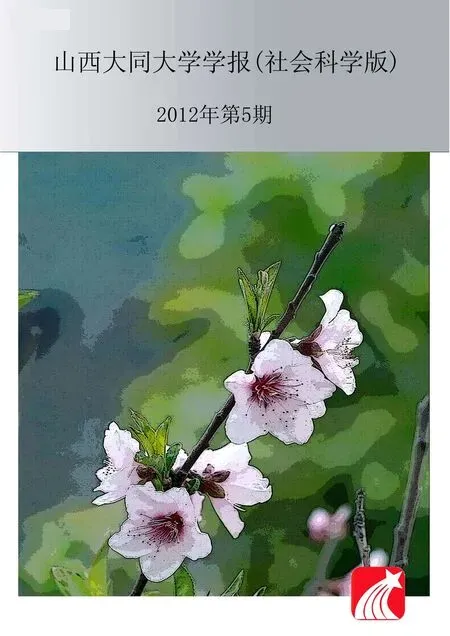《诗经》中“天”的演变
张晓娟
(山西大同大学文史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诗经》中“天”的演变
张晓娟
(山西大同大学文史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在《诗经》各篇章诞生的漫长年代里,中国古代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古代先民对自然的认识不断深入,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天”的认识的转变,集中体现了中国先民的思想逐步突破宗教的牢笼,开始审视“人”在自然中的地位,理性在人的思维中逐渐取得一席之地。这些思想对后来中国传统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
诗经;天;帝
在《诗经》各篇章诞生的漫长年代里,中国奴隶社会由兴盛转向衰亡,并开始有封建社会各因素的萌芽。在这一社会形态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古代思想也经由殷、周之际的起源而至西周的“学在官府”,并在东迁之后个人意识开始逐渐觉醒,为春秋末与战国初所谓学术下移民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诗经》某些篇章中可以看到,我国古代先民已经在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对自然及其运行规律的基本认识,并用其指导生产活动,如从《豳风·七月》、《小雅·十月之交》等诗篇中我们便可了解到周人已具有一定的天文历法知识。另外《诗经》中还有大量关于草木鸟兽虫鱼等生物的记载,虽然这些知识还停留在经验观察的阶段,且带有较浓厚的宗教成分,但它毕竟凝结了古代先民的理性认识,随着这种认识的深入,动摇了西周时期的天命观,为人们逐步摆脱宗教思想的束缚准备了条件。
这些产生于不同年代的诗篇反映出我国古代先民对自然的认识不断深入,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天”的认识的转变。“天”是中国哲学最为古老的范畴之一,“是贯通中国哲学始终,并构成中国哲学特点的范畴,它对民族心理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1]《诗经》各篇章对于“天”的认识的演变,集中体现了中国先民的思想逐步突破宗教的牢笼,开始审视“人”在自然中的地位。
一、“自天降康,丰年穰穰”
殷周之际,由于金属工具和畜力的应用,农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与农业关系较为密切的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在上古时期,农业的丰歉受人力影响还非常有限,更多的要受制于雨水、灾异等天时。这样必然导致上古先民对天的关注,并进而形成对天的认识,只是这时的认识更多的是从宗教的角度出发,正如席泽宗所说:“在人力所不及的领域,是巫术和宗教的领地;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经验科学在尽着自己的责任。”[2](P48)
当人类社会由原始氏族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人们的宗教崇拜也由万物有灵的多神崇拜过渡到一神崇拜。在殷人的崇拜中出现了“帝”、“上帝”的崇拜,殷人的“帝”、“上帝”是掌管自然、人类社会的主宰。郭沫若、陈梦家、张立文等学者以殷商时期最为可靠的材料——甲骨卜辞为据,认为殷商时期的至上神是“帝”或“上帝”,而“天”的概念是周代统治者提出的。但周代统治者提出的“天”已包含德的思想,与冯友兰所谓“主宰之天”[3](P45)还存在一定差别。所谓“主宰之天”是把“天”作为无上的权威,作为造物主,它是决定人类社会、自然界一切变化的终极原因。这里的“天”与“帝”、“上帝”的概念相当。《尚书·西伯戡黎》中记载,当商纣王得知周人伐黎时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从中我们可以判断,在殷末或殷周交替之际,“天”的概念应已产生。虽然《尚书》的成书年代要晚于殷代,但时间上应很接近,其所反映的殷代思想应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果仅以殷商卜辞为据不以其他资料佐证似乎也有不妥。
反映这一时期思想的文献中,“天”、“帝”、“上帝”往往混用,“天”即是“帝”、“上帝”。在《商颂》、《周颂》以及《大雅》的部分诗篇中这种状况较为多见。《诗经》中商颂虽然是商人后裔宋国君臣的乐歌,但从他们对其祖先的赞美中也可领略商朝统治者对“天”的理解。在《商颂·烈祖》“自天降康,丰年穰穰”的诗句中,“天”被塑造为能主人间吉凶,可以决定农业丰歉的宇宙最高主宰。侯外庐先生认为殷商时期的宗教崇拜是一元祖宗神,天、帝、上帝既是宇宙的主宰又是殷民族的先祖。但从《诗经》的一些篇章来看,这一观点似乎值得商榷。“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颂·玄鸟》)中的“天”是一位创造了殷商民族的造物主,从中我们很难发现“天”与殷商先祖有血缘关系。从“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天命降监,下民有严”(《商颂·殷武》)看起来,“天”更像是一位发号施令的主宰。再从《商颂·烈祖》来看,殷商的先王更应是侍于天帝身边的低一格的神祗,殷人通过祭祀先王来感知天命。“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周颂·天作》)中的“天”同样是一位造物主,只是这次创造的是周人的发源地。当“天”被帝、上帝代替时,“天”则成为具有人格的神。如《商颂·长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中的帝是一位主宰人类社会繁衍的人格神。它还能主宰王朝的兴衰更迭,“商之子孙,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大雅·文王》)。
殷至周初,人们对“天”的理解是在探索自然和人类生成过程中迈出的坚实一步,此时已经能够把自然界作为统一的整体来理解。虽然其中夹杂着宗教的非理性因素,并被用来解释统治权的天然合理性,但毕竟比前期神话式的解释要进步了一些。
二、“天监有周,昭假于下”
在殷人的眼里,天、帝、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它主宰着自然界、人类社会。从殷人遇事问卜的生活状态来看,天神的意志是很难捉摸的,人们只能惶恐地等待天神的判决,屈服于天神的绝对权威,没有一个可以借鉴的经验或原则来领会它的意旨。在这样的宗教信仰中理性没有立足之地。这种状况同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人类的知识还仅限于感官直觉,不足以把握自然运行的规律。这时的自然仍然是异己的、盲目的支配力,与之对应的天神则是与所有人相对立的。
到了周代,宗教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周初统治者为了解释商周变革,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对殷人的宗教信仰做出变革。“周人把天神想象和说成无限关怀人世统治的有理性的最高主宰,和祖宗神一样,是与自己同类的善意的神。这个天神不再是与人们相对立的盲目支配的力量了,它和最高统治者结成了亲密的关系,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嫡长子,选派他们统治疆土臣民。”[4]周代出现了天子的观念,周王往往自称天子,但这里的天子并不具有自然血缘关系的含义,而只是被天神选为嫡长子并统治天下。这里就存在一个选择标准的问题。天神为何放弃了殷商而选择了周?为此周人提出了“以德配天”的神权理论。在周人看来,君权虽然也来自天神,但他们取得君权是由于具有了高度的道德修养,能够成为天神在人间合格的代理者。正如《尚书·诏诰》所说:“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为恤。”商朝统治者因道德败坏而失去天命,周王必须时刻加强道德修养才能保有天命,永享天下。
经周人改造后的天神,虽然仍有主宰的功能,但天神的意志不再是难以知悉的了。它选择了有德的周人来治理天下,“德”成为天神选择合格代理者的唯一标准,成为天神、祖宗神和现实统治者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这时的天被周人贴上了“德”的标签,具有了“德”的属性,也即冯友兰所谓“义理之天”。[3]
这些思想比较全面地反映在《诗经》早期的作品中。“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大雅·文王》)常被人认为是疑天思想的反映,其实这是周初统治者为从思想上压服殷代遗民,告诫历代周王而提出的。这一观点表明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天神有一定的取舍标准,那就是德,殷人因无德而失天下,周人因有德而得天下。但周人如果失德,那天命也会变更。事实上表明了天的道德立法者的身份,而它的意旨——天命也是有着确定内容的。《大雅·大明》中“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表达了上天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人间,时刻在用德的标准衡量地上的君主,而王者也必须时刻以德治理天下“克配天命”。“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天监有周,昭假于下。”(《大雅·烝民》)则进一步表达了自然、人类社会无不按着天定的法则运行,同时“天”也关注着人类社会的秩序。《周颂·敬之》中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日监在兹”的句子,说明在周人的意识中,天随时监视人世,并以德决定个人的命运。
周代前期,“天”仍然是主宰,仍然统治着整个宇宙,但这时天的意志已经可以为人所了解,至少是部分了解。“天”不再是盲目的、令人战栗的支配力,而是“燕及皇天”《周颂·雝》),安然祥和的上天,有德之天,“义理之天”。[3](P45)人间的王者要想保持天命必须修德以配天。在对天的崇拜中,加入了对人事的重视,人的地位有所提升,理性的光芒开始进入人类意识。
三、“昊天不俑,降此鞠讻”
西周王朝的兴盛并没有持续很久,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阶级趋于分化,阶级矛盾日益突出。至宣王时期,“不但没有缓和社会矛盾,挽救当时的统治危机,反而越来越暴露出内部虚弱”。[5]此时,“国民阶级的觉醒将创造出新的文化”。[6]
西周末至东周初,奴隶制的危机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趋深化,统治者的权威也逐渐削弱。这种社会情况反映在思想上,就是西周以来维护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宗教信仰的动摇和神权的削弱。这时出现了怨天、疑天甚至骂天的思想。如《小雅·雨无正》中“浩浩昊天,不骏其德。”就明显表露出对天的怨尤。金建民认为怨天思想反映了古代先民开始反叛天命,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7]这种说法似乎不太准确,怨天未必是反叛天命的开端,也很难说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因为对天发出怨尤,必然是天应为而弗为才引发的。认为天应为,说明在诗人看来天或天神有一定的行为准则,而这个准则就是周初的“德”,这仍然是旧有的思想。天弗为只是引发怨尤的原因,并不是反叛天命的起点。《小雅·雨无正》第三章言:“凡百君子,各敬尔身。胡不相畏!不畏天呼?”说明作者仍然对天抱有幻想,并没有迈出反叛天命的一步,并没有否定天及其行为准则。“怨天思想,不否认天的存在,也不否认天对人的干预,而只是认为天的干预不公平”。[2](P29)当对天的怨尤不能改变现状时,就会产生疑天、骂天的思想。
疑天是对崇信天及其行为准则思想的动摇,骂天是对其进行斥责甚至否定。《大雅·荡》中“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认为上帝反复无常,没有确定的行为准则,怀疑其至高无上的权威。《大雅·云汉》中“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以问天的方式表达了对天的不满。《诗经》中有些诗篇直接对天、上帝提出了控诉,甚至是责骂上帝。如《大雅·召旻》中“旻天疾威,天笃降丧”,《小雅·节南山》中“昊天不傭,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都是对天的控诉。而《大雅·板》中“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犹不远”则是对天毫无顾忌的责骂,对天的权威的否定。
“在这些怨愤、责难中,周初统治者为上帝披上的‘天惟民主’、‘惟德是辅’的公正面纱剥落了,天命的权威扫地了”。[8]在控诉和责骂声中,天的人格神含义逐渐褪去,理性在人的思维中取得一席地位;人的思想部分地获得了解放,一定范围内可以在理性的支配下去探索自然,积累知识,形成关于自然及其运行规律的较为正确的观点。
四、“鸢飞戾天,鱼跃于渊”
在《诗经》中,有些诗篇里的天不具有以上属性,而是用来指代客观存在的、物质的天。这些诗篇中有些年代较早,基本上与表达“主宰之天”、“义理之天”思想的诗篇同时,如“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大雅·旱麓》,作于周初),有些则相对晚一些,如“有鸟高飞,亦傅于天”(《小雅·菀柳》,作于幽王时)。这里的“天”也即冯友兰所谓“物质之天”[3](P45)。说明“天”的概念在产生时,可能既有宗教性质的含义,又有自然性质的含义,只是由于帝、上帝的居所在天上,更多时候天与帝、上帝表达同一概念。
《诗经》中表达“物质之天”的诗篇各自从不同的侧面形容天的自然属性。如“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小雅·蓼莪》)形容天之大;“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王风·黍离》)形容天之深远。这些对“天”的描写是关于“物质之天”的最直观的体验和认识。
由以上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天”的概念产生时,其物质属性和宗教属性相夹缠,进而导致人们将自然现象同社会现象作种种比附,成为“天人合一”思想之源头;当“天”的人格神含义被逐渐剥除时,天又成为“物质之天”,人们认识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各有其背后的原因,这又为后世“天人相分”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早期思想都对后来中国传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2]席泽宗.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三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6]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金建民.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科学思想[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8]褚斌杰,章必功.《诗经》中的周代天命观及其发展变化[J].北京大学学报,1983(8):50-58.
Meaning Evolution of“Tian”in The Book of Poetry
ZHANG Xiao-juan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Shanxi Datong University,Datong Shanxi,037009)
During the 5hundred years recorded in The Book of Poetry,the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had undertaken tremendous changes.Our ancestors were gradually knowing more about nature and changing their recognition of“Tian”(heaven)in particular,which shows that our ancestors had gotten rid of the restriction of religion and begun to reevaluate the position of“man”in nature so as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rational.This thought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formed in a later time.
The Book of Poetry;heaven;God
I207.22
A
1674-0882(2012)05-0052-03
2012-08-21
张晓娟(1981-),女,山西山阴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book=68,ebook=162
〔责任编辑 郭剑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