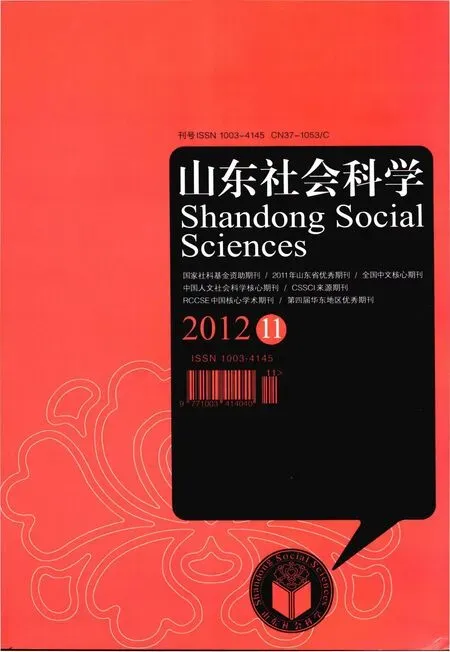地方性知识中的生态伦理与生存智慧
江 帆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 110036)
人类要适应环境,要在特定的生态区位内求得生存与发展,除了生物性本能与技能外,文化的发展也为之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或群体都形成有与所处生境相谐适应的独特的知识体系和生存智慧。这种文化是为了满足不同民族或群体的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需求而创造出来的,是他们对客观世界和自身认知的结晶,也是该群体进一步认知的基础和出发点。群体内的民众可以通过学习而不是仅凭先天的本能来适应环境,可以凭借其特有的文化去改造和利用其生存空间,以创造该民族或族群的全部生存条件和维系民族的延续。地方性知识,即是不同民族与群体创造的生存文化之一。
“地方性知识”是与普适性知识相对应的一个学术概念,是指在一定的情境(如历史的、地域的、民族的、种族的等)中生成并在该情境中得到确认、理解和传承的知识体系。地方性知识具有地域性、整体性、实用性等特点,是一定地域的民众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体力和脑力劳动创造并不断积淀、发展和升华的物质和精神的全部成果和成就,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具有育人、文化保护、生态保护、医学、环境与资源管理、农业研究、调解民间纠纷等价值。①邓正来:《“生存性智慧”与中国模式——在比利时根特大学的讲演》,《文汇报》2011年7月19日。“地方性知识”除了像风味饮食制作、民族居屋建筑等一些极具地域与民族文化色彩的标识性事象之外,还有许多散布于人类群体日常生活之中的大大小小、各具特色的文化创造,以及一整套较为完整的传承体系。对于这些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的地方性知识与生存性智慧,我们实难一一而论。但却有理由说,正是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文化创造及其演化传承,才构筑了人类文化金字塔的坚实根基。
地方性知识对特定民族或群体的生存与发展构成重要的作用与影响,是特定民族或群体的智力武库。若以地方性知识内蕴的生态伦理与生存智慧来看,在当代社会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本文拟以北方民族与区域群体的地方性知识为例,通过对其内蕴的生态伦理与生存智慧的观照与剖析,吁请深陷“生态危机”中的当代社会能够重新审视、评估地方性知识的价值,消减西方话语中的普世理性与科学主义,缓冲与消解工业及科技导致的“生态暴力”,促进“观念转型”,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感性实践与内省式认知:地方性知识建构中的生态伦理
美国认知人类学家沃德·古德纳夫认为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观察和组织物质现象的体系,我们要研究的不是这些物质现象的本身,而是它们在人们头脑里的组织方法。文化不是物质现象,文化是对物质现象的理性组织。古德纳夫指出:组成文化的不是事物、人、行为和情感,而是由常规和概念以及一套组织这些常规和概念的原则,文化存在于文化持有者的头脑里,每个社会的成员头脑里都有一张“文化地图”,该成员只有熟知这张地图才能在所处的社会中自由往来。人类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这张“文化地图”。①王海龙:《细说吉尔兹》,载[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地方性知识便是这样一张“文化地图”,其建构的显著特征之一即在于偏重对事物的直接感悟。通常情况下,人类群体在生存实践中很少用归纳和演绎来认识客体的性质,对客体的认识少有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人们直观的感受和内在的体验往往高于理性的思维,离开了直觉思维,就无法理解地方性知识,直觉是地方性知识形成与建构的基本特点。从宏观上看,每一特定区域内的民众都是对所处生境中各种经验现象进行酝酿、体会、内省之后,豁然开通而形成认知,这些认知与通过外向的思维,通过逻辑演绎所形成的普适性认知与观念有着种种不同,因而每一特定的地方性知识体系都带有鲜明的区域性特点,恰如丹纳所言,是“自然界的结构留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记”②[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225页。。我国北方民族与区域群体的地方性知识建构,便体现着这一认知特点。
由于地理的隔绝,历史上,生活在我国东北区域的满、蒙古、锡伯、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在政治上保持着与中央王朝联系的同时,在文化上又有着相对自主的发展空间。东北区域“生态位”作为一种生存背景,是区域内各民族生存的基础,世代栖息于此的各族民众,只能在这一背景之上去构建自己的认知与文化,自主选择着生态逻辑和文明逻辑,自发地谋求与所处生态区位的自然环境与资源条件的调和。这种认知与选择,经年历岁,不断累积、汰选,形成了富有东北生境特色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与文化传统。与中原内地农耕民众对土地的关注与崇拜不同,北方民族与区域内的群体对生存空间的认知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对山林、草原、旷野、湖海的依恋。区域内群体的地方性知识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族群与所处生境的资源关系来构建的。在其生存的视野空间内,所有物类的层次划定和意义区分都以其与人类生存的关系而定。
以东北渔猎群体的地方性知识来看,便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意蕴。在东北这片巨大且气象万千的“生态场”上,北方渔猎民族生产、生活习俗与文化的建构,处处体现着对区域生境与资源条件的自主或不自主的适应。“依山滨海”以渔猎为生计,要求渔猎群体必须熟稔区域内的山林与湖海的资源条件及生态特点,诚如俄国学者柯斯文所说,“完全熟悉自己的乡土、自己的求食地区和围绕着自己的自然界”③[俄]柯斯文:《原始文化论纲》,张锡彤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59页。。渔猎生计的资源核心不是土地,而是山林和江河湖海。在古代社会,东北区域多为人迹罕至的森林、雪原、海滨,与栖息于此地的渔猎民族关系最近的便是繁若天星的动植物种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渔猎民族的衣食之源都是向山林和江海索取,飞禽走兽、草木植物、海洋鱼类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和生活资料。渔猎生计的特殊需要强化了当地民众掌握地理知识的能力以及对周遭可摄取资源的注意力和记忆力,人们练就了卓异的观察力,谙熟各种野生动物和海洋生物的习性、行踪和生息规律,积累了广博细腻的动植物知识。在传统渔猎中,猎人采用蹲碱泡子伏击鹿、驼鹿,用狍哨引诱狍子,避开野兽的警觉向其接近等方法狩猎,出色的猎人从动物的一个脚印上获得的知识以及由此产生的敏锐的判断力,恐怕现代的狩猎者也得为之感叹。而以捕捞为生计的群体,很早便形成了对各种江河湖海生物的认知,不但能够识别数百种鱼类,一一说出名称,而且谙熟这些水中生物的生长习性,人们根据不同季节鱼类的栖息走向来选择水域,采取多种方法捕鱼。东北民间一些世代传唱的歌谣,反映了这类地方性知识的传承。如“九月狐狸十月狼,立冬貉子绒毛长。小雪封地没营生,收拾压关打老黄”,老黄指的就是黄鼠狼。这里是说农历九月狐狸的毛皮最好,十月的狼皮毛最好,小雪后黄鼠狼的毛皮最好,这些节气是最适合打这些猎物的。当然也有不适合狩猎的节气,如“打春的狍子,立夏的猫子,要吃它们的肉,不如啃棉花套子”,言外之意是告诉人们这时节动物的肉不好吃,就不要去打了。④参见杨林勃:《流传在承德的满族歌谣》,《满族研究》2001年第4期。其实,这一时节的动物正处于交配繁殖的旺盛期,适时禁止狩猎是为了保护这些动物种群的繁衍与发展。
同样出于生存的需要,东北渔猎民族在物候历法、季节划分、季节征象方面,也积累了大量的独特认知与经验。如满族长篇说部叙事《乌布西奔妈妈》中,对季节的物候知识便有这样的描述与传承:
正是海中大蟹肥的时节,正是海中大马哈要洄游的时节,正是海中群鲸寻偶的时节,正是海中神龟怀卵的时节,正是山中紫貂交配的时节,正是山中熊罴爱恋的时节,正是山中梅鹿茸熟的时节,正是山中花木快进入成熟丰满好时节,鞑靼寒流南下海水不冷不温,岩杵暖流北上海水不猛不涌,风浪再狂,海中生存最佳时分……①鲁连坤讲述、富育光译注整理:《乌布西奔妈妈》,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5页。
渔猎民族对自然环境与物候的这些观察与认知,蕴涵着丰富的生态知识与生存经验,堪称具有实测、实证性的乡土地理物候志。这些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生存策略,折射着东北区域民众在生存实践中的一种知识能力和创造能力。
以现代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人类只是生物群落中的一个种群,与同处于一个群落中的其他种群不仅具有生存竞争中的食物链关系,更具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互利共生关系。而这些具有现代生态伦理意识的理念,在北方渔猎群体的地方性知识中也多有体现,且大多内化为民众的精神信仰和行为规范,在民间有着深广的观念认同与传承基础,规约和控制着人们的经济活动行为及日常生活行为。
在北方渔猎民族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中,一切河川、森林、山峦,无不有精灵主宰。这些主宰神灵,其本性既非善,又非恶,他们对人类是友善相待,抑或恶意相加,完全系于人类的行为。人们笃信,只有虔恭敬奉、恪守山林禁忌和猎规,无非分之举,不乱捕乱杀,对主宰性精灵待之以善,才能有所收获;如违反猎规,触犯禁忌,则会触怒精灵,遭受惩罚。过去,北方渔猎民族素有“春秋不射鸟,盛夏勿网鱼”的习俗,以保护鱼类和鸟类的繁育。传统狩猎中忌捕杀怀胎、带仔的母兽及幼兽,若猎取这些野兽会被视为无能而受到人们揶揄;打猎忌讳“断群”,猎取十头以上的兽群,一般要放生几头;每次围猎的最后,都要放生幼兽和带仔的母兽。在北方渔猎民族传统的资源观念中,普遍都没有囤积居奇和赖以发财的意识,人们狩猎主要是出于衣食之需。诚如宋使萧大亨对蒙古族狩猎的记载:“若夫射猎,虽夷人人之常业哉,然亦颇知爱惜生长之道,故春不合围,夏不搜群,惟三五为朋,十数为党,小小袭取,以充饥需而已。”②郭雨桥:《郭氏蒙古通》,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第486页。在东北民族传承的各种动物神祭祀与神话传说,也在客观上对生态区位中动物的保护与繁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北方民众对于供给他们生存能源的山岭、森林、草原、江河、湖泊等,普遍怀有神圣的情感,不但经常进行祭祀,而且俗信对其进行污染是罪孽和不吉利的。这些禁忌的生成,皆源于人们对自然的崇敬、感激、畏惧和顺从之情。对北方民众来说,对自然的关爱与禁忌,已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或公约,更是一种心理上的信仰与信念,一种自主的价值取向。
上述这些与食物链相关联的地方性知识,折射着东北民众朴素的生态保护意识。尽管北方各民族地方性知识生成的背景不同,但其价值取向却是相同和或相近的,即:对于与自身生存利害攸关的自然物和自然力,普遍怀有敬畏的情愫,并因此而演化出各异的崇拜形式,形成种种行为规范。而一些民众奉之为神圣,在生产、生活中加以诸多行为禁忌的自然物或自然力,说到底不过是那些与该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利害攸关的价值物。在地方性知识中对许多神灵的崇拜,其实质也是对群体所处生境中的某些被歪曲地反映了的、神秘化了的自然资源价值的追求。这些体现着生态伦理、对区域生境具有维护功能的地方性知识,是北方各族民众在经年累月的生存抗争中的经验积累,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许多知识在今天来看犹是可取并值得发扬光大的。
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智力武库:地方性知识中的生存智慧
地方性知识所蕴涵着的生存智慧体现为对外部环境的认知与和谐互动。从生存智慧的角度审视北方民族的地方性知识,不难看出,大量具有族群认知经验特点与技术内涵的地方性知识,之所以在北方民间承袭千载,关键在于这些地方性知识生成于北方民族的特有生境,具有“合宜”的特点。由于人类的生存需求是反复出现的,因而为生存而采取的“合宜”的行动也必然反复进行,这种承前启后不断的反复演示,最终使一些生命体验与生存活动方式成为地方性知识。
在北方民间传统的饮食和用品加工中,各族民众掌握了大量与生活关联紧密的自然物质本身的特性和变化规律,积累了很多带有现代物理、化学知识特性的民间知识与智慧。例如,过去北方民间用自种的苏子榨油时,用自制的木制榨油床,再把经过蒸沸的苏子放入榨床里,用打楔挤压的方法榨油,出油率便较高;将蒸沸的稷子米发酵,采用蒸馏法酿制米酒,还可以调控酒精的度数。如此等等,都表现出北方民族在对这些自然资源进行能量转换、利用方面的知识与智慧。
北方民族对区域生境内各种动植物的认知并不仅限于满足日常的衣、食、住、行之需,这种认知还体现在对生境自然资源的利用广度和深度上。满族长篇说部叙事《乌布西奔妈妈》,便展示了满族及其先民对东北区域丰饶的动植物资源的药用、医用知识与智慧。他们或利用生境中植物的叶、根、茎、花、果等治疗不同的疾病,或利用动物、鱼类、自然界的水、土、岩石、汁液、寄生物等作为滋补、延寿的药物,其中一些民间医方、偏方,有显见的疗效与适应性,是北方渔猎民族民众以生命为代价总结出的实践经验。诸如:
突发天花魔蹂躏西邻,彻沐肯大玛法跑狗传信,求助乌布西奔。乌布西奔急领侍女多名,进锡霍特阿林山洞,采狼毒茶、耗子尾巴草、土瓜蒌、乌头草根,亲手筛研,蚌炊调浸,迅治老弱婴孕七症,创下神方十三宗。力倡病家息躲深渊大谷,远避患地腐尸臭瘟,彻沐肯四十多个日夜,青青峻谷搭病棚,萧萧慑祸匿消遁。从此,传下东海躲病之俗,山魈野叟保命经。①鲁连坤讲述、富育光译注整理:《乌布西奔妈妈》,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
叙事中还有北方民族以鱼耳石和吐丝草研熬苦汁敷治箭伤,用笸箩鱼骨针拍刺穴窍治病,用鱼油和草脂油燃灯熏香驱瘟,饮千年人参水、百岁海龟血延年益寿等认知描写,颇为细腻生动,显示出北方渔猎民族很早便拥有了将对自然的认知转化为实效的生存智慧。
对“征兆”的认知与把握也体现着一种生存智慧。征兆的被认识,是北方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反复观察、验证,不断积累、总结的结果,带有较强的实证性和一定的科学性。北方民族自古就沿袭以草木、星宿等自然物占卜的习俗,主要是观测其变化,以卜年成的丰稔、虫害、灾难、疫疾等,类似以自然现象变化进行卜验以及由此引发的俗信又称“前兆俗信”。为适应生产、生活的需要,北方民族必须对季节的交替有比较准确的判断。在群体智慧的世代累积下,北方民间在物候历法、季节划分、季节征象方面,积累有丰富的认知经验与生存智慧,诸如卜验春象的雪卜、冰纹卜、冰响卜、验地室、刺猬闹春等;卜验秋象的黄花报秋、青蒿断秋、江虫葬秋、鱼汛知秋等各种观测季节征象的方式与方法等等。②郭淑云:《原始活态文化——萨满教透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页。特别是在自然灾害、瘟疫及气象征兆的预测上,更是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功利性作用。如北方民间在观察地气物候时,常以该地域的诸生物体的动态为依据,对此,在一些北方民族的族传史料多有记载,如满族《瑷珲祖训拾遗》中便记载有:
测土质,查蚯蚓在一定方位中数目,多为沃,少为瘠。蚯身红嫩,蠕生液者为地润,堪喜;蚁蛭密布,群蚁络绎若闹市,吉地;蜂若团球,轰鸣扩耳,必花繁蜜甘,沃土;蜥肥尾壮,迅行如闪,栖殖愈久,地望甚夸。测湖质,查蛙蚪在一定方位中数目,多为淤,少为畅。验水,观鱼鳃,鳃红艳而洁,水清鱼肥;鳃灰泥滞,水混鱼悲;鳃褐宿虫,餐饭酿难。峥山藏猛兽,秀水栖龙龟,苍山鸣丽禽,峭岩屹鹫鹏。疠瘴染污穴,粗粝壮胃肠。懒卧生杂疴,勤作延寿方。熟研万事趋,天道豁然知。③石方:《黑龙江区域社会史研究》(续),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
在把握有关灾害、瘟疫、灾异的征兆中,民间也总结、积累出一系列的观察方法:
巢居无鸟,树叶卷萎为时疫来临之兆;一年四季燥旱燥热,或阴雨不止,或风啸弥天,均视为瘟疫前兆;草如柴,叶焦落,虫蝶死,塔头热,地生烟,不过五日即生流火;鸟群飞噪,连日不宁,必生灾异,凶象可断;村寨中有人突然身上发热,前身生白红相间的花点,奇痒难忍,重者甚至人事不省,或高烧,喉痛痒、便秘、喜冰、妄臆语,皆视为天花先兆;春燕弃巢不归,檐雀坠死,亦被萨满视为天花疫先兆;有客驱车而过,突然拉车之马喷鼻踏蹄不前,嘶叫不已,将有猛兽在此地出没。④富育光:《萨满教与神话》,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页。
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北方民众积累、摸索、开发出的土方、草药验方多达数百种,所治范围几乎包括了各种常见病。在缺医少药的漫长历史时段里,北方民族依靠土方验方祛除病痛,收到了使族群健康发展、提高生命质量的效果。
北方民族地方性知识所蕴涵的生存智慧还体现在对生境资源的利用与能量转换上。例如,西方的营养学家在18世纪就发现,玉米如果与碱混合食用,能够产生几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以及一种维B染色体——烟碱酸。在北方民族传统的饮食习俗中,将发酵后的玉米面以碱调制,蒸发糕、贴饼子,或者以微量面碱熬制玉米馇子粥,是北方民族最为常见的饮食。虽然普通民众不一定会在理论上通晓玉米与碱混合食用能够产生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但是生活的实践与经验开启了人们的智慧,使他们知道怎样做于人的身体健康有益,什么样的行为是“合宜”的。还有,北方民族对于自然周期给予人们生产、生活的种种限制,并非只是被动的顺应的。为了满足群体与个体的生存、发展的精神及物质需求,人们在生存实践中形成了一些对自然周期带有补救、转益特点的生产、生活习俗。在东北地区,自然界中的食物链会因气候、季节的影响而时断时续、丰寡不均。在寒冷而漫长的冬季,为了调剂饮食,北方民间创造出腌制、熏制、晾晒、风干、冷冻等多种保存食物的习俗。还创造了挖地窖贮藏蔬菜以保鲜的技术和方法。再如,古往今来北方乡间始终沿用的苞米楼,便体现着一种收纳、贮存粮食的智慧。苞米楼的建造并不复杂,其材料大都来自山林中的杂树,选出数根稍粗且直的做立柱,在距地一米多高的地方加横撑铺仓底,再层层向上加仓壁,并做成一面坡或前后坡的顶盖,四周的仓壁留有很宽的缝隙,以利于通风。由于仓底离地面较高,既可以防止老鼠和家畜家禽偷吃,又避免离地面太近使粮食受潮发霉。以这种方式贮存玉米,就可以放心地现吃现拿,如此等等,不一而论。
北方民族地方性知识文化是在民族的历史嬗变中自行生长、形成模式的自为过程,是北方民族民众自我选择的结果,对于与东北“绝域”生境抗争的满民族生存史,有全景式的展演。此中,生存智慧对于北方民族地方性知识的生成具有深层的建构作用。
三、消解现代“生态暴力”:地方性知识价值的重拾与提升
21世纪又被称为生态世纪。累积了几个世纪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所伴生的全球性生态灾难已经临近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阈限,各种可称之为“生态暴力”的行为充斥于人类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已经到了整个人类都不得不高度关注并需要共同采取果断措施的关键时刻。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我国北方区域内由于人口的快速增加以及森林、草原等自然资源的锐减与受损,北方民族的生计方式也不得不随之进行调整与改变,一些世代从事渔猎生计的群体,迫于生存的压力,开始陆续转为农耕。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精耕农业的推广,各种现代工业技术的引入,对北方区域生境的改变与影响非常明显。例如,在不适于种植的山区强行修造梯田,以极具破坏性的技术,将大面积层次丰富的原始自然景观改造得千孔一面,使一些山林植被的破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精耕农业对单一物种或是有限物种的集约性生产,其实质就是对其他可能的竞争性生物进行压制。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人们不计生态后果,不加区别地广泛施用各种化学除草剂和杀虫剂,将大量的化肥、农药撒向山林、平原,造成土壤与耕地的严重污染。各种化学农药以其特有的渗透力、破坏力、杀伤力,在向农作物病虫害宣战的同时,也给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链”留下了长久的隐患。导致人们今天的日常饮食中,许多食品中都残留有超标的有毒有害物质。化肥、农药对生态食物链的破坏,还表现为农业排灌用水的污染,这种污染直接殃及区域内江河湖海的其他水生生物,造成这些物种的大量死亡或变种。为了拥有永久性的平坦耕地,精耕农业可以毁林开荒,甚或围垦草原以扩大耕地面积;为了消除飘忽不定的降雨和干旱对作物生长的影响,精耕农业可以兴修水利,甚或改变河渠的流向,使其实现对耕地的充分灌溉;为了提高种植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可以优化作物的品种,进行人工施肥,并以多种手段控制杂草和病害,如此等等。由于精耕农业基本上重新安排了生态系统,因此农耕民众也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以保持这种人工打造的生态平衡。目前,在北方一些区域,精耕农业正在向集约化、产业化、现代化转变,这种转变的突出特征即是推广化肥、农药、塑料薄膜、机械、水肥耗量大的高产品种以及连作的方法,同时,一些相应的农业工程设施也在改变着自然。
林业生产也是如此。在北方一些地区的现代人工林营造中,人们将自己不需要的正处于生长阶段的其他树种和植被清除,阻止植物的腐烂和养料循环,清理树根下的杂草落叶、倒折的树木、残干和下层林木,使用各种杀虫剂和化学肥料。单一性的人工用材林确乎生长起来了,但是由于改变或中断了自然的生态系统演替,人工森林生态系统大大简化,造成生态系统极其脆弱,不仅难以抵御各种病虫害的侵袭,并且对人类的生存环境也构成种种隐患。
再如,在北方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一些较偏远的乡村,虽然目前尚未形成规模化的工业生产,因而还没有出现严重的工业污染。但由于受传统的生活陋习的影响,农村的生活垃圾与污水普遍处于随意丢弃和排放的状态,其对环境的污染也令人触目。以辽宁省新宾县腰站村为例,近年来有学者在当地调查中了解到,尽管当地没有工业,但生活垃圾对村内民众的生活已构成严重影响。平时,总有一些生活垃圾和建材废料堆积在公路旁和沿路的河流中。每当大雨过后,村前的河水浑浊上涨,许多污物在水面上翻腾漂流。一些村民反映,过去他们常在河里洗菜、洗衣,现在不仅不能洗菜,就连洗衣、洗脚也会引发皮肤过敏,水质已不再适合人、畜饮用。据了解,这是过多使用农药、化肥所导致的水污染。沿河的村子里的村民习惯于在河水中清洗有残余农药、化肥之类等有害物质的生产工具,日积月累,河水中有害的化学物质含量升高超标。同时,村民日常生活中对洗衣粉、洗涤剂、杀虫药等化工产品的使用量日益增多;常有过路的机动车和本村的农用机车在河里进行清洗;农家院前的水沟也成了洗东西、倒垃圾、排粪便的场所,而这些污水都辗转注入河中……据当地人讲,以前村前的河下雨涨水时,常有一二斤重的大鱼涌上来,若再回溯这个山村的村史,当年满族先民喜塔拉氏在此地是以打鱼为生计的,“喜塔拉”的汉语之意便是“结渔网的地方”,可见当年水肥鱼美之景况。然而如今由于污染严重,河水中早已不见一二斤重的大鱼,平时只有一寸左右的小鱼在河沙里钻来钻去。不仅鱼类减少,村里人已经不能在河里洗澡,有人在河里洗澡后都患上了皮肤病。①张晓琼、何晓芳主编:《满族·辽宁省新宾县腰站村调查》,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3页。不难想象,在北方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变革过程中,如果不考虑上述种种“生态暴力”对区域生境造成的负面影响,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区域内的各种生态灾难还将加深加重。
毋庸置疑,当今社会迫切需要重建生态文明。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近年来,许多与生态修复有关的新思维与新观念开始进入全球化语境,地方性知识便以一种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价值观,成为21世纪人类文明建构的重要取向。
目前,在奔向现代化的一路高歌猛进之后,我国社会已开始逐渐步入理性的发展阶段,近年来,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开始弥漫着一种文化上的返璞归真、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对民族与地方性知识进行重新审视和价值重新评估的后现代思潮。在北方区域,打造和构建“绿色农业”、“生态林业”的呼声日益高涨。“绿色农业”虽然仍以轮作、有机肥等传统农业习俗为基本,但却并非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充分应用现代农业工程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以及现代科学养殖方法,是一种可持续农业。“生态林业”则是摒弃“吃山吃到光,吃水吃到干”的思想,立足于山林的自然养育与修复,实行诸如林下参的栽培、林蛙的放养,种植花卉和各种苗木等带有生态技术性质的生计,不仅保护山林植被、水土,也为人类带来收益,实现人与自然的“双赢”。目前,这种生态经济已然成为北方区域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绿色农业”与“生态林业”的实施,从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代“生态暴力”对区域生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彰显出当代北方民众对其持有的地方性知识价值观的某种重拾与提升。
从北方民众的地方性知识之于当下的价值来看,其不仅是北方民族文化传统的再现,其中甚至还隐含着某种超越工业化、现代化的胚芽。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呼应与联系,就在于地方性知识具有的独特性、传统性和文化性,在于其中涵盖了一个特定的人类群体千百年的生存经验和智慧。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区域性与民族性文化,具有某种顽强的生命力,虽然它与现代化的模式有着某些距离,但在许多方面却和后现代的思考和理论有着可以呼应的地方。我们说,任何一个民族或群体的发展都必须有其内在的动力,这种内在的动力除了生存繁衍的基本需求动力之外,还有要求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是由该民族或群体的文化所提供的,而文化的核心则在于一些基本的价值取向、理想信仰和与此相适应的行为模式。地方性知识凝聚着不同人类群体世世代代对所处区域生态资源的配置、利用和维护中积累起来的生存智慧,与现代普适性知识相比较,这种知识与智慧对特定群体的生存与发展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地方性知识的多样性必然导致资源利用的多样化,如此将有利于分散人类社会利用地球资源的压力,实现对地球生态的维护。从本质上看,不同民族与区域群体的地方性知识是对主流知识体系的补充,它既能满足不同民族与群体根源性认同的需要,又是该群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同时也能为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存在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多样性的地方性知识体系蕴涵着不同人类群体发展的动力,也是使人类文化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重要缘由。在全球化的资源博弈中,地方性知识可以转化为其参与全球化资源博弈的文化资本,因而也是各民族探求多样性发展道路和现实生存方式的立足点之一。②参见邓正来:《生存性智慧”与中国模式——在比利时根特大学的讲演》,《文汇报》2011年7月19日。
对地方性知识价值的重新审视,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本质意义。在时代转折、文化转型的关头,各种地方性知识和生存性智慧应该也可以成为人类社会在21世纪进行文化创造的重要滋养与精神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