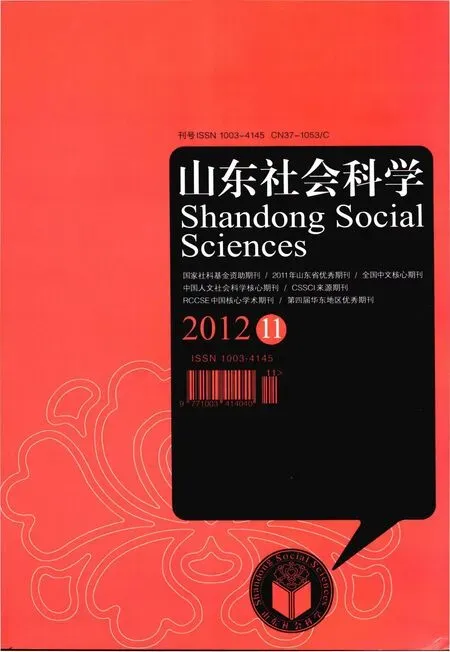权力转移理论视角下的东亚区域安全架构变迁分析
王 敏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一、权力转移理论与安全关系的分析
权力转移理论是上世纪50年代执教于美国密执安大学的奥根斯基教授(A·F·K·Organski)提出来的。“权力转移”是指由于世界政治中国家实力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原有的主导性大国地位下降而后崛起的大国地位上升并获得主导性大国地位的权力变化过程。②权力转移理论是基于权力政治发展而成的,其对权力的分析是整个理论大厦的内核。权力变迁意味着对原有的各种权力资源配置重新进行排列和组合,调整各个行为主体间的关系,进而带动整个政治安全格局的变更。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单纯性、绝对性的权力对于格局的调整与变更并不具备实际意义,只有当权力的变迁导致权力出现相对性大于绝对性时,权力的变迁才有现实意义。权力转移理论秉承了新现实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假设,认同权力的相对性是决定行为体在结构中地位的重要指标,这一相对性在现实权力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权力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在国际或者地区格局中,权力的变迁与安全密切相关。权力是实现安全的有效手段,所以权力的变迁伴随着安全感的消长、安全问题的产生、安全关系的调整、安全格局的变更,是直接导致国家对外安全政策和战略发生变化的决定性要素。在现实政治中,安全的稀缺性是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常态,各个行为体都在增强自我安全感,竭力弱化威胁或者增强自己应对威胁的能力,保证在体系中处于相对的权力优势地位,这种方式使得行为体之间往往以敌对者或者竞争者身份去界定彼此,“安全困境”由此产生。为了增强自身的权力,保证自己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一国往往采用增强军备、加强同盟、分化潜在威胁对象国等打压方式强化自身权力,这种做法会被其他国家视为威胁,进而导致安全困境的产生。
权力的变迁必然导致安全关系的调整。权力转移理论在论及此问题时,没有直接提及权力与安全的关系,而是将权力转移与国际(地区)秩序作了直接的链接。认为权力的变迁将导致权力要素的重新流动和配置,进而撼动国际(地区)秩序,使之进行符合现实权力态势的变革。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国际(地区)秩序的变化是通过一系列具体过程和事件体现出来的,安全关系的变更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力变迁促使安全关系大幅度调整的情形在世界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有时以极端形式如烈度较强的局部战争或者世界大战来完成,有时以和平过渡的形式完成。奥根斯基的贡献在于,他看到权力变迁作用于安全关系的调整方式存在多种可能性,以超前的理论眼光预设了基于权力转移带来的国际(地区)秩序的调整和安全关系的变迁存在以和平方式完成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是权力转移理论有别于(新)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特征。
二、美国对东亚区域权力转移的应对:“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
在后冷战时代,由于仍然主要依赖其在冷战期间构建的安全体系——军事同盟和前沿军事部署,美国对地区新安全议程的反应不是那么及时有效。传统盟国更加注重寻求自身的安全利益,而不是一味地服从华盛顿的意志。针对这一态势以及中国崛起形成的强大地区冲击力,奥巴马政府高调“重返东亚”,强调东亚安全在美国整体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
2010年5月27日,奥巴马政府公布了四年一度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是一份国际社会期待已久的美国政府文件,涵盖了美国政府外交、安全、防务等多项内容。这一报告首先对威胁的评估进行了实质性调整。报告取消了“先发制人战略”,突出强调通过合作、全球均衡发展和增强美国经济实力来保持或者强化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这一主旨。美国国家安全目标的战略优先考虑是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和繁荣,实质性地降低因经济秩序崩溃带来的不安全影响,取代了之前美国延续多年的推进全球民主的政治热情。报告尤其强调将保存和发展美国的经济竞争力——这是美国实力和影响力的基础。报告强调要形成一个“所有的国家都享有相关权利、并能承担相应责任的国际体系”,其他国家要与美国一起分担国际责任。
奥巴马政府从军事、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多方面利用地区政治中的“中国因素”来巩固美国在亚洲政治和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战略有三大核心内容:进一步增强对东亚外交与战略的关注,力争全面改善与地区内国家的外交关系;在东亚地区安全战略中重新定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突出美国在应对新兴经济体崛起挑战时保卫盟国的战略性承诺和义务;建设美国主导下的东亚地区安全架构,在确保美国担任地区安全“保证者”的同时,按美国的标准和需要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避免任何排斥美国的东亚共同体建设框架或机制,重申美国在东亚不可或缺的融入性角色和定位。美国意图在安全和经济两条战线上把握东亚区域政治发展的主导权,维持区域内国家对美国的战略信心和同盟依赖,宣誓美国牵制中国崛起的决心,削弱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的消极周边地区效应。
2012年1月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国防部长帕内塔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在五角大楼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题为《可持续的美国全球领导:21世纪国防战略重点》的美军战略利益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显示美国国防战略重点发生了转移,相应的全球战略部署也作了调整:第一,建议放弃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战略原则,改而要求美军只需具备在一场大规模常规战中作战的能力,同时在另一场可能突发的冲突中发挥“干扰破坏”潜在敌人的作用,被称为美国新的“1+”战略。该报告建议美军从欧洲再撤出一个陆军作战旅,只在欧洲大陆保留两个旅的驻军。第二,调整经济发展与国防开支之间的关系。美国是世界上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目前美国经济的困境与其动辄滥用武力密切相关。2012年是美国大选年,经济状况直接关乎奥巴马政府的政治命运。有效解决国内经济发展、医疗体制改革和就业等民生问题,日渐成为考验政府合法性的关键指标。在此背景下,奥巴马一方面不得不尽快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对已造成沉重负担的军费开支进行削减,①美 国国防部要求2013财年的国防预算为6130亿美元,这是继“9·11”时间以后美国国防预算的首次下降。今后10年内,美国将削减487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进而对美国全球军事战略作出新的调整。第三,新战略聚焦亚太地区。美国新的军事战略将重新致力于亚太地区军事安全,明确亚太地区将是美国安全战略中心,在逐步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美国正处于一个转折点,美国需与亚太地区盟国和伙伴建立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安全关系。
三、权力转移视角下东亚区域安全关系的调整与变化
(一)美日、美韩军事同盟的升级
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不断加强与日、韩、澳等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克林顿政府在1995年和1998年发表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了“以双边同盟为美国地区安全战略基础”的原则,②刘昌明:《地区主义对东亚双边同盟体系的挑战及美国的应对战略》,《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布什政府期间提出建立美、日、韩、澳“四国安全磋商机制”,以对付亚太地区的“潜在威胁”。美国一直试图把已建立的双边军事同盟逐步整合为多边军事联盟体,从而在亚太地区建立强大的军事联盟集团。“9·11”事件后,美国为了争取日本对其反恐战争的支持,公开鼓动日本“借船出海”,日本自卫队的角色完成了从本土防御到保卫周边地区再到向海外派兵的转变。2011年10月,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与到访的美国国防部部长帕内塔举行了会谈,就安全领域深化日美同盟达成一致。日本表示“日美同盟的根基在安全问题,日方愿同美方保持密切合作,力图提高防卫能力”。他同时提到“东日本大地震让我更加坚信,日美同盟是我国外交与安全的基轴”,帕内塔回应称,“日美两国50年以上的同盟关系才是保障太平洋地区安全的基础所在”,确认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①资料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 -10/28/c_122200040.htm.韩国李明博政府上台后,全面推进美韩军事同盟,韩国军方在2010年1月作出了重新评估加入美日导弹防御体系的决定。“天安舰”事件发生后,日韩防卫合作迅速升温。2011年12月17日金正日去世后,美日韩三国迅速进行协调,在军事方面作了充分的动员和预警,统一协调立场和方案,体现了美日韩三国同盟在面对重大危机事件时的牢不可摧。美日韩三国密切合作应对朝鲜前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去世后的局势及核问题,并于2012年1月在华盛顿举行了三方会谈,就朝鲜半岛局势、缅甸局势以及其他涉及共同利益的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进行磋商。
(二)美国——印度关系的发展
冷战期间,美印关系整体上处于一种比较冷淡的状态。冷战结束后,由于缺少了苏联这个制约因素,两国关系开始逐渐改善。奥巴马政府稳步推进美印之间各项关系,尤其是在防务合作方面。2009年10月印度和美国举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陆军联合演习。这次演习表明美国和印度之间已经把对方当作一个实质性的军事合作伙伴。2010年6月美国与印度的首次战略对话在华盛顿举行。两国在联合声明中承诺,将寻求在美印间建立起“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声明美印之间不仅有“共同利益”而且有“共同的价值观”,“美印关系将成为21世纪决定性的伙伴关系”,②资料来源:http://www.gmw.cn/content/2010 -06/08/content_1145248.htm.美国声明坚决支持印度的崛起,未来印度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美国主导的国际事务中。美国和印度提升双边关系是奥巴马上台之后与新兴大国合作趋向的重要体现,也是印度方面积极谋求参与国际事务的举措,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2011年12月,美国、日本、印度政府在华盛顿举行了首次三边对话,议题虽有意模糊指向“有共同利益的地区与全球性问题”,但《华尔街日报》一语挑明:“中国是三方未说出的潜台词”。此举似乎有意对在东海、南海及印度洋扩大影响力的中国形成制约或打压,美日印首次三边对话意欲打压中国在亚太影响力。长久以来,日本和美国一直在敦促印度举行三边会谈,并不断向印度施加影响,称印度为“亚太地区一个长期、坚定的盟友”。美日印三国有意定期轮流主办三方会谈,甚至考虑今后将会谈升级为部长级会谈。③资料来源:http://mil.news.sina.com.cn/2011 -12 -21/1050678172.html.五角大楼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显示,随着印美军事关系日益密切,两国联合军事演习也明显增加,其中2011年就有56次合作,比印度与其他任何国家之间的军演都多。除军事演习之外,美印还定期举行双边海军参谋人员交流,加强各级军官的往来,美印之间防务关系纽带日益紧密。
(三)日本——印度关系的变化和发展
日本和印度之间的防务合作稳步进行,他们的目标都是防止在本地区出现唯一的地区主导国家。④Joshy M.Pau:l“Emerging Power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Asia”,RSIS Working Paper,20 December,2010,P.3.2000年印度与日本建立全球伙伴关系。2004年起印度成为日本最大海外开发援助对象国。2005年3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印度,两国发表了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旨在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10月印度总理辛格访日,继而印日发表了《印日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和《印日全球战略伙伴关系进展联合宣言》。由于日印同是构建亚洲地区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加之日印关系在近年出现了异乎寻常的亲密,日印双边关系在短时间内取得飞速发展,其原因在于日印之间不存在领土争端等任何战略性矛盾冲突,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合作已经逐渐升格为日印双边关系的主旋律,推动了双边安全防务关系的发展。2012年6月,在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激烈摩擦之际,日本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在日本神奈川县举行了首次联合军演。
印度与日本之间的防务合作是在地区层面制衡中国的组成部分之一,这种合作关系被看做是亚洲安全构架牢固基础的催化剂。⑤Joshy M.Paul:“Emerging Power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Asia”,RSIS Working Paper,20 December,2010,P.19.戴维·康(David Kang)认为中国崛起能带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则认为同属新兴国家的印度从未从属于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印度在寻求制衡中国。⑥Amitav Acharya,"Will Asia's Past Be Its futur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8,No.3,2003/04,P.150.虽然这两个国家对于通过公开的军事联盟反对中国持谨慎态度,但是他们认为强有力的防务合作能够阻止中国强势崛起。
(四)美日澳三边安全对话与日澳军事防务关系
2001年7月美澳两国防长举行会晤,提出建立美、澳、日、韩“四国安全磋商机制”,以应对“地区潜在威胁”。①李学江、黄山:《美在中国边上拉联盟》,《环球时报》2001年8月7日第8版。在美国的支持下,2007年3月,日澳两国签署了《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宣称将在涉及共同战略利益的事务上加强合作与磋商,从而标志着以美国为核心的亚太地区三方安全同盟的形成。②信强:《东亚一体化与美国的战略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 期,第51页。2011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澳大利亚,宣布自2012年起5年内向澳大利亚增兵2500人。澳大利亚和日本的防务合作也得到了新的提升和增强。2010年5月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了《日澳相互使用军事设施的防卫合作协议》,这是继2007年《日澳加强安全合作协定》签署以来日本与澳大利亚防卫合作的新进展。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曾主动提出要求美国加强针对中国的“军事准备”。③Reuters,“Kevin Rudd Fires Back the U.S.over Wikileaks:It’s Your Fault,”Sydney Morning Herald,December 8,2010.2011年4月澳总理吉拉德访日,表示将在安保领域“加强同日本和美国联合的意向”。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自2007年起开始进行联合海上军演,三国的海上联合军演都在日本九州西方与冲绳海域。2011年7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宣布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文莱海域举行首次联合军演。④资料来源: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southchinasea/pages/southchinasea110709.shtml.2012年2月美日澳在关岛进行联合军演,这是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与美澳举行联合军演。2012年5月澳大利亚与日本签署了“情报保护协定”,以确保日澳两国在共享安全保障相关情报时不会泄露情报,该协定的签署旨在强化美日澳三国在安保领域的协作。
四、权力转移对地区安全架构的影响
(一)主导性大国战略姿态的调整
权力的变迁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相关各方战略的调整和重新部署,主导性大国战略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地区安全格局。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与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中美两国在地区性问题乃至全球性问题上的战略姿态作了相应的调整。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逐渐从地区性大国成长为地区性强国。中国的崛起带来了国际社会多种不同声音,中国威胁论一时甚嚣尘上。
权力政治的平衡与中国的崛起成为国际安全领域的热门话题。现实主义者一致认同传统大国会主动平衡一个新兴大国的军事力量,但是关于中等国家会作出何种反应却不存在一致的观点。经典现实主义理论认为中等国家的反应视具体环境而定,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除了个别实力极其弱小的国家外,大部分国家都会采取平衡战略。面对中国崛起的现实,美国必然会重新调整其全球战略。美国虽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东亚国家,却与东亚的地缘政治密切相关。东亚是美国霸权的支点之一,在欧亚战略的平衡上美国一度将欧洲确定为全球战略的重点,与欧洲形成巩固的盟约关系。新世纪以来,美国的战略重心由大西洋区域转移至亚太区域,东亚的重要性对美国战略部署的意义越来越凸显。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布局以双边安全合作为主要模式,同时辅以经济多边主义,而且强调安全双边主义与经济多边主义的相辅相成。⑤Ralph A.Cossa,“US Approaches to Multilater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 the Asia - Pacific”,in Foot Rosemary et al.,US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193.美国高调重返东亚是其最近一次战略调整的结果。这次战略的调整不仅是美国一国的变动,更重要的是美国与其亚洲盟友之间的关系的重新组合,这是关系东亚安全态势的核心因素。
(二)安全与防务关系的新变化
权力变迁带来的战略调整会带来安全和防务关系的新变化。二战后,美国的整体实力如日中天,随着世界进入冷战状态,两极格局形成。为了应对当时美苏为首的两个阵营的竞争,美国在1951年与日本签订《日美安全条约》,将日本纳入美国的遏制战略的轨道,并且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反对苏联的战略堡垒和军事基地。1954年签订的《美日共同防御援助协定》把日本涵盖到美国的远东安全保障机制内,自此美日之间的特殊关系正式确立。1953年美国与韩国签订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把韩国纳入其东北亚安全事态的保护伞下。美日、美韩结盟双方互有所需,双方均获益。美国取得在日韩的驻军权从而形成包围中、苏的战略态势,日韩则利用美国的安全保护,放手发展经济,取得了经济的迅速繁荣。1950年美国与泰国签订《美泰军事援助协定》、1951年与菲律宾签订《美菲共同防务条约》,在菲建立军事基地。1951年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美澳新安全条约》结成联盟,在西南太平洋建立牢固的战略后方,构成其东亚安全防务体系的外围。美国在东亚军事联盟体系的建立标志着美国霸权在东亚布局的初步完成。
随着冷战的结束、日韩经济的迅速发展,美国与日本的同盟防务关系逐渐向类似平等的伙伴关系发展,日本在东亚有与美国争夺地区主导权的意图,不再满足安全防务关系上的附属地位,不断向政治大国的目标迈进,这引起美国的警觉。同时,天安舰事件发生后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与日本的军演、与越南的联合军演等一浪接一浪,规模一次比一次大,航空母舰在太平洋游来游去,美国的军费开支几近天文数字,但在军事上仍然入不敷出。①资料来源: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3/forum_us101201b.shtml.美国的东亚安全防务需要其支付的成本越来越高,这是自冷战后美国在安全防务领域面临的最大考验。美国是否能有效地把日韩等盟友牢固捆绑在其东亚战车上,是否能让其忠实的盟友继续为美国的全球战略买单仍是一个未知数。②按 照 陆博彬的观点,韩国对中国崛起持接纳的态度,体现之一是首尔不愿在冷战后继续与美国的防务合作。韩国总统卢武铉(Roh Moo-hyun)宣布美军在干涉台海冲突时不能使用韩国的基地,美韩一直未能就美军在应对区域紧急事态使用驻韩美军基地达成一致。韩国防部长尹光雄(Yoon Kwang-ung)提出,韩国将减少对韩美联盟的依赖,加强与俄国和中国的合作,在东北亚地区扮演平衡者的角色。
(三)中等国家安全选择决策的调整
权力变迁对中等国家而言,意味着安全战略的重新选择或称“选边站”。对那些不具备大国实力的国家来说,它们对一个新兴大国将采取何种政策,主要取决于传统大国的政策及新兴大国的崛起对其周边实力均衡的影响。③[美]威廉·W·凯勒、托马斯·G·罗斯基编:《中国的崛起与亚洲的势力均衡》,刘江译,朱锋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页。中国周边的部分中小国家担心中国崛起后会实行强制性的和扩张性的政策,因此要么转而利用美国因素,要么增强自己的军费和防务开支,要么争取与中国有对抗关系的大国加强合作来牵制和防范中国。最近几年这种趋势在不断发展。澳大利亚2009年3月通过了新的国防白皮书,宣布将在未来20年增加军费760亿美元,采购新的F35战斗机、大型水面作战舰只和增购新的潜艇来应对“中国威胁”。澳大利亚和日本的防务合作也得到了新的提升和增强。韩国不仅推迟了原定2012年转交的美国在战时对美韩同盟的军事指挥权,还进一步宣布了新的军事发展计划,并正在积极考虑加入美国主导的东亚战区导弹防御系统。④有 关 亚洲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反应的分析,请参见:Sumit Ganguly,Andrew Scobell,and Joseph Chinyong Liow,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Asian Security Studies,London:Routledge,2010;Evan S.Medeiros,etc.,Pacific Currents:The Responses of U.S.Alliance and Security Partners in East Asia to China’s Rise,Santa Monica:Rand Corporation,2008.
日本是美国冷战遏制的关键支撑因素,东南亚则成为美国在远东最重要的战略支点和军事上的必争目标。⑤胡德坤:《美国东亚遏制战略与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世界历史》2002年第5期,第35-42页。2002年,印度尼西亚恢复了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会谈,并购买了许多美制武器装备;马来西亚也在不断强化与美国的防务合作,配合美军进行作战军演,提供港口供美航母停靠。新加坡和菲律宾是与美军合作最积极的国家,合作的领域包括提供港口、配合军事计划、签订军售合同等内容。新加坡国防部长说:“新加坡公开承认美国的军事存在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正是为此,新加坡才为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提供便利。”新加坡在2005年与美国签订了《新美战略框架协议》,强化了两国之间的防务和安全关系。菲律宾与美国在1999年签署《访问部队协定》,在2003—2004年度美军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军事演习次数增加一倍,在菲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地区联合军演,菲律宾成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非北约主要盟国”。
印度不得不继续在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争取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以及渴望在国际地位上不被中国压倒之间求得平衡。除非中国变得令人厌恶和恐惧,印度将很可能努力继续现在的做法,让美国和中国相互制衡,把制衡中国的主要经济和政治成本转嫁给美国。⑥陈琪、刘丰主编:《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中等国家的结盟政策并不由特殊的历史因素或者共同的文化特征来决定,而是由那些跨文化的、不随时间而改变的决定外交政策选择的因素所决定。⑦[美]威廉·W·凯勒、托马斯·G·罗斯基 编 :《中国的崛起与亚洲的势力均衡》,刘江译,朱锋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页。2010年以来,围绕着“南中国海”是否被中国宣布为“核心利益”的问题,部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发生急剧变化。越南正在通过加强美越军事合作、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甚至考虑开放金兰湾军港,引进“大国因素”来对抗中国和强化所谓越南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权争议。新加坡国防部长张志贤在2010年亚洲安全“香格里拉对话”上,大谈所谓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区域安全的不确定因素,反应了东盟国家在安全态势变化后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