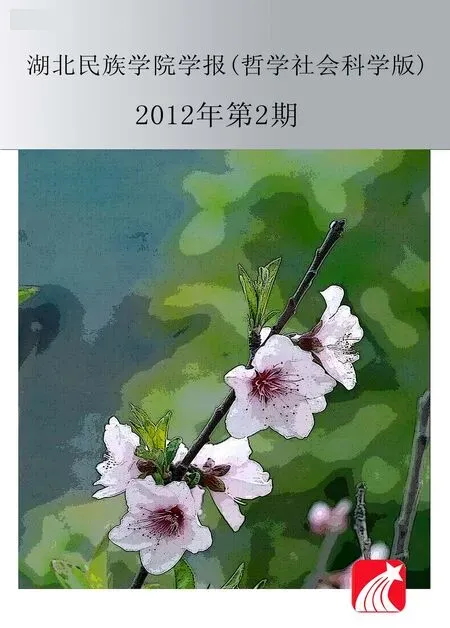土家族跳丧中的“丑歌子”现象
陈湘锋,吴 茜
(湖北民族学院 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湖北 恩施 445000)
跳丧,又叫“撒尔嗬”、“撒叶儿嗬”等,是土家民俗中最负盛名的文化经典之一,流行于鄂西南清江流域中段的山水之间,与流行于酉水上中游的摆手舞被称为“南摆手,北跳丧”。民间文艺、民俗活动中冒出一些“荤歌”、“黄段子”,本不足怪。但是,在沉痛肃穆的丧葬活动中,特别在跳丧这种只为寿终正寝的老者举行的庄重的丧事仪式中,竟能容忍甚至欣赏频频出现的“丑歌子”,却极为罕见,值得探究。
一、“丑歌子”的界定
2000年11月17日,笔者与宜昌群众艺术馆的白晓萍研究员为考察跳丧来到巴东县杨柳池镇。在得到准信后,我们前往离镇几里的杨家村4组的圆大包。刚近主家坎下,就听喇叭里传出广播:“各位村民都注意哒,今天有远道来的客人、湖北民院的教授来采访,大家都要文明点,遵守秩序。”打过招呼,主事人又对身边的人嘱咐:“叫他们都文明点,莫尽唱些丑歌子。”我和白教授相视一笑,连忙解释:“你们平时怎么唱就怎么唱,莫要顾虑,我们就希望看原汁原味的‘撒尔嗬’。”
事主是80岁的老汉谭运南,亡人是他的老伴覃桂香,77岁。村民们说的“丑歌子”出现在后半夜。此时堂屋里的人突然增多,观者如堵。跳丧中有一种段子叫“打哑谜子”,即兴随意,“丑歌”、“丑语”层出不穷。如歌师“两个大闺女睡一床——两河(合)口”一出口,围观的小伙们就会发出狂欢般的爆笑,你推我搡,乐不可支。①就连大闺女、小媳妇都不掩饰自己会意的笑声。
从形式上看,“打哑谜子”是一种文字游戏:谜面与谜底构成一段歇后语,如上例“两个大闺女睡一床——两合口”,而谜底则双关一个地名“两河口”。演唱时,一句歇后语加上若干句衬词,构成一问一荅的一段盘歌:
哑子哑谜子嗬,
哑子哑谜子嗬。
两个大闺女睡一床怎么说?
打个哑谜子嗬。
哑子哑谜子嗬,
哑子哑谜子嗬。
两个大闺女睡一床是两合(河)口,
跳个撒尔嗬。
除了“打哑谜子”外,“丑歌子”还出现在跳丧的其他唱词形式中。跳丧唱词名目繁多,有的相对固定,如历史演义,野史传说,孝道伦理、亡人生平等;有的则随意即兴,其中包含大量的情歌、风流歌、荤歌。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在这里将这三种唱词作如下界定:情歌指纯粹的爱情歌曲,风流歌指正式婚姻之外的私情之歌,荤歌指直接表现性意识、性行为的歌曲。
情歌。在丧葬仪式中大唱姐呀、郎呀、妹呀、哥呀的情恋之歌,似乎场合不对,气氛不对,因此它们被当地老乡列入“丑歌子”的范围。其实,这些“丑歌子”并不“丑”,它们“发乎情,止乎礼义”,并不具有“丑”的内容。因此,本文不将它们列入“丑歌子”的讨论范围。
风流歌。这类“丑歌子”主要表现婚外的风流韵事,即民间所谓的偷情。偷情歌常有长篇组诗,但它们对文化背景往往缺乏必要的交待,因此很难确定它们的思想意义。偷情歌往往用欣赏的态度表现主人公对这类畸形恋情的复杂心态。如:“远望姐儿身穿黄,手上戒指排成行。一不是娘家陪嫁你,二不是婆家攒私房,一个戒子一个郎。”
荤歌。跳丧中的荤歌是指直接表现性爱活动的唱词。性爱活动有两个层次:其一为一般性的性爱表现,如接吻、拥抱、裸露、挑逗等;其二为露骨性行为的具体展示。跳丧荤歌的内容多为前者,而后者的内容往往点到为止,或含糊其辞。影视作品中的色情片,有所谓“软心”、“硬心”之分。软心片在表现性行为时,比较注意情节因素,并赋予一点感情色彩。硬心片则基本为赤裸裸的性展示。跳丧中的荤歌大体亦可作如是观。有的写性是虚,写情是实:“想郎想郎真想郎,把郎画到枕头上。早晨起来亲个嘴,黑哒睡觉把郎摸,要你翻身压到我。”有的写情是虚,写性是实:“你的口水是我的蜂蜜糖,倒拐子弯弯是我的鸳鸯枕,手膀子就是我的枕鸳鸯。一对妈妈儿就是肉包子,罗裙就是红罗帐。悄悄话儿就是救命丸,你的身子就是象牙床。”
“丑歌子”由跳丧者自名其事,名字本身就反映出取名者的价值判断:“丑歌子”是丑的,难登大雅之堂。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丑歌子”的创作者、使用者和欣赏者,正是他们自己让“丑歌子”成为整个跳丧仪式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种矛盾的态度,折射出土家跳丧面临复杂的文化生态。
清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1],穿流在鄂西南的崇山峻岭之中。清江中段的两岸,正是跳丧的发源地和传承区。这片神奇的土地,东临富饶的江汉平原,西望文化重镇恩施古城,是东西部文化交流的天然通道,因此很难完全阻隔主流儒教文化的影响。
恩施老城有一座文昌祠,祠内有一块《袁了凡先生遏淫碑》。袁了凡、名袁黄,字申仪,明代吴江人。万历十四年进士,曾任兵部主事。其人博学好奇,律己甚严,日纪所行善恶,著述颇丰。清嘉庆年间,恩施郡一批官员名流将袁了凡先生的“遏淫说”书刻于石,立碑于文昌祠。碑文洋洋二千字,痛批男女之间的种种秽行恶习,呼吁救拔淫迷,遏止淫风,并提出拯救世风的措施。文中不无偏见地宣称,“至若婢女仆妇,尤易行奷,人口以此为家常茶饭”,以至“丑声籍籍,污人听闻”[2]。
《遏淫碑》在土家族地区的出现表明,改土归流后,主流文化的代表者强力推行自己的价值观是多么地不遗余力。结果,我们看到,跳丧文化覆盖区的边缘地带,“丑歌子”少了,消失了。恩施新塘是跳丧文化覆盖区的西部边沿,距恩施城仅数十公里。新塘的歌师傅就说,跳丧是祭亡人,唱情歌不正经,应该唱孝歌[3]。这种变化了的文化观念,继续传向跳丧文化的中心地区,如杨柳池、清太坪等地,人们跳丧时虽然还在唱“丑歌子”,但心里却像犯了什么错似的,于是就出现了前面我们谈到的矛盾的态度和心理。
二、“丑歌子”的功能
“丑歌子”之“丑”,就在于它涉“性”。但是,“食色性也”,“食”关乎个体生命的存活,“色”关于种群生命的延续,它们都是人类的自然本性,本无所谓美丑善恶。只是进入文明社会后,人的任何自然本性,都要接受文明规范的制约和导向,于是就出现了对于“性”的美丑善恶的道德判断。
任何文化的存在和演变,都有其适应生存环境的理由和原因,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跳丧中的“丑歌子”现象得以发生、发展并存活至今的原因,就在于它具有能够满足特定生存环境需求的特定功能。
(一)娱乐交际功能
娱乐中实现交际,交际中完成娱乐,“丑歌子”的这种复合性功能直接来源于跳丧本身。下面这位毛头小伙,“听到丧鼓响,脚板就发痒”,大概受到父母的阻拦,因此猴急起来:
半夜听到打丧鼓,
床上跳起二丈五。
胡穿衣来倒靸鞋,
爹妈骂我不成材。
我说人人都有父母在,
我去玩下儿就回来。
跳丧少则一两天,多则六七天,每晚的上半夜多唱些正经的内容,到了下半夜,“丑歌子”即开始大行其道。跳丧流行地区交通环境极其恶劣,前来参加丧礼的人们往往难以连夜返回。于是,如何打发漫漫长夜,就成了实际问题。上半夜还有流水席、牌席、烤火、聊天可供消遣。下半夜人们睏盹不堪,欲眠无处,跳丧中的“丑歌子”多在此时开场。听到这些搞笑的丑歌丑语,闻者精神为之一振,半夜来的疲惫一扫而光。这实在是土家人无奈而又充满智慧的安排。
跳丧的主场设在堂屋。停放于堂屋正里的寿棺已占去一定空间,加上围观的群众,留给跳丧者的舞台大概只是一个边长约2米的方形地面。舞者即在这有限的空间里,沿着边缘捉对而舞,故曰跳“升子底”。跳丧的主角是请来的歌师傅,歌师傅们往往极潇洒,他们引亢高歌,翩翩而舞,有的还耳架烟卷,口呷小酒,极尽显摆之能事。
堂屋里通常只能容纳一、二对舞者,跳的人多了,可随需延至门外的场坝,但仍得捉对而跳。此时,围观群中就会不断有人被推入舞池,于是,舞者之间的暗中较劲,舞者与围观者之间的语来言去、打情骂俏,有时是可以达到肆无忌惮地步的。请看下面这首由男人摸拟女人声口的男女对唱:
女:郎把眼睛眨两眨,
男:姐把眼睛梭两梭。
女:站开些啰,莫踏我的脚;
男:要拢来呀,看你怎么说。
女:伙计说是唱个闹灵歌,
男:我是奈不何。
合:还要闹几下,
撒尔嗬,撒尔嗬。
俗话说,巫师管生,道士管死,因此,土家人办丧事多请道士。但在跳丧文化圈,人们更倾向请跳丧班子来支撑丧事活动。跳丧的程序和仪式,远没有道士法事那么多的繁文缛礼,故极易吸引围观者的参与,形成群众性的娱乐交际活动,甚至是狂欢节。
(二)心理喧泄功能
二十七八打单身,
要与阎王把理评。
人家有妻还讨小,
我打单身一个人,
阎王做事不公平。
二十七八岁还没讨老婆,要讨个说法,评理的对象却不是月老,而是阎王,可见精神崩溃到连死的心思都有。
环境闭塞、交通艰难、社会不公平,给土家男女的心理带来诸多问题,如性的压抑、情的苦闷、婚姻的烦恼,等等。
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开创性地将心理研究的关注投向潜藏在人的意识之下的无意识,认为无意识是一股未被驯服的巨大能量,而它的基础和核心则是几乎支配着人的一切行为的性冲动。后来,弗洛伊德进一步提出“本我”、“自我”、“超我”的三重人格结构理论。简言之:“本我”指无意识的自然本能,它遵循“快乐原则”暗中支配着人的意识;“自我”指理智,即意识,它遵循“现实原则”时时压制着本能的原始冲动;“超我”指超越“自我”(理智)对“本我”(本能)的逆向施压,为本能、特别是性本能的释放,寻找新的可接受的出口和替代对象。
潘光旦先生在翻译霭理士《性心理学》时,引用了大量中国古代文献来注释书中的术语。其中一条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妇人年轻丧偶,誓不再嫁,寡居数十年,被誉为贞操不二的楷模。然有一事令人久惑不解,即长期以来,邻人总是在夜间听到寡妇屋里传出的笃笃声,彻夜不辍。后经好事者偷窥,终于水落石出。原来此妇每夜几乎通霄不眠,坐于床,将罐中铜板逐个数落到簸箕里。一轮数完,将铜板倒回空罐,从头再数。如此反复,直至天明。可见,寡妇是将长年累月独守空房的性苦闷、性冲动,转移到铜板上,转移到数铜板的动作上。
跳丧中的“丑歌子”,也是因各种复杂原因造成的性压抑、性苦闷得以排解的喧泄渠道和替代对象。关于性的心理问题,许多都存在于无意识的领域,因此,解决之道常常也呈现出无意识的状态。
(三)文化传承功能
首先,跳丧中的“丑歌子”传承着土家人豁达的生命观。
有一次,在跳唱“丑歌子”的间歇,我问一位年长的歌师傅:“唱这些丑歌子,会不会得罪棺木里的亡人?”歌师傅答道:“不会的,亡人也是人,也有活人的七情六欲,我们是在陪伴亡人快快活活走完最后一截路。”
我们都知道,跳丧反映出土家人面对生死积极达观的人生态度[4]。上述歌师傅的一番话也让我们明白,跳丧中的“丑歌子”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折射出的也是这种辨证豁达的生命观。
其次,跳丧中的“丑歌子”,传承着土家人成人礼的性启蒙。
与动物不同,人类的性爱活动不能仅靠本能的无师自通,还需要性知识、性经验的传承。下面诗中的“夯头姑”的表现,说明这种性启蒙的必要性:
砍柴莫砍枫香树,
捞姐不捞夯头姑。
逗一句来她不懂,
逗两句来喊她妈。
她不懂,喊她妈,
这回事情搞拐哒。
从民俗学的角度看,人生有四大仪礼,即诞辰礼、成人礼、婚礼和丧礼。其中成人礼要解决的问题是,即将成为社会正式成员的青年男女,如何应对社会身份的改变,以及性生理、性心理的变化。今天,包括土家族在内的许多民族的成人礼,已经淡化甚至消失,其内容往往转移到婚礼的某些环节中,其中包括长辈的提示,同辈的暗示等,有的地方甚至将春画、春囊、附有合欢图的小物件等压在箱底随女儿陪嫁。土家人则以其充满谐趣的“丑歌子”进行性的启蒙,可谓另辟蹊径。请看:
小小蜜蜂翅膀尖,
一飞飞到姐面前。
轻轻朝你射一箭,
你又痛来你又痒。
射一箭,你又痒,
又痛又痒又新鲜。
三、“丑歌子”的审美
美与丑,形若冰火,如何对丑进行美的解读?具体到本文议题,如何对“丑歌子”进行审美的关照?
美与丑是一对对立的概念。美的事物令人愉悦,丑的事物令人厌恶,在现实生活中,美丑两端,难以混同。丑的现象,如丑陋、卑劣、凶残、欺诈、愚昧、淫乱等,不可能让人产生愉悦的美感;反之,美的现象亦然。但是,生活中的丑一旦进入艺术的领域,情形就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艺术中的丑,不是现实的存在,而是的一种艺术的表现形态。欣赏者与这种艺术的丑之间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面对艺术中的丑,欣赏者生理和心理的反应,不会有面对生活中的丑那样程度的厌恶、紧张和抗拒。这样,艺术中的丑与生活中的丑被拉开了距离,从而为对丑的审美关照创造了条件。
法国艺术家罗丹有一件雕塑作品,叫《欧米哀尔》,刻画的是一位年老色衰的妓女。她肌肉萎缩,皱纹密布,面容憔悴,神情哀伤。在这里,艺术家表现的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不堪的时候的最不堪的形象。可是,正是这丑陋不堪的形象,却让观众流连忘返,惊叹:“啊,丑得如此精美!”
可见,艺术的形式对艺术的内容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力。好的艺术形式,可令并不美甚至丑的对象进入审美的关照,使生活中的丑转化为美的艺术之丑。[5]
下面,我们从诗情、诗艺、诗体三方面谈谈对跳丧中“丑歌子”的审美关照。
(一)诗情之美
“丑歌子”的歌词,有的取自传承的民歌,有的根据需要即兴现编。或选或编,很少考虑所谓的思想意义和文化价值,只要能搞笑、逗乐就行。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些“丑歌子”毫无审美关照的可能。“丑歌子”大多为风流不羁的言情之歌,却极少见玩弄感情、游戏婚姻的作品。即使其中表现非正常婚恋状态的作品,也往往透出令人动容的娓娓真情。下面这首“丑歌子”,从一个不可多见的角度写女主人公偷情时的心理,既有令人羞于启齿的低俗,亦有女性特有的细心和温情:
情哥说是今儿黑哒来,
我把挂起的腊肉煨一块。
他吃不得肥的吃精的,
吃不得精的喝一点汤——
免得玩耍时心里慌。
人人都有自己的隐私,古往今来,概莫能外。人人都有权保护自己的隐私,古往今来,只见容于当代。可在传统的土家族社会,却有这样一位勇敢而深情的女性,将心中的一角,永远留给一位婚外的情人。情人故去,仍痴心不改。这份挚着,是耶?非耶?
老鸦子喊来姐心焦,
情哥死哒信来了。
瞒着丈夫烧纸钱,
丈夫问起说还债。
烧纸钱,说还债,
箱子角里供灵牌。
沈从文的《边城》,写到了湘西茶峒码头的风俗人情。岸上的女人做着跑船男人的生意,有金钱交易,也有真情相许,一切都像面前流淌着的酉水一样,平静而自然。对此,沈先生在小说中有一段评述,可借鉴为我们对“丑歌子”中的真情之美的一种认知:
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谪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中人还更可信任。
(二)诗艺之美
跳丧中的“丑歌子”,属民间歌谣范畴,民间歌谣中那些容易激发即兴创作、搞笑逗乐情思的形式,如重章、叠句、叠字、双关、盘荅、猜射、歇后、巧喻等,均得以充分展示。但是,这不是说可以简单地用“俚俗粗放”概括“丑歌子”的艺术风貌。它们的无忌、率真以及强烈的表现欲,使不少“丑歌子”成为极具个性冲击力的艺术佳品。
一首诗,基本的艺术单位是意象。若干意象可以构成完整的意境,每个意象又可以成为诗中艺术表达的独立单位。意象是意和象的融合。意是思想感情,象是物象,包括自然物、社会物的具象。一首诗可以没有完整的意境,但决不能没有切合诗歌表情达意需要的意象的创造[6]。
意象创造的优劣,首先取决于对物象的选择和表现。如我们在前面引用的一首具有性启蒙意味的“丑歌子”,用蜂针刺蕊隐喻男女的交欢,充满谐趣,可谓“乐而不淫”。而另一些“丑歌子”却用钥匙开锁、鸡笼关鸡等来暗示性事,就显得低俗,令人生厌。意象创造的艺术水准,高低立辨。
意象创造的优劣,还取决于意和象的连接方式。这些方式有外化法、喻连法、映衬法、双关法等。其中外化、喻连两法在“丑歌子”中用得最多,最有特色。
挨姐坐来对姐说,
捡个棒棒戳姐脚。
戳一下,不做声;
戳两下,她就笑。
不做声,她就笑,
棒棒甩哒过手捞。
这里用的就是将内在的情思通过外在表情、动作、语言显示出来的外化法。情之初,女人羞涩点,男人胆小点,很正常。窗糊纸的捅破,还得试探。在这方面,爱情总能为少男少女们提供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本诗的细节提炼,让人忍俊不禁,亦可谓经典。
昨日与姐同过街,
郎卖簸箕姐卖筛。
郎卖簸箕簸两簸,
姐卖筛子筛两筛,
二人姻缘团拢来。
末句是全诗的意旨,“诗眼”就落在“团”字上。彰显这个意旨的,是一组双层设喻:第一层,用器具的圆形,喻示“团”的心愿;第二层,用操作轨跡的圆形,喻示“团”的性动作和姻缘诉求。这一对取材于男女主人公自己劳动生活的意象创造,平凡而不落俗套,通俗而不失精巧,让人耳目一新。
(三)诗体之美
跳丧中“丑歌子”的诗体五花八门,但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所谓的“五句子”歌。
早在秦汉时期,五句体诗就已见录于史籍。后来李白、杜甫等大诗人也都偶有所作。但它一直处于佳篇乏呈、热不起来的局面,这是什么原因?
我国自古就有阴阳二分的宇宙观,加上汉语是一种整齐的音节语言,因此汉语诗歌的正格就成了上下句两两相对的偶句体式,而奇句体式如三句体、五句体,则不易为人接受,故作之者寥寥,闻之者稀稀。
古代典型五句体的特征有三:五句成章,七言成句,单句(第3、5句)用韵。土家五句子歌对此皆有变通,但最具新意的变通发生在单句用韵和五句成章这两条老规范上。
单句用韵,除规定全诗韵脚的分配外,还习惯于前三句为一组,后两句为一组的韵律划分。这也是古五句体的通例,如杜甫《曲江三章章五句》的首章:“曲江萧条秋气高,菱荷枯折随风涛,游子空嗟垂二毛/白石素沙亦相荡,哀鸿独叫求其曹。”[7]
土家五句子歌却颠倒其序,变为前二后三,而且用韵灵活。如:“姐儿生得矮笃笃,一对妈子像称砣/白日挎起沿山跑,黑哒把给情哥摸,摸来摸去好快活。”此项变通,意义重大。它实际上是将原来嵌于诗中间的单句挪到了诗尾,而诗尾的单句正是五句子发挥其独特艺术功能的关键所在。
五句子歌常常将三、四句的句末三字,依次插入四、五句之间,形成拥有六句的五句子歌。新插入的部分只是简单的重复,并无新的内容,相当于衬词。如:
远望姐儿对门来,
胸对胸来怀对怀。
胸对胸来亲个嘴,
怀对怀来喊乖乖。
亲个嘴,喊乖乖,
快些快些怕人来。
这样重复的原因,在于延迟“抖包袱”的时间,增强“抖包袱”的效果。事实上,即使没有进行这样的重复,歌者也会在第五句亮底之前,加入一些衬词,如“撒尔嗬”等,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郦道元.水经注·夷水[M].时代文艺出片社,2002:278.
[2] 王晓宁.恩施自治州碑刻大观[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58.
[3] 田万振.土家族生死观绝唱——撒尔嗬[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101.
[4] 萧洪恩.土家族《撒尔嗬》的哲理思维初论[J].湖北民族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2):36.
[5] 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M].北京:新华书局,1992:191.
[6]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58.
[7]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