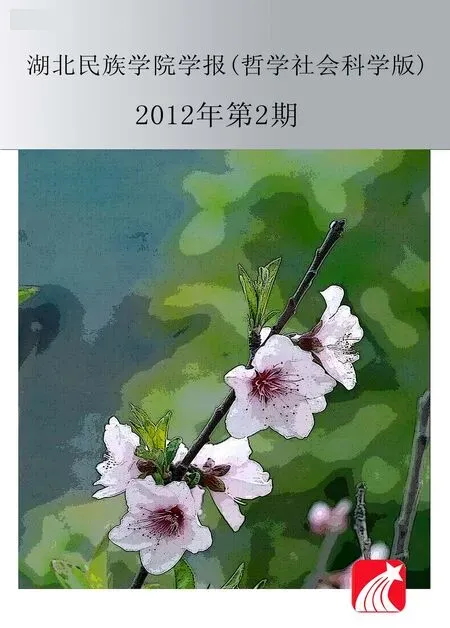何晓明与文化保守主义研究
周良发,祝义婷
(安徽大学 哲学系,安徽 合肥 230039)
文化保守主义,又称文化守成主义,是对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一种保守性的文化回应。这种回应不是一味地固守传统、不思革新,而是反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统天下。自19世纪60年代被卷入现代化潮流以来,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已经走过了近一个半世纪的历程。事实上,从中国现代化兴起之始,文化上的保守倾向与进步思潮之间就彰显出一股强大的张力,因而倍受知识分子的深情关切。当代著名学者,何晓明亦概莫例外,积极参与此论域的探讨与研究。二十多年来,他发表了十数篇学术论文,出版了《返本与开新——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新论》一书,周详深湛地剖析了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风貌,在海内外思想文化界产生强烈反响,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研究领域的大家。笔者怀着忐忑之心,拟对何晓明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成果作一系统的梳理、分析与评判,力图展示他对此问题的深切关注与卓越洞见。由于个人能力有限,粗疏浅薄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何晓明先生与学界专家批评指正。
一、对文化保守主义产生背景的历史钩沉
文化保守主义缘何兴起?虽不乏学者探稽考辨,但时至今日依然未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定论。在何晓明看来,文化保守主义的泛起不是根基肤浅、时髦一时的思想游戏,而是有着重大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思想背景。[1]321也就是说,文化保守主义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必然性。
(一)时代背景
作为一种文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是特定时代背景的必然现象。从历史上看,1500年是人类历史发展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水岭。1500年以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离的区域中;1500年以后,随着航海业的兴起、新大陆的发现,带动了欧洲商业和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各国陆续登场。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地区、民族的侵袭不止于掠夺原料、扩大市场,还试图从文化层面引领世界。不可否认,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代表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势与未来方向,但落后地区和民族的文明形态、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与之是格格不入的,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和野蛮行径产生一种本能的对抗与反驳,思想文化领域的保守主义思潮应运而生。
(二)历史必然性
何晓明指出,文化保守主义的泛起是现代化过程中异质文化相互碰撞、相互激荡的必然产物,也就是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出现具有历史必然性。在他看来,这种历史必然性可从三个层面略加评析:1.先进(现代化)国家、民族文化的对外扩张机制是文化保守主义必然产生的主要动因。2.后进国家、民族文化的传承机制是文化保守主义必然产生的反应因素。所谓传承机制,是指文化发展具有特定的历史惯性与顽强的持续性。3.文化保守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中蕴含着历史合理性。这种历史合理性可详述如下:(1)是对现代化思潮中科学主义、理性至上的反拨;(2)是对现代化进程中物质进化与精神退化二律背反的检讨;(3)是对现代化与传统内在关联的理性认识;(4)是现代化过程中保持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学理辨析。需要说明的是,承认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并非全面肯定其理论价值。文化保守主义虽然同意吸纳外来先进文化,但又将它归属于本民族精神统辖之下。他们通常将东方精神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置于完全对立、非此即彼、非褒即贬的决然境地。这种思维定势都是应当注意、批判和摒弃的。
二、对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系统省察
何晓明不仅对文化保守主义产生背景作出了颇为详尽的理论疏解,还对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进行了系统视检。他秉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维理路和话语模式,将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置于东西文化相互冲突与彼此交融的宏阔背景中,对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末叶近一个半世纪的保守主义思潮作了全景式的勾绘,构建了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较为完备的理论谱系。
(一)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勃兴
1.文化保守主义缘起何时。近代文化保守主义何时兴起?长期以来,学界虽有不同观点,但一般将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作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发端期。比如郑师渠认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起源于“国粹派”[2]12,欧阳哲生以康有为和“国粹派”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开端[3],卢毅则以张之洞“中体西用”论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源头。[4]然而在此问题上,何晓明不为时论所移,体现出史学工作者特有的理性精神。经过多年的历史研究与逻辑分析,他将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产生时间提前到19世纪60年代,比时论提早了近半个世纪。在他看来,学界之所以将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推迟了近半个世纪,是因为他们忽视了思想文化演进与发展的内在理路,即未能科学地阐释文化保守主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衍变过程。也就是说,他们忽略了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真正先驱作用。基于此,何晓明推翻学界之定论,认为冯桂芬是近代文化保守主义兴起的开启性人物:“在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史上,冯桂芬是有特殊意义的人物。可惜这一点长期以来为研究者所忽视。”[1]322
2.文化保守主义理论特质。虽然保守主义思潮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扩张而产生的一种普遍现象,但由于历史与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现代化介入方式的不同,各国文化保守主义表现出各呈异彩的理论特质。由于他国文化保守主义理论特质非本文主旨所在,故略去不谈,谨对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特质略加展示。在何晓明看来,近代文化保守主义具有四个理论特质:(1)民族立场与忧患意识。鸦片战争不仅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还将保守主义思潮推向了历史舞台。面对民族与文化的双重危机,民族立场和忧患意识自然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天然品格。(2)人文精神与反科学主义。在文化保守主义看来,中西文化具有不同的思维路向:中国文化是精神的、内在的、伦理的,西方文化是物质的、外在的、科学的。因此他们在认同与捍卫民族文化的同时,必然会高扬人文精神而反对科学主义。(3)道德本体与宗教情怀。文化保守主义不仅承续了传统文化的道德学说体系与道德实践体系,还将道德本体化,进而上升到人类“终极关怀”的层面,表现出浓厚的宗教情怀。(4)变易意向与中庸准则。何晓明认为,文化保守主义之“保守”的本义是不浪漫、不激进,但也绝不墨守成规,而是渐进、缓慢的趋新。正如当代新儒家牟宗三所言:“真正的保守,就是切实而落于实践的创新。”[5]110也就是说,文化保守主义将变易意向与中庸原则完美的统一起来。
(二)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推进
在构建文化保守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何晓明认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有两面旗帜:中体西用与保存国粹。依笔者之愚见,在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文化保守主义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论进路:中体西用、保存国粹与内圣外王,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体系。
1.中体西用。无论是真正学习西方,还是暂时的策略,中体西用都是文化保守主义探寻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条理论进路。从中体西用的内在衍进来看,有三个关键人物:冯桂芬、孙家鼐与张之洞。(1)冯桂芬:中体西用的最初倡导者。虽然冯桂芬没有明确说出“中体西用”四个字,但他的论著已初现端倪。在《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中,他不仅定下了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基调,还提出了中国自强的具体方略:“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这句话的误读从而贬低了冯桂芬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在何晓明看来,冯桂芬这句话的重心在后半句:“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即中国的现代化就要以“富强”为目标,以“诸国之术”为参照。(2)孙家鼐:中体西用概念的提出者。时任光绪皇帝老师的孙家鼐发现了冯桂芬,他不仅向光绪皇帝呈上冯桂芬的著作,还第一次提出“中体西用”的概念。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孙家鼐如是说:“今中国创办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6]426孙家鼐明确将“中体西用”作为京师大学堂的立学主旨。(3)张之洞:中体西用体系的完备者。如果说冯桂芬对“中体西用”论有首倡之功,孙家鼐第一次将它作为办学的指导原则,那么张之洞则承担了将它理论化、体统化的任务。在《劝学篇》中,他系统论述了“中体西用”的内涵,并通过洋务运动将它落到社会现实层面。
2.弘扬国粹。洋务运动之后,接续“中体西用”论的是国粹派,何晓明将它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第二面旗帜。不难发现,国粹派的身上始终飘荡着“中体西用”的幽灵。面对西风劲吹、西学东渐,传统文化摇摇欲坠的社会现实,国粹派希望高扬国粹旗帜来振奋民族精神,挽救民族危亡,“国粹存则其国存,国粹亡则其国亡”[7]自然成为他们的立论基点。在学术策略上,国粹派主张“古学复兴”。何谓“古学”?他们认为,“古学”即“国粹”,“国粹”即“古学”,二者统一于先秦以来的传统文化而非专指儒家。他们援引西方文艺复兴的例子论证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恒久价值与现代意义。正如文艺复兴绝非一味复古一样,国粹派的“古学复兴”也内含着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旨意。正如国粹派主将黄节对国粹概念的界定:“发现于国体,输入于国界,蕴藏于国民之原质,具一种独立之思想者,国粹也。”[8]何晓明指出,虽然国粹派将文化使命、政治责任与民族情愿融会于一炉,体现出浓浓的爱国之情,但内在的理论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1)国粹派貌似走文艺复兴之路,但他们并未理解文艺复兴的现代化倾向,而国粹派在政治立场上有“排满复汉”之意。(2)正因为政治上“排满复汉”,国粹派将清代学术排除在国粹之外,这是对传统文化不负责任的态度。[1]166
3.内圣外王。由于强烈的复古倾向,国粹派很快被现代化“其势汹汹、殆不可遏”之潮流吞噬了。真正将文化保守主义推向高潮,使之成为现代中国三大学术思潮之一的是现代新儒家。虽然现代新儒家仍然没有摆脱“中体西用”的窠臼,但他们充分展扬了儒家的内圣外王。面对新的时代特征,现代新儒家对内圣外王作了新的阐释,提出“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构想。总之,现代新儒家既承续了宋明儒学的“灵根”,又吸纳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通过“返本开新”、“灵根自植”的方式,希冀从儒家道统中发掘中国现代化的文化慧泉和精神动力。如其开山之师梁漱溟一方面宣称“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另一方面又要求国人“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9]528作为其另一中坚的贺麟也在思考儒家思想新开展的问题:面对空前的民族文化危机,他不仅提醒国人必须“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又认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立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是建立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10]8在何晓明看来,“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方略体现了现代新儒家“联结过去与未来的历史抱负、打通保守与创新的价值取向、融会中学与西学的知识追求”。[1]277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中体西用、保存国粹与内圣外王共同形成了文化保守主义理论推进的三条路线。通过对这三条路线的梳理与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文化保守主义对中西文化关系及中国现代化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与延展。
(三)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绝大多数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纷纷移居港台及海外,加之思想文化领域一次次的清算和荡涤,保守主义思潮气数直降、日见其微。曾几何时,改革开放,清风徐来,新文化保守主义随着“文化热”和“国学热”由风闻而拂面,再次成为人们关注与追棒的热门话题。如果说上世纪5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是“无可奈何花落去”,那么90年代以来人们发现它“似曾相识燕归来”,为学界带来多年未见的众声喧哗的生动气象。作为基本的历史事实,上世纪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复兴几成学界的共识。
不可否认,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泛起是对现代性反思的一部分。何晓明也正是从理性反思的角度来诠释当代文化保守主义,并认为它表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1.文化保守主义阵营的分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保守主义异不胜同的局面被打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表面出个性化的发展趋向。现在看来,文化保守主义阵营最大的异数乃是李泽厚。虽然李泽厚以新儒家自居,但他对文化保守主义的某些思想颇为不满,并提出自己的见解:(1)儒学四期说。在他看来,现代新儒家的儒学三期说有两大偏误:一是以心性——道德理论来概括儒学,二是抹杀了荀子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针对儒学三期说理论之弊病,他另起炉灶,另辟蹊径,提出儒学四期说:“我所谓‘四期’,是认为孔、孟、荀为第一期,汉儒为第二期,宋明理学为第三期,现在或未来如果发展,则应为虽继承前三期,却又颇有不同特色的第四期。”[11]13(2)“西体中用”论。自步入近代以来,如何处理中西关系历来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核心论题,并提出影响深远的“中体西用”论。然而在此问题上,李泽厚别出生裁、别开生面,提出“西体中用”论。他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是学问、知识、文化和意识形态之意,不能作为“体”。“体”应当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即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不止于此,2000年后,李泽厚公开反对文化保守主义,尤其对蒋庆等人倡导儿童读经运动提出尖锐批判。由此可见,当代文化保守主义阵营开始分化,并呈现个性化倾向。
2.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趋同。虽然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共同主宰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舞台,但由于时代的变迁,它们之间的关系呈现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以文化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关系为例略加评析:文化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呈现出一种由相互对抗(1949年以前)到遭受批判(新中国成立后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良性互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关系。90年代以来,尽管当代文化保守主义势头强劲,但它与自由主义的界限日趋模糊,二者关系也变得极其微妙。作为一股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当代文化保守主义以全球化、多元化为立论背景,不再与自由主义进行二元对立的论争,转而寻求双方的共通性。它以更为开放的文化心态,接引其他多种思想资源以发展与充实自身的理论体系。尤其是2000年以来,文化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更加密切。
(四) 文化保守主义的学术价值
作为20世纪中国三大学术思潮之一,文化保守主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作出了独特的学术贡献,在清理和阐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家一般难以望其项背。在何晓明看来,文化保守主义的学术价值可表述如下。
1.深度阐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如前所述,民族文化的空前危机促进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形成。从冯桂芬、张之洞到邓实、章太炎再到现代新儒家,他们始终对西方文化冲击下如何存续传统文化问题忧心忡忡。因此,深度阐扬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化的内在基因与生命机理,是文化保守主义自觉承担的精神慧命。作为具有保守情结与革新思维二重性的学术流派,文化保守主义不仅阐发了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千年常新的品质,还开掘了儒家人文主义的普适价值与现代意义。
2.深入探讨了中外文化关系。在与东西列强战争一败再败的现实面前,中国人意识到现代化的合理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对中国来说,现代化就是处理古今中外文化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文化保守主义体现了自己的学术立场。他们一方面肯定民族文化的本位性、独特性、多元性和不可通约性,另一方面承认民族文化之间可以相互融摄。[12]92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国粹派以捍卫民族文化而著称,但对西方文化的肯定丝毫不逊于其他学术团体。诚如许守微所言:“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7]
3.深刻批判了现代化的弊端。勿庸讳言,现代化无疑是人类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大发展,但它并不是完美无缺的。20世纪以来,两次世界大战,数次影响深远的经济危机已将现代化思潮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文化保守主义对现代化作了深刻反省与批判:唐君毅认为西方文化是“上帝与恶魔并在,人之神性与兽性同流”[13]143,刘述先归纳出现代西方社会五大问题:一,意义失落的感受;二,非人性化的倾向;三,戡天役物的措施;四,普遍商业化的风气;五,集团人主宰的趋势。[14]188文化保守主义认为,通过对现代化弊端的深刻批判,可为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何晓明虽然充分肯定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学术价值,但也尖锐批判了现代新儒家外王思想与大陆新儒家“政治儒学”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化倾向。在他看来,文化保守主义的政治愿景无论多么美好,其结果都将是一场无法实现的“世纪新梦”。
参考文献:
[1] 何晓明.返本与开新——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 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 欧阳哲生.中国近代文化流派之比较[J].中州学刊,1991(6).
[4] 卢毅.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嬗变与传承[J].东南学术,2000(2).
[5]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台北:学生书局,1970.
[6] 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M]//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
[7] 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J].国粹学报,1905(7).
[8] 黄节.国粹保存主义[J].国粹学报,1905(9).
[9]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1)[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10] 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1] 李泽厚.儒学四期说[A]//李泽厚.己卯五说.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
[12] 何晓明.再论文化保守主义[M]//刘东.现代化研究(1).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3]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M].台北:学生书局,1984.
[14] 刘述先.儒家思想与现代化[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