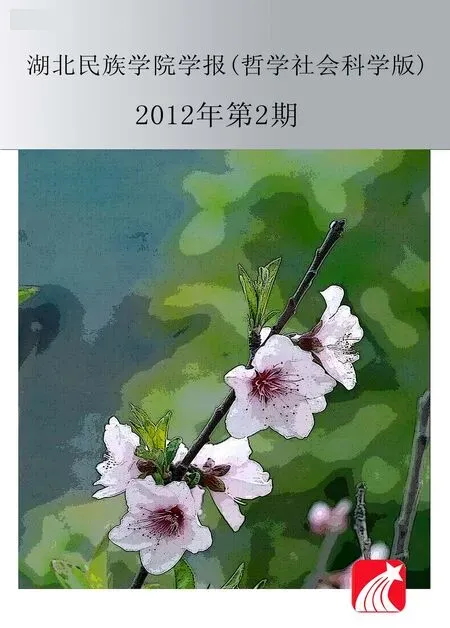从《荆楚岁时记》看南朝荆楚地区的节日饮食习俗
王增武,张甜甜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荆楚岁时记》是我国第一部专门描述岁时节令活动的民俗著作,也是现今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部古代记录楚地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笔记体散文,并第一次系统地、如实地记录了荆楚地区一年内依次进行的岁时节日习俗,其历史地位不言而喻,自古就有诸多专家学者对其予以研究。笔者认为,从饮食人类学视角来探讨该地区的节日饮食习俗,我们会发现许多被忽视的社会基本信息。同时,这种分析视角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反省当下节日文化渐淡的内在原因。
一、《荆楚岁时记》与饮食习俗简介
《荆楚岁时记》一书成于我国南北朝时期,其作者为萧梁北周之际的宗懔。该书在历史学、文学以及农学等方面拥有重要的地位,有学者认为,《荆楚岁时记》以新的记述方式及时记录了这一时期的民俗变化。在此后的一千四百余年中,本书不断被人们节录引用,成为说明民众岁时生活的历史依据[1]。可见,该书正是在文化变迁中获得更为丰富的价值。而以岁时民俗为基础,在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中更是具有深远的意义。《荆楚岁时记》成书问世之后,集录和记载岁时民俗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它们在引述节日民俗时,几乎无一例外地从该书引证。
《荆楚岁时记》原著有三十八条流传于世,并以时为序,从内容上可以将其分为七类:历史事件和人物,农事与生产,防病、治病及卫生,祭祀祖神,爱情、婚姻和家庭,文娱、体育与旅游活动以及迎新去恶等[2]3-4。其内容极为丰富,几乎囊括了下层人民节日民俗的方方面面。
目前学术界对《荆楚岁时记》的研究内容广泛、视角多维,例如对特殊节日习俗、节日禁忌[3]等研究。但是纵观这些研究成果,鲜有以该书为视角来探析南朝时期的节日饮食习俗的。作为从文化视角去探讨研究饮食行为和饮食文化相关问题的饮食人类学,在国外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4]241。该学科主要是研究人、饮食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人的归类简单概况为:“人是一种杂食动物”[5],从而人类饮食文化多样而丰富。在中国大陆地区,饮食人类学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是“搬运”西方研究成果的阶段。与灿烂辉煌的中国饮食文化相比,作为一门学科而言,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明显落后。饮食人类学近来成为学界研究热点,对其研究不仅有益于中华民族传统饮食文化的弘扬,也是在各种学科中凸显中国特色、中国学问的一个重要部分[6]。笔者认为,中国拥有灿烂的饮食文化传统、丰富的饮食民俗文献,通过对特定时间和地区的饮食习俗予以分析,可以了解其人民在生产、禁忌和信仰等多方面的情况。而《荆楚岁时记》一书正为此提供了不二的选择。
饮食在岁时节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荆楚岁时记》目前较为流行的谭麟译本中,涉及饮食习俗的节日有十四个,频率高达十九次,即全书有一半内容提及饮食或与之有关。从饮食习俗分布的月份来看,正月有四次,二月和腊月各三次,三月有两次,其它月份(除四月外,该月没有涉及节日饮食习俗)各分布一次。*本文所涉及的时间均按农历计算。可见,南北朝时该地区节日饮食习俗在月份分布上较均匀,多安排于农闲季节,并重点凸显岁首年尾。节日饮食习俗不仅在该书中涉及面广,并几乎和当时所有节日都有所关联,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笔者认为,通过节日饮食习俗这一分析对象,我们可以了解到萧梁时期荆楚地区下层人民的生产、生活、禁忌和信仰等内容,更为全面地把握当时的社会面貌。
二、南朝荆楚地区节日饮食内容探析
南朝荆楚地区的饮食内容丰富,对其加以分类是我们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根据不同标准,对节日饮食习俗分类的结果也有所不同。有学者根据时间将其分为:春令、夏令、秋令和冬令节日饮食习俗[7]。瞿明安教授从多重角度对饮食习俗加以分类,例如,从不同类型传统节日出发,我们可以把饮食习俗分为年节中的饮食习俗、纪念性节日中的饮食习俗、农事节日中的饮食习俗、祭祀性节日中的饮食习俗和其他类型节日中的饮食习俗等[8]217-241;从象征人类学视角对中国饮食习俗的象征意义加以探讨,可以将饮食象征系统符号加以分类,有象征食物、象征饮食器具和象征性饮食行为三种基本要素[9]。根据瞿明安教授的象征符号的分类标准,我们可以对《荆楚岁时记》中的饮食予以分类:
(一)象征食物
《荆楚岁时记》所记载的饮食习俗中,根据节日和功能不同,其食物品种和包含的意义也有所不同。瞿明安教授将象征食物分为三类,即吉祥食物、禁忌食物和占卜食物[9]。笔者认为,具体到南朝荆楚地区的节日饮食,归为养生保健食物、祈福避祸食物、祭祀食物三类可能更为妥当。
1.养生保健食物。养生保健是人类对食物的基本要求之一。在《荆楚岁时记》中,该类食物占据多数,如:正月一日,下五辛盘,即用韭、薤、葱、芸苔和胡荽这五种带辛味的菜来修炼形体。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飨其胙[2]55。其大意为五辛菜可使五脏之气顺通,在立春当日,在社树下搭棚屋,祭神后周围邻居共同享用用于祭祀的酒肉。显然,人们非常重视借助节日补充平日难得的食物。又如:三月三日,取鼠麴汁蜜和粉,谓之龙蛇粄,以厌时气[2]81。其意为在三月初三,采摘鼠曲草,用蜜汁加粉调和,做成饼团,叫做“龙舌饼”,可以治疗时气病。可见,人们善于根据时节变化,利用进食来提高自身抵抗力,达到保健的功效。养生食物主要是借助节日习俗与活动来为自身补充能量和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同时,通过提供各种食物可以让人们对节日更加期待,为人们在节日中参与各种活动提供动力,丰富节日活动内容。
2.祈福避祸食物。祈福避祸是节日生活的重要内容,人们在特定的节日中利用食物的特殊象征意义来表达自己对自然和生命等畏惧和祈福之意。在萧梁荆楚地区,该类食物主要是人们在特殊的节日中用于趋吉避害、祈福避祸。如:正月一日……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各进一鸡子。[2]5古人认为椒味精美能免除百病,喝屠苏酒可祈求平安,吃鸡蛋可辟除瘟疫之气[9];岁暮,家家留宿岁饭,至新年十二日,则弃之街衢,以为去故纳新也[2]147。留饭以示年年有余粮,祈求来年丰衣足食,至今仍在荆楚地区传承[10]。在节日中,通过饮食活动表现出当地居民规避天灾人祸,追求美好生活的心境。
3.祭祀食物。祭祀鬼神、祖先等是诸多节日的主要活动之一。长久以来,食物是祭祀必不可少的物品,人们只在特定节日中才制作这些特定的食品。如: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先以杨枝所指,仍以酒脯饮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2]37。即用就符和豆粥等祭祀蚕神,以期获得蚕丰收;在寒食节,禁火三天,造饧大麦粥[2]57。食用先前制作好的冷食,主要是用来纪念介子推。纵观整本《荆楚岁时记》,我们发现专门用酒肉来祭祀的并不多,原因是当时人民生活水平不高,难以用酒肉祭祀。而在腊月初八用酒肉祭祀灶神,可见,灶神在人民生活中的地位非常高,也说明人们通过祭祀与饮食关系密切的灶神,希望能保障自己基本的生活水平和提高生活质量。
在这三类食物之外,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食物,主要以纪念前朝的节日,如十月朔日,黍曤,俗谓之秦岁首[2]127。前朝的节日虽已不再纪念,现已只保留了饮食习俗,说明饮食在节日习俗传承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泰勒认为,滞留于现存文化中的那些旧的文化现象为文化残存,它被习惯势力从它们所属的社会阶段带入到一新的社会阶段,于是成为这个新文化由之进化而来的较古老的证据和实例。[11]28-29从残存的节日饮食习俗中,我们可以追溯已消失节日的的渊源、使用者的历史继承脉络等诸多内容。
(二)饮食器具
饮食器具虽然不比象征食物在传递信息过程中所具有的普遍性,但它作为一种特殊的饮食象征符号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中仍被人们加以充分的利用。象征饮食器具包括具有象征性的餐具、饮具和炊具三大类。在《荆楚岁时记》中,涉及该方面的内容并不多,但也存在一些典型案例,如:正月十五日,仍以酒脯饮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2]37。即用各种祭品和插上筷子的油脂白粥祭祀蚕神。在古代,筷子因其谐音象征快生子和勤快,在此表达人们对丰收的愿望。又如,三月三日,士民並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2]71。其大意是官民集会于环曲的水渠边,在上游放置酒杯,任其顺流而下,酒杯流到谁的面前,谁就取饮。从官民取杯饮酒的习俗中,我们发现,此时为官者主动参与普通民众的各种节日活动,了解人民的生活,并共用饮食器具,不分彼此,不难发现官民关系非常和谐。诸多学者对宗懔作为当时的官宦人士为何能如实记录下层人民生活感到匪夷所思,或许,官民共饮是真正原因之所在。这些习俗也成就了该书成为中国第一部记录下层人民节日生活不朽著作的原因所在。
(三)象征饮食行为
象征饮食行为作为象征食物和象征饮食器具的载体,成为饮食象征符号表达饮食象征意蕴最直接的手段,它所表现的是一种饮食主体与饮食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荆楚岁时记》中,可以将此类行为分为以下几种:
1.制作原则。各种饮食行为在节日中都承载着特殊的意义,所以在选材和制作中都有诸多讲究。选材上多按季节变化而有所不同,如在谈及寒食节时,人们即把鸡蛋列为滋补身体的美味。引用张衡《南都赋》中“春卵夏笋,秋韭冬菁”一说[2]63,即冬天的鸡蛋、夏天的笋子、秋天的韭菜和冬天的韭菜花,对人体最有益。许多节日饮食与传说、祭祀有关,所以在制作中尽力与平时饮食有所区别,如用刚生成的竹子做成筒粽,并缠上五色丝,称为长命缕[2]96,以此纪念屈原投江。
2.礼仪规则。从该书中不难发现,南朝荆楚地区从饮食习俗中延展出了一整套的礼仪制度,并成为社会规范的典型代表。例如,正月一日,凡饮酒次第,从小起[2]5。正月喝酒先从年纪小的开始,因为年轻人过年意味着年长了一岁,先喝酒有祝福他的意思,老年人过年意味着又失去了一岁,所以之后给他斟酒。年轻人先喝酒,明显区别于“孝为先”的传统准则,反映了在动乱的社会,人们对年轻人在未来社会中安邦定国的殷切期望。
3.祭祀准则。在饮食中,食物禁忌也是多种多样,它主要指人们在进行宗教消费和某些特殊性的非宗教消费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象征性饮食行为。在南朝荆楚地区,食物禁忌较多,如在以食物命名的寒食节禁火三天,造饧大麦粥[2]57。禁火一方面是提高防火意识,另一方面则用于祭祀介子推。关于宗教饮食禁忌,后文还会专门予以探讨,此处不再赘言。食物禁忌不仅有现实意义,还有宗教意义。另外,南朝荆楚地区用食物对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诸神大加祭祀,一方面希冀获得农业丰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此时此地的农业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三、对南朝荆楚地区节日饮食习俗的阐释
毋庸置疑,饮食习俗在中华民族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食物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生理所需的能量,还包涵了人类诸多的文化需求。从人类学、民俗学角度来看《荆楚岁时记》一书中的饮食文化,我们可以解读到荆楚地区在南北朝时期人类生存活动的基本情况。
(一)维持人类生存是节日饮食的首要目标
食物的获取离不开特定地区的生态环境,研究人类生存活动和与环境的关系的生态人类学非常重视人类食物的获取、消费等,并尤为关注人类营养均衡和食物能量的流动等[12]21。荆楚地区属于南方,气候温和,降雨量充沛,适宜稻谷生长。两湖地区至今仍以“鱼米之乡”著称,该地区人民以米饭为主食,千年未移其俗。《周礼》云:“荆州……其谷宜稻。”[13]2649该地区其主食以稻谷为主,兼有其他的多样性的结构特征。《荆楚岁时记》中则有:岁暮……留宿岁饭,至新年十二日,则弃之街衢,以为去故纳新也。而在新年伊始则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2]147。在新年这一年最重要的节日中完全体现了这样的特点,也说明他们在重大节日中,在注重节日氛围的同时也兼顾了均衡地摄入营养。
在南朝荆楚地区,节日中强调的多为副食,每个节日都有不同的品种,而不变的是主食,即以米饭为主。这也是我国南方地区的普遍习俗。从食物来源和制作来看,节日食物种类较多,更以时令蔬菜为特色,岁首唯食新菜[2]25,仲冬之月,采撷多种杂菜,乾之,並为鹹菹[2]130等。换言之,以食稻米为主的地区,蛋白质的摄入是没问题的,通过食入其它植物来平衡体内所需的氨基酸和维生素等,再加以调节,让人们注重营养的合理搭配,是提高这些食物的地位的最好方法[12]41-42。显然,这是农耕民生业的基本表现。
(二)重视节日素食习俗彰显人们基本的宗教信仰观
我们从能量来源的角度,发现当时人们的节日食物主要是素食,这不仅反映当时该地区连年战乱,人民流离失所,生活水平低下的事实。家中即使有个别牲畜,也是主要用于生产,而非食其肉。另外,一般农户维持温饱已是大事,根本没有多余的粮食来饲养家禽和牲畜。没有肉食来源,是节日重视素食的客观因素。
南北朝是我国佛教、道教势力极为兴盛时期。在该书中,七月十五日便单独提及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可见在南朝荆楚地区,佛教已广为流传。佛教教义要求人们放生禁杀,为生灵超度,形成许多与之相关的食物禁忌。有学者认为,自梁武帝之后,素食不仅成为佛教徒清规,而且逐步影响到民间,成为越来越多的民众的习俗[14]136。而道教也有诸多的禁杀思想。这种禁忌在该书中也多有体现,例如,在正月,一日(初一)不杀鸡,二日不杀狗,三日不杀猪,四日不杀羊,五日不杀牛,六日不杀马,七日不行刑。且初一不准吃鸡蛋[2]25。又如:十月朔日,黍曤。曤,指肉羹,此处特指菜羹[2]127。可见,很多以前的食肉活动被食草所替代。将宗教禁杀观念渗透到人们的节日饮食习俗之中,足见当时宗教信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这是节日中重视素食的主观因素。在饮食中刻意回避荤食,宗教禁忌是其根本原因。
(三)特定节日饮食习俗反映社会的变迁
比较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的基本方法之一。将南北朝时期的南北节日饮食加以对比,利于我们从整体上认识该时期的饮食习俗和社会生活。在《荆楚岁时记》中,宗懔不仅介绍了当时荆楚地区的节日饮食习俗,还在多处按语中提到了这些节日在北方的饮食习俗。例如,十月朔日,荆有黍曤,北设麻羹[2]127;又如,六月伏日,并作汤饼[2]104,也来自于三国北方的魏国。“南人食米,北人食面”的饮食格局自古有之,在该书中,多次提到“饼”类食物,在东汉末年,胡饼制作技术开始由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传入中原地区[15]403。而到萧梁时期,该食物已进入了南方地区。该按语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动乱,许多北方人来到南方定居后,逐渐放弃了之前的各种习俗,积极融入南方的环境和文化中;另一方面也反映迁移者对北方故土和亲人的思念,在节日中还不忘之前的习俗。同时笔者也注意到,随着当时南方的相对安定,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南方的习俗也开始传入北方地区,在节日中出现南北方人共度佳节的情况,例如,在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2]122,宗懔特别强调现在北方人也重视该节日。这不仅反映人们对长者的尊敬和长寿的追求,更折射出南北方人民对亲人的思念,所以这个节日在南方产生后很快深入人心,形成南北共度的盛举。可见,社会的长期分裂深刻反映于社会习俗之中,人们通过节日饮食来企盼与亲人早日团聚,希冀社会安定。从节日饮食习俗中可以窥视到国家统一是必然趋势。
(四)饮食馈赠行为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
馈赠行为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一直被人类学家所关注。人类学大师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著名的民族志《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就是通过描述新几内亚东部的群岛上的一种馈赠与交换行为——库拉,而牵扯了一系列独特的风俗信仰、巫术神话、经济生活和技术知识,浸透了土著人的理想、荣誉和智慧。法国著名人类学家莫斯更是著有影响深远的《论馈赠》,认为不同历史时期存在着许多形式的交换形式,而这一系列交换均在社会力量驱使下和一个具有三重义务的社会逻辑中进行。在这类社会中,人可以说是物的延伸,人对自己拥有和用于交换的物在很大程度上视为具有生命的灵性[16]5-6。馈赠行为是人与自然、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桥梁。
南朝荆楚地区的许多节令习俗来自于传说和祭祀,其形式多是因为人们认为神或者巫术的恩赐才得之,他们便用食物来馈赠和纪念神,并赋予了诸多的象征意义。该书和饮食有关的馈赠行为有十次之多,占饮食总数的一半以上,可见饮食的象征行为与馈赠行为密不可分。在这些馈赠行为中有:一是用食物馈赠神灵,祈求农业丰收和避祸趋吉,例如正月十五日,以酒脯及豆粥祭祀蚕神[2]37;九月九日到郊外饮宴来躲避灾难[2]122等。二是祭祀历史人物,例如,寒食节纪念介子推,就是因为他没有接受晋文公的馈赠而被火烧死,人们用寒食纪念他的正直[2]57-58。三是馈赠客人,例如在三月三日,在江渚池沼间“流杯”饮酒[2]71,即酒杯代表别人的祝福,流到谁面前则必须饮酒。
饮食行为本身就是人类从大自然的馈赠中获取营养的过程,同时为了分享彼此拥有的食物营养和能量,馈赠与交换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内容。在食物紧缺、社会动荡的年代,人们之间馈赠食物显得尤为显眼,比其它任何馈赠都要实用且受欢迎。另外,此时荆楚地区的许多人是北方的迁移者,他们初到南方,与当地族群接触、交流,乃至发生冲突都是不可避免。而彼此之间在节日期间通过互赠食物,不仅丰富了节日的生活,也增加了人们之间的交流机会,减缓紧张的社会关系等。由此可见,馈赠行为可以使动荡社会中的人们获得安全感,得到宽慰,同时在馈赠仪式中,加强了彼此间的信任和凝聚力,在现实和精神两个层面都有所依托,最终达致社会整合的目的。
结语
通过对南朝荆楚地区岁时节令中的饮食习俗的探析,我们可以大体了解当时社会的节日饮食习俗和整个社会活动的情况。在分析过程中运用象征人类学和饮食人类学的方法,可知荆楚地区饮食文化内容丰富,内涵广深。同时,对一千多年前的饮食文化予以探析,有助于我们了解荆楚地区乃至长江流域人类饮食习俗意义和变迁,也可以看到饮食这一文化对民族认同和社会结构分析的学术意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食物是社会关系的象征,是阶级、阶层、等级、层次、身份等的一种符号,并隐喻着一种文化的自我解释和族群认同的属性[17]。可见对食物和饮食习俗的研究,需要运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手法去理解、把握和解释,尤其如格尔兹的“深描”方法,即通过对被研究对象所作的解释的再解释,可以找到这种隐含于食物中的文化结构和符号象征意义,可以让我们更为有效地解释饮食习俗。
对南朝荆楚地区的节日饮食习俗的探析,我们不难发现,该时期荆楚地区的节日饮食习俗不仅内容多面,内涵丰富,还彰显出节日的神圣性、严肃性和有节律的特点,从而使节日意义非凡,并名垂千古。相比较时下人们对节日民俗越发感觉渐淡的事实,从民俗学角度看,其原因无外乎有:人们对饮食的神圣性意识渐淡;饮食习俗简化和庸俗化;在节日中无节制的放纵和狂欢,以消费、娱乐和放松为主要目的[18]53-56。将节日简单的娱乐化无疑是流于俗见蔽其真知,其后果必然会淡化节日原本丰富的文化意义,值得研究者和社会各界予以警惕。
参考文献:
[1] 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述论[J].民俗研究,2002(2):172.
[2] 宗懔.荆楚岁时记译注[M].潭麟译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前言3-4.
[3] 李道和.《荆楚岁时记》岁首占候风俗的文献考辨[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1)
[4] 张展鸿.饮食人类学[M]//招子明,陈刚.人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41.
[5] 叶舒宪.饮食人类学:求解人与文化之谜的新途径[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3.
[6] 彭兆荣,肖坤冰.饮食人类学研究述评[J].世界民族,2011(3):56.
[7] 陈光新.中国饮食民俗初探[J].民俗研究,1995(2):12.
[8] 瞿明安.中国民族的生活方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217-241.
[9] 瞿明安.中国饮食文化的深层结构[J].史学理论研究,1997(3):124.
[10] 萧放.岁时生活与荆楚民众的巫鬼观念——《荆楚岁时记》研究之一[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26.
[11]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28-29.
[12] (日)秋道智宏,市川光熊,大塚柳太郎.生态人类学[M].范广融,尹邵亭,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
[13] (清)孙治让.周礼正义[M].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2649.
[14] 牟中鉴.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卷三:宗教·文艺·民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36.
[15] 宋蜀华,陈克进.中国民族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403.
[16] (法)马尔塞·莫斯.论馈赠——传统社会的交换形式及其功能[M].卢汇,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5-6.
[17] 陈运飘,孙箫韵.中国饮食人类学初论[J].广西民族研究,2005(3):53.
[18] 孙邦杰.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时间现象学分析[M]//李松,张士闪.节日研究:第一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5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