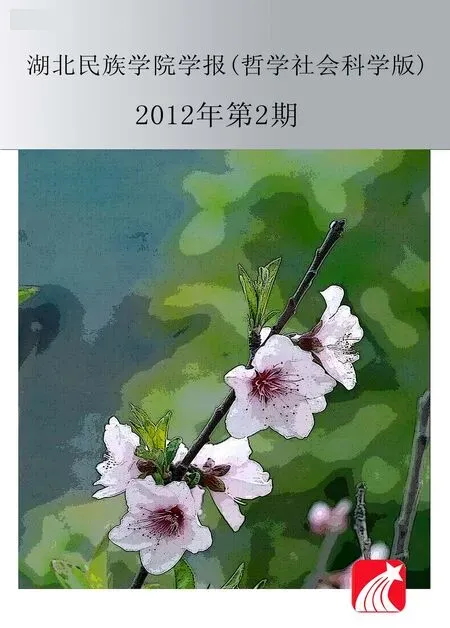群体行为视域下的民族群体性事件
徐光有,袁年兴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利益调整期,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冲突日渐凸显,群体性事件频发。群体性事件作为社会成员同政府交流的特殊方式,其影响极其复杂。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逐渐递延的三个方面:社会混乱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对公共秩序的破坏导致公共治理体系的瘫痪;社会共识的迁移导致反社会意识的形成。”[1]正鉴于此,国内外对群体性事件的关注日益增强,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探讨,特别是在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危害,及其预防和治理方面,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观点。但目前国内对民族群体性事件关注较少,本文试图从人际与群际行为区别的角度对民族群体性事件做一些分析。
一、 群体性事件的历史背景:大众时代的出现
将雅典的民主政治和古典文化带入臻于极盛雅典首席将军伯利克里在雅典英雄的葬礼演说中说:“我们的政体确可以称为民主政体,因为行政权不是掌在少数人手里,而是握在多数人手中。当法律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公正地调解人们的私人争端时,民主政体的优越性也就得到确认。”[2]
在权力普遍被个人或少数人所占有的时代,这个古希腊的政体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权力的下移。大众成了权力的主体,那是一个大众时代。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束,主权由寡头所有,这个大众时代淹没于历史的烟尘中。
古希腊的那个大众时代虽然远去,但是它的灵性熠熠发光,在千年以后终于得以复兴。培根的经验主义,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卢梭的人民主权、社会契约论一路走来伴随着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演进。“自由民主政体、科学实验和工业制度,19世纪以来的这三项原则培养和造就了大众时代的来临。”[3]在大众时代,公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公民是国家权力的来源和国家权力的主体并且平等地享受国家的权力。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全体公民平等,并且公平正义地享有各种社会资源,公平正义地享有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由于人类社会的结构特征,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阶层,不同类型的群体。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对社会资源展开争夺和博弈,社会资源占有也多寡不均。由于部分社会群体对资源的占有较少,又缺乏在体制内争夺和博弈的手段和能力,体制之外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社会发展又发展不充分的自然逻辑。
二、群体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
这里的群体是指在社会秩序体系之外的群体,其成员来自社会秩序体系之内,但在特定的时空情景里不接受日常社会规范,即日常社会规范不在场。社会成员加入群体后,自我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现代心理学认为自我概念包含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个人认同,指个体人格特征的自我鉴定,如“我”通常称之为“小我”。第二层次是社会认同,指以范畴成员资格为主要形式的自我鉴定,如“我们”通常称之为“大我”。社会认同和个体认同是相互联系的,社会认同是个体认同的一种扩展,有时社会认同中包含着个体认同。一般情况下社会成员有多种和多重的社会认同,随着时空的变换,情景的变换,社会认同也可能发生变换。在多种和多重社会认同中社会认同度存在着差别。
自我概念会外显为行为模式。自我概念的双重内涵,自我概念的功能会决定主体行为的多样性。个人认同决定的行为为人际行为,社会认同决定的行为为群际行为,群际行为通常因群体资格而出现。人际行为因个体的差异性而有一个正常的变化幅度,群际行为往往是一致的,变化的幅度较小。自我概念两个层次没有完全清晰的界限,主体的行为也呈现出多样性。一般情况下很难区分哪些行为是个体认同决定的,哪些行为是由社会认同决定的。主体的行为往往包含着两种认同,只是两种认同的程度有所差异。主体行为可以看做是一个连续体,在连续体的一端互动是由个人特征和人际行为决定的,在另一端互动是由社会认同,群体资格的因素决定的。主体行为在这两端中移动。人际-群体这种连续但有所区分的度量,并不是非此即彼。任何人总是带着个体人格特征加入一个群体,群际行为也经常留下个体特征。社会认同的多样性也导致主体行为的复杂性。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过程中,群体成员的行为有别于其日常行为,而体现出暴力性的行为特征。这种暴力倾向较个体的人际行为大幅增长。是什么导致群际行为较个体的人际行为更易出现暴力性行为?古斯塔夫·勒庞在其名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说“个体一旦参加到群体之中,由于匿名、模仿、感染、暗示、顺从等心理因素的作用,个体就会丧失理性和责任感,表现出冲动而具有攻击性等过激行动。”[4]个体处于群体情景中,其心理特征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改变。一般认为在群体情景下,惯常的社会约束消退,由于挫折引起的想要破坏、发泄的本能被释放,造成恣意的暴力和无理性行为。
这种恣意的暴力和无理性的率性行为被描述为退化到一种原始的或凭借本能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称之为匿名效应,匿名效应后发展为“去个体化”理论。“去个体化”理论发展成为一种正式的行为模型。[5]群体性事件中个体行为是以群体的名义进行的,日常生活中约束机制主要是制约着个体的行为,尤其是严重的破坏性行为(真实的或感觉到的)。对群体行为的约束机制则相对要少要弱(也是真实的或感觉到的)。匿名于群体之中消弱了行为主体对自我行为承担责任的恐惧心理,在遭受挫折时需要发泄的心理情绪被放纵出来,在群体情绪高昂之时,由于相互之间的感染和影响,由于循环的刺激反应,放纵出来的情绪被扩大。“群体的兴奋力量随群体中个体的数目呈几何级上升”。[5]大多数群体性事件冲击政府,阻塞交通,甚至发展到“打、砸、抢”等破坏性暴力行为。参与群体性事件的行为主体不是不知道这些行为的违法性,但是即使要承担责任也该由群体来承担,并且群体的规模越大,个体就越容易匿名于群体之中,个体承担责任的可能性和承担的责任就越小。“群体成员越无个性特征,作为个人的差异性越小,自我特征的感觉也就越小,他们的行为方式就越无负责性”[6]正是匿名、分散的责任和群体规模等因素的作用,使群体性事件中更易于出现近乎本能的暴力行为。
三、民族意识、群体认同与群体性事件
民族意识*本文所讲的民族的含义为马戎所指称的族群( the ethnic group)即偏重于文化心理nation-culture,而非偏重于政治nation-state。指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通过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特点表现出来。民族意识的一个重要社会文化心理功能是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将本民族与其它民族区别差序。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会逐渐形成以自己为主体和中心的相互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这种相互之间的关系,亲疏远近、感情厚薄、利益多寡错落有差。正如费孝通先生把中国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描述为“差序格局”一般,纵向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上下有序,横向人际关系远近有差。在这多种多样的或差或序社会关系中,民族意识是其主要影响的因素之一。个人是在群体中生产、生存、生活的,人的社会性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群体性。对各种群体认同是个人的社会认同的主要方式。民族认同是人们主要的社会认同之一。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联系密切。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内化为其人格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把包括自身历史和艺术、文学、英雄人物等在内的文化成绩作为民族自豪感的最重要来源。正是因为如此,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产生重叠。民族认同是群体认同的一种,在社会流动广泛存在的今天,民族认同导致同一民族的社会成员在不同的地方往往形成聚群现象。而大量思想和经历相似的人聚集在同一社会空间下为群体抗议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导致一些涉及到少数民族社会成员的人际行为容易转变成群际行为,引发民族群体性事件。在这样的民族群体性事件中,群体的形成与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有很大的关联。
“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可以有深浅强弱不同。”[7]在群体性事件发生过程中,涉及民族间的纠纷会激起更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既然这些认同意识都不是先天遗传而是后天得到的,那么只有在不同场景中并通过不同外在因素的刺激,才会产生和激发这些不同层次上的群体认同意识。”[8]在纠纷中,为了加强己方的力量,冲突方会下意识地通过各种方式强调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以加强群体认同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冲突加剧。
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导致群体的形成,纠纷中的人际行为变成群际行为,形成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反过来又强化了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群体性事件的冲突加剧,矛盾更加错综复杂。
四、民族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
“对于一个群体而言,只有当它与其他群体相互接触并在接触过程中鲜明地感觉到彼此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和利益冲突时,才会去强化‘本群体’的意识”。[8]为了减少涉及到少数民族群众的各种冲突和纠纷中因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而形成群体,将人际行为变成群际行为,引起民族群体性事件,即对民族群体性事件的预防的第一要素是坚持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我国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同时也有中华民族这个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是比各民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更高一个层次的意识与认同。强调更高层次的意识与认同就能强调共同的权益,即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是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原则的前提;同时由于国家的性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并且共为国家的主人。从民族群体的角度,从人民个体的角度,大家都是平等的,都同为国家主人。既然都是平等并且同为国家主人,那么就可以共同参与国家管理,共享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这是预防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体制改良,让各族人民能真正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中,能公平正义的分享到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
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同一般群体性事件一样,首先保障政府和社会相互之间信息流通渠道的畅通,做到及早发现,及早解决。其次积极引导各种社会矛盾,各种社会纠纷在机制内解决,坚决反对和制止各种非法手段解决矛盾和纠纷的行为。对于民族群体性事件处置还要注意的是,首先坚持法制原则,淡化民族意识,对于各种涉及到少数民族的事件,厘清事件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哪个民族成员只要是触犯法律的,依法处罚。对于一般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少数民族群众要加强法律知识宣传,进行批评教育。
在大众时代,无论是体制内的对社会资源和财富争夺和博弈,还是体制外的对社会资源和财富争夺和博弈,采取包括民族群体在内的多样性群体方式都是一种正常的手段,一种正常的社会状态,都能推动社会秩序运行发展。正是由于体制外争夺和博弈的巨大破坏性,促使社会秩序体系增强其开放性,将体制外争夺和博弈纳入体制内,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管理方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何哲.群体性事件的演化和治理策略[J].理论与改革2010:4.
[2]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M].徐松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3] (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M].刘训练,佟德志,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50.
[4]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4.
[5] 杨鑫辉.西方心理学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78-191.
[6] J.L.弗里德曼,D.O.西尔斯,J.M. 卡尔史密斯.社会心理学[M].高地,高佳,等,译.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584-585.
[7] 费孝通.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174.
[8] 马戎.民族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