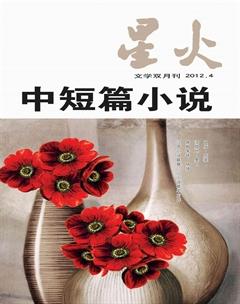流放地
墨白
首 长
我们在锡铁山以南四十公里处的万丈盐桥上,见到了面容阴沉的首长。在我们接近那辆深绿色的吉普时,首长正蹲在光滑的桥面上抽着闷香,他花白的灰发映在洁白如镜的桥面上,当我们的车在他面前停下他站起来时,我们才发现他是个驼背。
这儿离格尔木还有多远?
八十公里。
哦,你们抓紧时间。首长的声音在充满咸味的湖风里听上去有些沙哑,说完他不再理我们,而是独自一人走下盐桥。和我们一块儿回来的警卫员用胳膊肘儿碰了碰车门,也探腰走下盐桥,绕过一个用来修路的卤水坑,跟着首长朝远处湖边银白色的盐带走去。正在车里打盹的司机推门下来,一边惺忪着眼睛看着我们,一边从衣兜里摸出一个小布袋,撮出一些莫合烟粒放在一张二指宽的纸条上,又放在嘴上用口水封住,才递给我。
你们从新疆来?
对,石河子。我们从乌鲁木齐到吐鲁番,然后沿着312国道,哈密、嘉峪关、武威、兰州,本来是要去西安的,结果……可能是长途的劳累,司机的眼睛里充满了血丝。
那怎么到这儿来了?
找人,人跑了。
谁跑了?
司机往湖面上看了一眼然后说,首长的夫人。我们前天住在兰州,第二天一早人却没了。有人看到她上了一辆军车,一查,是往西宁的。等我们到了西宁,可是那个司机告诉我们,她人没到兵站,就换乘了另外一辆前往格尔木的兵车。我们就沿着青藏公路一路過来,没想,车到了这儿就抛锚了。
他们……在我们寻找他们抛锚的原因的时候,吉普车的发动机已经冰凉。那个时候驼背首长和他的警卫员的身影在覆盖着沙土的盐湖面上已经变得有些模糊,我们说,出了什么事儿?
司机用满是机油的手指指了指自己的脑门说,这儿有毛病。
她有精神病?
她和我们首长结婚那一天就疯了,后来每年她都会跑丢好几次,这样都七八年了,这次我们首长本来是想把她送回西安给她看病,没想到……那个长着络腮胡子操着一口东北口音的司机看到我们迷惑的目光,用舌头舔了舔有些干裂的嘴唇说,这你们不知道?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的时候,有十万大军屯垦戍边,说是十万,何止呀?十三万人,那时候刚打完仗,从军官到士兵,清一色的光棍。怎么办,王胡子就下令从内地招女兵,先从湖南拉来八千湘妹子,从山东拉来二千名女医护,从上海拉来九百名改良的妓女,接着就是河南、四川、北京、天津、湖北、江苏过来的,说是婚姻,其实是组织分配,从军官到士兵。一般的年龄都相差十几岁,就说从湖南来的湘妹子吧,最大的十九岁,最小的才十三岁。
哦,是这样……
我知道你的意思,先结婚后恋爱嘛。这种婚姻,要说幸福,有。先前是穷人家的女儿,吃不上嘴里穿不上衣服,一下就成了官太太,那还不幸福?如果是有文化的女兵,那就很难说了。1951年的时候,在哈密,有一个长沙女兵拒绝了一个营长,那个营长一恼拔枪就把她打死了,后来这个军官不是被军事法庭判极刑了吗?怎么,这事儿你们就没有听说过?我们首长的太太就是这样,人不但长得漂亮,又是个高中生,她比我们首长小二十岁,这还不说……司机说着,朝宽阔的灰黄的盐湖上看一眼。那个时候,驼背首长和他的警卫已经走到了环湖边上那宛如戴在盐湖上的美丽项圈的白色盐带上,他们的身影已经被午后的阳光所融化。络腮胡子说,我们首长的老婆刚死,撇下了三个孩子,你说她不痛苦?络腮胡子说着咽了一口吐沫,结婚的当天,她就疯了。
那辆绿色吉普车的马达重新发动起来的时候,我们的首长和他的警卫员却意外地消失了。在万里晴空的夏季的傍晚,在一阵吉普车的喇叭声后,在万丈盐桥上我们依着首长的吉普车眺望,我们看到在首长消失的地方出现了茫茫的大海,在那辽阔的海面上我们看到了层层楼阁。我们知道,当风和日丽的日子,在柴达木盆地的察尔汗盐湖上,往往会出现这种海市蜃楼。
我们并没有等待首长的归来,在和那个络腮胡子又吸了一支莫合烟后,我们就开车赶回兵站。在我们的卡车沿着光滑如镜的万丈盐桥离开时,我们又朝正在消失的海市蜃楼看了一眼。我们知道,在那美丽虚幻的景象下面,就是广阔的受风沙侵蚀的盐湖。在那里,盐类和泥沙混杂凝结,我们只有打开褐色盐盖,才能看到雪白晶莹的盐粒。那一天,我们本想着能在兵站再次看到那个寻找妻子的驼背首长和他长着络腮胡子的司机,但是,我们从此却再没有他们的音讯。当然,我们也不知道那位驼背首长找没找到他年轻美貌的妻子。
按摩师
前年我们在沙依巴克区黄河路上的赛里木大酒店附近的足疗养生会所打工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名叫胡阳的按摩师,由于他和我们同是毕业于洛阳陈氏按摩职业学校,所以我们的关系不同寻常,比如中午顾客较少的时候,他就会约我们一同到苏氏牛肉面去吃饭。有些时候我们会陪着他多走几步到五一路上的马有布牛肉面,或者到更远一些的吐鲁番路上的和记全味面。总之,我们吃的全和面有关,即便是我们打车穿过钱塘江路往南到阿里路上的山东饺子馆,胡阳也会问一句,有面吗?胡阳的口味或许和遗传有关。胡阳生活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从来都不多说话,无论干什么都是一个字。比如带我们到面馆里,坐下来之后他对服务说,面!等面上来之后,他说,吃!等吃完后他用纸巾擦一下嘴推开椅子站起来说,走!胡阳的干练给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我的眼睛稍微通点路,所以每次出去都是我走在前面拉着他手里的导盲棍,他的头则习惯性地往右首扬起来——如果你留意,会注意到可能只有我们盲人才会有这样的习惯——如果他不是戴着墨镜,你肯定会看到他翻出的眼白来,可惜的是——据我们店里的同事议论,胡阳什么时候都戴着墨镜,即使是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给人按摩也是这样——你没法看到他的眼睛。然而他的手艺确实出色,我们店里所有的按摩师都曾经受过他的培训。起初我们都不服气他——但这是老板的命令,老板用嘲讽的口气对我们说,你们,差远了——当我们躺在床上接受胡阳传授经验时,他会说,按!他的指或掌就在我们身体的某个部位有节奏地一起一落,他一会单手,一会双手,或肋下或腹部,指指点穴掌掌到位,那手法丝毫不亚于我们的导师陈双锁。等传授过“按”法之后胡阳又说:摩!他就这样一字一法地传授,推、拿、揉、捏、颤、打,按摩八法,招招独特,真的好。比如他的颤法,迅速而短促,每秒钟的颤动都在10次左右。最出众的是他的打法,手劲轻重更迭软中有硬刚柔相济,从一秒钟两下逐渐加到八下,先慢后快,完后你会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舒服和轻松。他对治疗腰肌劳损、肌肉萎缩和偏头痛尤其见长,一个疗程下来,保准你大见成效。通过实践我们都打心底里服气,就私下里称他老大。我们老大的手艺在整个乌鲁木齐都是有名的,许多达官贵人都会来车把他接出去按摩,要么是长江路上的伊力特酒店,或者是五一路上的鸿福大饭店、奇台路上的银星大酒店、新华南路上的格林豪泰酒店,还有更远一些的位于中山路上的东方王朝酒店,位于红旗路上的有着大型餐饮及繁华娱乐的旅游涉外的城市大酒店。总之,不讲远近胡阳去的都是我们只听说过没有去过的豪华酒店,为此,就连我们老板也让他三分。可有一天,几个警察突然闯进我们的会所里,把正在给客人按摩的胡阳给抓走了。
胡阳被抓走的消息是老板告诉我们的,我们听到都感到吃惊。为什么,他是个杀人犯!杀人犯?这消息就更让我们吃惊。十二年前发生在高新区的那起杀人案你们听说过吗?没有。看看,这么大的案子你们就没有听说过?当年有一个名叫谭祖豹的亿万富翁被人杀了,案发后他的合伙人就失踪了,这个人就是胡阳。就是他?对,就是他,你们知道吗?他也是个亿万富翁。他是个亿万富翁?老板的话更让我们吃惊,那他,怎么就把他给杀了?这个胡阳,哎,当然,他那个时候还不叫这个名字,胡阳是他后来的化名,他和那个姓谭的祖籍都是山西运城,运城你们不是知道吗?离你们河南很近,要不后来他怎么去了洛阳学按摩?1998年的时候胡阳和姓谭的签订协议,入股投资筹办高新区轻纺辅料综合市场,那姓谭的任董事长。可是后来因为资金的事儿俩人发生了冲突,这个胡阳要求退还股金,那个姓譚的不同意,结果这个胡阳出了五十万找人把那个姓谭的给做了。案发过后他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最初传说他像他的许多师兄弟一样去了国外,谁想到他会跑到洛阳学习按摩,更没有想到他在我这儿一待就是三年,唉……我们老板停下来呷了一口毛尖茶说,你们知道吗?其实他很多时候是出去会老婆。去会老婆?那可不是,我想着他已经把许多机关都买通了,要不到现在才来抓他?老板,你怎么知道他买通了?这还用问吗?如果没有买通,在人家眼皮子底下会老婆都会了三年了,会不知道?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个高人,你想,一个亿万富翁……
我们对老板的话都有同感,胡阳确实是一个才智过人的角色,就我们所知,他不但记忆力非凡,而且是个十分注意细节的人,就连我们盲人看的电子书他都会阅读,方舟子你们知道吗?胡阳习惯性地往右首扬起来说,就是那个到处打假的人,我们读的书都是经过他验证的。后来我们老板在电视里再次见到了胡阳,那个时候他正在接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据我们老板说,在审判长宣判他死刑的时候,胡阳那双明亮的眼睛眨都不眨。这我们相信,胡阳不止胆量过人,而且注意细节,在他每次带我们出门时,总会把他的帆布包像我们一样从右肩上斜挎下来,可是我们所有的人从来都没有接触过他的帆布包,也从来没有人知道他的帆布包里隐藏着什么。
赌 玉
在离开阿克苏之后我们才发现,我们把表哥看丢了。我们焦急地分头往列车的两头去寻找,向遇到的每一个列车员询问,最后连列车长和乘警都惊动了。列车长让身边的乘警和阿克苏车站联系,一边向我们询问我们表哥的基本情况,准备让播音员向K9788次列车的全体乘客寻求帮助。他叫什么名字?郑光明。他有什么特征?怀里抱着一块糖皮籽料,口里流着口水。哦……那个睡在中铺的胖子突然从铺上折起来朝我们问道,你们是不是从和田过来的?对呀。你们找的是不是赌玉赌傻的那个?我横了胖子一眼说,你才赌傻了。哦……对不起,唉说说,胖子说,他怎么回事?
我们从和田出发向南,一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边采玉一边沿着玉龙喀什河岸边的崎岖小路前往黑山。传说中融化的昆仑山雪水每天下午汹涌而过之后,在阿格居改山谷满河床的冰块或砾石之间,你会看到无数的美玉映射着太阳的光芒。那个让采玉人梦寐以求海拔在五千米雪线以上的地方不但冰川和巨砾遍布,而且时常会有山坡崩塌,所以很少有内地来的陌生人到达那个盛产玉石的地方。果然,在距离阿格居改山谷大约三十公里的喀什塔什乡,我们就停下了脚步。起初我们以为是河床里被踩翻的砾石碰伤了表哥的腿,但事实却是我们表哥的膝盖关节旧病复发。表哥坐在一块灰白色上的砾石上龇牙咧嘴地说,看来我是没这个命,这还没沾边呢,腿就疼起来了。
看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湍急的河水,我们也感觉到了那个还没有到达的冰川所带来的寒气。在这之前,我们所有的颍河镇人都知道表哥家那座两层小楼是他采玉采来的,却没有人知道,表哥为了采玉时常要趟冰凉过膝的河水到河中间的布满砾石的沙洲上去而得了严重的关节炎,更没有人知道表哥在这儿吃的是什么苦受的什么罪。为了采玉,表哥不但沿着墨玉与和田之间的喀拉喀什河往北到过这条以盛产墨玉出名的河流汇入和田河的入口,而且还沿着和田与洛甫之间的玉龙喀什河往南到过喀什塔什乡。当我们兴冲冲地从喀什六运公司边上的天南客运站坐车到达和田,又转乘市内10路车来到玉龙喀什河桥头,在当地人的指点下沿着河边小路往上游走了两公里的河岸上一间地窝子里见到躺在床上疼得喊叫的表哥时,真的让我们感到意外,没想到许多远道而来的冒险家都住在河边自己搭建的棚屋里或者表哥住的这像狗窝一样的地窝子里。表哥从地铺上坐起有些生气地看着我们说,恁还以为满河床的都是玉?
我们说,你信上怎么说的?在月光下,只要你在河里看到有东西在闪耀,那肯定就是玉。表哥苦笑了一下说,玉是多种矿物质的集合体,透光度差,当然会反光。我还说过你在一块石头上滴—滴水,如果水滴长时间不扩散,那也是玉!这是一般识玉的方法,可捡到捡不到玉,那是你的命。表哥说着伸手把竖在身边的锛扔给我们说,不信恁去挖。有的都来这儿两年了一块也没捡到。那是玉,成色好的一块能卖十几万,那能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捡的?可生气归生气,表哥还是拄着拐带我们去认识和他相邻的来自天南海北的采玉人,还自己掏腰包一人给我们买了一把锛让邻居老孟带我们到河道里的砾石滩上去碰运气。谁叫我们是姑表兄弟呢?等表哥的腿能着地了,他还带我们去玉龙喀什河大桥边上的玉石交易市场,不但教我们认识什么样的是山料、山流水和籽料,而且还站在人家的店铺前偷偷地教我们识别籽料的皮色,什么糖皮、石皮、色皮,等等。真是奇怪,我们看到的和田玉籽料不论大小圆方,或者长的短的细的粗的,没重样的,色彩也好看,什么秋梨皮枣红皮虎斑皮葵花皮鹿皮桂花皮,都快把我们给看晕了,末了表哥还通过华梦玉行的老板带着我们去看人家赌玉。
一个大腹便便约莫五十岁左右的胖子花了六十万,从一个当地商人手中买了一块重达15公斤的山料,从山料一角打开的小天窗上我们能看到质地细腻宛若羊脂的玉石。当那块山料放上机床被哧哧的电锯拦腰切割的时候,我们发现表哥浑身都在哆嗦,那被切的仿佛不是石头而是他的肢体。等山料切开后我们就听表哥轻声地惊叫着,垮了,垮了……如果不是我们扶着他差点就瘫下去。随着众人的惊讶声,我们看到那块被切开的山料的表层满是黄色的脏斑,其中还有裂纹和黑点,完全没有了窗口上那柔和如脂的光泽。那个胖子倒是个大玩家,虽说他额头上也布满了细汗脸色也有些苍白,但他还算镇静,他看了一眼玉店的老板说,还切!那店主就把其中的半块放在电锯下,当金属锯齿在山料中又发出哧哧声时,表哥的指甲都抓到我胳膊的肉里去了,这次切的仿佛不是他的肢体而是他的头颅。当那被切的石料闪开后,我们看到石面中间的部分乳白而细润,像涂了一层蜡,天色下闪耀着玉液之光泽,当时所以在场的人都同时发出了惊叹,表哥脱口连连叫道,赢了,赢了……赌玉的仿佛不是那胖子而是他,他一边叫还一边搓着双手,这下赢了……他整个人像刚从死亡里逃脱一样兴奋。在我们回住处的路上表哥还沉浸在刚才的场景里没有清醒,表哥说,和青玉、墨玉、黄玉相比,这白色的和田玉最名贵,白玉里的羊脂玉又比青白玉高一筹,这回恁算开眼界了,刚才切开的就是羊脂玉。恁知道一副羊脂玉手镯眼下值多钱吗?二百万,至少二百万,恁知道刚才那块玉能加工多少副吗?至少十副。这就叫赌玉,知道吗?赌!输了,就倾家荡产;赢了,那就是千万富翁!表哥说着朝浑浊的玉龙河水里吐了一口吐沫。然后在身下的砾石上蹲下来,像丢了钱包似的在砾石里瞅来瞅去,可我们没有在那儿看到羊脂玉。表哥说,这赌玉需要本钱,百儿八十万都是小钱,我们去哪儿弄?
没有本钱赌玉,我们就只好去河滩上的砾石堆里去挖玉,可附近的河滩都挖套了,我们撅着屁股在砾石堆里扒一天,眼都瞅花了也看不到一块哪怕是生了色皮的石头。等表哥的腿好了一些,他就领着我们往上游走,可这次同上回一样,我们刚到喀什塔什乡,他的关节炎就犯了。我们只好从维族老乡家里租了一辆毛驴车,把表哥拉回到我们出发的地方。我们把表哥安置好,就一天一天地往河道里跑,每天一早扛着表哥给我们买的挖玉的锛,撅着屁股在砾石里挖一天,晚上回来时怀里抱着那把锛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可是回到表哥的地窝子里看到表哥企盼的目光,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又一人扛着一把锛出发了。这一天我们正坐在河道里的砾石堆上就着凉水吃早上带来的馕,就见老孟骑着一头毛驴朝我们跑来,人还没到就朝我们喊叫起来,起初我们还以为他采到了玉,可他带给我们的却是我们表哥赌玉赌垮了的消息。老孟说我们表哥十万块买了一块五公斤重的山流水,他看准了里面会是一块好玉,可没想到一下就赌垮了。我们当然不信老孟的话,我们表哥从来没有给我们说他手里有那么多钱,再说,他也不会背着我们自己一个人去赌玉呀?可事实却出乎我们的意料,等我们回到表哥的地窝里的时候,他不但嘴里流着口水,而且双目痴呆。由于当时在场的人都在看那块被切开的山流水,却没有一个看清表哥是怎样倒下去的,等梦华玉行的老板回头询问表哥是不是把那块“白魔”再切一下时,我们表哥已经坐在了地上,裤子都被他的尿液浸透了。
看看,我没说错呀,还不是赌玉赌傻了?我们不能不承认那个胖子说的是事实。这时列车长过来说,找到了,他在阿克苏丢了车。哦,那我们怎么办?胖子说,新和到阿克苏的时间是两个小时零44分;从新和返回阿克苏最早的列车是从乌鲁木齐开过来的5827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次列车到达新和的时间是凌晨两点半左右,咱们到新和的时间是22点45分,两个多小时,赶回阿克苏,你们还来得及。
纪念碑
两天前我们就计划着来看老师,可这天上午等我们赶到市总医院肿瘤病房时,老师却不知了去向。医院里的护士比我们更焦急,她们把应该寻找和查问的地方都查过了,就是没有他的行踪。你说,他人瘦得站都站不稳,能到哪儿去呢?我们意识到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的老师一定是去了墓地。我们匆忙驱车赶到市区西边成吉思汗山脚下小西湖墓地的C区时,在飘扬的雪花里我们看到许多前来祭奠的人,在人们三三两两驻足的每一方白色的墓碑上都镶嵌着一张稚气未脱的孩子的面孔,在那些墓碑的下方镌刻着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的同样的时间:1994年的12月8日。可是我们找遍了墓地问遍了所有前来祭奠的人,却没得到我们老师的信息。一个被肝癌熬尽的油灯一样的生命,在这寒风四起的日子他能到哪儿去呢?难道在我们来市里的路上老师赶去了农场?可说好的是等我们把那座纪念碑塑成之后来接他的呀,难道老师有些等不及了?很有可能。
十六年来,我们的老师一直都为在那场大火中丧生的遇难者在人民广场上建一座纪念碑而奔走,文革时期曾经在颍河镇中学教授绘画的我们的老师连纪念碑的图纸都设计好了。遇难者纪念碑是仿照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来设计的,在纪念碑底层的周围是那些像鲜花一样年龄的孩子们的浮雕,为了征得政府的支持,在纪念碑的正面,我们的老师特别选用了政府当年为遇难者发出的讣告里的词语:
“12·8”特大恶性安全责任事故中的遇难者永垂不朽!
在纪念碑的另外三面,老师看着我们说,然后再雕刻上325名遇难者的名字。为了这座计划中的纪念碑,我们的老师无数次地奔走在相关的各个部门,他甚至四处游说为修建纪念碑募捐。一家盐湖有限公司出于道义为将要修建的纪念碑资助了一百二十八吨原盐。可是捐赠的原盐无处存放,老师只好拉到我们农场,我们当然全力相助,因为我们从内地到克拉玛依来承包土地,都是因为有老师的介绍。1984年,我们在陈州教师进修学校任教的老师受聘来到这儿的某所中学任教,等十年后那场因舞台纱幕被光柱灯烤燃的大火在当天的18时20分烧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刚从市总医院看牙出来。他知道那天他的学生和另外十几所中小学的七百多名师生正集中在市友谊宾馆,为迎接自治区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评估验收团举行专场文艺演出。当我们的老师赶到事故现场的时候,那里已经是一片混乱,我们的老师拼命用肩头撞着紧闭的卷帘门,发疯地踢门、砸门……真是惨不忍睹呀……每当讲起大火过后的事故现场,我们的老师都会眼含泪水,他颤抖着声音说,一闭上眼睛,孩子们的尸体就会出现在眼前,我无法忘记那些凄惨的场面,我们应该建一个纪念碑,把遇难的孩子们的名字都刻上去,我们要让这个城市记住那些亡灵和伤痛……
我们完全理解老师的心情,可是我们老师多年来的奔走没有结果,甚至连修建纪念碑的地点都没有确定下来。为了安慰老师,我们只好建议老师用他募捐来的原盐浇筑一座临时纪念碑。在老师的默认下我们出面请了一家建筑公司在我们的农场里搭建了一个框架,我们浇筑的方法是先把原鹽一袋一袋地化成盐水,浇铸在用木板扎成的模子里,等盐水结晶后再加上融化的盐水,然后再等待着盐水结晶……可是纪念碑刚刚开始浇筑我们的老师就住进了医院,他被诊断为肝癌,而且癌细胞已经开始大面积扩散。知道老师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们就一日紧一日地融化盐水,等我们把一百二十八吨原盐都化成盐水凝结再把四周的框架拆除,那座十二点八米高的用原盐浇筑的纪念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把我们都给镇住了。我们真的想给老师一个惊喜,可是老师比我们更迫切。等赶回农场,我们看到我们的老师正站在那座雪白的纪念碑前用一把刻刀雕刻着,那是一行字:
孩子们,不要动,让领导们先走!
这句著名的在火灾现场一个女领导对学生们喊出的话刺得我们的眼睛生疼,老师回过身看着我们说,耻辱呀……在老师颤抖的声音里那把灰色的刻刀从他手中脱落下来,有两行泪水从我们老师的眼角里像小虫子一样爬出来。
为了安慰老师,我们对临终的老师做了承诺,要把这座用原盐浇的纪念碑运到市中心的广场上去。在安葬了老师之后我们就四处活动,像老师那样我们也跑遍了所有应该去的部门,可是我们也像老师一样连一个安放纪念碑的地方都没有找到,哪怕是路边一个小小的公园。一眨眼,时光已经到了来年的夏季,由于天气炎热,那座用原盐浇筑的纪念碑开始融化,等到了第二年的十二月八日,那座雪白的纪念碑已经变得千疮百孔,我们老师雕刻在底层上的那些浮雕已经面目全非。我们伸手摸一下纪念碑,然后把手指放进嘴里,纪念碑上又苦又涩的原盐尖利地刺着我们的舌头,像刀子一样深深地扎到我们的心里去。
流放地
1971年秋天,我们从49团所在地盖米里克抽到喀什,在师部王副政委的带领下依照《兵团土地勘测制图规划》,参与对农三师所辖土地进行的实地勘测和绘图工作。在由从师部下属各团抽调的人员组成的测绘队里,有一个名叫刘期颐的人。这个不讲场合不讲地点都爱夸夸其谈的人给我们寂寞而艰苦的勘测生活增添了色彩,他近似病态的言语就是在吃饭时也不肯停下,他咬一口玉米面窝头说,盖米里克?你知道盖米里克什么意思吗?这谁不知道,就是维族老乡说的地窝子。可是……他把嘴里的食物咽下去看着我们说,地图上有盖米里克这个地名吗?没有,只有49团,以前你们那儿就没名,五零年农垦部队来这儿的时候没地方住,就挖地窝子……你五零年就到喀什了?我?那个身材彪悍的中年人喝一口带有苦碱味道的开水摇了摇头说,我是1958年来的。1958年?对。我是劳改犯,被流放的。
这个坦诚而博学的人确实对我们构成了引力,即便到了夜晚我们在胡杨树下用野麻铺床时也想和他挨着。真是路途遥遥呀……在讲起从内地到南疆的往事时他的语气充满了情感,三天三夜的闷罐车,我们就像一群牲口,吃喝拉撒都在里面,只听火车咣咚咣咚地走,到哪儿了都不知道,等下了车一问,老天爷,乌鲁木齐,大西北。接着,又是三天三夜,这回是卡车,一直往南,翻越天山,要么是戈壁,要么是沙漠公路,我连苦胆水都快颠出来了,那罪受的,死的念头都有了……刘期颐!你歪嘴骡子卖个驴价钱,吃亏就在嘴上!要不,你会被打成右派?没错……刘期颐朝发出责难声音的方向看一眼说,我是被打成了右派,可我内心无愧,五七年让鸣放的时候,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说要讲民主,要讲法治,难道这有错吗?你就是不讲阶级斗争!好,我不说。可是……刘期颐把目光收回来又说,你不让说,那现在干什么呢?他的话我们都有同感,在这无边的戈壁上,说话确实是我们排解寂寞和孤独的一副良药,在这戈壁上,在这人烟稀少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就是碰到一只野狗我们也有述说的愿望,更别说是人了。要不,他这样一问,就连王副政委也不说话了。刘期颐说,别说卖个驴价钱,就是卖个狗价钱,我也得说。你说,我人都活到这个境地,还在乎什么?不错,这个没家没室被流放到边疆劳动改造的人,他还有什么可在乎的呢?可这个歪嘴骡子在地理勘测和绘图方面确实是个专家,这位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的高材生有着让我们佩服的在复杂地理环境里作业的经验,要不我们王副政委会把他抽来?尽管夜间刘期颐受到了打击,但第二天我们一骑马上路,他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但后来有件事却改变了刘期颐。
这年深秋的一天,我们勘测队在巴楚境内的小海子水库附近救了一个昏倒在路边的男孩,那个嘴唇干裂骨瘦如柴的男孩一看就是极度缺少营养,他有气无力地躺在我们临时居住的地窝子里,刘期颐在他布包里的那本64开大小的红皮毛主席语录的空白处,发现写着一些我们熟悉的地名:巴楚、阿纳库勒、阿纳库勒牧场、曲许尔盖、英格勒吐格、科克塔勒、喀拉黑其尔、克拉克勤农场……刘期颐用他粗糙的手指指着那些用钢笔记下的地名对照着我们那份正在绘制的地图说,你们看,这是从红海水库顺着喀什噶尔河走的,往西偏南,一直到拜库勒水库……
刘期颐放下手中的地图看着那个躺在地铺上的孩子说,你记这些地名干什么?那是我们走过的路。你们?还有谁?我妈妈。你妈妈,她人呢?她走丢了。在哪儿走丢了?牌楼农场附近。牌楼农场?我们看到刘期颐拿着毛主席语录的手哆嗦了一下,我们都知道那个在喀什境内最大的劳改农场正是刘期颐被抽调的地方。怎么就走丢了?那天我们走着走着,突然刮起了沙尘暴,妈妈让我抱着路边的一树棵,可是等沙尘暴过后,妈妈就不见了。你妈就这样丢了?那孩子没有接我们的话,片刻,却有两行泪水从他的眼睛里流出来。刘期颐伸手给孩子擦了一把泪水说,你们从哪儿来?河南。河南什么地方?陈州。陈州?我们看到刘期颐拿着毛主席语录的手又哆嗦了一下,你们来这儿干什么?找我爸爸。你爸爸?我爸爸。你今年多大了?十三岁。我妈说,在我没出生的时候,爸爸就被送到这儿劳改了。再也没有回去过?没有。要不妈妈怎么会领着我到这儿。哦,你们是怎么来的?先坐火车到乌鲁木齐,然后又坐汽车,我们先到了一个叫三岔口的地方,然后往南,就到了巴楚……
哦,我知道了,你们就这样一个农场一个农场地往下找?孩子对他点了点头。刘期颐的目光又落在了手里的毛主席语录上,他一边用手指着我们正在绘制的地图一边对照着,克孜勒努尔林场、其干布拉克、帮克尔水库一闸,哦……他抬起头来看我们一眼说,他们这是从拜库勒水库一直往南,到了草龙库勒水库,那么接下来呢?肯定是要沿着协海尔吾斯塘渠继续往东南方向走。科克塔勒、且克且克、克孜勒库木、塔勒木、瓊库尔恰克,看看,果然不出所料,再接下来呢?是从英吾斯塘,到红星水库……刘期颐停下来看着那个孩子说,你妈妈是不是在从阿瓦提去牌楼农场的路上出的事儿?孩子又朝他点了点头。那么,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我要找妈……孩子话没有说完,泪水又从他眼睛里流出来。
刘期颐伸手又给孩子擦了一把泪,然后看着我们说,他肯定是一个人从南方折回来,你们看……刘期颐翻着那本毛主席语录查看着孩子记下的地名,果真是这样,他从麦盖提出发,下面就是前进水库附近的15连、12连,接下来就是9连、43团2营、良种2连、5连、农建1队、43团场。再接着下来呢?13连、10连、4连、2连、45团场,我的老天爷,这些全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上,他一个孩子是怎么走过来的?16连、12连、11连、13连、14连、15连,玛亚克勒克、艾力木阿吉托喀依、苏盖库都克林场、胡杨林场……他沿着叶尔羌河往西北走,三盆河、库热勒里克、皮特克库勒、阿其库木,老天爷呀……
我们听到刘期颐手里的地图因他手臂的颤抖而发出了沙沙的声响。从那天起,刘期颐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那个孩子,他一直待在地窝子里照看他。就这样一直到了第三天下午我们从野外勘测回来,却发现刘期颐和那个孩子都不在了,不知了去向。我们都在私下里猜测,刘期颐一定是带着那个孩子回头向南,帮他去寻找他的母亲了。王副政委看着空无一人的地窝子说,他们能去哪儿呢?他回身朝无边的沙漠看一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就再也没有说话。
追捕者
在夏季一个炎热的中午我们登上了西去的列车。在这之前,我们从罪犯居住在颍河镇的小姨子家里的一个小本上发现了一组数字,依着这个数字的号段我们查出这张工商银行卡的持有者就是罪犯的老婆。这张银行卡4月份在杭州取过钱,六月份在格尔木取过钱。随后,我们又发现了一个记在罪犯岳父家墙壁上的区号为0979的电话号码,这个打到罪犯岳父邻居家的电话同样来自格尔木。各种迹象都显示出那个名叫王中德的杀人犯潜逃的地点。在第三天的下午两点十分,我们乘坐的列车到达格尔木,我们脚一着地就从罪犯使用过银行卡和电话的地方开始追查。等到这天下午七点有目睹者反映,嫌疑人已在当天上午的十一点离开了格尔木。
我们接着就严格地盘查格尔木的几个出口。往回走去西宁,有两班汽车,一班火车;往北到敦煌有一班汽车;往西到拉萨有一班汽车。在调查过程中有目击者反应有一男一女两个河南口音的人带着两个小孩去了拉萨。我们立刻乘车奔赴拉萨,并且开展了地毯式的追捕,我们查过了拉萨市区和周围方圆二百公里的地方,就连布达拉宫下面的地牢我们都没放过,可是由于侦破工作没有得到丝毫的进展,两个月后我们只好回到锦城。
在案情分析会上,刑侦专家指出了我们的失误。王楼46岁的村民王中德出外打工回来,怀疑邻居王有权强奸了他老婆。他要找王有权理论,可这个邻居就是不给他见面,他一气之下,在一天早晨把王有权去上学的孩子用刀砍死。案发后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王中德已经和他老婆带着两个女儿和一个三岁的男孩潜逃。刑侦专家说,你们说罪犯带着两个小孩,这就不对了,明明是三个孩子嘛,那个男孩去哪儿了?
这年的九月底,我们又重新回到我们已经熟悉的那座游牧城市。我们分析,除去两万驻军,格尔木只有五万居民,罪犯只要走,客运信息上应该有他们的痕迹。这次我们的主要侦破任务首先是要吃透那一天的客运记录,我们要把罪犯离开格尔木那一天汽车、火车上所有的司乘人员全都访问完。侦破工作整整进行了二十天,最后我们终于从发往敦煌的客车上的女乘务员那里查知,那天是有一个身背铝锅的操着河南口音的男人和一个没有说话的女人带着两男一女三个孩子乘坐了他们的班车。
这一年接近十一月的时候,在敦煌迎接我们的是一场罕见的大雪。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我们在车站周围的饭店、出租车和推三轮的人员中间展开调查。十天过后,我们侦查的目标扩展到当地的出租房屋和菜市场。敦煌是一个居住松散的城市,我们在大面积的范围内清查了半个月也没见成效。最后,我们决定清查当地的学校和医院。我们分析,罪犯的三个孩子,大的十二岁,二的八岁,都是学龄儿童。而他最小的孩子才三岁,他们从中原来到这里,肯定会不服水土。在接近十二月的这段时间里,我们把当地的学校、医院清查了一遍,可是仍然没有得到罪犯的任何的信息,我们只好把搜查的目标扩大到敦煌市周围的卫生所。
到了這年的十二月中旬,敦煌再次降雪,在零下24度的气温里,我们踏着积雪行走在敦煌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在这一年倒数的第四天,我们在一个偏僻的卫生室遇到了一个中年医生,他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女的带着两个孩子看过病,女孩八岁,男孩两岁多。我们从医生留下的记录里看到,那个女人留下的并不是她的名字,但却姓王,而且是河南口音。这个信息让我们兴奋起来,我们开始以卫生室为点半径画圆,先切进去一千米,开展地毯式搜查。在第二天的下午,我们搜查找到这个卫生所所在的村委会。在风雪里,我们逐渐接近那个建筑在戈壁之上的房屋,我们远远地看到从房子里走出来一个人,无论他的走势和动作,都像那个我们甚至于在梦中也在追捕的罪犯。那个人一看远远地有几个人过来,他拔腿就跑。
在那个风雪交加的下午我们在茫茫的戈壁上追击了二十公里,那个曾经在野战部队服过役的罪犯比我们更有行走的经验,在渐渐暗淡下来的天色里,我们最终失去了目标。我们劳累过度的身子在无边的戈壁上一个个倒下来,从我们消瘦的面孔上生长出来的胡须像在中原深秋里的茅草一样在寒冷的风雪中摇动着。而那个从我们视线里消失的罪犯,像夏季里一滴在炎热的阳光下被蒸发的水滴,从此再也没有音信。
诗 人
一直到下午4点车过羌塘草原的时候,我们才看清她的真正面目。自从下午一点十分我们登上T24次列车准备离开拉萨,那个女孩就一直在我们对过下铺上面朝里躺着,她盖在被子下耸起的胯部和滑落的细腰形成的落差曾经让我们想入非非,但她苍白的面容和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像车窗外从措那湖上空落下来的雪粒一样的忧伤与迷茫让我们无法分辨出她实际的年龄。十八岁?二十岁?或者……我们真的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有一会儿,我们也曾经为把从她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忧伤与迷茫比喻成车窗外划落的雪粒而感到羞愧,不说迷茫,忧伤怎么能比喻成雪粒呢?但是,从她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忧伤真的像击打在窗子上的雪粒一样在我们心里击起了嚓嚓的声响。下午五点,在起身离开几分钟之后她就一直坐在窗前看一本厚厚的书,这之间她偶然还会在被裁成64开的纸片上写下一些文字,或者久久地面向车窗发呆。车窗外梦境里冰晶一样的唐古拉山峰和接下来出现在可可西里雪原上的藏羚羊或者牦牛,使她映在车窗上的面容更加忧伤,在我们的惊叫声里她会回过头来看我们一眼。我们说,不可思议,在可可西里还能看到飞鸟。但没等我们的话音散开,她忧伤迷茫的目光又转向窗外行驶在青藏公路上仿佛没有尽头的军车。这样的情境一直持续到车窗外的天色渐渐暗淡下来,等她把目光收回来就又落在了那本厚厚的在白色封面上印有一副黑白插图的书籍上。夜间,大约十二点钟列车上的灯光熄灭我们入睡时,她仍旧那样坐着。等从梦中醒来我们发现她仍然在那儿坐着,仿佛她从来就不曾入睡。那会儿列车已经停了下来,我眼睛惺忪着从铺上下来随口嘟囔了一句,到哪了?
德令哈。她梦呓一样的声音从我们的感觉里滑过。德令哈?她肯定地说,德令哈。那时她趴在茶几上,整个身子朝车窗倾着。等我上完厕所回来列车已经开动,在回到铺位上之前我看到她仍然保持着刚才给我说话时的姿势面朝窗外。凌晨五点的德令哈在车窗外的黑夜里沉睡着。等再次醒来我们发现她的铺位上空无一人,但那本厚厚的书籍仍然在茶几上放着,在明亮的车窗下,我们看到了那本书的名字:《海子诗全集》。一些她写过字和没有写过字的纸片不知什么缘故散落在地板上,我探身朝车厢走道左右看一下,犹豫片刻,最后还是蹲下来把那些散落的白纸一张一张地捡起来。出于好奇,或者是出于某种无法言说的因素我浏览了一些她写在纸片上的文字:海子,原名査海生,生于1964年3月24日,在农村长大。1979年十五岁时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83年自北大毕业后分配至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工作。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年仅二十五岁……海子?就是茶几上那本书的作者?我朝茶几上看一眼目光又落在了第二张纸片上:《途经德令哈》:几颗启明星/牵出高原辽阔/夜晚我在德令哈/想起海子/他穿越旷野/打湿小站女人的棉衣/等瘦一匹河岸的老马/他抖落身影邀请石头/点亮自己的头颅/烧红牛羊的耳朵/被罪恶刺伤了眼睛/这个举杯饮血的孩子/来过德令哈/他一个人放牧群山/吮吸羊奶/他一个人从孤灯摇曳中启程/嗒嗒涉冰过河 2010年5月26日5:35于途中。
她也是个诗人?很显然,她一定喜欢那个我们仿佛听说过的名叫海子的诗人和他的诗。这时我听到身后有轻微的呼吸声,等我回过身来看到她已经站在了我的面前,我不好意识地笑笑扬了扬手里的那叠纸说,掉在地上了。谢谢。她说着从我手中接过那叠纸又重新放在茶几上。你字写得好。是吗?她在床铺上坐下来,使我没有想到的是她又拿起那叠纸递给我说,好在哪里?我没想到她会对那句我随便说出的或许是为了排解我内心尴尬的话那么在意。我有些不知所措地拿着她递过来的纸而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她的字到底好在哪里?我的目光只好落在手中那叠纸上,然而写在最上面那张纸的是一组让我感到意外的词组:斧劈、上吊、开枪、溺河、投湖、蹈海、跳楼、卧轨。她肯定对我的表现感到失望,我听到她叹了一口气。但是那些刚刚从我脑子里划过的特殊的词语使我注视她的目光产生了疑问,我指着纸条说,这什么意思?
每一个词语代表了一种自杀的方式,结果他选择了最后一种,卧轨自杀……我在她梦呓一样的话语里哆嗦了一下,那一刻,我敢肯定她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如果你当时在场,肯定也会像我一样从她茫然的目光里做出这样的判断。她说,这八种自杀方式都出现在他的诗里,你看……她说着從我手里接过那叠纸,从中抽出一张纸条递给我。我在纸条上看到了下面的文字:我戴上帽子穿上泳装安静的死亡/在七月我总能突然回到荒凉——海子,《七月的大海》;伏在下午的水中/窗帘一掀一掀/一两根树枝伸过来/肉体,水面的宝石/是对半分裂的瓶子/瓶里的水不能分裂——海子《自杀者之歌》
等我抬起目光,她又接着说,1989年3月25日开始,他在山海关徘徊了一个下午和一个上午,到了第二天,也就是3月26日中午,他开始向卧轨的地方走去,而他最终选择了黄昏时分。你被劈开的疼痛在大地弥漫,这是他在临死的十天前写在《春天,十个海子》里的诗句。他写这样的诗句并非偶然,其实,死亡已经在他内心徘徊了很久。从25日一直到26日的黄昏,他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度过的?这些我们都能在他以往的诗里找到足迹,即使是黄昏,我也能在他的诗里找到死亡的意象……
我敢肯定,如果当时你在场也一定能像我们一样感受到她仿佛在梦中的情景,如果你是外人,从她的话语里你一定会断定我们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她一边说一边又递给我一张纸条说,你看。我们又在她递过来的纸条里看到了如下的文字:正是黄昏时分/无头英雄手指落日/手指落日和天空/眼含尘土和热血/扶着马头倒下——海子《太阳》)。在他的诗里,他卧着的铁轨也是死亡的景象,那铁轨就是不断出现的天梯。天梯?对,天梯,你看,他在《太阳》里开头是这样写的……说着,她又递给我一张纸条:在天空和大地之间/天梯静静地支撑在中间。他认为天梯是进入天堂的必经之路,我站在天梯上/我看见这天空即将合上。所以他选择了铁轨不是偶然的。
年轻轻的,他为什么要死呢?爱情。爱情?对,这是我的理解。他一生爱过六个女人,或者说是六个女性,他对每一个自己爱过的人都充满了热情,给她们写下了让人难以忘怀的诗篇,你看……说着,她又递过来一张纸条: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今夜我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滴眼泪/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德令哈……今夜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我把石头还给石头/让胜利的胜利/今夜青稞只属于自己/一切都在生长/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海子:《日记》。可是她们都流星一样从他短暂的生命里划过,而且每次结果都是一场灾难……
她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理解和关怀,比如他在铁轨边徘徊的时候,如果那六个女人之中的某一个出现在他的面前,或许他就不会死,他的生命就会呈现出另一种情景。比如现在,我们坐在前往西宁的列车上,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有谁知道我在想什么,有谁知道我被什么所困扰?实际,很多的时候,我们人都处在孤独之中,我们人需要关怀,需要理解,可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处在孤独之中……
她梦呓一样的话语确实使我们感到交流的困难,但是我们多少也能理解一些她的思想,这个在我们看来处在为某件事情比如失恋或者失去心爱的人之类事情所产生的孤独、忧伤和迷茫这些一时难以排解的情绪里的女孩,让我们产生了一些怜惜之心。我们看了她一眼,试着和她交流。你从哪儿来?喀什。喀什?不知道吗?知道,当然知道,那个在我们看来同样神秘的地方。由于喀什的出现,我们从她的眼神里感觉到了她正在慢慢地从梦呓里清醒。我说,你这是准备到兰州再往西走?不,我要在西宁停一停。有家人在这儿?没有。有朋友在这儿?也没有。哦,是旅游。西宁有许多可玩的地方,东关清真大寺,还有许多小吃……你们……我们在这儿做生意。青海湖好去吗?青海湖?好去,火车站就有车……如果你想包车,就给我们打电话……我这样说着,拿起她放在那本书籍边上的圆珠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了一个电话号码,然后递给了她。
不知是我们过于热情,还是她已经从梦境中清醒过来,她拿着那张写了我们电话号码的纸条看了一眼,然后目光转向了车窗。在远处,是被初升的阳光照耀下的深蓝色的青海湖,从她映在车窗上隐约可见的面容里我们仿佛又看到了她被忧伤和迷茫所缭绕,这样的情景一直从青海湖到上午十一点到达西宁车站,我们看着她背着一个桔红的旅行包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第二天中午,我们意外地接到了一个从青海湖景区打来的电话,说是有一个不知姓名年龄大约在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在游览青海湖的游轮上不幸落水身亡。我们驱车匆忙赶到事发地点,我们先在当地的派出所里看到了那个桔红色的旅游包,接着又在警察递过来的纸条上看到了下面的诗句:青海湖,请熄灭我的爱情!——海子:《七月不远——给青海湖,请熄灭我的爱情》。在那句诗歌的下面,我们看到了我写上去的那个电话号码。最后,我们在一条白色的被单下面再次看到了她。那时候,她苍白的面容上仍然残留着忧伤和迷茫。
责 编:朱传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