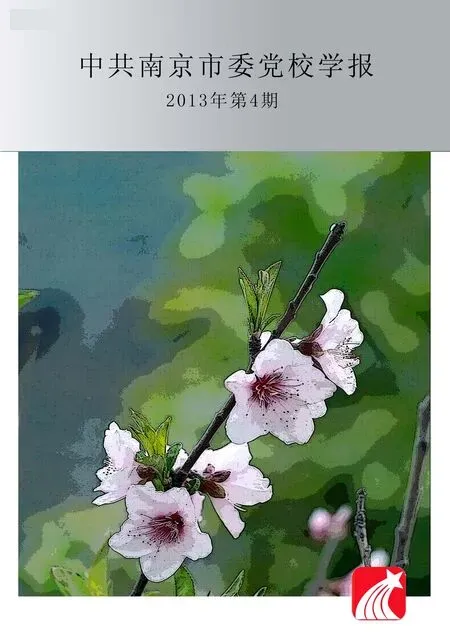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及其当代启示*
——纪念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争论三十周年
裴 勇
(南京大学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23)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是新时期我国哲学界一场重要的理论性和现实性的争论,涉及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异化问题讨论的是人的异化、社会主义的异化,它是人道主义历史观的重要观点之一,异化问题并不是人道主义之外的另一问题,而是因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因而与人道主义并列。
一、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争论的历史背景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学术性讨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便开始了。1983年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大会上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它引发了思想界的轩然大波,将这一争论推向了高潮。仅在这一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就达三百多篇。1984年胡乔木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报告,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权威总结。至此,全国范围内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基本结束。
这场争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历史背景。它是发生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变革”、“实行改革开放”[1]这一国内背景下,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苏联人道主义的传入也推动了我国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探讨。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化。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掀起了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反映在哲学上表现为:重提五四运动,反对教条主义和愚昧,反对“异化”。国内学术界掀起了学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热潮,集中表现为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人道主义。以真理标准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那段历史灾难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上仍然留下很深的阴影。有些同志从斥责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严重歪曲,从批评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左’的错误,走到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怀疑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地步。”[2]十年“文化大革命”,严重扭曲和践踏了人的尊严、人格,社会主义建设也遭到了极大地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们迫切地期望恢复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重提人道主义是对“左”倾思潮下全盘否定人道主义的拨乱反正, 是对“文化大革命”中种种罪行的清算。因此,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直接推动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兴起。
西方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思潮的涌入推动了我国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探讨。1923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提出了“物化”概念,对人类历史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作了人道主义的解释。“异化劳动”理论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重要内容,阐释了异化劳动的四种外化表现形式。由此,部分西方学者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思想最成熟的表现,此后的马克思便走向倒退,引起了早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的争论。前苏联也曾对人道主义展开广泛的讨论。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思想理论界鼓吹抽象的人道主义,淡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起步,这些思潮的传入对中国思想界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起了推动作用。
二、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争论的焦点
在这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争论的过程中,主要形成了三方观点:以周扬、王若水等为代表的一方认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是包含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以黄楠森为代表的一方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人类社会,不能笼统地否定人道主义,但也不能笼统地肯定人道主义,反对滥用“异化”概念,劳动异化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胡乔木则认为人道主义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要将二者区别对待,反对“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否定用“异化”论来解释社会中的消极现象。
(一)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王若水早在1980年便写了一篇题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一观点。王若水认为以往的哲学教科书很少提及人的价值、人的异化、人的解放,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创立唯物史观,正是从现实的人、实践的人出发。“马克思主义也是从人出发,但这不是费尔巴哈讲的那种名为现实而实则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实践的人,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3]薛德震认为在我国“谈人色变”的局面一定要打破。早在“文革”之前,人和人性问题的研究就已经是禁区。四人帮横行时期“不但人性、人道主义不能讲,连人和人生、人情和爱情也不准谈。”[4]
黄楠森对王若水关于“人是马克思主义出发点”持批判态度,认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有多种含义,并且质疑这里的“人”究竟指的是什么?“人指什么呢?指包括个人在内的人群或人类社会呢?还是个人?无疑,阶级、人民群众、人类社会的问题是共产主义理论要解决的问题,其中当然包括解决各个个人的问题,否则阶级、人民群众的问题就落空了。”[5]赵家祥认为如果把人当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则会将历史唯物主义同各种旧哲学相混淆,甚至把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降到某种旧哲学的水平。赵家祥指出不仅“抽象的人”不能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同样,“现实的人”也不能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徐建一也否定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一观点,他认为如果说“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那么“人”必然就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出发点。但是,马克思在论述他的政治经济学时,就十分明确地否定了这一观点。
胡乔木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中也对“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作了批评,指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观点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虽然主张“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人一再申明他们所指的“人”是现实的,并不是抽象的人,但是胡乔木认为这并不能改变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的实质,而且这个命题还包含着一个逻辑矛盾:“要说明人是‘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就不能把人看成是笼统的、没有分化和没有差别的,就需要说明人在其中活动的具体的社会关系,这就必须从具体的社会关系出发,而不能从‘人’出发。”[2]
(二)马克思主义是否承认人道主义
周扬、王若水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包含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需要人道主义。王若水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包含人道主义的,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需要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周扬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中指出:“我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之中,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6]汝信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笼统地和人道主义对立起来,更不能不加分析地把人道主义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虽然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完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包含人道主义的。
黄楠森则不同意周扬、王若水等的观点。他认为:“当马克思还没有完成唯物史观的发现,还没有完全摆脱旧思想影响的时候,确曾把自己的理论称为人道主义;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发现了唯物史观,实现了历史观上的革命变革的时候,就以这个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的指导,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并与人道主义划清了原则界限”。[7]邢贲思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使用人道主义这个口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一回事,更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包容人道主义。
胡乔木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中》指出人道主义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必须注意人道主义这两者的区别,以免造成意义上的混淆。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而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则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我们所要宣传和实行的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它立足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属于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这种意识形态”。[2]
(三)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异化
周扬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中》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存在异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广泛地存在经济、政治、思想领域中。“在经济建设中,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过去就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是我们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与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思想领域的异化,最典型的就是个人崇拜,这和费尔巴哈批判的宗教异化有某种相似之处”。[6]这些观点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极大地混乱,邓小平认为这是思想界的污染。1983年10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报告,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思想战线不能精神污染”,邓小平在报告中指出:“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判资本主义而在批判社会主义。”[8]
针对周扬等人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异化”的观点,施德福认为社会主义异化论是错误的,“它既在理论上又在实践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9]社会主义异化论在理论上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在实践上更是极为有害的。他认为异化理论既不能正确地说明社会历史,也不能说明社会主义社会。赵光武“社会主义社会是当今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沿,是迄今为止的社会历史上最进步的社会制度。但是,与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它的发展进程不可能是笔直的、平坦的;它的各个方面也不可能都是完美无缺的”。[10]他认为只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才能从根本上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才能认清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克服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消极现象。
胡乔木也批评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异化”这一观点。胡乔木在文中具体批评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经济、政治、思想领域的异化。宣传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的同志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条件,把异化这种反映资本主义特定社会关系的历史的暂时的形式,变成了永恒的、可以无所不包的抽象公式。然后,又把它运用于分析社会主义,从而提出社会主义的异化问题。胡乔木承认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有不少错误和挫折,也有不少的缺点和弊端,但是不能笼统地用“异化”论的思想来解释,“只有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过去的错误、挫折和现存的消极现象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才能针对不同情况制定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方针和办法。”[2]
三、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争论的当代影响与启示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在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后便戛然而止了,“这场争论虎头蛇尾,留下的是更多的分歧”。[11]但是这场争论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异化理论的研究,也纠正了一些学者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的错误倾向。直到今天,这场争论仍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针对性。
(一)百家争鸣: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繁荣发展
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中,有些学者一方面把“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当作新颖的观点来宣传,另一方面却又极力模糊“人”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应当认真领悟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精神实质,作出完整、准确的理解,避免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基本前提,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遵循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
学术争论是活跃学术气氛、促进科学繁荣的重要环节,也是判别真伪科学的重要手段。学术争论可以促进学术的研究发展, 促使人们对争论中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促进哲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主义在其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产生学术分歧和理论摩擦是在所难免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对待学术上的分歧和争论。在理论界开展学术讨论,可以明辨是非,纠正一些人思想中的错误倾向。因此,学术讨论是非常必要,也是极其有意义的。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繁荣发展的今天,必须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2]在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二)以人为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关于人的思想:“人之初,性本善”、“天人合一”、“民为贵”等。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一直没有把“人”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更没有进行系统的人学研究。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争论之后,人学逐渐诞生,中国理论界逐渐把“整体的人”作为研究的对象,开始讨论人学问题。关于人的主体性、人的权利、人的教育等问题日益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点。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它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就从根本上回答了“为什么发展”、“怎么发展”、“发展为了谁”的问题。“以人为本”不仅主张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更主张人是发展的根本动力。科学发展观之所以强调“以人文本”是为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以人为本”的提出从根本上是“为了充分肯定人对发展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突出人民当家作主这个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13]因此,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而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
“以人为本”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必须要正确理解“以人为本”和人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正如人道主义必须区分为世界观、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和伦理原则、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一样,我们也必须正确区分作为世界观、历史观的“以人为本”和作为伦理原则、道德规范的“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价值观可以被接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以人为本历史观则是唯心主义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正是把以人为本看成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观,而不是把它看成历史观。”[14]
(三)求真务实:理性看待当今社会中的异化现象
异化现象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对金钱的过度崇拜、对科技产品的过度依赖的现象。物质条件是个人生存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对金钱的过度追求必然会使人成为金钱的奴隶。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推进,科技异化越来越成为突出的矛盾,出现了过度依赖计算机、手机等科技产品的现象。人们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科技成果不仅与人本身相分离,同时还成为奴役人的手段,“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5]
异化现象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也必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亡。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否定了异化现象的出现。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从源头上杜绝了异化现象。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历史地长期过程,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我国当今社会中出现异化现象是必然的,但这种异化现象只是短暂地、暂时地而非永久地、长期地现象。
我们要正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下的异化现象,采取一些有效措施将异化现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首先必须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当生产力发展到“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以满足它的全体成员的需要”[16]的时候,异化现象必然会退出社会历史领域。同时面对当今社会现象中诸如经济的异化、科技的异化,观念的转变也是十分必要的。树立正确地世界观、价值观,减少对金钱、科技产品的过度崇拜、依赖。
参考文献:
[1]姜迎春.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综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175.
[2]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N].人民日报,1984-01-27.
[3]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86.207.
[4]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论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45.
[5]黄楠森.关于人的理论的若干问题[J].哲学研究,1983,(4).
[6]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N].人民日报,1983-03-16.
[7]北京大学哲学系编.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研究[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230.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42.
[9]北京大学哲学系.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研究[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84.
[10]北京大学哲学系.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研[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33.
[11]卢之超.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4).
[1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0-31.
[13]陈志尚.论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和意义[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1).
[14]黄楠森.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6.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