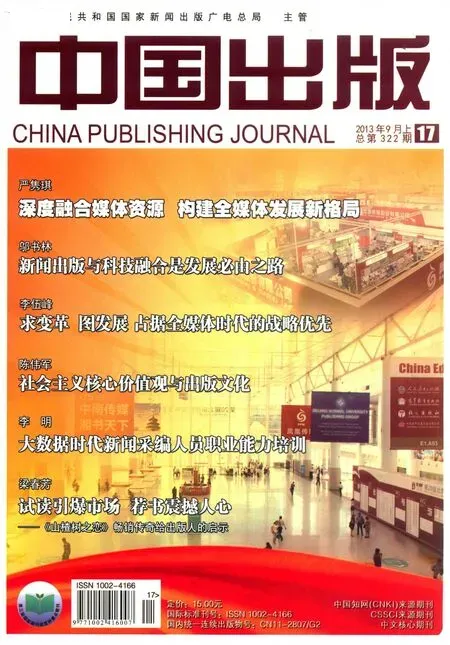出版引领:建构民族史诗整理探究新范式
文/张忠兰
2009年4月,贵州省紫云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发现,麻山地区苗族的一些歌师会在丧葬仪式上演唱“亚鲁”的故事。同年,“亚鲁王”被列入中国民族文化的十大发现。2010年5月18日,文化部公布的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新入选项目)中,由贵州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申报的“亚鲁王”,列入民间文学项目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6月,国务院批准《亚鲁王》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10月,新闻出版总署印发的《国家“十二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规划》中,《亚鲁王书系》榜上有名。2012年12月,《亚鲁王书系》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亚鲁王书系》分为《史诗颂译》《歌师秘档》《苗疆解码》三册,以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的新范式为出发点,以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整理编译为基础,分别从史诗《亚鲁王》本体整理编译出版的价值探究、史诗《亚鲁王》传承人歌师的情况调查研究、与史诗《亚鲁王》相关联的苗族各种表意文化形式的整合研究、史诗《亚鲁王》整理研究的相关学科理论和指导方法等四个不同的角度展开,是跨学科、整体性、多维度的观察探究史诗《亚鲁王》的成果。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贵州籍学者乐黛云先生在书系总序中,盛赞其“构建出一部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卓越典范”。
《亚鲁王书系》是一套由出版人牵头、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思想为指导、率先构建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研究范式的图书,系统全面地展示了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记载的社会生态与文化生态。本文以《亚鲁王书系》的策划与出版过程,介绍出版如何引领构建民族史诗整理研究的新范式。
一、“七根柱子”:跨学科搭建民族史诗整理展示的新平台
《亚鲁王》进入公众视野的过程,实质上是在贵州麻山地区苗族丧祭仪式中传承数千年的念唱形式从自在自为的存续状态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跃迁过程。在这之前,它是大家耳熟的“杨鲁的传说”;而现在,它被定义为“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伴随这一形式变化的实质是麻山苗族的‘亚鲁’文化从地方性的族群遗产扩展为公共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1]
史诗《亚鲁王》的发现,为每一个人都同样地提供了机会、提出了问题、提出了要求。如何整理史诗,如何保护史诗,如何搭建一个观察探究史诗《亚鲁王》的平台,是摆在研究者和出版人面前的问题。我国民族史诗蕴藏丰富,但是史诗研究起步较晚,史诗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而民族史诗的理论探讨,相对国外史诗的研究更显得薄弱,在国际学术界影响不大。[2]民族史诗整理的传统呈现形式,大部分是由民间文艺工作者,在懂民族语言的人帮助下整理民族史诗,然后翻译成汉文出版。这种方法,只解决了史诗从口头传承到文字记录固化保护的问题,读者看到的只是一个孤立的文本,没有解决民族史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整体呈现问题。
通过对民族史诗整理的情况进行认真讨论分析,基于多年对贵州地方民族民间文化的热爱与积累,该书系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社长曹维琼从出版的角度切入,认为必须转换民族史诗整理与展示的方式,拓展整理探究史诗《亚鲁王》的视野,并提出,民族史诗的整理研究要充分考虑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整体性展示,要置放于文化生态环境中去认识的建议。
史诗《亚鲁王》整理探究的选题如何做好?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展示”作为出发点和指导原则,对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整理和编译,就不再因局限于其民间口头文学的基本属性只是简单地整理编译为汉文出版,而是将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作为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样本进行整理、保护、传承和研究。该书系的策划编辑团队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评价、保护、传承的原则为指导,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保护必须关注的文化传承地域、传承族群、传承地域的生态环境、传承族群的生活习俗、传承人的状况、传承的方式、传承中的变异情况等七个基本要素为基础,开始了选题策划,思考建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史诗《亚鲁王》的整理探究模型。这七个方面,被书系主编曹维琼首先界定为是支撑《亚鲁王书系》的“七根柱子”,决定了《亚鲁王书系》的内生价值:
《亚鲁王书系》是活态原生性记录——编创人员“参与不干预”;
《亚鲁王书系》是遗产范式性整理——传承保护“系统与规范”;
《亚鲁王书系》是学科探究性梳理——主编需要“能力与实力”;
《亚鲁王书系》是成果综合性展示——呈现内容“真实与完整”;
《亚鲁王书系》是编辑创意性出版——出版做到“组织与引导”。
二、书系拓展:多维度探索民族史诗呈现的新路径
有了好的思路和打算,如何实现?还必须找到实现的路径与方法。历时两年,整理民族史诗《亚鲁王》的选题经历了从单本(《亚鲁王·歌师秘档》)到双册(《史诗颂译》《歌师秘档》)最终以书系三册(《史诗颂译》《歌师秘档》《苗疆解码》)呈现的过程,是摸索探究民族史诗多维度呈现民族史诗文化的一个艰难历程,也是多维度探究民族史诗新路径的一个创意过程。
最初,《亚鲁王·歌师秘档》选题的提出,只是源于摄影师卢现艺掌握的拍摄线索以及曹维琼对地方民族民间文化的热爱与积累,开始的设想,也只是给颂唱史诗《亚鲁王》的“歌师”这个特殊群体做一个影像的汇总呈现。
随着选题思路的拓展,书系编辑发现,如果只是单一呈现歌师群体,作为一般读者,拿到这个书之后往往会纳闷:为什么要做这本书?歌师是做什么的?歌师这个职业何以千百年来一直存在于苗族社会中?歌师在苗族社会中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然后要很费劲地去在厚厚的一本画册中寻找答案,不能一目了然。当然,这些疑问正是《歌师秘档》这一选题的意义所在。但是,不可否认,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基于一个事实与一个事物——史诗《亚鲁王》。既然如此,史诗《亚鲁王》本体的呈现必不可少,于是提出了再编一本《史诗颂译》,与《歌师秘档》并列。
有了对史诗必要性的认识,还得对史诗整理与编译进行定位与提升。首先,要保证整理与编译过程中的原生性,所以不是一味追求诗性的美感、押韵,而是确保苗语向汉语转换时的准确性,不是简单追求被读者接受的现代性,而是确保西部苗语的古朴性。其次,对此次史诗的整理与编译要有一个提升性的整体定位:史诗整理是一个文化标志,一个里程碑;史诗打开了观察苗族古代社会的窗口;史诗树立了苗族古代社会的英雄形象;史诗拓开了苗族古代社会的研究线索。
基于这种定位,曹维琼又发现,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与保护的范式打造”为目标的种种努力,如果仅仅囿于史诗本体的整理与编译,那么离“七根柱子”还差六根。虽然最初的选题设想是基于歌师群像展现,但是《歌师秘档》完全可以突破群像画册的展示,上升为对歌师口述史的整理与研究:口述史可以勾勒出诵唱亚鲁王的歌师群像;口述史可以验证史诗亚鲁王的活态原生;口述史可以提供研究苗族文化传承法的路径;口述史可以成为展示苗族多彩社会生活的纪实长卷。
至此,完成了两个分册的基本设想,但“七根柱子”只体现了“史诗本体、传承族群、传承人、传承方式”等四个方面,“传承地域、传承地的生态环境、传承变异”这三棵不可或缺的柱子还没有落到实处。那么,用什么方式来落实这三棵柱子?
自20世纪中期至今,民族文化工作者就开展了对亚鲁王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关于亚鲁的故事,在贵州、云南、四川等三省收集整理出版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集中有一些记载。但是,这些故事都处于零散片段记载的状况,没有能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史诗《亚鲁王》在苗语其他方言区也有流传,但是,相当大部分地区只留下短诗、故事、传说等史诗的变异形式在流传。史诗《亚鲁王》不仅因为各个次方言和土语而形成不同版本,即使是在同一个次方言和土语区内,由于歌师所在的家族不同,其唱述的版本都会有一定的差异。[3]为了印证“亚鲁”这一传说人物在苗族其他口头文学形式中同时存在,编辑提出,关于亚鲁故事的异文,要辑录到《史诗颂译》中,并配在相关内容段落旁。
在今天的不同支系苗族人生活中,老人们还能讲出舞蹈舞步、饮食风俗、节庆原由、服饰纹理花色、祭葬习俗与亚鲁王有关的故事,这种复合的民族记忆方式,是适应没有文字而记录刻骨铭心的英雄和事件的群体记忆模式,是令人称奇的传承智慧。所以,编辑认为,有必要用一个分册来专门梳理观照史诗《亚鲁王》传承地域的生态环境、苗族口传史诗诵唱、服饰纹样表意、舞步造型展示、节庆活动演绎、祭葬轨仪礼演等文化表意形式——第三分册《苗疆解码》的设想就此诞生。
《苗疆解码》除了解读史诗《亚鲁王》传承地的生态环境,还要通过各种表意文化事相验证史诗《亚鲁王》的活态原生、阐释相关表意文化事相的内在逻辑。
由此,三个分册使七根柱子得到落实,《亚鲁王书系》终于成型。隐约的思路如何明晰为确定的框架?亚鲁文化的概念如何找到落脚点?书系主编曹维琼组织其他两位主编及其他学者多次探讨,在资料整理、书稿修改、思路打磨和苦心探究的过程中,关于非遗整理保护的一条学术路径逐渐初现;亚鲁文化概念的提出,学科建设的设想、思路和构架逐渐开始显现。
三、亚鲁文化:整体性观察民族文化的新成果
在以“涵育苗族亚鲁文化的沃土”为题的《苗疆解码》后记中这样写道:当我们以史诗《亚鲁王》为线索去探讨、去串联汇集各种与苗族传统文化中与迁徙史、创业史和亚鲁王故事的关联点时,发现史诗《亚鲁王》与各种表意文化形式一起,共同构成了以亚鲁王故事为核心,以苗族迁徙史、创业史为主要内容,以涵盖苗族社会生活各方面知识为主题的苗族传统文化。这个贯连古今、体系完整、历史久远、博大精深、价值重要的传统文化,已成为苗族族群记忆、族群表达、族群特有、族群共享,对当今的苗族社会生活仍然有着重要影响的文化,我们认为可称为“亚鲁文化”。
确实,《亚鲁王书系》通过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逻辑紧密的三个分册,把碎片的、平面的、专业的事相叙述,拓展为完整的、立体的、普同的文化叙述,为我们开阔了视野,为我们建构起一个“亚鲁文化”的研究模型。独具特色的苗族“亚鲁文化”所蕴涵的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价值,将随着内容丰富的“亚鲁文化”研究的展开和深入而重新被人们认识。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吴大华甚至认为“它所散发的信息量,它所运用的方法,它所提出的概念与观点,对于贵州特色学科的学理孕育和成熟,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和促进作用……它有可能促成一门学科——‘亚鲁学’的生成。”[4]
“亚鲁文化”概念的提出,源于书系主编一直立足于以文化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理论为基础、以文化整体性的思想为指导、以史诗《亚鲁王》为主要线索、用整合的方式对苗族各种表意文化形式进行探究。这无疑是《亚鲁王》这一非遗项目整理保护的初步学术成就,拓展了苗族历史文化研究新领域,提供了民族文化研究的一种新范式。
四、特色差异:出版引领的编创团队新模式
《亚鲁王书系》出版后,贵州省文化厅厅长许明称它“不但为我们提供了史诗类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整理研究模式,而且在‘非遗’整理保护传承与自觉担当文化责任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5]
《亚鲁王书系》得以最终以三个分册全景展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亚鲁王》,打造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保护的新范式,而且还在学术探究上实现了路径的突破,编创团队的专业特色差异组合是关键。主编三人,曹维琼是出版人,麻勇斌是苗族文化研究者,卢现艺是民族文化摄影师,不同的专业特色,编创团队的优势突出,确保了图书的质量与水平和创新能力,而出版人在其中起到了中坚作用。
首先,对地方民族民间文化的积累是选题提出的基础。地方出版社作为一个地方文化机构,是传承地方民族民间文化的重地。地方出版社是文化的聚集地、发散地和创新地,她以多年积累与沉淀下来的丰富的出版物文献资料及浓郁的文化氛围,为地方民族民间文化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为社会公众、专业学者与地方民族民间文化搭建了一个互动的平台。作为地方出版社的工作者,曹维琼正是依托于对本地民族民间文化的积淀与底蕴、系统化的知识储备以及出版这一纽带和平台,在史诗《亚鲁王》发现之初,才能迅速地组织编辑开展深入发掘工作;在策划选题之时,才能敏感地认识到可以跳出单纯史诗翻译的局限而以全新的思路来展示《亚鲁王》;在项目实施之际,才会充分整合资源与学术力量参与到《亚鲁王书系》的实施当中。
其次,学术的视野和眼光是选题提升的催化。“从学者角度看,编辑应该具有对自身专业的学术关怀;从编辑职业这个角度看,还应该对整个人类学术事业本身的发展具有一种终极的学术关怀。”[6]所谓的“学术关怀”,落实到具体的出版工作中,就是要有学术的态度和能力。在《亚鲁王书系》的实施过程中,选题策划之初提出的“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保护的范式”本身就是一种学术的眼光与愿景,是作为主编人员的出版人理所具备的学术眼光与能力催化的成果。
最后,出版人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是选题实现的保障。有媒体报道,《亚鲁王书系》的出版,“引领世界从平面、单线条的《亚鲁王》史诗认知,进入到立体、多维度的‘亚鲁文化’活体释读,勾勒出色彩斑斓的苗族‘亚鲁文化”图景”。[7]这一成果的取得,是策划水平、编辑水平和学术能力交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提高的过程,从主编团队的组合、选题结构的变化、图书呈现的形式、文化命题的提炼、装帧设计的创意、出版经费的筹集,出版人的专业化与职业化是选题推进的重要动力,更是选题实施的有力保障。
在出版转型期,我们提出出版是文化创意产业,编辑是文化创意的主体。编辑的创意与整合,就是出版对选题引领的一种模式。《亚鲁王书系》的策划实施,正是编辑创意、出版引领的一种正向表达。
结 语
在《亚鲁王书系》中,编者和著者都超越了纯粹的文本写作和文化内容梳理,进入了进行学科建设的思想境界和行动自觉。
从微观意义上,该书系的策划出版引领整体性、多维度、跨学科地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亚鲁王》进行探究,率先建构出其整理保护的范式,还尝试性地提炼出贯连古今的苗族传统文化即可称为“亚鲁文化”的概念以供进一步探讨——这无疑丰富了《亚鲁王》整理保护的内涵,提升了其研究价值。乐黛云先生在书系总序中称“这将更使《亚鲁王》的整理和研究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并为之展开了辉煌的前景”。
从宏观意义上,在《亚鲁王书系》中,出版既为地方民族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保护、传承担负起了文化使命,又在社会公众、专业学者与地方民族民间文化瑰宝之间搭建了一个互动的平台,并且一直依托区域与人才优势引领项目实施。这既是出版工作者的文化底蕴使然,也是地方出版工作的创新。作为出版案例,《亚鲁王书系》的成功经验、出版对于文化的创意与引领,对于引领地方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研究、对于开启地方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研究的新思路,具有深刻的启发、推广和借鉴意义。
[1]杨春艳.文化遗产与族群表述——以麻山苗族“亚鲁王”的遗产化为例[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2(4)
[2]尹虎彬.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三十年[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3)
[3]吴正彪.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翻译整理问题的思考[J].民族翻译,2012,(3):39
[4]吴大华.“亚鲁王”可能催生“亚鲁学”——一个启于《亚鲁王书系》的猜想[N].贵州日报,2013-07-12
[5]许明.《亚鲁王书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担当[N].贵州日报,2013-07-12
[6]于晖,孙玲.编辑的学术关怀和职业素养[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
[7]黄蔚.《亚鲁王书系》开凿亚鲁文化研究矿脉[N].贵州日报,2013-05-23
——热销书系“恋恋中国风”再度强势来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