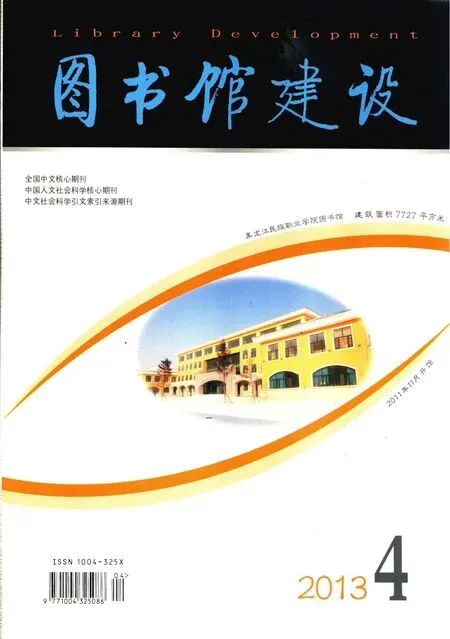基于著作权法视角的图书馆口述文献工作探析
周晓燕 (南阳理工学院图书馆 河南 南阳 473004)
口述文献(Oral Documentation Collection)是指用文字、图形、符号、声像等方法(或者相互结合)把口述内容固化在特定的介质上(如甲骨、青铜、缣帛、简策、石头、树木、纸张、胶片、磁性或数字载体等)而生成的资料。现代意义上的口述文献工作肇始于图书馆,图书管理员是第一批口述文献管理与研究队伍的组成部分[1]。虽然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图书馆开展口述文献工作的条件尚不成熟[2],但是这项工作的确在被日益推广,可谓方兴未艾。例如,国家图书馆[3]、新疆建设兵团党校图书馆[4]、汕头大学图书馆[5]等都一定程度地开展了这项工作。口述文献工作不只受到专业性原则和业务标准的调制,更是受到制度规范的活动。事实上,在现代口述文献工作的早期,著作权保护就是图书馆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1]。相对于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我国图书馆对口述文献工作中涉及的著作权矛盾与利益冲突还没有深刻的认识,更不可能将其当成图书馆著作权保护的专门领域开展充分研究。然而,著作权不断扩张的趋势及社会上频繁上演的有关口述文献的著作权纷争与诉讼事件应当引起图书馆的重视与警觉。口述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渗透着著作权法的理念及其制度内涵,图书馆应针对其特点和规律建立完善的著作权管理体系与著作权危机防范机制。
1 口述文献的著作权归属问题分析
探讨口述文献工作涉及的著作权问题的关键是要界定相关的权利主体、确认其创作贡献、厘清相关的法律关系,为此必须认识口述文献著作权的创作方式,而这又以了解口述作品的著作权特征为前提条件。口述作品的非实物载体性及口述文献后续整理、研究、开发的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决定了口述文献工作中存在着交叉联系、相互影响、彼此制衡的多种类型、不同性质的复杂的著作权法律关系。
1.1 口述作品与口述文献
《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1款中关于“讲课、演讲、讲道和其他同类性质作品”指的就是“口述作品”。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4条第4款中“口头语言形式表现的作品”与其相对应。“独创性”是口述作品得到著作权保护的必备条件之一,陈述语、感叹语、问候语、询问语等实用性语言并不是“作品”[6]。与其他作品类型相比,口述作品的最大特点是未经任何物质媒介“固定”,使得其在司法活动中存在“证据适用障碍”,这是美国、卢森堡、塞浦路斯等许多国家没有对其提供著作权法保护的最重要原因[7]30。但是,口述作品是在作者头脑中构思、加工而成的,是凝结了智力劳动的成果,体现着创造性,如果因为没有被“固定”就不对其保护,很容易被他人剽窃和复制,并将其当成非法营利的借口。目前,部分国家的著作权法已经有了新的调整,不再以“固定”作为口述作品得到保护的前提条件,而只是当成司法程序中的一种证据要求。口述作品的创作与存在特点决定了对其提供保护的高难度性,于是将其及时固化在物质介质上成为口述文献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也有利于后续的研究、保护、传承工作的开展。在速记、录音、录像和数字化复制等技术的支持下,没有加以“固定”的口述作品将越来越少[8]37。
1.2 口述者与口述访谈者
口述文献著作权的归属并不清晰,关乎此类问题的纠纷最常见。以创作法律关系为标准,口述文献可以划分成“叙述式口述文献”和“访谈式口述文献”两种类型。无论哪种类型的口述文献,口述内容都是其核心部分,口述者都能够享有并主张著作权,然而参与者(辅助人、合作人、受托委人)的身份、地位、创作贡献却有很大差异,这是口述文献著作权归属的复杂性所在。在叙述式口述文献中,参与者只做了辅助性工作,如提供场所和记录设备、记录口述内容、提供其他组织工作和咨询意见等。按照《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3条的规定[8]337,这些活动不具有创作成份,不应被视为创作。因此,参与者不能享有口述文献的著作权。在访谈式口述文献中,参与者的身份主要是访谈者。访谈者需要事先搜集研究资料、拟定访谈主题、设计访谈框架、提出访谈计划、准备访谈设备,并通过提问、引导等互动方式执行访谈。这样,访谈者的活动就具备了创造性,访谈者与口述者是合意创作者,应共享著作权,即民法理论中的“准共同共有”,应当按照《著作权法》第13条有关“合作作品”的规定归属著作权[9]。正如里奇指出的,访谈文献是双方共同参与制作的产物[10]。至于委托创作情形下口述文献的著作权归属问题,根据《著作权法》第17条的规定,则要考量口述者和访谈者之间是否有约定和约定的具体内容。一般认为,自传性口述文献的署名权不适用于合同约定。因为,如果自传性口述文献署名为访谈者、执笔者,那么就不能称其为“自传”,这属于“事实不能”。
1.3 口述访谈者与图书馆
在图书馆口述文献工作中,口述访谈者与图书馆存在着职务创作法律关系,访谈者实际上是图书馆的代理人,访谈具有职务性质,这决定了访谈者和图书馆之间的权益分配的法定模式。对于职务作品著作权的归属,各国法律规定的不尽相同。除了荷兰之外的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都规定职务作品的原始著作权归作者所有。英美法系大多数国家及大陆法系个别国家的法律规定,职务作品原始著作权归单位所有[7]183-184。大部分东欧国家法律则规定,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原则上归作者所有,但作者所在单位在其工作范围内以及国家在某些情况下,都可以代其行使权利[7]183-184。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图书馆职工履行职责创作完成的口述文献属于《著作权法》第16条第1款规定的“普通职务作品”[8]329,著作权归图书馆职工所有,图书馆在业务范围内有优先使用权。两年内,未经图书馆许可,图书馆职工不得许可第三人以与图书馆相同的方式使用口述文献。需要注意的是,图书馆为制作口述文献数据库研发的计算机软件,按照《著作权法》第16条第2款第1条的规定属于“特殊职务作品”[8]329,图书馆内部的开发者只享有署名权和获得奖励权,其他著作权(包括财产权和除署名权之外的精神权利)全部归图书馆所有。
2 图书馆口述文献工作中的著作权问题
著作权问题存在于口述文献采集、整理和开发利用的全过程。与其他类型文献工作相比,口述文献工作中的著作权问题有其特殊性。一方面,涉及的著作权项较多,除了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图书馆已经比较熟悉的财产权外,还会与图书馆工作不相干的汇编权、广播权、摄制权、翻译权、展览权等财产权利以及发表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等精神权利发生联系。另一方面,图书馆往往是口述文献及其衍生作品的著作权共享主体之一,但是图书馆行使自己的权利时又受到口述者享有的权利的限制。图书馆和其内部参与口述访谈、记录、整理、研究的职工之间的著作权利益平衡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此外,许多口述文献及其衍生作品极具开发潜力,增值空间较大,增值方法多样,能否对第三人利用著作权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管对图书馆同样是一个考验。
2.1 口述文献采集中的著作权问题
对图书馆最具挑战性的著作权问题就是有图书馆访谈者参与的互动访谈式口述内容采集,因为图书馆对其中涉及的著作权问题比较陌生。例如,访谈者用速写、录音录像等方式将口述内容“固定”,必会涉及复制权(包括数字化复制权)。如果访谈者在记录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思想、立场、情感、倾向,势必造成口述内容被篡改、变造;或者录制设备故障,使“固定”后的口述文献出现信息缺失,甚至可能侵犯口述者享有的修改权或保护作品完整权。显然,图书馆对口述内容的“固定”属于对口述者享有的著作权的直接行使。另外,基于网络的跨地域、跨时空利用网络摄像机、网络视频会议系统的口述访谈,通过博客、微博、电子邮件推送采集口述文献在美国等国家的部分图书馆已实现[1]。在此情况下,口述者自己直接行使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但是图书馆必定要将口述内容收集、储存在相应的设备中,这同样是一种复制行为。无论是以速写、录音录像或者数字记录方式,还是通过网络采集口述文献,都主要涉及对口述者享有的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而且这里面还涉及口述者是否享有“选择权”问题。例如,有的口述者就只同意笔录其口述内容,反对录音[11]。对此,美国口述历史协会制定的《口述文献原则和标准》规定,访谈者必须尊重口述者的意见,口述者有权拒绝访谈者的建议[12]。所以,图书馆在采集口述文献中保护著作权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只是履行“告知义务”,而是要在告知采集的方法、特点、目的之后,与口述者进行充分沟通,按口述者的意愿办事。
2.2 口述文献整理中的著作权问题
著名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认为,“整理”是整个口述文献工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3]。口述文献的整理有两种类型:其一,技术整理。即对口述文献进行分类、标引、编目,并制作相应索引、目录、文摘等工具。世界上最有影响力、最具通用性的口述文献技术整理工具是美国口述历史学会的《口述历史编目手册》(Oral History Cataioging Manual)。其二,内容整理。可以将其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对口述内容补充、更正、稽核、甄别,去伪存真、去芜存菁,这属于口述史研究的范畴。口述史整理研究可能产生新的作品,而这种新作品的著作权可能只归属于整理者,也可能由口述者与整理者共有。口述史研究尽管不是图书馆的主要工作范畴,但亦会有所涉及。二是只对口述内容进行简单的拼接、编辑、订正等学术逻辑和文法的整理加工,并将口述内容转换成文字或者数字形式,这是图书馆整理口述文献的重点。在此情形下对口述文献的整理必须是“原始性”的或者“原真性”的[14]。例如,隶属于英国国家图书馆的英国国家口述资料馆将所有录音磁带上的声音(包括寒喧、重复、咳嗽等)都严格按照原始声音转录成文字[15]。图书馆整理口述文献涉及的著作权问题最为复杂,因为具体的整理行为究竟是属于“口述史研究”,还是“原真性加工”,往往不容易区分。这又是一个必须明确界定的问题,关乎图书馆、口述者及其他主体对基于口述作品、口述文献的衍生创作成果的著作权益的分享。
2.3 口述文献开发中的著作权问题
彰显口述文献重要价值的做法就是加大开发利用力度,主要方式包括出借出租、编研出版、影视改编、陈列展览、专题研究及进行多媒体、数据库等数字化开发等。例如,美国杜鲁门总统图书馆的访谈抄本都按照受访者名字的字母或者访谈主题顺序实现了互联网络查询和检索,而且个别访谈抄本都已在网上全文发布,读者可以通过网络任意下载口述抄本。对于访谈的磁带,图书馆可以根据读者需要提供出租服务[16]。美国一些口述文献研究机构也专门提供录音、录像资料转录和整理的有偿服务,其中以康涅狄克大学图书馆口述历史办公室(Oral History Office, University of Connectivut)最具特色,其享有最高的声誉[1]。图书馆开发利用口述文献受到口述者享有的复制权、出租权、翻译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专有权的控制,如果图书馆许可第三人对口述文献进行小说、影视、戏剧作品等艺术创作或者出版,还要受到发表权、改编权、汇编权、广播权、摄制权、翻译权等权利及图书馆是否享有“再授权”权利的制约。图书馆在与口述者的谈判中,应争取尽可能多的权利,最好是得到专有使用权,甚至受让著作权。否则,图书馆开发利用口述文献的价值将大打折扣。由于图书馆可能成为口述文献及其衍生作品著作权的共享主体之一,所以图书馆在行使自身权利时要注重对口述者合法权利的保护,在权利无法分割行使或者权属不明时,更要恰当把握行使权利的“尺度”与“方法”,不能以牺牲口述者的利益作为实现图书馆利益的代价。
3 基于著作权保护的图书馆口述文献工作
就我国法律法规来看,在明确界定口述文献的著作权,对于尚未形成信息产品的原始口述资料,如何确定其著作权等方面存在法律障碍,至今没有解决办法[12]。在此立法状况下,图书馆应以现行法律法规既定的著作权原则为依据,建立健全口述文献工作中的著作权保护规范,尤其是不能忽视对法律风险评估与合同约定的著作权管理方法的运用。图书馆还要积极采取措施,培养、提高口述文献工作者的著作权保护素质,建设专业化的著作权管理队伍。
3.1 制定和健全著作权保护规范
要使法律法规的精神得到落实,必须在《著作权法》所确立的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图书馆保护著作权的自律性规范。例如,美国口述历史学会于1968年制定了《口述文献原则和标准》,1979年出台了《口述文献评价准则》,现行版本是2009年9月制定的《口述文献的通用原则和最优实践》,这些行业规范对口述者、访谈者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权利许可与转让和放弃等作了规定,还提供各种标准的法律授权样本,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实用性[11]。我国图书馆口述文献工作起步相对较晚,尚无行业性的政策或者指南。以现行法律法规为依据,借鉴美国《口述文献原则和标准》的相关内容,综合各种观点与实践,口述文献工作应遵循的著作权规范主要包括:其一,程序合法。将访谈的内容、时间、地点、方式(笔录、录音、录像、数字记录等)以及使用方式(编辑整理、开发利用等)与限制、优先权、版税等问题告知口述者,并征得其同意,即取得授权。例如,按照美国《著作权法》第101条规定[17],图书馆将口述内容以速写、录音录像、数字设备等方式“固定”,必须经过合法授权。否则,属于非法活动。其二,签字生效。对于口述内容整理、加工、编辑后形成的口述文献经口述者审查签字才能定稿。其三,证据保全。对录音带、录像带和底稿、光盘、照片、速记本以及其他收集到的材料要完整保存,整理出来的文字结构要保持原来采访流程的顺序,这不仅是出于对进一步研究与开发利用的考虑,在发生纠纷时还可以作为主张权利和应诉抗辩的佐证[18]。其四,利益共享。如果对口述文献的开发利用有经济收益(出版发行、调阅收费、影视改编或与此有关的其他收益),应与口述者合理分享[14]。其五,履行义务。与口述者和第三方开发利用者订立完备的著作权合同,认真履行合同约定,严格按合同办事。其六,谈判磋商。如果口述者要行使与图书馆共同享有的不可分割的权利,图书馆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而应主动与其协调,达成一致。其七,权限控制。例如,美国图书馆普遍对数字化口述文献的使用设置了诸多权限,防止非法复制和传播[1]。其八,内部管理。建立图书馆内部著作权管理制度,清晰界定图书馆与其职工之间的著作权法律关系。
3.2 评估不同业务中的法律风险
虽然图书馆对于每项口述文献工作都会事先制定详细的计划,其中包括应对可能出现的著作权纠纷与诉讼的预案,但是比较于对其他类型文献的搜集、加工、整理、储存和利用,口述文献工作仍然具有较高的法律风险。其一,法律法规不健全。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及其配套制度对口述作品、口述文献的阐述存在“盲点”,这也是有的学者认为国内图书馆尚不具备开展口述文献工作条件的理由之一[19]。其二,口述文献工作本身的著作权特点。例如,图书馆出于业务的需要不得不对口述内容编辑、加工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这种管理权势必会与口述者享有的发表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等权利发生冲突。其三,缺乏著作权管理经验。由于口述作品、口述文献、口述文献工作中的权利主体多而相互关联,绝大多数图书馆缺乏专业著作权管理人才,难以判明其中的法律关系,更别说制定科学的处置策略。其四,外部风险管理难度大。图书馆对经其授权的第三人(包括文学、影视、戏剧、曲艺的创作者和电子书商、录音录像制作商、数据库开发商与出版者等)利用口述文献的行为很难监控(即使订立有相关协议),如果因为第三人的过错造成侵权,作为口述文献提供者的图书馆自然会被牵连其中。对于我国图书馆,口述文献工作是著作权保护研究与实践探索的新领域,图书馆要对其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认真研究、掌握规律,积累防范和化解风险的经验,建立健全预判和预警机制。鉴于口述文献工作的特点,图书馆希冀建立一套针对所有业务类型的风险评估模式并不可行,因为每种类型的业务有不同的著作权特点与管理要求,需要开展专项的风险评价。
3.3 以著作权合同约定权利义务
在口述作品、口述文献著作权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的背景下,合同的价值凸显,其目的是将事后的权益分配和矛盾处理变成事前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界定,从而利于主张权利、助于防范纠纷、便于调解审理。合同可以是许可使用合同,也可以是转让合同,但一般应具备编辑和使用的限制,著作权归属、优先使用权、版税、资料的预期处置方式和各类传播方式及电子发行等项[20]。合同涉及的权利内容应尽可能宽泛(如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汇编权、广播权、翻译权、摄制权、放映权、展览权,以及发表权、修改权等),同时要约定图书馆是否享有转授权。对于口述文献及其衍生作品存在的合作创作、委托创作问题,合同中更要明确界定图书馆与口述者的权利、义务和法律关系。除了权利的归属和行使外,合同还要包含《著作权法》第24条、第25条规定的其他内容。合同对隐私权保护等法律问题也要有所触及,虽然这与著作权保护无关。总之,合同条款应细化,忌笼统和粗略,这样有利于对图书馆权益的保障,如“李宗仁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口述作品纠纷案”就是典型案例[21]。合同不宜采取口头或其他形式订立,而应是书面合同,并且口述者必须签字。在相关口述作品著作权纠纷中,有的当事人认为,其没有在合同书上签字,合同对其不产生法律效力[22]。合同模式同样适用于图书馆与其内部职工(口述访谈者、整理者,软件开发者等)之间的权利、义务与法律责任的约定,因为图书馆未与其内部职工签订著作权合同而导致的诉讼案件在我国图书馆界已有发生[23]。与其他著作权使用合同不同,图书馆应特别要求口述者在口述文献合同中订立“真实性条款”。因为,如果口述者的言论涉及到对他人的伤害、诽谤、诬蔑、诋毁、隐私或者泄密等而引起法律问题,图书馆作为参与者,自然脱不了干系。订立“真实性条款”是图书馆重要的自我保护措施,对口述者也会起到警示作用。
3.4 提高工作人员的著作权素养
口述文献工作增加了一个新变量,即历史的见证人和在场者──口述者,使得流程中增加了两个新的维度,即口述者与历史现象间的关系、口述文献工作者与口述者之间的关系[24]。这对口述文献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学者认为,口述文献工作者集图书馆工作者、档案工作者、历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等身份于一体[25]。对于口述文献工作,并非只要有热情就能做好,不经过相关的专业训练是无法胜任的。例如,对于怎样在尊重和保护著作权的前提下对口述内容以速记、将录音转成文字的方式固定下来,如何把握“口述史研究”与“原真性加工”的界限,如何向第三人授权使用口述文献及其衍生作品等问题,大多数图书馆工作者是不清楚的。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保证口述文献的工作质量,美国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就曾专门训练和雇佣了一批资深的图书馆员、历史学家来承担有关任务,这时期的口述文献工作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来说都有很大的提高[16]。1968年后,美国匹兹堡等大学的图书情报学院开设了“口述历史与口述传统”课程,讲授口述历史从口述到各种记录格式的发展、口述历史馆藏的开发与管理[26]。目前,在线口述文献知识培训服务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贡献最大的是美国口述历史学会于1995年创办的“口述历史论坛”(H-Oralhist)[27]。至于著作权素质对于图书馆口述文献工作者的意义,早在1968年,Zacher就认为,口述文献工作要求图书馆员补充新知识、掌握新技能,积累著作权保护经验[28]。为了解决我国图书馆口述文献著作权管理人才匮乏的问题,除了开展著作权保护普及教育外,可以借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部分图书馆的做法,创造条件逐步设置“著作权图书馆员”(Copyright Librarian)[29]岗位,由专人负责此项事宜。
[1]杨祥银.当代美国口述史学的主流趋势[J].社会科学战线, 2011(2):68-80.
[2]蔡 屏. 我国图书馆在现有条件下开展口述历史工作的局限[J].图书馆建设, 2012(1):39-42.
[3]国家图书馆中文资料组.国家图书馆关于征集“非正式出版文献”的公告[EB/OL].[2011-01-11].http://www.nlc.gov.cn/syzt/2008/0709/article27.htm.
[4]赵维景.口述历史:图书馆特色馆藏建设的新领域[J].科技创新导报, 2012(12):216.
[5]张 卫.口述历史收集与整理工作的意义与注意事项:以威宁县地方文献收集为例[J].图书馆建设, 2011(3):27-28.
[6]王 倩.谈口述档案著作权问题的特殊性[J].档案, 2011(1):15-17.[7]郑成思.版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8]李明德, 许 超.著作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9]董瑜芳.试论口述历史中的版权问题[EB/OL].[2011-12-17].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I.php?NewsID=4217.
[10]里 奇.大家来做口述资料:实务指南[M]. 2 版.王芝芝, 姚 力,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15.
[11]傅光明.口述史:历史、价值与方法[J].甘肃社会科学, 2008(1):77-81.
[12]郑松辉.图书馆口述历史工作著作权保护初探[J].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0(1):104-110.
[13]王杉胜.浅谈口述资料的搜集与整理[J].新疆地方志, 2007(3):16-18.
[14]曹幸穗.口述史的应用价值、工作规范及采访程序之讨论[J].中国科技史料, 2002(4):335-342.
[15]李小江.口述历史与档案工作[J].中国档案, 2006(1)55-56.
[16]杨祥银.美国总统图书馆的口述历史收藏[J].图书馆杂志, 2000(8):60-64.
[17]李明德.美国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153.
[18]陈俊华.图书馆开发口述历史资源探索[J].图书情报工作, 2006(6):126-129.
[19]蔡 屏.我国图书馆在现有条件下开展口述历史工作的局限[J].图书馆建设, 2012(1):39-42.
[20]尹培丽.口述资料及其著作权问题探究[J].图书与情报, 2011(3):53-56, 84.
[21]薛鹤婵.口述档案的知识产权研究[J].兰台世界, 2009(6):31-32.
[22]王 云.口述“红旗渠”修筑者获著作权[EB/OL].[2012-02-11].http://www.news.ifeng.com/society/1/detai/2012-10/22/184169540-shtml.
[23]秦 珂.图书馆工作中区分职务作品和法人作品的法律适用界定[J].图书情报工作, 2010(10):129-132.
[24]任中义.口述史学及其规范性研究[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2(3):92-95.
[25]张 燕.基于口述史的档案编研发展策略分析[J].山西档案, 2010(5):19-21.
[26]匹兹堡大学图书情报学院课程[EB/OL].[2012-11-16]. http://www.sis.pitt.edu/-lsdept/descrip.ht.
[27]美国口述历史论坛[EB/OL].[2012-11-16].http://www.h-net.org/-oralhist/.
[28]口述史在二十一世纪所起的文献作用[EB/OL].[2012-12-07].http://www.archives.sh.cn/docs/200802/d155517.html.
[29]陈传夫, 汪晓方, 符玉霜.国外版权图书馆员岗位设置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国家图书馆学刊, 2009(2):3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