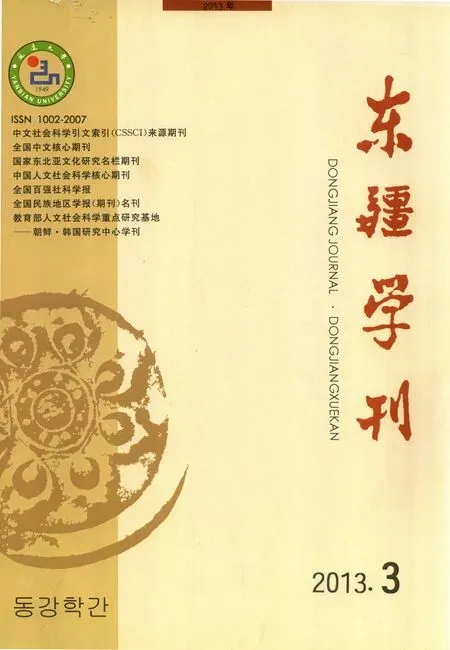打开东西方文化对话之门——论“间距”与“变异学”
曹顺庆,沈燕燕
一、“间距”的提出
法国著名学者朱利安(Francois Jullien)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年12月16~17日召开的“思想与方法:全球化时代中西对话的可能,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会议①引自《思想与方法:全球化时代中西对话的可能,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文集》 (未出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年12月16~17日。上,提出了“间距”理论。朱利安教授在《间距与之间:如何在当代全球化之下思考中欧之间的文化他者性》一文中分析了时下流行的“差异”概念所引起的弊端,从而提出与之相反的“间距”(é cart)概念。他尝试以“间距”打开“之间”,并以“之间”为工具,重建自我与他者对话交流的可能。这一途径可归结为:通过构建外在他者,从而达到解构目标文化的目的。朱利安指出:那“差异”与“间距”的区别何在?简而言之,“差异”是以认同为前提和导向,带有主观价值判断的概念,而“间距”则主张拉开对话两者之间的距离,尊重双方的独立性,采取的是不带偏见的超然立场。差异是一个认同的概念;我们在观察到这一点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一个与之相反的事实,那就是不可能有文化认同(il n’y a pas d’identité culturelle possible)。认同(l’identité)事实上至少用三种方式围绕着差异:一、认同在差异的上游,并且暗示差异;二、在差异制造期间,认同与差异构成对峙的一组;三、在差异的下游,认同是差异要达到的目的。因为差异首先就暗示一种更普遍的认同 (une identité plus gé né rale)——可以这样说:一种共同类型(un genre commun)——在其内部差异则显示为一种特殊性。那么,这个更普遍的认同会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一开头就知道的,正如我们可以在文化多元性的开端,特别是那些长久以来在语言上和历史上互不相干而彼此漠然的文化,譬如在中国与欧洲之间,这个更普遍的认同会是什么呢?”
显然,“间距”是一个理论新词,在会议上引起了激烈的论辩,受到多方质疑。笔者认为新词往往意味着新的方法。朱利安教授为何提出“间距”这一新概念?我认为,这恰恰是就反思东西方文明对话的弊病而提出来的。近百年来,学界研究东西方文化比较或对话时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中西之争,有主张中体西用,有提倡洋为中用,更有鼓吹中国全盘西化等等,说法不一而足。然而,争辩的结果却是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都没用了。朱利安在研究东西方文化对话时也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的时代。这使得中国人无法读懂中国文化,日本人读不懂日本文化,因为一切都被重新结构了,中国古代思想正在逐步变成各种西方概念”,“其实中国思想有它自身的逻辑”[1](82)。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在用西方概念遮蔽中国概念的过程中,各种文献文本都同一化为西方文化范本的注解,差异性思想在这种转述过程中不断失落,也使得中国文论已愈来愈难为今人所理解。比如“风骨”概念,时至今日,学习古代文论的人甚至相关的专家学者也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香港大学的陈耀南先生在《文心雕龙风骨群说辨疑》一文中梳理了当代百余篇研究“风骨”的学术论文,清理学术界关于“风骨”的解释,最后对“风骨”二字却仍不得要义,只能无奈地说,干脆请《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字彦和)自己站出来讲清楚,究竟什么是“风骨”:“请彦和回来示观,以破迷惑而广知见”[2](58)。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尴尬的情况,根源便在于东西方文化对话中,人们大多注重同一化的研究方法。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视西方概念为普适性楷模,例如阐释“风骨”,往往用西方文论的概念“内容/形式”或“风格”等等,而忽略东方文化或中国话语的独特性,只一味地向西方文论话语靠拢。在这样以西释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中国话语的“异质性失落”,甚至得出一些有悖常识的结论。例如:素有国学大师之称的王国维在学术界有很高的声誉。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 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并认为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方法“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世以轨则”。[3](1)然而这种“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如果忽略东方文化或中国话语的独特性,只一味地向西方文论话语靠拢。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中国话语的“异质性失落”,甚至得出一些有悖常识的结论。王国维用叔本华的生命悲剧意识哲学解释《红楼梦评论》,得出《红楼梦》一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然而,他又认为中国文化整体精神是乐天的,是没有悲剧精神的;在自相矛盾的无可奈何之下,于是乎,他竟然推导出《红楼梦》是“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的结论[4](358,359)。显然,这个结论实际上完全是谬论! 植根于中华文化的《红楼梦》怎么可能“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 王国维以叔本华的悲剧观为圭臬,判定《红楼梦》是真正的悲剧。他说:“《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4](359)然而遗憾的是,王国维却认为《红楼梦》的悲剧精神与整个中国人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他指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享;非是而欲厌阅者之心,难矣。……故吾国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尔。而《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4](359)在这里,王国维犯了一个绝大的逻辑错误:生长在中国文化精神土壤中的《红楼梦》,怎么可能“大背于吾国之精神?”难道《红楼梦》是无本之木?或者是天外的“飞来峰?”更有甚者,胡适、朱光潜等学者认为中国艺术的“神庙里没有悲剧之神的祭坛”[5](221),朱光潜先生明确指出:中国根本没有悲剧,“事实上,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仅仅元代(即不到一百年时间)就有五百多部剧作,但其中没有一部可以真正算得上悲剧。”[5](218)朱光潜先生这一论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然而近年来,许多人不同意这种论断。有人撰文比较中西悲剧观,有人编出了《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还有人针对朱光潜先生中国无悲剧的论据,进行了具体的反驳。①参见曹顺庆《中西比较美学论文集》中乔德的论文,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王季恩编《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以及张辰、石兰著《悲剧艺术论》,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朱光潜否认中国悲剧观,主要论点如下:中国人“是一个最讲实际,最从世俗考虑问题的民族。他们不大进行抽象的思辩,也不想去费力解决那些和现实生活好象没有什么明显直接关系的终极问题。对他们说来,哲学就是伦理学,也仅仅是伦理学。”“中国人实在不怎么探究命运,也不觉得这当中有什么违反自然或者值得怀疑的,善者遭殃恶者逍遥,并不使他们感情惊讶。”中国人既然有这样的伦理信念,自然对人生悲剧性的一面就感受不深。”[5](125~127)如果说中国完全没有悲剧,那怎么解释《赵氏孤儿》这部连西方人都承认是悲剧的元杂剧?这些尴尬都是完全以西方概念为普适性范式来分析中国文学而得出的荒谬结论。朱利安教授之所以提出以“间距”代替有同一化导向的“差异”概念,正是基于这样对追求同一性反思的背景,这是很有见地的创新性的提法。
同样,在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史上,几乎所有的学科理论也都是从求同性出发的,视相同性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以法国学派为首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的联系,实质上是求同性的同源影响研究,它仅仅关注同源性文学的关系。以美国学派为首的平行研究虽然突破了影响研究仅注重事实联系的局限,提倡跨学科研究,拓宽了比较文学的比较领域,却集中于同一文明圈的文学比较,相对忽略了异质文明文学间的比较。无论是影响研究或是平行研究,甚至是俄苏学派的类型研究,所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都强调共同性,同源性或类同性成了比较文学可比性的基础。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缺陷就在于:几乎所有人都完全忽略了比较中的异质性问题。通常,没有学过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人,在比较文学研究中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比较文学是既求同又求异的,比较就是求同中之异,异中之同。这种直觉,实际上是正确的。但是在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比较文学的根本目的是求同而不是求异。不管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其研究基础都是“求同”,是求异中之同。具体来说,影响研究求的是“同源性”,即渊源的同一性;平行研究求的是“类同性”,即不同国家文学、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类同性。对于不同国家文学的差异,欧美学者不是没有看到,也不可能没有看到,因为这是一个仅凭常识和直觉就能够意识到的问题;但是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角度来看,欧美学者认为,差异性是没有可比性的,对差异性进行比较是没有意义的。正如巴登斯贝格所说:“因为事实上,任何实际上的巧合都不能造成一种从属的关系”,“正如同一位18世纪大胆的生物学家把一朵花与一个昆虫之间的形象和色彩进行精巧比较那样。”韦斯坦因也认为,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文学不可相比较,他说:“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方能在思想、情感、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6](5)也就是说,只有在同一文明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文学才能进行比较。但是,对于比较文学理论而言,这种“求同”的理论模式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因为在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中,都存在着许多异质性因素,其变异性往往要大于“同源性”和“类同性”的因素。
中国比较文学发展之初,采用的也多是求同性的比较方法。钱钟书先生虽然认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但其东西方文明文学的可比性仍是建立在人性共通这一相同性之上的。也正因如此,朱利安教授才批评了钱钟书。他指出:“他(钱钟书)的比较方法是一种近似方法;一种不断接近的方法:一句话的意思和另一句话的意思最终是相同的。我觉得这种比较收效不大。”②引自《思想与方法:全球化时代中西对话的可能,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文集》(未出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年12月16~17日。对同一性的侧重造成了比较文学的一种研究怪圈,越是想要通过求同性的比较弄清东方或中国文论话语,却越是读不懂,中国文学的面目在这种比较中变得越来越模糊。同时,这种片面求同、不看差异的观点也导致比较实践中出现了大量流于表面的X+Y式的浅度比附。“间距”概念的提出是对这种同一化模式的反抗,也为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启发出一个新思维、新角度。中国学者习惯套用西方理论,并将其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殊不知如果不把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文化土壤相结合而盲目地套用,这么做是会出现问题的。我们在引进西方理论的时候,不应该把它当作绝对的真理,而应该注意它的异质性。我们知道,跨越异质文明对于不同文明有着互相补充、互为参照的现实意义,所以突出异质性,有利于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和融合,更有利于我们建构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这也是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的最终目的。
二、和而不同,和实生物
如上分析,“间距”是基于对同一性的反思而提出的概念,那么,它又从何而来?
朱利安教授原本是研究希腊哲学的,他将中国作为与希腊拉开距离的观察点,采取一种远离而又不断返回的迂回式研究方法。因此可以断言,“间距”概念是深受中国文化启发而来的。他指出:“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时眼中无全牛,只看到各关节间的间隙,故刀刃才可恢恢乎游走其间,也因此即便“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这便是间距存在的方便。
也许中国的另一说法更能直观地体现间距的重要性——“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是中国和谐观念的重要阐释,孔子将其应用于人际关系中,是指君子与人相处要保持距离,思想上不盲从,才能达到和而不同的和谐状态,如若只是一味跟风,最终只能沦为小人式的同流合污之同。因此,所谓“和”,不是一味的“同”,而是要保持各自的独立姿态,是有差别、多样性的统一,惟有拉开间距的思想才不会在对话中被对方淹没,所以“和”区别于泯灭了间距、差别性的“同”。这就要做到不人云亦云,不迎合别人心理或附和他人言论,而要有自己独立的姿态,必须与他人保持距离。中国古代文论呈现了与西方文论相当不同的异质性特征,它从知识谱系和知识展开等方面都全然异于西方的理论式话语。然而从五四时期开始,中国学界以科学的名义对中国文论话语系统进行生硬切割,力求以逻辑性、理论性、系统性的西式理论方式诠释、规范中国具有体验性、品味式的文论话语,结果西方范式全面取代了中国范式,造成中国文学文论传统与现代文论之间出现了断裂和失语。失语的同时,中国文论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审美蕴含多义性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失落。没有间距、一味附和的求同最终只能是“同而不和”。
“和而不同”的观念更早出现于《国语·郑语》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由此可见,“和而不同”的“和”不是凝滞的“和”,而是有着丰富孕育能力的、具有生物生长功能的“和”,这也正是朱利安教授所说的“有生产力的”(productif)是间距的本性。因为有了间距,有了差别,所以思想不会在对话中被淹没,对话的两者间的张力也才得以突显,进一步来说,间距所孕育的新本质也才能得以实现。
事实上,人类文明史上很多具有创造性的东西都是在间距形成张力以后创造出来的,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佛教是基于印度文化的产物,东汉末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进入中国这一异质文明国度的过程中,中印文明的间距促使佛教在这两者的张力间不断自我更新,慢慢中国化,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流派——禅宗。不仅如此,佛教还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历史、哲学、伦理道德、语言、词汇、音乐、舞蹈、绘画、建筑、雕塑、天文、医学、科技以及民俗民风、民族性格和心理素质等世俗文化的诸多方面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佛教更是为中国文学带来了许多从来未有的新东西——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素材、新的创作手法。这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是佛教在中印文明的张力中新生的,体现了在保持间距的对话中张力所带来的丰富的文化创新能力。
代表印度文明的佛教与中国文明间的交流无可辩驳地体现了间距和张力的创造性。只有拉开距离形成张力,文明间的交流才更能迸发出创造的火花,否则便会在求同的范式要求下泯灭自身的民族特性。由此观之,“间距”既是“和而不同”,更能“和实生物”。
三、变异学与间距
在全球化语境下,全世界学者都不得不面对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碰撞,然而,固有的比较文学学科还停留在以同一性为基础的理论阶段。实际上,文学在如今跨国、跨语言、跨学科甚至跨文明的流传影响过程中,更多的是变异性。影响研究注重同一影响的一面,而忽视接受变异的一面;平行研究则忽略了不同文明文学的异质性,导致“异质性的失落”。不论影响研究或平行研究都已无法满足当今比较文学的发展需求,时代在呼吁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国学派在提倡跨异质文明比较的实践中提出了变异学理论,这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思考角度,也是对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围。
弗朗索瓦·于连认为,文明的异质性非常重要,“这是一个要害问题,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的时代”。“中国古代思想正在逐渐变成各种西方概念,其实中国思想有它自身的逻辑。在中国古文中,引发思考的往往是词与词之间的相关性、对称性、网络性,是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如果忽视了这些,中国思想的精华就丢掉了。”[1](82)所以,当下的比较文学研究就是要从中国文化自身的逻辑出发,在与西方的对话中,坚持自身的基本话语规范和价值立场,不能盲目用“比较”一词来否定文明之间的异质性。而于连的整个思想体系也就是围绕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差异性”与“无关性”来展开的,也可以说是用“差异”来进行比较的;朱利安在中西比较中主动求“异”,通过“异”的比较来还原文明自身的原生态,让这些独立性、自主性的文明用自己的话语规则来言说,继而进行优势互补、对话融通。他指出:“文化的本性在趋向同质化 (s’homogé né iser)的同时也不停地异质化(s’hé té rogé né iser);在趋向统一性(l’unification)的同时也不断地多元化(se pluraliser);在趋向融合与顺应(se confondre et se conformer)的同时也不停地标示自身的特色,去认同而再认同(de se dé marquer,de se dé sidentifier et de se ré identifier);在趋向自我提升到主流文化(s’é lever en culture dominante)的同时也不断地让异议发挥作用(d’ê tre travaillé par la dissidence)。这就是为何文化肯定是复数的,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不过是其典范例子,我们今天要一起思索这两种文化的面对面。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为了避免张冠李戴的错误和差不多的领会;也为了避免使我们相信我们通过现在的标准化语言而彼此理解。然而,人们以为从此之后是大家的共同用语,却继续传递着分歧的含义。因为我们没自觉地意识到这种情况,所以它更加危险。唯有付出这样的代价,才可能在中国与欧洲思想之间进行一场真正的‘间谈’。”①引自《思想与方法:全球化时代中西对话的可能,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文集》(未出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年12月16~17日。
变异学是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中呈现出的变异状态与异质性的研究,以及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相互阐发中出现的变异状态的研究。主要从跨国、跨语际、跨文明文化和文学的他国化等几个层面进行,通过研究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时呈现的变异,探究比较文学变异的规律。因此,文学的差异性存在样态成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可比性基础,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的一个新的重要理论转折。
从以上对变异学的简略分析,也可以看出间距思维在变异学中的体现。首先,变异学跟间距一样,超越了以往比较研究求同的思维,解决了跨文明比较的合法性,两者反思的基础都是同一性(类同性);其次,变异学要求比较双方在相互尊重、各自保持文化个性的前提下进行平等对话,尊重文化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这同时也是保持间距对话的前提要求,实际上也是一种“间谈”,是注重异质性的“间距”;最后,间距要求主体走出自己所属的文化圈,从外围不带主观倾向地对此加以观察和发现,避免种族中心论。同样的,变异学也要明确自己的方向既不是东方问题也不是西方问题,更不存在东方学者站在东方的立场纠正反驳西方的问题,变异学思考的是整个比较文学学科原有理论所具有的缺憾,并试图加以解决。
因此,变异学的态度其实也是一种间距态度,比较的双方在保持间距的同时,通过不断对话交融,然后逐渐形成新的东西。上文所举的禅宗例子,用变异学的理论解释便是一种“文学他国化”的现象。禅宗是外来的印度文化与本土中国文化相融汇以后所产生的文化新枝,这种异质文明的接触与碰撞,使佛教在历史上日益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相结合,最终形成了独具本地区特色的佛教禅宗,表现出有别于印度佛教的特殊精神面貌和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特征。同时,佛教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文论——刘勰的《文心雕龙》与钟嵘的《诗品》,两书皆以佛教思想诠释他们的文艺批评理论;《诗品》提出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也是缘于佛教思想。禅宗更是把批评重点从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和把握转向为对主观心灵世界的感悟,南宋严羽作《沧浪诗话》便是运用禅宗的顿悟之说提出“诗道亦在妙悟”的“妙悟”说。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往往能够激活冲突双方文化的内在因子,使之在一定的条件下进入亢奋的状态,从而激发出无限的创造力。差异学同间距观一样,在以“和而不同”为目的的同时又“和实生物”。
需要注意的是,变异学虽然重新为东西方文学的比较奠定了合法性,肯定了差异也具有可比性,但变异学强调的是异质性的可比性,是要在同源性或者类同性的文学现象之间找出异质性和变异性。禅宗与佛教尽管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但它依然可以回溯到源头的印度佛教。变异学需要做的首先是在研究对象之间找到类同性,然后才能进一步研究变异性,并阐释类同性背后的差异及其深层文化机制。也就是说,差异学认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不仅包括异质性、变异性,也包括同源性、类同性,这点是区别于不承认一个预设共同价值追求的间距观的地方。间距观认为不存在一个既定的普遍认同,因此,它竭力否定差异概念,它所诉求的既非同一性也非差异性,它基本不做比较,而是通过一个独立的外在他者反思自身。这也是间距与变异学的分野之处。
四、结语
有间距才能有张力。有张力的存在,才会有真正的独立品德,才能有所创新。双峰对峙,风景才好。当然,一个新词的提出总会引起学术的争议,关于“间距”的概念内涵、名称合法性及间距的角度等问题都有待学者们进行进一步探讨。但新词往往意味着新方法,间距对于同一性的警惕,对于独立的异质性价值的重视,不仅是对当前全球化语境下对话原则的探讨与思索,也是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对变异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变异学与间距观之间有着许多异曲同工的诉求,但也存在着一定的视野分歧。不论是间距观还是变异学,都还有许多值得探索的地方,我们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西方学者常常发明新词,是因为新词中有新方法、新观点的形成,也唯有如此,学术才能常辩常新、保持活力。笔者支持朱利安教授提出的“间距”理论。
[1]秦海鹰:《关于中西诗学的对话——弗朗索瓦·于连访谈录》,《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2期。
[2]陈耀南:《文心雕龙风骨群说辨疑》,《求索》,1988年第3期。
[3]《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遗书(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4]王国维:《红楼 梦评论》,《王国维论 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5]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6][美]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