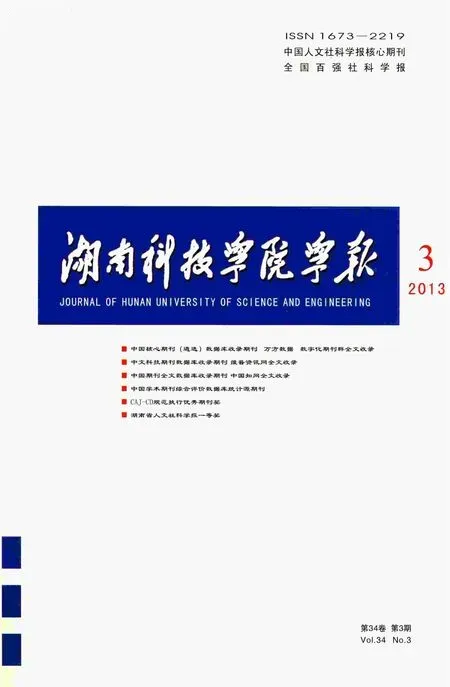站在全球经纬的高度来看待“学术大师”
董京泉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北京 100806)
余三定教授写的《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著作。我认真拜读了书的序言(《代序》),粗读了其中的几章,细读了第六章即《关于“学术大师”的讨论》。对这一章我很感兴趣,所探讨的问题也很重要,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学术通才(主要指思想家)及各学科大师们的思想论述,就没有真正的学术发展史。我非常钦佩余三定教授收集、积累、梳理和驾驭那么全面、丰富的资料,并对这些论著的观点作出概括和点评——这要比自己写一其他类型的书或长文要耗时费力得多。我自己读后受益匪浅,也引发出一点微不足道的看法,在此与大家做一交流。
关于培养和造就“学术大师”的环境和条件,许多论者包括一些著名学者发表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但恕我直言,他们似乎皆是从中国当下的情况出发加以分析的,而没有站在全球经纬的高度来分析问题,所以他们所讲的学术大师产生的土壤和机制等等,都可以找到相反的有说服力的例证。我觉得要研究这个问题,应当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全球视野,运用古今中外法,着力于个案分析,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从而发现其中的规律性的东西。首先要好好地分析一下一些世界级的学术大师是怎样成为世界级学术大师的?譬如老子、孔子、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释迦牟尼、耶稣,以及近现代的康德、黑格尔、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他们是何以成为学术大师的(其中的革命导师同时也是科学巨匠)。总之,对这个问题,似乎还需要作更深入、更拓展的研究。
要说社会政治环境和条件,这些人当时有什么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呢?他们几乎都是在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和简陋的物质条件下完成伟大创造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坟。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以上说明这些大师都是遭受重大人生磨难才造就成为大师的——可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苏格拉底、布鲁诺、耶稣是被反动势力或异教当权者杀害的,他们在被杀害之前的社会政治环境也并不宽松;有的革命导师是被“逼上梁山”,从而“风风火火创九州”的,在这个过程中成就了革命,也成就了“科学巨匠”。他们的思想学说都具有原创的性质,要说“培养”,是谁培养了他们?当然有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但从根本的方面说,是社会培养和造就了他们,甚至是对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勇于挑战的结果。当然,我并不因此反对而是非常赞同为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为学术大师的产生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事实上,由于中央的高度重视,采取一些得力的措施,现在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应当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而且还在改善过程中。
有一位著名学者说:“只有坚持不懈地为学术而学术,才有可能产生大师。”如果说搞学术研究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当然是对的,但这是一个全称判断。这一论断就似乎排除了产生或成为学术大师的过程中,学者个人需要有社会责任感或社会使命感这样一个条件。
然而,仅就中国而言,从古至今,学术大师似乎皆有比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或使命感,这恰恰是他们在成就学术大师的道路上最强大的思想动力。
这里举几个例子:
孔子。史书上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为《春秋》是一部信史,在《春秋》中凡列入“乱臣贼子”名单的,就等于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所以“乱臣贼子”怕得要命。使“乱臣贼子惧”,可能是孔子作《春秋》的重要目的,用于治国安邦则是其根本目的。不过,《春秋》是否为孔子所作,学术界是存疑的,但至少是经过了孔子整理和修订的。
老子。从古至今,人们对老子有着深深的误解,认为老子的政治态度和对人生的看法是消极的。其实,处于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时代,从他对社会动荡原由的反思,从他总结的“古之善为道者”的经验,从他提出的关于人生和社会问题的真知灼见,从他渴望的太平盛世,足以看出老子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反过来说,如果他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就不可能写出《道德经》这样彪炳千秋的著作,不可能成为中国古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
司马迁。他自己说,他强忍奇耻大辱,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撰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他在《报任安书》中说的,他在同一封信中还说:“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现,虽万被戳,岂有悔哉!”从而可以看出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张载。他是宋代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他说,他的学术活动目的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事实上,不仅张载自己如此,中国古代许多著名学者都是怀抱这样的志向,从而成为学术大师的。
鲁迅。众所周知,鲁迅先生在文学上的成就最为卓著,但他原来是学医的,他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呢?他是从一部反映日俄战争的新闻纪录片中,看到一些中国人围观日本人砍中国同胞的头时完全麻木不仁。鲁迅由此得到感悟,认为治疗人们思想精神上的麻木要比治疗人们肉体上的疾病重要得多,于是决定弃医从文。他的代表作《阿 Q正传》就是向人们揭露所谓“国民性”的,使人振聋发聩。这说明鲁迅的文学生涯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下面,我想就如何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谈谈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现在研讨当代学术史研究,其最终成果是史论结合的论著《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呢,还是要写一部《中国当代学术史》的历史著作呢?对此我不很清楚。
如果要写成一部以问题为中心的《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我觉得现在的这部书还是不够的。这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宏观扫描”,下编为“个案论析”,而上编的“宏观扫描”,似乎主要是就“学术规范”、“反对学术腐败”、“学术评价”、“研究生教育”、“学术大师”等几个问题的讨论,皆带有相关问题讨论综述的性质,余三定教授虽然对这些问题作了分析,以及对不同观点作了辨析,但是还不够充分和深刻,应当作深度分析,对不同观点应当加强辨析。
关于当代学术史研究,余三定教授已经主持召开了八次研讨会。有几个问题讨论得比较深入,但有的问题讨论得还不够深入。对不够深入的问题,今后可以继续召开同一主题的研讨会。每次会议人数不一定多,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与会代表应当提供会议论文或比较详细的发言提纲,会上应有比较充分的研讨时间,而且举办方应将此一问题以往学术界讨论的综述在会前10天左右寄送会议代表,请他们参考,以进一步提高会议质量,避免研讨会上作低水平重复性的发言。这样做,有利于把问题引向深入。对于学术研讨会,我的主张是:人数少一点,代表面宽一点,会期长一点,准备充分一点,投入多一点,讨论深透一点。投入多一点,就是要舍得花几个钱,这是把研讨会开好的物质基础。为了提高研讨会的质量,我觉得宁肯多花一点会议费,是值得的。开这样的研讨会,有利于提高湖南理工学院的知名度,知名度是一种无形资产,它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因此,开明的院领导应当给予大力支持。
再就是现在所列的这几个方面是不是就够了?书的序言中说到陈平原教授提出了当代学术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我觉得亦应列入其中,包括“改革开放前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其实,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不仅是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以来仍然有这个问题,可从正反两个方面去分析,正面的方面就是学术是否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既然是以问题为中心,那么对于应列入的问题就应当很好地策划一下,力求全一些,使其成为一个系统,而且力求达到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如有必要,应把所策划的问题大纲初稿拿出来,召开一次专门的研讨会加以讨论,至少是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便加以补充和修订。
就“个案论析”而言,代表性的人物(准大师)似乎有待于调整和补充,比如中国哲学史界的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汤一介、方克立、张立文等,国学界的季羡林、庞朴、陈鼓应等,还有文学界、史学界、政治学界、社会学界、法学界、经济学界等的最著名的学者,都应加以论析。我觉得对在世的著名学者应事先寄送采访提纲,使其有所准备,然后亲自登门采访。因为有的著名学者年事已高,身体不好,这种采访具有抢救的性质,应抓紧安排,以免错失良机,追悔莫及。我之所以强调作个别访谈,是因为只有他们才最了解自己,否则所作出的论析就难免不够准确和切实。
如果要写成一部《中国当代学术史》,所遵从的编纂体例又是怎样的呢?
从古至今,写中国历史,就编纂体例而言,基本上是两种,一是编年体,这是绝大多数,二是纪传体。人们一般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是纪传体历史著作。但也并不尽然。比较准确地说,《史记》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若干帝王将相的传记构成的。就编年而言,《史记》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汉武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包括了当时的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
如果要写一部《中国当代学术史》,那么与李学勤主编的11卷本的《中国学术史》、张立文主编的6卷本的《中国学术通史》,以及步近智著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稿》等学术史著作的编纂体例等方面相比,应当有些什么突出的特点呢?亦应好好地加以研究。如果觉得有必要,亦应召开一次研讨会加以商讨。
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现在有二十几个一级学科,二级、三级学科就更多,而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学术史(无论是否已经写出来了)。《中国当代学术史》当然不可能是各个学科学术史的汇集。我认为《中国当代学术史》应当是建立在各学科学术史基础上的,旨在揭示和概括它们的共性,从中探讨出共同的特点和规律,而由于是结合各学科学术史谈问题,因而也可以写得丰富多彩。
余三定教授在序言中设专节论述了“当代学术史研究的未来展望”,分析得很有道理。《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或《中国当代学术史》如果写得好,对于学术研究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于广大学术工作者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也将成为重要的学术文化积淀。我认为有余三定教授及其助手们的努力,有在座的和不在座的高人的指点和帮助,在三五年内,这部著作和相关的阶段性成果一定会搞成功,一定会出一批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