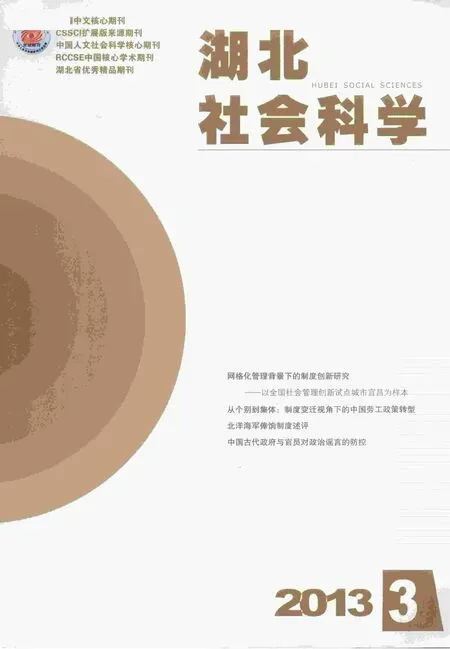必然与自由概念解析——以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融汇为目标
李宏昀
(华东政法大学 科学研究院,上海 201620)
……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至于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
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p89-90)
正如以上两段引文所显示的,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融汇,是马克思对未来的展望;就我而言,这也是我在一系列文章的论述中力图阐明的主题。之所以有必要这么做,是因为迄今为止的“自然科学”依然处于和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科学”的分裂、对立之中;无论从科学研究的实际状况上讲,还是从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常识性理解上讲,都是如此。
一、切入点:必然与自由概念的对立及其暧昧性
要领会这二者的融汇,先要理解它们分裂、对立的所以然。为此,首先必须找到一种恰当的方式来描述这一对立,以凸显出这一对立的本质内涵。依照康德对现象界、本体界的区分,我们似乎有了一个现成的办法:自然科学对应于现象界,处理的是人关于认识对象的知识,这个领域受“必然性”统治;而人的科学涉及的是人的行为(和道德相关),康德将之归入本体界,这个领域以承认人的“自由”为前提。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必然”和“自由”的对立理解为“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对立的本质内涵呢?倒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必然和自由这两个概念本身就有其暧昧不明之处;甚至有时候,它们的意义会纠结在一起、难以判然区分。这里先举两个例子:
物理上所谓的“自由落体”,在牛顿的体系里,恰恰就是“必然”的运动。这里的“必然”,意味着这一运动在整个系统中是被决定的,它完完全全是“自然规律”的体现,根本没有所谓“独立自主”的存在余地。顺便提一下,马克思所阐释的伊壁鸠鲁,正是通过对原子沿直线“自由落体”这一运动的否定来阐发自我意识的独立和自由;在这里,伊壁鸠鲁也严格地把“自由落体”理解为牛顿那个意义上的“必然”运动。
牛顿的物理学体系堪称“自然科学”的典范。可是,仅仅把“必然”归诸自然规律,这真的是天经地义的吗?在黑格尔看来,科学的“必然”规律其实是偶然的,因为它是“被理解”的;与之相比,“理解”本身才更有资格被称为“必然”的。在他的哲学中,最高的“可理解性”就是“自由”,而这“自由”同时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 “必然”——自由和必然概念在这一层次上再次融合了。
在上述两个例子中,自由和必然这两个概念都在某个层面上有所重叠。为了看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析这两个概念的内涵。
二、必然概念的两层含义
先来解析一下必然概念。
日常语言中,这词有本然、本该如此的含义;当事情按其“本该如此”的样子发生时,我们就倾向于说这件事的发生是“必然”的。然而,这里的“本该如此”根据何在?我们知道事情“本该如此”,是不是因为在既有的知识体系当中,这件事就处于如此这般的位置?这样的考虑就能引出必然概念的又一层含义:它是在一个体系中被决定的,故而是可理解、可把握、可预测的……如此等等。在此我们已经接近了自然科学中的必然概念。
然而在日常语言的含混理解中,上述两层含义是难以判然区分的。比如,我们把习以为常的事情看成是必然的,把难得的、显得不可思议的事情看成是偶然的:我们说人总是要死的,这是必然的;这话的意思既可以用大白话理解为“事情本来就该如此”,也可以比较有技术含量地理解为“我们既有的知识体系告诉我们,事情一定会如此发生”。而有人被陨石砸死,我们说这是偶然的;这里既可以包含“事情本来不该这样,这样是反常的”这么层意思,也可以包含“这样的事情暂时无法从既有的知识体系中推论出来,是无法预知的,因而是难以理解的……”这么层意思。
自然科学中的必然概念,着重的是后一层含义:在体系中被决定。科学的体系力求达成这样的理想:作为认识对象的事物各就其位;这些事物的状态可以用有限的法则来全盘地把握和预测。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一定条件下的事物处于何种状态应当是完全确定的——所谓“必然”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而“偶然”则是指事物“可能如此、也可能如彼”的状态,它是科学体系力图摒弃的(以上的说法固然不全适用于现代物理,但现代物理依然是一种以有限的法则来把握、预测事物状态的体系;在其中,传统的确定性概念遭到了挑战,这也为我们重新理解科学体系与人的认知的关系打开了一条路径——当然,这不是目前要讨论的话题)。
在这样的体系当中,我们就可以说,一切事物都受“必然性”支配;因为事物的状态被体系整体决定,没有任何独立自主性——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自由”不属于科学体系中的事物,这里没有“自由”的位置。
既然如此,那么事物沿直线下落的运动岂非彻头彻尾属于“必然”的吗?它何以会被称为“自由落体”呢?
看来,我们还得解析一下自由概念的多重含义。
三、作为“本然”的自由
“自由”可以意谓任意而为,不受任何外部条件约束,其状态无法用有限的法则来把握、来预测。作为和自然科学中的必然概念相对立的自由概念,其含义似乎就是如此。那么,这是不是“自由”一词唯一可能的内涵呢?
上面所说的不受任何外部条件约束,那是纯粹消极意义上的自由。若要给如此空洞的自由概念赋予积极内容,那或许是这样的:“自由”就是实现事物的“本然”。用日常生活中的老生常谈来说明这一点再容易不过了:有人说婚姻是对自由的约束;而有人说,只有在婚姻中,人的自由才得到真正的实现。克尔恺郭尔就曾用笔名扮演各种作者花了长篇大论来探讨这些。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自由概念的多重含义所构成的张力,而对于“本然”的不同理解也是问题纠结的源泉之一。
不知读者还记不记得,前面讨论必然概念的多重含义时曾经提到,“本然”也是必然概念的内涵之一。我们发现,在“本然”这个层面上,“自由”和“必然”重叠了。
带着这个眼界,我们就可以来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
自然科学那个意义上的必然概念在牛顿的体系中得到了堪称典范的发挥,然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则全然不同。亚里士多德把运动区分为必然的和偶然的。在他看来,出自物体“本性”的运动是“必然”的,比如重物从高处下落,这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完全是“本性”的表现;与此相对,物体受“外力”而“被迫”产生运动,那就是“偶然”的,比如弹簧受压收缩;而撤去压力后弹簧恢复原型的运动则又是“必然”的了,因为这是出自弹簧“本性”的。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发挥的是必然概念的前一层含义:本该如此,本然,出自“本性”。由于自由概念中也有“本然”这么一层含义,因此,物体沿直线从高处下落这一最为“必然”的运动被称为“自由落体”也是顺理成章的。这样的称呼,可以理解为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自然哲学所留下的痕迹。
在牛顿那里,“必然”和“自由”截然对立;而在亚里士多德,这两个概念是可以统一的。经过上述的分析我们知道,他们在运用这两个概念时,对于涵义的侧重点有所不同。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牛顿并没有驳倒亚里士多德,因为他们探讨的话题不在同一个层面?
四、“本然”在必然中消融
在前文分析“必然”的含义时,我们通过为“本然”寻求“根据”而接近了自然科学中必然概念的内涵:在知识体系的整体中被决定。在牛顿的体系中,“本然”这层意义上的“必然”已经完全消融在“被体系决定”这层含义当中了,“本然”终究没有了位置。从亚里士多德那个不受“外力”的意义上来说,或许纯粹惯性运动可以算是“本然”运动?但是在牛顿这里,这样的运动只是一个起“参照系”作用的设定,是为整个体系当中的计算、推导进程服务的,离开这个体系就没有意义了;而且,现实当中究竟是否存在这样理想的运动,也无关紧要。与此同时,事物的“本性”也没有位置了:事物被抽象为质点以及性质的载体等等,在系统中被决定、被把握、被操控。
上文所述,即事物的“本然”、“本性”在系统的整体运作中被消融、以致丧失自己位置的现象,我们可以在资本的现实运动中找到对应。马克思说,在封建的土地占有形式中,土地仿佛是领主无机的身体似的,它随领主而个性化,被领主的个性打上了感性的烙印;正如俗语所说:“没有无领主的土地。”而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使得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土地仅仅成了以地产为形式的资本之后,“中世纪的俗语‘没有无领主的土地’被现代俗语‘金钱没有主人’所代替。”[1](p46)
无须考虑具体事物的“本然”、“本性”,这对于操作来说意味着极大的便利:在自然科学中,承载着相等的可计量的抽象性质的事物是可以被自由替换而不影响操作后果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交往中,一切事物都有希望被换算成交换价值来自由地进行等价交换——即便这还没有完全成为现实,起码在理想中是如此;这就好比我们的自然科学,目前尚未实现完全的可计量化,但不可否认这是一个理想、一个努力的方向。
我们又一次和自由概念不期而遇:在这里,“自由”一词被用来形容可替换性、可交换性。“本然”这一层含义,倒是成了对“自由”的束缚;这里的自由,刚好意味着事物的“本然”全都被抽象掉、被夷平为数量关系了,于是事物之间可以自由地相互取代了——在这层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雇佣工人能够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也表达了“自由”一词的题中应有之义。
交换的自由,确实是自由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丝毫不奇怪。相对于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的大陆文明,古代希腊的海洋文明给人员的迁徙、物资的交换流通提供了较多的便利。在交换占据主导地位的生活方式中,抽象思维一定会比较发达,因为正如上文所说,把事物的“本然”抽象掉,这是自由交换的前提。古希腊文明以这种方式参与了对当代自然科学思维模式的奠基。既然交换的自由和抽象思维乃至自然科学之间有着这样的渊源,那么我们理所当然会在描述“本然”被必然、被体系消融的时候遭遇到它。
五、追问“本然”
康德所说的现象界,就是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知识来把握的世界。经过上文的讨论,现在我们容易理解,在何种意义上现象界是由“必然性”统治的:这里的必然,意味着事物在体系中被有限的法则所决定,因而是可预测、可操控的。
通过上文对自由概念几层含义的辨析,我们也能大略地知道,在何种意义上理解的“自由”才是和上述必然概念相对立、并且被康德拿来描述本体界的概念。雇佣工人自由地出卖劳动力这一现象,恰好可以用在这里作一个反面典型:此处的自由意味着夷平“本然”、抹杀个性,以便在可以已有的体系中自由地被交换、自由地转换位置——这层意义上的自由,完完全全地落在“必然性”的统治范围之内。康德的本体界所承认的“自由”,起码应该和“本然”这一层含义有关;而这一层次的“本然”应当是自然科学体系的“必然性”所消融不了的,要不然的话,本体界也就没有立足的根据了。
其实对于思维方式饱受自然科学熏陶的现代人来说,理解现象界的“必然性”应当没有什么难度;倒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必然”和“自由”的相容会让我们稍感困惑。时至今日,既然事物的状态在理想中完全可以用自然科学的体系来把握、预测和操控,既然“本然”、“本性”这层含义看起来已经完全消融在了体系整体之中,那么,对于“本然”的追究是否还有意义呢?究竟是否存在独立于知识体系、不必以体系为根据、甚至比知识体系更为根本的“本然”?抑或这种所谓“本然”只是形而上的妄想,可以被自然科学的“奥卡姆剃刀”剃除的?简而言之就是这么个问题:受“必然性”统治的自然科学知识是否足以把握和理解关于世间事物的一切?
关于这个,维特根斯坦曾这样说:
今天,闪电比两千年前似乎更为常见,更不令人震惊。
人必须清醒过来才会表示惊奇。大概所有的人都应该如此。科学是使人重新入睡的途径。[2](p6-7)
为何今天的闪电不再令人震惊?是不是因为,在自然科学体系预备好的因果链条中,闪电现象及其内部构造都已经有了明确的位置?它在知识体系中“被决定”了,人们能够说它是如此这般“必然”地发生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人已经完全“理解”了它?
或者,可不可以这样说:在此人们把握的是这一现象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前因后果”,甚至还能用因果链条来分析这一现象的内部构造……但也只是仅此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便我们完全掌握了关于闪电的“科学”,我们对于闪电现象“本身”仍然没有理解,甚至一无所知——维特根斯坦的上述言论要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那么如何才是“知”呢?维特根斯坦会说,为闪电感到震惊吧;“震惊”这一情感中就有本源的“知”。倘若掌握了科学知识便自以为是地认为再也没有必要“震惊”了,那就是切断了知识的本源;思维被自然科学彻底统治的人就堕入了“无根”状态——“科学是使人重新入睡的途径。”
用科学来把握现象的前因后果,这样的“知”竟然还不够?难道情感才是更为根本的“知”?这样的说法初看起来不容易被接受。人们从小就会关于各种现象追问“为什么”,对此一般的回答方式就是摆出这一现象在因果链条上的位置(为什么会有闪电?因为地面的阳电荷与云层底部的阴电荷互相吸引……如此等等);尽管对这一链条的追溯终归有尽头有界限,但人们久已学会满意并习惯于这一限度内的答案。但人们究竟何以会问“为什么”?如此追问的目的,当真原本就是为了得到“因果律”限度内的解答吗?来看看诗歌作品中的追问吧。以下是《楚辞·九歌·湘夫人》中的一段:
帝子降兮北渚,
目眇眇兮愁予。
嫋嫋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
登白薠兮骋望,
与佳期兮夕张。
鸟何萃兮蘋中,
罾何为兮木上?
沅有芷兮澧有兰,
思公子兮未敢言。
荒忽兮远望,
观流水兮潺湲。
麋何食兮庭中,
蛟何为兮水裔?[3](p45-47)
可称之为“追问”的是这么几句:“鸟何萃兮蘋中,罾何为兮木上?”“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翻成白话是这样的:“鸟儿为什么聚集在水草中,渔网为什么挂结在树梢上?麋鹿为什么到庭院里来吃东西,蛟龙为什么游到水边?”
为何要这样问呢?其余的诗句提供了情境。全诗以湘君的口吻,说的是湘君与湘夫人约会而湘夫人一直不来,描绘了湘君驰神遥望、祈之不来、盼而不见的惆怅心情。以上几句虽然是在追问“为什么”,但根本不是在盼望因果律限度内的答案;那样的回答也全然不能消解这里的追问——说到底,得不得到回答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追问表达了面对世界时的生存情感:恋人本该在身边而此时不在身边,于是发问者不能安心地栖居于这样的世界了,世间事物看起来显得陌生、反常,缺乏如此存在的理由……但何谓“有理由”呢?需要的不是因果律上的理由;也许只要和恋人在一起了,世界就不再陌生反常了,世间事物都会显得在应有的秩序中各安其位——于是再也无须追问“为什么”,如此这般地存在就是答案。
屈原的《天问》也是如此。诗人“指天画地有所争论”,到处追问“为什么”;然而他并不是想为天地间的事物、古往今来的事件寻觅勾画出完备的因果链条;那是失去了家国、无处安身立命的诗人在祈求命运的再次开启。
六、理解“理解”
现在来回顾一下本文第二小节讨论过的话题:必然概念的两层含义。其中的一层意思比较日常,即本然、本该如此;另一层较为接近自然科学中的用法:在体系中被决定,故而可以被把握、预测和操控。我们发现,有这么个意思,可以统摄以上的两层含义;它似乎比上述两层含义更为根本,那就是——“可以理解的”。
难道不是吗?当我们说,某件事情是必然的,那么我们多多少少表达出了这么个意思:这件事情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说,可以被如其所是地接受的。对于上一小节说到的“为什么”这类追问,“必然”可以成其为一个回答;无论它的用意侧重于“这事情本来就是这样,没什么好问的”,还是侧重于“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已经尽在我们的掌握……”
和“为什么”这样的追问相应的,就是本源意义上的理解。理解意味着暂时无须再追问;但同时,理解也是和追问相伴而生的,没有追问,也就无所谓理解。如上文所说,“必然”这样的回答,起码可以在两层意义上打消“为什么”这样的追问,这是因为,“可理解性”也是必然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感到无须问“为什么”了,事物可以理解了,那就是“理解”本身已经发动了……
到了这里,第一小节里提到过的黑格尔式的论述终于浮出了水面:科学的“必然”规律其实是偶然的,因为它是“被理解”的——换句话说,科学只不过是“理解”本身发动后的功用之一;与之相比,“理解”本身才更有资格被称为“必然”的。最高的“可理解性”就是“自由”,这意味着“理解”本身的充分发动,而这“自由”同时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必然”。
必然和自由概念在这一层次上的融汇,也可以说是融汇于 “本然”——当然,这层意思还有待下一小节的进一步展开。这一层次的“本然”统摄了人的“本然”和事物的“本然”,追问和理解的可能性也都在其中。顺便说一句,儒家的理想“成己成物”,我就是把它理解为实现、守护人和事物的“本然”。
其实,上面这些也算不上是我的创见。海德格尔说,“发问”行为本身即是“此在”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从而“此在”在存在论上具有优先地位。我相信,这一论述中也包含了与我的上述思考相类似的内容。
本源意义上的理解,或“理解”本身,意谓的就是光明的敞现、道路的开通,以便让孤独无助的人们能够在这陌生而充满危险的世界中暂时得以安居并生存下去。道路不止一条,而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便是对光明、道路和命运的祈求和决断。如何能够在面对世界时不再感到孤独无助?爱情是一条道路。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是一条道路。力图掌握、控制世间事物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这也是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可以通向自然科学的“必然性”体系。当然,止步于事物呈现给我们的感性直接性,不再追问而“活在当下”,这也是一条可能的道路;它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实现,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
在此我们看到,用自然科学来理解世间事物,这只是本源意义上的理解之种种可能性中的一种。自然科学的知识体系也并非理所当然地现成存在在那里静等人去发现,它是人类文明在生存斗争中通过决断创生并滋养出来的。只是时过境迁,如今的自然科学体系已如同星辰般冰冷而现成高悬于天空中,不再困惑不再挣扎不再悲悯,失去了命运的重量。但我们不该忘记,星辰原本来自混沌。
忠实于“理解”本身,也并不意味着排斥自然科学式的理解。它只是要求在践行一条道路的同时,保持对“混沌”的警醒和敬畏,以便让其余诸种可能的道路都保持着敞开的可能性;如此,也就能够对正在践行的那条道路存有一份批判的态度,道路本身的生命力正源于此。
七、康德的物自体:从现象界入手
像“苹果为什么会落地”这类话题,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应当不成其为问题,因为这就是事物的“本然”。而当牛顿对此进行追问(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这个具体追问,倒不是重点)时,“本然”运动和“被迫”运动之间的区别已经有了消融的倾向;牛顿想要做的是用简洁的法则把各种运动纳入到统一的体系中加以掌控,天文学上的实证发现也证明了他的成功。
当维特根斯坦说我们应当清醒过来为闪电感到 “震惊”时,他并非要我们从牛顿那个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体系中倒退回去,回到亚里士多德那个意义上去理解事物的“本然”——这层意义上的“本然”被自然科学的“必然”消融,几乎是不可逆转的。维特根斯坦确实在提醒我们注意闪电的“本然”;他的思考比自然科学的“必然”体系更进了一层,他所指示的“本然”,是前者消融不了的。要理解维特根斯坦这话的用意,康德的“物自体”学说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康德的现象界,对应的是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在康德看来,是我们的感性提供的直观形式以及知性提供的范畴加在感觉材料上,才做出了知识。简而言之,知识是由“心”规定出来的。现象界的知识体系并非对象本身、对象的“本然”;这个对象本身,康德称之为“物自体”。既然物自体不在现象界的知识体系之内,“心”提供的形式和范畴都没法规定它,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康德何以非要引入这么个概念呢?
在某些地方,康德将物自体解说成知识的“源头”或“起因”。但是,按照康德的学说,像“原因”这样的范畴是知性的产物,它只能用来构成知识,却不能用来规定物自体。可见,若是用现象界的因果性范畴来理解物自体的话,这学说本身就有了自相矛盾——确实,也曾经有人从这个方向批评过康德的物自体学说。可见,即便我们可以把物自体理解成现象界知识的源头或起因,这里的“起因”也不同于自然科学那个意义上的因果性范畴。
笔者认为,用这样一个比方来理解物自体学说,起码可以看清楚问题的一个方面:“心”规定出来的知识体系,就相当于地图;而物自体呢,则相当于风景本身。在既定的地图框架中增补细节,这相当于一般科学家的工作;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家,则对于地图的透视角度、投影方式等总体上的改变——比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之于牛顿的绝对时空观——有所推进。风景本身是我们可以直接去感知的;可是对于物自体呢,在康德看来,我们没有任何“知识”可说,因为一旦做成知识,就落进地图框架内了。不过,既然地图可以有不同的透视角度、投影方式,这起码表明,眼前的地图不是事情的全部,别样的地图也是可能的。在这层意义上理解的“物自体”,我愿意根据谢遐龄老师的见解,名之曰“本无”。[4]把物自体理解成现象界知识体系的源头或起因,这固然可以;但这么说仅仅是表明,眼前的知识体系是“理解”本身发动后的成果之一,“理解”的产物不可能被任何现成的知识体系所穷尽。也就是说,物自体标识出了这么一个可以称之为“本然”的维度:它对应着“理解”本身,它蕴藏着各种理解方式的可能性。这层意义上的“本然”,是知识体系中的必然所消融不了的;由此我们也可以明白,康德提出“物自体”的必要性何在。
八、康德的物自体:从自由入手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条进路来理解康德的物自体学说,那就是,从本篇讨论的必然与自由概念入手。
了解、掌握现象界的必然规律,以此来趋利避害,游刃有余地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把这样一种状态称为自由,看来顺理成章。确实,在现实中我们无法指望那样的“自由”,即随心所欲无拘无束,无视必然规律,仿佛必然性已经被全然“克服”掉了。相反,对于必然性的承认,才应当是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用斯宾诺莎的话来说,就是“自由即认识了的必然”。《庄子·秋水》中的这段话,描述的也是这一意义上的自由:
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兽弗能贼。非谓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宁于祸福,谨于去就,莫之能害也。[5](p341)
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合为一体的契机。既然明了现象界的必然规律是实现自由的前提,那么本文开头引用的马克思的话似乎就容易理解了。自然科学……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1](p89)这话里边大致可以先解读出这么两层意思:其一,为了生活,我们必须知道以必然性为特征的客观规律,所以自然科学向来就是生活的基础;其二,既然如此,那么人的科学应当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这些道理都没问题,那么,所谓“异化的形式”又是何意呢?
最关键的,是这么个问题:既然说自然科学是“基础”,那么人的科学中是否还包括自然科学涵盖不了的内容?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融合,是否意味着可以把后者完全还原为前者呢?于是又回到了前文的话题:是否存在知识体系中的必然所消融不了的“本然”?
从还原论的视点说,人的行为无非是由动机决定,而动机可以纳入因果性的范畴,于是说到底人的行为全都可以纳入到必然性的知识体系内。作为知性科学之分支的心理学、管理学等等,就是这样来处理“人的科学”的。
若要反驳上述视点,则可以这么说必然性的知识体系能够告诉我们的,无非就是达到具体目的所能使用的手段;正如庄子说的,认识必然性,我们就可以以此为指导趋利避害。但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究竟何为善、何为恶?这些问题涉及到价值判断,和人的道德有关;必然性的知识体系无法给我们提供答案,因为这就是人的“自由”所在,是必然的知识体系消融不了的“本然”——不错,康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了区别于现象界的本体界;在康德看来,人的自由不属于现象界的范畴,自由是“物自体”。
其实,从逻辑上说,上述观点倒也没有驳倒还原论。彻底的还原论者可以说,人把什么看成最终目的,人作出何种价值判断,这些终究是由人的性格决定的;至于人的性格呢,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纳入到必然性的知识体系中去研究,甚至也可以用科学的成果来塑造、控制人的性格——还原论的逻辑只要能走得彻底,眼下看来还是足以自洽的。当然现实中的科学尚未发达到这程度,但这不足以作为反对还原论的理由。在此,我不想就“自由意志”这个问题作过多形而上的探讨。要超越还原论,必须在视域的境界上笼罩住它。我只提出这么两点:第一,社会生活实践中,我们必须承认人能够自由地作出价值判断;起码就目前来说,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还是全然不同的,说到底是因为前者必须承认人的自由。第二,如前文所述,以必然性为特征的知识体系是“理解”发动后的产物,它仅仅是各种可能的理解产物中的一种罢了。倘若把视野限制在必然性的知识体系之内,那么就算是对于知识本身来说,也是斩断了源头活水,丧失了批判眼光。马克思说自然科学目前“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基础,他要表达的就是,人的“本然”在实践上有完全被必然性体系消融的趋向,于是所谓的“自由”就只剩下“丧失个性,在体系中可以自由地互相取代、互相交换”这么一层意思;这里的“自由”,无非就相当于雇佣工人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我已经阐释了康德“物自体”的两层含义:其一为现象界的界限,其二为本体界的自由。通过以上解释可以看出,这两层含义都指向同一个维度:必然的知识体系所消融不了的“本然”。于是在现象界、本体界的分裂、对立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二者融合的契机,即“本然”领域。黑格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必然”规律其实是偶然的,因为它是“被理解的”——用我的话说,它只是多种可能的理解产物中的一项罢了;与之相比,“理解”本身才更有资格被称为“必然”的。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最高的“可理解性”就是“自由”,而这“自由”同时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必然”。于是在“本然”领域中,自由和必然再一次地融合了。
前文中的维特根斯坦语录,也当如此理解:把握、运用自然科学中的“必然”,同时让“本然”领域坚守住自身、不被前者消融,如此才能实现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融会贯通。一方面,要对理解现象界的多种可能的视角保持开放态度,让无限丰富的现象界能够对人充分呈现;另一方面,要把必然的知识体系视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而非最终的目的和根据,以保持对前者的批判眼光——如此,就是所谓“成己成物”。
九、马克思笔下的必然与自由——通向历史批判科学之路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市场领域的的彼岸。……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必要条件。[6](p926-927)
在这里,马克思描绘了两种意义上的自由。其一属于此岸,大致上就是人与人团结协作,发展社会生产力,控制自然;其内涵不外乎就是尽量掌握必然规律为我所用,所以,“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另一层意义上的自由则位于必然王国的彼岸。它是 “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具体指的又是什么呢?是不是像马克思某段著名的话说的那样,一个人早晨打鱼,中午推小车,下午打球,晚上从事批判,这样充分发挥人之为人的各种能力,就是实现了“彼岸的自由”呢?但是,任何具体的行为,不是都得遵从客观规律吗?那么“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此岸的必然”?
本文的讨论提供了解答这一问题的眼界:关键依然在那个不能被必然消融的“本然”。承认“本然”,就意味着不把任何专门化、固定化的人类生活形态视为理所当然的、永恒的自然规律——这等看法即所谓 “意识形态”——而是把它视为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带着历史性的批判眼光来理解、运用具体科学的成果,保持其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变革的可能性,这样就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融合。作为融合之成果的活生生的学问,我们不妨称之为“历史批判科学”,这就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遗产。
当然,如果仅仅在思想上承认“本然”,那么即便融合的契机找到了,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在现实中依然会处于分裂、对立之中,真正的自由也依然位于“彼岸”。“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必要条件。”所以,历史批判科学的任务不仅仅是解释世界,改变世界也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维特根斯坦.文化和价值[M].黄正东,唐少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林家骊,译注.楚辞[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谢遐龄.砍去自然神论头颅的大刀[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5]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8.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