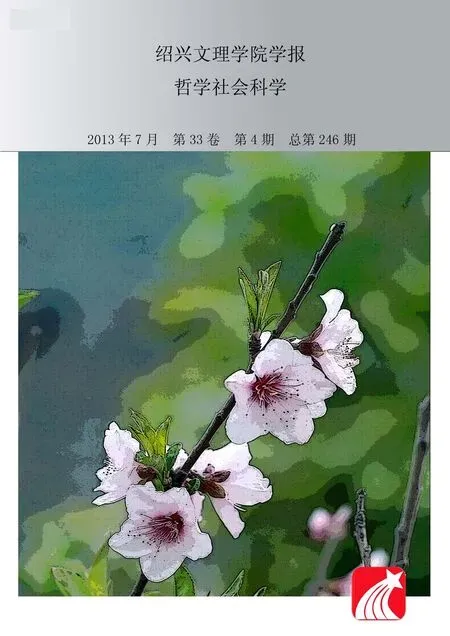鲁迅小说修辞传统性之魅力
许祖华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
鲁迅小说修辞的传统性是鲁迅小说民族性的一个具体方面,也是鲁迅小说艺术性的一个微观存在,作为鲁迅小说民族性的一个具体方面,鲁迅小说修辞的传统性具有彰显鲁迅小说民族性本质的功能;作为鲁迅小说艺术性的一个微观存在,鲁迅小说修辞的传统性则在文学艺术本体的层面显示了作为“语言艺术”的鲁迅小说获得成功的基本因素与原因。所以,对鲁迅小说修辞传统性的研究不仅是透视鲁迅小说艺术世界构造的杰出性的一个角度,也是界定鲁迅小说民族性的一个直接而具体的依据,具有显然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鲁迅小说修辞的传统性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遵循汉语自身的规范并充分发挥汉语在表情达意、叙事写人方面的所指与能指特性,遵循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的原则而灵活调遣、使用词语,又是最主要和最显然的方面,而此方面的研究又是之前关于鲁迅小说传统性研究的薄弱方面,所以,本文拟从这一关乎“文学是语言艺术”的艺术本质论问题方面展开相应的探讨,以期剔析凝聚在鲁迅小说修辞传统性中的诗性智慧及所投射出的厚重魅力,并由此直观展示鲁迅小说民族性的一个具体内容。
一、基于汉语词语能指特性营造的修辞效果
汉语作为一种表达观念、进行交际的人为符号,它与其他人为的语言符号一样,也是由其所指与能指在对立统一中构成的一个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中的符号,与其它语言符号一样,具有其他符号(无论是自然符号还是人为符号)所无法比拟的特点和优势,具有表达人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的无限可能性。不过,由于汉语是一种以表意文字为载体的语言符号,因此,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了自己与生俱来的个性特征,这种个性特征,从汉语的构成来说,既表现在语音方面,也表现在语词方面;既表现在物质外壳的字形方面,也表现在语法构成方面。而从语言功能的角度讲,汉语固然具有所指的功能,但却更具有能指的优势。这是因为,汉语,作为一种单音节的分析语,它既没有以表音为特点的印欧语那样复杂的构词形态,也没有印欧语那样确切的构形形态,“汉语也正是由于缺乏形态,才造成了词类的多功能性”[1]10,这种多功能性,既表现在同一个词在由句子构成的话语中能充当不同的成分方面,更表现在各类词语能指的优势方面。如,星期天,在“今天星期天”中充当谓语,在“星期天下雨了”中充当主语,在“星期天的任务完成了”中又充当定语[1]11。又如“好”这个词,请看鲁迅在《阿Q正传》中的使用:
“好了,好了!”看的人们说,大约是解劝的。
“好,好!”看的人们说,不知道是解劝,是颂扬,还是煽动。
鲁迅之所以判断在人们围观阿Q与小D“龙虎斗”的过程中发出“好”的声音时说“不知道是劝解,是颂扬,还是煽动”,是因为“好”这个词语,本来就“能指”多种心理倾向,能表达多种情感倾向,能以多种“音响形象”表达人的多种“心理印迹”。
也正是因为汉语具有能指的天然优势,所以,“在几千年的汉语文学史上,中国的大小文人无不纷纷投入诗词曲赋、散文与小说的创作,将大量的心血化在文学作品能指面的营造上”[2]16,并在长期的文学实践中,使“汉语文学一直有一个重视能指的传统”[2]117。鲁迅的小说创作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词语的运用(修辞)中充分发挥了汉语词语能指的优势,在负载深刻的新思想的过程中,将汉语文学这种重视能指的传统既给予了有效的发扬,更光大了这种传统的魅力,并由此较为直接地显示了自己艺术世界的传统底蕴和在此基础上的革命性创新。
鲁迅小说对汉语文学重视能指传统的发扬与光大,首先就表现在遵循修辞的规律精心选择词语方面。鲁迅小说对词语的选择,一方面最大限度地运用汉语能指的可能性,在具体的话语中最大限度地体现词语的价值并进而构造繁复而深刻的意义;另一方面则从成千吨的汉语“词矿”中精挑细选既与所要描写的对象及所要叙述的事情相吻合,又包含着自己或悲凉,或沉痛,或愤懑的情感内容以及睿智而丰富思想的词语。前者,在遵循汉语特点和规范中,以最直接的方式突显了鲁迅小说作为典范的汉语白话文的民族特色;后者,则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规范中直接彰显了鲁迅小说化古为新的艺术创造性本质。而这两方面所形成的最终结果,则是小说艺术世界的美不胜收。
汉语能指的可能性,从修辞学的角度看,是巨大的。陈望道先生曾说:“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所谓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一半是这些语言的习性,另一半是体裁形式的遗产。”[3]20所谓语言的习性,即语言的所指与能指的规范;所谓体裁形式的遗产,即传统的修辞手法,如赋、比、兴等。鲁迅小说修辞在这两个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
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规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具有任意性,即“能指和所指的联系上是任意的。”[4]102这种联系上的任意性,既表现在不同语类中,也表现在同一语类中。在不同的语类中,同一个所指(概念),可以由不同的音响形象(能指)来表现,如,树的所指,就与用作它的能指的声音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因为,树这个所指,在汉语中可以用shù的音响形象(能指)来表示,在英语中则可以用tree的音响形象(能指)来表示。在同一语类中,一个概念(所指)则可以有不同的音响形象(能指),在汉语中的“同义词”就是如此,如,表示太阳光的所指,既可以用“阳光”这个音响形象,也可以用“日光”这个音响形象。二是,能指又具有建立在社会的“约定俗成”基础上的不自由性和强制性,即“能指对它所表示的观念来说,看来是自由选择的。相反,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却不是自由的,而是强制的。”[4]107也就是说,修辞在利用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时,都必须遵循这些规范,只有遵循了这些规范,修辞才可能使包括词语在内的语言文字的能指功能得到合理而充分的发挥。
鲁迅小说遵循修辞的规律选择词语的时候,没有疑问是严格地恪守了词语的能指和所指的规范的,并且,很好地发挥了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的特点。不过,鲁迅小说词语修辞的可贵,并不仅仅在于遵循了能指与所指的规范,也不仅仅在于很好地发挥了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的特点,更在于构造了溢出词语所指的丰富意义,让词语能指的可能性实现了最大化和最佳化,以四两拨千斤的驾轻就熟,显示了汉语词语能指的非凡能量与强劲的魅力,将中国汉语文学重视词语能指的传统给予了发扬光大。如《孔乙己》中的“偷”与“窃”两个同义词的使用,就既体现了遵循所指与能指规范,更构造了具有丰富意义的词语修辞效果,既发扬了汉语文学重视推敲字词、重视词语能指的传统及追求“语不惊人誓不休”的精神,又根据表情达意和塑造深刻人物形象的目的给予了创造性的使用。
从词语所指的角度看,偷与窃两个词语作为概念所指的内容具有完全的同一性,都指将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的行为;但从词语能指的角度看,两个同义词的能指却至少具有两重明显的区别:首先,两个词语的音响形象不同,一个发tōu音,一个发qiè音;其次,两个词语的语体色彩不同,一个是可以在口头交际中使用的词语,一个则是地地道道的书面词语。正是两个词语在能指方面的不同,很有效地完成了小说艺术构造与思想情感表达的多重任务,也具有了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进行多重阐释的内涵,其显著的艺术效果也可圈可点。这些内涵和艺术效果,在我看来,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阐释:一个方面是,孔乙己用“窃”置换“偷”的言语行为,很真切而具体地表现了人物当时的心境,即孔乙己不想让自己做的不光彩的事被人知道,他之所以用“窃”更正别人使用的“偷”这个词,不仅因为窃的发音开口较小,而且因为作为书面语的“窃”的所指内容“短衣帮”的人大多不理解。从语言交际的角度讲,当一个词语被说话者说出,而听话者不能理解词语所指的内容的时候,交际也就无法再进行下去,当孔乙己说出的“窃”不能被短衣帮的人所理解之时,也就是交际停止之处,而当交际停止之后,孔乙己自己所做的不光彩的事也就在孔乙己自己的感觉中被模糊过去了(尽管事实上并没有被模糊过去);另一方面是,孔乙己用“窃”置换“偷”的言语行为直接揭示了人物的精神状态,即孔乙己尽管已经潦倒不堪了,却还要显摆读书人的架子,他用地道的书面语“窃”,至少在他自己看来,这正表明他比目不识丁的“短衣帮”要高一等,尽管无论从生存状态还是从谋生能力方面,孔乙己并非高人一等;第三个方面则是以简单而实用的修辞技巧,通过幽默的手段表现了鲁迅对人物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态度以及隐含的批判思想。
至于鲁迅小说充分发挥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特点使所选择的词语的能指功能得到充分体现的例子就更多了。随便列举一例即可由一斑而窥全豹。请看《故乡》这篇小说中的一段文字:
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
在这段话语中,有三个词语的使用是颇具匠心的,一个是一气,一个是隔绝,还有一个是隔膜。这三个词语在这段话语中的存在,从修辞的角度讲,我们完全可以说,既符合消极修辞的基本要求,更符合积极修辞的最高标准。消极修辞的基本要求是运用词语表达意思的明白、准确、纯正,即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所说:“消极修辞的总纲是明白。”[3]49这三个词语在话语中的存在正具备了消极修辞的品格。语言学家周振甫先生结合小说《故乡》所写的内容分析这三个词语达意的确切性时,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评说:“在这里,两次用了‘一气’,这是说宏儿在想念水生,宏儿和水生两个孩子相处得好。用‘一气’指两个孩子在几天的相处里,亲密无间的意思。这里不用‘一起’而用‘一气’,‘一起’只能说明在一处,没有亲密无间的意思,用‘一气’才是亲密无间。这里前面用了‘隔绝’,后面用了‘隔膜’,都有讲究。‘隔膜’只是因为大家不在一处,又不通音讯,不了解彼此的情况,变得‘隔膜’。这种‘隔膜’,要是大家又聚在一起,彼此情况又有了了解,就可打破。‘隔绝’是两人的思想感情完全不同了,‘我’叫他‘闰土哥’,他却叫‘我’‘老爷!’‘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即使‘我’不走,闰土仍在‘我’家打杂,这层厚障壁也无法打破了,所以称为‘隔绝’。”[5]303周振甫先生的分析,既基于三个词语的所指,又基于三个词语的能指,不仅言简意赅地解说了三个词语作为概念的所指特征及与作品中内容的高度一致性和严密的契合性,又切中肯綮地解说了三个词语能指的联想性意思,从而有力地揭示了这三个词语表情达意、叙事写人的明白性、准确性的修辞效果,可谓言之成理而持之有据。
如果说消极修辞追求的表达效果是准确的话,那么,积极修辞追求的目标则是词语表达的生动、深刻并意味深长,其审美意蕴套用一句俗语来说就是“增加一寸则长,减之一分则短”,换一个词则意蕴锐减甚至全无。汉语文学史上众多作品的成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如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中名词动用的“绿”词的使用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这种积极修辞,从词语运用的角度讲,更能充分发挥词语的能指功能,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文人在文学创作中如此重视积极修辞,甚至达到“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的地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面所列举的鲁迅小说《故乡》中的三个词语的使用,不仅达到了消极修辞的境界,更具有积极修辞的效果,这种效果的最明显表现就是它们无法被置换,如,如果将“一气”换成“一起”,虽然在表达宏儿与水生在一起玩耍的意思上没有根本性的影响,但是,却使小说所描绘的情景:宏儿与水生的亲密无间的韵味荡然无存了,呈现在作品中的除了一种事实之外,留给人品味的审美内容则没有了依凭的文字和寻索的线索,更为重要的是,也使后面“宏儿不正想念着水生”的叙述,没有了直接的依据。至于将隔膜与隔绝对换也是如此。所以,周振甫先生说:“这里的‘一气’,要是用了‘一起’,就不能表达出亲密无间的意思,就显得分量不够。要是这里的‘隔绝’用来‘隔膜’,那末无法打破的厚障壁的意思表达不出来,分量也轻了。要是这里的‘隔膜’用了‘隔绝’,那又显得太重,使上面用‘隔绝’处的用意反而模糊了。”[5]304周先生虽然主要是从达意的角度作出的判断,但也用简洁的判断说明了这三个词语与小说审美意蕴的关系,所谓“分量轻了”“显得太重”了其意所表达的就是小说审美的平衡性被打破了,当这种平衡被打破之后,小说的审美价值也就直接受到了损伤,甚至是伤筋动骨的致命的损伤。鲁迅小说这种精心运用词语的匠心与中国传统文人们千锤百炼词语的慧心如出一辙,都表现了对词语能指的倾情倾心。
二、罕见文言词语使用的修辞效果
就体裁形式的遗产的运用来看,鲁迅小说的修辞可以说是集大成,中国传统修辞学所青睐的各种修辞手法、辞格,汉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所采用的修辞方法、技巧,鲁迅小说不说全部含纳了,但至少主要的修辞手法在鲁迅小说中都有杰出的采用。不过,从发挥汉语词语能指特长的角度来看,我这里只准备选取这样一个内容,即,鲁迅小说对传统文言词语的运用及所形成的修辞的创新性。鲁迅小说对这些文言词语的采用,不仅在最基层的意义上构成了鲁迅小说修辞的传统性,而且,鲁迅小说对这些文言词语与白话词语的有机结合所形成的修辞效果,还以最显著的事实实现了五四新文学兴起之初,新文学先驱所提出的白话与文言合一的愿望,并由此显示了白话文学在语言层面的继承与革新。
鲁迅在谈自己的文学创作时曾说,如果“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6]。正是这样一种务实的态度和随物赋形的遣词方式,使鲁迅小说所采用的文言词语(古语),不仅得心应手地完成了用白话无法完成的表情达意、叙事写人的任务,而且,也激活了文言词语的生命活力,使这些文言词语如出土的文物一样地显示出自己无与伦比的价值和意义。不仅那些已经成为文学作品经常使用的词语,如成语的使用是如此,如《阿Q正传》中的“敬而远之”“著之竹帛”“刮目相看”等(将在第三部分分析),即使是那些在今天看来是比较罕见的,在传统的叙事文学中也鲜有采用的文言词语也是如此,如《故乡》中的辛苦“恣睢”等。但,在鲁迅的小说中,不管是哪一类文言词语的使用,都不能简单或仅仅只从词语的“所指”来解释,而必须从词语的“能指”性来解读;都不能只按消极修辞的原则来衡量,而应该同时按积极修辞的效果来看待,这是因为,鲁迅小说对文言词语的使用,从来就没有局限于文言词语的所指,其词语修辞的效果,有时虽然与消极修辞的原则相一致并达到了消极修辞所要求的基本效果,但更为常见的则是与积极修辞的准则相吻合并实现了积极修辞的目的,所以,我们分析鲁迅小说对文言词语采用的艺术效果,就必须要有全面的眼光,采用较为多样的视角,并从多个层面展开论析,如此,我们才有可能较为得体地把握鲁迅在自己精粹的白话小说中使用文言词语的匠心以及这些文言词语使用的意义和价值,也才有可能言之成理地揭示这些文言词语所指的传统性内容与鲁迅小说民族性风格的关系,也才有可能剔析这些文言词语能指的艺术能量在提升鲁迅小说艺术和思想境界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鲁迅小说在词语使用方面的创造性和杰出性。否则,误读和误解也就不可避免。如,对《故乡》中“恣睢”一词的阐释与解答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有人曾将《故乡》中的恣睢作为一个贬义词解释为“任意胡为”[5]304,此说并非没有道理,从历史文献来看,《荀子·非十二子》中即有“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之说;《风俗通·怪神·城阳景王祠》也有“吕氏恣睢,将危汉室”之说;《史记·伯夷传》中也有“暴戾恣睢”之说;近代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也有“那时候日本人在台湾恣睢暴戾,台湾人民畏之如虎”之说。等等。这些文献中使用的恣睢一词,均可以解释为“任意胡为”。但,将鲁迅《故乡》中使用的恣睢一词解释为“任意胡为”,则似乎不妥,不妥表现在各个方面,首先,这一词语的“任意胡为”的意思与前一个词“辛苦”的意思放在一起,不仅难以达到消极修辞准确性的基本要求,而且还因为不协调而不好理解。其次,如果将这个词语所在的整个句子“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与前面一句“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结合起来看,鲁迅所要表达的意思更模糊了。其三,由此,还直接影响了对这个词语所在的句子中别的词语所指(概念)的理解。如,有人就将恣睢所在句子中的“别人”解释为是指剥削阶级的人[5]304。之所以将“别人”解释为“剥削阶级”的人,是因为似乎只有剥削阶级才“任意胡为”。姑且不论此说的历史局限性和思想方法的生硬性,也姑且不谈鲁迅在创作《故乡》时是否具备了鲜明的阶级意识,即使从恣睢与辛苦两个词语搭配的角度来看,此说也难以自圆其说。辛苦虽然在词性上是一个中性词,但在使用中却多带褒义性,如,在日常交际中我们常说“您辛苦了”或“辛苦的劳作”,却没有谁说“辛苦的偷窃”“辛苦的杀人”,而意指“任意胡为”的恣睢又具有贬义性,一个具有褒义性的词与一个贬义词如此搭配,不仅不伦不类,而且莫名其妙。而如果进一步的将整句话一起来解释那就更无法自圆其说了,难道鲁迅是说不要如“剥削阶级的人的辛苦而任意胡为一样的生活”?这显然不符合鲁迅所要表达的意思。而如果说辛苦与恣睢并列搭配,表达的是鲁迅对剥削阶级的讽刺之意,但这种所谓的讽刺又与整句话所针对的“我们的后辈”的“真诚”希望相悖,也与小说中始终贯穿的沉痛、悲凉的情感相左。可见,仅仅从词语所指的内容并按照消极修辞的准确性原则来解读、分析鲁迅对恣睢这个文言词语的使用,不仅难取鲁迅小说使用文言词语的“真经”,而且还会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境地,更会损害鲁迅小说艺术的杰出审美价值。所以,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来解读这个文言词语,即从能指和积极修辞的角度来分析鲁迅在小说中对这样一些文言词语的使用。
不错,恣睢这个文言词的所指的确有“任意胡为”的意思,在我上面所列举的文献中,恣睢这一词语常与“暴戾”一起使用,描摹的是“日杀不辜,肝人之肉”的暴行,饱含了文献作者们对这种暴行的憎恶之情与批判之意。在这里,不管是按照上下文的所指,还是按照词语本身的概念内涵,将恣睢解释为“任意胡为”都是十分明了、准确并完全符合消极修辞的标准的。但如果按照《故乡》中使用恣睢这一文言词语的上下文的能指和积极修辞的要求来看,这个文言词语就不能解释为“任意胡为”。因为,词语(符号)所指和能指的组合固然具有任意性,但又可以具有动机性,其动机性主要由词语的能指体现出来,因为符号的音响形象(能指)包含着人的“心理印迹”。如果说,所指和消极修辞讲究的是明白、准确,那么,能指和积极修辞则更讲究灵动、鲜活,更讲究“化腐朽为神奇”,在文学领域,则更讲究通过词语的变异或超常搭配将平常词语艺术化,将古典词语现代化。鲁迅自己就常常如此,他不仅在杂文中常常“任意而为”地使用古语,在小说中也频频如此,如,在杂文《华盖集·导师》中鲁迅就“任意”改造了“笑容可掬”这个古语,而自创了“灰色可掬”“老态可掬”等词语;在小说《阿Q正传》中,鲁迅不仅任意改造了一些古语,如“牢不可破”,并在“老尼姑见他失了锐气,便飞速的关了门,阿Q再推时,牢不可开”这样的句子中使用,而且还“有意”地拆分了一些古语,如“肃然起敬”,并在“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这样的句子中使用;鲁迅不仅常常改造、拆分古语,而且还常常“腰斩”古语,如《头发的故事》“顽民杀尽了,遗老都寿终了,辫子早定了,洪杨又闹起来了”中的“寿终”就是“腰斩”古语“寿终正寝”的结果。鲁迅在小说中不仅喜欢任意或有意地改造古语、拆分、腰斩古语,而且还常常“反其意”地使用文言词语,如《示众》中的“首善之区”中,对“首善”这一文言词的使用;《阿Q正传》中“颇可以就正于通人”的“通人”这一文言词语的使用,还有“阿Q……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中的“完人”这一文言词语的使用等等,都与这些词语所指的正面意思相反。总之,在我看来,鲁迅在自己的白话小说中使用文言词语的时候,他更多的是依据这些词语的“能指”,而不是所指将它们安放于相应的句子中的。他既没有将文言词语“用死”,更没有“死用”文言词语。所以,我们解读鲁迅小说中的文言词语,也应该而且必须考虑鲁迅这个语言大师使用语言,包括使用文言词语的习性,如此这般,我们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这些词语在小说中的作用和效果的应有境界,才有可能更好地解说鲁迅小说修辞的传统性与创造性关系以及鲁迅小说修辞的杰出性与典范性。
如果按照我上面的所论来解读恣睢这个词语的能指,即根据鲁迅遣词造句的习性,特别是鲁迅用文言词而不将文言词“用死”或“死用”的习性,并根据这个词语存在的上下文和《故乡》这篇小说的主旨及情感倾向来进行解释,我认为,“恣睢”这个文言词语可以“翻译”为“放任自得”或具有现代意味的“据意而为”及“为达目的而为”。这是因为,在历史文献中,古人在运用这一词语时,本身就曾在“放任自得”的层面上使用,如,《庄子·大宗师》就有“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途乎?”成玄英疏:“恣睢,纵任也”,陆德明释文:“恣睢,自得貌。”我之所以如此“翻译”恣睢这个文言词语的意思,除了上面的一些事实、文献依据和鲁迅使用这一文言词语的动机依据之外,其实还有理论的依据,其理论依据主要有两个,一是能指本身的特性;二是文学语言生存的条件。关于能指本身的特性,索绪尔曾经指出:能指作为音响形象,它总带着人的“心理印迹”,具有联想的可塑性,它不似所指(概念)那样具有约定俗成的固定、明确的内容,而是充满了多种的“可能性”;关于文学语言生存的条件,索绪尔曾经指出:“文学语言是凌驾于流俗语言即自然语言之上的,而且要服从于另外的一些生存条件。”[4]194这些生存条件除了别的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文学的情境、语境和上下文,而词语的所指一般是不受这些生存条件限制的,如松柏这个词组,无论在什么文本中出现,它们的所指都是指两种植物,但它们的能指却会因情境、语境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联想,如“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在能指的层面,这里的松柏就不仅指植物,更是指人的人格和某种品格。这也就告诉我们,既然语言的能指具有这样的特性,我们就应该按照语言能指的特性来解读相应的词语;既然文学语言的生存,要依赖其所处的情境、语境和上下文,那么,我们当然也应该从情境、从语境、从上下文的关系解释具体的词语。既然词语的“能指”具有心理印迹的特性,还具有联想的可塑性,那么通过“恣睢”所指的“任意胡为”或“放任自得”联想到“据意而为”“为达目的而为”,套用鲁迅在《阿Q正传》中的话来说,“大约也就没有什么语病的了”[7]。而且,从小说的情境、语境和词语的上下文来看,如果将恣睢“翻译”为“据意而为”或“为达目的而为”,则不仅可以使“辛苦”与“恣睢”的搭配得到较为合理的解说并由此而与这两个词语所在句子的意思形成一个整体,而且其他的一些解释也可以水到渠成,如,句子中的“别人”,我们就不需要非将其解释为是指“剥削阶级”,完全可以将其看着是泛指“一类人”,一类“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辛苦”“而为”的人,如小说中的“豆腐西施”就属于这类人,那么,鲁迅希望“我们的后辈”不要像“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的意思,也就可以有理有据地解释为“不要像豆腐西施这样的小市民一样,为了得到一点小便宜而辛辛苦苦、费尽心机。”同时,鲁迅所说的“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的说法,也可以得到解释,的确,在白话中,没有一个现成的词语能替代“恣睢”这个古语在整句话中的能指,也没有一个现成的白话词语能在与辛苦的搭配中构成与“辛苦展转”“辛苦麻木”相匹配的词组。这正是鲁迅小说使用文言词语的匠心之所在,也是鲁迅小说“化腐朽为神奇”地使用文言词语,将古语现代化的神采之所在。
三、成语使用的修辞效果
至于鲁迅小说对文言中成语的使用,则更为神采飞扬。鲁迅在《集外集拾遗·〈何典〉题注》一文中曾经从自己使用成语的艺术体验和理性认识出发,十分深刻地指出:“成语和死古典不同,多少现世相的神髓,随手拈擉,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又即从成语中,另外抽出思绪;既然从世相的种子出,开出的一定是世相的花。”[8]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鲁迅对成语的青睐,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创作(包括一般的语言交际)中使用成语,能“使文字分外精神”;二是,成语多少总凝聚了“世相的神髓”,在创作和一般交际中使用成语,能言简意赅地描摹或揭示历史与现实的“世相”。他自己在小说中使用成语,也主要遵循了自己的认识,也完好地实现了自己使用成语的两个目的并潇洒自如地发挥了成语在小说中的其他作用。这两个目的的实现及对成语作用的发挥,不仅卓有成效地凸显了鲁迅小说醇厚、典雅的传统审美情趣和深沉、聚合的现代思想内涵,而且彰显了鲁迅小说流利通脱的修辞魅力,从而使成语这种特殊的汉语词语的能指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使小说的艺术世界在美轮美奂中焕发出了无与伦比的个性风采。
鲁迅创作的三十三篇白话小说,无论是现代小说,还是历史小说,大多数都使用过成语。不过,鲁迅小说中使用的成语,有的是“原生态”的成语,即规范的成语,如《狂人日记》中的“食肉寝皮”“易子而食”,《孔乙己》中的“君子固穷”,《一件小事》中的“耳闻目睹”,《补天》中的“莫名其妙”等;有的则是根据表情达意的需要改造过了的成语或化用的成语,如《一件小事》中的“头破血出”就是从成语“头破血流”改造而来的,还有前面我曾经提到过的“牢不可开”,就是从成语“牢不可破”改造来的,还有通过对成语的“拆分”“腰斩”等改造的成语。至于像《祝福》中所叙写的“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则是从成语“一灯如豆”化用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则是从成语“芒刺在背”化用的。但不管使用的是什么形态的成语——原生态的抑或是改造过的,也不管是“直用”成语还是“化用”成语,鲁迅对成语的使用都不仅达到了“使文字分外精神”并凝炼地显现“世相”的艺术与思想目的,而且还常常成为了小说中的一个个亮点;这些成语的使用,不仅为小说叙事、表情、达意、写人奠定了基础并使小说锦上添花,而且,还往往很有效地“以一斑而窥全豹”地彰显了主旨。如,《狂人日记》中“食肉寝皮”“易子而食”两个成语就直接与小说的主旨相关,两个成语的使用又以中国文学最传统的修辞手法——引典,简洁地表达了小说主旨的根本内容。众所周知,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的目的,就是为了暴露家族制度与礼教的弊害,而礼教和家族制度的根本弊害鲁迅将其概括为“吃人”,而这两个成语的所指就是“吃人”,而且是“概念”所指的吃人,即“吃人的肉”。同时,由于这两个成语都是历史掌故的凝聚,即“典故”,反映的是中国历史长河中上演的一幕幕“吃人”的惨剧,因此,这两个成语在思想层面凝聚的就是残酷的吃人“世相”,在艺术的层面,这两个成语的使用则形成了历史与现实情景的自然勾连,即中国历史上吃人的情况与现实吃人情况的勾连;历史上有“食肉寝皮”“易子而食”的怪象,现实中则有“狼子村的现吃”的惨象,从而,使现实的“吃人”与历史上的“吃人”连成一气,增加了小说的历史纵深感和现实的厚重感,也使小说中狂人的惊人发现,即,“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有了历史的依据并由此使狂人的这一发现与“食肉寝皮”等成语所凝聚的史实构成了“互文”性:狂人发现的是仁义道德等封建精神文化的吃人;“食肉寝皮”等成语揭示的是本义和物质意义上的吃人。两者结合,则全面地揭示了封建制度与礼教吃人的本质:不仅麻醉人的精神,而且还直接毁灭人的肉体。从两个成语使用的艺术效果来看,则不仅仅使“文字更精神”了,而且它们还以文献资料的形式,为小说全面揭示封建制度与礼教吃人的本质提供了历史的依据,而这个历史的依据并不是长篇的文献资料,仅仅只是两个成语,这又在艺术的叙事方面,大大地减轻了叙事的负荷和文字的负荷,使小说真正具有了“以一当十”的审美效果。在修辞的层面则形成了“其称也小,其意却张”的积极修辞效果。中国传统文学遣词注重能指,修辞讲究“引典”而实现言简意赅的艺术追求的神髓,在这里也得到了发扬光大。
同样,《孔乙己》中的“君子固穷”这个成语,也具有这种积极修辞的效果。“君子固穷”虽然只有四个字,从其所指和能指来看,却几乎概括了小说主要人物孔乙己外在与内在的主要特征及微妙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状况,也巧妙地揭示了主要人物与周围“短衣帮”的关系,还不露斧痕地显示了鲁迅对人物的情感态度及讽刺意味。从词语的所指来看,“穷”可以说是孔乙己真实的生存状态的概括,他一贫如洗的境况,正符合“穷”这个词语所指的生活资料缺乏的本义;“君子”的本义是有修养的人,而这些人大多是读书人,孔乙己正是读了书的人,所以,这个词正是孔乙己作为读书人身份的概括。但从“固穷”这个词组的所指来看,孔乙己的所作所为,如“偷书”,又恰好与“固穷”这个词语具有的本义“固守其穷,不以穷困而改变操守”的意思相反,由此,鲁迅“含泪的微笑”的讽刺之情、之意,也就力透纸背地渗露出来了。从词语的能指来看,由于这个成语是从孔乙己口中说出的,作为“言为心声”的这个成语的“心理印迹”烙下的正是孔乙己虽穷困潦倒却自命不凡的精神状态和穷酸迂腐性格特征。如果再结合这个成语后面的“小人穷斯滥矣”来看,我们则更会发现,原来,孔乙己不仅自觉地将自己与“短衣帮”分开了,而且,在他心里,只有“小人”,如“短衣帮”才会穷斯滥矣,自己一个读书人,一个君子,是能“固穷”的,这也就难怪他一个穷困潦倒到只能与“短衣帮”一起“站着喝酒”的“读书人”敢于理直气壮地申辩:“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很显然,孔乙己的强词夺理不是来自现实的依据(事实上,在现实的层面他也实在找不到任何依据),而是来自他心里的自我感觉,即他还认为自己是“君子”,既然他自认为自己是君子,那么,他拿别人的书,也不过是为了读书,自然就不能算偷了。他的思想逻辑就是如此,尽管这种逻辑十分荒唐,但对孔乙己来说,却是顺理成章的。鲁迅在小说中如此展开相应的叙述与描写,也就同样显得顺理成章了,“君子固穷”一个成语的能指性也就不仅仅作为一个“言为心声”的词语烙印了孔乙己的“心理印迹”,也表现了鲁迅在发扬传统中国文学重视词语能指功能,使用引典修辞手法方面的卓越才能和所取得的艺术成就。
还有《一件小事》中改造过了的成语“头破血出”的使用,也别具匠心,同样具有积极修辞的艺术效果,其艺术效果不仅达到了鲁迅所说的使用成语的两个境界,而且还超越了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小说《红楼梦》对这一词语的使用。这也正是这一词语使用的杰出意义之所在,也是我之所以专门分析这一词语的使用效果的重要原因。
从小说所写之事来看,这个词语,既与小说所描写的情况相吻合,又与“我”当时责怪车夫多事的心理活动一致,从小说情节展开的角度来看,完全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这个被改造了的成语的使用,才不仅使小说内容的叙事得以顺畅地展开,而且也为情感的表达提供了真实的基础。小说前面写“我”看到女人是“慢慢地”倒下的,而车夫拉车的速度也不快,且已经开始停车了,所以,车子即使将女人碰出了血,也只能是“出”血,而不会“流”血;正因为女人是“出”了点血,而不是“头破血流”,也就表明女人完全没有生命危险,“我”这个正赶着要去办事的人责怪车夫多事的心理活动也才有了依据。同时,也是因为女人仅仅只“出”了点血,而车夫却并没有因此而马虎处理或根本不理,而是毫不犹豫地、负责任地扶起她走向警察所,车夫的形象在“我”的眼中,特别是在“我”的心中的“高大”也才有了依托,而“我”最后的反省也才显得“真实”,小说的题目“一件小事”也才显得“名副其实”了(如果车夫将女人撞得‘头破血流’,直接危及到了女人的生命安全,那就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大事’了)。所以,这个被鲁迅改造了的成语在小说中的使用,的确就有鲁迅在论成语时所说的各种妙处:既增加了文字的精神,又展现了现实“世相”中不同人的不同精神境界,即车夫崇高的精神境界和“我”渺小的精神境界;既使小说叙事的展开在逻辑上具有了无懈可击般的坚挺性,经受得住“千锤百析”,又使“自我反省”的思想表达具有了坚实的事实基础,同时也与小说开头“我”对“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的反感形成了修辞学上的对比。
其实,这个成语并非鲁迅最早使用,在中国古代最优秀的小说《红楼梦》中就有使用,如《红楼梦》第九十三回即有:“那些赶车的但说句话,打的头破血出的。”这里使用“头破血出”,姑且不从词语的能指和积极修辞的角度来看这个词语在这里的使用效果,也不按我前面分析鲁迅小说时所说的为小说叙事、描写的展开提供基础的要求来分析这个词语使用的艺术性效果,即使按照消极修辞准确性的标准来衡量,也不能不说,这个词语在这里使用显得很牵强,因为,这个词语所描摹的情况和使用的情境,在事实逻辑和艺术逻辑上都捉襟见肘,难以得到圆满的解释。在“头破血出”这个成语之前作者使用的动词是“打”,从小说所叙之事的情景看,这种“打”并非是朋友之间的戏闹、开玩笑的“打”,而是车夫为了自己的利益的“打”,可见不会“手下留情”,而如此凶猛的“打”得人流了血,可以想象不会是“出”那么平和,而只能是“流”那么恐怖;可这里却偏偏用“出”不用“流”,所以,显得不是很恰当。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并不能代表《红楼梦》的艺术水准,的确如此,这不能代表《红楼梦》的整体艺术水平,但《红楼梦》使用词语,至少使用这个词语的牵强性,却也同样不能否认。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鲁迅使用这个成语的成功,超越了中国最杰出的小说的艺术水准,而这种超越的文学史意义则在于:从一个具体的方面体现了以鲁迅小说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小说对中国古典小说艺术传统的发扬及光大、继承及超越、吸收与创造的品格。
参考文献:
[1]邢福义.汪国胜主编.现代汉语[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张卫中.汉语与汉语文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3]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4][瑞士]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6.
[5]周振甫.现代汉语讲座[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3.
[6]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6.
[7]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34.
[8]鲁迅.鲁迅全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