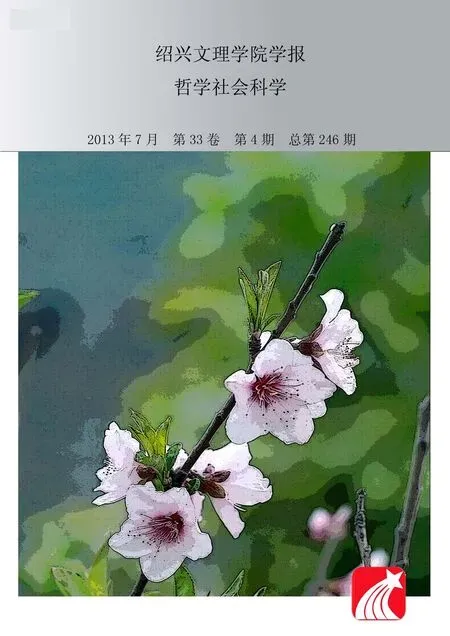明清之际吴江叶氏的闺阁生活与创作
孟羽中
(长安大学 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710064)
明清之际,吴江叶氏出现了许多令文学史家惊叹的名字:创作《甲行日注》《湖隐外史》而在明代小品文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叶绍袁、以拾遗补缺为目的编选女性作品集《伊人思》的沈宜修、有林黛玉原型之称的叶小鸾、中国第一位女杂剧家叶小纨、代表清初诗学理论高峰《原诗》的作者叶燮,真可谓“吴汾诸叶,叶叶交光”[1]673。这其中,以叶绍袁的夫人沈宜修为中心,三个女儿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为旁衍的女性创作,成就尤为斐然。其成就的缘由,可借用《朝鲜女俗考》的一句话概括之,“皆以天才,亦有地阀,得自家庭之学,诗礼之风。”[2]170
一
女子能文辞者多薄命,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情况到了明代中晚期多有变动。女性教育逐渐进入世人视野,并受到重视,“反映在最实际的婚姻市场上,文艺修养已成为中上层女性婚前教育的重要条件,实际上等于嫁妆的一部份”[3]376。一如《牡丹亭》中杜宝老爷所提及的,“看古今贤淑,多晓诗书。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4]9。吴江叶氏,素重闺阁教育。一家之主叶绍袁,为人开明,他曾言“男固宜爱,女胡不然”[1]372,十分重视培养女辈。
关于闺训的内容,杜宝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男、女《四书》,他都成诵了。则看些经旨罢。《易经》以道阴阳,义理深奥;《书》以道政事,与妇女没相干;《春秋》《礼记》,又是孤经;则《诗经》开首便是后妃之德,四个字儿顺口,且是学生家传,习《诗》罢。其余书历尽有,则可惜他是个女儿。[4]21
儒家经典的《大学》《中庸》《孟子》《论语》,诵读则可,以知晓伦理大意;《易经》“究天人之道”,失之深奥;《尚书》专讲政事,女子读无益且无用;《春秋》《礼记》微言大义,也不适合。只有《诗经》便于诵读,且蕴含后妃之德于其中,有教化之功。这种以诗学为主的闺训理念,与叶氏深相契合。
沈宜修自幼失母,赖姑母张孺人抚之,闺训似有缺失。但她“夙具至性,四五龄即过目成诵,瞻对如成人”,且“从女辈问字,得一知十,遍通书史”[1]17。学成之后的沈宜修,“钟情儿女,皆自为训诂”[1]18。教育之中,亦自有自己的理念。她“鄙中垒《左传》之读,陋蕙姬《女戒》之垂”[1]211,对描述过往兴盛演变的《左传》,以及强调女德的《女戒》之流,不甚欣赏。从“儿女一二岁时,(沈宜修)即口授《毛诗》《离骚》《长恨歌》《琵琶行》”可以看出[1]227,宜修注重诗学。叶氏男子“长就外塾”,学习应制之文,视野自然阔于以诗学为主的母教,但叶氏三女的学殖则端赖于此。
叶氏女子的教育,还可从季女叶小鸾身上简窥一二:
四岁,能诵《离骚》……;十二岁,……随父金陵,览长干、桃叶,教之学咏,遂从此能诗……。十四岁,能奕。十六岁,有族姑善琴,略为指教,即通数调,清泠可听,嵇康所云“英声发越,采采粲粲”也。家有画卷,即能摹写,今夏君牧弟以画扇寄余,儿仿之甚似。[1]202、
琴、棋、书、画的贤媛教育,令我们想到《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其中,叶小鸾于诗赋吟咏最为关注,曾尝言“欲博尽古今”,[1]202平日里“举止庄静,不妄言笑”,[1]299“默默与琴书为伴”[1]202。其余女儿的教育,大略相似。如长女叶纨纨,三岁读《长恨歌》,“不四五遍,即能朗诵”,“十三四岁为学诗词”[1]278,也是较早习咏。
叶氏素有诗学传统,沈德潜在《午梦堂集八种序》载:
吴江之擅诗文者固多,而莫盛于叶氏。其最著者,如虞部(叶绍袁)、廷尉、横山(叶燮)、莱亭诸先生。而横山则出自虞部,为余所师事。师门群从类长吟咏,虽闺阁中亦工风雅,郡志所载《午梦堂集》,妇姑姊娣,更唱迭和,久脍炙人口。[1]1094
令沈德潜“心窃契之”的分湖诸叶,从叶绍袁至叶燮,薪火传承,不坠家学,青不断出之于蓝,促成“门才之盛,几为一邑之冠”[1]1135。如此家学与母教,叶氏女性诗文方面的成就自然远高于经、史。明代女史梁小玉在《古今女史》自序云:“二十一史有全书,而女史阙焉。挂一漏百,拾大遗纤,飘零纸上之芳魂,冷落闺中之玉牒,是以旁摭群书,釐为八史。”[5]162对比之,叶氏女性似乎从来没有自目“女董狐”的愿力,诗文集中日常物景及春恨秋悲之思乃最常见的主题,而沈宜修意在蒐集海内闺秀片玉碎金的《伊人思》,其所选仍不出诗文之格局。
生活空间的拓展,亦是叶氏女性文学发端及质量提升的重要原因。得益于经济的发展、便捷的交通,以及引导士大夫归趣天真、委心自然的阳明思潮的流布,晚明社会旅游之风大炽,文人雅士游兴颇浓。袁中道称:“天下之质有而趣灵者莫过于山水。”[6]460都穆亦言:“余性好山水,所至之处,山水之佳者未尝不游,游必有作,所以识也。”[7]
江南人文荟萃,兼具形胜之美,叶氏世居分湖,地处嘉兴、吴江交界,“吴多佳山水,莫不可游观”[8]54,他们的游览固得楼台之便。
叶绍袁性爱山水,曾多次带子辈出访游玩。天启七年,叶绍袁授南京武学教授,即率“太宜人、内人、同诸子女偕往,逗舟江干,候风良久,取道龙潭,方得到任莅事”[1]838。明代晚期,秦淮河景象已然十分富丽,“水上两岸人家,悬桩拓梁为河房水阁,雕栏画槛,南北掩映。夏水初阔,苏、常游山船百十只,至中流,箫鼓士女阗骈,阁上舟中者彼此更相觑为景。盖酒家烟月之趣,商女花树之词,良不减昔时所咏。”[9]24“揽长干桃叶之盛,吊莫愁子夜之遗”,对于长年止步闺阁的女辈,无疑大大增阔了视野,而家中才女叶小鸾的吟咏之学,也是发端于此次游览。
叶绍袁的母亲冯太宜人素来礼佛,叶氏子辈也多次随同,前往杭州天竺寺进香。沈宜修十八岁时曾陪同前往:
余自初笄时,随姑大人往天竺礼大士,过西湖堤上,时值暮秋,疏柳环烟,岚光凄碧,迥波清浅,掩映空山,恨不能周览湖光山色,怅然别归,徒然神往。[1]171
作为新妇的沈宜修,深深被暮秋时分“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西子湖畔所吸引,但囿于时间急促,不能周览湖光山色,只能怅怅然而归。此次礼香,叶绍袁亦有同往,“辛亥二月,往天竺礼大士,次日至灵鹫一游”[1]876。据《天竺山志》载:“东晋咸和初,慧理来灵隐卓锡,登武林云,此乃天竺国灵鹫山之小岭,何年飞来此地耶?”由此,山名“天竺”,峰称“飞来”,后人把峰南所建各寺称“天竺寺”,分上、中、下三竺。此次登灵鹫、顺览西湖,给年轻的沈宜修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二十年后戊辰岁(1628)故地重游,沈宜修率领子辈,“复随姑大人再礼大士过此,时落红将尽,余绮翻风,细草茸青,鸟啼碧野,聊欲登览。又已斜阳衔山,暝烟笼树,大人急问归途,已月出矣。时正暮春十日,遥忆湖光泛影,山色浮风,此际不知是何景也”。[1]171尽管行程又是匆匆,但钟灵毓秀的山水之美,给叶氏女性留下了深刻印象。此番旅行,年仅十三岁的叶小鸾,留下了其惊艳之作《游西湖》,诗云:“堤边飞絮起,一望暮山青。画楫笙歌去,悠然水色泠”[1]311,直指“笙歌去后之水色清冷”,诗作意境超出尘端。
另据祁彪佳《寓山自注》载,叶氏家中的次女叶小纨,曾题咏祁彪佳所建的寓山园林,现存有《孤峰玉女台》诗,诗云:“荷花缺处天,鱼凫家于此。犹欲与之争,让鸥徒伪尔。”夏天荷花映日,游鱼在此自由凫翔,鱼儿的心境如此愉悦,甚而有与鸥鸟比试之愿,小纨的笔力透现着豪迈。孤峰玉女台为寓山一景,“由渡而东,一峰峙青,万衣簇碧,丹楼翠水”[10]271,风景殊美。
叶氏一门连珠、唱和自娱,群居切磋的家庭氛围,也为叶氏女性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叶绍颙在《重订午梦堂集序》中称叶绍袁“投林已还,与嫂氏举案之余,辄以吟咏倡随,暨诸侄女俱以篇章赓和。以是闺阁之内,琉璃砚匣,终日随身;翡翠笔床,无时离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积案盈笥,尽是风云月露矣。”[1]1092
在终日吟哦的氛围里,任何契端,都可引发唱和。如家中侍女随春,“年十三四即有玉质,肌凝积雪,韵彷幽华,笑盼之余,风情飞逗”[1]767,叶小鸾极喜之,为作《浣溪沙》词。之后,叶绍袁、沈宜修、叶纨纨、叶小纨均有庚和。首倡者叶小鸾词云:“欲比飞花态更轻,低回红颊背银屏,半娇斜倚似含情”。[1]320将少女随春的娇羞描摹地十分入神,黄媛介称叶小鸾词“情深藻艳”,“章章浣其天趣”[1]683,确实如此。次女叶小纨,用笔轻松简约,其词云:“惯把白团兜粉蝶,戏将红豆弹流莺。见人故意反生嗔。”[1]772勾勒出少女活泼的神态与易嗔的瞬间,风趣十足。又如壬申年(1632),叶氏家中置载太湖石,叶绍袁命子辈以《分湖石记》为名,同题共作,叶小鸾亦有文作。她叙分湖石“其大小圆缺,袤尺不一。其色则苍然,其形则崟然,皆可爱也”,并追想石之前世,“岂其昔为繁华之所,以年代邈远,故湮没无闻邪?抑开辟以来,石固生于兹水者耶?若其生于兹水,今不过遇而出之也,若其昔为繁华之所,湮没而无闻者,则可悲甚矣”[1]354。父亲叶绍袁读后,文末旁注:“何必韩柳大家,初学古文辞,辄能为此,真是千秋灵慧。”沈宜修长年引领家中的文化生活,她也十分勤于三女的诗歌联咏。检阅三女之作,叶纨纨《愁言》、叶小纨《存余草》、叶小鸾《返生香》中多有同题之作,如三女同有的《四时歌》,即旁注标明为“慈亲命作”。[1]303
此外,叶氏家中的典籍,亦是女性增加学殖的沃壤。虽然,有学者认为十六世纪中期江南文人书籍仍然匮乏[11],不过叶氏累代书香,似有积存。当年叶绍袁的父亲叶重第亡后,遗“书一床”[12],叶绍袁亦有书嗜,遇有典籍,常尽力而求。在他任南京国子监时,“同年同郡,及他相识,托余印《十三经》《二十一史》,大都二十余金便可印两部矣。余代人印去甚多,而不能印一本归。官贫无他恨,此可恨耳”[1]839。遗珠《十三经》与《二十一史》固然可恨,但另一方面讲,这份对书籍的热衷,当使他在其他时候没有遗珠之憾。一次逛书肄,他“偶见新刻《说郛》,镌镂甚工”,“亟买之”,虽然阅后发现,其中所收《齐东野语》,“旧本十一行细字,共七十三纸,而今本十行疏字,止七十纸,竟将前后极无关系者,存期首尾,中间尽行删去,不知是何肺肠。其他本本皆然,无一全帙,可恨之至”[1]893,此段记载,似已超越了泄愤具备文献考究价值,但就网罗典籍而言,平日生活中,这种“亟买之”的购书癖行为定所在多有吧。所以,沈宜修曾叙“然贫士所有,不过纸笔书香而已”[1]202,家中四子叶世侗亦称“平日,父母常有分与,或祖传书典,或随常器什,诸如纸笔、刀砺之属”。[1]432
值得一提的是,与叶家关系密切的平湖冯氏、同邑袁氏,也都是以藏书而知名。叶绍袁的表兄冯洪业(字茂远、号兼山),建有传书阁与万卷楼。辑有《耘庐汇笺》千余卷,亦悉心佛教典籍,刻有唐释玄奘译《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十卷、《佛说大方广十轮经》八卷等多种经本。明清之际著名史学家谈迁在《枣林杂俎》“厄书”条载:
平湖冯孝廉茂远,常熟钱宗伯谦益诸家,非流散则妬熖矣。缥帙缃函,何预天曹事?往往被厄,不能久锢。[13]254
钱谦益绛云楼,世人皆知,当年的绛云之火,堪为江南图书史上的一劫,“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14]13。谈迁在此将冯洪业与钱谦益同举,可见其藏书规模。据叶燮回忆,表叔冯氏所居的耘庐,“连山复岭,人行其间如在绝谷中”,梅、海棠、桂树数千,另有驯舞鹤三十余,“掷果空中,群鹤翱翔以赴争啅长鸣,声振山谷”[15]172。作为至亲,叶氏恒往来于耘庐,书香环绕,俯仰间流觞绮景,定是难得的悦读体验。
叶绍袁义父袁黄家藏书亦多。晚明与李贽齐名的紫柏大师,就曾在袁家“闭关三年,尽司马公诸书而去,以此益名闻天下”[1]1069。到甲申之年,袁若思子误信流贼,引尊为上客,因以兆祸。“有松江陆季先集兵,焚四履之屋,书籍器什,靡有孑遗”,最可悲的是,“数十年堂构化为灰烬,而异书秘本,邺架惠车,无一存焉”[1]872。叶绍袁从小寄养袁家,归家后又多年与袁若思同处备考,所焚“异书秘本”当历历在目,故有关心之痛。长女叶纨纨,嫁与袁若思子,得益于夫家的典籍之属,嗜于读书的她,学殖定当有所增长。
同时基于叶绍袁、沈宜修夫妇的豁达明识,叶氏阅读范围似乎颇广。叶小鸾有《又题美人遗照》六首,叶绍袁旁注云:“坊刻《西厢》《牡丹》二本,前有莺莺、杜丽娘像,此前后六绝俱题本上者。”[1]317沈宜修亦留有《题屏上美人》六首及《题美人图》三首。坊刻戏曲进入书香之家,家长不以为怪,且不吝于赞美,则子辈自可纳入阅读范围,增阔视野与识见。
二
清代骆绮兰在序《听秋馆闺中同人集》中,将男女书写者的处境作以客观比较,道出女子难工于诗的后天不足:
女子之诗,其工也,难于男子。闺秀之名,其传也,亦难于才士,何也?身在深闺,见闻绝少,既无朋友讲习,以沦其性灵,又无山川登览,以发其才藻,非有贤父兄为之溯源流、分正伪,不能卒其业也。迄于归后,操井臼、事舅姑,米盐琐屑,又往往无暇为之。[5]939
群居琢磨,登临胜景,父兄为之导引,且有闲情。骆绮兰所艳羡男子的诸般长处,
吴江叶氏的女性,幸而兼备。次女叶小纨中年以后,曾回忆道:“深闺从小不知愁,半世消磨可自由”[1]757,可为她与两姊妹待字闺阁中的写实。正是这种美意娴情的闺阁生活,使得叶氏女性得以全身心地投入诗文创作之中。
首先,叶氏女性的诗文从不吝于对女性美的妙赏。如同自然中其他景观一样,女性美,也是造化的妙笔,值得人们观赏。但自古以来,女性美与色关联,而色又多与德对立,孔夫子即云:“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明代程朱理学一统天下,将“理、欲之防”推向极端,过分强调“存天理,去人欲”以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世人“色又欲讳于言”,“置色弗谭”[1]1。不过,此禁锢到了明代中叶有所松动,李梦阳在《论学》中论证张扬情欲的正当性,云:“孟子论好勇、好货、好色,朱子曰:此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无者。是言也,非浅儒所识也。空同子曰:此道不明于天下而人遂不复知理欲同行而异情之义。”此种“好货好色”的观念,后经王学左派的推动,至晚明蔚为风气①。李渔即言:“妇人妩媚多端,毕竟以色为主。”[17]101午梦堂主叶绍袁提出:“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与色也,几昭昭乎鼎千古矣。”并称昔日荀奉倩伤神,后世儒者“摘其偏缪,訾其淫靡”,是故色“深讳于士大夫之口”,“冶容讳谈,折鼎一足,而才与德乃两尊于天下”[1]1。“三不朽”中,才与德已为世人接纳,唯有色遗珠于外,叶绍袁急于为其正名。
在叶绍袁的热情鼓励及社会自由思潮的陶染下,叶氏整体的“德、才、色”主体意识开始萌苏,叶氏女性大方地表露对于女性美的妙赏,这其中,尤以沈宜修为凸显。她曾拟颜延之《五君咏》而作,颜作以“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为题,刻画五贤的高洁品行,沈作以家中的五位女性为对象,着力描摹其容颜之丽。诗作很美,选录一首于下:
佳人字倩倩,绰约多娟美。丰既妍有余,柔亦弱可拟。巧笑思庄姜,宜颦羡西子。沉(原本作沈,似误)香倚画栏,独立谁堪比。春雨泣梨花,华清竟杳矣。[1]39
沈宜修的表妹张倩倩,体态丰盈,柔弱有姿,行动起来似弱柳扶风。她笑起来如“巧笑倩兮”的庄姜,嗔怒时又若西子捧心,流泪时宛若梨花带雨,笑颦之间,仪态万方。张倩倩肤色极白,“脂凝玉腻”,故姊妹妯姒间戏呼其为“华清宫人”[1]205。《五君咏》中,还有沈宜修的季妹沈智瑶,沈宜修称她“珠辉映月流,玉彩迎花度”,仅这一句,便令人产生持久的美感想象。宜修尝以季妹照镜为材口赠其诗,云:“星眸梦乍舒,宛转看不足。一笑绕春风,含情低黛绿。”[1]86佳人新起,慵懒且娇羞,她笑起来,黛眉簇动,静谧且温柔,一切宛若梦一般。
季女叶小鸾明秀绝伦,母亲沈宜修也常由衷而赞:“今粗服乱头,尚且如此,真所谓笑笑生芳,步步移妍矣,我见犹怜,未知画眉人道汝何如!”[1]203又一次,沈宜修、叶小纨、叶小鸾曾偶见双美,三人即各为赋诗,“若非拾翠来湘水,定是遗珠涉汉江”[1]310。在她们的眼中,双美若南湘二妃,汉滨游女,真乃神人谪世。
叶小鸾不喜旁人赞其美色,但她曾多次评赏自己。如十二岁年,小鸾画眉簪花罢后,即对影自赏,并付诸于笔端:“揽镜晓风清,双娥岂画成?簪花初欲罢,柳外正莺声”[1]311。后,金圣叹以泐大师的身份扶乩于叶氏时,以此为据,遂敷衍出冥中叶小鸾与泐大师之间的互答,泐公问:“曾犯淫否?”小鸾云:“曾犯。晚镜偷窥眉曲曲,春裙亲绣鸟双双。”[1]522
其次,叶氏女性热衷于创作彰显文字技巧的文体。回文诗,又称迴文诗,指反复回还均可成诵的诗。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言:“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道原为何?现已不可考。据现存资料,前秦窦滔妻苏惠的《璇玑图》诗,可谓之最早者。沈宜修有回文诗《秋闺》四首,回文词《菩萨蛮·春闺》等七首。这些诗词,辞句连续,可顺读、倒读,左右分读,巧妙组合。比如叶小纨的回文词《菩萨蛮·暮春》:“柳丝迷碧凝烟瘦。瘦烟凝碧迷丝柳。春莫属愁人。人愁属莫春。雨晴飞舞絮。絮舞飞晴雨。肠断欲昏黄。黄昏欲断肠。”[1]774每上一句子乃下个句子倒读而成,回旋往复,词作除却描述暮春之景愁人外,更注重的当是技巧的展现吧。
叶氏女性还会用特别的限定,来体现自己的用词精妙。沈宜修有《蝶恋花》六首,题记表明“桂、竹、梅、柳、蕉、薇六影,次楚女子朱琼蕤韵,不得言影,不得言本色”。如写桂:
蟾兔清辉浮碧树。帘榭横枝,恍惚淹留处。画出淮南招隐谱,广寒却趁幽芳注。叶底金鹅愁欲曙。蠹饵空濛,似滴庐山露。汉殿灵波奇艳吐,风来云外飘香暮。[1]179
细碎的桂花,从来是以幽幽的香气知名,但其影子,似乎无从下笔,而且约定不得言影,不得言桂花的本色,更增加了写作的难度。沈宜修采用旁注的方式,凸显出桂影。月兔与桂树同在月亮之上,有月兔的地方,自然有桂影。淮南王刘安作有《招隐士》之赋,赋中有“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故提及淮南,桂的影子也就浮在读者脑海中,沈宜修高超的写作技法着实令人佩服。
又如词牌《声声慢》,据传宋人蒋捷作此慢词俱用“声”字入韵。沈宜修“仿人旧作,韵用八声字”,其《声声慢》词的句末分别以“新声”“燕声”“鹃声”“秦声”“春声”“无声”“涛声”“数声”收尾[1]185,以应和主题,可见词人语汇的丰富。
连珠作为中国古老而又独特的体裁形式,具有独特的逻辑结构、假喻以达旨的文学性语言、对偶骈俪的句式特征、短小精致的篇幅体制等特征。叶氏所作连珠,更准确的名称当为艳体连珠,乃仿照梁代诗人刘孝仪《为人作连珠》而作,刘氏诗作中,每句用“妾闻”起句,“是以”承之:
妾闻洛妃高髻,不资于草泽;玄妻长发,无籍于金钿。故云名由于自美,蝉称得于天然。是以梁妻独其妖艳,卫姬专其可怜。
妾闻芳性染情,虽欲忘而不歇;薰芬动虑,事逾久而更思。是以津亭掩馥,秖结秦妇之恨,爵台馀妒,追生魏妾之悲。[18]64
前一首逻辑连贯词“妾闻……故……是以……”,后一首为“妾闻……虽……是以……”,构成双重因果,曲折回旋。内容上,前一首模艳女之美,后一首叙艳情之深,脱离讽喻的轨迹,专注于容貌与深情,用典趋繁,如第二首的最后四句,句句用典。在这里,艳体连珠已然脱离扬雄所开创的注重的事与理的传统,而专注于情与辞,注重华文丽辞所带给人的美的享受。
叶氏的仿作由叶小鸾肇其端,她以发、眉、目、唇、手、腰、足、全身、七夕为题。沈宜修见后甚喜,“亦一拈管”,所叙对象,仅少七夕一题,二人之作后被民国时期的虫天子收入《香艳丛书》中,该丛书《凡例》有云:“本集所选,以香艳为主,无论诗词乐府,足以醉心荡魄者,一例采入。”显示了诗作艳情的特质。试以目为例,看其创作:
盖闻朱颜既醉,最怜炯炯横秋;翠黛堪描,讵写盈盈善睐。故华清宴罢偏娇,酒半微阑;长信愁多不损,泣残清采。是以娱光眇视,楚赋曾波,美盼流精,卫称颀硕。[1]191
盖闻含娇起艳,乍微略而遗光;流视扬清,若将澜而讵滴。故李称绝世,一顾倾城;杨著回波,六宫无色。是以咏曼睩于楚臣,赋美眄于卫国。[1]350
沈宜修在作品中,摹写美人酒半微阑时,略带慵懒的目光,所用华清、长信、楚赋、颀硕之典,暗含“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奉帚平明金殿开”的班婕妤、“含睇宜笑”的湘妃、与诗经中硕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叶小鸾描写的重点乃美人举目流视的瞬间,并以李夫人“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以及“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来突显美人目光的感染力。沈宜修称叶小鸾的连珠体,“女实仙才,余拙不及也”,[1]190叶绍袁则于诗末赞“琼章(叶小鸾)之清丽与内子(沈宜修)之流雅”,[1]193俱有可观。
再次,在叶氏女子所写诗文中,娴用典故是一大特色。上述的许多文作中,即已可看出此倾向。沈宜修曾作《醉芙蓉赋》,醉芙蓉清晨和上午初开时花冠洁白,并逐渐转变为粉红色,午后至傍晚凋谢时变为深红色。根据这一特色,她展开了丰富想象:
有醉芙蓉者,独嫣然于水滨,旭旦则梁园之雪聚,昳日则潘县之粉匀。卓女姿含而待暮,何郎傅粉兮迎晨。于是素纨朝彩,绛缕夕新。梨容早秀,杏颊晚春。笼曙景兮娟娟,带落晖兮灼灼。飒金风兮参差,映琼月兮绰约。或拟姑射之仙,忽讶蜀帝之魄。[1]197
本段几乎句句用典,梁园雪景、河阳桃花;敷粉的何晏、红艳的卓文君;肌肤若冰雪的姑射之仙、杜鹃啼血的蜀帝之魂,皆一白一红,指合醉芙蓉朝白夕红的特性,让人目不暇接。《国语·郑语》云:“物一无文。”沈宜修学养丰富,方能将醉芙蓉描摹地如八宝楼台般繁复美丽。
又如,叶小鸾在艳体连珠《足》中,也采用了众多典故:
盖闻步步生莲,曳长裾而难见。纤纤玉趾,印芳尘而乍留。故素毂蹁跹,恒如新月;轻罗婉约,半蹙琼钩。是以遗袜马嵬,明皇增悼;凌波洛浦,子建生愁。[1]351
“新月”典出窅娘,为南唐后主李煜的嫔妃。相传她将白帛裹足,将两只脚缠成新月型,所以,当窅娘跳舞时就好像莲花凌波,俯仰摇曳之态十分优美动人。遗袜马嵬,指杨贵妃事。据《国史补》载:“玄宗幸蜀,至马嵬驿,命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马嵬店媪收得锦靿一只”。凌波一词从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而来。叶小鸾采众典故,以烘托足的美丽,流露出少女含蓄的喜悦,学者高彦颐称这种喜悦为“高贵的快乐”[19]176。
明清两朝,女性作家大量涌现。仅仅三百年间,就有两千多位出版过专集的女诗人。女性文学的空前繁荣,与明清文人对才女的扶持密不可分。如文坛宗师钱谦益,多次倾力为女性文集作序跋,在《列朝诗集》中,也特为闺秀诗人留有一定的位置。孙康宜教授在《明清文人的经典论与女性观》里指出:“我们可以说,当时的‘女性研究’其实是明清文人对理想女性向往的一种产物。他们一方面深深感到自己的边缘处境,一方面也对被埋没的才女赋予极大的同情,所以当时许多文人不惜倾注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努力收集和整理女诗人的作品。从政治上的失意转移到女性研究,可以说成了当时的风气。”吴江叶氏女性文学的繁荣与盛名,实与此时代大环境相关联。对此,午梦堂主叶绍袁有清醒认识,在子辈恳请为家中另一位早夭的男子编撰遗集时“姊妹两遗集出(叶纨纨、叶小鸾),几于上驾鲍刘,下掩魏李,何遽偁不可(次子叶世偁)”?如是答复:“红闺片玉,闻者色飞;彤管寸香,见者神艳。此是世间情想习障,今古尽然。”[1]407。叶氏后来之翘楚叶燮似乎亦明此理,在其颇具盛名的《己畦集》中,独附录母亲及三姊之作于后。
明清女性文学固然繁盛,但就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著录情况所看,以“绣闲”“绣阁”“绣余”“红余”“针余”“织余”命名者众多。名称本身,表明女性文学创作不脱日常生活的有限格局。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在深入探讨女作家的内心时,常看到的是“愤怒和自我的怀疑”,并认为“统一组合女性创作的便是压抑的心理,女性生存于父权制下的心理”[20]168。这种极端的情绪在中国女性创作中,鲜有看到,但女子在书写时候的矛盾与自我反省却是已然存在的,许多闺秀才妇都有易箦焚稿之举,女性文集以“焚余”命名即所在多有,彰显的便是“内言不出”观念下的焦虑[21]。叶氏家族女性的创作,不可避免地沾染时代及性别之通病,如诗文主题多为日常生活所感,视域狭小。但在午梦堂宽容鼓励的创作环境下,叶氏女性在文学创作中又可较为自由地自我抒怀,并对女性美毫不吝啬地赞美,几次游历也一定程度拓展了叶氏创作的题材范围。她们的诗文,文体精工,娴于用典,虽有时不免太过雕琢。但整体观之,美要眇兮宜修,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注释:
①按:此段论述参陈书录:《“德、才、色”主体意识的复苏与女性群体文学的兴盛——明代吴江叶氏家族女性文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叶绍袁等.午梦堂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韩)李能和.朝鲜女俗考[M].日本:东洋书院,1927.
[3]蒋寅.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清代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
[4]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5]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6]袁中道.珂雪斋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7]都穆.游名山记卷三观音岩.丛书集成新编史地类第90册[M].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5.
[8]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M].上海:上海书店,1990.
[9]王士性.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0]祁彪佳.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M].南京:江苏科技出版社,1983.
[11]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第二章第三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2]叶长馥.吴中叶氏族谱戌集[C].明万历(1573-1620)刻本.
[13]谈迁.枣林杂俎[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4]钱谦益.绛云楼题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5]叶燮.已畦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6]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7]李渔.闲情偶记[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18]陈翼飞.文俪[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本.
[19]高彦颐.闺塾师[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20]钟慧玲.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J].台北:台北学生书局,2000.
[21]张宏生.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J].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Abstract:The Ye’s,who lived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scored considerable achievements in poetry and literature,especially their females.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dwelling environment,their collection of books,reading experience and several literary tours,we can grasp their agreeable and harmonious mood. The ladies tended to choose the literary forms full of techniques to convey their feelings,such as catenane,palindrome etc. Shen Yixiu and Ye Xiaoluan selected the body as their writing object,which was a literary form called Lianzhu,reflecting their appreciation of feminine beauty and their ability in using allusions.
Key words:Ye clan;feminine beauty;literary form;allu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