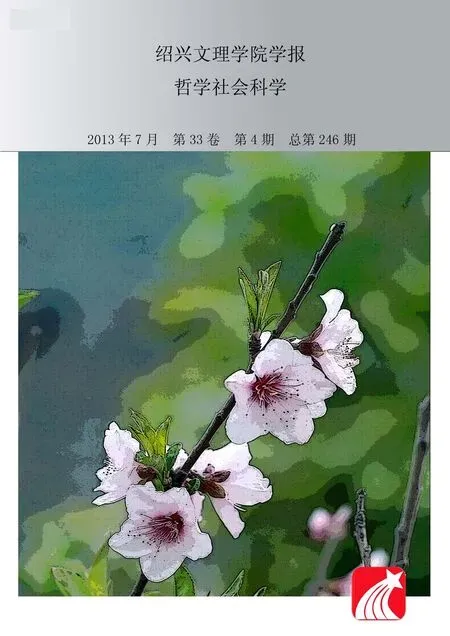书法文化视阈中的鲁迅与越文化
胡冬汶 李继凯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710062)
细致研究鲁迅与区域文化的关联,体现了鲁迅研究的细化和深入。而文化传统在区域文化中的实存及影响,对一位诞生和成长于某一区域中的文化名人而言,无疑具有感性积淀和认知升华的价值意义。从书法文化视域观照鲁迅与越文化,也会从一种“特色”文化的绵延中,真切体察到鲁迅“在墨迹中永生”的隽永意味。[1]本文即拟对此进行初探性的尝试。
一、书写一生的鲁迅与书法文化有着深广的联系
鲁迅以思想贡献和文学创作名世,并确立其世界性文化巨人的身份,因此,在一般读者意识中,对于鲁迅的认知即为思想家与文学家,更关注其批判国民性、反封建的思想和他的小说、杂文等创作,而对于鲁迅的书法生涯则了解不多,更不用说视鲁迅为书法大家了。即使就鲁迅研究的专业领域讲,大多数学者和研究者对于鲁迅书法层面的写字生涯也是关注甚少,了解有限且缺乏高度认同的。
至于鲁迅究竟算不算一位书法家,这个问题一直存有争议,亦无终结性结论。在汤大民、江平、李继凯、张瑞田、李建森、凌士欣等人的相关文章中,可见到这些研究者是在视鲁迅为书法家、甚至了不起的书法家这一前提下展开对鲁迅书法的阐释,并分析鲁迅书法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在这些研究中,有的论者直言今日研究界对于鲁迅书法研究的漠视是不正常的,忽视鲁迅的书法价值和地位也是不妥当的[2]。笔者以为,鲁迅虽未明确获得书法家的称号并以之名世,但就鲁迅的书写实践活动和成绩而言,他确实是20世纪中国一位独具面貌、不可忽视的书法家,此一点是本文阐述与立论的基础与前提。诚如汤大民所言,在研究思想鲁迅、文学鲁迅的同时,亦应“聚焦于书法鲁迅”。[3]
鲁迅“没有现代职业书家以书鸣世,以书求利,以书成家的动机和追求”,[3]他未曾想要做一个书法家,但却有大成。在书法实践层面,鲁迅堪称书法大家。鲁迅从实用便捷角度曾论及钢笔的优点与长处,在新式学堂和留日学习期间都曾用过钢笔,但其主要书写工具则是绍兴百年老牌子笔庄卜鹤汀所售的“金不换”毛笔。鲁迅使用毛笔手书的时间漫长,从其幼年开蒙起直至去世,前后约有50年之久,而且他用毛笔书写的文字存世的就约有七百多万字,数量之巨蔚为可观。鲁迅的墨迹主要存于他的日记、书信、文稿、诗和题赠等手稿中,以及近三百余万字的辑校古籍、石刻手稿、金石资料和金文手稿中。鲁迅虽不标榜自己的书法,但对书写一事却是深有自信的。1927年1月15日离开厦门的时候,鲁迅抄写了司马相如《大人赋》中的一段,还在将其送给川岛的时候说:“不要因为我写的字不怎么好看就说字不好,因为我看过许多碑帖,写出来的字没有什么毛病。”鲁迅自幼即习书,中年时期在抄古碑方面又用力甚巨,使得他在书法艺术方面的鉴赏眼光和品评标准自然是高的。当他说自己的字“没有什么毛病”时,显示了他对自身书法的明确自信。而且鲁迅多年间也曾多次书写书法作品赠送友朋,若无对自身书法的自信与认可,鲁迅又岂肯以手书赠人。从书法艺术本身讲,鲁迅的书法水平也是很高的。与鲁迅同时代的郭沫若,既是文学家,也是20世纪中国有定评的知名书法家,他在为《鲁迅诗稿》写的序中对鲁迅书法曾有过这样的论述:“鲁迅先生亦无心作书家,所遗手迹,自成风格,融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世人宝之,非因人而贵也。”[2]这可谓书法家郭沫若对于书法家鲁迅的中肯评价。
鲁迅未能享高寿,但其书写生涯是比较长久的,从接触毛笔书法,经年累月写字,历书风变化至书艺成熟这一道路中,是有越文化的影响在其中的。这也就是说,书写一生的鲁迅与书法文化确有深广的关联。即从地域文化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因为地域文化与生于斯长于斯的人及其社会文化实践原本是有着深层联系的。鲁迅出生在绍兴城,此地乃越文化的中心区,一度曾是江南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中心,文化发达,教育兴盛,多出才俊。毛泽东也曾说绍兴是“名士乡”。越文化作为江南文化中的代表性文化之一,有很多优秀面,诸如好勇轻死的尚武精神,民性刚烈坚毅,多“硬”“韧”气质,理性务实,开拓进取等,同时也有奔放飘逸、明慧文巧、沉静空灵的一面。鲁迅在《〈越铎〉出世辞》中曾写到:“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津液,善生俊异,后先络绎,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4]这里明显见出鲁迅身为越人的荣耀之心和对越地文化精神及先贤的由衷认同。鲁迅有身为越人的自觉,其精神气质、文化个性有明显的越文化印迹。在他晚年,在给黄萍荪信中还说:“‘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越地、越文化给予鲁迅的是成长的母文化滋养,其烙印是深刻的。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时,同学们都笑称鲁迅“斯诚越人也,有卧薪尝胆之遗风。”[5]考察鲁迅的思想、文学创作和书法都不能忽略其孕生且成长于越地,浸润于越文化这一现实,也就是说,越地及越文化与鲁迅书法的发生发展是有具体渊源关系的。
二、绍兴是鲁迅书法生涯起步发展的生成性文化场域
由个体家庭到外部大社会文化所共同建构的绍兴是文教发达、书学兴盛的越地主要文化场域,对于鲁迅的修习书法、奠定书功确是起到了积极正面作用的。
首先从外部社会整体环境角度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绍兴文化资源较为丰富,文化气息浓厚,魏晋家族文化遗风仍有余存,一般书香、官宦之家是很注重子弟教育的。当然这教育以国学传统教育为主,但又处在向新教育转换的历史途中。对于一般子弟的教育,于诵读修习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之外,书法教育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内容,书法的好坏也是考核读书成绩的重要项目,所以除家学示范之外,大多数家塾、私塾授课教师的书法大都是颇有水准的,即便算不得书法家,但也当得起儿童开蒙时期书法教习的任务。这一整体的地方文化教育观念和气氛对于入塾读书孩子的习书练字来讲是很有利的。鲁迅早年的书法学习也是在这样的社会空气中开始的。1887年至1891年,鲁迅在远方堂叔周玉田先生处就学。周玉田精通楷法,从“描红”入手教鲁迅习字。鲁迅则一丝不苟地描摹大楷书帖,受到了极为严格、正规的书法训练。1892年鲁迅入三味书屋,跟随寿镜吾先生读书,寿镜吾能作诗、工于书法。寿先生的书学兼学颜真卿、柳公权、苏轼、米芾等笔法,“用笔顿挫有力,方而见骨,结体方正丰满,章法茂密。”[6]他对学生的习字作业判阅严格,看到写得好的字,就画一个红圈,而鲁迅“总是一笔一划、一个字一个字认认真真写下去”,从不敷衍了事,在同班同学中以鲁迅写得最好。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鲁迅应该是以练习颜真卿、柳公权楷书为主,也练习唐宋行书以作笔记抄录之用。[6]对于这段经历,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有记述,“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显然,绍兴城浓郁的人文教育氛围和习书练字的教育传统对鲁迅书法的早期发生是有着积极的奠基性作用的。
其次从内部家庭环境看,鲁迅早年习书条件良好,起点也高。绍兴重文化、重教育的观念与氛围自然影响及于周家,某种程度上可视其周家为绍兴文教发育丰赡的一个样本。周家乃书香、官宦之家,家中文化气息浓郁,文化资源较丰富,注重家族子弟教育,书法方面家学渊源亦深厚。周家有家藏的名碑法帖,厅堂悬挂有许多字画,便于子弟观摩学习,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是个秀才,也善笔墨,他的祖父周福清更“是一位精于行草的高手,其书宗法王右军,兼掺米芾法,善于用笔,书体潇洒,气韵畅达,深得帖学神理。”[6]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家中长辈们对于子弟的修习书法自然是比较重视并有所要求的,而且鲁迅又天然地日日接受家中浓郁书法文化气息的熏陶,他的习书并热爱习书就是很自然的了。此外,这个家庭在败落之前,经济是宽裕的,也有一定的开明度,对于小孩子用零用钱买经书之外书籍的控制并不很严格,对于子弟修习正统经学书籍之外的课外阅读和爱好也并不粗暴干涉,这为鲁迅的文化精神发育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在多种课业外的活动中,看画、临画和作画对于鲁迅的练字习书是很有益的。鲁迅自幼爱画,无论是家中所藏还是购得的绘画类书籍,他基本都临摹过,具体如《花镜》《点石斋丛画》《诗画舫》《海仙画谱》《山海经》等。此外,还临摹过绣像小说《荡寇志》《西游》等。中国古代艺术观念中是强调书学与绘画两门艺术间的深层联系的,有所谓“书画同源”之说。鲁迅的赏画、描摹、画图是出于真正的兴趣和爱好,强大且持久。在绍兴的早年生活中,鲁迅便与画结缘,此后终生都对美术有浓厚兴趣和热情,形成其较深厚的美术修养,这一修养使他对于书法的线条质地、结构造型、章法布局等都有超越于一般人的领悟性,他在绘画方面的摹仿力与理解力对于他的书法学习和创作是大有益处的,有功于鲁迅的无心为书但却有大成的书法之路。可以说,新台门周家作为第一教育环境,其经济上的相对宽裕,书香文化气息的浓郁,观念的开明,对于鲁迅文艺心灵的发育和书法之心的启蒙是有着积极的促发、孕生作用的。
再次,从书法文化方面看,绍兴作为有名的“书法之乡”对于鲁迅书法具有不可忽略的浸润性作用和示范性影响。绍兴是吴越文化的发祥地,书法在这一地区有漫长的发展历史,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古越先贤于春秋时期即有意识地将文字视为艺术品,推动文字书法向艺术层面发展,并创写“鸟虫书”。魏晋时期,王羲之、谢安、孙绰等大批文人南下定居绍兴,逐渐促使书法艺术的重心由中原洛阳转移到江南。而文人云集绍兴,便促成了绍兴一时书法之大盛,其影响绵延至今不绝。晋时,绍兴出现过诸多书法大家,如王旷、谢安、王羲之、王献之等。其中成就最高者是“二王”,尤其是王羲之的书法,在当时就被赞誉为“飘若浮云,矫若游龙”,他在山阴参与兰亭修楔集会时,写下《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由于书法文化的光辉灿烂,从东晋时起,书乡成了绍兴的代名词,绍兴从此成了书法圣地。绍兴多出杰出名士,亦多有书法名家,东晋之后,有孔琳之、贺道力、智永、虞世南、辨才、贺知章、钱公辅、陆游、陈宗亮、徐渭、倪之璐、陈洪缓、王守仁、徐生翁、马一浮等。[7]而且近现代许多出自绍兴的杰出人士,虽不以书法家身份名世,但书法水平较高,如蔡元培、章太炎、秋瑾等。作为书法之乡,绍兴的书法艺术故迹是相当多的,如兰亭、戒珠寺、题扇桥、躲婆弄、金庭观、曹娥庙、会稽山、山阴道、沈园、青藤书屋等,有很多名碑传世,如“兰亭三绝”的“父子碑”“君民碑”“祖孙碑”,蔡邕书写的“曹娥碑”,贺知章的《龙瑞宫记》摩崖题记等等。在绍兴的街头巷尾,城市乡村,处处可见楹联、碑刻等各类书品。综而言之,绍兴的书法文化可谓是浓郁深厚至极。鲁迅生长在这样一个书法厚土之地,浸润于书法文化的空气中,一者自然受到潜移默化的滋养和影响,这是难以量化但却深刻的影响。二者当他主动习书时,学书资源无疑很是丰富,且观瞻便利,他曾多次随身携带拓碑工具到绍兴周边如会稽山等古迹地搜集古代碑版,也购买很多铭文砖和画像砖,这些活动对于鲁迅书法的修习是很有助益的,为鲁迅书法富于“金石气”奠定了最初的根基。三者鲁迅很是敬重“乡先贤”,这些越地的优秀分子从书学角度对鲁迅是有示范性激励作用的,而且在具体习书时可资学习、借鉴的书家多且鲜活,如王羲之,绍兴是王羲之定居生活之地,其居住地与周家台门并不远,相关书法的存世遗迹很多;再如章太炎,曾是鲁迅授业老师,其书法鲁迅自然是见之甚多。一般来讲,真切感知书家的学书比单纯的碑帖学习要生动鲜活得多,现场感强,给予学习者的影响也是比较直接强烈的,就此点而言,在越地绍兴,早年鲁迅习书的条件显然是得天独厚的。
三、越文化精神是鲁迅书法的重要精神文化资源之一
越地绍兴文化资源丰富,教育发达,书学兴盛,加之新台门周家书香传统深厚,人文气息浓郁,所构建出的滋养个体发展成长的现实性物质文化场域,对于鲁迅文艺心灵的孕育,对于鲁迅书法的开蒙起步发生着有益且有力的影响。同时,在这一文化场域中绵延漫布的越文化精神更参与着对于书法鲁迅的铸造,是鲁迅书法发生发展的重要精神文化资源之一。
其一,越文化作为海洋文化的开放性特质对于鲁迅书法多元多向吸收产生有益影响。越文化是不同于内陆型游牧——农耕文明的海洋性文化,王晓初认为,“长江文明,特别是它的下游最有代表性的越文化却是一种海洋型文明。”[8]面海多水作为越地的天然地理条件,使得越人在对自身文化充分自信的同时,发展起善于开拓,勇于开放,不断创新进取的海洋型文化精神。这一文化精神对于鲁迅是深有影响的,鲁迅在人生进取发展的各个层面和领域都取开放的姿态与精神,标举“拿来主义”思想,在书法方面也是这样。鲁迅学书,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他虽无意做书家,但在书法资源吸收方面,却是广采百家,可谓“操百曲”“观千剑”,其观摩、体味、吸纳是至广至博的。他的书法取法过唐宋、魏晋楷行,学过二王行书,掺有章草、篆隶之法,也时或掺入了时人笔意。鲁迅有着丰富的拓碑、读碑、抄碑经历,他早年即爱金石类书籍,在绍兴附近亲自拓碑甚多;中年阶段,更是广购各种拓片,藏有从先秦至民国各种拓片470余种,1100余张。他还大量购买金石类书籍,如《金石萃编》《金石萃编校字记》《艺风堂考藏金石目》《山右石刻丛编》等近百种,这些购买收藏,是鲁迅读碑,录碑、校碑的基础,可谓丰富至极。遍览古代金石碑刻的同时,鲁迅和当世书法亦颇有联系。鲁迅对于同时代的书坛并非无知,他对当世书家有其好恶,比如很是欣赏弘一大师后期的书作,他与同时代一些著名书家有比较密切的交往,如陈师曾,乔大壮等。此外,鲁迅与同时代的很多知识分子有书信往来,这些书信也多用毛笔写成,书写风格多样,品位不低,这对于鲁迅而言,其实也多了品鉴时人书法的直接机会。我们基本可以认为,鲁迅观览揣摩过中国书学自古至民国各家各派的书法作品,可以说,源于越文化的可贵的开放文化心态和吸收借鉴意识促成鲁迅至为广博的书法艺术视野,这对鲁迅修习书法自然是大有裨益。
其二,越文化的务实精神对于鲁迅书法的影响。越地先民在非常困难的自然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铸就越文化务实、理性,不虚浮的精神品格,这对于鲁迅的精神气质也有直接影响,形成了鲁迅的务实品格和理性精神。这务实品格与理性精神进而直接影响及于鲁迅的书法实践。具体而言,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书写工具和书桌布置尚简重实用。鲁迅于书写工具及书房用品方面向来不讲排场,全无浮华之风,以简素便利为上。他多年主要用卜鹤汀笔庄所售的“金不换”毛笔,价格便宜,离开绍兴后还曾多次托人购买此笔。萧红《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曾描述过鲁迅书桌的简朴实用:“鲁迅先生的写字桌,铺了一张蓝格子的油漆布,四角都用图钉按着。桌子上有小砚台一方,墨一块,毛笔站在笔架上,笔架是烧瓷的,在我看来不很细致,是一个龟,龟背上带着好几个洞,笔就插在那洞里。鲁迅先生多半是用毛笔的,钢笔也不是没有,是放在抽屉里。桌上有一个方大的白瓷的烟灰盒,还有一个茶杯,杯子上戴着盖。”[9]其二,是书写观念重实用,强调字要写清楚,让人不费力就认得。鲁迅很反感别人写字不清楚,令人难以辨认。这一点萧红也有记述,“青年人写信,写得太草率,鲁迅先生是深恶痛绝之的。‘字不一定要写得好,但必须得使人一看了就认识,青年人现在都太忙了……他自己赶快胡乱写完了事,别人看了三遍五遍看不明白,这费了多少工夫,他不管。反正这费的工夫不是他的。这存心是不太好的。’”[9]鲁迅自己的字是不拘各体,一向写得清楚易认。其三,是鲁迅书学实践绝大多数为实用性书写,具日常性,无表演性,也不为艺术表现。他的写字绝大部分是针对著述和抄录工作,时间久、数量大,所以书写既要求速度、也求便利,同时要求清楚、也求美观。从具体书写讲,鲁迅多写小楷,字偏规整,结体清晰,大小差异不多,多采用圆转、简练、雅洁、朴拙、洒脱等表现手法。长期大量的实用性书写实践使得鲁迅书法的这些特点日益完善并突出,在纯熟精进中愈加显出其书法朴素、清雅的个性。显然,与越文化内蕴相关的务实精神和实用追求对于鲁迅书法从用品、观念到书学风貌都有所影响和铸造。
其三,越文化的坚韧顽强精神和勤奋之风对于鲁迅书法的影响。越族多有坚韧顽强精神、卓苦勤劳之风,这一越文化传统历史悠久,从大禹治水到勾践复国,绵延不息。越人多出才俊名士,是因为他们处事富于认真、执着、勤苦的精神,在学业、事业上有“韧”劲和毅力。鲁迅对此有论,“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4]审视鲁迅自身,堪称是突出体现越人坚韧勤苦文化精神的优秀典范,在世50多载,鲁迅在文学创作,思想拓展及其它各种事务中的认真执着,坚毅刻苦少有人能比,而论及书写一事,鲁迅写字的勤奋与数量之巨也是少有人能企及的。鲁迅自幼习字时便极为认真,一丝不苟,先后受到老师周玉田、寿镜吾的嘉许,赞其在同学中总是写得最好的一个,这“最好的”即能说明他的用心认真、用功踏实。他年少时即喜爱金石,勤于收集相关书籍,并经常到绍兴多处古迹采集拓片,用心用力都不俗。为了记住《尔雅》中的繁难字,鲁迅就从《康熙字典》中将与这些字有关的部分抄录下来并装订成册。年少的鲁迅还抄录过《唐诗叩弹集》《花镜》《茶经》《二酉堂丛书》等。这些事都是非常耗费时间心力的,鲁迅做这些事是出于自身喜欢,但没有毅力,不下功夫也是完成不了的。除文学创作中的书写外,鲁迅的抄碑几乎是世无匹敌的。他在读碑、校碑的过程中不断抄写,为了保证抄碑的质量,他还抄了大量有关碑刻的古籍和资料,如《汉石存目》《汉碑释文》《罗氏群书目录》等等。中年阶段是鲁迅读碑、录碑最勤苦,接触历代各种书体最多的一个时期,他所抄录现今存世的有近千种,近万页,近300余万字的辑校古籍手稿、辑校石刻手稿、金石资料、手摹《秦汉瓦当文字》和金文手稿,这些数字是惊人的,背后的劳动更是难以想象,非有艰苦卓绝之精神不能完成。诚如周作人《题豫才手书〈游仙窟〉》所言,“豫才勤于抄书,其刻苦非寻常人所及,观此册可见一斑。”[10]康有为说:“临碑旬月,遍临百碑,自能酿成一体,不期然而自然者。”[11]何况鲁迅几乎是经年累月地写字抄碑,字量巨,抄碑勤,这于其书艺的进益和纯熟自然大有帮助,亦使其书法透出明显的“功夫气”和“金石气”。鲁迅持续一生的巨量书写活动充分展示越人坚韧顽强、勤苦奋进的特质,当然也证明着越文化精神强韧执着、踏实努力一面对鲁迅人格精神及其书学活动的直接有力影响。
其四,就美学特征讲,越文化成就鲁迅书法一个奇特现象——书写内容的“硬”“韧”特质与书艺的“和静”“古雅”韵味的组合共生。中国书学一般讲“字如其人”,可乍一看,鲁迅书法呈现的风貌是质朴宽厚、舒展但不狂放,韵味古雅,与一般印象中鲁迅为人为文的深刻犀利很不相似。这个现象很有意味,值得思考。越文化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文化内涵也很复杂多元。越文化有理性务实、硬气和韧性突出,刚烈尚武、坚毅勤奋的一面,但作为面海文明,它又有水性十足的一面,体现为沉静含蓄、灵动柔美的人文情愫和风骨。越文化有其矛盾性特质,即刚、硬、野与柔、细、雅的统一共生,有胆剑之气,又有琴曲之韵。越文化的矛盾性特质对于越人精神的铸造自然是多元多向的,所以越地杰出人士的心灵面貌往往深邃复杂、丰富立体,少见单一和单薄。周作人就曾说自己的灵魂里面住着一个“流氓鬼”,还住着一个“绅士鬼”。鲁迅写过“怒向刀丛觅小诗”,但也写过“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心灵的丰厚、深邃与复杂远过一般人,甚至有一些矛盾性的人格要素和精神特质共存于他的心灵中,并显现在他文学创作的艺术个性中,比如狂放与沉静,犀利尖刻与柔和温情,峻烈阴郁和柔美诗化等。考察鲁迅的书作,清晰可见其书写内容与思想精神的“硬”“韧”特质与书艺的“和静”“古雅”韵味的共生共在,可以说,前者与越文化刚性一面契合,张力大,战斗性突出,后者与越文化水性一面契合,张力小,书卷气浓,和静气息凸显,而这二者间的组合共生又是高度统一的,铸就独异的文学鲁迅和书法鲁迅。或者可以说,在书写的内容、思想面貌上,鲁迅是近于越文化中大禹、勾践所代表的刚性精神,在书写形式、美学精神上更接近他所爱好的越文化中二王所代表的沉静、中和气质。因为直面中国的现实和浓重黑暗,鲁迅的思想表达和文学写作是痛苦的,也多阴郁、锐利和沉重,而且鲁迅的写作时间久,量多,几乎每日皆有,那么激愤、强烈的写作情绪需要舒缓和平衡,思想、情感的艺术表现放出去亦要收得回来,使文学的表达、表现在一个最合适的度上,于是,富有和静气息、古雅韵味的宽厚舒展的文字书写就平衡了激愤、强烈的情绪,适时收住了热烈奔放的艺术表达。这样,写作的心灵不致过于脱控而至于消耗到虚脱,艺术的表现也不失却必要的冷静和节制,实现动与静的有机结合。此外,从实用性书写角度讲,凸显太过强烈的个性、情绪很饱满、表现方式很张扬的书法不易持久书写,基本上是做不到以这样的书写方式和状态进行长久大量的写字工作,而以和静圆融舒展之笔从容挥毫,方能一日复一日地笔耕不辍。某种程度上,对于鲁迅的创作和书写来讲,书写内容的“硬”“韧”特质与书艺的“和静”“古雅”韵味表面上看似矛盾、不协调,但在根本上是最和谐统一的共生体,在自我生命质感和艺术表达肌理的最深处,越文化所滋润养育过的鲁迅找到了自我和艺术双重的平衡以及美。
此外,我们还应该强调越文化的“现代重构”以及鲁迅的贡献。因为地域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需要标志性文化名人持续的实际贡献。笔者曾以参会者和旅游者的身份多次到过绍兴,便明显感受到绍兴文化景观及“旅游文化”的变化。打开越文化的“文化地图”或走进现实中的绍兴,总能从墨迹斑斑中看到鲁迅的“文化身影”。其中,以鲁迅墨迹为元素化成的牌匾、联语、中堂、条幅及碑石等,也已经成为当今越地文化特别是绍兴城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显而易见,鲁迅墨迹成为了绍兴不少单位和景点的重要的文化符号,与王羲之墨迹形成的诸多景观构成了耐人寻味的文化呼应与联通,为建构中的“现代越文化”的发展都做出了切实的贡献。同时,事实也一再证明,“文化鲁迅”在书法文化方面,也可以成为具有“再生性”的文化资源之一。如果能在绍兴诞生一处集大成且蔚为大观的“鲁迅碑林”,那便是笔者当下的一个小小的愿望和建议。当然,鲁迅的思想、文学和他的墨迹是一体的,书法鲁迅是文化鲁迅一个不可割裂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深入认识鲁迅的路径之一。当我们审视现代文人书法家鲁迅时,凝神看到的是:越文化的血液和精气是鲜活流动于鲁迅的书法人生中的,因此在较大程度上可以说,鲁迅及其书法都是越文化这棵长青“历史之树”上结出的硕大果实。
参考文献:
[1]李继凯.论鲁迅与中国书法文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3).
[2]江平.作为书法大家的鲁迅[J].鲁迅研究月刊,2003(6).
[3]汤大民.鲁迅书法的特质和渊源[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及设计版),2001(3).
[4]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沈瓞民.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段[A]//鲁迅回忆录(散篇)(上)[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6.
[6]胡卓君,章剑深.鲁迅书法风格及成因探究[J].绍兴师专学报,1991(3).
[7]胡源.越中书法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8]王晓初.“面海的中国”与中国的现代化(下)[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1(2).
[9]萧红.回忆鲁迅先生[A]//鲁迅回忆录(散篇)(中)[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723.712.
[10]周作.关于鲁迅[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553.
[11]夏晓静.鲁迅的书法艺术与碑拓收藏[J].鲁迅研究月刊,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