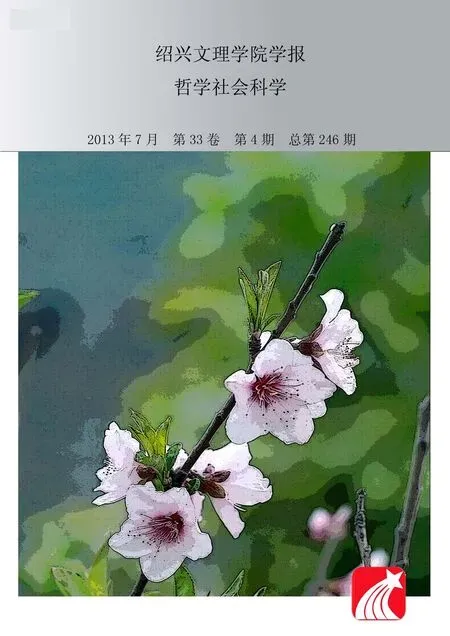论谭恩美小说的鬼魂叙事
——以《百感神秘》和《接骨师的女儿》为例
王小燕
(福建中医药大学 外语教研室,福建 福州350122)
美籍华裔女性作家谭恩美的很多小说,自发表不久就会荣登当时畅销小说之列,受到很多媒体和读者的好评,这也奠定了她在美国亚裔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在1989年,谭发表了第一部畅销小说《喜福会》,后改编成电影,随后又发表了小说《灶神之妻》(1991)、《百感神秘》(1995)、《接骨师的女儿》(2001)和《拯救溺水鱼》(2005)。谭的小说大都围绕着母女关系展开:中国母亲和美国女儿之间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不同的身份认同而矛盾重重,争吵不断,但最终都能达成和解。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谭恩美母女关系的母题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即鬼魂叙事,几乎在她的每一部小说里都有表现。在她的小说里,读者经常能看到光怪陆离的借尸还魂,神秘莫测的中国算命,还有让人不解的与鬼魂对话。鬼魂所代表的并不只是世界上那些未知的和无法描述的东西,也代表个体自我那部分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东西。
谭恩美擅长的鬼魂叙事写作策略与自身经历不无关系。谭的外祖母自杀而死。有时候因为一些小事她的母亲动不动就要去死,或者闹着要回中国,导致谭认为中国就像死亡,是个不祥之地。后来一次谭因为不想睡觉,谎称洗手间有鬼,可母亲竟然让她把鬼在哪里给指出来。从此以后母亲认为谭有“阴眼”可以看到鬼魂。这也就是《接骨师的女儿》里露玲和女儿露丝招鬼的故事原型。
西方主流作家群一直有着鬼魂叙事的传统,但其小说大都带给读者恐怖感,也被称作“哥特小说”。像艾伦·坡 (Edgar Allan Poe)的小说《黑猫》(The Black Cat)、《厄榭府的崩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 (H.P.Lovecraft)的《死灵之书》(Necronomicon,又译作《死者之书》);斯蒂芬·金 (Steven King)的小说《缅因鬼镇》(Salem’s Lot novel)等。在这些恐怖小说里,有着浓烈的恐怖气息,鬼魂都是有着怨气,以加害活着的人为目的。而谭恩美笔下的鬼魂大都是中国鬼魂,这些鬼魂被描述成善良的、对活人没有伤害的、和人的神秘感官紧密联系。这些无处不在的鬼魂,通过人的神秘感官,对被边缘化的、不自信的华裔女性有着自我身份认同的推动作用。鬼魂叙事是母亲重忆和重述过去的必要手段,而女儿们通过鬼故事唤醒了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也重新认定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对于西方社会高度发达的科技和理性而言,华裔作家笔下的鬼魂是必定会被贴上“他者”标签的,当然也会被反对和排斥的。一方面,谭恩美的鬼魂叙事可以满足西方媒体和读者对于东方的好奇心和窥视欲,因为西方总是以凝视者的姿态来处理与东方的关系。对于西方而言,中国的鬼魂之说是危及西方“自我”身份的“他者”因素。另一方面,鬼魂叙事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西方权利话语和主流文化的反叙事。
一
《百感神秘》是谭“最有智慧、最吸引人的作品”[1]。故事围绕着同父异母的姐妹——姐姐邝(Kwan)和妹妹奥利维亚 (Olivia)展开。她们之间有着前世今生的缘分和纠葛。也有着疏远难定的亲情和不同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奥利维亚相差12岁的姐姐邝在父亲死后,从中国移民来到美国。她全心全意的照顾爱护着奥利维亚,扮演着母亲的角色,却遭到妹妹的戏弄和背叛。因为邝是中国来的移民,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体面的工作、说着洋泾浜英语、穿着寒酸,并且她的文化和民族认同与白人主流社会格格不入,是属于被遗忘的“边缘”他者。但是她坚守着祖居文化,有着东方的价值观以及思维模式。虽然属于被排挤的边缘他者,邝不是完全失语的,她有着自己的言说方式,即讲鬼故事。“说话意味着有权利定义自己,从而抵制别人的定义。”[2]
美国当代叙事学家苏珊·兰瑟认为:“在各种情况下,叙述声音都是激烈对抗、冲突与挑战的焦点场所。”[3]在与西方主流社会的对抗中,作家谭恩美让拥有他者身份的邝采取了迂回的策略。因为西方人眼里,中国人是“愚昧”和“非理性”的,爱德华·赛义德在其《东方学》一书中指出:“人们用很多词来表达这一关系: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4]所以作者让邝讲述中国的“鬼”故事似乎是无奈之举。在西方主流霸权面前,唯有这样的叙事方式才是被西方读者所接受的。但“非理性”的东方却在某种程度上消解着西方的理性。
邝是神秘的,她告诉妹妹奥利维亚自己曾经跟邻居的小伙伴被洪水淹死了,可是七天之后她却借着小伙伴的身体离奇生还。她自诩有阴眼,能够看到阴间的人。那些鬼会从冥界来拜访她位于旧金山巴尔博亚街的厨房。她喜欢时不时地喋喋不休地给妹妹讲令人费解的怪异故事,并且让奥利维亚保守关于鬼故事的秘密。但是奥把这些秘密告诉了自己的母亲,这位白人母亲认为邝得了精神病,把她送到了神经病医院接受电击治疗。在以发达和理性著称的西方,鬼魂之说,特别是来自东方的鬼魂之说是万万要不得的。在这里华人与白人的种族对立以及文化冲突,又表现为理性与癫狂的精神对立。法国哲学家福柯在其作品《癫狂史》说道:“任何一个时代和社会的权力关系模式,皆由其历史话语中的概念,和等级分明的二元对立如理性和非理性,文明和癫狂等等构成,由此而确定何为知识和真理,何为人文规范……。”[5]西方人,如奥利维亚的母亲和她的白人男朋友,认为自己掌控着理性和文明,他们定义着何为人文规范,而来自中国的邝和她的鬼故事严重挑战了她们的人文规范的权威。
邝的鬼故事,有着神奇的疗伤功能。邝的鬼魂之说拯救了奥濒临破裂的婚姻,奥一直对于丈夫西蒙死去的前女友耿耿于怀,对自己的婚姻不自信。邝通过她的神秘感官和“阴眼”,想尽办法让她们复合。讲述鬼故事既是邝对祖国文化坚守的表现,也让奥利维亚对西方社会的理性产生了质疑。虽然奥利维亚有着一半白人血统和一半中国血统,但是她认同的只是自己的白人血统,对自己的另一半中国血统不认账。但是她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也产生了困惑。而邝的鬼故事让奥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认同。“几乎每一次与我谈话时,她都要提起中国,提起她是多么地该在一切都未改变和时机太晚之前返回中国……她有关鬼的话题说得越来越频繁了。”[1]24不断提起的鬼故事可以打破真实世界和梦幻世界的界限,让奥的前生与今世记忆之链连接起来,与自己的另一半中国血统和中国文化越走越近。邝经常在睡觉之前用中文讲鬼故事给奥听,虽然开始的时候奥对这些鬼故事是反感的,但的确“邝把中文传染给了我,……把她的中国秘密挤压进了我的大脑,改变了我对世界的思维方式。”[1]13渐渐地,奥开始意识到“尽管我们俩有着所有那些显而易见的差别,邝却认为我和她十分相像。在她看来。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一根广大无边的中国脐带,这根脐带给我了我们相同的遗传特征、个人动机、命运和运气。”[1]23慢慢地奥利维亚开始拾起被遗忘掉的历史,把自己和中国联系到了一起。后来在邝的坚持下,奥和西蒙回到了中国的故乡,更多地了解了自己的前世,感受到了姐妹情深。她感慨道:“我凝视着山峦,明白了长鸣何以看上去如此熟悉……在这里,我感到自己被隔膜成两半的生命终于融合为一。”[1]230奥如此感悟是因为她的一半白人血统和一半中国血统终于得到了融合。可以说,小说成功运用鬼魂叙事,帮助奥利维亚完成了真正的身份认同之旅。在这部小说里,谭巧妙地运用鬼魂叙事给我们展开了一幅神奇的画卷,有评论认为:“故事神奇而难忘。邝那萦绕心头的预言,神秘的感官以及将现在和过去相联系使小说闪耀着丰富的内涵,令读者读后回味无穷。”[1]
二
小说《接骨师的女儿》发表于2001年,是谭的又一部力作。在小说的扉页,作者这样写道:“母亲在世的最后一天,我终于知道了她还有我外婆的真实姓名,仅以此书献给她们两位:李冰姿 谷静梅。”[6]小说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作者的家族故事,这是一部关于一个家庭三代人之间的故事。评论家认为:“(小说)悲惨辛酸,既苦又甜。一个关于保守与揭示秘密,疏远与调和关系的动人故事。”[6]宝保姆是露玲的母亲,她在还没有结婚前就怀了露玲,但是公开的身份却是保姆。露玲既是母亲又是女儿,她与母亲的关系决裂是因为她不顾母亲的激烈反对,要和杀父仇人的儿子结婚,最后导致宝姨自杀;她与女儿露丝的关系紧张一方面是因为来美移民生活的艰辛,另一方面是因为严重的文化沟通障碍。
因为岁月年久,露玲竟然忘记了最亲爱的宝保姆的姓氏。“我念完百家姓,却没有一个能勾起我的回忆。那个姓氏很不寻常吗?难道是因为我把秘密藏得太久,竟在不知不觉中将它失落了?”[6]4心理学家认为记忆是作为自我存在的标志,记忆之链的断裂或记忆的丧失,意味着人格的不完整和破碎。所以来美之前的露玲是一个活泼可爱、聪明伶俐、对生活充满向往的年轻姑娘,而来到美国之后露玲似乎性情大变,她性格古怪、严厉、专横、小心眼,并且动不动对不服管教的女儿以死相要挟。这也许归咎于她失去记忆后的人格不完整。
为了找回母亲的姓氏,找回遗失的记忆,减轻自己对母亲背叛的愧疚。她一再让女儿露丝把宝姨的鬼魂招来。这样的行为让女儿很是反感。在露丝眼里,来自东方的鬼魂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八年以来,每年八月二十日左右,露丝就开始失声,说不出话来。因为每年这个时段是流星雨的高潮时期。母亲认为流星是鬼形所化,看到流星会倒大霉,“要是你看到流星,那就是有个鬼魂想跟你说话。”[6]8女儿露丝不相信这些鬼魂之说。对于从小就生长在美国的露丝来说,她有着美国的文化认同、思维方式和西方理性。
就像《百感神秘》里奥的母亲的反应一样,她的白人朋友嘉琵就曾经建议露丝带着母亲去看心理医生,“他们 (医生)很擅长处理文化差异——能了解东方人天马行空的思维方式,旧社会的压力,精气运行等等。”[6]47显而易见,露玲和邝都是来自中国的移民,她们的有些想法和故事,在不被西方人了解的情况下,必定会被认定是精神错乱的表现。
露玲借由女儿拿着筷子操作的沙盘跟宝保姆的鬼魂说话,露玲向宝姨乞求原谅,真诚地表达着自己的忏悔。她觉得女儿摔伤是跟宝姨的诅咒有关,“我求您了,若是诅咒还不算完,求您要了我的命去吧,只要您放过我的女儿就行。我知道她最近的事故算是个警告。”[6]75这样的行为虽然荒谬,可也让露丝知道母亲对自己的爱,渐渐地开始对母亲的故事感兴趣。
为什么露玲喜欢谈起鬼啊、命运啊?一方面是因为露玲对死去的母亲有着深深的忏悔和思念。她想借这样的方式抒发内心复杂的情感。另一方面母亲露玲远在异国他乡,很早就死了丈夫,生活拮据,自己一个人艰辛地抚养着女儿。评论家苏珊·美伦认为:“谭对中国母亲作为一个移民在这个国度苦苦挣扎的不幸遭遇没有得到评论界的重视。”[7]19作者花了大篇幅来描写露玲的艰辛生活经历。露玲是弱势群体的一员,说着蹩脚的英语,因为听不懂别人说的话而经常发生争执,她的身上全是中国味。一次当别人指着露玲,问那个女人是谁时,露丝竟然说:“我不认识她,她不是我妈。”[6]69她在日记里甚至让自己妈妈去死。鬼魂叙事是母亲露玲的精神寄托,是弱势群体的无奈之举,也是母亲反抗主流霸权话语的有力手段。
但后来露丝明白,“妈妈有时会说起这个宝姨,她的鬼魂就飘荡在空中,……他们注定要在阴间游荡,长发湿淋淋地垂到脚下,浑身都是血。”[6]75这样的鬼魂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鬼魂形象。对于这个受着西方文化浸染的露丝来说,关于鬼魂的想像慢慢开始中国化了。露丝打开了她关于中国的神秘感官。“露丝使劲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了一个女人,长头发一直垂到脚跟。”[6]76当母亲跟宝姨的鬼魂说话时,“露丝感到有东西碰到自己肩膀,不由吓了一跳。”[5]76
虽然女儿露丝是美国人,接受着美国教育,甚至有着美国人的婚姻观——同居不结婚。她的内心深处是不自信的,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露丝深知被当成局外人那种尴尬感受,她从小就经常遭人排挤。打小搬过八次家的经历使她非常清楚地体会到那种格格不入的感受”[6](p.58)。露丝总是能意识到自己非白人的现实,中秋节家宴上,“露丝看到亚特和米莉安 (亚特前妻)一起坐到另外那张桌子边,那边很快变成了‘非华人区’。”[6]86她和同居男友亚特之间有着大问题,她为亚特和他跟前妻生的两个女儿忙忙碌碌的过着每一天,可他们似乎对她的付出并不领情。“分开之后,她越发看清楚,自己已经习惯了,哪怕对方不提出要求,她也会主动妥协,迎合他的感受,这已经成了自己的情感模式。”[6]248这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情感问题,是东西方文化和思维模式碰撞的表现。
为了照顾因为老年痴呆而渐渐失忆的母亲,露丝搬去跟母亲同住,这个时候母女之间的隔阂慢慢消融,母亲的日记让露丝了解母亲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又是怎么来到这个国家的。“无法从口头上向对方说明自己的历史、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的时候,借助于文字书写成为她们表达过去不光彩历史的保险方式。”[8]露玲的日记郑重声明:“所有这一切都是真的。”她用日记独白的叙事方式介绍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事物。宝姨是接骨师的女儿,她秉承了父亲的接骨手艺,其中最神秘的药方就是“龙骨”(实则是北京猿人头骨)。她写一手漂亮的书法,嫁进了制墨世家,随后她在育婴堂的生活又以北京人头骨的发掘为背景。因此母亲的日记给露丝打开通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大门。对中文一窍不通的露丝,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走进母亲的世界,了解那段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最终两代人的感情上的伤疤得以愈合。
露丝发现在母亲的日记里有很多关于鬼的叙述,例如:宝姨在烫伤自己后,“小叔托梦给老太太,说若是宝姨死了,她们两个的鬼魂定要大闹家宅,找那些不肯怜悯宝姨的人报仇。”[6]166后来因为露玲决意要嫁给杀父仇人,宝姨以死相逼, “她披头散发,泪流满面,身上滴着黑血。”[6]203找到露玲的父亲(叔父),她责问他,且诅咒着,因为宝姨作祟,整个墨坊被火烧掉了。这样的鬼故事虽然有点可怖,但是符合中国人“善恶有报”的思想观念。后来在集市里,露玲碰到了一个瞎眼的女孩儿,她告诉露玲有个鬼魂要跟她说话,而那个鬼魂正是宝姨。后来有个道士又来到家里,把宝姨的鬼魂封到了一个醋罐子里,让她几辈子都不能出来。
通过那么多的鬼故事,露丝明白了为什么妈妈总是把“鬼”啊、“死”啊挂在嘴边。母亲的神鬼之说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跟她的经历和中国文化紧密相连。对露丝来说,寻找母亲的个人历史,也就是寻找自己的中国根性。“她想要在这里,听妈妈讲述自己的故事,陪她回顾生命中经历的种种曲折,听妈妈解释一个汉字的多重涵义,传译母亲的心声,尽量了解母亲的思绪。”[6]146从原来想要远离母亲,到现在自觉自愿地想跟母亲生活到一起,不仅仅是血缘亲情的作用,更多的原因是因为找到了一种跟母亲一样的身份认同。那些神奇的鬼魂叙事,曾经让露丝反感讨厌自己的母亲,却引领她找到了母亲在中国的过去。在露丝完全读懂了母亲的日记,了解了母亲的过去之后,她不仅找到了自我身份,也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又到了生日的时候,露丝没有失声。她跟母亲和解了。
鬼魂叙事在谭恩美的另一部小说《灶神之妻》里也有所表现。如飞行员甘告诉温妮他经常做关于鬼的梦。鬼的第九个预言是他会在他本命年——下一个虎年的时候死掉。鬼的其它八个预言都已经一一验证是真的。最终甘难逃厄运,在24岁生日那天他驾驶的战斗机坠毁,他阵亡了。在谭的新作《拯救溺水鱼》里,她巧妙地用鬼魂陈碧碧的视角来讲述整个小说。可以说,谭恩美的小说经常会创造一个魔幻般的世界,大多是由迷信、巫术、鬼魂和难熬的岁月等一系列戏剧性故事构成。
鬼魂叙事无疑是谭恩美小说浓墨重彩的一笔。谭恩美利用这样的叙事方式成功的塑造了一些“他者”母亲的形象,以及“两个世界之间”文化和思维方式的撞击和融合。要破除母女两代人的隔阂,最大的羁绊不是语言障碍,而是不同的文化和身份认同。母亲强烈地想让女儿听听关于中国的故事,在她们痛苦地打开记忆之门的时候,也就完成了自我建构,所以记忆是回想也是创造。同时,一个个鬼故事开始时是东西方两种文化冲撞时露出的地面岩层,到最后却成了“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
[1]Amy Tan.The Bonesetter’s Daughter[M].New York:Ballantine Books,2001.
[2]黄秀玲.从必要到奢侈[M].北京: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32.
[3]苏珊·兰瑟.虚构的权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7.
[4]爱德华·赛义德.东方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9.49.
[5]陆杨.后现代性的文本阐释:福柯与德里达[M].上海:三联书店,2000.75.
[6]谭恩美.接骨师的女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7]Suzanne D’Mello.China Tan:In Amy Tan’s Fiction,American Daughters Despise Their Chinese Mothers[J].The Weekly Standard.2001,2(4):19
[8]陈爱敏.母女关系主题再回首[J].外国文学研究,2003(3):7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