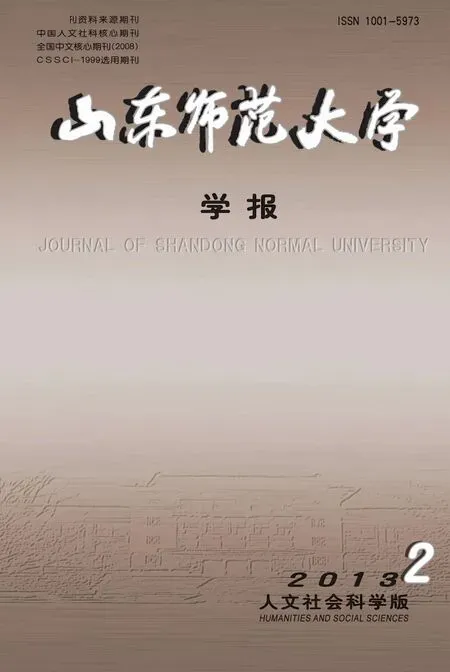帝国法与近代早期德国的宗教关系(1517
—1648)*
高宗一
(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 )
帝国法与近代早期德国的宗教关系(1517
—1648)*
高宗一
(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 )
为调解德国宗教改革时期(1517—1648)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纷争,神圣罗马帝国在法律层面上通过了多项决议,尤其是《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和《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主要表现在宗教合法化、自由化甚至中立化等方面。帝国从中表现出了日渐清晰的政治理性原则,直至完全抛弃了宗教因素的影响,确保了近代早期德国宗教关系的和平稳定。帝国调解宗教之争,实质上是对世俗领地格局的调整。帝国政治在此过程中日益世俗化和宪政化。
近代德国;帝国法;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奥格斯堡宗教和约
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在德国威腾堡张贴《九十五条论纲》掀起了席卷欧洲范围内的宗教改革运动,把社会分裂成了新教与罗马天主教两大阵营。在两大教派纷争不休、战乱不止之中,西欧诸国均以暴力消除宗教信仰差异的方式成功实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稳定,而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却能够在宗教信仰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在法律层面上维持着新教与天主教在宗教信仰上的二元化,最终在近代早期的德国实现了宗教的长久和平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帝国体制从中所表现出来的治国能力“令人着迷”*Winfried Schulze. Majority Decision in the Imperial Diet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8. Suppl. (December 1986). p. 46.。帝国法就是这种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帝国法”,尽管欧美法学界和史学界对其概念从未有过共识,但一般来说,是指建立在帝国权威之上的所有成文法。确切地说,在近代早期的德国,帝国法是指“神圣罗马帝国借以规范帝国等级秩序的法律文本、协议章程以及敕令诏书等等,用以确定帝国等级的级别、特权、权限、责任以及相互关系”*[德]彼得·克劳斯·哈特曼:《神圣罗马帝国文化史——帝国法、宗教和文化(1648—1806年)》,刘新利、陈晓春、赵杰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页,注释一。。帝国法,一般由天主教徒占据多数派的帝国议会(Reichstag)制定通过,经皇帝批准方可生效。帝国法的执行取决于帝国十大行政区之下具有离心倾向的邦国的意愿。
本文通过研究帝国法在调节近代早期德国宗教关系中表现出的理性和成熟,主要说明宗教改革时期帝国在政治上世俗化和宪政化过程。
一
从马丁·路德发起教改运动(1517)到德国边地侯战争(1552),帝国议会共计召开了20次。帝国议会虽然每次都涉及宗教问题,但在政策上大致缺乏统一性和稳定性,一直在高压和宽容之间摇摆,可谓变幻无常。帝国公开的决议、条例以及皇帝敕令等均不能为长久的帝国法提供基础。它们甚至多次规定了临时性的开战或停战。这暴露了帝国法最严重的危机。
这次影响广泛的教改运动,实质是对个性自由的主张,无疑挑战了一切形式的教俗权威,既打碎了传统天主教的教义体系,也明显与帝国所谓的统一观念背道而驰,致使帝国秩序陷入了空前的混乱。为恢复秩序实现统一,帝国议会先后通过了若干法律。
1521年1月沃尔姆斯帝国议会通过了《沃尔姆斯敕令》,宣布对马丁·路德实行最为严厉的剥夺法律保护令。据此法令,不仅路德将丧失一切权利不再受帝国法的任何保护,而且其著作也将被禁止传播并收缴焚毁,其追随者也将被严厉查办*James Harvey Robinson. Readings in European History. Volume II. from the opening of the protestant revolt to the present day. Ginn & Company. 1905. pp.83-88.。第二年的纽伦堡帝国议会宣布不再执行该敕令。之后,连续两次纽伦堡帝国议会(1523;1524)均通过决议再次执行该敕令*Adolf Erman. etc..The Historians' History of the World.Volume XIV. Henry Smith Williams. 1909. p.259.。不久之后的1526年,施佩耶尔帝国议会竟然通过决议,对以前违反《沃尔姆斯敕令》者予以宽赦,甚至还决定在德国的一个城市召开宗教大会之前,每个邦国应该按照各自希望对上帝和德皇所作的保证去做事*Johannes Janssen. History of the German People at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 Vol. V. London: R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 & CO. LTD., 1903. p.74.。帝国这种和解政策实施不久即告失败,因为1529年施佩耶尔帝国议会宣布废除那个“充满错误的看法和误解”的1526年帝国决议,再次执行《沃尔姆斯敕令》,禁止宗教改革*Thomas M. Lindsa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Volume I, Second Edition, Edinburgh, 1933. p.345.。1530年帝国议会在决定继续贯彻《沃尔姆斯敕令》之外还发出了威胁:如果路德新教派至1531年4月15日之前不重新回到旧教会的怀抱,不偿还旧教会的教产等,将被剥夺法律保护令*Adolf Erman. etc..The Historians' History of the World.Volume XIV. Henry Smith Williams. 1909. p.270.。此举可谓帝国对路德新教派最严厉的威胁,然而很快又峰回路转:1532年纽伦堡帝国议会提出一项非正式“条例”,即无限期延长宗教和解;废止帝国上诉法庭的反新教诉讼程序;不得因宗教分歧而对任何邦国提出起诉*Adolf Erman. etc..The Historians' History of the World.Volume XIV. Henry Smith Williams. 1909.p.271.。之后的3次帝国议会(1541;1544;1545)围绕着宗教和解展开工作,尤其以1544年施佩耶尔帝国议会成效最大。然而,1547—1548年“顽固的”奥格斯堡帝国议会把《奥格斯堡临时措施》强加给路德新教派,教改又被严厉禁止*Michael Kotulla,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vom Alten Reich bis Weimar (1495-1934),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Verlag, 2008. p.41.。
帝国在法律上对路德新教派政策不确定,呈现出一定的摇摆性,必然对德国宗教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第一,路德新教派与天主教派一度进入了所谓“和解”的新时代*Martin Heckel. Deutsche Geschichte,Bd. 5,Deutschland im konfessionellen Zeitalter, Gättingen,1983. p.37.。教改运动爆发后,由于帝国断断续续采取了宽容政策,宗教和解在一定时期内也得到了实现。比如在1526—1529年短短3年之内,德国北部除了勃兰登堡、萨克森公爵区和布伦斯维克-沃尔芬比特之外几乎所有的地区都信奉了路德新教*Thomas M. Lindsa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Volume I, Second Edition, Edinburgh, 1933. p.344.。在1532—1546年间,帝国的宽容政策除了1532年非正式提出了和解“条例”之外,1544年帝国议会还首次赋予路德新教当局对其教会和修道院享有“基督教改革”权;也规定了新旧教派无论其宗教信仰如何,在教产、教会收入、保护信众等方面均享有平等权*Martin Heckel. Deutsche Geschichte,Bd. 5,Deutschland im konfessionellen Zeitalter, Gättingen,1983. pp.36-37.。这把宗教和解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德国罕见地出现了持续10年之久的宗教和平。在新、旧教矛盾为这种临时的、模糊的政策所暂时隐藏的情况下,路德新教领地得以继续扩张:德国北方两大天主教邦国勃兰登堡选侯区和萨克森公爵区均加入了路德新教阵营。德国南北的路德新教徒甚至在搁置争议的基础上前所未有地团结了起来*Thomas M. Lindsa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Volume I, Second Edition, Edinburgh, 1933. p.333.。新、旧教如此并存,帝国内部甚至日渐产生出了一种新的思想认识,即人们具有双重信仰的权利*Martin Heckel. Deutsche Geschichte, Bd. 5, Deutschland im konfessionellen Zeitalter, Gättingen,1983.p.36.。
第二,路德新教派与天主教派从公开对抗到宗教战争。帝国对路德新教派的摇摆政策,是以宣布其为非法教派为前提的,所以随着教改运动的发展,路德新教与天主教之间分歧的加大,他们之间的张力也与日俱增,至1530年奥格斯堡帝国议会时,双方的对抗最终公开化。为应对以皇帝和帝国议会为代表的帝国天主教势力的威胁,路德新教派于1531年3月29日在萨克森选帝侯约翰·弗里德里希、黑森侯爵菲利普的领导下,在施马尔卡尔登缔结自卫防御同盟。面对领地迅猛扩张的路德新教派咄咄逼人的挑战,天主教派于1538年在皇帝查理五世发起和领导下,奥地利、巴伐利亚、美因茨、萨尔茨堡、萨克森、不伦瑞克等领主在纽伦堡组成了同盟*Adolf Erman. etc..The Historians' History of the World.Volume XIV. Henry Smith Williams. 1909. p.270.。双方难以调和的矛盾最终引发了施马尔卡尔登战争(1546年夏至1547年4月)。皇帝和天主教控制的奥格斯堡帝国议会趁新教方面失利之机制定了所谓的《奥格斯堡临时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过去罗马天主教会的信条和宗教仪式,路德新教派提出《莱比锡临时措施》以示抗议。双方分歧难以弥合,各派力量重新组合,最终又爆发了边地侯战争。
帝国对路德新教派政策摇摆不定,缺乏连续性和统一性,甚至自相矛盾发生了违反帝国法之怪举:一次帝国议会(1529)通过决议否决了另一次合法的帝国会议(1526)决议。这是因为:一方面,帝国从根本上是反对路德新教的。帝国是天主教的,皇帝是天主教的,帝国议会也是天主教的。广阔的帝国明显需要罗马天主教会发挥作用。路德教改不断发展,支持者越来越多,新教领地日益扩大,必然会削弱皇帝权力基础的帝国宗教——天主教,帝国联邦架构及其延续下来的法权秩序的根基终将被撼动,那个由最悠久的传统和最庄严的权威所共同神圣化了的帝国事业亦将消失。可以说,帝国反对路德新教运动是一种本能行为。另一方面,帝国又不得不对路德新教派做出一定的妥协,采取宽容政策。因为在此期间,帝国不断与邻邦进行战争(主要与法国进行战争,直至1544年9月为止;自1532年起与土耳其、1535年北非突尼斯,自1536年起与意大利、1541年在阿尔及尔),尤其是对抗土耳其的侵略战争,直接影响了帝国对路德新教的政策,因为帝国需要路德新教诸侯在财政和军事上提供支持,所以对日渐分离的新教派不得不给予必要的退让。可以说,每当有外部压力,帝国就会对路德新教派做出一定的妥协。“土耳其的威胁”次数越多,帝国对路德新教派妥协的次数就越多。
皇帝和帝国议会,作为帝国最高决策者和最高权力机关,首先关注的是帝国的统一,但是由于新教领地随着路德教义病毒式的传播而迅速扩张,直接威胁着天主教派的领地和既得利益,完全打乱了既有的社会秩序。所以,帝国政策的根本目标是实现社会秩序的和平稳定和帝国统一,这也因此导致了帝国几乎完全被动地受制于宗教问题。
事实上,宗教因素对帝国决策的影响一直非常强大。第一,帝国议会为天主教多数派所控制,采取的是多数裁决原则;而且常常讨论所谓宗教的真理问题,比如1521年沃尔姆斯帝国议会、1529年帝国议会、1547—1548年奥格斯堡帝国议会等等。第二,皇帝查理五世自认是教会天然的保护者,不仅组织、主持宗教会议(比如1541年雷根斯堡会议等),而且还于1538年领导一些南方天主教诸侯成立了反对新教的联盟。第三,罗马教皇对帝国决策的影响也不容漠视,有时甚至直接干预帝国的决策。比如教皇里奥十世使节亚历山大不仅参与起草了1521年帝国议会《沃尔姆斯敕令》,而且还极力游说皇帝予以批准,提议要发动世俗力量执行敕令等*Thomas M. Lindsa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Volume I, Second Edition, Edinburgh, 1933. p.298.。罗马教皇克莱蒙7世的红衣主教坎培吉奥在1524年1月纽伦堡帝国议会上呼吁,要无条件镇压“异端”,最终促成了帝国议会作出尽可能执行沃尔姆斯敕令的决议*Thomas M. Lindsa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Volume I, Second Edition, Edinburgh, 1933. p.259.。这反映了在当时政教难分的情况下,深陷内外困境之中的帝国难以保持更多的政治的理性原则,也难以充任超越教派的仲裁者的角色,更遑论在新、旧教派之间发挥应有的平衡作用了。
二
从边地侯战争(1552)结束至30年战争(1618—1648)爆发之前,在这半个多世纪里帝国召开了13次议会。其中成效最大、影响最大的是1555年奥格斯堡帝国议会,因为它是帝国第一次用政治理性的原则解决宗教问题的完美的尝试。这次帝国议会制定的许多政策及其精神大致统领了之后50余年的帝国议会。自此之后,帝国的宗教政策具有了统一性。
帝国在1555年召开奥格斯堡会议,是因为帝国所有等级在经历了从宗教分裂到数次宗教战争之后不得不承认,弥合宗教分歧实现教会统一的时机尚不成熟,因此迫切希望建基于既有状况暂时达成一个原则性的应急谅解:废除政治上的争执和军事上的协议,恢复帝国的和平秩序,其方式是尽可能让宗教信仰在帝国法的框架下实现合法化、自由化。
鉴于路德新教派势力之强大难以完全被征服从而实现教会统一,帝国为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在这次帝国议会上不得不做出妥协,通过了《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对路德新教所造成的既成事实给予了承认。路德新教派因此在法律上取得了一些重大权益:第一,路德新教徒赢取了合法地位。和约规定,帝国任何阶层均不得危害“奥格斯堡告白派”的安全,他们除了和平地享受其地产以及其他的权利和特权以外,还能够享受其宗教信仰、礼拜仪式等,而不必遭受来自帝国禁令的威胁处罚*Emil Reich. Select Documents Illustrating Medieval and Modern History. London: P.S.King & Son, 1905. p.230.。路德新教徒为此实现了长久以来的夙愿。第二,路德新教诸侯对教会的掌控权获得了合法性。根据“在谁的国家,信谁的宗教”(“教随国定”)的原则,新教诸侯可以自由选择宗教信仰,能够决定其臣民的宗教信仰,重要的是,他们对辖区内的教会所实施的最高管理权和司法裁判权从此获得了帝国法律的认可*Emil Reich. Select Documents Illustrating Medieval and Modern History. London: P.S.King & Son, 1905. pp.231-232.。此举废除了罗马天主教会主教长期以来的专属特权。第三,路德新教徒被允许“迁徙自由”。根据规定,帝国境内路德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一样,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想和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一起离开去另一地方定居,他们在支付税收后其地产不应受到任何阻挠,他们的荣誉也不得受到损害*Emil Reich. Select Documents Illustrating Medieval and Modern History. London: P.S.King & Son, 1905. p.232.。尽管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宽容,但是帝国在法律层面上消除了因信仰不同所招致的宗教迫害。这是该和约较以往法律最大的新颖之处。
帝国在法律上认可了路德新教派的一些合法权益,但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仍旧体现了天主教派单方面的意愿,凸显了帝国对天主教派的偏袒倾向和对路德新教派的傲慢姿态。第一,“教士保留权”。根据规定,大主教、主教、高级教士或其他宗教阶层在放弃旧教皈依路德新教时,必须放弃其对原来主管教区的统治权、世袭领地、圣职和俸禄;根据当地的法律或者习俗,教士会议和类似机构有权选举一位信奉旧教的宗教人士充任此空缺职位,而且他能够拥有和享受该职位的所有权力和收入而不应受到任何阻挠和偏见*Emil Reich. Select Documents Illustrating Medieval and Modern History. London: P.S.King & Son, 1905. p.231.。这项法令是天主教派强加给路德新教派的,路德新教派对此强烈反对,并声明不接受它的束缚。第二,和约规定,路德新教派诸侯应该对其领地内的天主教徒在宗教、财产和安全等方面予以宽容。路德新教派尽管也要求天主教诸侯对其辖区里的路德新教徒给予同等的待遇,但因遭天主教派反对,只是获得了国王费迪南个人的执行承诺*Johannes Janssen. History of the German People at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 Vol. VIII. London: R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 & CO. LTD., 1903. p.354.。天主教派与路德新教派在这两个敏感问题上分歧严重,反映了它们对领地的激烈争夺。事实上,1555年之后的历次帝国议会虽无显著成果,但在这些问题上,尤其是在“教士保留权”上争执不断,最终诱发了30年战争。
帝国所有等级极其渴望能够制定一个“持久有效”的和约,以解决由宗教争端所导致的领地之争,这反映在他们在磋商时频繁使用了beständiger, beharrlicher, unbedingter, für und für ewig währender等词语(这些德文词语意为“永久的”)*Thomas M. Lindsa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Volume I, Second Edition, Edinburgh, 1933. p.396.。但事实上,该和约仍为一个临时性停战协定。新、旧教派在和约之后的关系不仅更加分裂了,而且双方都在利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进行巩固和扩大各自的领地,以期能够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赢得整个帝国。在和约之后的10年间,路德新教派凭借帝国在法律上所给予的权利,在对已占领地进一步巩固之余,继续保持一股强劲的扩张势头,在1560年代把领地扩张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整个德国北部、西部和西南部几乎完全为路德新教的势力范围*A. W. Ward etc.. 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Atlas, map 18, Western & Central Europe, The Progress of the Reormation to 15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2.。天主教派也在帝国法的庇护之下在16世纪50-60年代,特别是1563年特兰托会议结束之后开始了自1526年以来的第一次复兴,出现了所谓的“重新天主教化”的现象(直至1624年达到高潮),比如在德国西部明斯特、奥斯纳布吕克、威斯特伐利亚、福尔达、普法尔茨、维茨堡等地区信奉了天主教*A. W. Ward. etc. 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Atlas. map 28 Religious Divisions of Germany c.1610. Cambridge at the Univerisity Press. 1912.。天主教在与路德新教的激烈竞争中,不仅在争夺教会教职上占据了优势(比如1559年亚琛、1582年科隆、1583-1598年斯特拉斯堡),而且在地方议会和帝国议会的较量中也完胜(比如1593年亚琛市议会;1600年科隆议会;1608年雷根斯堡帝国议会)。很多地区纷纷放弃新教重新接受了天主教,天主教从根本上扭转了新教派领地扩张的势头。最终,新教徒在1608年5月在安豪森联合缔结了“新教联盟”,而天主教也于翌年7月在慕尼黑成立了“天主教同盟”。两大对立教派矛盾不可调和,最终爆发了30年战争。
帝国藉此和约虽然没能实现宗教统一,而使宗教分裂更甚,但是由于在法律上寻找到了一条可以实现宗教妥协的途径,把宗教冲突至少暂时经过了合理化的处理,临时缓解了世俗领主对领地的争夺,让帝国的政治和平在可见的未来不再遥不可及。帝国长久以来逾期未实现的政治和平优先于宗教上的最终统一,或者说帝国在维持宗教分裂的情况下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严格说来,欧洲其他地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精神完全没有如此先进*Michael Kotulla,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vom Alten Reich bis Weimar (1495-1934),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Verlag, 2008. p.50.。
帝国试图以此和约解决长久以来备受困扰的宗教问题,然而保持了帝国以往对天主教派明显的倾向性,而且教派之间也没有相互的宗教保证,这暗示了新旧教派在未来关系的不确定性,也注定为以后的教派矛盾和冲突埋下了伏笔。然而,帝国在制定该和约时罕见地没有触及悬而未决的宗教的真理问题,甚至在法律上进一步疏远了与罗马天主教廷的关系;而且从帝国法的角度看,新旧教派在1555年之后虽然继续发生激烈的宗教冲突,但在神学教义上的争执却大大消减了,更突出地表现为世俗的领地之争了。这说明了在帝国层面上已经悄然开始了世俗化进程,说明了帝国在进行宗教决策时日益表现出政治的理性原则。
三
30年战争(1618—1648)之后,大致以新教派诸侯及其支持者瑞典为一方,以天主教诸侯及其支持者法国、皇帝为另一方共同参与制定了和平停战条约《威斯特法利亚和约》。该和约后来由帝国议会接受为帝国法,它所制定的政策及其精神在调解战后德国的宗教关系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后世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该和约在相互睦邻和大赦的前提下,在对《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予以确认的基础上,本着完全的世俗原则而不是宗教原则,全面修正和完善了以往的相关法律、法规,在德国实施全面的宗教合法化、自由化,甚至中立化。
1.帝国扩大了宗教合法化的政策:在法律上承认了新教改革宗。根据和约规定,帝国所赋予天主教和路德新教的所有权利和利益,以及帝国其他所有的决议,对被称为改革宗的那些人也适用*Arno Buschmann, Kaiser und Reich, Klassische Texte und Dokumente zur Verfassungsgeschichte des HI.Römischen Reiches Deutscher Natio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4. p.338.。同时还规定,新教两大派之间实现和解,相互尊重,任何一方不得损害另一方;一方的领主在两教派之间可自由改变宗教信仰,但是对其臣民、宗教、秩序和财产等均不产生任何影响*Arno Buschmann, Kaiser und Reich, Klassische Texte und Dokumente zur Verfassungsgeschichte des HI.Römischen Reiches Deutscher Natio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4. pp.336-338.。帝国与新教改革宗、新教改革宗与路德教派分别达成了和解协议,让1555年之后不受《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帝国法保护的巴拉丁以及整个德国南部大量的改革宗信徒一方面获得了合法身份和安全保障,另一方面也接受帝国法的约束,这从法律层面上消除了自16世纪中后期新教内部两教派之间激烈的领地之争。
2.帝国规定了宗教自由化。(1)废除1555年制定的“教士保留权”。天主教和路德新教的高级神职人员在改变宗教信仰时,只是他个人丧失公职,其荣誉、财产和岁入不受任何影响,而且有权要求其同一教派的人填补其空缺*Arno Buschmann, Kaiser und Reich, Klassische Texte und Dokumente zur Verfassungsgeschichte des HI.Römischen Reiches Deutscher Natio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4. pp.313-314.。(2)在天主教邦国里的抗议宗臣民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而不受任何方式的骚扰,包括其所属物*Arno Buschmann, Kaiser und Reich, Klassische Texte und Dokumente zur Verfassungsgeschichte des HI.Römischen Reiches Deutscher Natio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4. p.323.;而且还规定:无论在天主教邦国,还是在抗议宗邦国,其臣民宗教信仰是否与领主的一致,都应该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不得遭受任何的干扰和虐待*Arno Buschmann, Kaiser und Reich, Klassische Texte und Dokumente zur Verfassungsgeschichte des HI.Römischen Reiches Deutscher Natio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4. pp.324-325.。此外,帝国又对移民自由有了更详细的规定,比如迁出的时间、财产的保护等等更明细化,使之具有更大的可操作性*Arno Buschmann, Kaiser und Reich, Klassische Texte und Dokumente zur Verfassungsgeschichte des HI.Römischen Reiches Deutscher Natio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4. p.325.。这些规定,全面修正和完善了1555年和约中频频引发宗教争执和武装冲突的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从而尽可能减少甚至杜绝了由此导致的世俗领主之间对领地的争夺。
3.帝国规定宗教中立化,即宗教绝对平等。这是帝国在宗教合法化、自由化政策上的进一步发展,也是该和约较帝国以往调解宗教关系的法律的最大的突破之处。根据规定,在所有问题上,在天主教和路德新教两大教派的选帝侯、王子和邦国之间要恪守严格的、相互的平等,真正完全符合帝国法和以往的惯例:对两大教派必须保持公正,两派之间的所有暴力行为必须永远禁止*Arno Buschmann, Kaiser und Reich, Klassische Texte und Dokumente zur Verfassungsgeschichte des HI.Römischen Reiches Deutscher Natio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4. pp.308-209.。具体表现为,帝国议会、帝国最高法院、枢密院等一切公职均硬性规定在人数上教派之间完全平等*Arno Buschmann, Kaiser und Reich, Klassische Texte und Dokumente zur Verfassungsgeschichte des HI.Römischen Reiches Deutscher Natio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4. pp.331-334.。这种“绝对的相互平等”,甚至已经上升为帝国法的最高准则;而且在宗教问题上废除了多数裁决原则*Arno Buschmann, Kaiser und Reich, Klassische Texte und Dokumente zur Verfassungsgeschichte des HI.Römischen Reiches Deutscher Natio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4. pp.311、332.,改用“个别投票”权,即在决定宗教问题时,在新旧教之间应该以一种友好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按照帝国议会以往的由多数人来决定的惯例*James Bryce. The Holy Roman Empire. A New Edition. Revised. Macmillan and CO. 1866. pp.375-376.。事实上,“严格地遵守教派均衡和严格的比例代表制,虽然最终变成了一种实际的对少数派的保护,并使得帝国体制有些僵化,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是可笑的,似乎是吹毛求疵,即便是当时的一些启蒙思想家也曾取笑这种苛刻的比例代表制”*[德]彼得·克劳斯·哈特曼:《神圣罗马帝国文化史——帝国法、宗教和文化(1648-1806年)》,刘新利、陈晓春、赵杰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64-65页。,然而它意义重大,因为它从根本上消除了由于教派在帝国政治上的不平等而发生的矛盾和冲突,也使世俗领地之间的争夺减少到了最低的程度。
帝国通过上述政策,极大程度消除了在教派之间爆发以宗教为动因的冲突的可能性。因此,在1648年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德国境内罗马天主教、新教路德派和改革宗等教派虽然宗教分歧依旧,也没有完全避免宗教迫害,甚至小范围的宗教战争也偶有发生,但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该和约大致让德国各地呈现了“令人乐见”的宗教和平。第一,小邦国为帝国法所保护。有的小邦国以天主教为国教,虽然邻邦皆信奉新教,但也不太顾虑遭受侵犯,比如下萨克森的奥腾堡;而有的新教领地也很弱小,但也不惧怕来自四周是天主教邦国的骚扰,比如帝国修道院林道*Michael Kotulla,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vom Alten Reich bis Weimar (1495-1934),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Verlag, 2008. p.102.。第二,势力强大的邦国也受益于帝国法的保护。例如普法尔茨选侯国,领地广阔,国力强大,但是它的一些领地为其他教派的领地所包围,只是由于帝国法的保护,它才能够享受到安宁和平。第三,教派之间出现了新的宗教宽容。比如信奉改革宗的普法尔茨选帝侯国,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特别是颁布了宗教宽容敕令,以鼓励不同教派的人们前去发展;奥斯那布吕克主教管区规定两大教派轮流充任封侯主教,以保证天主教徒和路德新教徒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德]彼得·克劳斯·哈特曼:《神圣罗马帝国文化史——帝国法、宗教和文化(1648-1806年)》,刘新利、陈晓春、赵杰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67页。。第四,第一次出现了教派联合的尝试。1690年代的这次宗教和解由哲学家莱布尼茨、柏林新教改革宗布道师雅布隆斯基和荷兰天主教主教斯皮诺拉联合发起*Eda Sagarra. A Social History of Germany 1648-1914,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9. p.108.。这一前所未有的现象,预示了德国宗教和解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上述宗教和解局面的出现,除了得益于《威斯特法利亚和约》所确定的宗教政策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即该和约对战后德国的领地格局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调整和划分。这项极有意义的工作的总原则是恢复教俗领域的动产和不动产的产权,并以1624年为标准年,大致以新旧两大教派各自占领的领地为基础。事实上,该和约相当部分的条款内容均致力于此,可谓事无巨细。这不仅从根本上消除了世俗诸侯之间围绕领地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也使未来可能发生的宗教之争丧失了实际的物质基础,从而确保了近代早期德国社会的长治久安。
以宗教为动因的30年战争把新教与天主教之间在神学上的对立降至“荒谬”的程度*[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8卷),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34页。,而战后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则完全摆脱了宗教因素的影响,更没有触及宗教的所谓真理问题,甚至不仅终止了主教的权利,而且废除了宗教法庭*Arno Buschmann, Kaiser und Reich, Klassische Texte und Dokumente zur Verfassungsgeschichte des HI.Römischen Reiches Deutscher Natio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4. p.330.,彻底中断了罗马天主教皇与德国的联系。卸掉这一历史包袱,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固然丧失了“神圣”性,丧失了赖以存在的法理基础,但却由此进入了近代文明。该和约完全以世俗政治的原则解决了长久以来影响社会稳定的宗教问题,表现了帝国在政治上发展了日渐成熟的理性原则,这不仅对德国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实效,而且其确立的宗教自由平等思想更具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四
法律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早在13世纪孕育之初,帝国法就大量“继受”了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方法上都较为丰富的罗马法,而罗马法在帝国的深入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是以教会法为代价的,或者说是受益于教会法在帝国境内的重要性日渐衰微。这个去宗教化的漫长过程本质上就是帝国之契约实践、管理实践和司法实践等法律思想越来越理性化与科学化的过程*Heinz Duchhardt.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1495-1806. Stuttgart Berlin Kölin: W. Kohlhammer GmbH, 1991. p.15.。帝国法自马克西米连一世(1459—1519)继任德皇之后呈现出了一种特别的发展态势,一直持续到1654年帝国议会。在此期间,帝国法在秉承以往法律传统的基础上不断理性化,在宗教政策上越来越体现出政治的理性思维,即让宗教信仰合法化、自由化,直至中立化:从16世纪前半期帝国议会在调解宗教关系时零星表现出点点理性思维,到1555年帝国议会通过《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第一次尝试用理性思维来解决宗教关系,再到1648年帝国通过《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完全以世俗政治的理性原则而不是宗教原则来处理宗教关系。帝国法在日益理性的发展中趋向成熟。
帝国通过法律调节宗教关系,本质上是对世俗领地的调整。在1517—1648年间,德国世俗领地当局把宗教改革运动视为一个最大程度谋取政治利益的最佳时机:通过支持教改无偿接受教产从而增强势力扩张领地;而领地内的教会渴望借助领主之政治力量保持或者变为其唯一的权威从而建立和传播自己的学说。世俗领地当局及其教会之间是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Michael Kotulla,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vom Alten Reich bis Weimar (1495-1934),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Verlag, 2008. p.34.。路德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爆发神学教义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自背后的支持力量——世俗诸侯之间在领地上的争夺。帝国为维持社会秩序,制定了诸多调解宗教关系的法律,实际是在法律层面上对世俗领地进行调整和划分。尤其是1648年帝国法权秩序重新确立了世俗领地格局之后,德国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分界基本稳定了下来,双方大致处于一种微妙的利益均衡状态,任何一方也难以指望以损害另一方的方式来扩张领地了,德国由此进入了一个比较长久的宗教关系和睦、社会秩序稳定的时期。
从帝国法的角度看,1517—1648年间的德国几乎从来就没有稳定过。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帝国法从开始发展到日渐理性和完善。帝国政治在此过程中悄然进行了世俗化和宪政化。从宗教到政治,从道德到法律,说明了人类社会在自我重组和调节中不断走向成熟和文明。
The Imperial Law and the Religious Relations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GAO Zongyi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To mediate the religious disputes between Protestantism and Catholicism in Germany during the Reformation, the Holy Roman Empire enacted quite a few laws, especially the “Religious Peace of Augsburg” and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with an aim to deal with the disputation over the question of religion. These laws centered on legalization, liberalization and neutralization of religion. That the Empire mediated the religious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religious sects adjusted essentially the fight over the secular territories. During the course the Empire showed its rising rationality in politics and finally abandoned wholly the influences from the religious factors and safeguraded religious peace in Germany, revealing that the Empire was increasingly secularized and constitutionalized in politics in the early modern times.
early modern Germany; imperial law; “Religious Peace of Augsburg”;“Peace of Westphalia”
2013-03-02
高宗一(1974—),男,山东临沂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K516
A
1001-5973(2013)02-0084-08
责任编辑:时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