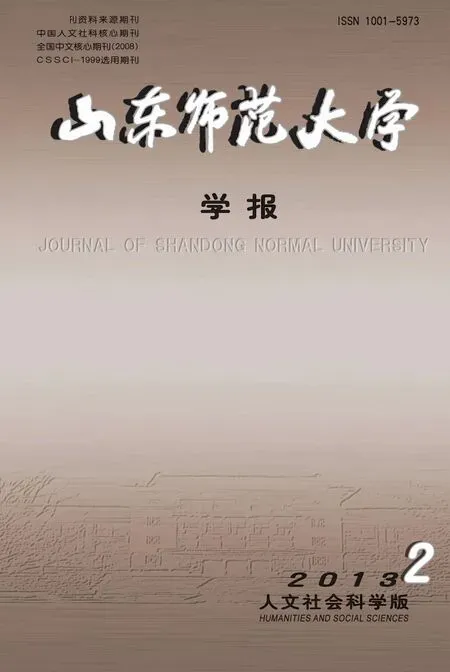试论中国古代王朝宗室的构造特征*①
刘 军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吉林长春,130012)
古汉语中的“宗室”一词有两层含义:广义泛指所有家族、宗族,如《晋书·张昌传》:“(王)伛、(吕)蕤密将宗室北奔汝南,投豫州刺史刘乔。”《魏书·卫操传》:“始祖崩后,(卫操)与从子雄及其宗室乡亲姬澹等十数人,同来归国。”这里说的都是普通士人之族;狭义专称皇帝或君主的同族,如《史记·商君列传》:“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魏书·孝明帝纪》:“(孝明帝)宴太祖以来宗室年十五以上于显阳殿,申家人之礼。”皇族概念层面的宗室独享天潢贵胄的声威,既是头等高门,又是特权阶级,其家国关系至为紧密,因此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专制皇权的附属物,宗室是揭示东方封建主义和中华帝国现象的锁钥,也是探析古代王朝政局走势和社会发展的切片。有鉴于此,宗室群体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并已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不过,在研究的基础环节,即宗室的构造范围尚存继续深入探讨的余地。故笔者试列举几个典型王朝的宗室,就其结构特征加以概括总结。
中国历代王朝宗室的构造基本上是以理想状态的两周宗法为蓝本的。儒家经典文献《礼记·大传》有云:“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对此,张光直先生的大作《早期中国文明》精辟地阐释道:“政治上的相对地位取决于所谓的宗法制度,至少在名义上如此。周代宗法制的最主要特征是,每一代的长子构成世系与政治权威传承的主干,以次诸子则另立门户,建立新的次一级权威。距离主干越远,政治权威也就越弱。”②转引自[美]贾志扬:《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看似玄妙的宗法制原则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嫡长子序列无限传承,别子与之相隔五世便脱离王族沦为庶民,即所谓的“五世而斩”。换言之,周王室仅限五世以内的近属。
汉朝是中国古代宗室制度演变的里程碑,其宗室族群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众所周知,汉高祖刘邦出身布衣,最初的汉室宗亲就是由他的平民家庭转换而来。其成员范围相当狭窄,具体包括本人及长兄刘伯、次兄刘仲、弟楚王刘交、从父兄荆王刘贾、从祖昆弟燕王刘泽六房。《汉书·高帝纪下》载高祖界定宗室为“九族”,实则是对当时普遍存在的父兄妻子构成的个体家庭的笼统称谓,并非是真的九世③杜正胜:《传统家族试论》,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家族与社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 0 0 5年,第6 0页。张学正:《甘谷汉简考释》,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7页。。后来随着儒家传统伦理的强化和家族规模的扩大,宗室族群也日渐膨胀。《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五年(5)正月诏书:“朕以皇帝幼年,且统国政,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顷、楚元之后,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虽有王侯之属,莫能相纠,或陷入刑罪,教训不至之咎也。……其为宗室自太上皇以来族亲,各以世氏,郡国置宗师以纠之,致教训焉。”这说明,至迟于西汉晚期,宗室已突破家庭或家族的局限,开始向尊奉同祖、边际模糊的广义宗族体靠拢,否则决不会有10万之巨。需要强调的是,宗室这种信马由缰式的繁衍不受服纪关系递变的影响。以东汉光武帝刘秀为例,他所在的南阳一房祖出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发,至刘秀已传五代,照理他亲尽而斩,但朝廷仍视之为宗室。当地人李通曾任本郡宗卿师,专门监管刘秀一干南阳支庶,可谓有力的旁证①《后汉书·李通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73页。。又汉末割据巴蜀的刘焉,祖出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东汉章帝时举家迁徙江夏竟陵,此地汉室苗裔甚多,传至刘焉世系已然不详,但他却能“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②《三国志·蜀志·刘焉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65页。。足见,汉代宗室伴随中古宗族组织的成长而扩张,服纪不再是判断宗室身份的标准。
但服属远近在宗室内部并非毫无意义,它起码还是辨别亲疏,配置利益的尺度。《汉书·宣帝纪》载地节元年(前69)六月诏书:“惟念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若有贤材,改行劝善,其复属,使得自新。”《哀帝纪》载哀帝即位,“赐宗室王子有属者马各一驷”③杜正胜:《传统家族试论》,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家族与社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 0 0 5年,第6 0页。张学正:《甘谷汉简考释》,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7页。。可见,出服疏宗亦在宗室之列,只是待遇不及近属而已。实际上,这种现象前人早有明断,《朱子语类·论财》:“如汉法:宗室惟天子之子,则裂土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则嫡者一人继王,庶子则皆封侯;侯惟嫡子继位,而其诸子则皆无封。故数世之后,皆与庶人无异,其势无以自给,则不免躬农亩之事,如光武少年自贩米,是也。”在朱熹看来,汉代距上古不远,故近宗、疏族的分野还是宗法制循环运作的结果。总之,汉代宗室的法定范围是高祖之父刘太公及个别旁支的全体后裔,五服的宗旨在于区分亲疏远近,而非辨族的基准。西汉的另类之处在于,外戚虽是异姓,但作为骨肉同胞亦被纳入宗室,此举在东汉时遭到摒弃④牟润孙:《汉初公主及外戚在帝室中之地位试释》,《注史斋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9页。。
晋朝宗室制度具有承上启下的转折意义,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两晋皇族出自河内温县大族司马氏,宣帝司马懿兄弟8人声著当世,在士林中享有“八达”美誉,此“八达”的所有子孙都是晋朝宗室。与汉朝相仿,晋朝同样不以服纪作为宗室的断限。典型事例是东晋末年归降北魏的司马楚之。史载,司马楚之是司马懿之弟太常司马馗的八世孙,“时年十七,送父丧还丹杨。值刘裕诛夷司马戚属,叔父宣期、兄贞之并为所杀。楚之乃亡匿诸沙门中济江”⑤《魏书·司马楚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54页。。司马楚之与东晋帝室血脉悬远,可是身为疏族的他却仍被当作宗室追杀。据此可知,两晋宗室同样是突破服纪的开放式宗族结构,这与中古北方士族营造超大族群的传统不无关联。
北朝是中古制度传承的枢纽,拓跋魏立足本民族的习俗,又借鉴汉晋典章故事,创立了极具特色的宗室制度。应该说,北魏前期宗室更多地保留了草原时代的氏族“直勤”体制,拓跋子孙通常冠以“直勤”名号,标志着特定血缘群体内对等君位继承权的拥有⑥罗新:《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直勤”就相当于王朝阶段的宗室,然而其上限应在“七分国人”的献帝邻,而非《魏书·宗室列传》标定的始祖神元帝力微⑦刘军:《论鲜卑拓跋氏族群结构的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直勤关系下,拓跋子弟的身份差别不甚明显,由此引发的夺位纷争始终困扰着统治者。为巩固专制皇权,加速宗室政治角色的转变,崇尚汉化的孝文帝于太和十七年(492)前后采用华夏的丧礼五服对宗室进行系统的家族化改造。与汉族王朝不同,孝文帝充分发挥五服辨族之功效,将宗室的范围严格限定在“当世五属”或“四庙子孙”之内。也就是说,只有当朝皇帝的服内亲属才算宗室,出服疏宗尽皆除籍。在界定宗室问题上如此惟五服是从,孝文帝堪称古今第一人。其意图在于借助礼制的载体向宗室灌输尊卑有序、长幼有别的纲常名教①康乐:《孝道与北魏政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4本第1分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同时最大限度地压缩宗室规模,相应地削减利益配置量。后来,孝文帝的心腹近臣左卫将军元遥道出事件原委:“先皇所以变兹事条,为此别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于吴蜀,经始之费,虑深在初,割减之起,暂出当时也。”②《魏书·景穆十二王上·京兆王子推传附遥传》,第446页。此观点值得学界重视。不过,若对太和年间的宗室族制改革进行连续跟踪,会发现北魏末叶限于主客观因素未能遵循孝文帝的既定方针,宗室的范围依旧是始祖神元帝力微的全体后裔③刘军:《论北魏孝文帝的宗室辨族》,《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而移植过来的服纪关系同样只能充当分配权利的标尺,辨族工程被无限期搁置④刘军:《北魏宗室的家族制建构与利益分配格局的演变》,《西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中古王朝以唐代宗室体系最为庞杂,变更也最频繁。李唐皇室标榜门第为陇西成纪李氏,自称西凉国主武昭王李暠的子孙⑤据 陈寅恪先生考证,李唐先世实为赵郡李氏之破落户或假冒牌,陇西李氏乃其伪托。参见其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94页。。唐高祖李渊尊其祖父西魏大将李虎的庙号为太祖,规定太祖后裔为宗室的骨架。此外,唐朝沿袭北周旧制,把罗艺、徐世勣、杜伏威、高开道、胡大恩等赐姓功臣划入宗室⑥王溥:《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29页。。更为夸张的是,唐明皇痴迷道教,竟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宣布道士、女冠并隶宗正寺⑦王溥:《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29页。。当然,这种基于宗教信仰的扩编只是皇帝一时兴起,并未形成常制。单就李氏自身而言,其上、下边界也时常变动。据王溥《唐会要》“宗正寺”条所载,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吸纳李暠之孙李宝以降绛郡、姑臧、敦煌、武阳四个房支为宗室;天宝五年(746),敕九庙子孙晋升宗亲,且永为常式。我们知道,天子宗庙有七,宗室亦称七庙子孙,此所谓“九庙”,或许是将宗室的上限推至李虎的祖父李熙,这样宗室族群便出现了严重冒顶的现象。关于唐代宗室的下限,《新唐书·百官志》有载:“(宗室属籍)凡亲有五等,先定于司封:一曰皇帝周亲、皇后父母,视三品;二曰皇帝大功亲、小功尊属,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周亲,视四品;三曰皇帝小功亲、缌麻尊属,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大功亲,视五品;四曰皇帝缌麻亲、袒免尊属,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小功亲;五曰皇帝袒免亲,太皇太后小功卑属,皇太后、皇后缌麻亲,视六品。……降而过五等者不为亲。”意即只有皇帝的五服亲属才是宗室,易言之,宗室有明确的服纪轮廓。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定义宗室的服纪框架被轻易打破。唐高宗永徽二年(651),皇族诞生了第一批出服疏宗,宗正卿李博文回答皇帝质询时说:“以属疏降尽,故除,总三百余人。”也就是将其革除宗籍,剔除出宗室,高宗最终“追远之感,实切于怀,诸亲服属虽疏,理不可降,并宜依旧编入属籍。”⑧王溥:《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29页。也就是默认了出服者在宗室中的存在。至唐德宗建中元年(780),“赦文入庙子孙非五等亲,任用如始封王荫,不限年代。补斋郎三卫,至简选日,量文武稍优于处分”⑨王溥:《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30页。。此诏颠覆了“天子族亲五等”的拘束,使宗室下限彻底洞开。于是,李唐宗室也变成了漫无边际的开放式结构。验之以个案,《新唐书·宗室列传》记录世祖李昞第四子蜀王李湛世系一直到七世孙李戡,他生计无着,“大寒,掇薪自炙”,处境与庶民无异。足证出服与否不再是甄别宗室身份的标准。总括以上,唐代宗室以帝系为轴线不断扩张,其上限跨越太祖、下限突破五服,所谓“宗亲五等”从一开始便失去了辨族的意义。
宋代宗室的资料浩若烟海,除二十六卷《宋史·宗室世系表》堪作基本史料外,还有现存二十二卷的《宗藩庆系录》、三十卷《仙源类谱》残篇以及大量的名人文集。除非对这些文献进行周密、细致的梳理,否则不应对宋代宗室的复杂情况妄加揣测。近年,美国汉学家贾志扬先生的名著《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在大陆翻译出版,使我们对宋代宗室的构造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本节的内容全部引自该书,特此说明。宋代玉牒明确规定,以太祖赵匡胤的父亲宣祖赵弘殷的后裔作为宗室的范围,具体包括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匡义和魏王赵匡美三个分支。贾氏依据《太祖皇帝玉牒大训》的记载,推断早在北宋建国伊始,朝廷就将宗室定位于绵延不绝、无限拓展的宗族层面上,因此无论千秋百代、有无服属,赵氏子孙均在大宋宗室之列。该书的第四章“重新定位宗室”提到,11世纪晚期,宗室人口激增,出服疏宗首次出现,背负巨大的财政负担,酿成“谱系危机”。宗正寺力主作革籍处理,但礼部秉承皇帝意旨予以驳回,坚持把众多的服外亲录入玉牒,只是不再享受赐名授官的特权而已。他认为此举“实际上破坏了按服纪确认家族的惯例,更倾向于建立一种谱系边际开放的宗族结构”。
明清继续沿用开放式宗室结构,宗室成员的身份丝毫不受服纪的限制。特点鲜明的是清宗室,它根据先祖的差异分为宗室和觉罗两个部分,以太祖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的子孙为本支,称为宗室;以其叔伯兄弟,即祖父觉昌安的其他子孙为旁系,称为觉罗。虽同属皇族,但宗室与觉罗的待遇大相径庭。为显示差别,宗室腰束黄带,注黄册;觉罗腰束红带,注红册。宗室嫡子可受封,无封者称闲散宗室,18岁时统交宗人府汇题,授四品顶戴。雍正、乾隆年间,宗室人口剧增,统治者采取集中迁徙关外的办法予以缓解,但从未利用服纪加以断限裁撤。至辛亥革命前夕,宗室累积达3万多口,且普遍缺少谋生手段,穷困潦倒,只得由王公贵族出面成立宗族生计维持会,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①秦国经:《明清档案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397页。。
宗室是政治权力和宗法关系融汇产生的家族变体,它既不同于嫡长子继承分封的宗法体系,又与围绕丧礼五服展开的家族制迥然有异,惟有在皇权的映衬下方能显现其特性。通过对周、汉、晋、北魏、北周、唐、宋和清宗室的类型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归纳出中国古代王朝宗室结构的一般特征:
首先,历朝宗室的构造体现在宗正卿掌管的皇室谱籍当中,玉牒的修撰原则客观反映了国家的宗室政策和时人的家族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剖析宗室又是古代家族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屡遭毁损,能够完整保存至今的玉牒资料少之又少,迫使我们采取变通的办法,而与玉牒最为接近的替代品无疑是历代正史中的“宗室列传”②以《魏书·宗室列传》的编撰为例,据《北齐书·魏收传》,魏收修“宗室列传”参考了北魏济阴王元晖业所著三十卷本的《辨宗室录》。元晖业乃宗室元老,历司空、太尉、领中书监、录尚书事等要职,必有机会调阅宗正寺收藏的皇族玉牒。《魏书·宗室列传》既以《辨宗室录》为创作媒介,可视为北魏玉牒的翻版。。所以,如何提炼“宗室列传”里的结构信息便成为突破的关键,也是本文论证的方法论基础。
其次,宗室族群的形成以敬奉某位共同祖先为前提,是为“尊祖”。这样,族人便可通过谱牒修撰和祭祖仪式实现身份认同和意志凝聚。必须澄清的是,开国皇帝尽管开创一朝法统,却不能以先祖自居,宗室的上限通常选择在本族历史上做过巨大贡献、享有崇高地位的英雄人物,至少也应是开国君主的父祖,以昭示皇族血脉的连续性。上述事例中,北魏和李唐宗室远尊先辈,其他王朝则近奉父祖。另外,等同于宗室的契丹横帐除太祖耶律阿保机本支外,还有两个伯父、五个兄弟的族属构成的三父房③刘浦江:《辽朝“横帐”考——兼论契丹部族制度》,《北大史学》(第八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元的黄金氏族也不限于铁木真一系,而是包含其父也速该的所有子孙④转引自罗新:《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同祖的全体后裔都可著录玉牒、参与太庙祭祀,此乃取得宗室资格的基本条件。
再次,宗室族群以帝系为轴线,是为“敬宗”。成员的家族地位取决于距此轴线的远近。这里牵扯到的礼学难题是北魏后期发生的“当世五属”与“历代有服”之辩。孝文帝等激进的改革者仰慕南朝时尚新风,以“当世五属”或“四庙子孙”,即在位皇帝的五服范围圈定宗室,于是便有了疏宗元遥、元继革籍事件。而稳健的礼学家则固守“历代有服”或“七庙子孙”的宽泛标准,其依据是魏律的条文:“议亲者,非唯当世之属亲,历谓先帝之五世。”实际上,两派争执的焦点是宗室族群究竟保持在广义还是狭义层面。从历史上看,更多的王朝倾向于前者,也就是覆盖历代皇帝的全部亲眷,若以某位皇帝为基点,则“天子属籍不过十数人而已”,与“广帝宗,重磐石”的初衷背道而驰①《魏书·景穆十二王上·京兆王子推传附遥传》,第446页。。所以说,宗室在理论上是由环绕整个帝系的层层服纪圈串联而成的。
最后,宗室在“收族”实践中通常不受服属的制约。前面的事例表明,五服制仅在北魏孝文帝和李唐初年被用来鉴定宗室身份,更多时候只是衡量族内关系、区别设置待遇的工具而已。宗室既定义为边际开放的宗族体,入族就不应有服纪的障碍。简而言之,只要是同祖后裔,都能获得宗室资格。事实上,依五服辨族绝非轻而易举,日本学者谷川道雄敏锐地指出:“宗族自体无法根据大宗制、小宗制的礼制来严格地对其制定出体系,虽说丧服制是可以较为严格遵守的,五服范围是可以由小宗取得一致的,但是其他繁多的宗族关系也这样进行约束则是难以想象的。”②[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30页。北魏孝文帝强行辨族,结果“复各为例,令事事舛驳”③《魏书·礼志二》,第2764页。,又“七庙之孙,并讼其切,陈诉之案,盈于省曹”④《魏书·张普惠传》,第1743页。,导致纠纷不断。唐初也很快废除了相关条款,准许出服疏族保留宗籍。可见,上古宗法“五世而斩”的原则对后世宗室根本行不通,宗室的膨胀是无法有效遏制的。
当然,宗室特殊的家族构造不是凭空臆想的,它有其现实的原型和需求。我们认为,宗室组织的演变与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的发展紧密相伴,不会脱离实际的家族理念和固有形态而孤立存在。汉初的家族仅限五服以内的近属,故高祖刘邦把汉室宗亲维持在“九族”的规模。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奠定,民间聚族现象与日俱增,宗室相应地放宽了入族标准。魏晋以降,远尊同祖、超越五服的宗族方兴未艾,宗室宗族化的迹象也渐趋明朗。北魏孝文帝的辨族便因与盛行北方的宗族传统相悖而终遭废弃。唐宋明清基本沿袭中古成型的宗室架构,并根据所处时代的族制特点加以整饬。历代王朝致力打造宗室为超级族群还有深刻的政治用意。任何封建家族统治都依赖于庞大而稳固的亲族,宗室势力人丁兴旺、坚如磐石,自然可以达到藩屏皇室、家国永固的目的。这或许就是中华帝国长期存在、东方专制主义死而不僵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