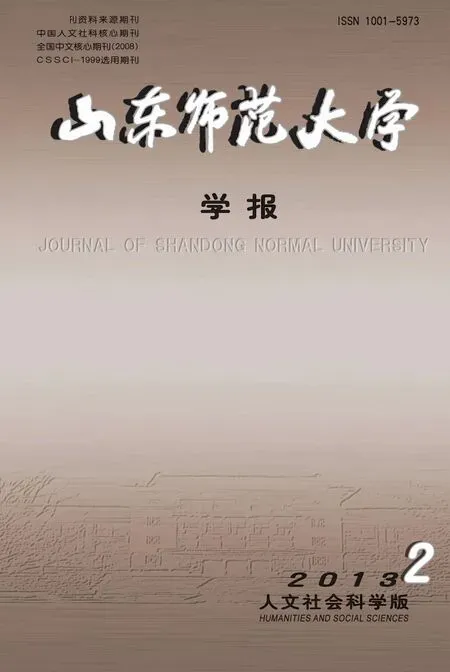作为道德教育理论框架的自由主义:前景与问题*
德怀特·鲍伊德
( 多伦多大学 安大略教育研究学院,加拿大 多伦多 )
作为道德教育理论框架的自由主义:前景与问题*
德怀特·鲍伊德
( 多伦多大学 安大略教育研究学院,加拿大 多伦多 )
良好的道德教育是有一个强有力的哲学框架来支撑的。北美的道德教育大都立足于自由主义哲学传统之上。评判这种教育在道德上的合法性,就要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这个哲学传统:首先对自由主义进行综述,然后对这一框架给予评估,并为构建规范框架提出建议,以期能为道德教育带来某种改变。
道德教育;自由主义;规范框架
引言
作为一位深信道德教育意义重大的哲学家,我认为良好的道德教育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哲学框架来支撑。没有哲学框架,道德教育的发展将会步履维艰,接受道德教育的学生也会觉得这种教育肤浅而愚蠢*我认为在目前流行于北美的“人格教育”运动中的许多做法上这种批判也完全适用。。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始终牢记,道德教育在本质上是招险棋。哲学框架若有严重缺陷,道德教育就会严重危及学生。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北美的道德教育大都立足于自由主义哲学传统之上。如果我们要来评判一下这种教育在道德上的合法性的话,我们就要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一下这个哲学传统。自由主义的优劣之处是什么——它有何前景,又有何问题?对道德教育来说,用自由主义来做理论框架是否合适?反观过去37年里我的工作*可参见如下两篇论文:“An Unabashedly Non-Arm’s-Length Account of My Lifelong Affair with Philosophy.” Paideusis. Vol. 19, no. 2, 2010, pp. 32-41. (只在网上发表的论文); 和 “Learning to Leave Liberalism…and Live with Complicity, Conundrum, and Moral Chagrin.”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Vol. 40, no. 3, September 2011, pp. 43-51.,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那就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
在本文中,我将对这种矛盾心态进行探究。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将首先对我所理解的自由主义进行综述。这一综述将会包括我所理解的可作自由主义规范框架基础的种种非道德假设,然后指出组成这一框架的最基本的道德和政治要素。之后,我将对这一框架进行评估。我将先阐明我愿意支持的自由主义的长处;在本文的后半部分,我会着重探讨其非常严重的一个缺点,这也是让我非常担心的一个缺点。这个缺点与一种全球皆有且极其有害的人际关系相关联,代表了一种自由主义无法充分意识到的问题。在结论中我将为构建规范框架提出建议,希望这一框架能在道德教育中带来某种改变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摇摆不定”的难题,纯属我自己的难题。因此,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是站在我所坚定支持的某一特定流派的立场上来表态的,这一流派是存在于自由主义之内的众多观点之一。它往往被贴上“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 theory)的标签,其富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包括约翰·洛克(John Locke)、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以及近代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罗尔斯在流派上的发展对我影响极深,因为他是我读博士期间的导师之一。
自由主义理论框架中非道德层面的假设
要探知作为道德教育框架的自由主义的优劣,我们似乎只需对这一理论的道德和政治内容加以审视就够了。不过,我认为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这一框架既包括非道德要素,也包括规范要素,这些要素共同作用才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两者对道德教育皆有影响。此外,我认为如果不首先揭示道德教育中包括的非道德层面理论的话,就不可能对其规范要素进行充分理解和评估。因此,我要首先谈谈这一点,指出自由主义五种非道德层面的假设。
1.一个见解:个体是所有人际关系中的社会构成单位
我们必须要把自由主义对个体观念进行概念化的特殊方式视作对这一理论进行充分阐释的初步假设。尽量简洁地说,我认为有一个特殊社会实体构成了自由主义中几乎其他一切内容的概念核心。这个实体有三大构成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个体这种概念将人体现为意识和经验在本体论上唯一的中心。我说的“本体论上的唯一”,指的是在这个理想化的概念层次上,没有两人完全相同,没有两人必须有联系,而且没有人从来就是一群人中的一员。“每个人都是唯一的”不只是个人人皆知的自由说法,它也代表着自由主义认识中的本体论现实。第二个特点是,所有的这种实体与所有其他实体呈对等性定位。这种对等性将每个人都置于同一个本体论层面,从原则上讲,在这个平等竞争的层面上,每个人都有可能会充分认识和理解他人。第三个特点是这样一种假设,那就是与所有其他个体相对应,所有个体的这个对等位置在政治上是中立的。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存在于各种通过社会规范、期望和规则以及国家的一切法规和制度体现出来的权力关系之外。
2.一个认可:个体之间在追求成功人生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冲突
自由主义将上述这个意义上的个体视作构建社会世界时的意义决策者和目标追求者。第一个方面是指所有这些个体会寻求以自己的方式阐释他们的人生,成功人生在其意识之内是有意义的。在他们的人生中有些事情会比别的事情更重要,他们认为这些重要性强的事情会让人生更有价值。第二个方面是指这些个体也会积极地去追求这些对他们来说非常有意义的目标。从一定程度上讲,这种目标及其给予这些个体的意义将会使他们有所成就。
但是人们相信,人生会有众多至于无限的意义、规划和目标,这会使整个情况变得错综复杂。此外,个体之间的关系可能会——也必定会——产生紧张,这样一来,追求一种目标就不只局限于一种目标或更多程度上大同小异的其他目标。更重要的是,人们可能还会相信,这样的个体在社会交往时,差异和冲突不可避免。我认为对这一思想最有说服力的阐述来自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他不但指出了人类目的的多元化构想,而且指出了我这里所说的冲突的不可避免性。
我相信,如果人生目标众多,而原则上并非所有目标都可以和谐共存,那么无论是从个人角度看还是从社会角度看,人生之中的冲突——以及悲剧——都永远不会得以根除。*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68-169.
3.一个认识:组织社会关系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对这种冲突的管控
自由主义理论谈到此处,其务实色彩就清楚地展现出来:如果冲突不可避免,那么如何去应对就成为关键。社会关系如何构建才能对冲突进行管理呢?我认为,下一步要制定自由主义的规范框架,其策动力就直接源自它对这个问题的正视以及有效应对。将自由主义视作乌托邦式的空想是一种严重的归类错误。恰恰相反,自由主义必然会认为任何形式的乌托邦式理论均是以内在的错误观念为基础的,是对社会关系的错误理解方式,而这种理解方式是很危险的。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必定会对有价值的人生目标何在这一难题得出一个不成熟的结论。与此相反,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一目标应当是通过对冲突的管控来思考人际关系,使人们能在这个充满艰险的世界中得到能够为己所用的东西。
4.一个信念:通过个体之间的合作以及自由选择的集体合作来改善关系, 在此过程中诉诸理性是有效的
为了完成这种务实的目标,自由主义对于个体的见解有着另外一个特色,那就是人们在自我改善、进行社会管控时有着诉诸理性的能力。自由主义对个体概念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对等定位这一理念进行了扩充,其主要方法之一就是假定所有个体在区分和追求其目标的过程中都有诉诸理性的能力。这可以通过个体和集体来完成。在个体层面,人们会学习对相互竞争的预期目标进行评估和比较,寻求实现目标最有效的方式。不过,也有些目标是难以通过个体行为来完成的。对于这些目标,理性会提示人们通过集体努力来完成。因此,与志同道合者共事来达成目标这一理性选择也是自由主义的内容。但需铭记在心的一大要点是,在自由主义之中,个体选择会将、也一定能够将这种集体理念包括在内。
5.另一个信念:可能会存在一种中立的社会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人们可以作出最佳理性选择
第五个假设是以前四个假设为基础的,概括了改良型理性的正确使用。这个假设有两个环环相扣的部分。第一部分包括这么一种信念,那就是相信从一个中立的社会位置我们可以对改进冲突管控的方法作出道德和政治上的判断,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认识论上是可取的。换句话说,如果某人能够为了作出一个真正客观的判断而超越他所处的社会位置,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作判断者的实际社会位置无关紧要。第二部分,以这种假设的中立性和客观性为前提,我们也可以假设使这些判断普遍化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事实上,这并不是说某些道德信念在任何文化中都很普遍。相反,它所讲的是什么理由能让道德判断站得住脚。也就是说,作出判断者必须愿意坚持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如果任何人身处同一种境地,他们也应该作出同样的评判。总之,这两部分合起来所带来的影响包括,从原则上讲,无论人与人有何不同,任何人都应该能够为所有其他人代言。
自由主义规范框架的基本组成部分
有了对自由主义非道德层面的假设这一基础的认识,我们就可以对其规范框架的基本组成部分加以概述了。由于时间有限,我会只讲几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我认为有个根本的动机或目的将这几个方面联系在了一起,这个动机或目的出自我刚刚指出的那几个非道德层面的假设。我认为一个有目的的动机使这几个基本组成部分结合起来,这个动机所根据的假设即组织社会关系的首要目标是对不可避免的冲突的管控。这个动机号令人类想方设法通过人际关系将对他人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要首先指出形成于道德领域的组成部分,然后延伸至政治领域,但这个动机一直会是我优先关注的对象。
(一)道德领域的组成部分
1.“善”与“正当” 这两个概念之间的本质区别
自由主义在道德层面的第一个规范框架是直接建立在上述非道德层面的基础之上的。将伤害降到最低的其他要素都基于一个重要的概念上的区别,即“善”(good)这个概念与 “正”(right)这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作为意义决策者和目标追求者的个体在自问“我的人生中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终极目标?”的时候,他们会用“善”这个概念。相反,个体会意识到别人对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于是他们在问“在涉及他人的时候我应当怎么办?” 这个问题的时候会用“正”这个概念。对“善”的判断被认为是个体可以决定的事情,因为这些判断在本质上都是主观的、多元的。但是,在求“善”之不同观点的过程中个体之间就会产生互动,传统上人们会使用“正”这一概念来管控这种互动。如何表达和使用 “正” 这个概念决定着社会合作的状态。
大家可能觉得我在玩文字游戏,这种区别有那么重要吗?*尽管对大多数哲学研究者来说这种区别实属老生常谈,但不搞哲学的人往往会犯糊涂。此外,当今北美盛行的人格教育运动中公认的学术专家常常模糊这一区别。(见Howard, Berkowitz, and Schaeffer, “Politics of Character Education,” Educational Policy, Vol 18, no. 1, 2004, pp. 188-215)。然而,要正确理解自由主义,这种区别的确非常重要。为此,请允许我引述孔子的哲言来打消各位的疑虑: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转引自Louis Goldman, “The Logic of Euphemisms and the Language of Education,” Educational Theory, Vol. 26, no. 2, 1976, p. 186.
虽然我已将这个区别定性为“概念上的”区别,但它依然有道德功能,即将“正”的原则从其他类型的规范性问题中分离出来并强调了它的重要作用。总之,“正”的原则在将伤害降到最低程度上所起的作用极其显著。“善”的原则可以从单个个体的角度来审视,但“正”的原则却不行。相反,这种原则设立了一种前提条件,那就是个体要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来看,这些原则的合法性和长处在于它们将不同个体间各有不同的多重视角考虑在内。更重要的是,这些原则可以降低一些潜在的伤害,这些伤害源自个体之间的冲突,而正是因为个体之间对“善”有着不同而相互竞争的观念冲突才会产生。
2.平等的核心作用
作为“正义”这个概念的体现,平等原则是构成自由主义道德框架的第二大基本组成部分。戈德堡(Goldberg)是这样清晰而有力地来阐述这个核心的:
……所有自由主义者都一致同意的平等主义核心包括了对一个共同道德地位的承认,无论个体差异如何。从自由主义角度来看,个体之间的明显差异不会对他们的道德价值造成影响……*David Theo Goldberg, Racist Culture: Philosophy and the Politics of Meaning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3), p.5.
我想说的是,这个对平等核心的承诺起着这样的作用,它提升了自由主义对独立个体的初始理念,将其从单纯的本体论概念上升到了人际道德层面。这一点是通过前面提到的三个特点来实现的,但我所假设的所有个体的对等定位这个规范表达所起的作用更为显著。坦率地说,通过这一实体来认可他人只能通过平等的道德地位这个与关系相关的角度才能实现。平等原则旨在防范最恶劣的那种伤害,这种伤害是一方不将另一方当作完全的人来看所造成的。
3.尊重他人的有效作用
但是,为了认可他人平等的道德地位,个体需要做些什么呢?具体实施这一认可的基本组成部分可在“正当”的原则中找到,“正”的原则在此可以解释为“尊重他人”。这一原则可以视作平等个体之间如何在道德上管控其互动的一个行得通的观点,对它的解释至少可以追溯到康德和他对其所谓“绝对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阐述。我想提醒大家的是,绝对律令的一种形式是这样的:“不论对待自己还是他人的人性,绝对不能只当作为了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同时总是将其当作目的。”总之,要尽量将对他人的伤害降到最低,每个人都应当总要认可他人,承认他人也是其自我经验中同样唯一的对象。显示这种尊重有两个彼此相关的方法:一是对待他人如同他人的利益和目的也是自己的一样;二是在制定道德规范的时候不要只用于他人而不用于自己。
(二)政治领域的组成部分
我认为,上述三点构成了自由主义规范框架中最基本的道德领域的组成部分。但是,要全方位地理解这个规范框架,必须要了解政治领域的组成部分。我这里所讲的“政治”是指社会中组织管理大量个体之间关系的制度。要了解政治层面上的自由主义框架,将它与刚刚概述过的道德领域的基本组成部分联系起来看或许是个好主意。
先来谈谈道德领域组成部分的三个方面是如何与政治相关的。谈的时候我会分别阐述。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样做纯属是为了表述的方便。事实上,这些方面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共同作用才能真正体现这个框架的本质。是什么使这个有机整体不至于分裂,又是什么将其激活,这是宪政民主体制中一个公民应该持有的观念。重要的是,“好公民”的理念并不等同于“好人”的理念。公民身份是人们可以承担的一种角色,人们也可以承担其他各种角色,如父母和教师等。正是承担这一角色的个体之间的关系才使政治制度组织起来。
1.“善”/“正当”之别在政治层面的应用
约翰·罗尔斯在其首部著作一开始就极有说服力地指出:“恰如真理是思想体系中的第一美德一样,正义是社会制度中的第一美德…… 人人享有建立在正义之上的不容侵犯的权利,就连整个社会的福利在重要性上也无法与之相比。”*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3.这个引言的第二句话清楚地表明,这种对正义的强调直接立于“善”和“正”的概念区分之上。它们不仅是不同的规范问题,而且其重要性也有所不同。可以说,“正”要比“善”更有“地位”。*Rawls, Theory, p 31.公民对“善”会有不同的有时是不相容的观念,他们会通过社会合作来寻求那些让他们满意的东西。罗尔斯认为,正义作为“正”的一个原则,“可以解决社会合作中占得上风之后产生的权利冲突……”*Rawls, Theory, p. 16.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罗尔斯在后期作品中将这一区别的实质延伸至产生于世界观层面的不可避免的冲突上,他将这些世界观称为“完备学说”(comprehensive doctrines),这些学说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有着真正的文化多元性。从本质上讲,他的观点试图确定一个“独立”(free standing)的政治自由主义,并期望这种政治自由主义可以实现他所说的“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也就是说,它可以从任何合乎情理的完备学说的角度为人接受,即使为人接受的原因本身部分源自该完备学说。*他在其后期作品《政治自由主义》中指出了这样一个严重问题:“现代民主社会不仅具有一种完备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之多元化特征,而且具有一种互不相容然而却又合乎理性的诸完备性学说之多元化特征。”(p. xvi)因此,他开始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合乎理性但却相互对峙的诸完备性学说,怎样才可能共同生存并一致认可一立宪政体的政治观念?”(p.xviii)换言之,罗尔斯此言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一种有关正义的政治观念,从而不去回避某些公民持有的任何完备性学说。尽管我认为他并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我认为这种变化的本质一定会让他放弃其早期作品中含蓄指出的对于道德判断普遍化的假设。同时我也认为,他在试图指出“重叠共识”性质的时候保留了一个不太明显的版本。
2.道德平等的政治含义
道德地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的道德自由信念在政治领域有着特殊含义。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任何有关正义的合法理论都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所有公民都具有平等的政治地位。任何公民——或一群志同道合的公民——在正义面前都不应使用“善”的观念来取得特权。所有其他公民或许永远不会认为这种特殊待遇是公平的。另一个例子说的是宪政民主体制中“权力分离”这一重要概念。独立于立法和行政权之外的独立司法权在这里显得尤为相关。法律体系本应是依照正义组织起来的基本制度之一,全体公民应在法律面前有着平等的地位。不论你是谁,社会地位如何,是富人还是穷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道德层面的平等原则会将某些人不将他人视作完全的人这种伤害降到最低,而政治层面的平等——尤其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将会在最大程度上降低某些人不被当作完全的公民而造成的伤害。
3.尊重他人在政治层面的表述
尊重他人的原则使道德层面人人平等得以实施。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它在政治领域也为实现公民平等开辟了天地。例如,罗尔斯从未将其公民必须被平等相待的假设与这些公民可以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割裂开来。诚然,人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如果公民无法自由追求自己的人生的话,他们的平等就会是个较为空洞的概念。因此,罗尔斯有关正义的理论将自由置于明确的首要地位。他有关正义的“第一原则”是这么说的:“在整体平等基本自由的体制中,每个人拥有最大程度的平等权力,与相类似自由制度下的他人相等。”*Rawls, Theory, p. 302.
在其理论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罗尔斯还设想将其理论应用于宪政民主体制中。正是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正式的政治理论与宪政民主体制的实际结构产生了互动。也就是说,一个宪政民主体制在其最高级别的法律制度中将罗尔斯有关正义的第一原则中对于自由原则的具体表述以法律的形式保护起来。这些表述以各种具体自由的形式受到宪法保护,收录在俗称的“人权法案”中,如“集会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等。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受法律保护的自由有着非凡的规范意义。原因有三:(1)它们建构起非常具体的平台,在此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自由来采取他们认为合适的行动;(2)在公民之间产生冲突的情况下,有人就会提出其他类型的辩护理由,由于有宪法保障,这些自由在法律上会凌驾于其他类型的辩护理由之上;(3)随着现代社会的规模和复杂程度日益增大,国家的巨大权力可能会侵犯其公民的自由,某种人权法案的出台会力求将这种伤害降到最低程度,这一点或许更为重要。
作为道德教育理论框架的自由主义之评价:前景与问题
如果以自由主义来作道德教育的框架,我会怎么看?我会赞同吗?我的答案非常简短,既“会”也“不会”。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我的确很想指出其前景可观的长处。也就是说,它的确提供了一些我不愿放弃的指导。不过,我也想以消极的态度专注于一个主要问题,我认为任何道德教育方案都应解决这个问题,但自由主义并不会提供很好的指导。因此,我最终认为这些长处在很大程度上必然会有局限性。
先说一说“会”这个回答。 这个框架在我眼中有何长处呢?首先,三个道德领域的基本组成部分——“善”与“正当”的区分、所有人平等的道德地位以及实施这种平等的对他人的尊重——对我来说似乎比较合理。对我来说,它们在决定道德教育工作的性质时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相对来说又没有争议。将其合起来考虑,人们可能会认为它们在使人际关系概念化的过程中有着两个主要目的:(1)给予个体的唯一性以适当的道德意义;(2)提高这些个体之间互动的概念化过程中的互惠程度,以便保持其唯一性。作为道德教育理论框架的自由主义在寻求尽量减少社会关系中的潜在伤害过程中,它们代表着最基础的方式。因此,我认为它们是学生成为有德之人要理解和遵从的底线。
对于这三个道德领域的组成部分在政治领域的表现,我想提出一个更强有力的理由。作出这一评估的原因在于,政府的权力在各个层面,特别是在国家这个层面,永远都不应该被低估。它可能也时常会伤害本国的公民。比方说,我相信布什总统在应对911恐怖袭击时对自己行政权的使用——以及国会对其领导能力的盲从——确凿无疑地严重侵害了美国公民的自由,这些自由即使能够恢复,也要花很多年时间。
总之,我认为自由主义的重要优势之一是它会提供一种指导,让人们去思考政府权力是如何严重伤及公民的,要使用何种手段来将伤害降到最低程度。我在此特指的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观念以及受人权法案保护的种种自由。这个长处我一定会赞同。因此,我主张在为了下一代成为公民者将道德教育概念化的过程中让这个长处发挥核心作用。有个关键之处我想在此提醒大家,我这里讲的是宪政民主体制中未来公民的道德教育,其前提是要承诺维持这种政治组织形式。罗尔斯致力于坚持这一承诺,同时也没有回避任何合理的完备学说,他在这些方面的显赫成就吸引了我的注意。但我不能完全肯定他已经取得了圆满成功。然而,我似乎很清楚这一点,那就是如果自由主义作为道德教育的框架能够在加拿大和美国等多元文化社会里得以完全接受的话,那它一定可以以某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来说说“不会”这个回答。现在,我们到了让我“摇摆不定”的分界线了。你看,我的这条分界线还是很明显的。尽管自由主义有我所赞同的长处,但我也找到了自由主义的一大问题,这让我极为关切。我的关切来自对一种人际关系的认识,这种关系与上述分析中的那些关系有所不同,不应与其混为一谈。我认为将其混为一谈会是个很严重的错误,可能在道德上造成严重伤害。而且我认为自由主义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但是,如果将它视作一个相当不同的关注领域来理解的话,承认这个问题可能不会影响到上面提到的种种前景,条件是要将它们在程度上的局限性牢记在心。
全球主义(globalism)有多种特征,其一就是让人们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全球范围内无处不在的某些极其有害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每个已知社会里,至少有一个集团的优势或支配地位要比其他集团更加明显*F. Pratto, J. Sidanius, and S. Levin. “Social Dominance Theory and the Dynamics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Taking Stock and Looking Forward”,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17, 2006, pp.171-172.。此外,这种优势时常会以压迫这种强大的形式对待某些从属集团。
玛丽莲·弗莱(Marilyn Frye)将压迫用鸟笼打了个恰当的比方,将其描述为“一种用势力和障碍圈成的结构,企图使一群人或一类人无法行动、力量削弱”*Marilyn Frye, The Politics of Reality (Trumansburg, N.Y.: Crossing), p. 11.。艾丽斯·杨(Iris Young)则认为“压迫”指的是一种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受压迫的集团“发展与行使自身能力以及表达自己的需求、想法和感受的能力会受到某种抑制”*Iris Marion Young,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New Jersey, 1990), p. 40.。她进一步解释道:
这种意义上的压迫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少数人的选择或政策的结果。其目标存在于某些无人质疑的准则、习惯和符号之中,也存在于对基本制度规则的采纳以及遵循这些规则所产生的共同后果之中。*Young, Justice, p. 41.
这样的关系有很多种。在此,我想谈一谈因性别、种族、阶级和性取向而区分开来的不同集团。对于我们如何理解这几种集团,自由主义有一种软弱无力的理解,这种理解十分危险。在自由主义之内,所有社会上活跃的集体组织都被看作是因个体选择加入而形成的。但我在此重点关注的社会群体与这种自由主义的观念有很大的不同。*Young, Justice, pp. 40-48.我对社会集团的理解直接来自杨的分析。我们是“被迫”进入这些群体并在这些群体内“发现自我”的。举例说来,我并未选择去作“白人”,我生来就是白人。也没有选择去作男性,因为我生来就是男的,而且发现自己被建构在“男性”社会群体中。那些社会群体就在我面前,它们部分构成了我的社会存在。此外,这些群体只是作为与另外一个群体有关系而存在的,这对说明我的意图尤为重要。继续以我个人为例,我身处一个被认为是白人的集团之中,这种情况只有在别人被组成黑人集团(或除白色之外的其他肤色)的时候存在;我身处一个被认为是男性的集团之中,这种情况只有在别人被组成女性集团的时候存在。尽管还有其他集团,但我相信这些用关系来界定的社会集团是表明我自己社会位置的两个最显著的标志。尤为重要的是,和那些用来对照的集团相比,还有两个把我置于统治地位甚至压迫地位的标志。而且,我向各位保证,尽管出于某些原因我对自由主义很有感情,但身处这个位置,我实在是身不由己,这不是我自己选择的。
反过来讲,自由主义在这几种人际关系上的误解建立在其第一个非道德层面的假设上。这种严重问题的来源是,自由主义错误地将其有关个体的特定观念输入到了以集团为基础的人际关系情景之中,如同这些情景与上述那几种道德和政治情景没有任何不同一样。然而,它们的确是不同的。对此,我要解释一下,让我将上面提到的组成自由主义对个体的核心理念的三个特点与作为这些社会集团成员的人的种种实情作一下对比。
首先,自由主义在概念上的个体被认为在本体论上是唯一的:没有两人完全相同,没有两人必须有联系,而且没有人从来就是一群人中的一员。但是,现在我们讨论的那种社会群体中的成员却不能这样来设想。恰恰相反,正是群体成员之间所能意识到的共性使之成为该集团中固有的组成部分。对于这种作为人际关系一部分的实体,自由主义并没有理论空间。第二,自由主义在概念上的个体与其他个体处在相互对等的位置,处在同一个公平竞争的平面,原则上能够认识和理解所有其他人的社会经验。但是,这却无法反映社会集团成员与其他社会集团成员之间存在着关系这一现实。对这些集团的相对关系的描述事关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统治和压迫。这是一种非对等的定位。此外,因为它往往试图维持这种统治和压迫功能,统治集团成员很有可能就会歪曲从属集团成员的经验。最后,自由主义在概念上的个体被认为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存在于任何权力关系之外。但恰恰是这些权力关系最能说明不同社会集团成员人与人之间是如何存在的。之前我曾提过,有些人相对于他人处于统治或压迫地位,这是通过系统表述的和结构性的权力体现出来的。这种假设的政治中立的自由个体根本无法被引入已存在固有权力的人际关系之中。
此外,自由主义的另一个非道德层面的假设也带来了这个问题。我再次提醒大家,自由主义假设人际关系中差异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自由主义将存在于这些社会集团关系中的差异和冲突完全忽略了。从自由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自由主义假设在遇到任何的差异和冲突之前个体就已经存在了。这个人际关系中能够造成伤害的问题本是自由主义的道德和政治理论旨在解决的问题。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因统治或压迫而产生关系的集团在其成员确立之前就已存在了。因此,差异和冲突就建立在了个体作为这些集团成员的种种社会位置之中。
这些看法有着严肃的意义。由于自由主义视个体为组成所有人际关系的社会实体,因此它无法容许社会集团的建构,也无法容许这些社会集团存在于统治和压迫背后的固有的政治化的相对关系。实际上,当它试图解决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等严重问题的时候,这种对个体的关注就会严重妨碍人们看到问题的真正本质。因此,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它能够在其他类型的人际关系中将伤害降到最低程度,但是对于以集团为基础的人际关系,我们可以说,它却成了造成伤害的因素。
对道德教育的几点反思
尽管我在本文中承认自己“摇摆不定”,但我觉得自己的论调并不是消极的。如果道德教育无法解决以用关系来界定的集团为背景的那种人际关系以及广为存在的统治和压迫问题,它在教育事业中就会一败涂地,毫无价值。因此,这个问题迫使我自问:我该提出什么建议呢?
我的确有些建议,这些建议可能会为道德教育的理论框架带来某种改变,我认为这是必要的。不过,我承认大家可能会觉得我的建议太激进,因为它对大多数道德教育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提出了质疑。这个假设是,因为道德必定旨在以种种有意义的方式将人们聚集在一起,道德教育必须要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所有学生。也就是说有一种普遍适用的道德教育。基于本文考虑的种种社会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摒弃这个假设。忽视道德教育中集团关系的非对等性不仅能为这些关系推波助澜,从而不幸使它造成伤害而非减轻伤害,我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一点。
因此,现在的问题成了:“如何才能有效地避免这种伤害?”我认为必要的出发点是要对因果责任(causal responsibility)以诚相待。简单说来,鉴于伤害之因来自统治和压迫集团的成员,我认为为改变承担主要责任的应当是我们。我们应当更以批评性的眼光来审视自我,将我们视作这种伤害的源泉。因此,这种集团成员的道德教育必须被重新设想。反过来说,这就意味着指导道德教育的哲学框架也需改变。为此,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然而,我提议,作为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也是解释性的一步,我们应当开始将一种新的道德原则理论化。这个原则旨在应对统治集团成员的需求,以求负责地、批判性地反思——和“处理”——他们的统治地位。我将这个原则称作“统治敏感度”(Dominance Sensitivity)。
下面我要讲一讲作为统治集团成员的“我”自己需要培养的这种敏感度。作为这样一个成员,我绝对不能从自由主义所建议的那种中立的社会位置来做。相反,我只能从我具有相对占统治地位的位置来做。同样,尽管是从个人角度来谈的,但这并不意味我要做的事情只与我自己相关。相反,大家应当认为我的建议可能会适用于任何人,只要这些人是从作为一个统治集团(或数个统治集团)成员的角度在世界上开展行动的,无论是什么情况,在什么时候,有着怎样不同的程度。它对某些人并不适用,尤其是那些属于从属集团或者受压迫集团的成员。
为了充实我的建议,我将我所提出的“统治敏感度”原则分为三个组成部分。这三个组成部分概述如下:(1)弱化唯一性;(2)为合谋行为承担责任;(3)抵制特权意识。我认为这个原则既有认知层面,又有情感层面,这会通过每个组成部分、特别是三部分的结合体现出来。提出这三个部分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找到对自我进行批判性反思的不同方式,而且为了说明它们必然对我“意义”重大,促使我采取相应的行动。我将逐一解释一下这三个部分。
1.弱化唯一性
我认为培养统治敏感度必要的第一步是对自由主义最基础的假设,也就是对个人的绝对特殊性提出批判性的质疑。我深切感受到,在某些情景中合情合理的个别而又“特殊”的地位在被引入另外一些情景时却成了一种危险的幻象,对此我需要好好理解。在这些情景中,我是作为某一社会集团中的一员与他人进行互动的,这一社会集团是以与另一集团及其从属或压迫地位的相对关系来界定的。如果我真心诚意地想学会如何弱化在这些情景中我的社会位置所带来的统治或支配地位,那我必须要放弃我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在这些情景中行动的想法。相反,正是我与某些集团成员之间的共性才是这里的要点所在。例如,只要我所具有的男性气质与世界上的许多其他人大同小异,在某些情景中我才和他们没有区别。世界上聚合成为统治和压迫的那些行动,如性别歧视等,并非源自我的唯一性,而是源自我与他人的互换性。在不同层面上接受这一点,需要学会弱化我的唯一性。
2.为合谋行为承担责任
弱化唯一性固然重要和必要,但它只是第一步,后面的要求将会更难做到。如果由我所在集团的成员资格确立的那个“我”可与集团中的其他人互换,那么“代理行动”(proxy action)也能够确立一种对统治关系的积极表达。“代理”(proxy)是一个被授权为他人行动的人。与统治和压迫的关系直接建立在与成员间的互惠授权之上,这些互惠授权关系与使关系具体化的期望、规范、价值观、思考和感觉方式以及行为有关。我可能能够抵御许多这样的东西,但我不可能永远天真地做局外人。原因是,其他人有以我的名义,作为我采取行动的权利。我作为“男性”的社会位置有一部分是由相互授权确立的,因此具有代理权。继续谈一下有关性别的例子,全世界的女性不论是在公司还是在政府任职都会遭遇所谓“玻璃天花板”的无形障碍,这种无形障碍是由男人建构而成的。无论我对那些对女性的限制有何感想,与女性相比,它为我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还有一个例子与此类似,但在道德上更令人不安,那就是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有着全球化的趋势。其含义是明确的:我无可避免地合谋参与了这个以集团为基础的伤害事件。如果不为这种合谋行为承担责任,就不会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等问题提出严肃挑战。
3.抵制特权意识
如果我不为自己的合谋行为承担责任,就不会发生很大改变,但它本身仍然显得太消极了。对于统治敏感度,可能还有许多更积极的体现。但我在此想要指出的这个组成部分对我来说十分特殊,因为它可用多种方式适用于许多不同的层面。我将其称作“抵制特权意识”。我曾指出,在此与我相关的那种社会集团关系是不对等权力关系的建构。表现这些关系的常用方法之一是期待着被赋予特权。站在处于统治或支配地位的一方不仅意味着拥有更多大家可能都想要的东西,而且感觉这很自然,是我“应得”的。事实上,更进一步讲,这意味着根本就没意识到因为我拥有的更多,别人拥有的就少这种不平衡。我们可以再次从性别上来看一个易于理解的例子。作为男子,我很可能不知道——或干脆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一个包括男女的集团里我往往比女性有更多的机会说话,更咄咄逼人。或者这样一个事实,在公司或政府中,我会比女性更容易担任要职。或者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完全相同的工作,我要比女性赚得多。对这类不平等故意视而不见是统治地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其当作特权加以抵制代表着一种削弱权力非对等性的重要手段,因此也是行使某些统治敏感度的一种方式。
结论
我承认,我对自由主义作为道德教育的理论框架是否得当“摇摆不定”。在本文后半部分我一直关注一种全球存在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对许多人极其有害。我将这些人际关系的特点总结为统治和压迫,它们存在于以彼此关系来界定的集团之间。我发现自由主义的严重问题在于它无法处理这些关系。更糟的是,在这种情景下使用自由主义本身会造成这些关系中内在的伤害。
不过,在本文前半部分,我的态度更积极一些。我的确看到了这个框架中的某些非常重要的长处。如果人们理解这些长处并将其应用于有限的人际关系中,而不是错误地以为它们是处理集团之间的统治和压迫关系的适当观点的话,我会将其视作种种理想目标而加以支持。
然而,即便如此,我认识到这些长处还远远达不到其现实目标。现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在北美仍很盛。这种情况说明,人人享有平等的道德地位和人人应得基本的尊重这一理想在现实中并未普及。同样道理,这些观念在政治上的充分表达在很大程度上也未普及。也就是说,在这两种情况下,对很多人来说,这些理想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仍旧只是一种“前景”而已。
当人们认为这些人是被统治和被压迫的集团中的成员的时候,自由主义的理想本身可能就会遭到质疑。但我并不认为,这就意味着这些道德上令人难以接受的现实的存在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法纠正的。不过,我相信,要对其进行纠正,真正的希望在于统治集团成员的道德取向要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而且,我们要将这种改变融入我们的道德教育框架之中。我认为,培养统治敏感度是值得迈出的第一步。然而,它只是第一步而已,前方的征途会漫长而艰险。踏上这个征途,急需全球同仁的努力。因此,我邀请在座的有志者和我一起踏上这个征途。
莒文化的历史源渊、精神内涵与特色(笔谈)*
Liberalism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Moral Education:Promises and Problems
Dwight Boyd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Good moral education must have a strong philosophical framework. It fairly safe to most moral education efforts in North America today are grounded in th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of liberalism. Judging their moral legitimacy,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a critical look at that tradition. Firstly, synthesize liberalism, then this framework is assessed, and the suggestion of imagining a normative framework is put forward in the end, which might initiate the kind of change needed in moral education.
moral education; liberalism; normative framework
莒文化是齐鲁文化的先声和前导,是中华多元文化体系中深具特色的重要地域文化之一。本组文章对莒文化从多视角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尹盛平的《莒文化源远流长》一文认为莒文化的直接源头是大汶口文化,在其后发展中与龙山文化、商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认真发掘和研究莒文化,不仅对于认识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文化的发展史有益,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振兴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孙敬明《从莒地出土两周十四国金文看莒文化的交流与影响》一文介绍了莒文化区域内出土齐、鲁、诸、莱、郈、曹、陈、徐、吴、越、樊、黄、邛、楚等十四国(族)之有铭铜器,这对探索莒文化交流与影响大有裨益。蔡运章《大汶口陶罍文字及其相关问题》一文认为目前所释大汶口陶罍文字应是大汶口先民祭祀天神时“制器尚象”习俗的产物,可名之为物象文字,这种神秘文字的发现和深入研究,对探讨中国文字起源和形成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莒文化;历史渊源;精神内涵
2013-02-12
德怀特·鲍伊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翻译:贾磊,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校订:于天龙, 美国南伊利诺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泰山学者”特聘教授。
G40
A
1001-5973(2013)02-0108-10
责任编辑:时晓红
G127
A
1001-5973(2013)01-011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