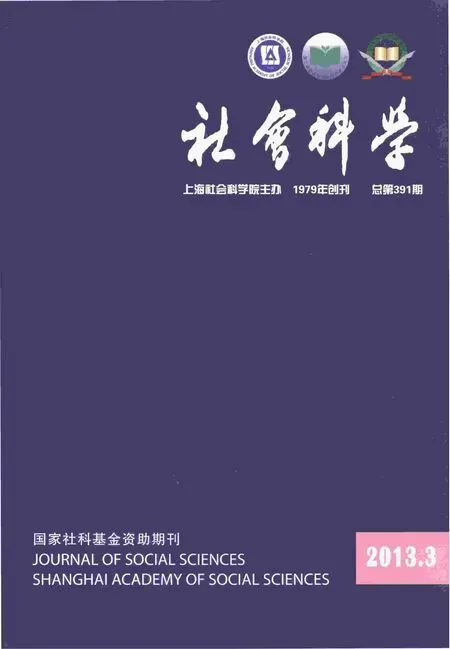上海文化产业供需协调增长预期目标——既往20年分析与未来10年测算
王亚南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向应以扩大人民群众文化消费需求和促进城乡、区域均衡共享进行定位,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必须从不可或缺的“内生动力”中拓展出来,更应当落实在自身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之上。本项研究以扩大文化消费需求、促进城乡文化共享为目标,测算全国各地城乡文化消费需求的“或然增长”和“应然增长”目标,并以此度量上海文化产业未来10年的发展空间。上海文化产业如何才能成为支柱性产业自在其中,单纯追求“文化GDP”支柱产业目标并不足取。
一、上海城乡文化消费及其相关背景增长态势
城乡文化消费需求总量是文化产业生产总量实际进入城乡居民日常生活消费的具体表现,也是文化建设和文化生产的发展成果实际转化为城乡人民群众文化消费需求的具体体现。总量数值有利于把握上海总体态势,但总量演算受到人口增长及其分布变化影响,误差较大,因而本文仅在开头和结尾涉及总量演算,中间则基于人均数值展开分析测算。
1991-2011年,上海乡村与城镇文化消费总量及城乡文化消费人均值增长态势见图1。囿于制图篇幅限制,图中各五年规划期头年与末年直接对接。文中分析历年增长态势时,则运用测评数据库后台演算功能,筛测出的最高与最低年度值包含图中省略年度。
1991-2011年,上海城乡文化消费总量从22.75亿元增长至532.25亿元,增加509.50亿元,年均增长17.07%。三个五年规划期相比,上海城乡总量“十一五”年均增长幅度高于“十五”2.46个百分点,低于“九五”2.92个百分点。

图1 1991-2011年上海乡村与城镇文化消费总量、城乡人均值增长态势
1991-2011年,上海城乡人均文化消费从169.96元增长至2,289.18元,增加2,119.22元,年均增长13.89%。三个五年规划期相比,上海城乡人均值“十一五”年均增长幅度高于“十五”1.04个百分点,低于“九五”4.34个百分点。
在这20年间,上海城乡文化消费需求增长态势显露出两个方面的问题:(1)与“九五”和“十五”期间相比,“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幅度明显下降,无论是总量值测算,还是人均值测算,情况都是如此;(2)城乡差距显著扩大,20年以来,上海城镇总量总增长高达乡村总量增长的5.53倍,城镇总量年均增长幅度高出乡村年均增幅8.84个百分点;城镇人均值总增长高达乡村人均值增长的2.05倍,城镇人均值年均增长幅度高出乡村年均增幅3.6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就上海总体而言,提升消费需求并促进城乡共享迫在眉睫。
当然,上海城乡文化消费需求状况分析不能孤立地进行,前后时段之间、城镇与乡村之间总量增长比较也只是一种表层的比较,还需要把上海城乡文化消费需求增长放到经济发展、民生进步的社会背景中展开全面考察。鉴于人均数值分析演算更为精确,以下采用人均值进行测算。
上海历年人均产值、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消费和积蓄 (收入与消费之差)各项绝对值 (详见本文后续各图表)转换为以上一年数值为100的年度增长百分比指数,得出1991-2011年上海人均产值、城乡人均收入、消费 (分为非文消费与文化消费两部分)、积蓄增长态势见图2,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若干具有规律性、趋势性的动向。
1991-2011年,在上海人均产值、城乡人均收入、人均非文消费、人均文化消费与人均积蓄之间,有三对数据组的关系值得注意:
数据项 (1)与 (2),即上海人均产值年增指数 (柱形)与城乡人均收入年增指数 (带菱形曲线),二者相关系数为0.7679,亦为其间历年增长幅度在76.79%的程度上保持同步。
数据项 (2)与 (3),即城乡人均收入年增指数与人均非文消费年增指数 (带方形曲线),二者相关系数为0.3145,亦为其间历年增长幅度在31.45%的程度上保持同步,相关性很低。
数据项 (4)与 (5),即城乡人均文化消费年增指数 (带圆形曲线)与人均积蓄年增指数(带三角形曲线),二者相关系数为0.3165,显得相关性很低。然而,分时间段考察,可以看到其间存在着极其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日常所说的“成反比”:2001-2009年间相关系数为负值0.8804,2001~2005年间相关系数为负值0.9018。这意味着,上海城乡人均积蓄年度增长幅度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乡人均文化消费年度增长幅度在2001-2009年间便下降0.88个百分点,在2001-2005年间更下降0.90个百分点。若在“正相关”关系中,这一相关系数还不算很高,但在“负相关”关系中,这一相关系数已经极高。

图2 1991-2011年上海人均产值、城乡人均收入、消费、积蓄增长态势
在上海城乡人均文化消费年度增长曲线与人均积蓄年度增长曲线之间,特别是在“十五”至“十一五”期间,呈现出较为“完美”的横向“镜面对应”或“水中倒影”负相关关系。这就是本项研究多年前揭示出来并不断补充后续年度数据一再加以证实的重要发现——中国城乡文化消费需求体现出一种“积蓄增长负相关效应”。其中的社会背景因素在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必须辅之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相配套,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严重滞后,民众不得不更加注重积蓄以求“自我保障”。譬如建立“子女教育基金”、“个人病老基金”等。
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联系,从以上分析中提取三对关键性的数据组,正好构成了从经济增长到城乡文化消费需求增进的完整而简明的数据关系链:上海人均产值增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人均非文消费绝对值增长而占收入比重值降低;(取人均收入与人均非文消费之差反转为)城乡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剩余增长——人均文化消费增长。由此可以揭示出上海人均产值增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多——人均非文消费占收入比重值降低——人均非文消费剩余增大——人均文化消费增进之间的多重协调关系状况。这是本项研究独创的一种分析思路和检测方法。
这三对数据组分别形成一种比例关系:(1)城乡人均收入与人均产值的比例值,检验“国民总收入”与城乡居民收入的关系;(2)城乡人均非文消费占人均收入的比重值,检验城乡居民收入与“必需”的非文消费的关系;(3)城乡人均文化消费与人均非文消费剩余的比例值,检验城乡居民“必需消费”之外余钱与“非必需”的文化消费的关系。特别是其中后两项比例关系值分析,为本项研究从“中国现实”出发的独到构思设计,没有以往的研究经验和现成数据可供参照。于是在本文里,上海城乡层面的既往事实也就成了“第一手”参考依据。以1991年以来上海城乡综合演算的以上三项比例值的历年最佳值作为一种“应然”参考值,追求上海城乡自身近期曾经实现了的“目标”,这样一种期待显得更加切合实际。
此外,“城乡比”指标演算系本项研究的独创方法,专门用于测算全国及各地诸方面城乡差距的“发展缺陷”。本文同时测算上海人均收入、人均非文消费和人均文化消费的历年城乡比变化,作为城乡之间各方面增长协调性分析的“应然”参考值。
二、上海城乡民生基础系数的增长协调性检测
在本项研究中,居民人均收入与人均产值的比例值设定为“民生基础系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首先就落实在居民收入之上。
按照国际通行做法,我国现行统计制度以“国内生产总值”(英文简称“GDP”,中文可简称“产值”)来体现经济总量。“国内生产总值”再加上国外净要素收入,就构成“国民总收入”。“国民总收入”原称“国民生产总值”,即我国以往统计制度长期使用的“GNP”。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历年国外净要素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例极低,以《中国统计年鉴》2012年卷校正数据来看,2008年仅为0.63%,2009-2011年甚至为微小负值,只好忽略不计。这样看来,“国内生产总值”是构成“国民总收入”的主要部分,于是不妨将居民人均收入与人均产值的关系近似地类比为居民收入与“国民总收入”的关系。同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分地区经济统计数据只有作为“国内生产总值”分解的“地区生产总值”,而无“国民总收入”的地区分解数据。本项研究把“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国民总收入”的相近替代数据看待,相关演算就可以推演至各地。这就是设定居民人均收入与人均产值的比例值为“民生基础系数”的数据依据和技术原因。
在本项研究中,这一“民生基础系数”以数值大为佳,直接反映“初次分配”基本情况。本文将以此检验上海经济增长带动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历年变动状况,并提取1991年以来历年“最佳比例值”,作为推演测算所依的应然参考值。“国民总收入”分配是决定城乡居民收入的基本前提,而城乡居民收入又是其民生消费与文化民生消费的直接基础。离开以上海产值增长来体现的经济发展,自然就谈不上以城乡居民收入增多来体现的最基本的民生增进 (就业当然属基础环节,但不在本项研究范围之内);离开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城乡民生消费与文化民生消费提升也就无从谈起。所以,这一项指标分析是本项研究逐步向下推演测算的逻辑基点。
1991-2011年上海人均产值、城乡人均收入绝对值、比例值变动态势见图3。

图3 1991-2011年上海人均产值、城乡人均收入绝对值、比例值变动态势
图3将上海人均产值、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绝对值转换为图形面积比例,从中可见,1991-2011年,上海人均产值年均增长13.17%,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4.53%,产值年增幅度低于居民收入年增幅度1.36个百分点。其中,“九五”期间,上海人均产值年均增长11.75%,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0.49%,产值年增幅度高于居民收入年增幅度1.27个百分点;“十五”期间,上海人均产值年均增长11.67%,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9.79%,产值年增幅度高于居民收入年增幅度1.89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上海人均产值年均增长8.10%,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1.22%,产值年增幅度低于居民收入年增幅度3.12个百分点。三个五年规划期相比,二者增长差距在“十一五”期间减小,近两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与人均产值的比例值迅速上升。
详细考察图中年度,除了1996年、2000年和2005-2006年出现微小回降以外,上海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与人均产值的比例值一直呈现逐步上升趋势,由1991年32.44%提高至2011年41.17%。20年间逐年考察,上海城乡此项比值最低值为1991年32.44%,最高 (最佳)值为2011年41.17%。“民生基础系数”大体上一直在增高,意味着“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程度逐渐提高。这与全国居民收入增长普遍落后于产值增长的状况正好相反。本项研究将此变动态势作为一项检测指标,按照已经取得的“协调增长”实际进展继续推演测算。
1991-2011年上海城乡人均收入绝对值和城乡比变动态势见图4。
图4将上海城镇居民与乡村居民人均收入绝对值转换为图形面积比例,从中可见,1991-2011年,上海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4.70%,乡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0.97%,城镇年增幅度高于乡村3.73个百分点。其中, “九五”期间,上海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0.26%,乡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5.68%,城镇年增幅度高于乡村4.58个百分点;“十五”期间,上海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9.73%,乡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8.07%,城镇年增幅度高于乡村1.67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上海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1.30%,乡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1.13%,城镇年增幅度高于乡村0.17个百分点。三个五年规划期相比,“十五”期间上海城乡之间收入增长的差距明显减小,“十一五”期间上海城乡之间收入增长的差距有所减小。

图4 1991-2011年上海城乡人均收入绝对值和城乡比变动态势
详细考察图中年度,除了1996年和2011年以外,上海城镇人均收入增长一直高于乡村人均收入增长。作为城乡差距的衡量指标,上海居民人均收入城乡比由1991年1.1652扩大至2011年2.2568,20年间最小 (最佳)值为1991年1.1652,最大值为2004年2.3609,总体上呈现明显扩增趋势,意味着城乡之间在民生基础层面“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程度有所降低。这一问题还没有引起学术界和政府界的足够重视。本项研究将此变动态势作为一项检测指标,推演测算由此而来的城乡“均衡发展”应然差距。
在此做出若干假定测算作为预设:(1)如果上海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与上海人均产值的比例值能够保持2011年最佳水平,即维持当前达到的历年最佳值不变;(2)如果上海居民人均收入城乡比能够保持1991年最小程度,那么2011年上海城乡人均收入应达到35659.81元;(3)如果上海居民人均收入城乡比能够弥合而实现无差距理想状态,那么上海城乡人均收入应达到36230.48元 (即2011年城镇人均值)。这样一来,随后推演的一切后续数值都会发生变化。
最后在至2020年“协调增长”、“均衡发展”的预期目标测算中,将取上海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与人均产值比例值的历年最佳值,上海人均收入城乡比的历年最小值,乃至城乡之间人均收入无差距理想值,分别推演后面的各项数值,最终测算出上海城乡文化消费需求应然增长目标。
三、上海城乡民生消费系数的增长协调性检测
在本项研究中,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占人均收入的比重值设定为“民生消费系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的“需求”主要表现为消费需求,满足人民群众“基本需求”主要体现为满足必需消费,包括最基本的衣食温饱也不例外。“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最终应落实在民生消费之上。
本项研究在人均总消费之中划分出“非文消费”部分,假设全部非文消费皆为“必需消费”,其间包含人们不可或缺的物质生活消费;也包含当今时代必要的社会生活消费。当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必需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消费支出也有可能接近成为一个常量,甚至相对于收入的比重值还会有所降低,这就为“非必需”的文化消费需求增长留出了更多的余地。显然,这一“民生消费系数”以数值小为佳,反过来即以“必需消费”之外的余钱增多为佳。本文将以此检验上海城乡居民收入保障基本民生消费的历年变动状况,并提取1991年以来历年“最佳比例值”,作为推演测算所依的应然参考值。与“必需消费”相对应的另一面则是“必需消费剩余”,文中称为“非文消费剩余”,其中正包含着本项研究最终关注的“非必需”文化消费需求。
1991-2011年上海城乡人均收入、非文消费绝对值、比重值变动态势见图5。

图5 1991-2011年上海城乡人均收入、非文消费绝对值、比重值变动态势
图5也将上海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人均非文消费绝对值转换为图形面积比例,从中可见,1991-2011年,上海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4.53%,人均非文消费年均增长12.99%,人均收入年增幅度高于人均非文消费年增幅度1.54个百分点。其中,“九五”期间,上海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0.49%,人均非文消费年均增长8.30%,收入年增幅度高于非文消费年增幅度2.18个百分点;“十五”期间,上海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9.79%,人均非文消费年均增长9.29%,收入年增幅度高于非文消费年增幅度0.50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上海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1.22%,人均非文消费年均增长10.47%,收入年增幅度高于非文消费年增幅度0.75个百分点。三个五年规划期相比,二者增长差距不断加大,城乡居民人均非文消费 (必需消费)占人均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
详细考察图中年度,除了2005年出现微小回升以外,上海城乡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占人均收入的比重值一直呈现逐步下降趋势,由1991年81.92%降低至2011年62.53%。20年间逐年考察,上海城乡此项比值最高值为1991年81.92%,最低 (最佳)值为2011年62.53%。“民生消费系数”大体上一直在减低 (以小为佳倒序),亦即“必需消费”之外的余钱占收入的比重一直在增高。这意味着,上海城乡居民“必需消费”增长或许已没有多少余地,“必需消费剩余”正日益增多,在基本民生消费层面“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效应日益得以显现。这是本项研究的独有设计带来的一个发现,可以说明20年来上海经济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增多体现在基本民生消费层面的实际成效明显。本项研究将此变动态势作为一项检测指标,按照已经取得的“协调增长”实际进展继续推演测算。
1991-2011年上海城乡人均非文消费绝对值和城乡比变动态势见图6。
图6也将上海城镇居民与乡村居民人均非文消费绝对值转换为图形面积比例,从中可见,1991-2011年,上海城镇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年均增长12.94%,乡村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年均增长10.36%,城镇年增幅度高于乡村2.58个百分点。其中,“九五”期间,上海城镇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年均增长8.08%,乡村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年均增长2.71%,城镇年增幅度高于乡村5.37个百分点;“十五”期间,上海城镇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年均增长8.97%,乡村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年均增长12.12%,城镇年增幅度低于乡村3.16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上海城镇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年均增长10.70%,乡村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年均增长7.76%,城镇年增幅度高于乡村2.94个百分点。三个五年规划期相比, “十五”期间上海城乡之间非文消费增长的差距有所减小,“十一五”期间上海城乡之间非文消费增长的差距明显加大。
详细考察图中年度,除了1995年、2000年和2010年以外,其余年度上海城镇人均非文消费增长幅度皆低于乡村,有可能接近成为一个常量;与之相反,乡村人均非文消费增长幅度在较多年度高于城镇,保持着进一步增长态势。作为城乡差距的衡量指标,上海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城乡比由1991年1.4069扩大至2011年2.2344,20年间最小 (最佳)值为1992年1.3015,最大值为2000年2.2987,总体上呈现逐步扩增趋势。其中,进入“十五”期间明显缩小,近几年又有所扩大,意味着城乡之间在基本民生消费层面“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程度在“十五”期间有所提高,近几年来又有所降低。这也是本项研究的独有设计带来的一个发现,至今还没有引起学术界和政府界的应有注意。本项研究将此变动态势作为一项检测指标,推演测算由此而来的“协调增长”应然差距。
在此做出若干假定测算作为预设:(1)如果上海城乡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占人均收入的比重值能够保持2011年最佳水平,这是当前比值而结果不变,取上一类最佳比例值叠加测算,那么2011年上海城乡人均非文消费应达到21251.85元,反转则是人均非文消费剩余增多至12737.23元;(2)如果上海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城乡比能够保持1992年最小程度,那么2011年上海城乡人均非文消费应达到22058.63元,反转则是人均非文消费剩余增多至13601.18元;(3)如果上海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城乡比能够弥合而实现无差距理想状态,那么上海城乡人均非文消费应达到22641.36元 (即2011年城镇人均值),反转则是人均非文消费剩余增多至13589.12元。这样一来,随后推演的一切相关数值也会发生变化。
最后在至2020年“协调增长”、“均衡发展”的预期目标测算中,将取上海城乡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占人均收入比重值的历年最佳值,上海人均非文消费城乡比的历年最小值,乃至城乡之间人均非文消费无差距理想值,分别推演后面的各项数值,最终测算出上海城乡文化消费需求应然增长目标。
四、上海城乡文化需求系数的增长协调性检测
在本项研究中,居民人均文化消费与人均非文消费剩余的比例值设定为“文化需求系数”。这是衡量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际效果的重要指标。
本项研究多年前揭示出中国城乡文化消费需求的“积蓄增长负相关效应”,当然一向特别关注上海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增长与积蓄增长的特殊互动关系,特地从总消费里分解出“非文消费”,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与之对应的“非文消费剩余”。借用经济学把收入与总消费之差称为“消费剩余”之说,收入与非文消费之差也就可以视为“非文消费剩余”。
人均文化消费与人均非文消费剩余的比例值正好体现了文化消费与积蓄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此消彼长的“负相关”关系势必形成对于“必需消费”剩余部分的相互“争夺”。在本项研究中,这一“文化需求系数”同样以数值大为佳,间接涉及“二次分配”状况,能够衡量文化消费的民生需求涨落。与之对应的背景因素则是社会保障建设的实际效果,由此自然能够缓解广大民众的“必需积蓄”,从而增加“非必需”的精神文化消费。本文将以此检验上海城乡居民非文消费剩余增减左右文化消费需求涨落的历年变动状况,并提取1991年以来历年“最佳比例值”,作为推演测算所依的应然参考值。
1991-2011年上海城乡人均非文消费剩余、文化消费绝对值、比例值变动态势见图7。
图7仍将上海城乡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剩余、人均文化消费绝对值转换为图形面积比例,从中可见,1991-2011年,上海城乡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剩余年均增长18.78%,人均文化消费年均增长13.89%,人均非文消费剩余年增幅度高于人均文化消费年增幅度4.89个百分点。其中,“九五”期间,上海城乡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剩余年均增长16.80%,人均文化消费年均增长17.39%,非文消费剩余年增幅度低于文化消费年增幅度0.59个百分点;“十五”期间,上海城乡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剩余年均增长10.90%,人均文化消费年均增长12.01%,非文消费剩余年增幅度低于文化消费年增幅度1.11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上海城乡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剩余年均增长12.77%,人均文化消费年均增长13.05%,非文消费剩余年增幅度低于文化消费年增幅度0.27个百分点。上海城乡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非文消费剩余的比重值总体降低,主要还是“九五”后四年明显下降积累下来的。

图7 1991-2011年上海城乡人均非文消费剩余、文化消费绝对值、比重值变动态势
详细考察图中年度,除了1996年、2005年和2010年出现回升以外,上海城乡居民人均文化消费与人均非文消费剩余的比例值一直呈现逐步下降趋势,由1991年41.68%降低至2011年17.97%。20年间逐年考察,上海城乡此项比值最高 (最佳)值为1991年41.68%,最低值为1994年16.13%。“文化需求系数”大体上一直在降低,意味着文化消费需求增长明显持续受到积蓄增长的反向牵制,其社会背景因素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依然显得滞后,广大民众应付“未来不明年景”而自保的“必需积蓄”难以降低。这还是本项研究的独有设计带来的一个发现,揭示出20年以来上海城乡居民文化消费需求增长并不容乐观,反过来看也可以说还蕴藏着巨大潜力。本项研究将此变动态势作为一项检测指标,推演测算由此而来的“协调增长”应然差距。
1991-2011年上海城乡人均文化消费绝对值和城乡比变动态势见图8。
图8仍将上海城镇居民与乡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绝对值转换为图形面积比例,从中可见,1991-2011年,上海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年均增长13.89%,乡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年均增长10.28%,城镇年增幅度高于乡村3.60个百分点。其中,“九五”期间,上海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年均增长17.27%,乡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年均增长16.91%,城镇年增幅度高于乡村0.36个百分点;“十五”期间,上海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年均增长12.09%,乡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年均增长10.87%,城镇年增幅度高于乡村1.23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上海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年均增长14.07%,乡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年均增长1.27%,城镇年增幅度高于乡村12.80个百分点。三个五年规划期相比,“十五”期间上海城乡之间文化消费增长的差距有所加大,“十一五”期间上海城乡之间文化消费增长的差距持续加大。

图8 1991-2011年上海城乡人均文化消费绝对值和城乡比变动态势
详细考察图中年度,除了1995年和2000-2001年以外,上海城镇人均文化消费增长一直高于乡村人均文化消费增长。作为城乡差距的衡量指标,上海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城乡比由1991年1.4120扩大至2011年2.6862,20年间最小值 (最佳值)为2001年0.9339(此为“城乡倒挂”,即乡村人均文化消费高于城镇),最大值为2011年2.6862,总体呈现持续扩增趋势,意味着城乡之间在文化消费需求层面“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程度有所降低。这仍是本项研究的独有设计带来的一个发现,揭示出20年以来上海城乡之间文化消费需求增长极不平衡。本项研究将此变动态势作为一项检测指标,推演测算由此而来的城乡“均衡发展”应然差距。
在此做出若干假定测算作为预设:(1)如果上海城乡居民人均文化消费与人均非文消费剩余的比例值能够保持1991年最佳水平 (简称“消除负相关测算”,即文化消费增长与积蓄增长之间不再构成负相关关系),那么2011年上海城乡人均文化消费应达到5309.38元,总量可达到1234.46亿元;(2)如果在保持此项最佳比例值基础上,上海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城乡比能够保持2001年最小程度,那么2011年上海城乡人均文化消费应达到5752.26元,总量可达到1337.44亿元;(3)如果同样在保持此项最佳比例值基础上,上海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城乡比能够弥合而实现无差距理想状态,那么上海城乡人均文化消费应达到5707.38元,总量可达到1327.00亿元。
至此,上海城乡文化消费需求增长相关方面的诸多差距一目了然:一方面在于经济增长与基本民生、文化民生增进的协调性差距,另一方面在于城乡之间文化民生增进的均衡性差距。最后在上海今后10年“协调增长”、“均衡发展”的预期目标测算中,将取上海城乡居民人均文化消费与人均非文消费剩余比例值的历年最佳值,上海人均文化消费城乡比的历年最小值,乃至城乡之间人均文化消费无差距理想值,并叠加上两类协调性差距检测分别推演,最终测算出上海城乡文化消费需求应然增长目标。
有必要补充说明,以上就上海城乡三个方面逐一开展独立分析,类似设置了一种纯化的“实验室”条件,分别针对上海城乡三个方面之一的比值关系及其变化单独进行演算,而暂时搁置上海城乡其他方面的比值关系及其变化影响。然而实际上,上海城乡这三个方面的比值关系及其变化恰恰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最终必须综合在一起进行统一分析演算。
就此继续做出若干假定测算作为预设:(4)如果同时取“民生基础系数”、“民生消费系数”和“文化需求系数”三类最佳比例值叠加测算 (简称“最佳比例值测算”),那么2011年上海城乡人均文化消费应达到5309.38元,总量可达到1234.46亿元;(5)如果在保持三项最佳比例值基础上,上海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城乡比能够保持2001年最小程度 (简称“最小城乡比测算”),那么2011年上海城乡人均文化消费应达到5752.26元,总量可达到1337.44亿元;(6)如果同样在保持三项最佳比例值基础上,上海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城乡比能够弥合而实现无差距理想状态 (简称“弥合城乡比测算”),那么上海城乡人均文化消费应达到5707.38元,总量可达到1327.00亿元。
综合以上三类检测,最后进行更加理想化的假定测算:(7)如果上海居民人均收入、人均非文消费和人均文化消费三类城乡比同时得以消减至无差距理想状态,即取各项城镇人均值,按上海城镇实现三类比例值历年最佳水平演算 (简称“城乡无差距测算”),那么2011年上海城乡人均文化消费应达到7090.41元,总量可达到1648.56亿元。
五、文化需求增长目标暨文化产业发展空间测算
在“十二五”期间注重“协调增长”的预定目标之下,寄期实现既往年度“最佳状态”的应然测算,在技术上提供了一种简单易行的检测方法,在现实中也实在不过是一种起码的期待。同样,面向科学发展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理念要求,寄期实现未来“理想状态”的应然测算,可以检验出距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想目标的现实差距。
2011-2020年上海城乡人均文化消费增长暨文化产业发展空间测算见图9。鉴于需要基于2011年统计数据进行测算,这里将2011年作为“未来10年”的头一年处理。作为必不可少的背景因素,2011-2020年上海人均产值增长先按照1991-2011年实际年均增长率推算,得出文化消费需求增长目标差距;再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预定的产值年均增长7%推算,得到增长目标差距校正数值。

图9 2011-2020年上海城乡人均文化消费需求增长测算
图9同时提供了上海城乡人均文化消费需求增长的七类测算结果。除了第 (1)类历年均增值测算以外,其余各类测算均以所需年均增长幅度来表现距离“协调增长”目标的差距。各类测算的目标取向、演算方法不同,其间各类增长曲线即使十分接近 (图中“弥合城乡比”测算增长曲线与“最小城乡比”测算增长曲线几乎重叠,“消除负相关”测算增长曲线恰好被“城乡无差距”测算增长曲线完全覆盖),也不可视为相互涵盖。
(1)历年均增值测算:以1991-2011年上海城乡人均文化消费年平均增长率推算未来年度文化消费需求增长趋势,这是基于统计概率的最“可能”增长结果。如果2011-2020年同前保持13.89%的年均增长幅度 (省域间实际增长第8位),那么到2020年上海城乡人均文化将达到7377.07元。由于1991-2011年间上海城乡人均文化消费与人均产值的比例值呈现缓慢上升态势,2020年城乡人均文化消费增长测算值与上海人均产值增长测算值之间的比例值将升高至2.93%。显然,继续维持这样一种常规增长态势,并不能实现支柱性产业发展目标。
(2)支柱性产业测算:以文化产业支柱性发展目标测算未来年度文化消费需求增长趋势,即依据通常支柱产业的产值比重,按照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的供需协同增长,以文化消费增长目标来反推文化生产增长目标。基于文化消费测算值与产值测算值之间的比例值达到4.86%反推,到2020年上海城乡人均文化消费应达到12227.73元,即2011-2020年年均增长幅度需达到20.46%,为以往20年实际年均增幅的147.37%(省域间目标距离第1位),却是到“十三五”末年上海文化产业达到支柱产业供需目标所必需的。
本项研究设定全国城乡人均文化消费与全国人均产值比3.76%(此项比值演算逐年修订,现为2011年数据修订值)为中国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必需“临界值”。其演算依据在于:2011年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为13479亿元,占同期GDP的比重为2.85%;本项研究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演算得出可对应值:2011年全国城乡文化消费总量为10126.19亿元,城乡人均文化消费为753.36元,与全国人均产值的比例值为2.14%(更精确小数为2.1414%)。在文化产业增加值——文化生产数据与城乡文化消费——文化需求数据之间,存在着一定对应关系,其间的差额包括公共文化服务部分 (大都未能进入城乡居民日常生活消费),当然也包括文化产业提供产品和服务没有进入城乡居民日常生活消费的部分 (譬如公费书报刊购买订阅)。假定此间的对应比值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大致恒定,那么当全国城乡人均文化消费与全国人均产值的比例值增高到3.7568%(更精确小数)时,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同期GDP的比重也将达到5%。各地此项比值各有不同,上海2011年演算值为4.8645%(更精确小数)。
(3)最佳比例值测算:以1991-2011年间城乡人均收入与产值比、非文消费占收入比、文化消费与非文消费剩余比三项比例值的历年最佳值测算未来年度文化消费需求增长趋势,即假设维持曾有的三项比例关系“最佳状态”。如果到2020年上海城乡三项比例值实现“十五”以来最佳状态,那么城乡人均文化消费应达到16165.33元,即2011-2020年年均增长幅度需达到24.26%,为以往20年实际年均增幅的174.70%(省域间目标距离第1位),城乡人均文化消费增长与人均产值增长测算值之间的比例值将上升至6.43%。尽快实现这一目标实属协调增长的基本要求,应当努力实现。
(4)弥合城乡比测算 (最小城乡比“倒挂”地区用此类测算可以避免“矫枉过正”,上海就是如此):在三项最佳比例值测算基础上,以上海城乡文化消费城乡比的无差距理想值测算未来年度文化消费需求增长趋势,即假设城乡差距得以消除测算增长状况。如果到2020年上海城乡实现1991年以来三项最佳比例值,同时乡村人均文化消费增长幅度迅速提升,人均绝对值与上海城镇水平持平,那么上海城乡人均文化消费应达到17380.39元,年均增长幅度需达到25.26%,为以往20年实际年均增幅的181.94%(省域间目标距离第1位),城乡人均文化消费增长与人均产值增长测算值之间的比例值将上升至6.91%。这是推进城乡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的基本要求,有必要及早实现。
(5)最小城乡比测算:在三项最佳比例值测算基础上,以1991-2011年上海文化消费城乡比的历年最小值测算未来年度文化消费需求增长趋势,即假设“回到”并维持原有的文化消费城乡比“最佳状态”不至进一步扩大,作为下一步缩小以至消除城乡差距的基础。如果到2020年上海城乡实现1991年以来三项最佳比例值,同时实现文化消费城乡比最小状态,那么上海城乡人均文化消费应达到17499.65元,年均增长幅度需达到25.36%,为以往20年实际年均增幅的182.62%(省域间目标距离第1位),城乡人均文化消费增长与人均产值增长测算值之间的比例值将上升至6.96%。尽快实现这一测算目标,实属控制文化消费需求城乡差距不再扩大的起码要求,应争取尽快做到。由于上海历年最小城乡比为“城乡倒挂”(见图8中2001年),最小城乡比测算目标距离反而大于弥合城乡比测算目标距离。
(6)消除负相关测算:以1991-2011年间上海城乡人均文化消费与非文消费剩余比例值的历年最佳值测算未来年度文化消费需求增长趋势,即假设文化消费增长不至继续受到“必需积蓄”增长的反向牵制。如果到2020年上海此项比值实现“十五”以来最佳状态,那么城乡人均文化消费应达到21454.31元,即2011-2020年年均增长幅度需达到28.23%,为以往20年实际年均增幅的203.29%(省域间目标距离第7位),城乡人均文化消费增长测算值与上海人均产值增长测算值之间的比例值将上升至8.54%。这是三项“最佳比例值”中的单项差距测算,也是影响上海城乡文化消费需求增长诸因素里最为重要、最为直接的一项单独测算。由于另外两项比例值呈现向好发展趋势,而上海城乡文化消费的“积蓄增长负相关效应”显著,这一单项比例值测算的目标距离反而大于三项比例值测算。
(7)城乡无差距测算:以人均收入、人均非文消费、人均文化消费三项城乡比的无差距理想状态实现最佳比例值测算未来年度文化消费需求增长趋势,即首先假设上海乡村方面各项人均值加速增长逐步与城镇持平,其次取城镇标准保持曾有的三项比例关系“最佳状态”。如果上海乡村人均各项数值增长幅度迅速提升,至2020年各项人均绝对值与城镇水平持平,同时以上海城镇标准保持1991-2011年间三项“最佳比例值”,那么上海城乡人均文化消费应达到21588.00元,年均增幅需达到28.32%,为以往20年实际年均增幅的203.93%(省域间目标距离第1位),城乡人均文化消费增长与人均产值增长测算值之间的比例值将上升至8.59%。这是按照上海城镇总体水平进行测算,属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共享经济发展、民生进步成果的理想假设,属于未来既定努力方向。
如果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把上海“十二五”期间产值年均增长控制在7%,并延续至“十三五”期间,则以上上海城乡文化消费需求人均值增长测算中,与产值演算间接相关的第 (1)、(6)类测算的文化消费绝对值不变,而与产值比将分别增高至11.41%和33.17%;与产值演算直接相关的第 (2)至 (5)和 (7)类测算的文化消费绝对值相应减少,而年均增长幅度 (其实是目标差距)将分别减低至3.60%、6.86%、7.72%、7.81%和10.35%(详见图下注),显然更加容易实现。总量值增长测算与之类似。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不仅经济与环境 (包括资源和能源)的关系要求适当控制GDP增长,而且经济与社会 (包括民生及文化民生)的关系也要求适当控制GDP增长。这正体现出一种应有的发展智慧。
同时,还应该看到,以上海经济 (包括文化生产)增长、社会 (一般民生)发展与文化需求 (文化民生)增进的关系来看,实现“支柱性产业”测算目标并不难,但实现“最佳比例值”、 “弥合城乡比”、 “消除负相关”和“城乡无差距”测算目标却不容易。毫无疑问,与“GDP崇拜”和“文化GDP追逐”相比,增强经济与民生 (包括文化民生)发展的协调性,增强城乡之间发展的协调性,更应当成为科学发展理念之下政府实绩考核的主要指标。
在人均数值增长测算基础上,测算2011-2020年上海城乡文化消费需求总量暨文化产业增长目标见图10,图中同样提供上海城乡文化消费需求总量增长的七类测算结果。总量数值有利于总体把握基于扩大文化消费需求、促进城乡文化共享的上海文化产业发展目标。数据演算是对事实的数理抽象演绎,年度数据链所体现出来的增长走势已经说明了一切。需要补充说明一点,人均数值与总量数值测算在本项研究的演算测评数据库里同步分别完成,由于所依据的基础数据不同 (总量增长会受到人口增长及其分布变化影响),所求取的目标数值不同,其间年均增长幅度演算结果略有差异。

图10 2011-2020年上海城乡文化消费需求总量增长测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