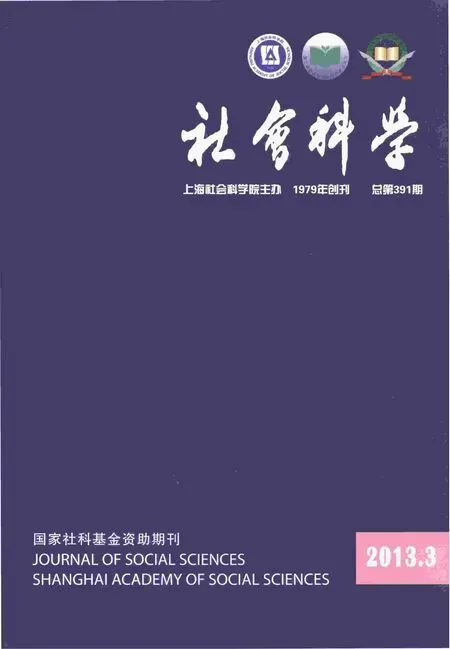哲学基本概念“事物”在中文里应为何义
张 法
一、回到中文的“事物”本身
宇宙之大,物类之众,千差万别,但都被哲学用一个词来表达:事物。事物是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中文的事物,对应于英语的thing。作为中国现代哲学的事物概念,就是在西方thing的影响之下,改变古代汉语的原义而来。高清海对“事物”的界说,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哲学定型后的关于“事物”的经典表述:
对象在现实中既有共性又有差别性。这二者的统一,就构成事物。作为对象的具体性的存在即事物,所以在这一意义上应当说,对象即是事物,事物是对象的进一步的规定。
事物的本质特性,是它的个体性,事物也就是一种具有个体性的确定的存在。
事物这一范畴人们运用得也很广泛,具有多种不同的涵义。在这里必须区分它的两种基本涵义。一种是通常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讲的“物”。这个“物”往往和实物、物体相同,如这张桌子,那幢大楼,这都是事物;至于属于事物的属性和关系的东西,属于观念和思想的东西,便都不包括在这一涵义的事物范畴之内了。另一种是哲学所讲的作为对象的事物。这种意义上的事物极其广泛。凡是构成人们认识对象,包含差别性和统一性的确定的存在,都可以看作是事物。事物与实物、实体的存在不同,它是更抽象因而也就是内容更空泛的一个概念。一个实物可以作为对象,一类实物可以作为对象,属性和关系以及观念的东西也可以作为对象,它们作为确定的认识对象,都可以称为事物。只是在认识进一步深化以后,才能对不同的事物作出更具体的规定,把上述不同事物作为不同对象区别开来①高清海:《哲学体系改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页。。这段话表明了,中国现代哲学中的“事物”变成“物”的偏义复词,只有“物”而没有“事”。这令人深思:“事”为什么会在中国现代哲学“事物”概念中消失?事物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具有怎样的词义?古代的词义与西方的thing有何同异?在认识了事物词义的古今差异、中西差异之后,从哲学的普遍性来讲,应当怎样重新思考汉语哲学中的“事物”概念?
本文的主要任务是回到古代汉语中的“事物”。以此来突破中国现代哲学中事物一词的局限。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事与物是两个词,物用来指实在的东西,事则是物在时空的运动中形成的一个整体。事总是物之事,而物总是在天地大化的运动中。因此物必然有事,事肯定是物之事。二者是统一的。偏重于物的运动与关联,称为事;偏重于运动和联系中的实体,称为物。当二者并重之时,可称之为“事物”。先秦文献《伊文子·大道》用“物”字24次,用“事”字17次,也有1次“事物”合用:“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先秦以下,凡两义并重时,都合用为“事物”。比如,韩愈《送高闲上人序》:“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陆游《孝宗皇帝挽词》:“凝神超事物,观妙极希夷”;朱熹“学者若得胸中义理明,从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应曲当”①《朱子语类》卷一三。。正因为事与物本有内在关联,因此,《诗·大雅·烝民》(“有物有则”)的传,《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的疏,《礼记·哀公问》(孔子对曰“不过于物”)的注,以及《玉篇》等文献,皆把“物”解释为“事”。但物与事除了有交迭的共义之外,更有不同偏重。为了理解二词的同异离合及词义内蕴,须回溯它们的字义起源。
先讲物。《荀子·正名》:“物也者,大共名也。”论述了在万物之众而各有别名的情况下,“物”是对各有别名的万物之共性的抽象。《说文》也说:“物,万物也。”但这一抽象的思路是怎么来的呢?《说文》说“物”字的构成是:“从牛勿声”,即“物”与牛和勿相关。甲骨文中有相当数量“物”字,主要有三种构成,如下:

② 本文中所引古文字皆剪贴自中国古文字网站http://www.chinese etymology.org,并参照相关的甲骨文字典和金文字典。
一是勿上牛下,二是牛右勿左,三是勿右牛左。具体是什么意义呢?《说文》“物”字中对牛构成“物”的意义,讲了两条:一是牛本身的重要性,“牛为大物”(段玉裁注:牛为物之大者,故从牛),二是牛在天相中的重要性而代表天之规律(“天地之数,起于牵牛”)。《说文》强调:牛、理、事,三字同在古音第一部,音韵上的紧密关联后面,正是字义上的相互关联。段玉裁注释说:牛之事是“牛任耕”这一农耕之事。牛中含“理”,正由农耕而生,《庄子》“庖丁解牛”讲“依其天理”,透出了牛与天理的内在关联。事在上古不是一般之事,乃为重大之事,是可以写进“史”中之事,是士 (文化精英)所关注和从事之事 (事、史、士等的关联,后面会详讲)。《说文》又讲,由“牛”而来的“件”就是由牛而来的事理。回到远古,牛之所以重要,在于其为农耕文明出现的代表。反映在意识形态上,文献中的神农、炎帝、蚩尤,都以牛的形象出现,而青铜器中的牛的形象和牛成为饕餮形象的组成构件,都表明了牛与远古文化的根本性质相连,其最后演成为万物的总名,具有深厚的原因。《说文》 “物”条中没有详讲“勿”,但“勿”条中说:“勿,州里所建之旗。”段玉裁注释说《周礼》、《乡射礼》、《士丧礼》都讲了建物 (物即勿即旗)之事。《说文》又说,“勿”字是“象其柄,有三游”。段玉裁注说,古代的旗有多种,从字上,与之相关的有旗、旌、旄、旂、旃、旟、旜、旙、旘、旖、旒、旍、旈、旇、斿、斾、物……这些字的不同在于建者的等级不同,使用的功能不同,从而形成旗的样式不同。游是旗的飘带 (游即飘带)样式之一,而游又有九游、七游、五游、三游之分。勿 (物)这种旗是三游。繁复的区分是文化复杂化之后的发展,最初应是简明而具有象征意义的三游(勿)。甲骨古里有很多“勿”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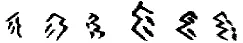
这些勿字,或向左飘,或向右摇,以三游为主。而中国文化中“三”字为圣数,在已经发展的多种游里,三游盖既有旗之一种之意,又有各种旗的概括之义。这样勿 (物)才不仅指旗之一种,而可为旗的总名。《说文》讲旗是由一种专门的帛“襍”做的。因此,勿又表示由多种色而成的“杂色”。《诗经》《周礼》 《释名》及其注疏都有把“物”解释为色 (色彩)之例,特别解释为杂色 (杂色牛、杂色旗……),因此,从视觉 (色)角度突“物”,是古义之一。
《说文》的物、牛、勿,分别讲了牛与勿,但二者的本质关联是什么尚未讲透。徐中书《甲骨文字典》从牛、勿的关联着眼,把勿讲成来自于用耒作用于土之形,进而说因土而与土之色相关①参见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这样,牛与勿,成了牛与土,正好把农耕文化的两大要项关联起来。这个思路是对的,强调土也很重要,但不全面。实际上,勿作为旗,与旗相联的字,大都有方。但方不是一般的土,天圆地方,方代表土的本质 (后来的地坛即为方形),从而方是土中最有象征性之地,是建旗之所在。旗的前身是立杆测影之杆,这个杆也叫中杆,立杆也叫立中,中国的观念由此而生②参见张法《中国美学史》第一章第三节“中:文化核心与审美原则”,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立杆而测影,整个天文现象都由之得出,立中之地是最神圣之地。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中杆是原始文化都曾有的图腾柱或宇宙树。而中国的中杆,与其他文化的不同之处,在于中杆上有游 (勿),是旗帜。中,甲骨文为:

勿是旗帜,与牛一样,是把天的规律和图腾标志结合在一起,把土、牛、帛这三项中国农耕文化最重要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神农、炎帝、蚩尤的“勿” (旗帜),其“游”就应由帛做成,杆旗上应有与牛相关的形象,象征着丰饶的大地。“勿”内容的深厚更在于,根据古代汉语音同义通的原则,勿同巫、同舞、同無。远古社会中,原始仪式是由氏族的领导人 (巫)来主导的,巫举行仪式是以舞 (诗乐舞合一)进行的,仪式的对象是天象,远古之神主要不是直接的天象 (日月星)本身,而是决定具体天象后面的东西,可体悟而难以言传,是無 (中国形而上的天道是以無来描述的,《老子》有“天下万物皆生于有,有生于無”,“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物、無、惚,音意相联)。勿同形而上之無,它是具体现象的否定,又是形上本体的肯定。义合于甲骨文牛下勿上的字形。牛之成为大物,已经不是某一具体的耕牛,而是氏族本质的图腾之牛,不但与农耕社会中土的生殖神力相关,与牛作用于土之后的丰产相关,更与氏族图腾所凝结的整个宇宙的本质相关。巫以牛的形象在原始仪式中的出现,不是牛的原形,而是经过文饰(艺术加工)之后的牛,是兼杂五色内蕴着观念内容的牛,牛作用于土地,农作物的繁盛也是五色缤纷的,而这杂色又经过观念加工 (五色牛、五色旗、五色土),配合着人、社会、宇宙的本质而进行的,物与色相关,物色不仅是某一色,而是天地中色的规律之体现 (刘勰《文心雕龙》有《物色篇》正是此义,其中的“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表达得很准确)。巫在有牛的图象的旗下之舞,正是总结着和建构着与时代的思想相一致的宇宙观念。因此,“物”的内含,作为图腾是万物之源,作为巫师是思想之源,以牛之形象出现的巫,通过在勿 (旗帜)之下仪式之舞,通达形而上的無,都是对宇宙万物的把握和总括,由牛与勿结合而成“物”,在起源上就内含着宇宙的本质,在理性化之后,成为万物的共名,顺理成章。
物作为万物的共名,在于内蕴着万物共有的本质,这一本质在远古社会是图腾、是神、是帝、是天,先秦理性化之后,是道、是天、是气,《庄子》曰:“通天下一气耳。”气是万物的本质,气化流行,产生万物,物亡又复归于宇宙之气。这样中国之物的一个重要特点显示出来,中国的“物”,以“气”为根本,因而在本质上是生命性的(《周易》“天之大德曰生”)。这与西方的thing在本质上是物理性的根本不同。
再来讲“事”。“事”的甲骨文为:

《说文》说:“事,职也。从史、之省声。”这表明“事”包含了两个方面:“史”和“之”。前面讲了甲骨文中“事”与“史”是同一字。远古之时,史巫合一。巫这个字表现了巫在主持仪式之舞的功能,而史则呈现巫的言说和记录,《说文》“史”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这里凝结了历史发展的许多内容。中,前面讲了是中杆。关于“中”,《说文》曰:“中,内也。从口、丨,上下通也。”这里讲了中的两个特点:第一,中杆的形象是丨,丨同时又表示着天上地下的汇通,即人在中杆下的仪式反映了宇宙的规律。第二,口,包含中杆下仪式中的言说 (以诗形式说出的咒语)和中杆下的食味 (中国型的仪式一定是与饮食相关连的,彩陶和青铜都是饮食器皿,而且在仪式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鼎成为夏商周王朝的象征)。“史”不但讲述着在仪式中出现的上下通之事,而且要记录这上下通之事,还要体味着这上下通之事。在历史的演化中,中杆有一系列变化,一方面中杆是旗帜,旗帜是可以移动的,巫 (史)成为持旗之人,中杆由空地之杆,变为台上之杆,再变为宫殿前的华表和宗庙里的牌位。无论仪式在空地、在台坛、在祖庙,“史”都将之作为记录,在记录中不但仪式本身成为一个过程,记录本身也成为一个过程,“史”的记录结果呈现为事,仪式本身和记录本身也呈现为事,因此,史即事。甲骨文中,史即吏,吏是巫的记录功能,巫是吏的行政功能,吏偏于记录,巫则重在做事,事由巫吏产生出来。事用作动词就是做事。仪式本身就是做事。史、吏、事又与士相通,在远古,史和吏都是巫,理性化之后,史就是士。士与王在远古为一字,士就是王、就是巫,三代的礼乐文明,王与士分化,先秦理性化,王成为天的象征者 (天子),士成为知识和行政的承担者,记事和做事都与士联系了起来,《说文》“士”字中的“士,事也。”与“事”字中的“事,职也”可以互注。由人 (士/巫/王)的观察、总结、记录而成为事,由人的行动而形成事。
再来看“之”,《说文》解说道:“之,出也。象艸過屮,枝莖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意思是下面一横是土地,而上面的屮就像艸 (草)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甲骨文的“之”为:

这三个甲骨文都呈现了草生长的动态。“之”字正体现了按照生物的规律向着未来奔去这一动态。草木由无到有、由幼到壮的全过程,就是“事”。段玉裁在对“之”的注释中,归纳了两个特点:一是“训为此”(如“之人”,“之德”);二是引申为“往”。而这正是中国文化中“事”的特点,事由一个个点组成,这就是“此”,但又不停止在某一点上,而要向前发展,这就是“往”。事与史相连,是对宇宙中和社会上的神圣事物 (巫的仪式)的关注,与之相连,是与一般的事 (草的生长)的细察,但在远古文化的互渗中,草木也与人生和神迹紧密相连,《诗经》中用草木起兴的诗,在于草木呈现了与人生相连的内在规律,《楚辞》中的香草美人,直接与主人公的心性、德行、命运相关。更为重要的是,“事”无论是与史相关的仪式,还是与草相关的自然,都体现“事”的中国特点,具有生命性和体味性。
在古代汉语中,物与事,虽然是两个词,但又是可以互训的,因为物总是处在事 (时空和运动)中,而事总包括物在其中,是物之事。面对事物,因着重点不同,而可以用物去表达,也可以用事去表达,物重在个体,而事考虑关联,物重在空间上的定点,事重在时间上的往还,物突出在宇宙之中的客观性,事具有主客相关的互动,因此,对于物,要求的是“格物致知”,对于事,要求的是“实事求是”。对于物与事,看到其统一与看到其差别同样重要。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最为重要的是物与事与宇宙 (即一物与万物,一事与万事)的关联方式。
二、事物之“物”的一面在中国文化中的体现
事物在中文里具有怎样的含义呢?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事物之物,一是事物之事。就物的一面来讲,事物的性质是由宇宙的性质决定的。在中国文化中,宇宙由气构成。《张子·正蒙》曰:“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耳。”气化流行而成万物,气为虚,形为实,宇宙万物皆有虚实合一的结构。《荀子·王制》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意思是万物虽然有物质、植物、动物、人之分,但都有气在其中,都是生命体。《西游记》中孙悟空由石头所化育,为什么石头可以变成猴,猴成精而为人呢,因为石与人一样,都是由气化而来的生命体。这与西方文化把非生命的矿物与有生命的动植从本质上区分开来完全不同。西方的妖魔鬼怪不可能由非生命体所变。在中国文化由虚实合一组成的事物中,人作为宇宙气化的最高级,具有了宇宙之物的典型性。因此,中国文化中个体事物的结构,典型地在人体结构中体现出来。刘邵《人物志》讲人的结构是“含元一【即气】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再进一步细分,可为“九征”: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这里,九征之“征”,既是对象的特征,这特征又是由观者之看而来的。九征之一的气,不是宇宙本质和人的本质之气,而是表现于外的气色。这九征可以进一步分为三类:神与精一类,属神;筋与骨一类,属骨;气、色、仪、容、言一类,属肉。再要简略,则可为形神。因此,人从本质层面,是一个气、阴阳、五行结构,从现象与本质的合一上,是一个神形-神骨肉-九征的结构。面对具体的人,不同的气-阴阳-五行和神形-神骨肉-九征,就会有不同个性之人。比如,从本质结构看,人体的木、火、土、金、水,对应着生理的骨、气、肌、筋、血,相通着性格的弘毅、文理、贞固、勇敢、通徽,还与社会品质的仁、义、礼、信、智相连。一个人属于木、火、土、金、水中的哪一行,在他身上哪一行偏胜,此人的个性就体现出来了。又比如,从现象本质结合的结构看,通过九征中每一征的考查,在神的平陂、精的明暗、筋的勇怯、骨的强弱、气的静躁、色的惨怿、仪的衰正、容的态度、言的缓急上具体是怎样的,再加以综合,此人具体个性就呈现出来了。在本质结构里,木、火、土、金、水都有气在其中,是一个虚实结构,在神形-神骨肉结构中,形和肉骨是实,神是虚,是一个虚实结构。中国宇宙中的万物都是由气化而成,都是生命体。因此,人体的虚实结构可以适用于一切事物。对于自然山水,郭熙《林泉高致》说:“山以水为血脉,在草木为毛发,以云烟为神采。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云烟而秀媚。水以山为面,以亭榭为眉目,以渔樵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渔樵而旷落。此山水之布置也。”这里,神采和精神是虚,血脉、毛发、面、眉目是实,活、华、秀媚、明快、旷落是虚实相生而来的境界。在建筑上,《黄帝宅经》说:“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屋舍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得如斯俨雅,乃为上吉。”这里,身体、血脉、皮肉、毛发、衣服、冠带是实,而由此显出的俨雅是虚。建筑是一个虚实相生的结构。在艺术上,顾恺之说:“四体妍媸,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睹 [眼睛]中。”谢赫评晋明帝画说:“虽略于形色,但颇多神气。”这是从形神而论。张怀瓘论画:“张 (僧繇)得其肉,陆 (探微)得其骨,顾 (恺之)得其神。”这是从神骨肉而论。荆浩《笔法记》说:“笔有四势,谓筋、肉、骨、气”,是多层而论。谢赫六法,除“传移模写”外,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既可为三:气韵、骨法、形色,又可为多:气、韵、骨、形、色、筋。但无论从哪一结构谈,都体现了一种虚实结构。除了自然、居室、艺术,哲学境界也是一种事物,也可以用虚实结构去把握。《五灯会元》讲达摩祖师要离开中土西归,叫弟子讲学佛的体会,道副把自己的心得概括为四句话:“如我所见,不执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达摩说:“你得我皮。”女弟子尼总持说:“我今所解,如喜庆见阿閦佛国,一见更不再见。”达摩说:“你得我肉。”道育说:“四大本空,五蕴非有,而我见处,无一法可得。”达摩说:“你得我骨。”最后慧可上前向达摩施礼,一句话也没有说,然后站到自己的位置上。达摩说:“你得我髓。”然后又看着慧可,对他说道:“以前如来以正法眼付予伽叶大士,一代代相传,到了我这里。今天我传付予你,你要好好护持,一道传你的,还有袈裟,以为法信。”这里的哲学境界,是由皮、肉、骨、髓构成,前三者为实,髓即精髓、神髓,为虚,也是一个虚实结构。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中的个体事物,是一个虚实结构,虽然虚的一面具有本质性,但一定要虚实相生,才成为一个具体的事物。虚实相生的关系,也就是空与实的关系,正如周济《宋四家词选》所讲空与实的关系,他说作词一方面要空,“空则灵气往来”,另一方面要实,“实则精力弥漫”。虚实相生的关系,也就是有无相生的关系。《老子》曰:“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中国文化关于具体事物的独特性和巧妙性正在于,既不只偏于虚,也不只偏于实,而是虚实相生。中国文化的事物之所要讲虚实相生,而且强调虚的重要,气的重要,就是在于面对事物,是不能将其划界隔离开来,而是必须把它放在天地之间进行体悟。但又不是只讲事物之气与宇宙之气的关联,还要重视事物的具体性,看重其“实”的一面。只有既重实也重虚,才能进入中国文化关于事物的“众妙之门”。
在中国文化中,宇宙万物具有独特的分类和结构。《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知北游》云:“通天下一气耳。”这些讲的都是万物分类的总原则。《周礼》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显示了事物分类的基本思路,从天地人的整体性出发进行分类。《周易·系辞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这里整体性分类形成了阴阳-四时-八卦-万物的基本框架。董仲舒《春秋繁露》说“天地之气,合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他把气论、阴阳论、五行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气、阴阳、五行、万物的整体结构。至秦汉以来,各种八卦表和五行表都显示中国文化中事物的分类结构。下面仅以五行表为例:

表1
在表中,竖格形成了西方学科体系的分类,但从横向看,中国事物分类的特点就显现出来了。西方文化中通过划界而把各门学科 (色、声、味、时、位、情感、道德、神话……)区分开来,而中国又加上横格,让这些区分开来的系列又关联起来。正是这一关联,让从西方学科分类看不到的东西呈现了出来。比如,在中医里,如果一个人的眼有病,医生开的药方里有时会出现猪肝二两作为药引,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眼与肝都属木,具有性质上的同一性,又比如,一个人的肝有病,做气功治疗,对着树木做比不对着树木做,效果要好,因为肝属木,与树木有相通性。而眼、肝、木的关联,从竖格上是看不到,只能从横格上显示出来。而横格之间各事物的关联,是实验室里观察分析不出来的,这一关联是虚的,但又带有本质性。因此,中国文化中事物的分类,不但有由竖格体现的“实”的一面,还有由横格体现的“虚”的一面。虚实结合才显出中国文化中事物分类的性质。因为有“实”的一面,中国文化讲究“格物致知”“实事求是”,在训诂、考证方面有类似于西方文化中求“实”的科学精神;因为有“虚”的一面,中国文化要求由实入虚、得意忘言、“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有类似于印度文化中悟“空”的宗教韵致。因为有求实的一面,中国人绝不会像印度人说“四大皆空”那样得出五行皆空的结论,正因为重虚的一面,中国也绝不会像西方人那样面对事物去下一个科学型的定义。中国事物的分类结构是一个虚实相生的结构。
中国文化从先秦开始,就把事物的本原归结为气。宇宙万物,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山河草木,禽虫兽人,皆由气生。与物质和原子是物质性的不同,气是生命性的。与物质性的事物之形成是由实体 (原子)到实体 (事物)不同,气的事物之形成是由虚体 (气)到实体 (事物)。与物质性的事物的生成是由元素到整体不同,气的事物的生成是由整体到元素。与由实体到实体的事物是可分割、可分析的相反,由气到实体的事物在实体层是可分割、可分析的,但到虚体的气则是不可分割、不可分析的。与由原子和实体构成的事物可以与其他事物和宇宙整体分割开来进行研究相反,由气形成的事物不能与其他事物和整个宇宙分割开来进行研究,因为一隔离则气断,气断则物亡。正如中医不高估尸体解剖,人死气绝,本质性的精气神都没了,解剖得出来的知识再精确,也已经不是本质性的知识。因此,在中国文化里,面对事物,由实而虚,由形而神,由质而气,是基本方式;从整体 (精气神在整体之中)看部分,从虚体看实体,是基本方法;抵达可意得而难以言宣的神、情、气、韵是最高境界。
三、事物之“事”的一面在中国文化中的体现
中国文化的气化万物是一个动的宇宙:“天之大德曰生”①《周易》。,“四时行焉,百物生焉”②《论语·阳货》。。事物对事的强调,突出的是物在天地大化中运行。中国文化中的事物,不仅要从物的方面即静的方面理解,同时要从事的方面即动的方面理解。但中国事物的动,不仅是类似于西方实体性的科学公式或历史规律,更重在超越实体性知识的一面。由宇宙之气而来的事物在本质上是气与形的统一。其在天地之间的“运动”,在中文里有独特的含义,“动”与事物的外在之形相关,是看得见的,可以完全认识的;“运”与天地的内在之气相关,是看不见的,不可以完全认识的。因此,运与动是宇宙本质之虚与外在现象之实的虚实相生的关系。同样事物在运动中产生的“变化”,在中文里也有独特含义,“变”是与形相关的看得见的变化,“化”是与气相关的看不见的变化,变与化也是宇宙本质之虚与外在现象之实的虚实相生的关系。因此,事物之事,不但要从运动与变化两个方面理解,还要从运与动、变与化的虚实合一上理解。正因为运动和变化都有虚的一面,因此,“事”既有形的现象层面可以形成名言和定义并进行预测的一面,又有气的本质层面不能形成名言可定义而无法预测的一面。因此,事物在天地中的发展,就客观方面来说,既有见其事的形和实的一面,还“不见其事而见其功”③《荀子·天道》。的神和虚的一面;在主体方面,应胸怀“尽人事,听天命”的态度,能够把握的一面,一定尽力去把握,不能把握的一面,则顺其自然。事物的天地中运行之事的一面,之所以在更深的层面不能把握,在于中国的事物在天地中的运动,不是可以通过实验一点一点把握就能上升到总体,而是天地万物形成一个极为丰富极为复杂的共进互动,从《夏小正》到《月令》把事物在天地间的互动演进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出来。且以《月令》中的孟春为例: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皋,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大簇,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路,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这里天上、地下、动植、人类、鬼神、色、声、味、器等,有一个相当全面的互动,各类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就是在天地全面性的互动中演进的。当只以某一事物,某一视点去看,并不会得出全面的认识。这里各种各样的“事”都是在一个阴阳五行八卦的虚实相生的无形网络中演进的。《荀子·天道》云:“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这里的“得其和”“得其养”,突出的就是一事物与天上地下各类事物在运动和变化中实实虚虚的多样关联和互动。理解了这一个地轴天杼运转不息的宇宙,事物之“事”的一面,“事”的中国性质,才得以彰显。
从天地之间的关联性和整体性上讲事物之事的一面,在其具体性和可把握性上,与三个词相关:事、史、势。凡形成了事,就意味着具有“史”的性质,把具有动态的关联的事,作为一种“原始要终”的史 (历史)来看待。要懂历史,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叙》讲的原则,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呈出“事”的规律性,势则显示“事”的动态性。势,《说文》曰:“盛权力。从力从埶。”《说文·丮部》曰“埶,种也。从坴、丮,持亟种之。”埶与蓺、藝相通,皆指植树。埶,古文字如下:
在远古文化里,树、木、杆,皆内蕴神圣观念。势之种植是与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说,势是在中杆下面拥有权力,这权力来自于天地鬼神,具有一种不可见而可感的威势。藝演化为六艺,六艺在两方面使用:一是诗、书、礼、易、乐,落实为学术文化,强调的是术的一面;二是礼、乐、射、御、书、数,落实为与从政相关的政治技术,更进一步演进为法术势的政治运作。其中,势不但内蕴着与权力相关的政治运作,还抽象为对一般的事的描述,呈出事的动态性。因此,在中国文化里,事、史、势成为事的三个基本项。事把物作为一个整体的时空动态项来予以把握,史则是事里的内在规律性,势是事的鲜活动态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与事相关的词汇,可分为如下:事实:已经发生的之事;事务或事项或事体,是把事作为一个相对整体(一个项或一种务或一种体)来进行;事业或事功,是指示事的正面性质,是一种值得骄傲和荣耀的业或功;事故是已经发生的具有负面性质的事;事端和事变,强调事的发生的突然性;事情和事态:突出事的具体情态和状况;事件,是指事的严重性和重大性;事理是指事之发展的内在规律;事势或形势,突出事的发展趋势,特别强调事中可感觉但难以细划的一种虚体而又确实存在的东西。由事生发出来的各种词汇,虽然把事做了相对的整体把握,如:务、项、件、体……但也不断地突出其虚体性和关联性,如:情、态、变、势……这是具体之事的虚,这具体之虚又与宇宙本质中的“运”和“化”之虚紧密相连。当对“事”作了这样的把握之后,中国的事物所内蕴的事的一面就得到了突出。
四、事物在中国当代哲学中应当进行怎样的新解
中国的事物,如上面所揭示的,第一,是一种生命体 (与西方的物质体不同),第二,是虚实合一体 (与西方的实体性不同),第三,是时空合一体 (与西方的实验室思维而来的界定不同),第四,在天地间互动 (与西方从学科分类思维而来的认识不同)。前两点强调事物之物,后两点强调事物之事。中国的事物,是事中有物,物中有事,可分可合,讲物则事在其中,讲事则物在其中,这就是中国的事物之理,正如程颐所说“物则事也。凡事上穷其理,则无不通”①《程氏遗书》卷十五。。在词的运用上,古人往往互文见义,如程颢的“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②程颢《答横渠先生定性书》。。因此,按照中国的方式去理解事物是重要的,如程颐所讲“至如一物一事虽小,皆有是理”③《程氏遗书》卷十五。,如朱熹所讲“事事物物皆有个道理”④《朱子语类》卷七五。。
西方语言的thing(事物),虽然其词义起源和内蕴特质与中国的事物不同,但也是包含着事与物两个方面,只是在世界现代性的进程中,在与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相伴随的语言变革中,事的一面才大大地被弱化,而且几乎从作为哲学概念的thing中消失。世界现代性进程带来的特征,从正面讲是科学化,首先是用经验态度和实验室方式来对事物,把任何东西都归纳为一个物,是可以到实验室里进行解剖和分析的,然后用理性态度 (所谓科学逻辑)进行整体的归纳。从反面讲是去魅,即从经验态度到实验方式到理性总结,把与西方型的科学-理性-逻辑相反的宗教、玄学以及一切怪力乱神都排斥出去。现代性体现在经济上就的工业化 (由可计量的部件构成的整体),体现在政治上就是民主化 (由可计量的选票筑成的权力)。现代性特征对思维的影响,就是要把动态变成静态,将虚体转成实体,以便进行科学思考。这一思维随着现代性的世界进程而扩大其影响,成为世界范围的哲学思维之特征。中国哲学正是在现代转型中受西方哲学thing的变化之影响而让事物一词中的“事”消失了。然而,当现代性进入到全球化时代,西方开始了对科学型思维的反省,事物这一概念也受此影响而显出了新的变化。在哲学上,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一开头就讲: “1世界是所有发生的事情 (fall/case)。1.1世界是事实(Tatsachen/facts)的总和,而非事物 (Dinge/things)的总和。”①[澳]《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卷,涂纪亮主编,陈启伟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括号中的词为德文原文和英文译文。“事物”这一概念被更精确的“事实”和“事情”所代替。怀特海反对近代思想把“静止的时空和物理的形式秩序的必然性的心照不宣的假定”②[美]怀特海:《思想与方式》,韩东晖、李红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要求思维的中心从物理性和元素论转到有机性和整体论,并把有机论和整体论强调的时间和过程引入到对事物的思考中,他说:“过程对于实存是基本的……个体单元就必须被描述为过程。”③[美]怀特海:《思想与方式》,韩东晖、李红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每一种实际存在物本身只能被描述为一种过程,它在微观世界中重复着宏观世界中的宇宙。它是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过程,每一种状态都是其后继者向有关事物的完成继续前进的实在基础。每一实际存在物在其构成中都承载着其条件为何是这种条件的‘根据’。这些‘根据’是为它而客观化的其它存在物。”④[美]怀特海:《过程与实在》,杨富斌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392页。正是在这种新的氛围中,艾布拉姆斯的书Doing Things with Texts里的“thing”就只宜释成“事”,中译本确实译为《以文行事》。语言哲学上的言语行为理论和文学理论中的述行理论,都是把言语和文本当作一个投进时空中进行互动的因素来研究,总之是要让事物动起来,极大地突出thing作为“事”的特征。
理解了事物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内容,感受到西方哲学thing的新变化,对于中国现代哲学的事物概念仍然是有物而无事的现状,是到了可以进行思考,并予以改正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