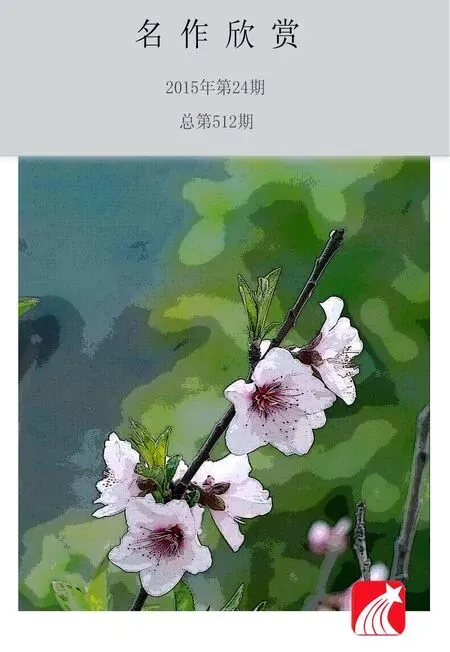“弄”出的境界:张先《天仙子》新探
⊙江合友[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石家庄 050024]
张先词《天仙子》是公认的宋词名作,其中“云破月来花弄影”一句,历来脍炙人口,宋代吴曾即有“往往以为古今绝唱”(《能改斋漫录》卷八)之说。清代沈雄《古今词话·词评》引《乐府纪闻》:
客谓子野曰,人咸目公为“张三中”,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也。子野曰:何不谓之“张三影”?客不喻。子野曰:“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坠飞絮无影”。此平生得意者。①
可见此句是张先本人甚为得意的作品,自推为代表作。对此句意蕴和艺术特点,历代词家各有诠解,但迄今为止,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评价最为著名:“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然而王氏点到为止,未曾详为解说。沈祖先生同意王氏之论,说:“他不注意‘影’字而注意‘弄’字,很有见解。”②但也没有更多解释。王国维评论此句的同时,还提及宋祁《玉楼春》:“‘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人间词话》)从这一语境推测,王氏似在推许其下字之妙,锤炼之工。有人认为“弄”字使用了拟人的修辞,将繁复而富于动态的夜景写得鲜活自然。同样的意思,古人早有提及。如明人杨慎欣赏其写景的鲜活:“‘云破月来花弄影’,景物如画,画亦不能至此。”(《评点草堂诗余》卷三)沈际飞强调其情和景的自然天成:“心与景会,落笔即是,着意即非。”(《草堂诗余正集》卷二)清代的李渔又表彰其琢句炼字的新奇:“‘云破月来’句,词极尖新,而实为理之所有。”(《窥词管见》)当然,这些观点对于理解“云破月来”一句的妙处颇有裨益,但是仍然略嫌皮相,孤立阐说,停留在印象批评的层次,既没能与整首词的篇意建立联系,也没有结合张先的人生体验。
要想准确理解“云破月来花弄影”这一句的妙处,必须顾及全篇,《天仙子》词前小序曰:“时为嘉禾小 ,以病眠,不赴府会。”词作正文如下: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首先要重视词前的题序。沈祖 先生对此有过关注:“词中所写情事,与题很不相干。此题可能是时人偶记词乃何时何地所作,被误认为词题,传了下来。”③沈先生否定了题序的意义,推测它与作者的关系仅在于表明时地,依据在于词的内容与题序“很不相干”。这个判断本身存在问题,因为张先传世的165首词中有70余首使用了题序,从数量上看相当可观,多用题序是张先填词的特点之一,没有充分的理据证明《天仙子》的题序是“时人”所加。所以,在缺乏有力的反证之前,应当认定题序乃张先本人所加。沈祖 先生归纳词的主旨为“临老伤春”,通过题序,可以进而认为,词中情感不是泛泛抒发“临老伤春”之情,而是浸透了张先的独特人生感受。也就是说,这首词所抒发的感情是从个人情怀出发的,而非泛泛的“临老伤春”之作。张先作嘉禾(秀州的别称)通判的时间,约在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这一年他52岁。通判是知州的佐官,在北宋“掌 贰郡政,与长吏分礼”(马端临《文献通考》),号称“监州”。一般地说,通判官阶不算很低,但从题序“小 ”的称谓,则可看出其嗟叹官卑之意。仁宗天圣八年(1030),张先考中进士时已年届不惑,宦海沉浮十余年之后,年纪老大,还仅是地方上的佐官,难以有大的政治作为。韶年不再,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思之念之,一种无奈而又伤感的情绪就涌上心头。再加上“病眠”,年老而体衰,虽不至于如韩愈《祭十二郎文》所叹“年未四十,而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却一定更增添无法实现人生志向的痛苦。题序奠定了词的抒情基调,一个在病中的老人感慨青春逝去,人生理想与自己正渐行渐远。
首句“[水调]数声持酒听”就已表达了哀伤之情,目前这一点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如沈祖 先生说:“持酒听歌,本是当时士大夫享乐生活的一部分。可是,这位听歌的人所获得的不是乐,而是愁。”④这是从下一句“愁未醒”推知的,从享乐中体会到愁苦,当然也可说通,却不够准确。前一句“享乐”和后一句“愁”似乎反差太大。音乐之所以能感动人心,与其旋律的悲喜有关。晏殊《浣溪沙》起句“一曲新词酒一杯”并未明言所听何曲,曲情本身并不重要,人情和体悟才是表达的重心,这与词中淡淡的哀愁以及闲雅的怀抱是相适应的。张先强调所听的是[水调],则曲情和人情之间必有深深的契合。那么[水调]的曲情是怎样的呢?明胡震亨《唐音癸 》:“《脞说》:[水调][河传],隋炀帝幸江都时所制,曲成奏之,声韵怨切。”又王奕清等《钦定词谱》卷四十:“其第五叠五言,声调最为怨切。”因此[水调]本就是“怨切”之乐,白居易有诗可以印证:“五言一遍最殷勤,调少情多似有因。不会当时翻曲意,此声肠断为何人。”(《听歌六绝句·水调》)这一曲情在北宋得以保留,贺铸《罗敷歌》(即《采桑子》)云:“谁家[水调]声声怨?”基于此,前两句不是转折关系,而是顺承关系。听着怨切的乐曲,借酒消愁,可惜酒淡愁浓,即便颓然就醉,醒来愁绪依旧。音乐作为写抒情主体白昼情事的背景,已渲染出了深沉、执著的愁绪氛围。年老而沉沦下潦,张先的愁是激切的,力度很强,与少年即得志的晏殊有显著差别。
整个上片叙述了这样一个时间流程:暮春的上午,抒情主体伤春之情郁结,听悲歌,喝闷酒,终于醉倒,下午醒来,愁怀依旧,于是黄昏揽镜自照,看到镜中苍老的容颜,韶华已经永远逝去,只是留存在记忆之中,任凭自己徒然凭吊。“送春春去几时回”与“夕阳西下几时回”(晏殊《浣溪沙》)异曲同工。区别在于,“夕阳”句乃是对时序流转不息的叹惋,而“送春”句则强调美好时节的一去不返,不舍以至于相送,殷勤询问能否回转,都在暗中切合抒情主体垂老无成的心境。“临晚镜。伤流景”化用唐诗,杜牧《代吴兴妓春初寄薛军事》:“自悲临晓镜,谁与惜流年。”这里“晓镜”改成“晚镜”,一字之差,却在抒情向度上完全不同。杜牧诗代人抒情,主人公是女子,故晨起照镜;张先词乃直抒胸臆,主人公是男子,故日暮照镜。追惜流逝的光阴,暮春伤怀,原是艳情词中表现相思别恨的常见模式,这里张先用以表现士大夫的人生慨叹,从艳情的写作套路中来,又超越并改变其意指,从而达到雅化的目的。上片末句“空”是个否定意味很强的字,与前面的“未”字遥相呼应。“记省”往事的意义被“空”所否定,那么青春永逝的悲伤就无法忘怀,也即“愁未醒”。“几时”表达对“回”之确定性的疑虑,也就是送走了的“春”难以回来。上片各句之间构成紧密的意义整体,在否定性的意指中完成抒情主体的情绪宣泄,即对现实人生处境的不满和伤感。
下片的表层意义是描摹景物,从暮色中的“沙上并禽”,一直写到夜深入户、风狂人静,而其深层语义则在象喻上片所抒发的深沉愁绪。“云破月来花弄影”是全片乃至全篇的中心,生动如绘,深刻感人。杨慎所谓“景色如画”,这一特点沈祖 先生说得十分透辟:“其好处在于‘破’‘弄’两字,下得极其生动细致。天上,云在流;地下,花影在动,都暗示有风,为以下‘遮灯’‘满径’埋下伏线。”⑤而其中所蕴含的隐微之“情”却未得到阐说。王国维所谓“弄”字使境界全出,境界是什么呢?又如何理解这一句?《人间词话》云:“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可以认为,王国维是从情景融汇的角度去理解“弄”字的。张先将最真切的感情倾注在“弄”字之上,使得整句、整片乃至整篇的意蕴得以升华。“云破月来”表明这是一个有月但多云的晚上,因此月亮光华洒下的瞬间让人感觉那么弥足珍贵。“花”在片刻间突然显出她的美丽,但这是怎样的“花”呢?从篇末“落红应满径”可以推知,是枝头已不再容光焕发的“残花”。她的命运是必然凋落枝头,而且后文“风不定”也揭示了她被正遭遇“催逼”的处境。但她有无限的依恋,不忍离去;她无比珍爱自己残存的美丽,还要展示一番。月光洒落的刹那,她在枝头随风摆动,“弄”影于地,顾影自怜,自伤命薄。然而风雨无情,伴随春天离去的脚步,她即将飘零,成为覆径的落红!“残花”有情,已令读者动容;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病弱老人的眼中,惺惺相惜,同病相怜,他的心中有着难言的痛楚!此刻的他就如同这“残花”一般,命运无情,人生偃蹇,而老之将至。“弄”影的“残花”与“临晚镜”而“伤流景”的他何其相似!抒情主体的愁情与“残花”弄影之态形成鲜活且紧密的同构关系,互相生发,从而感人至深。这样就恰到好处地沟通了上片之情和下片之景,使全篇成为一个艺术整体。
换头一句中的“并禽”意象在抒发相思别恨的艳情词中很常见,用于揭示抒情主体的孤独寂寞,如温庭筠《菩萨蛮》“双双金鹧鸪”便是。与上片“临晚镜”一句相同,张先在此也袭用了艳情词常用的书写模式。沈祖先生认为“并禽”是“用以对照自己的块然独处”⑥,极为恰切。下片从一开始就营造了“幽独”的情境,所写的景物、行为、意念均发生在静谧无人的空间里,抒情主体与外在自然的交流是自由的、不受干扰的。同时其情愫是纯个人的,难以直言叙说,不为旁人所理解的。接下来“弄影”的场景是他与“残花”之间的对话,隐微之情得以外显。“重重帘幕密遮灯”极写“风”之横暴,对“残花”命运之关切溢于言表,已然是残损不堪,又兼狂风催送!末句推想“明日落红”,看似淡淡写来,然而经过前面的铺垫,已蕴含了深厚的情意。“满”是力度很强的字,“满径”的落红,就是满目的凋伤!曾经“弄影”的“残花”,多么美丽,那么多情,抒情主体无比珍爱和怜惜啊,终于还是要被狂风吹落!从结构上说,这一句呼应了上片“送春”一句,万花凋零,春天无可挽回地离去了。
王国维认为“弄”字使“境界全出”自然是称赏其炼字精工、修辞恰当、摹写如绘等优点,但“弄”字的更可贵之处在于切合抒情主体所要抒发的真情实感,并把它细腻婉转地表现出来。结合题序,联系上下文,可以发现“弄”字处于全篇的中心位置,是“词眼”。这一个“弄”字,真正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使情和景水乳交融,振起了全篇,不唯神采飞动,亦且感动人心。由此我们认识到,细读并赏析词作,首先必须知人论世,了解作者或抒情主体的身份和人生体验,从而超越印象化阐说的层次,确定并落实其抒情指向;其次是名句的审美最好要顾及全篇,以免孤立分析,仅能得到片面或模糊的观感,而不能充分体味其精微和深刻之处。
①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81页。
②③④⑤⑥ 沈祖 :《宋词赏析》,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8页,第16页,第16页,第17页,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