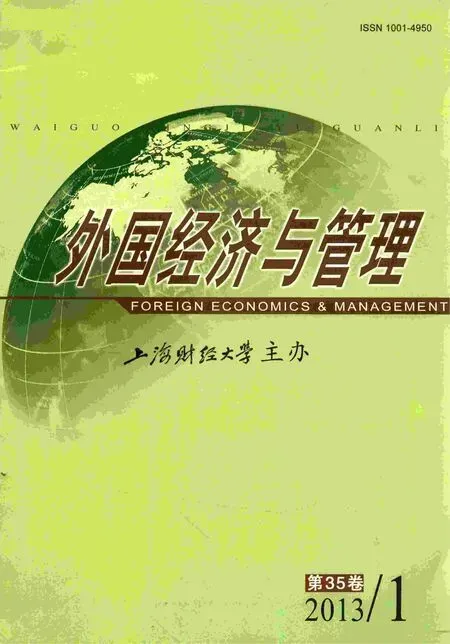悖论视角下的领导者—追随者契合研究探析
张军成,凌文辁
(暨南大学 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一、引 言
在当代经济与商务环境中,产品和技术更新速度越来越快,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深,企业在充分享受经济发展所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生存和发展方面的严峻挑战。企业要想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并维持竞争优势,必须在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各个方面均有卓越的表现。其中,领导作为一项重要主题,历来都是组织管理研究者密切关注的热点(Morrison,2010)。综观既有文献,领导研究先后经历了领导者中心视角(leader-centric perspectives)和追随者中心视角(followercentric perspectives)的研究潮流(Meindl,1995),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近年来研究者也逐渐意识到,在领导研究中单方面地只重视领导者或追随者都是不完整的,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对领导过程的理解过分简化,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和启示(Küpers和 Weibler,2008)。为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把领导概念化为分散在领导者和追随者等特定社会系统成员之间的一个更广泛的过程(如 Gemmil和 Oakley,1992;Gronn,2002;Collinson,2005;Bedeian 和 Hunt,2006;Uhl-Bien等,2007)。如此一来,从领导者—追随者契合(correspondence)①出发探讨领导问题,渐渐成为微观组织行为领域领导研究的一个前沿和热点。
领导者—追随者契合研究与过去几十年备受组织行为研究者关注的一致性(congruence)或匹配(fit)研究颇有渊源。就理论源头而言,个人—环境匹配、个人—工作匹配、个人—主管匹配等主题的研究基本都可以追溯到B=f(P,E)这个基本公式,即个体的行为是个体本身与其所处环境的函数。尽管上述基本公式隐含着发展意味(Tinsley,2000),但既有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着眼于匹配双方相对稳定的方面,例如个人特质与环境特征,很少涉及可能发展变化的行为。这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当涉及具有高度主观能动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匹配(如个人—主管匹配)时,研究的全面性将有所欠缺。而源于对动态组织环境的关注而发展起来的悖论理论(theory of paradox)(Smith和Lewis,2011)能够进一步拓展和丰富匹配研究的内容体系。具体到领导研究领域,它为从领导者和追随者双方动态契合的角度探讨领导相关问题提供了更加合宜的理论基础。然而,在悖论视角下探讨领导者—追随者契合问题,仍存在一些理论方面的困惑;并且,从悖论视角看待领导者—追随者契合,往往要关注对偶双方在特征和行为方面任意水平组合的情形,从而在实证分析策略方面向相关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鉴于领导者—追随者契合研究的发展历时不长,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悖论理论尚未成熟,相关研究在理论和实证方面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本文将从理论基础、研究范例和实证分析策略三个方面分别对现有研究进行述评,最后对该领域研究进行总结与展望,希望能够为感兴趣的研究者提供参考。
二、管理研究中的悖论理论
悖论原本是哲学范畴的一个术语,但近年来它已经引起国际管理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Smith和Lewis(2011)对12种国际权威管理学期刊过去20年刊发的论文进行调查后发现,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采用悖论理论来探讨个人、群体和组织等多个分析层次的众多组织现象。在他们所调查的期刊中,关注组织悖论的文章多达360篇,文章数量平均每年增加10%。之所以出现这样一股潮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代组织的复杂性、多元化和动态性等特征越来越明显,导致西方传统管理理论中的“要么/或者”(either/or)思维面临过度简化管理实践和要求的风险,因此相关研究和实践迫切需要一种更加全面和系统的理论思想的指导(Lewis,2000)。在此背景下,管理研究中的悖论理论应运而生,它能指导研究者超越过分简化和极化的观念,充分意识到组织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模糊性(Cameron和 Quinn,1988),并为其研究提供合宜的应对思路。
然而,虽然管理研究对悖论议题的关注已有较长历史,但管理学界对悖论的界定依然莫衷一是,它与两难(dilemma)和辩证(dialectic)等概念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具体来看,悖论是指“同时且持久存在的、相互矛盾但又相互关联的一组成分”(Smith和 Lewis,2011),其显著特征可以通过图1a所示的道家阴阳鱼图形加以描绘:图中A和B被中间的分界线隔开,说明它们是相互区别甚至相互对立的两个成分;同时,外部的边界又把A和B包含在同一个圆中,说明它们同属于一个更大的系统,形成一个整体;A和B首尾相接,并且各自又都包含少量对方的某些元素,说明两者在同一个系统中具有相互协同、相互联系甚至相互转化的动态关系。两难的特征可以通过图1b所示的天平加以描绘:图中A和B分别具有明显的优势或劣势,除非特别声明,否则它们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不存在相互协同。辩证的特征可以通过图1c所示的图形加以描绘:原本相互矛盾的A和B可以合并形成同时具备它们各自部分特征的C,与此同时,代表对A和B各自特征不同偏好的D将出现,并且D与C也是相互矛盾的。事实上,如果能证明两难和辩证中相互对立的A和B在时间上存在持久的相互关联,它们也可能具有悖论的属性(Lewis,2000);然而,两难和辩证中相互对立的A和B从本质上说泾渭分明,并不存在一个更大的系统把它们约束在一个长期动态协同的整体当中(Smith和Lewis,2011)。

图1 组织管理中三种对立的区分
鉴于悖论、两难和辩证存在较大的区别,它们对管理研究的启示也各不相同。例如,组织的探索与开发两种策略常常为获取组织资源而竞争(Gupta等,2006),悖论、两难和辩证视角对此存在不同的思路(Smith和Lewis,2011):起初,研究者和管理者从两难视角看待探索与开发,试图在不同时期或机构执行上述两项活动之一;与两难视角非此即彼的思路不同,辩证视角认为探索与开发可能促使新旧两种观点、技能和策略融为一体,融合的结果代表了对探索与开发不同程度的偏好;而悖论视角则认为,整个组织的成功同时取决于探索与开发,虽然它们在短期内为获取组织资源而竞争,但却相互强化进而促成组织的长期成功。两难视角实质上体现的是“要么/或者”思维,意味着在一定的时间或空间条件下存在最合宜的一种做法。而辩证和悖论视角都强调因应不同情况和条件而协同,区别在于前者并未体现时间持久特征,并且具体对每一个对立面的重视程度不够。因此,在复杂、多元和动态情境下,悖论视角能够给出比两难和辩证视角更加全面、系统的管理启示。
事实上,悖论理论与当代广为接受的权变理论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它对权变理论形成了有效的补充。权变理论目前仍是解决组织对立问题的主导理论,它认为组织管理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境和条件权宜应变,制定合宜的管理决策(Luthans和Stewart,1977)。在面对上述探索与开发两种对立的策略时,权变理论的观点可能是:在追求短期效率的情况下,开发比探索更有效;在追求长远创新的情况下,探索比开发更有效。换言之,权变理论通常分别考虑对立双方,然后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更合宜的一方。这就决定了,权变理论所能解决的问题大多局限于较短的时间范围,并且可能发生变化的情境变量较少,各项因素变动不大(Tosi和Slocum,1984)。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经济与商业环境快速变化,组织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内部组织过程日益复杂,组织管理中的对立要求也变得日益突出和持久(Lewis,2000)。在这种背景下,允许多个情境变量在较长时间范围内动态变化的悖论理论就成为理解和引领当代组织研究的一个关键理论,它对权变理论形成了有效的补充(Smith和Lewis,2011)。最后,需要明确的是,权变理论和悖论理论各有特点(参见表1),解决一个涉及时间较短,涉及情境因素较简单且变化不大的问题,权变理论相当有效,而在处理涉及复杂情境因素且持久动态变化的问题时,悖论理论则比权变理论更有效(Smith和Lewis,2011)。

表1 权变理论与悖论理论比较
三、悖论视角下的领导者—追随者契合研究
与权变理论能够广泛应用于各个组织管理研究领域从而形成组织结构权变理论、人性权变理论和领导权变理论等主要理论类似,悖论理论也可以应用于包括领导研究在内的多个组织管理研究领域。在领导过程中,领导者和追随者分别归属于不同的群体,因此也有着不同甚至有时对立的利益诉求。但从完整的领导过程来看,领导者和追随者都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之间良好的协调与配合是领导活动取得成效的关键。按照Smith和Lewis(2011)对悖论的界定,一组元素要能形成悖论,就必须同时持久存在,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关联。不难看出,领导者—追随者对偶中的双方同时持久存在,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关联,因此我们可以借鉴悖论思想来探讨领导者—追随者双向契合相关问题。
悖论视角下领导者—追随者契合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方向是,同时考虑领导者和追随者双方的人格特质对相关结果变量的个别和联合影响。其中一个典型范例是,Zhang等(2012)在其新近一项研究中,对领导者和追随者双方前瞻性人格的一致性与工作结果之间关系的探讨。前瞻性人格是指个体主动采取行动来影响自身所处环境的一种持久行为倾向(Bateman和Crant,1993)。在同时探讨领导者—追随者对偶双方的前瞻性人格时,很容易出现“主动悖论”(initiative paradox):就领导者而言,尽管他们可能开诚布公地鼓励员工积极主动,但当员工挑战既有公认做法时,他们又可能视之为威胁(Campbell,2000);就追随者而言,尽管他们可能积极支持和实施建设性变革并寻求改进,但当领导者持不同观点时,他们的积极主动将遭受质疑(Frese和Fay,2001)。因此,单方面强调领导者或追随者的前瞻性人格并不能确保领导过程取得理想的结果。然而,以往相关研究却大多单方面探讨员工前瞻性人格对工作结果的影响,认为员工前瞻性人格对其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有着正向影响(如Thompson,2005;Li等,2010)。该类研究忽略了领导者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而悖论视角允许研究者同时关注领导者和追随者双方前瞻性人格对相关结果变量的个别和联合影响,这一点可以从Zhang等(2012)运用结合响应面(response surface)分析的多项式回归(polynomial regression)方法探讨领导者—追随者双方前瞻性人格的一致性对员工工作满意、情感承诺和工作绩效等结果变量影响的研究得到佐证。该研究不仅对既有前瞻性人格相关研究进行了更加合理的拓展,而且从悖论视角开展领导者—追随者契合研究也更加贴近领导过程的真实情境。
与上述从人格特质出发的取向不同,悖论视角下的领导者—追随者契合研究也可以把领导者和追随者双方的行为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探讨它们对相关结果变量的个别和联合影响。现有的一个典型范例是DeRue和Ashford(2010)对领导者身份(leader identity)和追随者身份(follower identity)索要(claim)与授予(grant)行为分析框架的构建。在以往悖论视角的研究中,与身份有关的归属悖论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这些学者认为,组织中存在不少既相互对立又共同存在的角色或身份,从而导致组织成员在想要归属自己的身份时,以及身份归属不同的成员之间,都可能面临矛盾或对立局面(如Pratt和Foreman,2000;Fiol,2002)。具体到领导情境,传统观点认为,领导者和追随者是领导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两种身份,它们在领导活动持续期间同时存在。在包含个体A和个体B的领导情境中,假设双方都持有阶层式领导结构图式(Gemmill和Oakley,1992),即认为在该情境中只有唯一的领导者,并且领导者身份与追随者身份相互排斥,那么,如果A和B同时索要领导者身份或者追随者身份,他们就无法形成和谐的领导者—追随者关系;如果A为自己索要领导者身份而把追随者身份授予B,同时B为自己索要追随者身份而把领导者身份授予A,或者B为自己索要领导者身份而把追随者身份授予A,同时A为自己索要追随者身份而把领导者身份授予B,则他们之间就能够形成和谐的领导者—追随者关系(DeRue和Ashford,2010)。换言之,为自己索要某种身份就意味着把对立身份授予对方,而把某种身份授予对方就意味着为自己索要对立身份。DeRue和Ashford(2010)构建的上述分析框架同时从领导者和追随者两个方面出发,从悖论视角创造性地阐释了身份索要和授予行为随时间动态展开,从而使得领导者—追随者关系通过个体内化、关系认可和集体赞同在群体当中得到明确与接受的过程。该分析框架充分体现了悖论视角的特征,丰富了基于身份的领导研究理论体系(如Van Knippenberg和 Hogg,2003;Van Knippenberg和 Van Knippenberg,2004),对领导概念及领导关系发展等领域的研究进行了拓展,有望促进分布式领导和共享式领导等新型领导理论的发展,并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不管是人格特质取向还是行为取向,领导者—追随者契合研究均要求在对偶层次上进行探讨,这也正是悖论视角下领导研究的一项重要特征。Zhang等(2012)的研究与既有的有关领导者与追随者价值观(如Kristof-Brown等,2005)等方面匹配的研究似乎区别不大,但他们的研究涉及潜在对立的“主动悖论”(Campbell,2000;Frese和Fay,2001),这在以往的匹配研究中并不多见。然而,由于悖论视角追求对立面之间的协调或匹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悖论视角下人格特质取向的研究与既有匹配研究区别不明显,可以相互借鉴。而行为取向则是以往匹配研究较少涉及的,尽管匹配研究的基本逻辑也涉及发展过程(Tinsley,2000),但行为契合在以往研究中依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而源于对动态组织环境的关注而发展起来的悖论理论有望为探讨领导者—追随者对偶双方动态行为之间的契合提供有价值的指导,从而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传统匹配研究的内容体系。
四、领导者—追随者契合研究的实证分析策略
在悖论视角下,领导研究者同时关注领导者—追随者对偶双方各自的特质或行为,这些特质或行为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最终决定领导者—追随者对偶层面的结果。换言之,领导者特质与追随者特质,或领导者行为与追随者行为不同水平的组合,可能导致对偶层面的不同结果。从数学意义上说,对偶层面的结果是领导者和追随者双方特质或行为的连续函数,这对相关研究在实证分析方面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鉴于悖论视角下领导者—追随者契合研究与匹配研究或一致性研究的渊源,可以借鉴匹配研究或一致性研究领域由Edwards和Parry(1993)提出的与响应面相结合的多项式回归方法来展开悖论视角下的领导者—追随者契合研究。多项式回归方法由于能够克服以往常用的差异分数法存在的众多问题,因此自引入以来已迅速成为个人—工作、个人—组织、个人—团队、个人—主管等领域匹配研究所使用的主流方法。该方法所依赖的基本回归方程是这样一个二次多项式:Z=b0+b1X+b2Y+b3X2+b4XY+b5Y2+e,其中,Z为因变量,X、Y为自变量,e为误差项。单就该回归方程而言,并不能清晰地体现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但运用计算机软件可以方便地根据回归系数绘制反映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关系的三维曲面——响应面,从而直观地描绘出一对自变量各自任意水平组合的相应结果。因此,与响应面相结合的多项式回归方法,不仅适用于传统匹配研究,也能满足悖论视角在实证分析方面对领导者—追随者契合研究的要求。
事实上,Zhang等(2012)的研究就使用了这种方法来探讨领导者—追随者双方前瞻性人格对员工工作满意、情感承诺和工作绩效等结果变量的联合影响。以其中领导者和追随者前瞻性人格对领导—成员交换关系质量的影响研究为例②,其得到的多项式回归方程为:Z=5.28+0.33X+0.15Y-0.04X2+0.73XY+0.16Y2。根 据Zhang等(2012)的上述回归分析结果,运用Mathematica 8软件可绘得如图2所示的响应面。在图2所示的水平面上,沿左后角到右前角的对角线表示领导者和追随者双方前瞻性人格一致,另一对角线则表示两者不一致。由图2所示的曲面可以看出:(1)曲面沿不一致的对角线呈倒U形,说明领导者和追随者双方在前瞻性人格方面的得分只要任意一方高于对方,领导—成员交换关系质量就随双方前瞻性人格差异的增大而变差,亦即前瞻性人格一致能促成良好的交换关系。(2)曲面沿一致的对角线呈U形,并且曲面沿该对角线往左上升更快,且取值略高于右方对应情形,这又进一步说明,领导者和追随者双方前瞻性人格得分在不同水平取得一致对交换关系质量的影响也相应有所区别,具体表现为双方前瞻性人格得分同时较高时交换关系质量更佳。(3)曲面实质上还反映了领导—成员交换关系质量在双方前瞻性人格任意水平组合时的具体情况。相比传统差异分数方法回归方程Z=b0+b1|X-Y|+e只提供描述两个自变量一致性与结果变量间线性关系的少量信息,结合响应面分析的多项式回归方法无疑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图2 响应面示例
然而,尽管上述方法在执行回归分析和绘制响应面方面并不存在多大困难,但为了全面把握响应面的特征,需要进行多项繁杂的基于多项式回归系数的计算③。并且除了响应面沿两个自变量一致(Y=X)和不一致(Y=-X)所对应两条直线的斜率和曲率以外,其余各个特征在数值上对应的标准误均涉及回归系数的非线性组合,需要用jackknife、bootstrap和delta等非参数程序计算它们的标准误,从而给响应面特征指标的显著性检验造成较大的不便(Edward和Parry,1993)。所幸Shanock等人(2010)在其文章附录中提供的基于SPSS和Excel两个软件的操作示例,为完成上述计算工作提供了比较简捷的指南。
另外,在响应面分析方面,悖论视角下的领导者—追随者契合研究与传统匹配研究对响应面特征的关注点略有差异。在传统匹配研究中,研究者通常关心的是两个自变量在数量上相等时的图形特征,理想结果是响应面极值点在自变量平面上的投影与直线Y=X重合,其在分析上对Y=X和Y=-X这两条直线比较感兴趣。而在悖论视角下的领导者—追随者契合研究中,研究者关心的是响应面在何处取得最大值,理想结果并不必然出现在Y=X的时候,X和Y任意水平的组合都可能导致结果变量取得最大值,其在分析上对代表X和Y组合的任意一个点都予以关注。换言之,悖论视角下领导者—追随者契合研究对实证分析提出了更复杂、更精细的要求,而与响应面相结合的多项式回归方法无疑是一种较好的解决方案。
此外,与一致性研究的情况类似,包含潜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能够克服多项式回归关于变量不存在测量误差这项内隐假设限制(Edward和Parry,1993),也可以应用于悖论视角下的领导者—追随者契合研究。
在一致性研究方面,结构方程模型的一项新近应用是由Cheung(2009)构建的潜变量一致性模型 (latent congruence model,LCM)。该模 型把所关注的两个变量当作一阶因子,这些一阶因子在旨在代表一致性(即差值)和水平(即均值)的二阶因子上具有固定的载荷(参见图3a)。潜变量一致性模型通过把所关注的两个变量分别设定为具有多个指标的潜变量,把测量误差纳入考虑范围。从测量的角度来看,潜变量一致性模型考虑了测量误差,从而能够避免多项式回归中可能存在的估计系数偏差问题,进而能够避免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无疑是一致性研究在实证方法方面的一大进步。然而,实质上,使用潜变量一致性模型却又是一种退步,这是因为:(1)一致性研究的基本假设认为,一致性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是曲线的(Edwards,1994),但潜变量一致性模型却被局限于线性关系,无法解决一致性研究中处于核心的曲线关系;(2)潜变量一致性模型把关注点从原本应该受到关注的变量转移到其差值和均值,因此会掩盖每个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具体关系,并且还重新带来了多项式回归方法原本想要解决的与差异分数有关的其他众多问题,因此可能产生误导或导致不正确的解释(Edwards,2009)。
针对潜变量一致性模型的不足和缺陷,Edwards(2009)提出用以自变量本身代替其差值和均值的线性结构方程模型来加以改进(参见图3b)。对比图3a所示的潜变量一致性模型,Edwards(2009)的修正模型(参见图3b)能够通过直接求解得到各个自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影响,从而避免潜变量一致性模型容易混淆和掩盖每个成分与结果变量之间具体关系的问题。然而,与潜变量一致性模型相同,Edwards(2009)的修正模型从本质上说仍然是线性的,无法解决一致性研究中的曲线关系这个核心问题。
由于在悖论视角下的领导者—追随者契合研究中,领导者和追随者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其各自的特质和行为都可能共同影响对偶层面的结果(例如,领导者—追随者关系质量和领导过程的有效性等),因此,相关研究在实证分析策略方面,可以借鉴以往匹配和一致性研究所使用的多项式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然而,由前文的分析不难看出,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前者虽能很好地解决曲线关系问题,但未考虑测量误差问题,因此可能得到有偏差的系数估计值,从而导致错误的结论;后者虽然解决了测量误差问题,但却无法解决一致性研究中的曲线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并且早期的潜变量一致性模型还存在掩盖各个成分与结果变量之间具体关系的问题。因此,把多项式回归方法中典型的二次方关系转化到结构方程模型中,再结合响应面分析技术(Edwards,2009),有望为悖论视角下的领导者—追随者契合研究提供更好的实证分析方案。

图3 一致性研究中的线性结构方程模型示意图④
五、总结与展望
在当代动态、复杂的商务环境中,因应组织内外悖论式对立要求而发展起来的悖论理论为推动领导者—追随者契合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启示。它允许对领导者和追随者双方的特质和行为等因素同时予以关注,探讨双方特质匹配和行为协调(或配合)对领导效果的协同影响,从而积极响应了Avolio等(2009)关于把领导者和追随者整合到同一框架以便对领导主题进行更加全面探讨的号召。然而,从既有文献来看,这方面的研究尚未成熟,至少存在以下三个理论或实证问题迫切需要学者们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
首先,明确究竟哪些领导主题可以从悖论视角进行探讨。管理研究中的悖论理论目前仍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并且以往该理论视角主要被应用于组织理论和战略管理领域的研究,而在领导研究领域应用较少(Smith和Lewis,2011)。因此,未来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判断究竟哪些领导主题适合从悖论视角进行探讨。鉴于领导研究者日益强调领导者及其追随者之间的协同,未来可以尝试围绕领导者—追随者双方在某些重要心理特质或个体行为方面的契合展开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往匹配研究涉及的气质、人格、价值观等要素基本上都可以作为领导者—追随者契合研究的基本内容;领导者及其追随者在双方人际互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行为或行为风格等也可以作为领导者—追随者契合研究的内容。特别是后者,虽然其更能体现基本公式B=f(P,E)隐含的发展意味(Tinsley,2000),以及悖论理论所强调的动态、复杂特征(Smith和Lewis,2011),但以往的研究却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今后的研究尤其应该在这方面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挖掘。
其次,拓展前因、结果变量及相关作用机制方面的研究。在与领导者—追随者契合研究颇具渊源的个人—主管匹配研究中,以往研究者已就个人—主管匹配对相关结果变量的影响展开了不少探讨,但对于究竟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匹配”,以及该匹配与相应前因和结果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究竟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发生的,现有研究仍缺乏系统讨论。因此,今后的领导者—追随者契合研究在拓展前因、结果变量及相关作用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时,有必要重点考察“契合”的前因变量以及“契合”与其前因、结果变量之间关系的中介和调节因素。另外,现有个人—主管匹配研究往往在个体层次探讨“匹配”与个体变量之间的关系及相关作用机制,并不能很好地体现悖论理论同时强调各方面因素的基本精神。这就要求今后领导者—追随者契合相关实证研究尤其要在分析层次上突破单一的个体层次,更多地从领导者—追随者对偶层面进行探讨。
再者,进一步明确领导者—追随者契合研究中“契合”的操作化及测量问题,并相应发展更完善的实证分析方法。一般而言,在悖论视角下,既不应该直接测量双方在特质、认知和行为方面的契合,也不应该根据分别测量所得结果的差异分数构建契合,而应该将分别测量所得结果及相应高阶项作为解释变量,并结合响应面分析技术,探讨契合对领导效果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就实证分析方法而言,由于未考虑二次以上更高阶项可能对结果变量产生的影响,前文所列举最高仅包含二次项的多项式回归方程并不能保证足够良好地描述变量之间的关系(Edwards,2009)。这就要求今后的研究明确模型中究竟应该包含哪些高阶项;同时还要考虑把契合研究中描述变量间曲线关系的典型高阶项恰当地转化到结构方程模型中,以规避多项式回归方法由于未考虑测量误差而可能引起的估计偏差问题。此外,由于上述结构方程模型涉及潜变量的交互项、平方项或更高阶项,这给模型构建及参数估计造成极大不便,这个问题也有待后续研究予以解决。
最后,仍需指出的是,从悖论视角开展领导者—追随者契合研究既是从双向互动视角整合领导者和追随者这两个方面的新尝试,也是太极思想等东方智慧在“东学西渐”过程中与西方管理理论相互融合的一项新应用。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从悖论视角开展的领导者—追随者契合研究还很少,今后研究者应该充分借鉴管理研究中的悖论思想,围绕上述三个主要问题展开深入、细致的理论思辨和实证考察,以拓展悖论理论的应用范畴,尤其是进一步发展与完善领导理论体系,并为理解和应对当代组织中的领导问题提供更合宜的指导。
注释:
①Tinsley(2000)认为“fit”、“correspondence”和“congruence”三个词基本代表同样的含义,可以互换使用。其中,“fit”译为“匹配”和“契合”均可,但前一种译法更为常见。而与传统匹配研究只强调稳定特质之间的配合(Tinsley,2000)不同,悖论视角还允许对动态行为——例如个体通过在他人面前像领导者那样行事来索要领导者身份(DeRue和Ashford,2010)——予以关注,而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契合”含有“符合”的意思,比较适用于上述情境。因此,本文参考国内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相关文献中比较常见的译法,把“fit”、“correspondence”和“congruence”分别译为“匹配”、“契合”和“一致性”。
②Zhang等(2012)将领导者前瞻性人格和追随者前瞻性人格分别标记为L和F,根据他们的回归分析结果,常数项、L、F、L2、L×F和F2的估计值依次为:5.28、0.15、0.33、0.16、0.73和-0.04。
③详细情况参阅Edward和Parry(1993)。
④为了方便与多项式回归方法进行比较,图中的模型并未严格用结构方程模型常用的希腊字母来标记潜变量。图中,均值为(X+Y)/2,差值为X-Y,两个自变量都可以按照研究需要确定指标数目i、j和k。
[1]Bateman T S and Crant J M.The proactive component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A measure and correlates[J].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1993,14(2):103-118.
[2]Bedeian A G and Hunt J G.Academic amnesia and vestigial assumptions of our forefathers[J].Leadership Quarterly,2006,17(2):190-205.
[3]Cameron K S and Quinn R E.Organizational paradox and transformation[A].Quinn R E and Cameron K S(Eds.).Paradox and transformation:Toward a theory of change in organizations and management[C].Cambridge,MA:Ballinger,1988:12-18.
[4]Campbell D J.The proactive employee:Managing workplace initiative[J].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2000,14(3):52-66.
[5]Cheung G W.Introducing the latent congruence model for improving the assessment of similarity,agreement,and fit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J].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2009,12(1):6-33.
[6]Collinson D.Dialectics of leadership[J].Human Relations,2005,58(11):1419-1442.
[7]DeRue D S and Ashford S J.Who will lead and who will follow?Asocial process of leadership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organizat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0,35(4):627-647.
[8]Edwards J R and Parry M E.On the use of polynomial regression equations as an alternative to difference scores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J].Academy of Management,1993,36(6):1577-1613.
[9]Edwards J R.The study of congruence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research:Critique and a proposed alternative[J].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994,58(1):51-100.
[10]Edwards J R.Latent variable modeling in congruence research current problems and future directions[J].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2009,12(1):34-62.
[11]Fiol C M.Capitalizing on paradox:The role of language in transforming organizational identities[J].Organization Science,2002,13(6):653-666.
[12]Gemmill G and Oakley J.Leadership:An alienating social myth?[J].Human Relations,1992,45(2):113-129.
[13]Gronn P.Distributed leadership as a unit of analysis[J].Leadership Quarterly,2002,13(4):423-451.
[14]Gupta A K,et al.The interplay between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6,49(4):693-706.
[15]Kristof-Brown A L,et al.Consequences of individuals’fit at work:A meta-analysis of person-job,person-organization,person-group,and person-supervisor fit[J].Personnel Psychology,2005,58(2):281-342.
[16]Küpers W and Weibler J.Inter-leadership:Why and how should we think of leadership and followership integrally?[J].Leadership,2008,4(4):443-475.
[17]Lewis M W.Exploring paradox:Toward a more comprehensive guid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0,25(4):760-776.
[18]Li N,et al.The role of proactive personality in job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A relation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10,95(2):395-404.
[19]Luthans F and Stewart T I.A general contingency theory of management[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77,2(2):181-195.
[20]Meindl J R.The romance of leadership as a follower-centric theory:A social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J].Leadership Quarterly,1995,6(3):329-341.
[21]Morrison E.OB in AMJ:What is hot and what is not?[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0,53(5):932-936.
[22]Pratt M G and Foreman P O.Classifying managerial responses to multiple organizational identiti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0,25(1):18-42.
[23]Shanock L R,et al.Polynomial regression with 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A powerful approach for examining moderation and overcoming limitations of difference scores[J].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2010,25(4):543-554.
[24]Smith W K and Lewis M W.Toward a theory of paradox:A dynamic equilibrium model of organizing[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1,36(2):381-403.
[25]Thompson J A.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job performance: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5,90(5):1011-1017.
[26]Tinsley H E A.The congruence myth:An analysis of the efficacy of the person-environment fit model[J].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2000,56(2):147-179.
[27]Tosi Jr H L and Slocum Jr J W.Contingency theory:Some suggested directions[J].Journal of Management,1984,10(1):9-26.
[28]Zhang Z,et al.Leader-follower congruence in 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work outcomes:The mediating role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2,55(1):11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