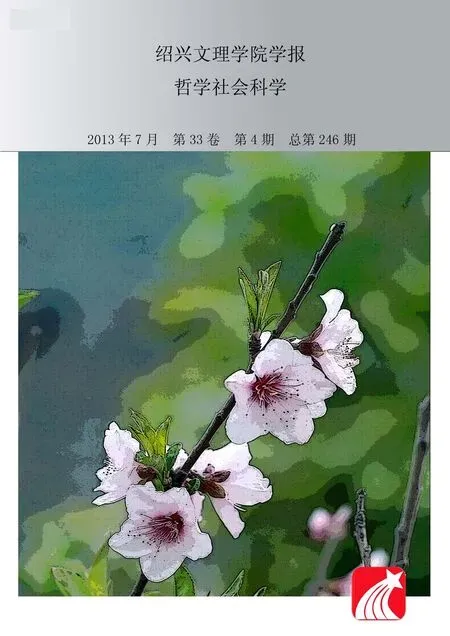许地山与《佛藏子目引得》
陈振文
(福建江夏学院 人文系,福建 福州350108)
许地山(1893~1941),原名赞堃,字地山,乳名叔丑,笔名落华生,以字行。祖籍台湾省台南市,寄籍福建龙溪(今漳州)。①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许地山一生涉猎广泛,对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考古学,甚至生物学,都有深入研究,其中以文学、宗教著述为多。
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各有一套大型丛书,佛有《大藏经》,儒有《四库全书》,道有《道藏》。其先后顺序是先有《大藏经》,道家仿之而编《道藏》。正所谓“道之有教,因佛而兴。道之有经,因佛而成。”[1]儒家也不甘示落,遂有编撰《四库全书》之举。这三套大型丛书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且卷帙浩繁,检索工具的编制成为其研究的重要基础。《四库全书》有纪昀主持编纂的《总目提要》为我们提供了方便,而“佛藏”检索工具的编制,首创之功要归于许地山和他所编纂的《佛藏子目引得》。
一、佛教典籍与佛藏目录
释迦牟尼一生游化讲道,在世时并未留下什么明确的文字记录。释迦牟尼涅槃后,为维护正统教法,佛教弟子开始了结集的活动,由最有威望的比丘根据自己和众僧的记忆,把佛生前的说教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形成了佛教典籍的原始形式。
学术界一般认为佛经最早传入中国是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国使者伊存口译的《浮屠经》(已亡佚)。现存最早的汉文佛经是《四十二章经》。中国的译经工作则始于东汉末年,鼎盛于隋唐。
佛教的经典被称为“三藏”。“藏”的梵文原意是盛放东西的竹箧。古代印度没有纸张,采用贝多罗树叶加工而成的贝叶刻写经典。一部经文需刻写许多张贝叶,刻完后在贝叶之间穿孔系绳,两头用木板夹紧。僧侣们制成贝叶经后,往往将同一类经文装入一只箱笼之中,称作“一藏”。佛教典籍分类固定后,“藏”也就成了分类的代名词。
佛教典籍浩如烟海。佛教以“三藏”概括佛经的全部典籍,近乎“全书”之意。佛经的全集称《大藏经》,最早包括经(佛经,记载释迦牟尼的讲说)、律(戒律,记载僧众宗教生活的规章制度)、论(论著,对教理的解释和研究的著作)三部分。约公元六七世纪(隋唐时期)即有石刻《大藏经》(如房山石经),公元十世纪(北宋开元年间)始有木刻雕印的《大藏经》。中国佛教发展以后,又出现了许多关于佛经的著作,如经序、注疏、论著、目录、史传等,丰富和发展了佛经的内容。后来,汉文的《大藏经》名义上是佛教大丛书,但也包括了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学、建筑等内容。据国内重编的《中华大藏经》统计,所收佛教典籍有4200多种,23000余卷。卷帙浩繁,非其他宗教可比,其内容之多足以让任何天才学者穷经皓首。
在中国历史上,佛教与文化关系密切,对中国的哲学、思想、艺术等领域影响深刻,甚至可以说不懂得佛学,就不能完全懂得中国文化。胡适当年编写《中国哲学史》半途辍笔,就是因不懂得佛学仅写出上卷。所以,编纂一部便利佛教研究所需的佛藏索引自然成为学者们的期盼。
佛经之有录始于东晋道安之《综理众经目录》(成书于374年,已佚)。据许地山统计,中国佛藏现存的旧目录,计有:
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天监间出,约当西历五百十余年顷),隋法经《众经目录》(西历五百九十四年),唐费长房《历代三宝记》(西历五百九十七年),彦悰《众经目录》(西历六百零二年),静泰《大唐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西历六百六十三年),道宣《大唐内典录》(西历六百六十四年),《续大唐内典录》(同前),靖迈《古今译经图纪》(西历六百六十四年),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西历六百九十五年),智昇《续古今译经图纪》(西历七百三十年),智昇《开元释教录》(西历七百三十年),圆照《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西历七百九十四年),《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西历八百年),南唐恒安《续贞元释教录》(西历九百四十五年),元庆吉祥《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西历一千二百八十七年),王古《大藏圣教法宝标目》(西历一千三百零六年),明《永乐大明重刊三藏圣教目录》(西历一千四百二十年),智旭②《阅藏知津》(西历一千六百六十四年),清《大清三藏圣教目录》(西历一千七百三十八年)。[2]2
上述目录中,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③是现存最大的一部佛经目录。唐道宣的《大唐内典录》,创“有目阙本”一录。尤其“众经举要转读录”一篇将异译别行诸经,各择一最善之本做代表,极有益于读者。姚名达将其与唐智昇所撰《开元释教录》合称为空前绝后的伟大名著。[3]100宋王古撰、元管主八续集的《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属提要体裁,对经论教理之内容,传译之渊源,译本之方合同异,一一论列,文简意赅。姚名达称其为一部空前绝后的佛经目录。[3]107海外的佛经目录有日本刊行的《昭和法宝总目录》④和(英译)《大明三藏圣教目录》⑤。
传统治佛经者或依目录、帙号检读,或凭记忆翻查经品,既费力,又费神,就像大海捞针。旧籍中,虽然也有一些可起到索引功用的,主要有:梁宝唱的《经律异相》,唐道世的《法苑珠林》《诸经要集》、李师政的《法门名义集》,宋道诚的《释氏要览》、法云的《翻译名义集》、明一如的《大明三藏法数》、圆瀞的《教乘法数》等,但这些都是用分门别类法和数目法编成,实际上只是类编并不是索引。日本川上孤山《大藏经索引》三册,虽号称“索引”,其实也是类编的一种。[2]1真正意义上的佛藏引得的编纂直到20世纪初方成为现实。
二、《佛藏子目引得》的编纂经过及引得内容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先后刊印了四种藏经:明治十四年至十八年(1881~1885)弘教书院刊印的《大藏经》,四十函,以《千字文》编序,起“天”迄“霜”,简称为“弘”;明治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1902~1905)藏经书院(为佛教图书出版会社所设立)刊印的《卍字藏》⑥,三十六套,每套十册,套、册以数字标序,简称为“卍”;明治三十八年至大正元年(1905~1912)藏经书院刊印的《续藏经》,分甲乙二编。甲编又分一二两编,第一编九十五套,第二编三十二套,乙编二十三套,凡一百五十套,每套五册,简称为“续”;大正十一年至昭和七年(1922~1933)“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刊印的《大正新修大藏经》,八十五套,简称为“大”。这四种藏经基本上汇集了历代撰译的佛教经典。当然,20世纪初,日本刊印四种藏经时并未见到佛藏中的稀世之珍《赵城金藏》和《房山石经》,故收录并不完全。
1922年《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时,许地山寄希望“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在经书出齐后,能刊行佛经全藏索引。1929春,清华大学图书馆刘廷藩、燕京大学图书馆田洪都,邀许地山为两校图书馆编《大藏经》细目。许地山当时就推测,在《大正新修大藏经》刊圆以后,像《昭和法宝总目录》(即《大正新修大藏经》之总目录)一类的佛藏完整目录不久就会编撰,而且又听说“大正一切经刊行会”不准备刊印此索引,于是就在编辑《大藏经》细目的基础上,扩大工作,计划着手编撰《佛藏子目引得》。对此事经过,许地山在《佛藏子目引得》序中作了介绍:
正在进行写片子底时候,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裘开明先生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将他编底《大正藏》前五十五册底目录片子寄到燕京大学图书馆,拟由燕大图书馆继续工作,将《续藏经》及《大正藏》全部底目录版子编就复印,以供两馆之用。洪煨莲先生以为抄片排列之事可由引得编纂处办理,教我加入编纂底工作。当然我知道详细的索引不容易由一个人来做,并且我又不能专工编辑,做下去定要稽延时日。于是略定范围,将这部《引得》底内容分为五部。第一,《撰译者引得》;第二,《梵音引得》;第三,《经品名引得》;第四,《旧录引得》;第五,《史传引得》。所选底标准本为《大正藏》,此外加入《续藏经》,《卍字藏》,和《弘教藏》。后三藏只作参照底用处,子目底页数,只记《大正藏》。[2]2
花了两年多时间,到1933年,在引得编纂处其他同仁的共同帮助下,许地山编制完成了撰译者、梵音、经品名前三册引得,并由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刊行。其余《旧录》与《史传》两册引得拟收录中国古代历代佛藏目录及与佛教有关的碑传,原定由引得编纂处的李书春继续编制,后因故未能编成。这部引得在引得编纂处所编引得中属周期最长的一种。个中原因,洪业在《引得说》中曾有说明:“因编纂条例之改变,遂使数月可成之简单引得,一变而为较细引得,一年有半而后成稿,如《佛藏子目引得》是。”[4]
《佛藏子目引得》内容分三部分。
第一,《撰译者引得》。以撰译者的人名为目,以其生活的朝代、官衔、籍贯、撰译佛经名称及在四种藏经中的卷、页数为注(目、注分别以五、六号字体区分,下同)。撰译者为帝王的,则以其朝代和谥号立目。同名不同人的分别立目。“目”的编排采用“中国字庋撷”法,将“目”的第一字化为数码,按数码大小先后,小的在前。要查某人名(经品名亦同),可将其第一字化为庋撷号码,即可检得。可用以检索撰译者撰译佛经的情况。例:

一;绣阿弥陀佛讚(乐邦文类6∶3);


第二,《梵音引得》。先将撰译者姓名有梵音的集中在一起,以四藏经名、品名、撰译者名有梵音者为目,以其汉文名为注,附注经、品号码,但不注具体出处,通过经名、品名、撰译人姓名的汉文名再检《经品名引得》,即可查出在四藏中的卷、页数。同一人有不同译音者,设互见条。梵音用英文字母拼出,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可用以检索四藏中经名、品名、撰译人名的梵音。例:
Abhutadhamma(A.IV.127)阿难(增壹阿含经25∶3)
第三,《经品名引得》。以经、品名为目,以经之卷数、撰译者及经在四藏中的卷、页数为注。一经见于四藏者共立一目,一经数名者分别立目。品名中含人名、寺名、地名、物名、朝代名及官名者酌量立为主目,前面之字移置于后。如“晋永嘉中有天竺国人”(见《法苑珠林》)作“天竺国人,晋永嘉中有”,以“天竺国人”为主目。经名、品名、撰译者僧名前所冠之字也仿此。如经、品名前所冠之“佛说”“阿毗”“阿毗达摩”“阿毗昙”“御撰”“御制”“大乘”“大乘阿毗昙”“大乘阿毗达磨”“佛说大乘”“佛说阿毗昙”“释”“注”等字,都移于经、品名之后。撰译者僧名前所冠之“瞿昙”“尊者”“竺”“释”“僧”“支”“白”“康”“帛”等字,也都移于僧名之后。采用“中国字庋撷”法编排,并附笔画检字。可用以检索经名及经中所分品名的撰译者、所在书名及在四藏中的卷、页数。例:
08900之裸国经[叔本生](六度集经52)


《佛藏子目引得》中的经名、撰译者姓名,都是以上述四种藏经的目录为准。其中的品名、梵音,则以《昭和法宝总目录》为据,有时也参看《大正新修大藏经》的经文及注解;梵音有时还参看《大藏经南条目录补正索引》、赤诏《汉巴四部四阿含互照录》。经名凡是以梵字开头的,都归并排列在一起,称之为“经品名引得梵字部”,附于《经品名引得》之最后。
三、《佛藏子目引得》述评
许地山早在1913年赴印度佛教北传之国——缅甸仰光侨校任教期间就开始研究佛教。他对佛学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撰写《大乘佛教之发展》《陈那以前中观派与瑜伽派之因明》等佛学论著。二是编写《佛藏子目引得》,填补了国内佛学界的一项空白,为后来佛学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佛藏子目引得》是汉文佛藏的第一部引得。因为它编纂较晚,收经较多,印刷较精,校注较科学,被后人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佛藏索引”。[5]此前,《法宝义林》别册所附的经名、人名索引只限于《大正新修大藏经》前五十五册,与《昭和法宝总目录》差不多,它的自身并不是引得。而《佛藏子目引得》则兼收、标引《大正新修大藏经》《卍字藏》《弘教藏》和《续藏经》四藏,近2000册,数量远非前者可比。
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各种引得均有序文与叙例。序文内容的体例是洪业设定的,主要包括编辑缘起、编辑经过、作者考证、版本源流与异同比较,包括纠正书中的衍讹误字等。许地山为《佛藏子目引得》所撰的序文也基本按这个要求来写。但与众不同的是,这篇序文有一半篇幅详列不是由许地山本人负责编纂的《旧录引得》和《史传引得》要标引的经书目录,而事实是这两册引得没有面世,所以这篇序文似谶语,仿佛冥冥之中预料到这两册引得不能如愿编成,特意把这两部分引书的相关信息详细告之读者。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多少算是遗憾中的补偿吧。
引得编纂处所编引得的周期一种多控制在三四个月,有的甚至只用个把月,而《佛藏子目引得》却前后花了两年左右。个中原因,洪业在《引得说》中曾有说明。这其中除《佛藏子目引得》所标引的经书卷页浩繁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在标目的编排上遇到许多问题,给编纂条例的确定带来困难。
编纂《佛藏子目引得》时,选作标引对象的类型涉及撰译者、经品名和有梵音的撰译者、经品名等种类。同一种类中又出现各种现象,如:以撰译者为标引之类的,有首字、二字……乃至更多字相同,或二人同撰(译)一经,或一人有一种以上著作,或二撰译者同人名,或一人数名,等等。以经品名为标引之类的,有一经附有其他独立名称经书的,或一经同时见于数藏的,或一经数名,或一码数经,或一经某人撰、某人译、某人注,或经名同而撰译者不同,或经名同而卷数不同,或一藏收同经数本,或经品名、撰译者僧名前冠有他字,或品名中含人名、寺名、地名、物名、朝代名及官名等。此外,还有:所据《昭和法宝总目录》与原经也存在差异,如总目录不注原经之品而原经分品,或总目录与原经品名不同;《杂阿含经》中的品名,总目录有未注明的;或《杂阿含经》品名后不著卷数(其他经也有类似情况)的;在版本问题上,除了同一经可能同时在四藏中出现外,还有一种经书可能有宋、元、明或其他多种版本……如此等等。在编纂时,如何梳理上述情况,以解决编排中可能出现的杂乱?如何选目?遇到同名异人、同书异名等如何附加限定信息?在款目的编排上是采取字顺、数序、分类,还是混合编排?这些问题都要在确定编纂体例时进行通盘考虑,而这不仅需要对标引对象内容非常熟悉,更需要科学统筹的智慧。可以说,《佛藏子目引得》的编纂很好地解决了上述困难,经反复修改后的编纂条例不仅详细,而且采取条举式,详细说明各目收录原则、排列方法,并举例说明。引得丛刊每种引得的叙例数量多在8~10条之间,而《佛藏子目引得》的叙例,则多达35条,是其中最多、最详细的一种。可见其复杂程度,当然也是编纂所需。
《佛藏子目引得》是汉文佛藏的第一部引得,也是我国佛藏索引的经典之作,至今仍然在科学研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任何事物都不是至善至美的。该引得所列《续藏经》中各经的编数与原经的情况并不吻合,“《续藏经》(原经)只有壹辑,分壹、贰两编;其中第贰编又分正编和乙编,但正编只标作‘第贰编’。引得(叙例)言‘分甲乙二编;甲编又分一二两编’,盖仅据原经书的书根所题而臆作归纳耳。引得以‘壹’‘贰’‘乙’代表编数,倒也简捷,只不过‘乙’应理解为第贰编之乙编罢了。”[6]这给查找带来了一定的麻烦。但瑕不掩瑜,这部索引终是填补空白之作,且迄今无替代之书。
许地山学问渊博,更是中国现代宗教研究大家,史学大师陈寅恪对许地山在佛教与道教领域的研究成就十分推崇。当年马季明曾邀陈寅恪为“许地山先生纪念专刊”写篇序言,陈寅恪婉拒道:“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学,然于道教仅取以供史事之补证,于佛教亦止比较原文与诸译本字句之异同,至其微言大义之所在,则未能言之也。后读许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二教史论文,关于教义本体俱有精深之评述,心服之余,弥用自愧,遂捐弃故技,不敢复谈此事矣。”[7]以陈寅恪在学术界之声望,如此赞许,可见许地山佛教、道教研究之精深。
许地山对道教之研究,据其弟子李镜池称,是从大学念书起。许氏曾积二十五年之学历,想要写一部《道教史》,可惜只完成《道教史》(上),共七章,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另外还有遗稿七章,为前史之续。194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另一道教论著《扶箕迷信底研究》。许地山为了写《道教史》,曾要李镜池帮他做《道藏子目通检》,李镜池说:“做了一年多,才把这一千一、两百本底道藏及辑要底详细子目,写成两、三万张卡片。交商务印书馆排号码次序而抄录册,预备把这稿本再修改,然后拿一册交商务排印,作为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丛书之一。”[8]可惜天不假年,许地山在1941年8月4日病逝。几个月后日军占领香港,原先存入商务的稿卡,因之散失,《道藏子目通检》终究无法成书。这一未竟事业后来由翁独健接过了接力棒。
注释:
①许地山的籍贯历来说法不一。《辞海》《中国文学家辞典》称“原籍福建”。王盛的《许地山籍贯考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称“寄籍福建”,持论有据。鉴于许地山三岁时全家就在福建龙溪(漳州)落户,他本人又多年在漳州的福建省立二师附小、华英中学任教,母亲、兄嫂都定居漳州。后来许地山虽客居他乡,但常回漳州探亲,与福建关系甚为密切。故本文取“寄籍福建”说。参见陈振文著《闽籍学者与索引运动》,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47。
②《阅藏知津》一书《四库全书》未著录,参见何多源编《中文参考书指南》,称(明)释“晶旭”编。商务印书馆,1939:301。
③《中文参考书指南》误刊为《出三藏集记》。
④日本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监修,1929年7月由东京大藏出版社出版,共三卷。作为《大正新修大藏经》的组成部分,收录《大正新修大藏经》印度、中国撰述部总目录、日本各地寺院所藏历代大藏经目录、敦煌本古逸经论章疏并古写经目录、日本奈良时代古写经目录等。
⑤《大明三藏圣教目录》明万历二十九年刊刻。1883年,日本净士宗南条文雄(1849~1927),在英人马克思·缪勒支持下,将《大明三藏圣教目录》译成英文,1888年由牛津大学出版,向西方介绍汉传佛教。
⑥《佛藏子目引得·叙例》记录为“大藏经”。有的书籍记录为“卍正藏经”,见罗伟国,佛教与道藏,上海书店,2001:121。本文据《佛藏子目引得·弁言》,统称“卍字藏”。
参考文献:
[1]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55.
[2]许地山.弁言,佛藏子目引得[M].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1933.
[3]姚名达.目录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4]洪业.引得说[M].燕京大学图书馆,1932:38.
[5]罗伟国.佛藏与道藏[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21.
[6]张子开.读藏三题[J].宗教学研究,1998(3):70.
[7]陈寅恪.论许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学,陈寅恪文集之三·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16.
[8](台湾)蔡登山.传奇未完:张爱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