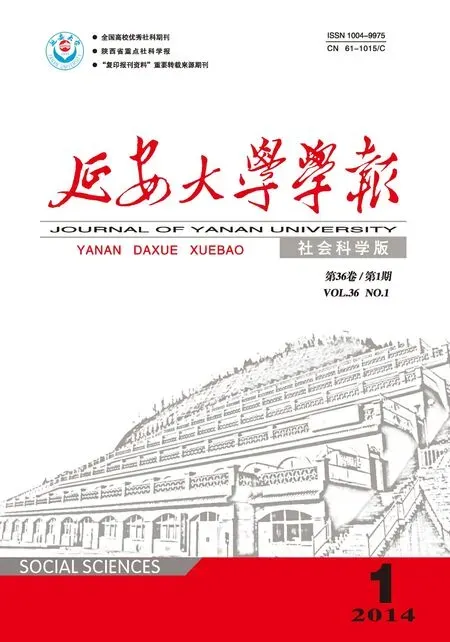论韩非法哲学的技术性转向
陆玉胜
(临沂大学 法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5)
战国末期,韩非通过对诸侯国内个人、共同体(血缘共同体和地域共同体)、社会和国家及国家间相争逐利的形势判断,对新的维持社会秩序形式由以成立的条件和可能性分析,以及对法律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不二选择及其具体的操作性实践的逻辑阐述,解构了儒墨等所倡扬的道德形而上的社会治理方式,建构了其以法律为核心、法术势并举的法哲学思想。下面,笔者拟沿着如上理路,探究韩非的法哲学思想。
一、经验性的利益转向
韩非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事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韩非子·五蠹》,以后关于本书内容只注篇名。)从中可见,韩非大体上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划分为三个或四个不同的阶段,即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并且,他把社会历史规律概括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或是“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八说》)。因此,韩非提出了“世异则事异”的社会历史观点(《五蠹》)。
韩非看到人人都有衣食等“欲利之心”,即人人“皆挟自为心”。“自为”一词源处于《慎子》一书,意即自己为自己打算,自利、为己之意。因为在韩非看来,“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着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解老》)。韩非认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每个人内心都在为自己打算,人与人之间则在互相计算利益;无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还是普通的人际关系,都不例外。其一,就一般家庭内部而言,“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又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谯之。父、子,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外储说左上》)。另外,即使就万乘之主、千乘之君的家庭内部而言,其与后妃夫人、太子之间亦莫不是各怀利己、算计之心。韩非说:“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于利己死者”(《备内》)。其二,就社会层面而言,社会中一般人之间的关系亦莫不是算计性的功利关系。对此,韩非说:“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备内》)。再有,就国家而言,君臣之间也是一种买卖关系:“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难一》)。值得强调的是,韩非认为,君王亦怀有自利之心——君王的大利在于耕战。
综上所见,韩非认为,即使远古时代的尧舜禹是德盛之士,平时以仁义为言行的圭臬,而常人被他们感化而“风行草偃”般行德;但是,“世异则事异”,今世无论是个人,抑或是国家与社会,皆弛骛于私利。藉此,韩非通过设定“人人皆有自利之心”而把儒墨的凌空蹈虚的仁爱与兼爱之德还原为感性的利益存在,或者说,他把人的道德形而上学本体置换为感性的利益本体。
二、社会治理方式的技术性转向
针对当时的人人“皆挟自为心”的社会现实,儒墨的德政贤治思想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韩非对新的社会治理方式何以可能进行了孜孜矻矻地探求,最后探骊得珠。现略述之。
其一,韩非把儒墨的道、德技术化,并首创了技术性、可操作性的理的概念。韩非曰:“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里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解老》)由此可知,道是万物的总根源,而理则是事物的内在规定,即“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欲成方圆而随其规矩,则万事之功形矣,而万物莫不有规矩”(《解老》)。韩非认为,“理”包括“物理”和“事理”。进而,韩非认为,道与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他认为,理是物之内在规定与事之内在法则,而道则是万物之终极本原和万物之总和。由此可进一步推知:理是附着于物事的,它会像物事一样有生死盛衰,而道则是恒常存在的;理可以言说,而道则不可言说。此外,韩非认为道与理也是有联系的。韩非认为道无常操,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改变,总是和具体事务的规律(即理)相适应的;相反,韩非又说:“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可得道也”(《解老》)。可见,虽然道“不可道”,它仍然可以用名言或概念进行论述,如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等等。至于德,韩非说:“凡德者,以无为集,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为之欲之,则德无舍;德无舍则不全。”又说:“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身以积精为德”(《解老》)。所谓德,就是道理之寓于具体事物者。就人来说,只有无欲、无为、不思、不用,才能“从于道而服于理”,顺从自然规律行动,从而使“德”在自己身体中集积起来、稳固起来。反之,如果有为、有欲,“德”便失去寓居之所了。而在韩非看来,“德”就是人身中积聚的“精气”,“德”是由精微的物质组成的。韩非说:“知治人者,其思虑静;知事天者,其孔窍虚。思虑静,故德不去;孔窍虚,则和气日入。故曰:‘重积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气日至者,早服者也。故曰:‘早服是谓重积德’”(《解老》)。韩非认为,那些懂得治人事天的圣人,理性安安静静,感官虚以待物。所以,他们已获得的“德”能保持不失,而自然界的和气又不断地进入体内。这种不断“积德”的人就是“早服者”。
其二,韩非强调执一。韩非通过假借矛盾的寓言故事以说明冰炭不同器、寒暑不兼时而至。韩非说:“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矛盾之说也”(《难一》)。在此思维框架下,他把圣与众、无欲与欲、不忧与忧、公与私、法与德等对置概念二元化,并选择了重前者而轻后者、以前者统御与引领后者。首先,就圣与众、无欲与欲、不忧与忧而言,韩非区分了圣人和众人,并认为:“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忧也。故圣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虚,则不忧矣。众人则不然,大为诸侯,小余千金之资,其欲得之忧不除也”(《解老》)。由此可见,在韩非的心目中,对待物质欲望的看法有两种:一种是圣人的看法,主张衣食只要能满足日常生存需要就行了,因此可以“不忧”;另一种是众人的看法,他们对物质欲望的追求没有止境和永不满足,因此终日“忧”。韩非主张以圣人的无欲和无忧御众人的有欲和忧。其次,就公与私而言,韩非提醒君主要分清公与私。韩非说:“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五蠹》)。在韩非法哲学体系中,公私关系首先表现为君国(公)与臣民(私)之间的利害关系。韩非认为:“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饰邪》)。因此他说:“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有度》)另外,韩非的公私关系还包括公说(君主的法令)与私议(臣民的言论)。其三,就法与德而言,韩非要求君主实行法治而捐弃德治,因为在韩非看来,贤治与势治、德治与法治,都是不可并立的、不相容的“矛盾之说”。
其三,韩非注重守中。在韩非看来,君主管理的臣民应是中民。韩非依人的品性或外在行为特征而将人划分为三类,一类是轻让天下的许由,孝行卓著的曾参、史蝤,仁义圣人的孔子,他们特立独行、洁身自好而不为赏劝;第二类人是赏足以劝、罚足以禁的“中人”;第三类人是“毁廉求财,犯刑趋利,忘身之死”而“罚不足以禁”的盗跖。而其实从行为特征上讲,这三类人又可归结为两种类型,一是行为上不可操控的,即第一、第三两类人;二是行为上可加以操控的、人数也最多的“中人”。还有,即使君主也不再是儒墨的圣君,而是“庸君”、“中主”,亦即韩非所说:“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
其四,韩非强调了做事要讲求功效。在检验认识的正确与否时,韩非特别注重以实际功效作为判准。他举例说,大家都闭着眼,你就不知道谁是瞎子;大家都不说话,你就不知道谁是哑巴。但只要叫大家都睁开眼看东西,提出问题让大家回答,那谁是哑巴,谁是瞎子,一下子就判断出来了。又比如,光凭剑的颜色,即使冶剑专家也很难一下子判断出是否锋利,但如果拿剑去砍一下东西,那末一般人都能判断出剑的利钝了。另外,在判断言行是否相符时,韩非也强调要以功效为“的彀”。他说:“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问辩》)。任何一种言行,都必须以一定的实际功用为目的。他举射箭的例子说:一个人毫无目标地乱射,即使箭箭都射中最细小的东西,也不能说他是一个好射手。如果设一个五寸大的靶,十步(八尺为一步)远的距离,那就非好射手是不容易射中的,因为它有一定的目标。
综上所述,鉴于人人皆逐利的社会现实,韩非从道德理技术化、执一、守中及功效等几个方面探求了整合社会秩序的新的方式得以可能的条件。在韩非看来,这种新的社会秩序整合方式非法律莫属。
三、实证化的法律治理方式的构建
韩非根据“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的思想,构建了以法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韩非的法治理论范式的核心是君主制,即以君主为核心,在君主治国理政结构中,法是中心,势与术是推行法治的两条基本轨道。在此架构下,韩非探求了法、术、势三者相即不离、轻重有度的法哲学思想。
首先,韩非强调了法律在维护新的社会秩序中的核心作用。“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非圣人之治也。”(《八说》)也就是说,在人人皆逐利的社会形势下,德治、贤治已经迂腐不堪、不合时宜。这是因为:“夫施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爱也。夫有施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则暴乱者不止。国有无功得赏者,则民不外务当敌斩首,内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货财,事富贵,为私善,立名誉,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众,而暴乱之徒愈胜,不亡何待!”(《奸劫弑臣》)为此,韩非还用周文王与徐偃王作为正反两反面的例子来论述之。他说:“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五蠹》)。
因此,在人人皆汹汹逐利的情况下,韩非登高一呼:君主再也不能做不知海的井蛙、不知冰的夏虫,而应该“随自然”、“因自然”、“缘道理以从事”与“因人情”(《外储说右下》),采用壮士断腕的精神而力行变革。韩非力谏:要废德治而纳法治——“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五蠹》)。韩非指出,法律具有如下特点:强制性与权威性(“刑罚必于民心”);普遍性与客观性(“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稳定性与公开性(“编著之图籍”,“布之于百姓”);普适性(“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甚而庸君亦“不得背法而专制”(《南面》),而应该“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饰邪》)。
韩非论述了法治是君主治国理政的必然选项。他说“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执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用人》)。犹如规矩尺寸是匠人用以制作物件的工具,韩非主张以法治国,强调社会生活一切遵法,一切由法裁断,法是治国的不二法门。另外,韩非强调,法治的目的在于废私立公:“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诡使》)。韩非的公私观包含两个要点:其一,“公私分,则朋党散”(《难三》);另一方面,公私关系还涉及公法与私议、私说之间的关系。韩非说:“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问辩》)
还有,韩非强调国之强弱治乱,悉视能否奉法、遵法而定。对此,韩非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有度》)。他还说:“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有度》)。
其次,韩非批评了商鞅重法轻术,因而兼容了申不害的术。所谓“术”,韩非定义为:“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定法》)。其一,“因任而授官”,指君主知人善任,因能力大小而授群臣以不同官职,使其职与能相当。其二,“循名而责实”,则指“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臣》)。如何循名责实?韩非说:“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者,言与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二柄》)。这里所说的“名”与“刑”(形)、“言”与“事”的关系,也就是“名”与“实”的关系,而“审合刑名”,也就是循名责实,其目的是达到“形名参同”(《扬权》),也就是名实相符。韩非在名实关系上,主张循名(言、辞)责实(事、功)。韩非强调实(事、功)与名(言、辞)的完全相符,言大而功小要罚,言小而功大也要罚。韩非说:“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大功,故罚。”(《二柄》)在名与实中,他更加强调实(事、功),名只是手段。他一方面重视对“事”应“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臣》),另外,他又有鲜明的“功”利主义倾向,他说:“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问辩》)。任何一种言行,都必须以一定的实际功用为目的。他举射箭的例子说:一个人毫无目标地乱射,即使箭箭都射中最细小的东西,也不能说他是一个好射手。如果设一个五寸大的靶,十步(八尺为一步)远的距离,那就非好射手是不容易射中的,因为它有一定的目标。同样,任何一种言行,如果不以一定的实际功效作为目标,即使讲得再明白,做得再坚决,也像乱箭一样没有用处。这就是韩非说的“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问辩》)。
在君主如何判定名实相符方面,韩非诉诸于君主的内在存养问题。于是,韩非乃盗用道家观念,而有“清静无为”之说。韩非说:“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处其宜,故上下无为。使鸡司夜,令狸执鼠,皆用其能,上乃无事。上有所长,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辩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国故不治。用一道以名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扬权》)此言君主“适动静之节,省思虑之费”,用虚静之明以役众人,无强为之事,无与下争竞之意,则天下万物皆可就范。甚至,在韩非看来,“术”还指一些阴谋权诈之术,如“疑使鬼诏”、“挟知而问”、“倒言反事”(《内储说上》),即故意下达虚假的命令,或者是故意说错话、做错事,设置圈套和陷阱以检验臣下对自己是否忠诚。
其三,与法不同,术具有如下的特点和性质:法的对象是全体臣民(甚至也涉及君主),而术的对象是官僚臣属;法是一种明确的规定,而术则是一种暗中运用的权谋;法要君主与臣民共守,而术则由君主独操;法要公开,公诸于众,使人人皆知,而术则要深藏于胸中。
其四,韩非借鉴了慎到的势的思想,强调了势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韩非指出,一个政权想推行它的法令,必须有专政的权力。这个威力就是“势”。他说:“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下临千仞之谿,材非长也,位高也。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非千钧轻而锱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故短之临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贤以势。”(《功名》)韩非区分了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并强调他说的势乃人为之势。韩非说:“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今曰尧舜得势而治,桀纣得势而乱,吾非以尧舜为不然也。虽然,非一人之所得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若吾所言,谓人之所得势也而已矣”(《难势》)。从中可见,韩非把势分为“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自然之势”是指君主生而在上位所具有的权力;而“人为之势”是指君主在可能的条件下,通过人为的努力而能动地营造设置的、可使臣民不得不服从而为君所用的权力,它又可以分为:其一为“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奸劫弑臣》)的“聪明之势”,其二为作为“人主之筋力”而“所以行令”(《诡使》)、“可以禁暴”(《人主》)的“威严之势”。韩非注重“人为之势”,认为君主不必为圣贤,即使中材之主仅凭“人为之势”即可治理好天下。可见,韩非非常看重后天的外在条件——“人为之势”。并且,韩非强调这种人为之势必为君主所独享,不可分于人。韩非说:“夫马之所以能任重引车致远道者,以筋力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候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人主》)。韩非又说:“势者,胜众之资也”(《八景》)。韩非还说:“夫赏罚之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内储说上》)。以及“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内储说下》)。这说明势对君主的重要性。韩非又说:“夫虎之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则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令君人者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二柄》)。
韩非强调明主要获得强势,必须统一言论。韩非说:“或问曰:辨安生乎?对曰,生于上之不明也。问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辨也,何哉?对曰: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若其无法令而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贵其实,言当则大利,不当则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此所以无辨之故也”(《问辨》)。韩非主张一切“言”统之于“令”,一切“事”统之于“法”。
君主欲维持权势,统一言论,所凭之手段为何?韩非强调在技术方面,应该注重“二柄”。所谓“二柄”,是指:“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二柄》)。
四、结语
韩非从世移事易、事易则备变的新的历史观出发,阐发了其法术势相结合的法哲学理论。韩非的法哲学理论范式的核心是君主制,即以君主为核心,在君主治国理政结构中,法是中心,势与术是推行法治的两条基本轨道。对于韩非法哲学思想的评论可谓见仁见智的二元极端化,有的站在儒家的立场,极端毁誉其“严刑峻罚”思想,认为其苛薄寡恩;另外,也有的人认为,韩非法哲学思想乃先秦政治智慧的高度结晶,它帮助秦王朝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击败各诸侯国并统一中国,铸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大秦帝国。笔者认为,我们对韩非法哲学思想的评价应该置于多元文化发展的整体视域来看,其所倡导的法治思想以其技术层面的管理技巧恰能补儒家该方面的缺失。
韩非的法哲学理论无疑对于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他山之石”的借鉴作用。首先,我们应该明确:时代变了,社会治理的方式也应该随之而变。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攻坚时期。在该时期内,就国际而言,我们遭逢着国际环境的大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在经过自由(工业)资本主义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时期之后,已经进入了全球化资本主义(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该时期又被称为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或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另就我们国内而言,我国正奔驰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征途中;我们国家在经历了党的三中全会而后的三十多年快速发展,“GDP”已经取得世界第二的骄人业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光鲜的背后也透露出一些令人痛心和焦虑的问题,诸如贫富悬殊、大面积及深重的官员腐败、不少党员干部严重脱离群众、假冒伪劣泛滥、诚信严重缺失、教育机会不均、创新动力衰竭、道德底线日下、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等现象。真可谓中国正遭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在如此国内外环境下,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乃至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都要随之而变。可是,有些学者却身陷三重错位而不知,即一方面他们头脑仍耽滞于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的野蛮及贪婪),另一方面他们头脑仍迷执于我国前改革开放时期(高度计划经济时期的绝对平均主义而对民主宪政投鼠忌器),还有,他们头脑超前于现代而提早进入了西方后现代时期(他们借西方后现代学者猛烈批评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而惮于直面现代性的宪政民主、法治、自由等现代性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国人应该清醒起来,认清当前中国的现实,让我们的头脑根植于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当为首务之急。
其次,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攻坚期,此时出现利益复杂化和分化。当此之时,神学世界观、道德形而上学等方式已不再能作为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法律作为新的社会治理方式而成为不二选项,因为法律(民主乃法治的当然前提)作为社会问题的转换器和枢纽能够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征程中,韩非所倡导的法治思想以其技术层面的管理技巧,在我们实践“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先进理念的过程中无疑会发挥重要作用。当然,我们在借鉴韩非的法哲学思想、采用法律来整合社会秩序时要发生法律范式转换,即由君权、君主而至民权、民主;要建成以民权、民主为核心的新的法律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