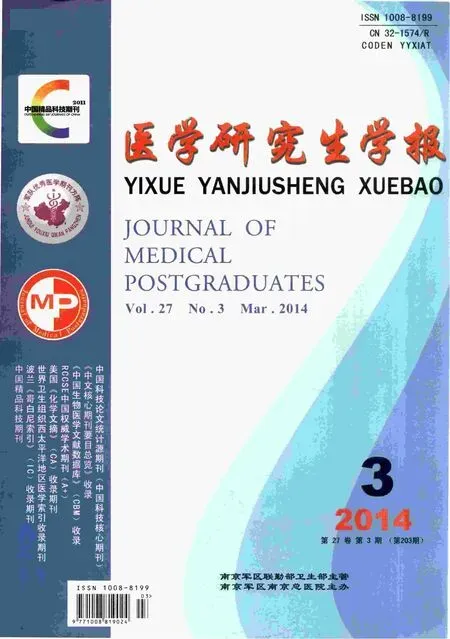脑卒中的转化医学研究
刘新峰
从事神经科临床医教研工作近30年,最让我揪心的是目睹春秋鼎盛的中年人,因脑卒中而困守轮椅并陷入生活的无奈,因脑卒中丧失语言能力而无法表达自己的感伤,也因脑卒中失去自由而沮丧沉沦。作为神经科医师,常常有种挫败感,既无外科医师手起刀落,切断烦恼的麻利与爽快,也没有其他内科同行药到病除的神奇。卒中的治疗没有见证奇迹的时刻,有的只是医师悲天悯人后的感慨和患者苦苦等待后的失望。然而,相比临床诊断治疗的苦难深重,山穷水尽之态,科学家们对卒中的研究成果可谓是喜大普奔,柳暗花明。在基础神经科学研究中,一个大脑都可以控制另外一个大脑的思考和行动了;而在临床实践中,却对小小的脑血管阻塞引发卒中的徒唤奈何[1]。作为医师,面对患者的痛苦,我们有拯救的义务;而基础研究又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知识,现在就是要把知识和义务转化为我们的行动。
近年来国内外兴起的转化医学就是要在基础和临床中间驾起一座桥梁。应该说,大部分研究从开始就是为了治疗。换句话说,就是有转化的动机和想法。比如,神经元在缺血中会受到损伤,因此科学家开发了种种的神经保护药物,从化学分子到中药,从骨髓干细胞到神经干细胞,然而我们收获的却是失败的临床试验结果。仅以进入临床试验的神经保护剂而言,截至2006年,就有1024种,总的研究经费超100亿美元,然而最终一无所获[2]。美好的愿望并未收获美好的结局。那么如何才能使患者分享知识的果实呢?我觉得还是转化医学,转化医学的核心就是转变,那么又如何避免前面的悲剧呢?
1 转变研究者的思维
决定事情成功的是人,决定人前进方向的是人的思维,决定转化医学成功的是研究者的思维,在卒中领域内尤其如此。现代医学的标志是医学知识的爆炸性发展,导致的后果就是原本想通的学科渐行渐远,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就是基础医学的研究者在忙着各种分子的纠结,从脱氧核醣核酸、核糖核酸、蛋白分子到microRNA、microDNA,各种新式概念层出不穷。临床研究工作就是各种临床试验,从蛋白摄入多少到上教堂是否影响卒中的发生等不一而足。一线临床医师又忙于各种文字工作,忙于和患者打交道。各自的研究和工作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固化,带来的思维也随之固化。然而转化医学是一个开放的学科,只有开放的思维才能促进学科的发展。回顾脑卒中治疗的医学史,可以看到转化医学成功的典范,从中看到开放的思维对于研究的促进作用。脑卒中领域内使用最广泛的莫不是阿司匹林的应用。阿司匹林最初用来消炎镇痛,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口腔科医师发现患者拔牙后出血不止,随后科学家进行关注,解答了这个机制,就是阿司匹林抑制环氧化酶-2活性,减轻血小板的聚集;接着心血管科医师发现减少血小板聚集可以减少冠心病的发病,而神经科医师借鉴心脏科的理念,将其推广到脑血管病的领域,很多的临床试验都证实了这一点,目前阿司匹林成为脑卒中预防和治疗的最重要药物。在此期间,科学家从中获得启发,又研制了许多抗血小板的药物,如氯吡格雷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基础,临床医师和临床研究者,不断打破自身学科的壁垒,互相借鉴,互相学习,共同发展,思维在不同研究群体中碰撞出火花。
2 转变研究模式
正确的思维只有得到正确的模式支撑才能发挥正确的结果。反之,错误的研究模式会僵化思维,最后阻滞发展。目前的研究大多数是线性延伸,其实研究应该是面的组合,是网格化的发展。我科临床医师组成的研究团队尽管具有不同的研究方向,但基本是研究不同疾病或者一种疾病的不同亚型,但这种团队的组合不适于目前转化医学的潮流。我们的初步经验在团队内部进行分组,目前我们我科分为5个紧密相关的组,分别是临床医疗组、基础研究组、临床研究组、遗传研究组和转化医学研究组。临床医疗组就是管病床的临床医师,这一组的医师主要负责临床患者的诊断和治疗,并不断提出目前存在的临床问题,供研究选题用;然后是临床研究组针对临床医师提出的问题,依托大型数据库平台——南京卒中注册和中国卒中介入注册进行研究,或是横断面探索和发现问题关联,或是队列研究确定影响因素,或是随机对照研究验证新型的治疗方法或者药物[3];接着遗传组使用分子遗传学的办法,依托生物样本库,对可能影响基因或者变异进行研究,当某个基因或者单核苷酸多态性确定后,基础研究随即跟上,对确认的基因采用基因敲除或采用抑制剂,在卒中动物模型或者体外实验中验证机制;转化医学研究组全程对各研究组跟进,了解问题,寻求解决方法。我们发现尽管已经是一个开放的模式了,但还是一个系统内部的整合,因此称为小循环。
其实,除医学背景人员参与医学领域的研究,还需要更多其他领域的人员,包括工程开发、市场营销、公司管理等不同背景的人员参与。有2个较为成功的案例,一个是国外的,一个是我们自己的。血管介入曾经使用的镍钛合金,也就是记忆金属做出的支架,当日本学者最初合成出来的时候除了好玩之外,一时想不起什么用途。日本有个很好的研究传统,不同公司的人员会定期交流新的东西,来探索各自新的用途。一个内衣厂家提出,这个可以用做女式内衣的衬托,保持不变形。结果一上市,就获得巨大成功。当1986年第1例血管内球囊成形术成功后,镍钛合金就顺势从工业部门留到医学领域了。这个例子看到的是不同领域的专家对同一物品从自己的领域阐述其用途,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第2个例子是我们科的,椎动脉支架植入术已经使用多年,临床医师和临床随访研究都发现支架植入术后的再狭窄率很高,但心脏科采用的药物涂层支架由于采用的都是神经毒性较大的抗肿瘤药物,所以一直没有很好的方法。当心脏科的光学相干成像系统出来后,我们发现主要是椎动脉支架贴壁不良造成,贴壁不良的原因是目前的支架都是圆柱形的,而我们的椎动脉是从远到近逐渐变小的。问题发现后,我们就想到对支架进行重新设计,当然我们自己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和设备,工程人员又不了解临床存在的问题,于是我们与工程设计人员共同设计出了第一款椎动脉专用支架。支架设计和初步小样本制作后,转化医学研究组和基础研究组利用小型猪制作的模型,对支架的安全和有效性进行了验证。临床研究研究组又设计了临床方案,目前正按照方案进行临床验证。因此,我把这超出我们医学领域的不同人员的组合称为大循环。小循环套着大循环,这也许是卒中转化研究的比较好的模式。
3 转变研究方向
卒中不是单一的疾病,而是一组综合征。发病的原因及发生后的病理生理机制复杂繁多,没有正确方向,即便有了正确的思维和合适的团队,也只能是南辕北辙。卒中是血管发生了阻断,因此首要就是尽快恢复重建血流。静脉溶不通就动脉溶,药物不行就器械开通,器械不行就开发更好的器械取代之。为此,我们团队就组织实施了一系列方案,建立卒中的绿色通道,建立卒中取栓的应急团队,面对目前取栓装置没有取得良好临床试验结果的情况,与工程人员合作开发新一代取栓装置——RECO。这些努力就是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脑血流的重建和闭塞血管的再通。
面对已经开发的种种神经保护剂,目前药物的临床试验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如何使药物到达脑组织内发挥作用,因为脑组织受到血脑屏障的保护,药物分子很难透过去。所以,不难想象,药物都不能进入脑组织内,如何发挥保护作用呢?经鼻靶向给药可以无创高效地将各种大分子快速送达脑组织内。为此,经鼻靶向给药是解决这一困境的最可能的途径之一[4]。目前我们在基础上对经鼻靶向给药的通路,剂量和可通过的分子进行了大量的前期探索,并正在和工程人员合作开发专门的经鼻给药装置,而经鼻途径给药来治疗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试验也正在开展之中。
总之,脑卒中的转化研究是一门新兴学科,各学派百家争鸣,百舸争流,各种研究方兴未艾。正如文中所述,转化医学是一门开放性学科,卒中的转化尤其如此,因此我们需要各种新思维,新力量的不断加入,才能充实和扩大我们的循环,不论是医学背景的小循环,还是整个研究的大循环,我们都亟待和欢迎各个有志者加入到脑血管病(卒中)的相关工作中来。
[1] Shanechi MM,Hu RC,Williams ZM.A cortical-spinal prosthesis for targeted limb movement in paralysed primate avatars[J].Nat Commun,2014,5:3237.
[2] O'Collins VE,Macleod MR,Donnan GA,et al.1026 experimental treatments in acute stroke[J].Ann Neurol,2006,59(3):467-477.
[3] Liu X,Xiong Y,Zhou Z,et al.China interventional stroke registry:rationale and study design[J].Cerebrovasc Dis,2013,35:349-354.
[4] Liu X.Clinical trials of intranasal delivery for treating neurological disorders--a critical review[J].Expert Opin Drug Deliv,2011,8(12):1681-1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