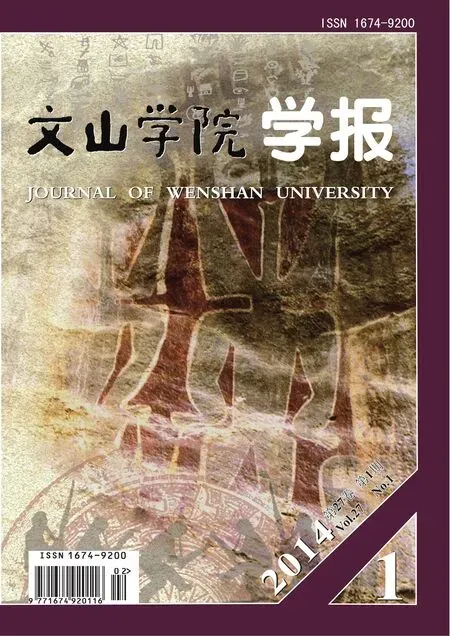《边政公论》有关云南研究述论
段金生,董继梅
(1.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2.云南教育出版社,云南 昆明 650034)
《边政公论》有关云南研究述论
段金生1,董继梅2
(1.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2.云南教育出版社,云南 昆明 650034)
《边政公论》作为20世纪40年代关于边疆研究的代表性刊物,其创刊主旨明确,对推动边疆研究的深入发展、廓清国人的边疆认识起到了积极作用,其影响及贡献十分突出。在大量的论著中,关于云南的研究也很多,涉及云南边疆民族、历史、地理、政治、边界、文化与教育等方面。作为由蒙藏委员会下属研究团体主办的刊物,所载的一些论著不可避免地参杂着时代色彩,体现了国民政府边疆观念、民族认识的局限性,但大部分论著仍是相关学者基于客观事实的考察,论著中关于云南边疆问题的一些主张,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只不过时代学理及国策内容不尽相同。其借鉴意义,不可抹灭,有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
《边政公论》;云南;边疆
19世纪西力东渐,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之边疆危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边疆危机仍然严重,且随着日本的全面侵略,形势更加严峻。面对严重的边疆危机,关心国是的先驱们纷纷著书立说,向国人宣传边疆,以求达到认识边疆、保卫边疆的目的。这一时期,兴办了一大批以刊发边疆问题为主旨的刊物,刊载了大量的研究边疆的论文,对推进边疆研究及国人的边疆认识起到了重要作用。1941年,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组织相关学者成立了中国边政学会,并创立《边政公论》。自此,《边政公论》成为当时学者研究边疆及边政理论问题的重要阵地,刊发了大批著名学者关于边疆及边政问题的论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20世纪40年代关于边疆研究的代表性刊物。①在《边政公论》发表的诸多研究论著中,关涉云南者亦占一定比例。本文即以《边政公论》中所刊载的有关云南的研究论著进行初步分类整理,并试作阐述。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一、《边政公论》创刊的目的及其意义
1941年,正处于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年代,“边疆问题的重要性和边疆建设要求的迫切,已为举国人士所公认”,而蒙藏委员会为什么还要组织相关学者成立边政学会,并创办《边政公论》,这有深刻原因:虽然边疆的重要及边疆建设的迫切毋庸繁述,但“于边疆建设的步骤和方法,则尚未能与目前的需要相配合,而待讨论的地方正多”。[1]表明创办《边政公论》的目的在于讨论边疆建设的步骤和方法。
《边政公论》的创办者们指出:“我国对于边疆问题,向持漠视的态度,虽然边疆与中原发生关系肇自远古,但对于边疆问题作有系统的研究,对于边疆建设作积极的推动,还是近年来的事情。因此,边疆工作这一部门,现在还如入座新宾,真正面目,犹未为大家所认识。我们知道:任何问题的解决,都应该以事实的研究为根据,而后才有正确的办法。病症未认清,当然无法下药。基于这种原故,所以现在有关边疆的一切建设,都尚未能如我们理想中所预期的急速地进展。无论政府机关学术团体以及热心边事的人士,都已深切地感觉到这一点,而展开其研究的工作。这种工作,也恰如韩信将兵似的:多多益善。不过,一切的研究和学说,都就以切合时用为最终的目标,方可产生伟大的效果。故我们对于边疆问题的研究,也必须根据着学理和事实,同时根据着国策,以求能与当前的边疆政治相配合。”[1]上引体现了中国历史上边疆问题的一个大致演变轮廓,并指出讨论边疆建设的意义及应遵循的原则:讨论边疆建设的意义在于通过对边疆问题的系统研究,以求彻底解决边疆问题;边疆建设研究的原则一方面应遵循学理和客观事实,同时应与国家实际的社会政治状况相一致。其关于边疆建设的意义及原则在今天仍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关于《边政公论》的研究范畴:第一,政治的实施必凭藉着政策和机构,盖政策是指导政治活动的方向,机构是执行政策推动政治的工具。政策和机构两者,为政治成败的决定要素。这在边政方面,便是边疆政策和边政机构的问题。第二,政治是社会现象之一,欲推动政治工作,则必对其所寄托的社会有彻底的认识。而欲认识一个社会,又必须从人、地和文化三个要求上去研究。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地是社会存在的空间,文化则为其纵的历史和横的交互关系之总和,即表现于外的各项社会形态。边疆现在所以仍有其特殊状况,便是由于这三个要素上的问题。边疆人的要素即是民族,地的要素即是自然环境。[1]《边政公论》所阐述的其研究的两大方面的范畴,边疆政治自不待言,其后关于人、地、文化三要素的表述,说明政治是与社会相联系的,边疆政治之研究,离不开对边疆社会的探讨,表明了边疆社会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2]
《边政公论》之发刊,“欲凭客观的见地,真诚地研究,一方阐发一般边政原理,使得边政实施能有个正确的理论做参考基础;一方研讨实际问题,收集实际材料,冀能为建设边疆尽其前哨的义务”,即“使理论与实际溶成一片,行政与学术取得配合”。“切盼我国内从事边疆工作和注意边疆问题的贤达,以及研究政治经济社会人类民族语言史地等学问的鸿博之士,予以多方的鼓励批示和帮助”。[1]体现了《边政公论》的创立是为了将学术应用于社会实际,以推动社会发展。所言虽具有一些国民政府的色彩在内,但也体现当时学人对边疆研究的一些认识。
《边政公论》创立后,直到1947年停刊,先后出版了7卷,刊发了一大批边疆研究者关于边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教育、语言、考古、文献、考察、地理、历史、研究方法及途径等方面的论文。它们有的借鉴西方学理,有的从中国传统研究方法着力,但不论是中西学理的结合研究还是遵循中国的传统研究方法,其研究均较深入地对边疆相关问题进行了展开分析,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边疆研究的深入发展,对国人廓清边疆认识起到积极作用,其影响及贡献十分突出。而在这大量的论著中,关于云南的研究也占有相当数量。
二、《边政公论》中涉及云南的研究内容
《边政公论》办刊近7年,刊载文章门类众多,涉及全国各边疆省区。其中关于云南者,其研究涉及内容主要包括云南边疆民族、历史、地理、政治、边界、文化与教育等方面。
云南边疆民族是《边政公论》所刊文章中涉及最多的问题,主要包括云南边疆民族的源流及演变、边疆民族的研究史回顾、民族关系、民风民俗等。丁骕《西南民族考释(一)》(第一卷第7、8合期)一文,考证了哀牢、濮、僰、两爨与南诏、白蛮及民家等西南边疆民族源流及其演变;在《西南民族考释之二》(第二卷第3、4、5合期)中又分别对古蜀国、獠、仡佬等民族源流演变进行了考证。江应樑《苗人来源及其迁徙区域(上)》(第三卷第4期)、《苗人来源及其迁徙区域(下)》(第三卷第5期)对居住在西南边疆苗人的来源及历史上的迁徙路线等进行了研究。江应樑《摆夷的种属渊源及人口分布》(第七卷第3期)分别从摆夷与僰、摆夷与百越、摆夷与百濮、摆夷与哀牢夷的分别及其分布地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此外,涉及边疆民族源流的研究论文还有岑家梧《由仲家来源斥责泰族主义的错误》(第三卷第12期)。
有论者从语言学等方面对云南边疆民族的分类问题进行了探讨。罗莘田《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的分类》(第一卷第7、8合期)一文认为以往学者关于云南民族的分类或太简、或太繁,主张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从语言上对云南民族进行分类,对汉语以外的各种语言分为两系四组十一支:汉藏语系,包括掸语组(仲家支、摆夷支)、苗徭语组(苗族支、徭族支)、藏缅语组(倮倮支、西番支、藏人支、缅人支、野人支);南亚系,只有猛吉蔑语组,包括蒲人支、瓦崩支。对于了解云南的民族源流具有一定意义。
关于云南边疆民族关系及边疆民族研究史方面。闻宥《哀牢与南诏》(《边政公论》第一卷第2期)从语言学及文身习俗等方面对史书所载哀牢夷与南诏的关系进行了辨析。芮逸夫《西南边民与缅甸民族》(第四卷第1期)对民国时期西南边民与缅甸民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岭光电《黑夷与白夷》(第七卷第2期)对黑夷与白夷的历史关系及演变进行了简要论述。陶云逵《云南摆夷族在历史上及现代与政府之关系》(第一卷第9、10合期)一文,对云南摆夷族的分布、人口状况及各部分的汉化程度进行了阐述,论析了摆夷族的源流及演变,对元、明、清直至民国时期摆夷与政府的相互政治、经济关系进行了分析。陶氏另一文《云南土著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第一卷第5、6合期),对云南土著民族类别繁多、非汉语人群时至民国仍较多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对国内外学者关于云南土著民族研究的状况及今后对该问题应如何展开研究进行了论述。该文对了解云南土著民族的研究历程具有较大意义。
关于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社会组织等,《边政公论》亦刊登了一些相关研究论文或考察记录。李景汉《摆夷的摆》(第一卷第7、8合期)对民国云南芒市那木寨宗教活动的一个实施地的“摆”活动进行了调查并介绍。徐益棠、杨国栋《打冤家儸儸氏族间之战争》(第一卷第7、8合期)从儸儸家族组织、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等方面分析了儸儸族际间的战争背景,并论述了战争的形式及原因、过程及其影响等。闻宥、杨汉先《乌蛮统治阶级的内婚及其没落》(第二卷第11、12合期)一文,对西南民族中的乌蛮统治阶级实行内婚制的历史原因、具体表现形式等进行了分析。杨汉先《西南几种宗族的婚姻范围》(第三卷第6期)对苗族、徭族等族属的婚姻形式及范围进行了探讨。罗莘田《再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第三卷第9期)一文,对藏缅语系下各宗族的父子连名这一文化特征产生的原因、现象进行了分析。雷金流《云南澄江儸儸的祖先崇拜》(第三卷第9期)是作者1929年在云南澄江松子园社会进行社会考察后所写的内容。马学良《黑夷风俗之一除祸祟》(第三卷第9期),作者1933年在武定茂达乡黑夷区考察,记载了万德村所见的黑夷风俗之一除祸祟的具体过程及内容。此外,还有马学良《倮族的招魂和放蛊》(第七卷第2期)、陈宗祥《倮儸的宗教》(第七卷第2期)、马学良《倮族的巫师‘呗耄’和‘天书’》(第六卷第1期)等均是探究少数民族风俗及文化的论文。银涛《丽江妇女的生活概况》(第一卷第3、4合期)对云南丽江妇女的日常社会生活、信仰、教育等进行了论述,指出应提高丽江妇女的知识水准。陶云逵《十六世纪车里宣慰使司与缅王室之礼聘往来》(第三卷第1期)一文,对16世纪明王朝车里宣慰使司与缅甸王室婚嫁礼聘习俗进行了考察。李式金《澜怒之间(一)》(第三卷第7期)、《澜怒之间(二)》(第四卷第2、3合期)、《澜怒之间(三)》(第四卷第4、5、6合期)记载了作者1930年7月26日至8月21日在澜沧江、怒江间的见闻,是了解当地地理环境、民风民俗的重要资料。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的社会组织方面。吴泽霖《麽些人之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上)》(第四卷第4、5、6合期)、《麽些人之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下)》(7、8合期),从麽些人的来源及分布、经济纽带等方面对麽些人的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进行了探讨。是对麽些人社会组织及民俗研究较为具体的论文。吴氏还通过对麽些人的研究提出了关于边政的几条原则和认识,体现在《从麽些人的研究谈到推进边政的几条原则》(第五卷第2期)中。
关于云南边疆地理。宏观论著方面,严德一《云南边疆地理(上)》(第四卷第1期)、《云南边疆地理(下)》(第四卷第2、3合期)对云南边疆形势、边疆地理环境等进行了论述;江应樑《云南边疆地理概要》(第六卷第4期)从边疆范围、边区面积、山川形势、气候、物产等诸方面进行了论述。均是民国时期研究云南边疆地理的重要论著。张印堂《云南经济建设之地理基础与问题》(第二卷第1、2合期)一文,对云南经济建设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欲从事建设,必须在此基础之可能范围内妥筹适切之计划,并针对此困难问题,预谋解决之途径,庶乎其有成功之望”。孟宪民《滇西边境的矿产》(第七卷第4期)对云南西部的矿产资源品种及分布等进行了探讨。
对民国时期国人所关注的滇缅边界问题,研究者亦进行了探讨。郑象铣《滇缅南段与新订国界》(第一卷第3、4合期)一文,对滇缅边界南段历史问题的由来、自然环境状况、新定界区的文化特征、新定界务的检讨、巩固新定边界的边防问题等进行了阐述,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滇缅南段划界的影响因素、得失及治理措施。黄国璋《滇南之边疆情势及今后应注意之点》(第三卷第3期)从滇南的边界形势、边区社会状况、边民特性、边防要点等方面进行了阐述,指出滇南毗连缅越、地当要卫,而国际关系复杂,国防建设之进行为刻不容缓之要图。严德一《中英滇缅未定界内之地理》(第三卷第7期)对滇缅未定界区域的山川、气候物产、民族文化、设治沿革等进行了论述。
关于边疆政治方面,相关论者主要从边政制度及边疆政策制订方面进行了研究。凌纯声的《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上)》(第二卷第11、12合期)、《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中)》(第三卷第1期)、《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下)》(第三卷第2期),分别从土司起源、土职品衔、明代之土制、卫所与土司、土司与土地、土司之袭职、清代之土制、民国时的土司等八个层面对土司制度的起源、发展及演变、现状等进行了分析,指出土司发展至民国时期,应进行改革,“以土司划归边省与中央专管边政机关直辖,使土官不和,藉口为土司而自处于法外”,但须因地制宜,各地不必划一。江应樑《云南土司制度之利弊与存废》(第六卷第1期)通过土司制度的沿革与现状的考察,指出土司制度具有破坏行政统一、加重人民负担、阻碍经济生产等弊端,应在有合理的治边方针及理想的边疆官吏前提下废除土司制度。江氏还在《请确定西南边疆政策》(第七卷第1期)中指出抗战前国民政府对西南苗夷诸族均漠然视之,自抗战后政府始为重视,才将西南的苗夷区域视为边疆。作者从西南边疆的民族、语言等方面探讨了西南边疆存在的问题,呼吁政府应设计一贯的边疆政策以妥善解决边疆问题。方国瑜《云南政治发展之大势》(第三卷第1期)一文将云南分为远古至汉初部落时期、汉武帝开拓西南至南朝宋齐郡县时期、自梁至南宋朝贡时期、元明清行省时期,对各个时期的政治发展趋势进行了论述。另外,李絜非《南诏建国始末》(第三卷第4期》一文从南诏的兴起、与唐朝的关系、移民与留学、社会情况、文化等方面对南诏的建国历史进行了论述。
关于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与教育方面。罗莘田《语言学在云南》(第二卷第9、10合期)论述了193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搬到昆明后,充分利用云南丰富的语言学“黄金地”,对云南的各地方言进行分类研究的内容。罗常培《贡山怒语初探叙论》(第三卷第12期)一文,作者根据1942年到大理旅行时所得到一些资料对怒语的发音、语法等进行了分析,是我们了解怒语语言的重要材料。江应樑《西南边区的特种文字》(第四卷第1期)也是关于西南边区少数民族文字研究的重要论文。邱纪凤《滇黔边境苗胞教育之研究》(第四卷第9、10、11、12合期)对滇黔边境苗族的教育背景、教育演进、教育近况、教育课程问题、教育师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劳贞一《西南边疆的宗教改革问题》(第六卷第3期)对西南边疆的宗教状况及应采取的宗教政策进行了论述。
此外,谭方之《滇茶藏销》(第三卷第11期)一文对云南普洱茶的功效及采茶过程,销往西藏的历史及应注意事项等进行了论述。《边政公论》还收录了《黔滇边境土司筹设开发黔西富源》(第一卷第3、4合期)、《滇缅南段界线划定》(第一卷第1期)等边政资料,是我们了解当时历史的重要文献。另,袁复礼在阅读洛克1947年所著《The Ancient Na-Khi Kingdom of southwest china》(1947,哈佛燕京研究院专刊第八种,由美国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部印行,原文为英文)一书后,撰写了该书的书评《西南徼之Na-KhiD古国》(第七卷第4期),对洛克所著一书的写作背景及主要内容等作了简介,是较早介绍西方学者关于云南边疆研究的论文之一。
三、小结
近代中国边疆危机严重且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威胁对象由传统边疆少数民族或政权向中原腹心地区的扩张变为西方列强及其附属国通过各种方式蚕食中国边疆领土;性质由内部民族间的争斗演变为国家与国家间对领土等利益的要求,由边疆少数民族谋图统一中原变为西方列强利用附属国及中国边疆地区的少数分裂势力企图分割中国领土。[3]而边疆危机严重到出现“现在中国的国事,一谈起来,谁都说内忧外患,纷至迭乘,无可救药”[4]之论。
而“边疆问题,就是中国存亡问题,必须对于这个问题,予以有组织与计划之切合事实的研究,以唤起全国人士的注意”。[4]《边政公论》作为有组织、有计划研究的重要提倡者,正如前述所指出的,其创刊宗旨在于讨论如何建设边疆,其所刊文章大都是专门研究边疆问题的专家学者或政治家结合历史与现实进行思考的产物,并且是在二三十年代相关边疆研究基础上的一次升华,所论对于解决中国边疆问题具有较大的学术参考与现实指导意义。
《边政公论》所刊载关于云南研究方面的论著,或是经过亲身考察,或是通过现实与历史结合的反思,既有历史资料保存的价值,也有边疆与民族问题解决的理论意义。正如20世纪30年代初有论者言道:“我们在国内市场上看见许多关于边疆的丛书和刊物,如果我们下番工夫审察他的内容,大都是人云亦云,辗转抄袭,并且虚造事实来充塞篇幅,同时我们又能看见许多考察团到边地去考察,他们到了边地,仅调抄了地方政府的旧卷,并没有作实际的考察的工夫,这种旧卷,既不是科学的,拿时间来讲,概是清末民初的东西,并且内中充满了‘概’‘略’等字样,纯是一种无根据的估量,我们看到了这种丛书和刊物只承认他能唤起一般民众注意边疆,而不能把它作为研究边事的材料”。[5]上述《边政公论》中关于云南研究的论述表明,相关论著立论均较为明确,对于云南边疆问题的阐述较为透彻,资料搜集与辨析亦十分详细,对于推进国人对云南边疆问题的认识及思考解决云南边疆问题的途径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虽然《边政公论》由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下属的研究团体所主办,所载的一些论著不可避免印有时代色彩与国民政府边疆观念、民族认识的局限性,[6]但大部分仍是相关学者基于事实的客观考察,所论关于云南边疆问题的一些主张,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不过时代学理及国策内容不尽相同,其重要的借鉴意义,不可抹灭,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① 参见段金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及其发展趋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1期;《边疆研究与近代民族国家之构筑——以1941年<边政公论>发刊词为中心的考察》,《烟台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20世纪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方法与理论—以<边政公论>为中心的考察》,《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1]边政公论社.发刊词[J].边政公论,1941(创刊号):1-7.
[2]段金生.试论中国边政学的研究内容及其学科建设[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9(5):49-56.
[3]段金生.近代中国的边疆社会政治及边疆认识的演变[J].社会科学战线,2012(9):124-130.
[4]边事研究会.发刊词[J].边事研究,1934(创刊号):2-3.
[5]陈祥麟.研究边事的基本问题[J].边事研究,1934(创刊号):4-5.
[6]段金生.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6):88-93.
On the Studies of Yunnan in Public Opinions on Frontier Politics
DUAN Jin-sheng1, DONG Ji-mei2
(1.School of Humanities, 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Kunming 650031, China; 2.Yunnan Education Press, Kunming 650034, China)
Public Opinions on Frontier Politics as a representative frontier research publication in 1940s has aclear theme and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frontier research and making peopleunderstand frontier clearly, whose impact and contribution are very prominent. In a large number of works there area lot of researches on Yunnan involving frontier ethnic groups, frontier history, frontier geography, frontier politics,border, frontier culture and education. As a publication sponsored by a research group affiliated to the Mongolian andTibetan Affairs Commission, papers published inevitably mingle with colors of the era, and reflect the limitations infrontier concept and national recogni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but most of them are still based on objectivefacts. Some ideas about Yunnan frontier issues, in today, are not out of date though theoretical principles and policies,but the times science and policy are not the same. It still has indelible significance for reference and is worth an indepthstudy.
Public Opinions on Frontier Politics; Yunnan; frontier
K297.4
A
1674-9200(2014)01-0057-05
(责任编辑 杨永福)
2013-11-26
段金生(1981-),男,云南师宗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及边疆史地研究;董继梅(1981-),女,云南宾川人,云南教育出版社副编审,主要从事云南地方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