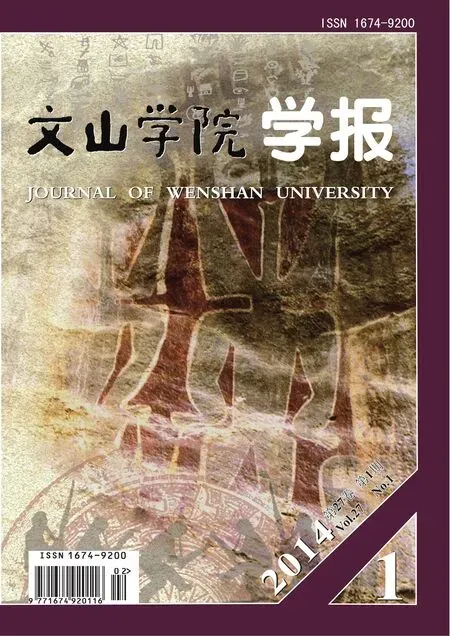论教育的世界眼光
王光斌
(文山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文山 663000)
论教育的世界眼光
王光斌
(文山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文山 663000)
中国正处于深刻的转型期,教育也必须转型,教育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顺应全球化,以全球化思维来谋划中国教育的发展。首先是要坚持邓小平提出的“三个面向”,克服中国教育的偏狭功利性和狭隘的民族性;其次是以世界的眼光来办教育,培养合格公民;再次是与国际先进教育接轨,培养国际化人才,深度融入国际社会。这样才能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并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三个面向;全球化思维;世界眼光;人类性;人文性
国际化、全球化、一体化是当今世界最为明显的发展趋势,是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型。虽然这个转型尚未最后完成,但这个趋势已经被各国有远见的政治家、商界领袖所意识到,并且采取了积极的促进措施。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东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等等区域经济体或组织的出现,以及中美洲自贸区、南美经济共同体、非洲经济共同体、澳洲经济体、东北亚自贸区等呼之欲出,都说明这个潮流的不可阻挡,并且可以预见在未来一定会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发展。这个转型使全世界成为“地球村”,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的相互影响、相互依赖使各国利益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不可分割。这意味着人类真正进入了“全球化生存”和“共同发展”的时代,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造福全人类。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定意义上讲就是顺应这个潮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加入的国际组织只有十多个,而现在达到一百多个。作为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中国目前进入了一个全方位转型的时期,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不断融入国际社会。新一届中国政府在施政理念中不断强调“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预示着中国的转型是深刻、全面而持续的。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必然要求教育的转型。因为社会的转型,根本上是人的转型,而人的转型要依赖教育的助力来实现。那么,中国教育如何转型?中国人要转型为什么样的人?就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显然,中国教育的发展和转型,也必须顺应全球化,以全球化思维来加以谋划。在笔者看来,首先是要坚持邓小平提出的“三个面向”,克服当下教育的偏狭功利性和狭隘的民族性;其次是以世界的眼光来办教育,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合格公民;再次是与国际先进教育接轨,培养国际化人才,深度融入国际社会。这样才能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并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一、坚持“三个面向”,克服中国教育之殇
由于传统的生命压力、实用理性和近代的生存焦虑、意识形态等种种因素的影响,中国教育之殇或许主要就表现为偏狭的功利性和狭隘的民族性。与当今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对照,这一不足尤显突出。
先说中国教育偏狭的功利性。中国教育始终没有脱离实用理性的藩篱,价值取向直指“成功”,“成功”的标志是出人头地,金钱财富,名利地位。太功利的教育,势必强化教育的工具理性,而弱化教育的人文理性,忽视最基本的人性的教育。多少励志故事和成功学教材莫不如是,大行其道的厚黑学更是如此,只鼓励人们如何成功,却忽视了教育人们如何做人。我们唤醒了学生追求名利的成功欲望,而教育的第一要义——学会做人则被遮蔽。培养出来的人只懂得丛林法则,只顾自己生存,不懂或不愿遵守人类社会生活应有的道德法则,缺少人文情怀。“有教无类”异化成为狭隘的应试比拼,“因材施教”被改造为无视学生兴趣爱好的标准化训练。本来,一个孩子的爱好特长被发现并得到充分尊重,是孩子成长为优秀人才的前提,但应试教育却以标准化考试训练学生,经过格式化后,学生只有盲从和适应。上大学后再踏上发现自我的苦旅——绕了一大圈之后,虽有少数成功者,但多数却只有湮灭的结局。即便是少数成功者,也是带“病”的成功者,某种意义上讲是成功,实质恐怕还是失败。这是教育启蒙的失败。西方国家的富豪以乐善好施、回报社会为自豪,展现的是美好的人格与向善的人性;而中国的富豪则以财富为资本如皇帝选妃一般相亲选美,炫富示威。难怪世界第一智库美国兰德公司在一份提供给美国政府参考的《中国问题研究报告》里说:“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与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1]这虽然有夸大的成分,甚至有故意贬低中国教育之嫌,但也不无道理。其中一点就是我们的教育不仅没有培养出具有自主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人才,连具有基本素质的合格公民也没有培养出来,只培养出各类“卓越”的机器(赚钱机器、奴才机器、投机机器、仿造机器)。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缺乏诚信、正直、勇气、爱心、宽容等品质,不懂生活的真谛是回报社会与奉献人类,却有着丰富的“生存智慧”,善于投机取巧,总以“聪明才智”贪婪地攫取想要的一切。没有天国的向往,没有地狱的恐惧,只有人间的贪欲,时时幻想着免费的午餐和好运的降临,连道德都可以成为绑架勒索的手段。国人在国内外旅游的种种劣行,都是明证。巴菲特到中国举办“慈善午餐”遇到的清冷和尴尬,只说明中国富豪的爱心是一种稀缺品。成才而不成人不是人才,是工具,甚至是魔鬼。偏狭的功利教育所强化的成功欲望,实质上是享受的欲望。这在消费上表现为只顾今天不顾明天:竭泽而渔、焚林而猎,疯狂发展、疯狂消费、疯狂耗费资源。湖南郴州一个高中生为筹措购买ipad和iphone的费用卖掉自己的一个肾,多么荒唐的消费。这种不留余地的“绝户事”反映出的是生态观念和价值理念的扭曲,终究还是教育的失败——功利教育惹的祸。
再说中国教育狭隘的民族性。在二战纪念馆里,面对纳粹军官面带微笑枪杀犹太人的照片,西方讲解员问的问题是“他为什么笑”,面对日军狂笑着枪杀中国人的照片,中国讲解员是不会提出类似问题的,只会义愤填膺地控诉日军暴行。前者站在人类的高度直面人性中的阴暗面——作恶的快乐,施暴的快乐,剥夺别人生命的疯狂,引起人的反思,有利于人类向善发展;后者则是煽动民族情绪,引发爱国主义仇恨,对于人类的健康发展恐怕无益,也不适应当今全球化的要求。前者具有世界眼光,人类眼光,后者还陷于狭隘的国家、民族眼光。我们是不能忘记耻辱,但也不应产生仇恨,仇恨不能解决问题。先贤智者早已发现“冤冤相报无了时”,目前在世界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人文宗教也几乎都否定仇恨与报复,主张爱与宽容。站在人类的高度来看,一切仇恨都是魔鬼,所有战争都是错误的选择。有国人发狠说:到日本旅游要扛一箱伟哥去,要狠狠报仇。若真如此,这与日军对中国妇女的暴行又有何区别呢?这些都是人的教育缺失的结果。钓鱼岛之争,中国人抵制日货,砸中国人买的日系车,这是爱国的狭隘性产生的仇恨和暴力,是缺乏理性、爱与宽容的疯狂。当美国人为恐怖袭击中的外国人默哀悼念时,我们的很多年轻人却在为“敌人的灾难”而幸灾乐祸。当某个城市为了市容整洁而驱逐乞丐、流浪汉时,就有很多市民在拍手称快,认为就是应该驱逐,因为“他们”影响了“我们”的市容。请注意这里的“他们”与“我们”的划分——谁规定我们居住的城市就是我们的,而不是流浪汉的——宪法规定公民有自由迁徙定居的权利,更何况是在公有制为主的国度。再者,一个杂乱的城市是包容的城市,包容的城市是具有发展活力的城市,有乞丐、流浪汉的城市肯定是有爱心的城市,没有流浪汉的城市一定是慈善缺失的城市,杂乱有序的社会才是自由和谐的,标准一律的社会一定有专制的影子。这个差异说明我们的国民尚未具备世界眼光和人类眼光,狭隘而狂热的民族性遮蔽了我们最起码的人类情怀和人文关怀。这实际上也是中国教育的差距,缺失世界眼光的差距。
我们并不否认教育固有的功利性和民族性。人类的工具理性决定了教育的功利性,人类的自觉意识决定了一切精神性的文明都具有民族属性。但不能以此固守不变,以功利性否定人文性,以民族性否定世界性,以个体性否定人类性。要适应时代社会发展潮流,就不能排斥教育的人文性、人类性、世界性。在这里,需要重温和确立三十年前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全面践行这个思想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这“三个面向”规定了教育的空间、时间和现实要求。其基础是教育面向世界,面向全人类。以此为前提,面向未来就不只是国家民族的未来,更是全世界(全人类)的未来;面向现代化不只是国家民族的现代化,更是全世界(全人类)的现代化。而我们当下的教育仅停留在国家、民族甚至是集团、家庭、个人的层面上,只是培养国家、民族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集团的骨干力量,家庭的经济支柱,甚至仅是训练为个人获取功名的技能等等,这样的教育已经显得狭隘。因为国家、民族并不是人类概念,只是亚人类概念,过于强调爱国家和民族,为国家和民族,忠诚于国家和民族的教育,必然会在最高层面上与人类共同体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早就预言:在未来的社会里,“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依赖所代替了”[2]618。其实这就是当今正在实现的全球化,它使全人类的利益越来越紧密联系,连传染病都是跨国流行的。以集体主义逻辑推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更高于集团、家庭、个人利益。概言之,面对全球化,所谓祖国利益、民族利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都具有了狭隘性。过多强调己方的利益,必然损害对方的利益,许多利益纷争皆源于此。所以高明的政治家或商人在利益博弈中都会考虑双方乃至多方的利益,追求双赢或多赢的结果。双赢或多赢不只是商业智慧,也完全可以成为政治智慧。作为商业智慧,这在财富匮乏的古代不能实现,但在财富总量已经足够全人类温饱的今天,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道理很简单,食物只够一个人吃的时候,众人必然为活命而争夺,但食物足够众人吃饱的时候,大家要做的只是找到合理可行的分配办法。作为政治智慧,这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也是必须而且是可行的。因为人类的每一个成员,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民族,不论其大小、强弱都应该有平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所以,我们的教育也要着眼于全人类的利益,而不能局限于国家、民族,更不能短视于眼前和个人功利。
二、树立世界眼光,培养合格公民
眼光是一种战略思维,眼光决定我们做事的高度和广度,决定我们走得多远。教育亦然,有什么样的眼光,就培养出什么样的人。中国要走向世界,必须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公民,这就需要教育的世界眼光。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合格公民,其次才是培养人才,先成人后成才。失去这些,我们的教育再卓越也是“失去灵魂的卓越”,不能视为成功的教育。
教育自有其独立性,教育有教育的逻辑,教育不仅是属于民族的、国家的,更是属于世界的、人类的。不能以太过功利的国家政治逻辑或经济逻辑强加于教育的发展。新形势下的中国教育应该树立世界的眼光。世界眼光就是人类的、人文的、宽容的、仁爱的眼光。其中人类性和人文性是教育世界眼光的两个维度。宽容和仁爱是人类性、人文性的题中之义,在人类的存在中特别重要。人类性是教育的特质之一,因为人作为群居动物,其社会存在形态是一种“类存在”。这决定了人的关系的紧密关联性和复杂多变性,它使人必须以“类存在”为起点,去思想和行动,否则就会破坏人的“类存在”,进而危害个体的独立自由存在。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就是同时维护人的公共性的“类存在”和私人性的个体存在的。可以设想,如果我们没有创造伦理道德、法律制度、政治宗教等文明,人类社会就是一个混乱无序的“类存在”,在这个混乱的状态下,人的独立自由本质就会丧失,个体性存在也就受到损害。再设想,如果没有宽容,小到一个家庭、单位,大到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世界,必定矛盾丛生,残酷争斗,最终影响人的整体发展。所以作为人类自觉活动的教育的眼光应该是世界的、人类的。教育的眼光还应该是文化的、人文的,而不仅仅是功利的政治经济和科技。教育的根本在于文化,即用文化把自然人化育为社会人。文化就是人类在确立人的主体性和自觉意识的进程中所创造的一切文明,包括科学技术文明与思想道德文明。前者的价值在于让人掌握技能,控制自然,学会生存,其常态是索取,而后者的价值在于让人成长为社会人,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其常态是给予。这就要求教育要以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作为化育人的养料,同时也决定了教育既有功利性,更有人文性,既有民族性,更有世界性,既有个体性,更有人类性。教育培养人的生存技能,这是形而下的物质层面,它解决的是人如何生存,何以为生的问题,具有直接功利性;教育更要培养人的价值信仰,这才是形而上的精神层面,它解决的是生的价值,为何而生的问题。显然后者是教育更为神圣的使命,它思考并解决的是人的终极命题,因其人文性而更值得重视。特别是面对当今世界科技发达,物质财富相对富足,而价值信仰失落,精神危机重重的现状,更是如此。对于一个充满你争我夺的富翁家庭与一个充满仁爱包容的小康家庭,不难判断哪个家庭更幸福!这说明了人文的重要性,教育的最高层次就是人文性。正如康德所言:“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除了教育从他身上所造就出的东西外,他什么也不是。”[3]5
教育是传承文明的,人类文明进程不可逆转,反人类反人性的逆转现象只是暂时的,这是教育正确向前发展的前提。但教育又总是当下的实践活动,这是教育发展的时空场。面对现实的教育总是需要相应的眼光,才能实现其传承文明的目的,避免反人性的逆转现象发生。而当今教育的全球化、国际化、市场化、大众化已经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中国教育从高等教育到中等教育再到基础教育,都已经与国际教育不同程度地关联起来,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中国教育要发展,必须具备世界眼光,这种全球化战略思维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非常重要。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没有世界眼光的教育,只能培养出没有世界眼光的公民。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几乎同时开始,都是两国面对西方列强步步进逼而实施的改革开放运动,目标诉求都是为了实现现代化,达到强国图存的目的。但甲午战争后两国的命运却大相迥异:大清帝国奄奄一息,危机四伏,苟延残喘,而日本则一跃成为世界列强之一。这只能说明清政府“师夷长技”虽然能实现“船坚炮利”,却无法达到“制夷”的目的,而日本彻底“脱亚入欧”的维新却使其走向现代化。从思想文化教育的视角看,晚清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遮掩下不动摇封建专制体制,是抱残守缺,没有世界眼光,必败;日本明治维新的“脱亚入欧”,实际是学习世界一切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因为当时最发达最先进的科学文化在欧洲,有这样的世界眼光,日本想不强大恐怕都不行。再看西方文艺复兴,表面是恢复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但实质是在人文主义旗帜下的思想解放运动。人的解放激发了欧洲人的探索和创新精神,于是就有了哥伦布的环球航行,有了新地理大发现,有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有了基督教文化传遍世界。不论是对天文地理的探索,还是基督教文化的传播,都说明文艺复兴发生后欧洲人获得了一种世界眼光。基督教的传播固然有该文化的扩张性因素,更与传教士令人钦佩的传教精神有关。西方传教士到世界各个角落,特别是偏僻落后地区传播上帝的福音,是信仰使然,也是基督教教义所具有的世界的、人类的、宽容的、仁爱的眼光使之能够坚持并成效卓著。通过启蒙运动,欧洲人又获得了民主与科学的理性,造就了辉煌的西方近代文明,当然也给亚非拉带来了殖民苦难。但抛开殖民主义、文化侵略的政治评判尺度,就眼光论之,西方近代文明的殖民扩张也比“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眼光更宽阔。面对上述事实,是面向世界还是闭关自守,优劣了然。
以上所论虽然是思想文化,似乎与教育无关,但教育是思想文化的重要传承途径。从“教育的根本是文化”的意义上讲,思想文化的眼光就是教育的眼光。因此以史为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优秀文化要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先进文化的一部分,就需要传教士精神,需要世界眼光,需要放弃农耕社会小国寡民自我感觉良好的传统心态。以这样的眼光办教育,就能培养出具有普世价值和世界眼光的合格公民。在全球化背景下,合格公民应该具有某国公民和世界公民的双重身份,并且需要特别强调世界公民身份。而世界公民应该是具有“人类整体意识、地球村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尊重国际公约和规则,尊重他国主权和文化,协调人与自然关系,致力于人类共同利益,实现世界和平发展,实现天人合一”[4]的人。培养出合格公民,既解决个体的问题,也解决人类的问题,既解决中国问题,也解决世界问题,也就顺应了全球化潮流。因为人类是由个体组成的,而人性是相通的,作为“类存在”的人类当然具有“类本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推己及人都是这个道理。世界眼光实际就是全球化思维,没有全球化思维,就不能解决全球性问题。试问哪个国家或个人能够独自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越来越严重的资源枯竭问题、环境恶化问题、人口膨胀问题、核武威胁问题、毒品和犯罪问题,以及不同文化和价值的冲突问题”?[5]2不能,就只有合作,共同解决。这就需要具有世界眼光的教育来培养出具有世界眼光的公民。
三、培养国际化人才,深度融入国际社会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甚至在很多方面扮演领导者的角色”[6]。中国企业在吸引外资的同时,也在不断扩大海外投资,中国资本正在流向世界各地。这就预示着我们将面临许多全球性问题。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要人类共同面对挑战、共同寻找出路,也需要全球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变,从对立思维转向联系思维和合作思维,从殖民主义思维转向平等主义思维,从而形成经济领域的全球市场、文化领域的全球共同价值和政治领域的全球秩序”[5]。这些变化决定了中国教育必须与国际先进教育接轨,培养国际化人才,深度融入国际社会。
国际化人才,应该具有国际的视野、人类的情怀,具有道义感和责任感,关心他人和世界。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2007年哈佛大学毕业纪念日的演讲中提到了一个概念:“ubuntu”,意思是“我因你而成”,这是一种认为人类之间息息相关的观念,即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的一分子。在全球化的时代,这里指的“社会”当然是“国际社会”,这说明个人的命运与社会、与他人有密切的诸多关系。所以克林顿认为人们不应将自身视为个体去追逐个人的成功,而应为全人类的福祉而奋斗。思考问题时不应分为“他们”和“我们”,而应都视为“我们”,因为世界如此紧密,“他们”的问题与“我们”息息相关。非洲的艾滋病不只属于“非洲”,印尼海啸不只属于印尼。曾经最有权力的克林顿没有鼓励哈佛毕业生以自己的才智去赚大把的钱,去当老板或政界高官,而是敦促他们“花尽可能多的时间、爱心与精力去考虑那99.9%的人”。[7]美国最富有的比尔·盖茨作为演讲嘉宾在同年的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同克林顿如出一辙。他讲了他与妻子梅琳达扪心自问“以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怎样能最大化地造福最多的人”的心路历程,令人信服地阐释了“如何利用纷繁复杂、让企业和政府获益的现代科技,在发展中国家拯救生命、改善生活”的初衷,同时以挑战的方式鼓励哈佛毕业生:以你们过硬的文凭、才智和天赋,能否应对重大的全球问题。“我希望,你们将来评价自己的标准,不单单是以职业上取得的成就,也包括你们为改变这个世界最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所作出的努力……以及你们如何善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除了同为人类之外与你们毫无共同之处的人们。”[7]显然,他们都讲到了对全人类的博爱,谈到了借助人们的才智与能力服务于更大福祉的需要,提及了人们应当跳出自我、超越个体成就的狭隘。[7]这或许就是国际化人才的胸怀。当然人们可以说这是美国公共人物在公共场合唱的“高调”,不足为信,但是他们的实际行动则令你不得不信。克林顿卸任总统后创建了克林顿基金会,这是世界上应对全球卫生健康问题最成功的组织之一。富可敌国的比尔·盖茨后半生所从事的志业(不是为谋生的职业)是做慈善,他与妻子一起成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基金会之一,并捐赠了超过270亿美元(其财富大约720亿美元)以解决世界范围内的医疗和极度贫困问题。[7]美国第二富翁——“股神”巴菲特已宣布将把大部分财产捐给盖茨的慈善基金会。他的财富大约有535亿美元,他只计划给三个子女每人26亿美元的股份,并且不是一次性,而是每年给一笔,也不是给他们用于消费或投资,而是用于慈善——他早就为三个子女分别创建了慈善基金会。[8]上述事例传达出什么信息呢?他们的谦逊以及对全人类的同情心展示的是“大我”,他们的行动已经超越个体层面上的同情与怜悯,达到了追求人类全体福祉层面的大爱,在为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而全力以赴。其价值理念是个人的成功只是“小我”的价值实现,为全人类作出贡献,为多数人谋福利才是“大我”的价值实现。过度的权利优越感和巨大的金钱财富,往往会使人极度膨胀,变成愚蠢的权威或救世主,与暴君往往只差一步。但是,作为世界公民的国际化人才的素养总是包含谦逊和慈善的品格,盖茨和巴菲特的作为是否传达了这样的信息?答案是肯定的。这个信息对我们教育的启示是国际化人才应该具有人类情怀,追求大爱与给予,而不是以救世主面目出现的财富暴君,更不是贪婪索取的可怜虫。而我们的富翁可以为美女一掷千金,却难以为各种贫困雪中送炭,没有道义感和责任感,不关心他人与世界,一切只为私欲的满足和享受。这种差距不能说是教育造成的,但与教育有着莫大的关系。
要深度融入国际社会,我们的教育需要摒弃国家主义和中华中心主义。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价值意义都在于追求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否则就是不合理的。因为自由是人的本质要求,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若非,人类就只能陷入“创造物质,满足欲望,创造更多的物质,满足更大的物质欲望”的怪圈,甚至革命也会成为“伪革命”——主人与奴才的轮流坐庄,奴役与被奴役的颠倒轮回,社会发展就会失去方向和目标。教育作为实现人的本质要求的最主要途径,[9]如果陷于国家主义和中华中心主义泥淖之中,将永远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因为国家主义的教育往往会要求统一教材,统一思想,不允许异质思维的存在,这样的教育专制当然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也创造不出新文化,何以实现自由与创新?国家主义往往打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要求“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必须牺牲个人的一切;而其实施的结果,必然是为了‘国家代表’的利益,牺牲公民的合法权益”[10]。而中华中心主义则很容易让我们因忽视别人的利益而成为孤家寡人,失去和平发展的环境。本来在全球化的今天,爱国与爱世界,爱族民与爱人类虽然不完全等同,但最起码是不矛盾的。国家主义和中华中心主义一旦被标榜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往往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如在民族尊严和感情的名义之下强调寸土必争,两个国家为弹丸之地发动战争,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得不偿失,甚至不顾当地居民的意愿,只顾争去夺来,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不以人民权利为基础的爱国主义终究要滑向强调精忠报国的国家主义,不以爱人类为前提的民族主义很容易演变成唯我独尊的中华中心主义,它们是有根本区别的。失去理性控制的国家主义,还会发展成为恐怖的法西斯主义,二战时纳粹德国意识形态的狂热宣传就是真实的例子。因此,爱国的情感与民族的振兴必须以自觉的理性为前提,这个理性应该自觉涵盖人类情怀。而要培养这种自觉理性的教育,也必须具有人类情怀,跳出国家主义和中华中心主义的陷阱,才能助推中国深度融入国际社会。
综上所述,中国要走向世界,深度融入国际社会,实现全面转型,我们的教育必须具有世界眼光。这种眼光作为教育的战略性思维,应该克服偏狭的功利性和狭隘的民族性,摒弃国家主义和中华中心主义,以人类情怀和人文精神培养合格的世界公民。
[1]美国兰德公司.中国问题研究报告[EB/OL].http://blog. sina.com.cn/s/blog_4d1f0ba00100yok9.html.
[2][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德]康德.论教育学[M].赵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冯建军.教育转型·人的转型·公民教育[J].高等教育研究,2012(4):9-15.
[5]张应强.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现代大学制度改革[J].高等教育研究,2013(9):1-7.
[6]苏洁.中国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J].中国新闻周刊,2013(33):46-47.
[7]王可.哈佛的“最后一课”[N].中国青年报,2013-07-19.
[8]孙浩.美国的富二代[N].新华每日电讯,2013-07-04.
[9]王光斌.论教育问题与人的本质要求[J].文山学院学报,2012(5):77-81.
[10]钱理群.知识分子的本分[J].中国新闻周刊,2013(21): 78-80.
On a Global Vision of Education
WANG Guang-bin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shan University, Wenshan 663000, China)
China is undergoing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so education must be transformed. One importantaspect of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is to adapt to the globalization, and plan China’s education developmentglobally. The first is to adhere to Deng Xiaoping’s “Three Orientation” to overcome insularity, utilitarian and narrownationality of China education; the second is to improve education and train qualified citizens from the world pointof view; the last is to be in lin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dvanced education, train international talents, and integratecomprehensively in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nly by this way can we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development of China's peaceful rise and provide talent and intellectual support.
Three Orientation; global mind; global vision; human nature; humanity
G40
A
1674-9200(2014)01-0084-06
(责任编辑 杨永福)
2013-06-17
王光斌(1966-),男,壮族,云南西畴人,文山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和高等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