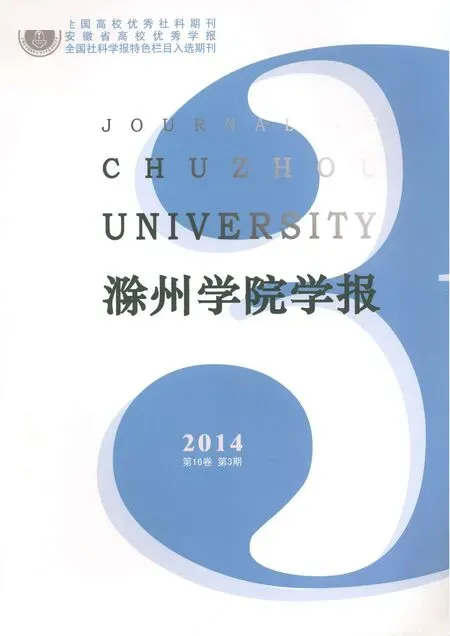文学论争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刍议
孔刘辉
文学论争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刍议
孔刘辉
文学论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现代文学论争大致具有三个特征:发生频率高;地域性和阶段性;产生原因复杂多样。在文学论争的教学中,不仅要求教师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还要有分析判断的能力和超越的历史眼光,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文学论争;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
19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和教学的总趋势是返归文本,回到文学本体,而重视文本阅读、艺术分析和审美教育,成为课任教师的共识。这一观念变化以及相应的教材编写、教学改革、教学实践,改变了现代文学史长期以来依附中国革命史、政治史的从属地位,建立了文学作为审美艺术的主体地位,其意义自不待言。但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与具体作品联系不够紧密的文学论争可能会被忽视或作淡化处理。
有研究者曾说,“历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作,对文学论争的评述更是存在着不少不足之处”:涉及的文学论争太少,分析评论的“篇幅太小”,多是“鉴定式的结论”,缺乏“科学性”[1]。由学界名家所写的专著和教材尚且如此(当然也有客观原因),一般专任教师更难免会轻视或忽视文学论争的课堂教学,可能导致的不良效果就是,学生虽赏鉴过不少现代文学经典作品,但仍然对新文学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与形成的内在机制还是不甚了了,“史”的观念是片段的、零散的,乃至是残缺的、破碎的,从而也制约和影响了对作家作品的认知和理解,这显然偏离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设置的本义和初衷。本文首先讨论中国现代文学论争的一般特征,提请广大一线专任教师注意并重视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中文学论争的教学,并尝试提出一些解决的办法。
一
1936年,由赵家璧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10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中,除《建设理论集》(胡适选编)外,还另有一卷《文学论争集》(郑振铎选编),共收长短论争文章100余篇,这表明新文学的创造者和见证者们已经注意到了文学论争已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事实上,不独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间如此,从1917年“文学革命”至1949年短短三十年间,文学论争都是此起彼伏,从未间断。
稍作罗列,就会发现,那些影响较大的文学论争就有很多。如“五四”时期的新文学阵营与林纾、学衡派、甲寅派的论争,“双簧信”事件,“问题与主义”之争,“整理国故”论争,新旧诗、新旧剧的论者、创造社与文研会论争,以及围绕胡适的《尝试集》、郁达夫的《沉沦》、汪静之《蕙的风》等具体作品展开的论争,1920年代后期则有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茅盾等人的论争,左翼作家与新月派论争等,1930年代有“民族主义文学”论争,左翼作家与“自由人”“第三种人”论争,京派与海派论争,“两个口号”论争,抗战时期有“与抗战无关”论争,“歌颂”与“暴露”论争等,“民族形式”问题论争,左翼作家与“战国策派”论争,现实主义与“主观”论论争等。这些或大或小、或整体或局部、或内部或外部、与文学或远或近的论争,与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文学流派、文学现象、文学批评等范畴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有机体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些论争是现代文坛的重要事件,深刻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走向,不搞清楚这些难以计数的文学论争,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甚至会出现把谬误当真理的歧途,文学论争也理所当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例如抗战时期,梁实秋的某些说法被批判者罗织为号召作家写“与抗战无关”的题材,其实,梁的核心意思是:“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也没有益处的。”[2]其本意肯定不是反对抗战题材,但是在国家危亡之时,即使是保守的批评者也认为梁试图在抗战之外再提出一个创作方向,会冲淡抗战题材的创作,滑向为艺术而艺术极端,有碍于抗战文化,甚至连老舍也说:“此种玩弄笔墨之风气一开,则以文艺为儿戏者流,行将盈篇累牍争为交相谇诟之文字,破坏抗战以来一致对外之文风有碍抗战文艺之发展,关系甚重”,“目前一切,必须与抗战有关,文艺为军民精神食粮,断难舍抗战而从事琐细之争辩。”[3]客观来讲,梁实秋的观点是尊重文艺的,更强调文艺的艺术性,与抗战无关的题材也应当有其存在的价值和位置。梁实秋招致批判的原因非常复杂,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只是最终的结果很清楚,梁实秋反对文艺为抗战而背负了几十年的恶名。虽然梁实秋在政治上是反共的,但其文化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的,若仅把眼光局限在他与鲁迅的论争与所谓“与抗战无关”说,显然是一叶障目,更何况那些论争本身还有可探讨的余地。
就中国现代文学论争所涉内容而言,不仅局限于文学范畴,还触及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革命史等众多领域,与中国现代史的进程密切相关,特别是与政治紧紧缠绕在一起。众所周知,尽管北洋政府和蒋介石政权在思想、文化方面实行控制,也的确想钳制,甚至是扼杀与政府为敌的“进步思想”,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三十年间,文化氛围是相当自由的,言论空间是广阔的。除了发生在延安批判王实味等极少数案例外,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在大体上是不同文化思想和文学理念之间的自由交锋和平等论辩,即使是一些论争背后隐现的是不同乃至敌对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但一般不会因言获罪,给论辩者带来直接的人身危害。也就是说,文学论争不仅是文学的事情,从中也可以洞见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三十年间国人思想、文化、精神、生活等方面历史变化,对认识中国现代史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文学论争在现代文学史的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
虽然每一具体文学论争产生原因、时代背景、参与人、具体过程以及影响意义等方面各不相同,但总体而言,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具有以下显著的特征。
首先,发生频率极高。不妨以刘炎生所著《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为参照来作一个统计。该著以具体案例作为小节标题,全书四章共计小标题(节)90个,虽然少数小节讨论的是同一文学论争,但另有一些小节则同时讨论了几个文学论争,按此计算,该著涉及的文学论争有90个。若再加上刘著尚未涉及的文学论争,就意味着三十年间发生的大小文学论争有上百次,如此惊人的数量,着实令人咂舌。1980年代以来所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等丛书,皆大致循照1936年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经验和体例,文学论争也占有不少的份量。而各种文学史专著和教材也总要耗费一定的篇幅来专门介绍和评述文学论争,但囿于种种原因,涉及的往往也就是那耳熟能详十来个典型案例,大部分则被隐而不表,忽略不计。其次,地域性和阶段性。所谓地域性,指的是那些较有影响的文学论争一般发生在文化和文学较为发达、文人集中的中心城市或这些城市之间,如1917-1937年间北方的北京、天津,南方的上海、南京等地,抗战时期的武汉、重庆、昆明、桂林、香港等地以及解放区延安。当然,这些地方也同样是政治、经济中心城市。而阶段性,指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论争的发生原因和具体内涵不一样,从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王国维),中国现代文学不仅映射了历史的进程和时代的演进,还深度参与了政治的变革与社会的转型,而文学论争的发生不仅与中国现代历史进程密切相关,而且论争的表现形态和具体内涵也打下深深的时代烙印。民国时期(1912-1949)的历史进程大致经历了北洋军阀时期、南京政府时期和抗日-解放战争时期三个阶段。文学创作倒有可能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文学论争则不可避免的与三十年动荡多变的时局发生紧密的关联,带有历史的阶段性特点。总体而言,新文学最初十年间的文学论争,主要是新文学阵营与各保守势力之间的对垒;第二个十年的文学论争多聚焦于文艺思想,几乎所有的论争都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文学的社会功用问题有关,论争双方主要是提倡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和崇尚人文主义的自由派文人。1937年抗战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经对外对内两次生死存亡、你死我活的全面战争。在此种社会大变局中,文学论争与各种政治势力、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冲突紧密缠绕,虽然表面看来是趋于多元化,但贯穿的一条主线则仍是左翼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之间的对抗。
再次,文学论争的产生原因复杂多样,但有迹可循。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间的文学论争背后的根本原因都在于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之间的激烈冲突,最终都落实在要不要打破传统、再创新制,建立新文化、新文学上来。如新文学界与林纾、学衡派、甲寅派等的论战,有关白话文、废除汉字、新旧诗、新旧剧的论争,以及围绕《尝试集》(胡适)、《沉沦》(郁达夫)、《蕙的风》(汪静之)等具体作品展开的论争,尽管这些论争涉及的内容包括文学的思想观念、语言形式、表现内容等等,但本质上都是新旧之争。新文学第二个十年间,文坛纷争此起彼伏,乱作一团,让人目不暇接。围绕“革命文学”“革命的罗曼蒂克”“三民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自由人”“第三种人”“文艺大众化”“两个口号”“反差不多”等概念,以及新月派、论语派、左联等特定文学集团,乃至《子夜》、《八月的乡村》等具体作品,皆发生过双方或多方的论争,但细究之下,这些论争又大多与异军突起的左翼文学有关,论争的焦点也集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的社会功能等文学理念上。
如果说1930年代左翼文学家所倡扬革命还只是文字上的乌托邦,那么抗战以后,随着中共以及解放区的合法化,这种理想的种子则渐渐找到了现实的土壤。与之相应,1940年代发生在国统区的文学论争虽然表面上多与抗战有关,实际上或隐或显都与意识形态有关,举凡“利用旧形式”“与抗战无关”“民族形式”“文学贫困论”“反对作家从政”“战国派”以及围绕《华威先生》、《野玫瑰》、《屈原》、《清明前后》、《芳草天涯》等具体作品的论争,皆是如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标志,在中共直接的组织干预下,由内向外辐射,发生了几次较大的文学论争,如王实味事件、对胡风文艺观点的批判、对萧军的打击和批判,由此,中共逐渐完成了对文艺的彻底统制。总体看来,自1920年代末左翼文学诞生之时起,论争愈来愈与政治纠缠不清,以至于有些论争事件至今尚未得到公平合理的评判。
三
文学论争既是历史事件,又不可避免的带有某种价值判断,其教学看似简单,其实却并不容易,双方论争的具体问题通常只是表面现象,隐藏在背后动因则更值得关注。所以任教教师首先要做到“心中有数”,客观全面的掌握史料,从宏观了解这些文学论争的大致趋势和整体特点,并从微观上把握具体论争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这样才能在课程上穿插自如,合理分配教学时间,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结合时代背景,历史地看待论争
对于文学论争的评价,不能人云亦云,要充分考虑论争的时代背景,把背景因素作为论争双方评价的出发点,由此方能得出客观的评价。例如林纾与蔡元培关于文言文与白话文的论争。林纾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古文家,曾翻译过上百部小说,被称作译界之王,其翻译的《茶花女》风靡中国,他的古文造诣深厚,也为文言文的改良做出过重要努力,1917年他针对胡适、陈独秀提倡白话文,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提倡保留古文,不应当完全废除,1919年他又发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和《致蔡鹤卿太史书》,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建议不要提倡废除古文,对文学革命也颇有非议。蔡元培回复《答林琴南书》,明确表示支持白话文,赞同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客观来讲,文言文历经磨练,曾经产生过多次辉煌,语言水平已经非常成熟,而白话文一直是底层民众自发使用,并未经过正规化的锤炼研究,语言基础薄弱,短时间内难以达到成熟,与文言文水平相距甚远,正如林纾也说:“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是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请君拭目俟之!”[4]但是结合时代背景来看,林纾的观点便有了保守色彩。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已经从君主制国家进入到民国时代,国民普遍具有了强烈的现代化要求,此时社会已经渐渐融入资本主义时代,再也回不到保守闭塞的农业文明,文言文产生并成熟于农业文明时期,其表达方式和内容都是源于农业社会,比如残灯如豆、老死不相往来等词汇早已被淘汰,世外桃源、男耕女织等生活图景也早已被现代化的机器生产所取代,要表达现代人丰富精密的思维方式,对应西方文学的语言表达习惯,唯有倡导白话文,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文言文具有非常高的水平,也要以保守的眼光看待。
再如对于《野玫瑰》论争评价。陈铨的《野玫瑰》主要内容是国民党特工夏艳华和刘云樵潜伏到北平大汉奸王立民身边,伺机探听情报并刺杀他。关于这部话剧,国共两党人士争议很大,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会颁发了三等奖,中共文化人士却一直批判,例如颜翰彤(即刘念渠)的《读〈野玫瑰〉》,指责该剧“隐藏了‘战国派’的毒素”,即“争于力”的理论,是“法西斯主义的尾巴”、“法西斯主义的应声虫”。[5]究竟如何看待这次论争,不能简单地从作品分析,还要和当时社会背景相联系。《野玫瑰》在重庆公演,已经是1942年,皖南事变的后一年,国共合作的蜜月期早已过去,如今是既团结又斗争的阶段,中共文化人士更加强调对国民党的批判的一面,而不再是单纯强调团结,所以围绕这个抗日题材作品,便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但是客观来讲,《野玫瑰》无疑也是抗日题材戏剧,有着政治合理性,“陈铨的民族主义的政治正当就在于对民族国家‘政治统一体’的追求。‘政治统一体’的诉求不一定导源民族主义;国家作为‘政治统一体’是政治法学勘测政治的必然,而陈铨由寻求‘政治统一体’走向民族主义,却是现实政治情势的使然。”[6]而且此时陈铨的民族主义口号与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为内战辩护的民族主义口号截然不同,陈铨的作品与黄震遐、万国安的“屠夫文学”也天壤之别,他不是歌颂暴力残杀,而是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其宣传鼓动牺牲个人一切为抗战的精神应该得到肯定。
(二)全面掌握史料,评述客观
能否客观评价文学论争,常常受限于掌握材料的全面与否。例如“两个口号”的论争,周扬等人首先提出了“国防文学”口号,之后鲁迅、冯雪峰和胡风认为这个口号有缺陷,从而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当时都以为这个口号是由鲁迅提出,并由胡风撰文公开的,所以茅盾等人都为了支持鲁迅而赞成这个口号,由此也使得这个口号一直与鲁迅紧密相连,但是“文革”中冯雪峰所写的交代材料揭秘这个口号是胡风提出的,才使得文学界能够客观看待这两个口号,理性地评价两个口号各自的得失。再如延安文艺整风中对于丁玲和王实味的批判,不能仅仅从文艺创作方面加以认识,还要对当时延安的政治情况有清晰的认识。皖南事变之后,国共矛盾激化,国民党向延安派遣特务引发延安的高度警惕,甚至过度敏感,同时国民党利用丁玲、王实味的文章进行反共宣传,使得中共不得不考虑文化工作上的问题,催生了对文艺界的批判运动,最终造成了冤案。
(三)抓住各个论争的特点
每个文学论争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把握这些独特性是认知它最好的切入点。例如京派与海派的论争,涉及到地域问题,所以要联系双方地域特征。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文化中心也南移,北京就成了被冷落的旧都,此时尚有许多作家留在北京大学校园和报刊社,他们作品中大多以人道情怀观照乡村世界和人生,在美学观念上崇尚和谐、节制情感,这种创作观念与北京文化相通。而作为海派的上海作家,深受十里洋场的都市文化影响,创作上也表现出新潮、时尚、前卫的特点。这个论争是以地域为阵营,所以要充分认识到上海与北京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差异,较多比较两个地域的环境差异,由此引导学生认识到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
综上所述,文学论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文学教学的重点之一,教师要充分认识到它的重要性。而要想在文学史课堂上处理好文学论争的教学,不仅要求教师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还要有分析判断的能力和超越的历史眼光,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1]刘炎生.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前言.
[2]梁实秋.编者的话[N].重庆:中央日报·平明,1938-12 -01.
[3]老 舍.“文协”给《中央日报》的公开信.[C]∥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资料选编.成都:四川商会科学出版社,1983:282.
[4]林 纾.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C]∥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81.
[5]颜翰彤.读《野玫瑰》[N].重庆:新华日报,1942-03-23.
[6]魏朝勇.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31.
A Discussion about Literary Controversy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eaching
Kong Liuhui
Literary controvers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and an important role in teaching.Modern literary controversy generally have three characteristics:high frequency of occurrence;regional and stage;complex and varied cause.Literary controversy in the teaching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not only requires teachers to have a wealth of historical knowledge,but also have the ability to analyze and judge and transce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o as to achieve good teaching results.
literary controversy;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teaching
李应青
I206
A
1673-1794(2014)03-0110-05
孔刘辉,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安徽滁州23900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751038)
2014-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