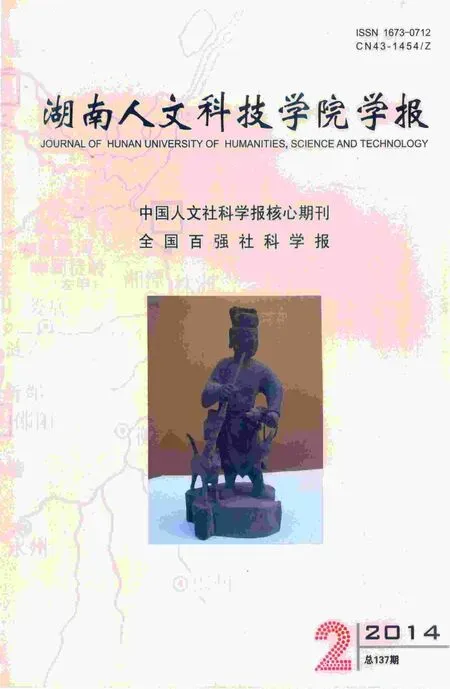托马斯·哈代与西奥多·德莱塞创作之比较—— 以《德伯家的苔丝》、《珍妮姑娘》为例
曾青梅,王淑良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04)
比较文学方法是一座桥梁,它可以使我们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历史地比较研究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文学现象的关系及文学与其他学科间的关系,通过比较寻求各作家、各民族文学的特点和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对哈代和德莱塞及其作品进行纵横向的比较研究,无论是创作主题、结构还是创作技巧、方法上两位作家都有着相似而又迥异的特点,这些特点尤其体现在《德伯家的苔丝》、《珍妮姑娘》2部作品中。
一
托马斯·哈代(1840—1928)是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在英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留下了极为光辉的一笔,他的小说大多以他的故乡为人物活动和情节发展的自然背景。通过许多含蓄而富有象征意义的物象来表现其作品的深层次内涵,以揭示作品的主题,唤起读者的共鸣。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侵入英国农村,导致小农经济解体,个体农民逐渐走向贫困和破产。哈代对当时现实极为不满,用批判现实主义的眼光来审视观察社会,并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苔丝》就是其中最优秀的一篇,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通过女主人公苔丝震撼人心的爱情悲剧,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经济、法律、道德等进行了强烈的控诉。
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为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一生坚持以生动有力的笔触描绘美国的残酷现实,揭露资本主义国家尖锐的社会矛盾。《珍妮姑娘》以贫苦女子珍妮为主线,描写了美国社会底层人民的悲惨遭遇。这部作品的出版使德莱塞在文学界赢得了很大声誉。
仔细研究《德伯家的苔丝》、《珍妮姑娘》两部作品,其创作表现出几个重要特征,文中关键的几个章节有着惊人的类似。《德伯家的苔丝》中,一个重要的场景就是“第一章——纯洁的女人”末尾有名的诱骗情节。亚雷载着苔丝从市场回家的路上,离开大道进入丛林深处,违背了苔丝的意愿占有了她:“周围充斥着黑暗和寂静,四周耸立着冬青树和橡树,刚睡醒的鸟儿在柔声歌唱,兔子在悄声地窜来跳去。但人们禁不住要问,哪里才有苔丝的守护天使,哪里才是她信赖的场所。正像爱嘲弄人的提斯比人所说,他的守护神在高谈阔论,在追求寻觅,或是在旅途中,或者是在酣睡,一时半会不会醒来……为什么粗鄙总是配上优雅,男女错成鸳鸯,历史悠久的分析哲学理论也难以解释这种混乱……”[1]从那时起,苔丝的纯洁从文学上被毁灭了。哈代把笔触从动作描写的诱惑场景移向长长的充满沉思的心理描写,创造了一种环境决定命运的氛围,从瞬间洞察永恒,这种诱惑情景在小说的结构上也起着重要作用,标志着小说叙事的转折点,一切都跟苔丝的生活息息相关。
相似的主题和结构亦出现在《珍妮姑娘》中,德莱塞的情景描写方式跟哈代的类似。作者在诱惑情节描写的关键时刻笔锋突转,插入了梦幻情景:“英国的杰弗里斯告诉我们要造就一个纯洁的女人需要一百五十年……如果美丽的玫瑰,优美的音乐,温润的晨夕触动过你的心灵,如果这一切美都将逝去,而在世界消失之前,你被赋予了这一切,你愿意放弃吗?”[2]这段诱惑情景描写的末尾与哈代的描写有类似的方面。首先在唤起与妇女命运相关的历史形象方面,哈代与德莱塞都创造了一个男人诱惑女人的情节,作者偏离诱惑本身花大量的篇幅去谈论读者意料之外的事,对先祖的回忆和民间文学的叙述跟正在发生的事情形成对照,永恒和当下放在一起,赋予当下以复杂和模糊。其次,在两段描写中,作者都给主人公以伤悲和怜悯之情,在人类的大背景下,个人的悲剧被放大,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的运用不仅使读者更接近现实和小说的重要主题,而且使读者更接近当时小说主人公的情感。
二
哈代与德莱塞作品的类似还体现在两人都努力在作品中传达情感的力量,哈代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总是把眼光投注在社会最糟糕的一面。作者笔下的主人公都纯洁无瑕,并都对她们寄予深切的同情,两个妇女都深受家庭困难的牵制并被迫作出牺牲。珍妮的生活里包括两个为她提供物质生活的男人,然而也正是他们使得她成为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而苔丝因为与前男友重逢的关系,跟自己所爱的男人的婚姻变成了灾难。而且两个妇人都向她们所爱的男人隐藏了不光彩的过去。苔丝和珍妮都有一个非婚生的小孩,都是作为男人的情妇生存着。那么,这不只是两部作品简单的相同,而是如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的对相同现象的类似描写的问题。左拉宣称:“自然主义就是回到自然,就是从物体和现象出发,通过实验和分析,寻求物体和现象的本源。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是直接的观察、精确的解剖以及对世上所存在的事物的直接接受和描写。”[3]哈代和德莱塞都强调人的内在自然。哈代在小说中对苔丝的古老姓氏的重要性和遗传影响作出冥想。虽然德莱塞宣称他“从来没读过一行左拉”[4],但他是巴尔扎克的狂热崇拜者。就像吉尔伯所说:“巴尔扎克的巴黎证实德莱塞美国观察的真实性并首次引起他思索……他的未来……有没有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法国无法被美国所复制?”[5]尽管吉尔伯分析了德莱塞对法国文学理论的传承,但德莱塞自称没有受到任何哪一种理论的影响:“比起其它单一因素,我认为创造性写作跟情感更具相关性,普遍而强烈的情感是我所要表达的……”[6]这些话表明德莱塞不愿接受任何理论,他作品中对情感的独特表达使得他能与哈代相提并论。
哈代和德莱塞都强调遗传的重要性,然而不像受左拉宿命论理论影响的其他作家,他们都对反社会的鲜活个体赋予强烈的敏感性并对其倾注了作者自身强烈的情感。这种方法与左拉的精确描写生活和以科学实验的方法描写事物完全不同。当作者失去了个人性格的感知,小说不可避免地变成另一个机械实验,人物没有任何可辨别的特点,只是简单的重复而已。相反,哈代和德莱塞透过宿命论的厚雾,看到了个体的存在,他们似乎进入了个体的生命并与个体一起生活着,而不仅是一个旁观者或是没有同情心而言的科学家。正如哈克坦尼对德莱塞的评论:“德莱塞看美国正如巴尔扎克和左拉看他们的国家。对德莱塞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观察过程,但是他无以回避。没有商议,没有妥协,没有退让。”[7]并进一步指出:“纵观他的一生,德莱塞是他自己经验和信仰的顽固而坚定的实践者。”并且也没有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就像巴尔扎克,他努力寻找……,多么富有,多么严峻,就像一曲交响乐。”[7]201德莱塞从未把他笔下的主人公描绘成完全无助和没有希望的个体。就像克里奇在评价《珍妮姑娘》的宿命论主题所说:“珍妮意识到她永远也不可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珍妮的性格跟苔丝的类似……说明受生活压力所迫的善感的女人命运摇摆不定,但是她从来没有被打败,她对人类的爱永远也不会消失……”[8]两人都觉察到命运的存在和生活的不可避免性,都强烈感觉到个体生存下去的力量。不管身处何方,珍妮都受到社会的排斥,当她的爱人去世,她只能像一个陌生人一样旁观,然而她从来没有失去她温和的个性和她热爱他人和生活的固有品质。女儿死后,她收养了一个孤儿,继续着生活中她爱的角色。故事的结尾,她以一个强者的身份出现,生活因为自己的努力变得更加美好。
在另一个压抑的时代和社会,苔丝挣扎着生活。一开始她拥有坚强的性格,然而在她经历痛苦的过程中,她几乎被命运和身边的事件打败和摧毁。在小说结尾我们看到她似乎经历了哲学理念的重要变化,通过挑战道德和和社会不能容忍的行为来反抗这个社会。然而,她至少选择的是她命中注定的角色。她面对社会强势力量的微弱反抗导致了她的死亡,但她已经受到救赎并且不再害怕,坚信纯洁,美丽和真爱最终能战胜命运。正如文章所说“女人们受了这种耻辱以后,一般总照旧活下去,恢复了精神,又带着感兴趣的眼光,东望西瞧,有生命就有希望,那种坚定的信心。”[2]229因而他们对于个体的描写充满着真挚的情感和热情,具有永恒的吸引力,从这个层面来说,两人都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三
作为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的创作手法又都体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虽然哈代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但他又巧妙的运用了象征的艺术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对于“象征”的解释正如梁宗岱先生概括的那样:“借有形寓无形,借有限表无限,借刹那抓住永恒……”[9]哈代把他自己无形的感受寄寓于有形的人物、事物当中,构成了意象,使之不但有具体的形象特征,还有丰富的内涵,并深隐了作者许多难以言述的意念。文中的动物象征,植物象征,颜色象征,地名象征等构筑了显、隐两大艺术世界,为他的作品营造出一定的寓意性效果,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哈代通过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巧妙结合,使《苔丝》成为一部带有神秘色彩的小说。作品超越了题材本身的意义,充满了辽远深邃的精神意蕴,并使一个被凌辱的农村少女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甚至有些单薄的故事具备了悲剧的规模和深度。
德莱塞相信他是“心灵的现实主义者”[10],“至于德莱塞,”正如Hakutani所说,“文学几乎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他的文学创作过程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过程,与他自己的经验和观点相吻合。”[7]89也正是他的这个特点,使得他更加接近哈代。德莱塞在塑造人物时,也富有艺术感染力,表现出他的观察细致犀利和深邃有力。作家戴维·卡斯纳曾经概括过德莱塞的创作特点:“他一手拿着放大镜,把他另一只手上欢蹦 乱跳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富人、穷人、乞丐、偷儿、医生、律师、商人,以及社会上各界 领袖人物都照彻得纤毫毕露。”[4]267就是这样,在德莱塞栩栩如生的描绘下,老工人格哈特的诚实、勤恳、耿直和贫贱不可移的品性跃然纸上。
在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的创作过程中,两人都表达出社会和环境因素对小说主人公悲剧命运形成的重要性。哈代的悲剧创作始终以真实为出发点。他认为,文学作品应当是艺术品或者是表现真理的作品,应当真实地反映人生,暴露人生,批判人生。他指出,“人们称我是悲观主义者。如果像索福克勒斯那样认为没有降生为最幸福就是悲观主义的话,我不拒绝这一称号。生活中充满了痛苦。痛苦过去存在,现在仍然存在,任何将来的幸福也不能消除过去忍受的痛苦。”[11]哈代对悲剧的真知灼见来源于他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和他敢于正视惨淡人生的勇气。因此,在创作《苔丝》时,他始终把目光聚焦在人类社会中“悲剧的种种可能”,在哈代的悲剧思想中,神是不存在的,人的命运不是由神主宰的而是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他把他的悲剧小说统统归于人物与环境的小说。命运只不过是哈代探索生活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苔丝的悲剧是由旧的习俗道德和残酷的法律造成的,因此,苔丝的悲剧与其说是命运悲剧倒不如说是社会悲剧。他要以令人不快的、以真实为基础的“悲观主义”给虚伪的、盲目的乐观主义以迎头痛击,让读者对世界,对人生有清醒的认识,作出深刻的思考。哈代对苔丝寄予深厚的同情,认为她是无罪的,是个受难者。他把这样一个犯了“奸淫罪”和“杀人罪”的女子称做“一个纯洁的女人”,并用这一称号作为本书的副标题,向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道德提出抗议。
在德莱塞笔下,珍妮的命运也是社会和环境制约的结果。每当她面临重大决定时,她所处的环境都会促使她作出不利于自己的决定。因为家境贫寒,作为长女的珍妮被迫来到宾馆做些零活帮助养家,从而结识了在此下榻的参议员白兰德。当白兰德对她颇有好感时,珍妮的哥哥巴斯锒铛入狱,家里毫无办法,这时白兰德欣然帮忙,出于一时的感激,珍妮决定以身相报。白兰德突然死亡,珍妮美好生活的梦想破灭了。她到富人家当女仆,遇见了来做客的莱斯特。当莱斯特对珍妮公开表示爱意遭到拒绝后,珍妮家却又一次因老葛哈特的受伤而陷入绝境,为了全家的生计,珍妮只能答应莱斯特的要求。当珍妮终于过上其乐融融的幸福生活时,环境再一次抢走了她的幸福:她了解到莱斯特如继续和她呆在一起将失去应得的家产。善良的她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一个选择,她主动提出分手,结束了自己的幸福。
德莱塞在继承美国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创作真实性的基础上,又深入剖析了人们不同命运的内在因素,提出自己独到的自然主义道德哲学。在当时的美国,流行的是温文尔雅、谨小慎微的维多利亚传统,即“优雅传统”。作品中的女主角必须写得纯洁无瑕,而且故事要有美好的结局。男性违反道德的行为是可以谅解的,而对于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女性的身上,她们就必须得到应有的报应,用死来惩罚。因此,哈代笔下的苔丝被判处死刑,斯蒂芬·克莱恩的街头女梅季投河自尽。当时的文学倾向已经决定了她们悲惨的结局,但德莱塞另辟蹊径,率先打破了传统的道德教条。德莱塞认为,人的行为是内在和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的本性和他所处的环境早已决定了他将采取的行为,个人只是被动的实施者,所以他不需要为他的行为受到任何惩罚,这显然又使得他跟哈代区分开来。
德莱塞和哈代同处于变迁的时代,大体相似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他们创作中有某些相似的可能。哈代生活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后期,他以犀利的笔锋,撕破了资产阶级卫道士所鼓吹的乐观主义的面纱;德莱塞创作的盛期已到了美国“黄金时代”的尾声,认清这实际上是个“镀金时代”。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使他们把笔触放在社会下层被压迫、被污辱的小人物身上。现实主义为主的创作笔调,类似的主题结构、创作技巧及情感表达并没有使彼此成为另一个人的影子。相反,同中有异,异中求变的创作手段使他们各自在文坛上绽放着异彩。
[1]西奥多·德莱塞.珍妮姑娘[M].傅东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31.
[2]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M].郑大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26―28.
[3]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0.
[4]蒋道超.德莱塞研究[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232.
[5]GERBER D.Extreme and bloody individualism[M].A-merican Literary Naturalism:Heidelberg C Winter,1975:107.
[6]ELIAS.Letters of Theodore Dreiser[M].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59:112.
[7]HAKUTANI.Dreiser and realism[M].New York:Macmilan,1964:112.
[8]KRIGER.Determinism in Theodore Dreisers novels,masters thesis[M].Kent:Kent State University ,1967:30.
[9]梁宗岱.梁宗岱选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321.
[10]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M].陈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80.
[11]朱维之,赵渔.外国文学史欧美卷[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