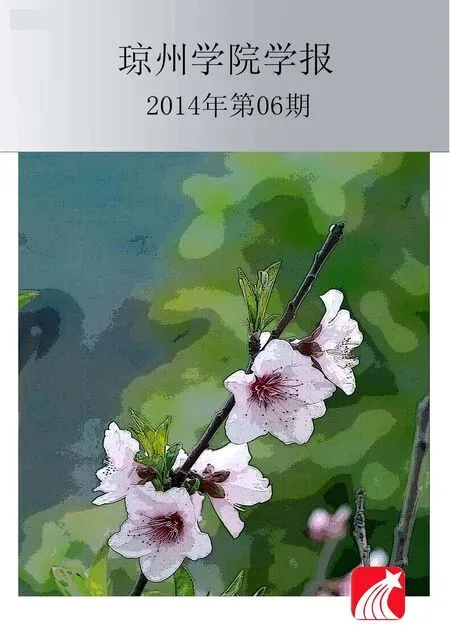王佐对贬谪海南人士的吟咏——兼谈王佐研究的一些问题
李景新,高海洋
(琼州学院 a.人文社科学院;b.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海南三亚572022)
一、关于王佐研究的一些问题
王佐是海南历史上的一代名贤,有“吟绝”之称,就流传下来的诗歌数量看,明代海南籍诗人无出其右者,他还有其他文史作品,以此而推,其诗歌创作在海南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人在海南文化史上具有一定地位。但是后世对王佐的研究却十分薄弱。
就以对其诗歌创作的评论观之,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是非常零星的,主要来自明清时期《鸡肋集》编辑出版者的序、跋、传。“大方家每服其词之平易温雅,气之光明隽伟,当比拟于古诸大家。”(唐胄《原集序》)[1]卷首1“亦足以明其心之所酷嗜,盖非特以诗文自鸣,亦庶几因文以见道者。”(邢祚昌《原集序》)[1]卷首3“作为文与诗,得风雅之正轨。”(樊庶《原集序》)[1]卷首4“其诗文比之欧阳文忠,信然也。”(樊庶《王汝学先生传》)[1]卷首8“味之腴者,人固咀嚼不厌;即淡如太羹元醴,其中亦自有真味也,‘鸡肋’云乎哉!”(李熙《重刻王桐乡先生鸡肋集序》)[1]卷首6“提学新喻胡荣称其博学多识,静思力践,见道精审。故其诗辞和平温厚,文气正大光明,当比唐宋诸大家。”(王国宪《王桐乡公传》)[1]卷首14“至其诗文有唐宋名家风格,前人论之已详。”(王国宪《<鸡肋集>后序》)[1]卷十41“爱其诗文温厚和平,卓然大家风格。”(王光谟《桐乡公 < 鸡肋集 > 跋》)[1]卷十41
这些评论自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是都很笼统模糊,且多为诗文并提,无法判断诗的价值和文的价值之区别;二是多陈陈相因,最早为《鸡肋集》编辑出版的唐胄对王佐做出评价之后,后来者基本都是相因其观点,基本上没有什么新意;三是评价者与王佐有非常密切的世代关系,或学生,或后人,或临高官员,在临高这块并非广大的区域内,他们都满怀对此乡最值得推崇的人物王佐的极度崇敬,评价是否有偏爱之处,就不好确定。这些都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王佐时所不能不考虑到的。
现当代学术也极少有对王佐诗歌做过细致研究者。叶显恩1994年作《祝贺<鸡肋集>新订本出版》谓:“以诗词论,在海南人士中首推王佐,已成定论。”[2]9然而是谁“定论”的?是哪个时代、哪个文献、哪个论证给出“定论”的?皆不得而知。我们必须注意,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定论”一词是不能轻易使用的,是要十分谨慎使用的。没有深刻的研究,没有严密的论证,就对一个历史人物得出定论,那不是太轻率了?我们在浩如烟海的《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搜索,有关王佐的文章居然只有两篇:其中一篇题为《海南史上四大才子之一:王佐》的文章是来自《神州民俗/海南·临高频道》的一般介绍性文章,并非学术论著;唯一的学术论文是发表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上的未署名文章《王佐和他的海南风物诗》。此外就是周济夫先生的《琼台小札》中有一篇《咏物与咏史的融合——王佐的两首咏花诗》短文,简单分析了王佐关于木棉、含笑花的两首诗;他在《椰阴诗话》中还有几篇类似的短文。可见对王佐的诗歌创作乃至对整个王佐的研究,是多么薄弱。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我们还能盲目相信“以诗词论,在海南人士中首推王佐,已成定论”的观点吗?如果我们继续停留在以前对王佐陈陈相因的浅层认识上,而不脚踏实地做卓有成效地深入研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之做出客观评价,这不是对这位海南著名历史人物的爱,而是对他的不尊重,也是对历史的不尊敬。
那么怎样进一步加强对王佐的深入研究?我们认为,对其作品做基础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对其诗歌、散文、史著、论著等文本进行具体而细致的研究的基础上,再把他放在整个海南文化、文学史上,与其他著名历史人物进行切合实际的比较,才能够对其作出比较合乎事实的评价。就诗歌而言,在题材内容、体裁形式、艺术风格、师承源流、在当时的影响、对其后的影响、在整个海南乃至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何影响,等等,都需要做踏踏实实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对得起这位被后人推崇的海南历史名人。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选择了王佐诗歌创作中的一个侧面——对贬谪海南人士的吟咏——进行比较详细的论述。
二、王佐对海南贬谪人士的吟咏在其咏史诗中的分量
王佐擅长于咏史。检点《鸡肋集》,今存诗歌中广义的咏史诗约五十首。除关于唐宋贬谪题材之外,如《咏史》八首,《哀四义士》四首,《歌风台》五七绝各一首,《唐马图》四首,《读唐元宗纪》《越台怀古》《彭城怀古》《聊城怀古》《周瑜墓》《荆王太子墓》《夜宿武夷止庵》《韩氏双烈》《贞女唐亚妹》《过富春江严子陵祠》《杜甫游春图》《王子猷访戴图》等各一首。这些作品,或直接咏史,或因遗迹而怀古,或观古代题材的绘画而引起对历史的思考,时间跨度从先秦到元代,涉及到帝王将相、隐士、诗人、烈女等对象,空间跨度涉及全国各地,体裁运用了古体、律诗、绝句,算是比较丰富的了。但是经过比较,这些题材都比较松散,不成规模,无法构成整体的冲击力。王佐最为集中、能够成为规模的咏史题材,则是唐宋时期海南贬谪文化,诗作数量达十八首之多,计有:《海外四逐客》四首,《茉莉花》二首,《含笑花》二首,《崖州裴氏盛德堂》《读宋史》《咏史八首之李卫公德裕》《木棉花》《题东坡祠》《次友人游载酒堂》《澹庵井》《卢相多逊》等各一首。涉及的对象包括苏东坡、“五公”(李德裕、李刚、赵鼎、李光、胡铨)、卢多逊、丁谓,他们代表了唐宋时期贬居海南的最重要的人士,他们与当时的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海南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吟咏的方式看,有分咏,有合咏,有直接对历史人物进行吟咏,有通过历史遗迹对历史进行吟咏,有因读史而咏史,有将咏史与咏物融合,有组诗,有单篇。体裁为七言律诗和七言绝句。我们可以说,有关唐宋时期海南贬谪人士的吟咏,在王佐咏史诗中是最富有冲击力,代表着王佐咏史诗的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海南士人的某种心态。
三、“海外四逐客”在王佐咏史作品中占重要地位
综观王佐对海南谪客的吟咏,以组诗《海外四逐客四首》最具有感染力。这组诗共四首,分咏李纲、赵鼎、李光、胡铨,形成对“南宋四名臣”的集中歌咏。
第一首题为《李忠定公纲》,题下自注“至琼三日遇赦返”:
公来方始是朝廷,争奈吴儿苦讳兵。当扆戴天宁国是,杜邮兴念岂人情。忍教丞相过南海,更有何人说北征。自古浮云能蔽日,重昏世及几时明。[1]卷九25
诗下作者加按语云:“晦庵先生尝言,李纲入来方成朝廷。杜邮乃秦杀白起处。时京城围急,李纲当国以兵为任,群奸欲阻其谋,劝钦宗杀纲和金,同列有书杜邮二字示纲释兵者,二帝在金,封徽宗为昏德侯,钦宗为重昏侯。礼运疏云:父子相继为世,兄弟相传为及。”[1]卷九25参照按语,诗篇引用朱熹之语来肯定李刚入相对朝廷的重要性,又运用秦国杀白起的典故对投降派欲害忠良的事件进行了深刻批判,“重昏世及几时明”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昏聩的徽钦二帝。力主用兵的栋梁被贬谪海外,讳兵如疾的奸邪却如豺狼当道,释兵的二帝昏聩无能,这正是诗篇所要揭示的宋朝历史的悲剧。
第二首题为《赵忠简公鼎》,题下自注“卒于崖州斐氏宅”:
身骑箕尾作山河,气壮中原胜概多。立赞建康开左纛,坐挥羯虏倒前戈。孤忠唯有皇天在,万口其如国是何。直待崖州沧海涸,英雄遗恨始消磨。[1]卷九26
赵鼎是被《宋史》称作与李纲齐名的“南渡名相”,力主抗金,为秦桧所忌,被多次贬谪,最后贬谪到吉阳军。为表现对投降派的抗议,赵鼎绝食自杀而死,临死前自书铭旌曰:“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3]王佐诗化用赵鼎自书铭旌句,歌颂了赵鼎在抗金过程中的伟大贡献和气壮山河的英雄气节。但是在万口议和的政治环境下,赵鼎的孤忠和壮志,只能成为千古遗恨。诗在正面歌颂的同时,表现了对投降主义的愤恨之情。
第三首题为《胡忠简公铨》,题下自注“恩宥还”:
大朝廷作小朝廷,人世乾坤已不成。志士拊心思蹈海,渠奸呼党贺登瀛。共知甘饮三吴水,谁念幽栖五国城。公去如今三百载,海潮尤有不平声。[1]卷九26
这首诗歌咏的对象为胡铨,但诗的重点却是对南宋小朝廷的议论和讽刺。首联站在正统立场上谓南宋王朝偏安一隅,大朝廷已不存在,人世乾坤已不成立。颔联用对比手法,抨击以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占据上风,像胡铨这样的志士虽有抗金之心,却难以成功。颈联最为沉痛,徽钦二帝被金人幽禁在北国的五国城,对于这种中华有史以来都没有过的奇耻大辱,却没有人念及,宋高宗和秦桧等一群昏君奸臣不知耻辱,只躲在东南一隅甜甜地喝着三吴之水,所含讽刺和批判是何等深刻。末联感叹胡铨力主抗金、统一祖国、迎回二帝,反遭远谪海外,说三百年之后,海潮犹为之不平,实际是表现了作者和人民的不平。第四首题为《李参政光》,题下自注“恩宥还”:
五十三家祸未消,何人海外得逍遥。皇天后土尤堪倚,明月清风不费邀。但看琼岛一身在,莫怨图书万卷烧。千古牧羊亭下土,好还天道不曾饶。[1]卷九26
诗后作者加按语云:“秦桧恨光不已,必欲致其死,根究贬人通书,光家惧罪,书籍万卷尽烧之。牧羊亭,秦桧葬在建康,今应天府境内,明弘治初年,冢为盗所发,其祸甚惨。”[1]卷九26四首诗中,这首诗写得最为轻松愉快。虽然开头一句下得沉重,但是次句一转,以旷达观点荡开,谓李光在海外反而能够逍遥生活,享受海南的清风明月,只要能够保存一身,万卷图书被烧又有何惜?最后以天道公正、终究不饶奸贼作结,反衬出高风亮节的李光之永垂千古。
这一组四首,皆以七言律诗为之,一气呵成,笔法多变,顿挫有致,堪称王佐咏史诗之杰作。
对于南宋四名臣,王佐最为崇敬的是胡铨。除于《海外四逐客四首》合咏之外,王佐还创作了《澹庵井》《和友人归姜驿夜宿胡澹庵祠》《茉莉轩》四首诗来写胡铨。
胡铨因作《戊午上高宗封事》力主抗金而忤秦桧,被贬谪吉阳军(今三亚),经过临高境内时,曾在一片树林避暑,而得甘泉,惠及一方,后临高名士戴雄飞因于其处立“澹庵泉”碑记之,汲者不绝,遂为井。王佐过此而作《澹庵井》:
中兴封事百年无,身倚皇天自不孤。酌罢清泉问秦桧,已无寸土寄头颅。[1]卷十21
诗下有个长长的自注,记叙秦桧阴结金人,杀害忠良而与金国议和,宋高宗反而归功于秦桧。秦桧为自己作墓,恐人发冢,而于墓中暗射机关。至明弘治年间,秦桧的坟墓为盗所发,机关已尽失其效,头颅骨灰被弃于草间。王佐在自注的结末感叹道:“噫!澹庵先生,生前立朝,曾无容足之地,而身后足迹所经,皆为乡井。秦桧生为宰相,志欲全吞吴越,而死无葬地。善恶终报如此,天道昭昭,其可诬哉!”[1]卷十22读此自注,则《澹庵井》诗作的主题便不言而喻了。七律《和友人归姜驿夜宿胡澹庵祠》
炎荒回首望中原,云海茫茫正断魂。空有寸心悬日月,难将一手转乾坤。北人府库千金费,南国封章万古存。当日戴天称叔侄,可曾都是赵家昆。[1]卷九24
为和友人之作,友人夜宿澹庵祠而作诗,王佐因而和之。澹庵祠为临高人为祭祀胡铨所立,寄托着临高人民对胡铨的爱戴之情。王佐作品前四句遥想胡铨被贬谪海南,茫茫北望,徒有雄心,而无力扭转乾坤的愤慨心情。接下来高度赞扬了胡铨《封事》一文对金人的震撼和永垂千古的价值,最后辛辣讽刺了宋高宗的屈辱行径。
茉莉轩为宋朝临高县令谢渥所建,胡铨贬谪吉阳军路过临高,应谢渥之请,于茉莉轩为当地儒生讲学,胡铨因为之题额“茉莉轩”。王佐的《茉莉轩》由两首七言律诗组成:
茉莉香中小小轩,历年三百尚依然。珠崖逐客才过海,南渡君臣已戴天。磊落封章轰宇宙,凄凉遗墨化云烟。我怀千古中原恨,几度经行涕泗连。(按:封章指澹庵所上封章事,金人购之千金不可得者。遗墨,指所书轩额,久废,今始复之。)[1]卷九27
相逢莫话绍兴年,每为先生一怃然。国是到头成底事,奸非开路逐忠贤。忍同刘豫三分国,卖却唐尧一半天。杰阁格天今草莽,乾坤犹罩小茅轩。[2]9
从诗意看,王佐造访茉莉轩之时,胡铨的题额墨迹早已不存在,使得王佐心情不免低落,更主要的是南宋小朝廷的软弱无能,投降派的横行霸道,胡铨等爱国英雄的悲惨命运,使王佐痛心彻骨。“我怀千古中原恨,几度经行涕泗连”,正表达了王佐莅临茉莉轩时的悲愤心情。但是历史总有一天会还公道,“杰阁格天今草莽,乾坤犹罩小茅轩”,卖国贼的豪华府第早已变成荒野,而忠良曾住过的小小茅轩却永远立于乾坤之间,这给王佐心理添加了一些平衡。
对于“南宋四名臣”,王佐何以尤其偏爱胡铨?我们认为,这尽管与王佐特别推崇《戊午上高宗封事》有关,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恐怕不在这里,而是因为胡铨是唯一与临高发生密切关系并留下美好故事的一人。胡铨除发现澹庵泉之外,对临高更重要的贡献是受县令之请,为学生讲学,在当时就发生了作用,所形成的文化风气,对后世的影响更加深远。王佐于“四名臣”都很崇敬,而所受遗风影响最多者,当首推胡铨。王佐是一位十分热爱自己家乡的儒者,而胡铨成为家乡临高的骄傲。在这种文化心态之下,王佐尤其多歌颂胡铨,就是容易理解的了。
四、《宋史》、盛德堂:王佐“宋史情结”的综合载体
如果说上述对“四名臣”的歌咏是通过一个个历史人物来表达作者对宋朝那段屈辱历史进行评价,那么王佐的《读宋史》和《崖州裴氏盛德堂》则是通过历史著作和历史遗迹的感发,运用合咏的方式,扩大所涉及的历史人物,来表现他的“宋史情结”。
王佐的七律《读宋史》,虽题为读“宋史”,所咏历史却并非全部宋史,而重点仍是“南宋四名臣”生活的那一段:
南边七叶选重光,世及重昏亦可伤。宫色渐非天水碧,柘袍又看女真黄。外夷岂敢分中夏,一汴何因说二杭。堪恨三朝谋国是,是谁惟有杀忠良。[1]卷九25
前六句历数从太祖灭掉南唐后主(李煜字重光)统一中原的兴盛,到钦宗(被金人封为重昏侯)被外夷所掠北宋灭亡,宋高宗被迫逃到杭州建立新都,以反诘语气表现作者的伤痛。末联仍把宋代衰亡的原因归于投降主义对忠良的杀害。作者在此诗下有自注云:“徽杀陈少阳,钦杀李伯华,高杀岳飞父子。”作者在《澹庵井》按语中叙述秦桧杀害忠良的经过时亦云:“桧实阴恃虏势,度宋帝畏虏,不敢违己。而虏人所忌者,中兴四将。于是首起大狱,杀岳飞父子,以威韩、张三将。暮年又起大狱,必欲尽覆异己者赵鼎、张浚、胡铨等五十三族。”可见本诗“堪恨三朝谋国是,是谁唯有杀忠良”是对批判投降主义迫害“四名臣”的扩展,或者说王佐的“四名臣”情结始终与对北南宋之交屈辱历史的伤痛交织在一起,对四名臣等忠良的爱与对投降派奸邪小人的恨是等同的,它们共同构成了王佐对这段历史的诗史式的评价。
位于崖州的盛德堂,原为唐代名相晋国公裴度后人的居所,宋代赵鼎与胡铨先后贬居于此,赵鼎死于此地,胡铨居数年遇赦而归。王佐作七律《崖州裴氏盛德堂》咏道:
晋国亡来六百年,云礽今见海南边。风流尚是元和脚,主客谁同南渡贤。落落朱崖余栋宇,盈盈绿野旧风烟。我怀三姓上千古,欲向杭州问老天。[1]卷九13
诗下作者加按语云:“裴氏,晋公度孙也。赵忠简公鼎、胡忠简公铨谪崖时皆住此堂,李参政光时相往还。裴祖闻义在宋守昌化军,即儋州,儋在隋为朱崖郡。”又作者在“我怀三姓上千古”句间自注云:“秦桧于天章阁书胡赵裴三字,憾之。”由此可知,裴氏也在秦桧憎恨之列。王佐从当代名相裴度写起,而延伸到宋代的同被秦桧所迫害的赵、胡、李、裴,则其所怀,实乃曾居于盛德堂的唐宋名贤。从结构看,诗的大部分是在歌颂唐宋明贤,而于篇末显露批判之笔,杭州为南宋都城,则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偏安一隅的南宋昏君奸臣。
五、苏东坡、李德裕:崇敬中的复杂心情
在海南岛,“五公”齐名,并嗣于一祠,为海南人民所崇敬。王佐对李德裕也是敬佩的,但是从《鸡肋集》中对贬谪之士的歌咏看,他对待“宋代四名臣”与李德裕的态度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鸡肋集》中关于“四名臣”的吟咏,除了《澹庵井》是绝句之外,其余全部用七律,而关于李德裕的吟咏,只有两首七绝。更深刻的是,王佐总是把“四名臣”与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交织在一起,笔下的“四名臣”都是充满民族气节而受迫害的英雄,与之对立的则是民族败类、奸邪小人。而王佐笔下的李德裕则有所不同:
孤寒八百望崖州,恩怨分明未是仇。但使君心合君子,不须憎李自憎牛。[1]卷十23
这首诗为王佐《咏史》八首之一。诗中虽表现出作者对李德裕的正面肯定,但是赞扬的内容却只是取自《唐摭言》的一则题为《好放孤寒》的轶事:“李太尉德裕颇为寒畯开路,及謫官南去,或有诗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 。’”[4]可见,诗中所肯定的仅仅是李德裕爱惜贫寒之士的美好品德。再从诗的后二句看,王佐是在“牛李党争”的背景下,只是把李德裕看作党争中的“君子”一方,并没有就是否关系到国家的大是大非做出评价。王佐的另一首诗关于李德裕的诗是题为《木棉花》的咏物诗:
艳艳烧空出化炉,一春花信最先孚。看花未暇评牛李,且醉东风听鹧鸪。①这首诗亦摘自周济夫所著《琼台小札》,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
据周济夫分析,李德裕虽不失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但是他身陷党争,纯属宗派之争,古代的有识之士早看到了这一点,王佐此诗是咏物与咏史的结合,用木棉花的光明磊落反衬人间的蜗角之争,“‘看花未暇评牛李’,实在是对一切私党争斗的绝妙讽刺和无情唾弃。”[5]周济夫用语虽然严重了点,但是王佐对“牛李党争”的态度,与对宋代“战和斗争”的态度,确实具有很大的区别。
王佐对另一位文化巨人苏东坡崇仰有加,他以载酒堂和东坡祠为载体,表现了对苏东坡的观点:
鹃送南声到洛阳,浮云白昼掩阳光。南来文字乱天下,天遣先生閟海乡。过化真成孚草木,人心犹自爱桄榔。无因得载城南酒,仰止惟持一炷香。[1]卷九24
——《次友人游载酒堂韵》
先生辙迹到遐荒,象魏新年法渐详。卜世渐看杭易汴,传衣又见吕仍王。本来大块为安宅,不道眉山是故乡。人定胜天千载下,尽输琼岛一枝香。[2]156
——《题东坡祠》
两首诗都涉及到了北宋的政治,但是北宋政治党派的斗争,与南宋主战派、投降派的斗争,性质是有差别的,所以这两首诗中对新党的批评并没有像其他诗中对投降派的抨击那样激烈。第一首诗的重点是“过化真成孚草木,人心犹自爱桄榔”,苏东坡贬谪海南以其伟大的人格和空前绝后的学识对海南历史文化的影响,寄托着海南人民对这位伟人命运的惋惜和恩惠的不忘。“仰止惟持一炷香”则鲜明地表现了王佐对苏东坡无上的崇敬之情,这种语气在其他咏史诗中是没有的。
王佐在学问和思想上受苏东坡的影响是重大的,他常常直接运用苏东坡的语言和观点进行议论,如在《赠地师曲全徐先生序》中,自“盖阴阳相化”至“气之所在,何有于内外远近,东西南北之间乎”[1]卷三28,基本是苏东坡《天庆观乳泉赋并序》的翻版。《重建载酒堂记》,谓苏东坡生前“似乎不能一日终其身”,后数百年却俨然享有祠祀,“此岂人为所能也哉”,接下来有一段议论:
盖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惜先生作韩昌黎庙碑,固尝言之,而今验之矣。是故堂不废者,此理存也。不废之者,存此理也。此理存,是人心之不亡也;存此理,是人心之所不亡也。皆天也,非人也。传曰,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至是而知天之定也久也。[1]卷二2
这段议论直接依据苏东坡《韩昌黎庙碑》的观点,再引用古人关于天人关系之理论,而得出天定与人定的辩证关系。明乎此,再来看《题东坡祠》的末联,诗意不解自明。
但是王佐对苏东坡也不是盲目尊崇。他作《论<古史孔子列传>》,对苏辙在《古史》中把《史记》的孔子“世家”改为“列传”的做法进行了批判,谓:“大抵观人得失,必本于父兄师友。余观子由之失,而知其有自来矣。盖由其兄子瞻平日不喜《史记》,故子由作《古史》,务矫马迁之作,自以为是,而无所忌惮。自以为是于家庭,而不能尽合于天下之公言者,苏氏之学也。”[1]卷四2认为苏子由的错误来自其兄苏东坡的影响,并指出“苏学”的缺点。王佐的观点是基于朱熹之学而产生,明代把朱熹之学定为科举考试的正宗,王佐在这种政治文化环境之下产生这样的观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王佐对苏东坡的异议,并没有在诗歌中表现出来。诗歌中所表现的,完全是一片景仰之情。
六、卢多逊、丁谓:王佐笔下的反面谪客
王佐是一位是非分明、观点鲜明的诗人。宋代谪臣中,“五公”和苏东坡在他笔下都是歌颂的对象,而另外两位贬谪海南的宋代宰相卢多逊、丁谓,则成了其笔下的反面角色。
卢多逊是一位历史评价颇为复杂的人物。作为北宋重臣和宰相,他在开国、平乱、编纂典籍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史学家。但是其缺点也非常明显。他初与开国元勋赵普不和,后又以遣堂吏赵白交通秦王廷美事件而下狱,终流配吉阳军,居水南村。王佐在《卢相多逊》诗自注中记述一件揭示卢多逊人格污点的文字:“宋太宗朝,卢相交通秦邸,贬崖州。尝于旅邸中遇老媪,能言京邑旧事。问之,云:‘吾儿为某官,被宰相卢多逊以私恨贬来,死,遗老身。彼卢相者,妒贤嫉能。倘不死,终当见之。’多逊赧去。”[1]卷十26虽然丁谓居住崖州水南村时,事实上对当地文化发展产生了正面影响,但是王佐对他的污点仍无法原谅,于是作《卢相多逊》加以讽刺:
青天明主不堪欺,磐石元勋岂可移。莫怪老姬穷旅邸,能谈京邑旧因依。[1]卷十26
王佐对丁谓的吟咏是凝聚在《含笑花》二首咏物诗中的:
尧草元能指佞臣,逢花休问笑何人。君看青史千年笑,奚止山花笑一春。
白白红红竞好春,含香羞涩似含颦。无端却被崖州户,错怪闲花解笑人。[1]卷十19
丁谓同样也是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但与卢多逊相比,丁谓的人品则更多为人所诟病。他曾极力讨好名相寇准,当成为参知政事时又极力打击寇准,取而代之,迎合皇帝,大造宫观,勾结宦官,独揽朝政。苏东坡在《荔枝叹》中曾讽刺过“前丁后蔡相笼加”[6]2127,把他与大奸臣蔡京同等看待。丁谓被贬崖州,见含笑花,曾作诗自嘲:“草解忘忧忧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①见王佐《含笑花》诗下自注。王佐接过丁谓的自嘲而作《含笑花》二首,直指丁谓为“佞臣”,指出佞臣必为青史所笑,又安能怪罪山花?笔调明快,讽刺辛辣,可谓咏物与咏史融合的佳作。
七、王佐的文化心态与个人才情
综上所论,王佐之咏史,在宋代贬谪文化方面用心最苦,用情最深,用力最大,成就最为突出,这代表着王佐历史文化心理结构上的一个鲜明特点,我们在论述中已称之为“宋代情结”。这个情结不仅仅存在于王佐一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也存在于明清时代其他海南知识分子心理结构中,成为海南人文化心态的重要特征。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宋代情结呢?
海南岛虽然建制较早,但是以中原黄土文化为核心的统治理念,以及以北方少数民族为主要矛盾的现实状况,使得孤悬海外的海南岛长期不受中央重视,“即使国力比较强盛的汉代,也没有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必要的开发”[7]②朱玉书、林冠群《苏轼与海南文化》,朱玉书《海外奇踪》,海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至南北朝晚期,冼夫人统一了包括海南岛在内的岭南广大区域,并于隋朝建立之后归附中央,于海南岛重新设置郡县,后来冯盎又以此地区归于唐朝,中央对海南的有效统治自这段时期才算开始。但一方面冼夫人所代表的文化并不属于中原文化,另一方面唐朝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北部边陲,因此中原文化对海南的影响仍然十分薄弱。虽然海南岛在唐朝时已有设立学校的记载,但直到北宋后期苏东坡到达儋州,学校依然形同虚设。这样,海南岛上的正统文化教育一直处于极为缓慢的发展状态。苏东坡、“四名臣”等众多宋代被贬谪海南的正面形象,乃至具有争议的负面人物的到来,才真正改变了上述状态,成为海南文化教育发展的转折时期。后经元代的沉潜,至明代而达到海南文化的繁荣。从海南历史文化发展轨迹看,对明清人来说,元代基本是个空白,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东西。如此,宋代就成为明清尤其是明代海南士人难以割舍的珍贵历史。再加上北宋党争和南宋“战和”之争非常激烈,其中许多杰出人士被贬谪海南,于是贬谪文化成为宋代历史弊端与海南文化发展的纽带。那么,海南士人具有强烈的“宋代情结”,那就是很自然的了。王佐自幼接收中原文化教育,性格清正,爱憎分明,具有正统的爱国思想;又始终沉沦下僚,政治上不得志,那些遭受压制、贬谪海南的正面士人更容易引起他的共鸣。理清了这些问题,王佐为什么沉醉于对“四名臣”、苏东坡的歌颂,为什么对贬谪海南的反面人物进行讽刺,为什么对宋代政治进行如此深沉地思考,等等,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从上述咏史诗看,王佐的这些作品并非表层的就人论人,而是擅长于将历史人物放在政治大事中进行歌咏,将人的命运与政治得失紧密结合起来,做出深沉思考。是非分明,感情强烈,风格以沉郁顿挫为主导。王佐擅长于驾驭七言律诗,格律工稳,只有个别地方超出了格律,如“当日戴天称叔侄”。王佐有一些序文涉及到诗歌,但从这些论述中,我们无法直接看出他本人诗歌创作所承继。从具体作品看,其语言不属于自然流淌一类,而是有一定的锤炼的痕迹,显示出一定的生涩特征,整体上是多议论而少浑成。我们从这些特征大致可以判断,王佐诗歌创作学习宋诗的色彩比较鲜明。另外,上述十多篇诗歌中,相似的情感观点——如遭贬之士的冤屈和遗恨,奸臣之遭报应——不断地在重复;词语如“国是”“重昏”“戴天”“乾坤”等也重复使用。诗歌的数量并不是很多,而出现这样多的重复,令人感到王佐的思路和词汇并不是属于那种十分开阔和丰富的类型。王佐被列为“海南四大才子”之一,毫无疑问,在海南士人之中,是才华出众之人。但是从诗歌创作中所显露的才情看,他的才华也是有一定局限的。他的情感严肃有余而跳脱不足,胸怀朴厚而思路却偏于狭窄。总体说,王佐与中国文学史上的大诗人相比,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1][明]王佐.鸡肋集[M]//海南丛书:第三集:第一卷.海口:海南书局,1927.
[2][明]王佐.鸡肋集[M].王中柱,校注.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
[3]赵鼎.自书铭旌[EB/OL].(2014-12-04)[2014-12-14].http://baike.baidu.com/link?url=Vb07iMJZtvWw5V4Mi30 jAh2wez9LWWvLjXN4Cf8bvkHmiT5SdUf1ESFBXyMefL9IlZ-Rbzk15HGnF-IZu263k_
[4][五代]王定保.唐摭言[M].杨羡生,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9.
[5]周济夫.琼台小札[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147.
[6][宋]苏轼.苏轼诗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2127.
[7]朱玉书,林冠群.苏轼与海南文化[M]//朱玉书.海外奇踪.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