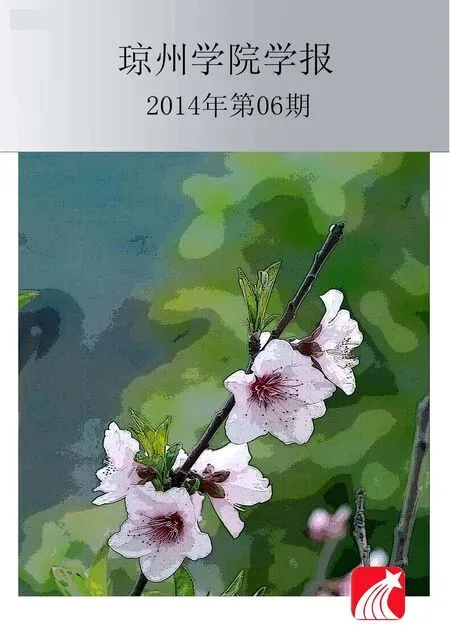叙述与描写:中语纪实文学的美学表现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海南 海口571158)
一、叙述的基本技法
“文章惟叙事最难。”[1]前人这一认识,是对叙事文兴起以来,历代作者在叙事技巧上尽力展现才情,使文章显示出千姿百态的一个总结,也是对研读或写作中为寻找文章形体与客观事物的微妙关系而煞费苦心的经验之谈。它也是对写作艺术难臻佳境的深长的慨叹。难怪章学诚在《论课蒙学文法》中也这样说:“叙事之文,其变无穷。故古今之人,其才不尽于诸体,而尽于叙事也。”[2]
中学语文教材的纪实文学中,文言文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从以正史为主的史传文学,到别传、志、状、碑、序、杂记之类,体裁多样,说明我国的叙事文有悠久的历史。复杂的历史生活,在不同的创作主体那里得到不同方式的叙述、表现。历代作家在叙述客观生活时,又不是简单的照葫芦画瓢,而十分注重表达技巧;讲究叙事笔法,认为叙事要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显,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或“烘云托月,背面傅粉”。叙事意识是一种审美意识的体现。力求笔法多变,避免单调,表明叙事的目的不在于单纯地复述、告知,而是追求艺术效果,发掘主体的创造性,顺应审美感受规律,打动和吸引读者,使文章在完成“述事”的功能之外,具有可供欣赏的独立存在价值。
历代作家积累起来的丰富的叙事经验,得到了印象式的理论总结。有关叙事笔法的论述,就有不少。元代陈绎在《文筌》一书中就将叙事归纳为正叙、总叙、间叙、引叙、铺叙、略叙、别叙、直叙、婉叙、意叙、平叙等十一法。李绂的《秋山论文》则进一步归纳总结,更为准确地概括出顺叙、倒叙、分叙、类叙、追叙、暗叙、借叙、补叙、特叙等叙事笔法,还加以分析举例说明。清人邵作舟在《论文八则》里,又把叙事笔法归纳为十四种:正笔、旁笔、原笔、伏笔、绕笔、补笔、带笔、铺叙立案之笔、捏掇呼应之笔、关锁串递之笔、断制咏叹之笔、详略虚实之笔、宾主映射之笔、点缀传神之笔。而且对每一种笔法都作了解释。更晚一些的章学诚和刘熙载,也分别在《论课蒙学文法》和《艺概·文概》里对叙事笔法作了归纳和概括。
前人的遵从着审美创造和审美接受的规律的叙事经验,为现代人所继承并发展。当代写作家,更为简明地对叙事的基本技巧予以分类归纳。比如就叙述类别而言,以叙述的先后次序,将叙述分成顺叙、倒叙和插叙几种;以叙述的详细程度,分出概叙与细叙;以叙述的线索关系,分为分叙和合叙;以叙述的不同角度,区分出直叙和借叙,等等。从叙述的常用技巧看,有视点、节奏、线索、悬念等,得到注意。此外,繁简、疏密、隐显等艺术辩证法,也在叙述中得到运用。无论是前人所称的叙事笔法,还是今人所说的叙述的技巧,在中学纪实文学中都构成了审美表现中的因素,下面择要举例简析。
顺叙。又称为“直叙”,是按照事件发生、发展、变化等过程的“自然时序”而进行的叙述。顺叙是最常见、也是最基本的叙述方式。运用这种“叙述语言”,叙事结构与事序结构的展开取同一方向。它由头至尾,次第井然,便于组织材料,容易贯通文理,和读者的“接受心理”亦更为贴切、合拍。用顺序来记叙的作品,在主、客观两方面具有这样的特点:时间本身是较为奇特或重要的,无须在表达时予以特殊的强调;作者对它怀有较庄重、持正的态度。如果用西方叙事学的观点来说,它属于叙述者低于主人公的一类。比如,陆定一的《老山界》,叙述红军翻越老山界的过程,就是按现实中的时间顺序来写的,时间本身的每一步展开,都足以引人入胜。鲁迅的《藤野先生》,怀着深沉的、敬重的感情追忆他在异国的恩师,依循老师进入他的生活、印象和情感的过程来写,就很打动人。史传文学在记叙人物时,也多用顺叙。如《屈原列传》《苏武》《张衡传》《海瑞传》等。现代记叙文中的怀人之作,也常用到,如《回忆我的母亲》《一件珍贵的衬衫》。运用顺叙的作品倘若不具备上面说过的审美关系,就会影响审美效果。李绂在《秋山论文》里就说:“顺序最易拖沓,必言简而意尽乃佳。”[1]为了避免平板,拖沓,作者往往在顺序的夹缝中进行描写、议论或抒情,以使文章曲折生姿,又不影响整体格局。从《藤野先生》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技巧的变换与作家的主观介入怎样丰富了叙述的情调。
倒叙。就是将事件的“结局”或“高潮”提前,然后再依“自然时序”而进行的叙述。俗称“倒插笔”。它的好处是其“突发性”造成对读者的“强刺激”,以撩人的“悬念”制造接受者审美心理上的张力。审美时空与现实时空的错位,能使人更直接地感受到把握对象世界过程中的“精神确证”。比如《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汉堡港的变奏》就是用倒叙法。前者是将高潮提前,造成悬念。后者是将结局提前,用事件的效果吸引人们了解原因和经过。《离不开你》用倒叙将一座美的雕像兀然推到读者面前,并以一个疑问,“召唤”人们共同寻求这位女性命运的答案。倒叙使文章活泼而不呆板。清人王源在《左传评》中就说:“叙事之法,切不可前者前,中者中,后者后。若前者前之,中者中之,后者后之,印板耳。”如用倒叙之法,“中者前之,后者前之,前者中之后之,使人观其首,乃身乃尾;观其身与尾,乃首乃身,如灵蛇腾雾,首尾都无定处,然后方能活泼也。”[3]活泼产生节奏、运动感,能刺激审美欣赏。
插叙。是一种暂时中断原叙述线索而插入另一事件的介绍、交代的叙述方式。关于插叙的审美特征及其功用,刘锡庆的《基础写作学》有过这样的揭示:“插叙因系从中插入,所以一般不长,只具有‘片段性’;且多为交代诠释、连带叙介、补隙堵漏的文字。它虽然在客观上能起说‘此’而顾‘彼’、勾‘前’而联‘后’的作用,但主要却体现了作者在叙述中对读者‘阅读心理’的一种体察和尊重。”[4]这种“插叙”的好处是:在突出叙述“主线”的同时,顺便即把一些次要的事实或事件做了叙述,使主次“交叉”,叙述“容量”加大;这种“插叙”有点像电影画面的“切入”与“化出”,适当运用能“调剂”读者的神经,使文章有断有续,有张有弛,在“结构”上富于变化。
随着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和人的叙事思维的发达,插叙在现代文中得到更频繁的使用,它不仅适宜于在有限的文字篇幅内容纳更多的生活内容,也符合人的意识活动的规律。在一篇作品中,假如插叙的频率提高,而“片断”又缩小,那么它就近似于“意识流”或“拼贴图”的叙述方式了。它同叙事结构中的放射线结构方式相对应,表现了人对世界和自身的一种新的认识和把握方式。这在小说中更为常见。插叙又可细分为“补叙”(不发展情节的插叙)、“追叙”(和主要情节线相关的插叙)、“逆叙”(由近及远、由今而古的逆行插叙)等。中学纪实文中的插叙多半是追叙和补叙。比如前面已经分析过的《离不开你》《汉堡港的变奏》。《同志的信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也运用了插叙。史传文学常用作品人物的语言来交待跟主要时间不同步却又相关的内容,也可看作是一种插叙。《苏武》中苏武兄弟因触犯御忌而相继自杀,母亲去世,妻子改嫁,妹妹和子女流散,下落不明的情况,就是由李陵在劝降时讲出来的。
概叙与细叙。概叙即概括的、粗线条的叙述;细叙是详细、具体的叙述。或者是作为审美表现的材料的生活内容本身有主有次,或者是作者有意用密度不同的事实呈像来调整叙述节奏,在一篇作品中,作者不会平均使用笔墨,而有粗细之别。如《鲁迅自传》,作者用点面结合的方法,详略得宜地介绍了自己的家庭状况、求学过程和工作经历。对家庭状况和工作经历用的是概叙,而对他在日本求学,由于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叙述得就细致一些,特别是提到看电影而促使他弃医从文的细节。又如魏巍《依依惜别的深情》,在叙述志愿军战士“美化营地”及“留赠爱物”时,一连用了六个“有”字,概略而粗要地叙述了战士们在离别前夕对朝鲜战友“袒出了他们的一颗颗红心”的动人情景。战士们拿出贴身私藏的爱物:手帕、荷包、腰带,每一件“礼品”都该是包含着一个生动的“故事”的,但作者却并不一一展开,只以“概叙”渲染了浓烈的气氛。而对于典型材料,生动场景,“骨干”事例,即胡明富等三人绣花、题诗的事件,就是生动、细致地展开的,写得详细、具体,有枝有叶,有声有色。概叙“粗”而“快”,犹如电影里的“大全景”,视角开阔,轮廓清晰,给人以整体的认识,较快地推进事件的展开;细叙“细”而“慢”,像是电影里的“特写镜头”,在放慢的时间里给人以“细部”的洞察,精雕细刻地展现事物的面貌。两者结合,粗细相间,快慢有致,叙述因而有点有面,有详有略,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是取得表现效果最常用的方法。
分叙与合叙。分叙是分别叙述同一时间内不同地点的人物活动;合叙则是使分叙的事件复归于原叙述线索的常见顺叙。现实生活中的事序结构是时间轴上的多项空间,在同一时间内,不同的活动在不同的地点发生和存在,而叙事结构只能顺时地,按表现的因果关系将复杂的立体图形投射到书写平面上,这就有了分叙的必要。现代的“分叙”已从“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传统叙述方法中走出来,而采用电影“蒙太奇”多线索“齐头并进”的剪辑方法,如《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在“二月三日下午五点多”这同一时间,就分别叙述了三个地点所发生的三件事情。或者几条线索“交叉并进”,时断时续,自然穿插,如《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的第一节,就同时叙述了三条密切相关的线索。
直叙与借叙。直叙即正面的、直接的叙述,而“借叙”却是从旁借助于他人言谈的间接、侧面叙述。后者相对于前者表现为一种技法,多用于写人。例如《信陵君窃符救赵》,用很多笔墨去写管城门的侯生,正是为了表现信陵君的礼贤下士。这种旁径侧出,借他人他事来表现此人此事的借叙手法,增强了审美兴味,又更有力地表现了人物。
衬笔。是叙事的局部上用以表现人物的一种技法。实际是一种对比。事物的价值是在对比中显现出来的。因此,衬笔的技法在纪实文学中运用率较高。衬笔有正衬、反衬之分。用对立相反的因素互相对照叫反衬;用性质相同的事物互相烘托叫正衬。例如张溥的《五人墓碑记》一文,几乎全用衬笔:用“高贵之子”、“得志之徒”死后默默无闻,和五人英勇就义后的被人所尊敬对比;用“缙绅”的迫于阉党淫威而改变初志,和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对比;用“高爵显位”者的苟且偷生和五人为了保护群众,挺身投案,从容就义作对比,这样,就更有力地反衬出五人的高贵品格。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用的则是正衬笔法。文章写左光斗生前逸事,处处以史可法的刻苦攻读,人才出众,衬出左光斗的高大形象。在一些表现民族气节的古典作品中,正面人物的崇高形象、壮美情操,往往是在对比中显得更为鲜明。比如《苏武》《阎典史传》,都是用降将的怯弱或无耻,衬托出主人公严辞拒降的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叙述角度。是指作者在叙写事件时所采用的观察点。即作品从什么“窗口”观察生活,从哪个方面反映生活的问题。它同主题密切相关,同一题材,可以从各个不同方面表现,从不同的角度去反映。角度不同,其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的内蕴也就不尽相同。比如,作为客观发生过的“三·一八”惨案,不同人就可以有绝然相反的判断。“几个所谓学者文人”发表文章,污蔑遇害的爱国学生“莫名其妙”、“没有审判力”,因而盲目地被人引入“死地”。而鲁迅才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地看到了青年学生爱国行动的进步意义。又如《离不开你》要是从刘桂芬本人的角度看,也许更多是她和丈夫的感情经验,即特殊的人生之爱、夫妻之情的一种并非大不了的延长。然而,作家茹志鹃从一个较高的时代制高点上却发掘出了普通人爱情中蕴含的先进社会理想的巨大力量。再如,《壮士横戈》,如果在另一种写作境遇里,或是从另外的角度写,也许主人公个人的切身生活要求同意识到的非个人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要被回避,因此反而减弱了人物选择的悲壮色彩,削弱了艺术感染力。可见,纪实文学的叙述角度虽然不及虚构文学的小说显得至关重要,后者通过不同的观点——自知观点、旁知观点、次知观点、全知观点的叙述,创造出意味不同、审美角度和方式不同的文学世界,但是,纪实文学的不同的叙述人称(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对客观现象的选择及意义的显现还是大有关系。
视点。是视角重点的简称,从电影艺术中借用而来。由于视点不同,我们可以将客观物体分为特写、近景、中景、远景和全景等等。纪实文学的叙事,也会看到视点的变化。比如《挥手之间》一开头写到“从清凉山上望下去,见有不少人顺着山上大路朝东门外飞机场走去”,这是远景。作者跟几位同志一起“加入向东的人群,一同走向飞机场”这是中景。“送行的人群陆续朝飞机场走去”,又是远景。到“飞机场上人越来越多”,移至中景,接着,吉普车转过山嘴驶来,车上人跳下来,就是近景了。其间又有中景和近景的几次交换,到毛主席站在机舱门口向送行群众挥手,就是“特写镜头”了。视点的交换极成功地制造了波澜和节奏,推出了高潮,完成了对主题的揭示,作者随自我感情的起伏,调节着审美表现的力度和速度,收到很强的艺术效果。
二、描写的技巧及审美要求
作为“呈象”的艺术,描写能够把作家头脑中的意象描绘、浮雕为可感的语言意象,起到再现社会的、自然的环境与风貌,为人物提供活动的舞台或背景,形象地给人物图形写貌并表露其内心世界的作用。根据这一表现功能和目的,描写按不同的标准分为直接描写和间接描写,细描和白描,人物描写和景物描写。其中人物描写又可分肖像描写、语言描写、行动描写、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景物描写又可分为自然景物描写和社会环境描写。此外还有综合性的场面描写。
在中学纪实文学里,人物描写是其重点。因为具有历史和文献价值的纪实文始终是把活动在历史舞台上的人物作为追光对象的,客体的重要性,始终高于叙述者的主观情态,所以它不像抒情散文或虚构小说那样,可以借景物描写寄托创作主体的审美感情,曲折婉转地表达作家对社会生活的看法,或者从自然世界寻回人在历史实践中失落的东西。景物描写中社会环境由于跟人物活动直接关联着,人物的举手投足都会牵动既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因此在纪实文学中还较多地涉笔。而自然景物,则在必不可少的时候才做一些烘托或点缀。偏重审美价值,以抒情性见长的《从百草圆到三味书屋》在中学纪实文学中例外地有大量自然景物描写,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在人物描写中,中学纪实文学重点又放在语言、行动和细节描写上。这是由于纪实文所写的是真人真事,它要表现的是人物对社会的独特贡献,或所作所为的表率作用、认识价值,而不像虚构小说那样可以采用典型化手法,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塑造“性格”,让其活灵活现地成为“这一个”。在小说里,人物的外貌、表情,通常是人物性格的重要表征。为了刻画人物性格,作家又可以利用视角上的方便,按性格化的逻辑设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而纪实文学重在“人物”,不在“性格”,所以肖像描写只用于说明人物行为态势,而不是让它帮助人物在读者心中活起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来,也就用得很俭省。在《藤野先生》《我的老师》《为了忘却的纪念》这样一些抒情性较强的作品里,外貌描写才显示出其特有的光彩。纪实文学的写实性也限制了它不可能去虚拟人物的心理语言。从现代叙事学的角度看,纪实文学的叙述只有“自知观点”和“旁知观点”,而没有真正的“全知观点”。对写实原则的恪守,弱化了它的心理描写。像《离不开你》那样细腻地描写女主人公在遭受丈夫在工伤事故中失去了双臂的意外打击时剧烈的心理冲突,在中学纪实文学里不多见。心理活动能够展示人物的精神境界、思想品质,同时也为外在行为、举止提供理由,它揭示出人物积极选择的动机。这一功能,在中学纪实文学中通常为人物语言描写所取代。语言描写一般又是同动作描写结合在一起的。
比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写在澠池会上,蔺相如大智大勇,再克秦王的场景:
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缻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缻,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缻。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
继章台殿之机智夺璧,慷慨陈辞,不辱使命之后,蔺相如的性格在这里又一次得到辉煌的爆发,他的善于判断,应对敏捷,为了维护国格、宁愿以死相拼,凛然大义威慑上下,通过一连串推进性很强的语言、行动描写表现得淋漓尽致。秦王的恃强倨傲,以强凌弱和在死亡威胁面前的尴尬,赵王的怯懦,秦王左右的失措,也都历历如绘,跃然纸上,在对比中进一步衬托出蔺相如智、勇、义聚于一身的光辉形象。人物语言、动作包括神态的进逼性和针锋相对,又准确地再现了当时的“场面”,富有戏剧的情趣。又如《左忠毅公逸事》描写左光斗被诬下狱,遭受酷刑,作为深得知遇的史可法冒险混入牢房探视的情景:
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柱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左光斗发“怒”的动作和语言,饱含着这位正直的爱国者对奸人的憎恨和锄奸救国的急迫感,对后继者寄予的厚望以及对无谓牺牲的焦虑。个人的生死置于度外,一心以天下事为念。为了救国,他必须斩断私情,因此,骂得越重,爱得越深,所望越是迫切。在语言、动作和神态的背后,是人物坚强不屈、大义凛然的的动机所在。
描写用以刻画人物形象,可以是正面进行,也可以“烘月托月”,从侧面予以表现。侧面描写,是叙述中的衬笔的细致化,上两例中,秦王的“不怿,为一击缻”和“左右皆靡”,都是对蔺相如的智勇慑人的反证。史可法的话:“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进一步表现了左光斗的锄奸救国的坚强意志。《苏武》中,李陵劝降未成,“喟然叹曰:‘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霑衿,与武决去”,也从另一个角度写出了苏武可杀身不可夺志的浩然正气。侧面描写,是对人格主体的社会价值的一种“取证”。
描写作为人物品质和事件性质的手段,其审美要求就是“突出特征,绘声绘色绘形;以形传神,新颖精妙逼真”[5],白描、工笔画、细节描写,都是达到这些审美要求的最有效的技法。
“传神”是语言表现的追求目标。宋人黄庭坚就提出过,“事须钩深入神”[6]。所谓“神”就是指人或事物内在的本质特征。状物写人,若能抓住内在的精神特质,就可以说达到了传神的地步。传神写照关键在于抓住对象的个性特点,即写其精神“独至”之处,因为“人之为人有一端独至者即生平得力所在……人精神聚于一端,乃能独至,吾之精神亦必聚于此人之一端,乃能写其独至”[7]。中学纪实文学所写到的历史人物和当代英雄,莫不是执着于某一个方面,意志和生命力都聚焦在一个信念上,宁折不弯,从而成为意识主体的观照对象。作家对他们的内在精神品质,往往用生动的细节予以表现。蔺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和“‘……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的动作和语言描写,雕像般地呈现了他的英勇精神。左光斗“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骇目惊人,人物的内在精神能量放出灼目光彩。《殽之战》里,先轸听说文嬴出主意放了秦囚,当着襄公的面发怒,“不顾而唾”的细节,极富个性化地表现了这位军人的耿直以及对军情国事的预见能力。
“白描”是最见功力的传神写意手法。它用最少的笔墨,不加渲染地勾勒出事物的特征和形貌,表现事物的内在神韵。它通常不设喻,不藻饰,只是以质朴的文字抓住描写对象的特征,以叙代描,淡淡几笔,简明生动地勾画出形象来,以少胜多,平中见奇。汉语文言是一种极精练的表达工具,所以白描是我国叙事文的传统。鲁迅先生很提倡这种写法,他说自己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能将意思传达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这一创作原则,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体现。例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下读书那段:
……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极简洁的文字勾勒出了一位沉醉在古文的韵律之中的老先生的神态。令人忍俊不禁。又如《为了忘却的纪念》写柔石对社会的看法:“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廖廖几笔,就画出了一个心地纯朴天真而又带着几分迂气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
跟工笔细描的精雕细刻、体物入微相比,白描不在于对象在画面上的纤毫毕现,穷形尽相,而是摄其精要,留下空白,让读者调动意识经验去填补。
[1][清]李绂.秋山论文[C]//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四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4004.
[2][清]章学诚.论课蒙学文法[M]//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686
[3][清]王源.左传评[M]//丁琴海.中国史传叙事研究.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256.
[4]刘锡庆.基础写作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217.
[5]朱佰石.现代写作学[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410.
[6][宋]黄庭坚.赠高子勉[C]//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1979:320.
[7][清]魏际瑞.伯子论文[M]//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四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3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