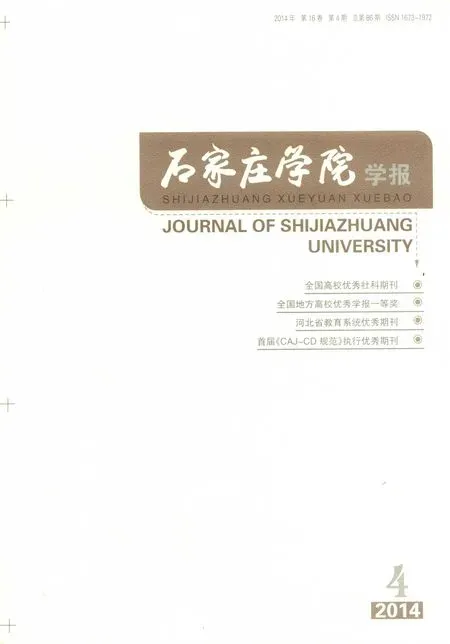从元氏汉碑看东汉的祷山求雨弥灾
王文涛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从元氏汉碑看东汉的祷山求雨弥灾
王文涛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汉代帝王将山岳与河流的祭祀纳入祭礼,使其成为国家祭祀活动的一部分,元氏汉碑中祭祀山神的文字正是东汉帝诏的反映。碑文记述了元氏县境内名山纳入国家祭礼和建祠祷山求雨的内容。祭祀元氏诸山神的费用主要出自郡县的地方财政,地方财政困难,可申请朝廷财政资助。碑文中的“王家”指朝廷,“王家钱”和“王家经钱”是中央财政经费,不是常山国的经费,也不是常山王私人的费用。东汉中央和地方政府为求雨而举行的祭祀名山活动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灾害救助方式。
元氏汉碑;祈祷山岳;求雨;弥灾;王家钱
元氏县旧为冀州地,战国初属中山,后并于赵国,始封公子元于此,因称元氏至今。这里曾是今石家庄地区的文化政治中心。汉代常山国治元氏(在今河北元氏县殷村乡故城村),辖13县。元氏县境内有六大名山:无极山、三公山、封龙山、灵山、白石山、石溜山,均为秦汉三国时期的北方名山。元氏东汉碑刻七通,从汉安帝元初四年 (117年)至灵帝光和六年(183年),历时66年。杜香文先生编著有《元氏封龙山汉碑群体研究》一书,对元氏汉碑群体作了系统的历史考察和叙述,着重介绍和论述它们在中国文化史和书法史上的深远影响及重要地位,对于本文所论问题有所涉及,但论述不够集中和深入,本文的工作是希望通过对元氏汉碑和汉代文献的解读,丰富与元氏汉碑相关的祷山求雨弥灾观念和行为的认识。下面先按时间顺序叙述七通元氏汉碑祷山求雨的内容。
一、元氏七通汉碑所见祷山求雨
(一)祀三公山碑
《祀三公山碑》全称 《汉常山相冯君祀三公山碑》,俗名 《大三公山碑》。东汉安帝元初四年(117年)常山国相冯君立。杜香文认为,三公山不是今河北元氏县仙翁寨山,而是元氏县西部高、中、低一组三座山的统称。[1]50三公,意为三阶、三台。这一带是汉代常山郡祭祀、祈雨的重要场所。
元初四年(117年),陇西郡人冯君就任常山国相,“到官承饥衰之后”。在此之前的元初元年(114年),“郡国十五地震”,水、旱、风、雹灾、山崩等相继发生。元初二年(115年)“郡国十九蝗”。冯君听当地人说,元氏境内的三公山神和御语山神十分灵验,以前官吏和百姓祈祷祭祀,常常乌云兴起不过肤寸,就能普遍降雨。近几年遭受羌乱影响,加之蝗灾和旱灾屡有发生,百姓流亡,道路荒芜,祭祀稀少,因此,祥和瑞气不至。于是,常山国相冯君命人占卜选择风水吉地,在县城西北建立祠堂神坛,“荐牲纳礼”,让三公山神享用。“神熹其位,甘雨屡降,报如景响。国界大丰,谷斗三钱,民无疾苦,永保其年。 ”[2]33-34
(二)三公御语山神碑
《三公御语山神碑》又名《三公山神道碑》《三公山神碑》,与《无极山碑》常混为一谈。建于质帝本初元年(146年)。沈涛《常山贞石志》首录其文,并详加叙述和考证,遂为世人所知。沈氏认为此碑是“因求法食,兼记开道之绩”[3]。“法食”,祭祀用的食物。
本初元年(146年)旱灾严重,“自春涉夏,大旱炎赫”。五月甲午,质帝下忧旱诏:“祷祈明祀,冀蒙润泽。前虽得雨,而宿麦颇伤,比日阴云,还复开霁。……郡国有名山大泽能兴云雨者,二千石长吏各洁斋请祷,竭诚尽礼。……遣使者案行,若无家属,及贫无资者,随宜赐恤,以慰孤魂。 ”[4]卷六
碑文内容是常山国元氏县吏民承奉朝廷诏旨,祷山请雨获应,于本初元年(146年)二月上书尚书台,为三公山神和御语山神求法食。此碑漫漶严重,缺失太多,几不可读。碑文第十四行:“遣廷掾□□具酒脯,诣山请雨,计得雨。 ”[5]14《三公御语山神碑》中还有“山道”“通道往来”“通利故道”“王家经钱给直”等文字。修祠庙祭山神求雨和“通利故道”都是大工程,元氏县的财政难以负担,由常山国相奏请朝廷,用“王家经钱给直”协助解决。事毕,勒石刻铭,以颂功德。
(三)封龙山碑
《封龙山碑》又名《封龙山颂》,全称《元氏封龙山之颂》。汉桓帝延熹七年(164年)十月常山国相汝南人蔡龠立。此碑最早被南宋郑樵收录在《通志·金石略》中。
碑文中说,封龙山是北岳诸山中的精华。山势雄伟高大,“与天同燿。能烝云兴雨,与三公、灵山协德齐勋。国旧秩而祭之,以为三望。遭亡新之际,去其典祀”。桓帝延熹七年(164年)正月,常山国相蔡龠、长史沐乘敬奉山神的美德,请求举办隆重的祭祀。认为山神广施恩惠于百姓,理应受到敬献圭璧和七牲的盛大供奉。桓帝下诏批准,命官员郞巽等人,“与义民修缮故祠”。神灵享受祭供,感谢百姓的信奉,雨泽施布,粮食丰收,“粟至三钱”。于是常山国相蔡龠建碑立铭,刻纪封龙山神的功德。“惠此邦域,以绥四方。国富年丰,穑民用章。 ”[2]243-244
(四)三公山碑
《三公山碑》又名《小三公碑》。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四月元氏左尉上郡人樊子义立。此碑最早收录于北宋欧阳修《集古录》中,北宋赵明诚《金石录》中也有收录。碑文云:
三公山神明的降福和保佑是在暗中,表面看不到行迹。①王充《论衡·明雩》:“况雨无形兆,深藏高山,人君雩祭,安得耐之。”在它的神力作用下,“触石出云,不崇而雨”。还能“除民氛疠,莫不祯祉”。三公山神“德配五岳,王公所绪”,一年四季享受圭璧奉祭,每月有酒和干肉祭祀。“飏雨时降,和其寒暑。年丰岁稔……仓府既盈”,百姓都得到了赡养。于是感恩食德,立铭勒石。乃作颂曰:
兴云致雨,除民患兮,长吏肃恭。……四时奉祀,黍稷陈兮。……百姓家给,国富殷兮。仁爱下下,民附亲兮。遐迩携负,来若云兮。……民移俗改,恭肃神祗,敬而不怠。皇灵□佑,风雨时节。农夫执耜,或耘或耔。童妾壶馌,敬而宾之。稼穑穰穰,榖至两钱。[6]43-44
(五)无极山碑
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八月常山人盖高、上党人范迁借神使传言请命,由常山相南阳人冯巡立。欧阳修《集古录》最早收录②当时欧阳修未能辨认出名字,称之为《北岳碑》。,赵明诚在《金石录》中予以更正,此后再无踪迹可寻,亦无拓片传世。南宋洪适在《隶释》中收录了完整的碑文。碑文对事件过程的记载颇为详细,首先是主管宗庙礼仪的太常陈耽和太常丞敏给皇帝的奏书:“男子常山盖高、上党范迁,诣太常言为元氏三公神山。本初元年二月癸酉,光和二年二月戊子诏书,出其县钱,给四时祠具。”盖高、范迁曾经为三公山向太常索法食,请求将祭祀三公山纳入国家祀典,因此,常山国相冯巡“复使高与迁及县吏和卞令俱诣大常(即太常),为无极山神索法食”。尚书代表朝廷询问核实,可见朝廷对于地方神祇进入国家祀典持谨慎态度。碑文说,光和三年(180年)五月,常山国相冯巡派官吏王勋等到三公山求雨,山神让盖高等人传言:把封龙、三公、灵山、无极山的山神聚焦在一起祭祀,可以得到好雨。遵照山神之意祭祀以后,“三公山即与龙、灵山、无极山共兴云交雨”。常山国相冯巡和元氏县令王翊分别举行赛神庙会,报答山神的恩惠。山神又令盖高、范迁与县吏和,尽快晋见太常,“为无极山神索法食,比三公山”。
太常陈耽怀疑“高、迁言不实”,将文书移送常山国,令常山相核查落实。常山相回文说,常山国部督邮书掾成喜与县令王翊“参讯实问”。元氏县界有名山,“其三公、封龙、灵山皆得法食。每长吏祈福,吏民祷告如言,有验乞今。无极山比三公、封龙、灵山祠□,七牲出用王家钱。小费蒙大福,尊神以珪璧为信”。太常陈耽判定常山国相冯巡所言属实,“为民来福,以祠祀为本。请少府给珪璧,本市祠具,如癸酉(指本初元年)、戊子(指光和四年)诏书故事报”。汉灵帝批准,尚书台秉承旨意办理。尚书令忠将实施意见奏报雒阳宫。光和四年八月十七日,尚书令忠下发皇帝的诏书给太常陈耽。太常陈耽和太常丞敏又将诏书下发给常山相。常山国向下传达执行。诏书中说:
昔在礼典,国有名山,能异材用,兴云出雨,为民来福除央,则祀。元氏县有先时三公、封龙、灵山,已得法食,而独未。光和四年二月,房子大男盖高、上党范迁,奏祀大常。大常下郡国相南阳冯府君,咨之前志,□问耆叟,佥以为实神且明。每国、县水旱,及民疾病,祷祈辄应时有报。……在礼秩祀,有功必报。今时无极山应法食,诚其宜耳。于是言大常,奏可。其年八月丁丑,诏书听其九月更造神庙,恢拓祠宫,置吏牺牲册制。月醮时祠,礼与三山同,乃立碑铭德,颂山之神。[6]44-46
(六)八都神庙碑
杜香文考证,元氏《八都神坛庙碑》为汉灵帝光和年间常山国相冯巡立。该碑在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被磨砻,碑石改刻为《大唐八都神君之实录碑》。地方志中,有《八都神坛庙碑》之名而无其实。[1]128-130因八座神山——封龙山、三公山、无极山、灵山、长山、石溜山、白石山、黄山(即珍珠山,上有北岳神祠)相距较远,祭祀不便,所以在常山城(今河北故城)西门外建八都神坛庙,祭祀八座神山,立有汉碑《八都神坛庙碑》。元代纳新《河朔访古记》云:“八都神坛,在县西故城西门外。”很遗憾,此碑没有保存下来,也没有拓片和文字资料流传。
东汉中后期,常山国、元氏县的官吏民众每遇干旱,即向八位山神求雨。在求雨过程中,不断建庙立碑,形成了八都神坛,就是共祭八座山神的神坛。《大唐八都神君之实录碑》:“八都坛者,都望八山之始坛也。此地名山封龙之类有八,因坛立庙,遂为号焉。”“昔汉光和,州将冯氏,敬而不怠,谷至两钱,感恩立铭。”
(七)白石神君碑
《白石神君碑》俗称《白石山碑》。汉灵帝光和六年(183年)常山国相冯巡、元氏县令王翊立。碑阳云:
礼有五经,莫重于祭。①礼有五经,莫重于祭。语出《祀记·祭统》。郑玄注:“礼有五经,谓吉祀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也。”祭礼也称吉礼,为五经之首,所以最为重要。祭有二义,或祈或报。报以章德,祈以弭害。
古先哲王,类帝禋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建立兆域,修设坛屏。所以昭孝息民,辑宁上下也。
白石神君居九山之数……体连封龙,气通北岳。幽赞天地。长育万物。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终朝日,而澍雨沾洽。前后国县,屡有祈请。指日刻期,应时有验。……
县界有六名山,三公、封龙、灵山,先得法食。
去光和四年,三公守民盖高等,始为无极山诣太常求法食。相、县以白石神君道德灼然,乃具载本末,上尚书求依无极为比,即见听许。
遂开拓旧兆,改立殿堂。营宇既定,礼秩有常。县出经用,备其牺牲。奉其珪璧,絜其粢盛。旨酒欣欣,燔炙芬芬。敬恭明祀,降福孔殷。故天无伏阴,地无鲜阳。水无沉气,火无灾燀。时无逆数,物无害生。用能光远宣朗,显融昭明。年谷岁熟,百姓丰盈。粟升五钱,国界安宁。
尔乃陟景山,登峥嵘,采玄石,勒功名。其辞曰:
唯山降神,髦士挺生。济济俊乂,朝野充盈。灾害不起,五谷熟成。……四时禋祀。不愆不忘。……牺牲玉帛,粟稷稻梁。神降嘉祉,万寿无疆。 子子孙孙,永永番昌。[6]46-48
根据《无极山碑》和该碑的记述,光和四年(181年)二月,常山国房子县巫师盖高和上党郡人范迁,呈文太常,为无极山神求法食。当年八月,得到批准。常山国相冯巡和元氏县令王翊具文说明事情的原委,向尚书台请求,“求依无极为比”,希望白石山也能像无极山神那样得到法食供奉,很快得到批准。这是当时常山国和元氏县的一件大事,收到批文后,扩大旧庙边界,改建殿堂,举行隆重的祭祀。感动了山神,因此“年谷岁熟,百姓丰盈。粟升五钱,国界安宁”。于是建立此碑,歌颂白石神君的功德。
二、元氏汉碑所见常山国官祀经费的筹措管理
汉代国家祀典中的祭祀活动有皇帝祭祀和地方官祀两个等级。皇帝主持的国家大祭的费用由朝廷财政负担,地方官祀的经费主要由郡县地方财政承担。[7]元氏汉碑中的记述,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问题。
祠祀活动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地方官祀经费不足,国家财政予以补助。例如,《隶释·樊毅复华下民租田口算碑》载:“县当孔道,加奉尊岳,一岁四祠,养牲百日,常当充,用谷藁三千余斛,或有请雨斋祷,役费兼倍。”[6]28多数情况下,地方官员发动本地居民出资助祀。如《封龙山之颂》云:“允勅大吏郎巽等,兴义民修缮故祠,遂采嘉石,造立观阙。”[2]244这些义民不是普通的编户,应为当地的豪强大族。《三公御语山神碑》载:“荐圭璧□牲,四时祠□……万□□,以王家经钱给值。”[5]14前引《隶释·无极山神碑》载:“出其县钱给四时祠具。……乞合无极山比三公、封龙、灵山,祠□七牲,出用王家钱。”《隶释·白石神君碑》载:“相、县以白石神君道德灼然,乃具载本末,上尚书求依无极为比。即见听许……县出经用。”
这三通碑记载了常山相、元氏县令及民众请求为境内的三公山、无极山和白石山神确立官祀资格的经过。碑中有三个涉及祭祀费用的关键词语:“王家经钱”“王家钱”和 “县出经钱”。有研究者认为:“‘王家’指的是常山王国,‘经钱’指的是财政的经费。‘王家经钱’‘王家钱’都应是王国财政经费,而绝非是诸侯王的‘私奉养’。因为这三山之祠属地方官祀,不是诸侯王私祠。”[7]此说不妥。“王家”之意有二:第一,犹王室,王朝,朝廷。《书·武成》:“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孔颖达疏:“王季修古公之道,诸侯顺之,是能缵统大王之业,勤立王家之基本也。”[8]卷十一第二,王侯之家。后面有详细的例证作具体论析。东汉的诸侯王国是同郡一样的行政区划,归朝廷直接管辖,诸侯王“衣食租税而不治民”。所以,碑文中的“王家经钱”“王家钱”不能理解为常山王国的财政经费。如果这样解读,碑文中的“王家”就应指常山王之家,“王家钱”就是常山王的私钱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将“王家钱”强解为常山王国的经费,但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常山王国因经费困难向朝廷申请资助以供祭祀山神,所以才有“出其县钱”和“出用王家钱”的区别。检索汉代“王家”一词的用例,没有发现“与郡同级的王国”的含义。限于篇幅,重点讨论东汉“王家”的用例。
(一)《后汉书》中“王家”指王室、王朝、朝廷的用例
《张衡传》:“咎单、巫咸实守王家。”李贤注:“咎单、巫咸,并殷贤臣也。”《尚书》曰:“咎单作《明居》。”又曰“巫咸保乂王家”也。[4]卷五十九
《光武郭皇后纪》:“自古虽主幼时艰,王家多衅,必委成冢宰,简求忠贤,未有专任妇人,断割重器。 ”[4]卷十上
《梁冀传》:东汉外戚梁冀“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殆将千里”[4]卷三十四。
(二)《后汉书》中“王家”指诸侯王之家的用例
《灵帝纪》:“甘陵王定薨。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百余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国文学吏。”李贤注引《汉官仪》曰:“太子舍人、王家郎中并秩二百石,无员。 ”[4]卷八
《光武郭皇后纪》:“郭主 (真定恭王女。恭王名普,景帝七代孙)虽王家女,而好礼节俭,有母仪之德。 ”[4]卷十上
《光武十王传·沛献王辅》:孝王广“有固疾。安帝诏广祖母周领王家事”[4]卷四十二。
《光武十王传·东平宪王苍》:“以骠骑长史为东平太傅,掾为中大夫,令史为王家郎。”李贤注引《汉官仪》:“将军掾属二十九人,中大夫无员,令史四十一人。”“初,苍归国,骠骑时吏丁牧、周栩以苍敬贤下士,不忍去之,遂为王家大夫,数十年事祖及孙。”[4]卷四十二
《光武十王传·中山简王焉》:“永平二年冬,诸王来会辟雍,事毕归蕃,诏焉与俱就国,从以虎贲官骑。”李贤注引《汉官仪》:“驺骑,王家名官骑。”[4]卷四十二
《章帝八王传·河间孝王开》:平原王硕嗜酒,“多过失,帝令马贵人领王家事”[4]卷五十五。
《续汉书》志三○《舆服志下》刘昭注引《东观书》:“中外官尚书令、御史中丞、治书侍御史、公将军长史、中二千石丞、正、平、诸司马、中宫王家仆、雒阳令秩皆千石。”[4]卷一百二十
根据以上的史例,可以认为元氏汉碑中的 “王家”是指朝廷,“王家钱”和“王家经钱”是中央财政经费,而不是常山国的经费。从元氏汉碑的内容看,祭祀元氏诸山神的费用主要出自郡县的地方财政。地方财政困难,可申请朝廷财政资助,而不是诸侯王“私府”之费。地方官祀资格的取得,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必须经由太常直至皇帝批准,足以说明汉代朝廷对地方官祀经费有严格的管理审批制度。这类祠祀活动反映出地方长吏权力日增、地方宗族势力开始向精神信仰领域伸张、中央对地方控制渐趋削弱的东汉地方社会政治生态。[9]
与祭祀经费的管理和使用相关,地方官府还负责官祀用牲的费用,并派专人负责牺牲的饲养管理。如《白石神君碑》说:“县出经用,备其牺牲。”元氏汉碑中,多有祭祀用玉的记载。关于少府对祭玉的保藏和供给,《无极山神碑》说:“为民来福,以祠祀为本,请少府给王圭璧。”
三、汉代山岳祭祀中的求雨弥灾观
汉代祷山求雨弥灾的观念源自远古时代的原始巫术。祭祀山川,是因为“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10]。祈求山神降雨,改善气候条件,减少水、旱、风、雹灾害的发生是祭祀的主题。《礼记·传》曰:“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10]禜是古代禳灾之祭。为禳风雨、雪霜、水旱、疠疫而祭日月星辰、山川之神。山川崇拜与国家制度、政治思想相结合,表现了突出的政治化倾向。与之相适应的是山川神灵的自然属性弱化,社会属性增强。[11]
古人祭祀有很严格的等级制度。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祭以三公之礼,四渚祭以诸侯之礼。诸侯只能祭其邦域内的名山大川。大夫祭门、户、井、灶、室中之神,士庶人等祭祖先而已。《礼记·祭法》说:“功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又说:“日月星辰,民所以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以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10]这里规定了祭祀的对象和说明祭祀的目的。“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10]祭祀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汉代的山岳崇拜继承于先秦。刻于桓帝延熹八年(165年)的《西岳华山庙碑》中有很好的概括:
《春秋传》曰:“山岳则配天。”乾坤定位,山泽通气,云行雨施,既成万物。《易》之义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卬也。地理山种,所生殖也。功加于民,祀以报之。”《礼记》曰:“天子祭天地及山种,岁遍焉。”自三五迭兴,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诸侯。……高祖初兴,改秦淫祀,大宗承循,各诏有司,其山川在诸侯者,以时祠之。[6]25
汉代帝王从维护其统治出发,大力提倡崇拜祭祀山川神灵。汉王二年(前205年)刘邦下“重祠诏”:“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12]卷二五上随着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对国家祭祀活动的影响与渗透逐步加深,对山岳的祭祀就越来越为国家统治者所重视。建元元年(前140年)五月,汉武帝诏曰:“河海润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为岁事,曲加礼。”[12]卷六此诏将国家对山岳与河流的祭祀纳入祭礼,使其成为国家祭祀活动的一部分。
《封龙山碑》中提到“亡新之际,去其典祀”,“亡新”指王莽建立的新朝,因其改制激化社会矛盾,天下大乱,很多正常的祭祀活动被迫停止。
东汉时期,祭祀山岳仍然是国家祭礼的重要内容,并且规定更为明确。建武之元,事举其中,礼从其省,永平十八年(75年)四月,明帝下祷雨诏:“自春以来,时雨不降,宿麦伤旱,秋种未下。……二千石分祷五岳四渎。郡界有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者,长吏洁斋祷请,冀蒙嘉澍。”[4]卷二诏书将国家祭祀的山岳分作两类:一是五岳名山;二是郡国辖区内的名山。建初五年(80年)二月,章帝下“祷雨诏”:“令二千石理冤狱,录轻系,祷五岳四渎,及名山能兴云致雨者,冀蒙不崇朝遍雨天下之报。务加肃敬焉。”元和二年(85年)二月,章帝下“增修群祀诏”:“今恐山川百神应典礼者尚未咸秩,其议增修群祀宜享祀者,以祈丰年,以致嘉福,以蕃兆民。”[4]卷三阳嘉元年(132年)二月庚申,顺帝“敕郡国二千石各祷名山岳渎,遣大夫、谒者诣嵩高、首阳山,并祠河、洛,请雨”,甲戌,诏命“侍中王辅等,持节分诣岱山、东海、荥阳、河、洛,尽心祈焉”,正所谓“分祷祈请,靡神不禜。 靡神不举”[4]卷六。
元氏汉碑中祭祀山神的文字正是东汉帝诏内容的反映。碑文中反映的饥荒、战乱、疾病、旱灾、“沉气”“灾燀”,都是为害人民的祸害和灾殃。碑文中说“为民求富,除殃则祀”,“每国县水旱及民疾病,祷祀辄应时有报”。其他汉碑中也多有类似的词语。例如,蔡邕作《伯夷叔齐碑》曰:“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祷请名山,求获答应。……天子开三府请雨使者,与郡县户曹掾吏登山升祠。手书要曰:‘君况我圣主以洪泽之福。’天寻兴云,即降甘雨”[4]卷一百三。《西岳佛山庙碑》云:“其有风旱,祷请祈求,靡不报应。 ”[6]25“有报”还是无报,难以考证是可以想见的,“兴云致雨”肯定与神灵的作用无关,但反映了汉代民众强烈的生存意识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追求。东汉初年,佛教刚刚传入中国,道教形成于东汉后期。原始宗教中的山岳崇拜在东汉时代依然盛行,长期统治人们的思想意识。人们普遍相信山川之神有超乎寻常的神力,能降雨弥灾。所以对山神恭敬有加,“荐牲纳礼”,“令德不忘”,还要“纪功刻勒”,垂之后世。
元氏汉碑都是为祭祀山神所立,故称为神碑。碑文在讲述天旱祈雨、神明佑助、普降甘霖、农业丰收和谷价低廉的过程中,张扬为民求福的旗号和招牌,以含蓄的笔法,颂扬地方官员常山国、元氏县官员和地方豪强大户的功绩。另一方面,地方官吏祠祀境内名山的活动是其职责所在,祈祷的直接目的是祈盼农业丰收,如果灾害不息,影响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地方官员必须要承担责任。“皇天感物,不为伪动,灾变应人,要在责己”[4]卷三○下。 《后汉书·独行列传·谅辅传》记有地方官员舍身祈雨的故事,反映了循吏覆职尽责的精神。东汉人谅辅任郡从事,遇上夏季枯旱,“太守自出祈祷山川,连日而无所降”。谅辅在庭院中曝晒求雨,发誓说:“如果到了中午还不下雨,我就自焚。”时至中午,大雨降临。“世以此称其至诚”[4]卷八十一。
在祈祷攘灾的观念占主导地位的东汉时期,也有质疑祈祷山川求雨灵验的声音,“若令雨可请降,水可攘止,则岁无隔并,太平可待”[4]卷三○下。但是,由于生产力和抵御自然灾害的力量低下,无法科学解释灾害不息的原因,在天灾人祸面前,祈求神灵佑护的观念依然非常盛行和难以动摇。祭祀名山求雨与雩祭结合,体现出国家统治者渴望降雨的迫切愿望。[13]结合东汉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灾害救助措施来看,在旱灾面前为求雨而举行的祭祀名山活动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灾害救助方式,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1]杜香文.元氏封龙山汉碑群体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2]高文.汉碑集释[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5.
[3]沈涛.常山贞石志[O].清道光二十二年刻本.
[4]范晔,司马彪.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6]洪适.隶释·隶续[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王柏中.汉代祭祀财物管理问题试探[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1999,(1):26-30.
[8]孔颖达.尚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8.
[9]沈刚.东汉碑刻所见地方官员的祠祀活动[J].社会科学战线,2012,(7):99-104.
[10]戴圣.礼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1]张怀通.先秦时期的山川崇拜[J].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2):50-57.
[1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3]张鹤泉.汉碑中所见东汉时期的山岳祭祀[J].河北学刊,2011,(1):62-67.
(责任编辑 程铁标)
On the Praying to Mountain for Rain in Han Dynasty from Yuanshi Ancient Tablets
WANG Wen-tao
(School of History&Culture,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Hebei 050024,China)
The emperors of the Han Dynasty took the praying to mountains and rivers as national sacrificial rites.The inscriptions of praying to mountain deity of the Han tablets in Yuanshi County of Heibei Province are just the reflection of the imperial edict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The sacrifice expenses came from local finance.If in financial difficulties,the aid from imperial finance could be applied.The sacrificial ceremony held by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would be a significant disaster relief.
the Han tablets in Yuanshi County;praying to mountain;praying for rain;disaster relief;wangjia qian
K234.2
A
:1673-1972(2014)04-0019-05
2014-05-0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经验研究”(10BZS013)
王文涛(1956-),男,河南潢川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秦汉史、社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