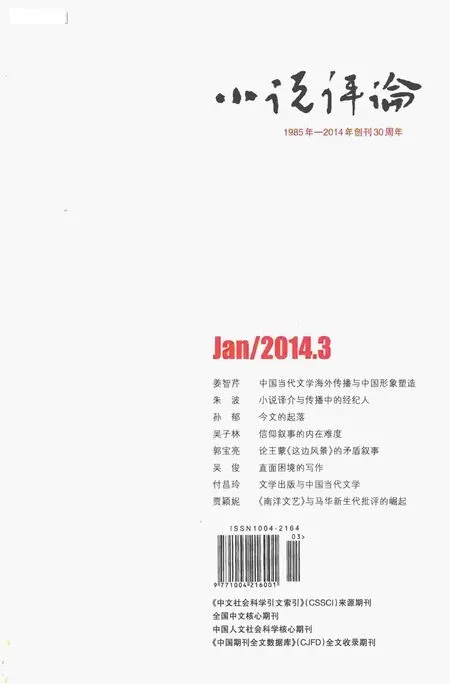个体生存的两难困境与诗意消解——读胡学文的中篇小说《落地无声》
韩传喜
读毕胡学文的小说新作《落地无声》(《钟山》2014年第3期),我产生了一种独特的、交织着尖锐和复杂的审美体验。作品以显微镜般的精细与解剖刀般的精准,逼近当下生活的真实内核,细致而深刻地呈现了个体生存的两难困境与诗意消解,以一种罕见的力量击中了生活的要害,深深地打动着阅读者的痛感神经。
一
漫无边际的现实生活一见到底又深不可测,身处其中的人们很多时候难免遭遇生存的“两难”困境而苦不堪言。究其原因,“人既是一种社会的存在,文化的存在,又是一种个体的存在,生命的存在”,一方面,作为社会的存在,个人总要受到社会秩序、文化伦理的规范与制约,而另一方面,作为生命的存在,个人又总会有自身的生命欲求与自由心灵,但这两种存在又并非始终保持内在的一致,更多时候反而呈现为一种矛盾状态。在《落地无声》中,胡学文以其独特的视角与真切的体察,洞见了个体生存的这种隐秘的矛盾状态,从而向我们展现了个体生命的丰富与复杂。
小说将主人公乔先置放于伦理与情感的纠缠中,通过他的命运遭际传达了生命中难以言说的隐痛与沉陷其中的无奈。在会展中心工作的乔先身体瘦弱、阴郁寡言,处事思虑犹疑、优柔寡断,这种典型的虚弱形象与抑郁气质,使得我们的主人公具有明显的辨识度,不仅指涉了其日常生活的艰辛囧顿,同时也轻而易举地彰显与契合了其精神成长的畸零压抑。
乔先的精神成长是在与母亲的相依为命中完成的。毋庸置疑,像所有“伟大”的母亲一样,乔先的母亲表现出了应有的吃苦耐劳与坚韧顽强,作为一个视儿子重于自己生命的寡母,她甚至处处有过之而无不及:自己吃剩菜,给儿子做喜欢吃的,对她而言是日常的自然行为而已;儿子“提出吃她的肉,她会毫不迟疑地割下来”,乔先对于母亲的此种理解一点也不夸张;任何她认为不利于乔先的事情,甚至女孩子的一封情书,于她都是一种必须坚决清除与扼杀的威胁……尤其在乔先的婚恋问题上,她更是表现出了异常的敏感、审慎与决绝,并亲自选定了可以倾心照顾乔先的朱燕。母亲的这种爱本应给乔先带来踏实的幸福感,成为他积聚生存力量勇往直前的不竭源泉与随时可以停靠的心灵港湾,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它成为一种超出了乔先偿还能力的“巨额债务”,他活着,就必须背负。究其根源,乔先所承受的母爱带有的极强的专属性与专制性,从根本上排斥、禁锢了乔先作为一个鲜活个体的心灵欲求。人不仅需要关爱,同时也需要自由,这两者其实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但在乔先这里却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问题”。母亲规训乔先的制胜法宝是自虐,她可以抽打自己的耳光,直到口角流血;也可以以头撞墙,终至血流满面。每次面对母亲的自虐,乔先都痛彻心扉。母亲的行为显然与自己的心灵欲求完全相悖,但这毕竟是深爱着自己的母亲,违背母亲的意愿更是大逆不道。作为一种规范的社会秩序和文化伦理,母子伦理关系以无可阻挡的巨大优势让乔先顷刻间败下阵来。可以说,乔先的成长经验中渗透了太多的心灵挣扎与精神隐痛,在这种伦理与情感的矛盾纠缠中负重成长的乔先,逐渐丧失了与生活抗争的勇气,更难积聚起自我救赎的力量。
从小说的叙事结构来看,乔先的精神成长是一个内隐的故事,是叙事的起点;与朱燕的矛盾纠葛则是一个外显的故事,是叙事的重心。这两个故事互为表里、紧密相连。当朱燕进入乔家之后,在天然的母子伦理关系之上,又添加了一种新的契约性的夫妻伦理关系,此时的乔先必须面对双重伦理关系的规约。无论在伦理上还是在情感上,朱燕都是乔先母亲的接班人。母亲是有独到眼光的,当然也是煞费苦心的,为了考验朱燕,她甚至不惜摔碎自己的膝盖骨。事实证明,在照顾乔先母子方面,朱燕无疑是非常尽职的,这是朱燕的骄傲,也成为她日后控制乔先的利器。朱燕第一次审判乔先,是婆媳联手共同执行的。从婆婆手中接过杀手锏之后,朱燕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她割过三次腕,服过二次毒,跳过一次楼,绝食五天——而如此极端地以自戕相挟,表面看来,不外乎是逼丈夫承认与别的女人有染的“罪名”,其实质,是对乔先心理与人格的更为极致的控制欲使然。这也就不难理解,每次极端行为后,随之展开的“猜忌和审讯”,“几乎覆盖住乔先的春夏秋冬”;而这期间,朱燕仍在自然又故意地“做牛做马”,为乔先做上一顿熨帖肠胃乃至脏腑的饭食,细致宁静地打理家中的花草……以其“无私奉献”的另一种姿态,“如思维缜密心灵手巧的裁缝,凭着一针一线,把乔先缝进不透风的袋子”,多面织牢夫妻之间的这种契约性伦理关系,将乔先彻底地驯化与收服。
面对母亲和妻子专制性的爱护,乔先的内心异常复杂,体验着一种类似于虐恋式的矛盾与纠结。面对母亲的严肃管教以及朱燕没完没了的无理取闹,乔先也进行过反抗,试图改变,但最终都以屈服告终。在无休止的反抗与屈服中,乔先已经变成了一个情感的“奴隶”,灵魂的分裂给他带来的不只是痛苦,还有一种隐秘的难以言说的“享受”,对这种“痛并快乐着”的情感状态,乔先已经上了瘾。且此种“自虐式”挟制与极端的精神凌虐,在主人公无知觉甚至厌恶对抗中,内化为其性格的一部分和处事待人的一种范式,如在向无辜卷入他们夫妻大战的童晓蕾道歉而不得原谅时,“他狠狠揪着稀稀拉拉的头发,替她惩罚他。很突然地,他的手停在半空,惊恐地望着四周。是母亲和朱燕的灵魂附体?还是他已经彻底扭曲?他的自虐与母亲朱燕如出一辙,一脉相承。他傻着,久久地,如同被自己点了穴。”在生活中,有的人为梦想而生,有的人负重前行,正如童晓蕾所言,乔先“天生就是背债的主”,这个身份支撑他活着,也支撑他继续活着,这是他的不幸,或许也是他的幸运。如果一定要为这位可怜的主人公,在其令人难过的生活与倍感抑郁的命运中找到一点“可悲”的意味,那应该就是他最终的异化与彻底归降。
乔先两难的生存困境,作为一个隐喻,消解了日常生活所有薄如蝉翼的诗意。虽然在以往理性的认知中,我们也明了当下的日常生活并非处处鲜花和阳光,但是,庸常生活中充满如此多的琐碎与无聊、矛盾与困惑,甚至挣扎与痛苦,读来还是令人惊心。小说以“落地无声”为题,其实便寓含了这样深层的意义指向: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应该是落地有声的、精彩的,但真实的现实生活却是碎片化的、灰色的,被太多的琐碎与无聊充斥着。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与灰色的生活,我们更多的是无奈与无助,欲说无语,只能默默承受。
二
基于这样一种意义预设,《落地无声》写的都是一些生活中的小人物,现实中的弱势群体。乔先的母亲与乔先相依为命,妻子朱燕也只能与他相互取暖。乔先是她们仅有的依靠,害怕失去的强烈恐惧心理让她们变得如此敏感多疑,甚至以死相逼。被无辜卷入乔先夫妻无尽无聊的争斗之中的童晓蕾,同样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小人物。一个离了婚的女人,独自带着孩子,生活中时时处处小心翼翼,又常常被生活小节折磨得疲惫不堪。面对朱燕的步步紧逼,她只能一退再退、一逃再逃,但生活过于逼仄,她最终无处可逃。迫于此种情势,童晓蕾才会对并非有真感情的男人投怀送抱,意图找到一种想象中的依靠与温暖,结果只能以再一次失望与受伤而告结,继续着自己无望的日子。和这三个女人一样,身为男人的乔先,既非卡里斯马,亦非盖世英雄,他也只是一个在生活的泥沼中左冲右突艰难前行的小人物。面对母亲和妻子的极端举动,他无计可施;面对受自己牵连而被朱燕不断伤害的童晓蕾,他亦计出无门——这就是人们生活的真实样貌。在粗粝的现实面前,这些小人物都沦为了生活的“奴隶”:无力,无能,无以解脱,更无由超越。
这种日常生活的诗意消解是通过细节描写来完成的,可以说,细节的魅力是《落地无声》的一大成功之道。小说没有大开大合的宏大叙事,而是完全由日常生活的生动细节环环相联,这与我们可感可触的日常生活密切贴合,真切鲜活。但这种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并非一地鸡毛式的写实,而是注重精神层面的开掘与情绪内隐。日常场景与生活细节只是叙事的外壳,其内核则是小人物内在心灵的委婉曲折与波澜激荡。小说通过夸张的细节描写,呈示了人物极致的矛盾心态。朱燕无休止的自残与追逃行为虽然比较夸张,但作为文学形象,确实映现了现实生活中的某种集体焦虑情绪与失控情节。在急剧变化的现实面前,那些边缘处境的小人物普遍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活无力感,以及太多的困顿与惶惑不安。《落地无声》虽没有着意书写大时代的精神地理与历史坐标,但这些小人物却与大时代有着恰到好处的勾连,他们的命运遭际,像一面镜子,映现出了大时代的清晰面影。
鲁迅曾说,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落地无声》中琐碎无聊的生活虽然谈不上有多大的价值,但正是这些琐碎和无聊却将日常生活的美好诗意消解殆尽,因此,弥漫在小说字里行间的无奈与感伤情绪确实又将悲凉之意宣泄无遗。现实生活的诗意薄如蝉翼,我们的小人物就是在这种生活中左冲右突疲惫不堪,虽有稍纵即逝的心灵激荡与诗意想象,在逼仄的生活境遇面前总会被轻易地解构与颠覆。面对逼仄的生活境遇,他们背负枷锁艰难前行,既无法避免生活中的意外,更没有扭转乾坤的能力,除了忍耐与承受之外别无他途。作为叙事的小说,虽然在乔先的手机又发出激烈鸣叫时画上了句号,但这样的生活却仍在继续,不堪重负、伤痕累累的小人物,重又投入与生活无有尽头又不得停止的周旋与争斗中,而这注定是一场无结局无胜负的争斗。正如加谬所引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日复一日,永无止息地重复着自己的苦役。
即便生活如此,这些小人物仍然不失善良本性与不甘沉沦的力量。乔先为人本分,乐于助人,在童晓蕾为了孩子入学一筹莫展之时,主动提供了帮助。对于妻子的无理取闹,他不仅没有怀恨在心施以报复,反而在妻子需要保护时,毅然张开了双臂,成为“妻子的整个世界”。童晓蕾同样是一个知恩图报之人,对于乔先的帮助她铭记在心,后虽受尽朱燕的百般侮辱与损害,仍未采用极端报复行为,甚至看到朱燕与乔先相拥离开时,她的内心不禁升腾起一股暖意。这是作家在灰暗的日常生活中注入的一种向善的力量。
如果说揭示个体生存的两难困境体现了作家的问题意识,那么这种道德重量的承载则体现了作家的人性思考。胡学文对人性的信念让我们深怀感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将《落地无声》视为一个关于人性的价值叙事。在《落地无声》中,美好的人性并非遥不可及的乌托邦,亦非虚无缥缈的浪漫想象,而是隐含在琐碎无聊生活中的真实存在;它不是悬浮的价值理想,而是现实世界中支撑人们继续生活的力量。胡学文摒弃了空泛的道德咏叹,而是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展现人性的困局,尤其是以个体生存的两难困境来探究人性深处的隐秘图景时,显示出了一个优秀作家的深刻与睿智。
三
奥地利小说家赫尔曼·布洛赫曾经说过:“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伴随着社会的转型和文化的嬗变,中国当下社会生活,涌现出太多的困惑与问题,尤其是普通人的日常心理与文化心态,更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状况,因而关切现实生存中,作为“人”存在的心理境况与情感困境,已成为很多作家的自觉选择,甚至成为很多作家关注与表达的重心。胡学文的这部中篇,一方面,以独特至奇异的切入视角、戏剧至荒诞的叙事安排、真实至肌理的细节描写以及充满张力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普通人”的心理挣扎与灵魂困境图景。另一方面,它更为阅读者提供了一个意蕴无穷、思味不尽的“现代寓言”,象征了这一时代某类人的人生状态,这是作品更深远的意义之所在。阅读者被其所隐含的细密深厚甚至令人窘窒的情绪所包裹,在其绵密细致、外松内紧的叙述节奏中,不再是一个读者,也不仅是一个旁观者,而成为一个体验者、当事者乃至反思者。
小说是对存在的探索与发现,胡学文的此种写作,显示的正是一个作家写作的根本价值和意义。新世纪以来,在文学“向内转”的价值调整之后,“底层叙事”、讲述“中国故事”成为时尚,但如何真正地发现生活与人性的底里,并通过有效的表达,感染与启发读者,却是当代作家亟需思悟透彻与实践跟进的。胡学文以自己的创作,实现了这种深层探求与审美表达的有效对接,对于中国文学如何将日常经验转化为文学经验,从粗粝浮躁的现实抵达纤细敏锐的心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