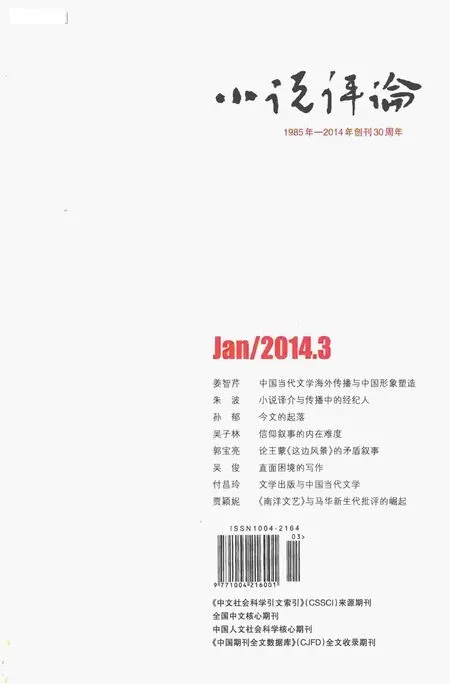点亮心灵深处的灯盏——余一鸣短篇小说论
洪治纲 曹浩
一
余一鸣是一位非常机敏且又不乏情怀的作家。他喜欢从那些庸常世俗的生活入手,将一些红男绿女置于各种尴尬或错位的人生境域之中,由此凸现种种复杂而吊诡的人性面貌。但人性又并非他的叙事目标,而只是他的叙事“桥段”;他试图通过那些诡异的人性,揭示这个欲望时代的伦理乱象,极力彰显人们应有的道德意识。在他的短篇小说中,这一情形尤为突出。从《最后的刀锋》、《我不吃活物的脸》、《城里的田鸡》、《把你扁成一张画》,到《剪不断,理还乱》、《鸟人》、《变姓记》、《夏瓜瓤红,秋瓜瓤白》等,在这些短篇中,余一鸣笔下的人物总是奔波在各种欲望的红尘中,或遭受命运的戏弄,或饱受情感的折磨,但是最终,他们还是会在道德意识的拷问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道德意识似乎是一个容易让人困惑的命题,因为文学创作常常离不开“冒犯”,即对一切现实秩序和伦理观念的拒绝或解构。但是,对于余一鸣来说,我们生活的这个现实,其实是无处不在“冒犯”,因此,真正的“冒犯”或许不再是无情的解构,而是必须回到重构的轨道上来,为这个失序的生存提供一条出路,为各种迷失的灵魂点亮一盏心灯。对各种习以为常的“冒犯”说“不”,其实也是一种“冒犯”。只不过,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冒犯”。当余一鸣将这种“冒犯”确立在道德意识之中,一方面是为了表明我们这个时代的伦理乱象,另一方面也折射了创作主体的生命情怀。
余一鸣的道德意识,在那些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物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这些刚刚从泥土里拔出脚来的年轻人,一旦踏足纸醉金迷光怪陆离的城市,在强大的物质利益的驱使下,内心深处最易感受到困顿,迷茫,乃至最终陷入道德的沦丧。《鸟人》中的胡森林就是如此。挥别农村,他来到城市做了一名“见不得阳光”的调查员——以调查男女不正当关系为业。此时,毫无疑问,他的灵魂业已蒙上了一层灰尘。而在调查的过程中,胡森林却意外发现被调查对象竟是自己的好友王国庆,同甘共苦的回忆涌上心头,于是他决意放弃这单业务,而此时,更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王国庆这枚同样在物质利益驱使下的棋子,竟是被花钱雇来搞男女关系的。笼罩在如此混乱的物质利益网络下,胡森林震怒了,“我操你娘的,你们都是些什么人呵?猪狗不如!”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难道不是余一鸣在震怒么?一种在道德层面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震怒?面对这种伦理的困境,胡森林所能做的,只有攀上大树冒充“鸟人”,为那位即将失去父亲和完整家庭的小孩摘下那只汽球。对于胡森林来说,走在现实的大地上,迎面扑来的,都是一些肮脏不堪的灵魂,包括自己的好友王国庆,或许只有在树梢上,像鸟一样,他才能看到内心的一份期待。
在物欲对灵魂的长期腐蚀下,在两者无声而持久的角力中,震怒过后,心存良善的小人物们必将呐喊。在《把你扁成一张画》中,由于经济拮据,林浩然和二狗不得不为一家艺术拍卖公司做卧底,潜伏在客人之中,伺机举牌,抬高竞价。余一鸣一开始就在他们身上撒下了人性污点,为小说的最终走向做好了张力铺垫。当林浩然发现女人所买书法为赝品时,及时举牌阻止了她。秉着“做人要讲良心,做了有钱人更应该讲良心”的念头,他跑去和老板据理力争,“我可以不拿这工钱,可我要去报社电视台揭发你公司昨晚那些伎俩”。耐人寻味的是,等不及去揭发,他就失去了自由——是的,令人诧异的一幕发生了,他竟无意跌入了一张画里,大张着嘴,却发不出声音!这一超现实的结局,无疑寓意了小人物们在面对物质世界林林总总的道德沦丧时,心底无声而坚决的呐喊,持续乃至永恒的呐喊。与此同时,小说所展现的创作主体浓郁的道德意识,对人性善的呼唤,读来悲怆而有力。
强大的物欲现实所肢解的,不仅仅是正常的人性面貌,还有人们赖以维持生存尊严的情感伦理。《最后的刀锋》就演绎了这样一幕情感与伦理冲突后的生命悲歌。驼背老五在湖滩上被船佬所挟持,不得已将和尚推进了凹坑,而他恰恰又同和尚的妻子相好。和尚被活埋后,他带着所得的二十四块银元返回家中,心灵上便经受了严厉的拷问,“不知道要不要去找和尚嫂,银洋揣在袋里像揣着一块烙铁”。他终究鼓足勇气去了,依然不肯与她光明正大过日子,及至杀掉船老大,才“把自己的铺盖搬到了茅儿墩,做了和尚嫂的第二个男人”。是的,作为读者,我们以为此后他们便可岁月静好地过下去,但余一鸣打破了我们的想象。老五婚后的生活依然不太平,先前所犯下的罪恶依然啃噬着他的心,他“讨厌和尚所有穿过的衣服”,每到和尚的祭日总会到湖滩上烧纸,并“跪上很久很久”。这种罪恶感一直持续,直到日本佬用刺刀把他们赶到稻场上,老五用剃头刀割开了翻译官的喉结,同时自己也被“各种枪打出了十几个窟窿,倒卧在小杨树下圆圆的树荫里”,才以死亡的形式获得了解脱。如此残酷的结局,可谓充分体现了作家深切的道德敏感和道德忧虑,象征意味颇为浓郁。
坦白讲,《最后的刀锋》毕竟充满了传奇色彩和寓言意味,而作为芸芸众生的我们,或者确切地说小人物们,在素日柴米油盐的生活里,在自己身处情感与伦理的道德困境、挣不脱甩不掉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悲歌吧——“悲而不能歌”的生命悲歌。当今文坛有一个不容质疑的事实,那就是,多数作家在创作关乎当下生活的作品时,总显得捉襟见肘,而令人惊喜的是,余一鸣却完成得相当出色。《剪不断,理还乱》就是典型的一例。小小借私家侦探之手获取了丈夫的“艳照门”照片,讽刺的是,身旁安慰她的姐姐大大,同时也接到了自己丈夫出轨的讯息——和其他女人生下的儿子即将满月。不知不觉,她们已经陷入了作家所设置的无形的道德困境中。姐妹俩试图挣脱,乃至反抗,小小说,“姐,我要撕了那婊子的皮,拔了那婊子的毛。”而大大也一样,“我一定要找到那个婊子,让她好看。”一向沉稳的大大甚至还开始了报复,大肆购物,剪碎包包,50元钱卖了一次身。可结果又能怎样呢?她们似乎也只能选择退缩。小小说,“姐,我们能有什么办法,比青春我比不过人家,比文化那婊子还是大学生,只有认命。”而结尾处,“大大手中的剪刀坠入袋底,没有人能听见硬器被柔软包裹的叹息”,可不正是作家余一鸣的叹息?无奈的叹息。在处理现实生活的题材中,无形地植入道德上的无奈,由此看来,余一鸣的创作水准,实在不容小觑。
二
展示现实的乱象,是为了追问人性的本质;追问人性的本质,又是为了寻找救赎的灯盏。就余一鸣的短篇而言,道德意识之所以成为一个较为突出的审美目标,关键在于,太多的人性溃败都是源于人们对道德的轻松践踏。在《拓》中,利欲熏心的徐大春在无计可施之际,开始在一块无名墓碑上大肆做文章。他先是花钱召开专家论证会,以时迁墓的名义向上级汇报,并最终轰轰烈烈开启了时迁景点工程,建成了时迁墓和义节神纪念馆,还有所谓的大宋一条街。更为讽刺的是,结果他还真的靠这场忽悠发了财,“时迁景点很快热了起来,大车小车停满了村头,村上不得不专门开辟了一个停车场”。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利益网中,一时间,各色人等奔走呼号,蝇营狗苟,几乎乱成了一锅粥。从私下收取钱财的专家,到言之凿凿“这碑是在我家地里挖的”的三爷爷,甚至最后徐安全自己都要来分一杯羹。为将此般反讽意味推向极致,余一鸣再次设置了奇诡的一幕,最后,墓碑主人的灵魂附在了拓片上,并唱响了自己的心声,“我不是时迁,我不会梁上功,我只要回到葬我的土地里”。让死者不得安宁,让谎言成为谋财的道具,让欲望支撑起“义节神纪念馆”,而且,这种无视基本道德的伦理乱象,居然还成为当地的一个文化符号,这不能不引人深思。
美国学者爱因·兰德曾经指出,在现代文明中,道德堕落的最明显的症状是人们对道德问题持一种“只有灰色”的态度,而且“‘灰色’是‘黑’的前奏。”如果我们将余一鸣笔下的那些物欲之徒聚拢起来,就会发现,他们尽管面目各异,身份不同,但本质都是一样:自觉地回避各种正常伦理,对道德持以“灰色”的态度。如《我不吃活物的脸》中“鬓狗一般专门嗅死尸啃死尸的经纪人”陈律师;《把你扁成一张画》里,靠所谓的艺术拍卖公司诈取他人钱财的老板,其人生信条就是“做人不懂规则很悲哀的”;《剪不断,理还乱》中大大和小小那富裕起来后相继出轨的丈夫;《鸟人》里专门雇人跟自己妻子搞外遇以此来离婚的男人……这些人物之所以能够在现实中呼风唤雨,光鲜亮丽,皆因太多的人默认了现实的乱象,并为欲望提供了看似合理的价值标尺。
余一鸣对此显然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为此,在演绎各种人性溃败的场景时,他总是不断地将主要人物置入各种关系网中,多方位地展示各种缭乱的生存秩序。在《把你扁成一张画》里,以老板为首的那家艺术拍卖公司,为了捞取钱财,真可谓殚精竭虑地策划着一出出天衣无缝的伎俩,不仅仅有“培训”,还有“革命分工”。“你的任务是‘D’号作品,凡是牌价没达到下面这个价位时,你都要举牌保证不被别人拍走,因为低于这价格公司就亏本了……拍价超过这个价格,你就歇手。”“……打五角星的作品……并不是真卖……不论客人举牌价多高,你都得举牌超过他。”“打三角符号的作品,作者是名气不大的人……实际上没客人肯举牌,你得举牌……这是帮他炒作打造呢。”天罗地网的精彩设计,像助理说的那样,就是为了“把他吸引进场,才有商机,才有宰他的机会。”而《鸟人》中,那位自始至终未曾露面的尤总,那个仅以五个字“高个子,光头”来概括的“无脸人”,其道德溃败的身影却几乎覆盖了全篇,其肆意享乐的价值观如影随形,余一鸣正是以这个人物为中心来拓展小说的。“光头尤总雇王国庆做胡一萍的驾驶员是一个阴谋,尤总交给王国庆真正的任务是勾引尤总自己的老婆,尤总有了新欢,但又担心胡一萍不肯离婚,让王国庆搭上胡一萍,抓住证据,胡一萍成了过错一方,婚就能顺利离成。尤总开给王国庆的报酬是月薪三千,事成之后奖励十万。”怎一出精明的好戏了得?生意场上,那些摸爬滚打多年一夕翻身的男人,甩掉糟糠之妻搭上年轻小蜜,似乎已经成了时下的流行趋势。余一鸣笔下的尤总,不可谓不典型。
与此同时,在这种吊诡关系中,余一鸣还展示了人性中诸多复杂的困境。《剪不断,理还乱》中,面对丈夫的公然出轨,大大何以剪不断,又何以理还乱呢?从开头部分“艳照门”中小小的丈夫那“青筋毕露高昂的男器”,到结尾处“婴儿的裆间物嫩芽似的几分茁壮”,无疑都隐喻了强势的男权,而作为一个女人的大大,在心理上她首先就将自己摆在了一个附属的位置,她找不到勇气来剪,包括婴儿“那黑亮的眼球蓝天白云般清纯,乌黑的发丛间散发出青草味道的奶香”所勾起的关乎她与丈夫早年温存的回忆,都莫不彰显着在感情上她对男权的依恋,又如何理得清?余一鸣仿若拿着一台显微镜,在沉默的人群中调查探究,最终所搜寻到的,都是无可言喻的人性困境。
道德的“灰色崇拜”已遍布我们的现实,如何寻找灵魂的出路便成为人们无法回避的人生命题。在余一鸣的短篇小说中,作者就充分展示了必要的道德关怀与完整生命的诗性重建之意愿。在《我不吃活物的脸》中,我们看到,丁良才最终将陈律师塞给他的“信封”递给处于丧子之痛的老汉,并在归家后的晚餐上,当妻子挟上他爱吃的鸭头时,他挟了回去,“下次别再买了,我以后不吃活物的脸。”从此前仅仅抱着息事宁人的心态来处理一次伤亡事故,到而今对死者家属的切身关怀,整篇小说读下来,一步步,诗性重建的痕迹颇为清晰。尤其最末那句“我以后不吃活物的脸”,深远的寓意之外,浓浓的道德关怀氤氲在字里行间。
而《城里的田鸡》在传达这一意蕴时,则自始至终都透露着散文诗般淡淡的美。同样探讨道德重建,余一鸣在这篇小说的处理上却别具声色,在轻与重的考量上亦拿捏得相当到位,在人物关系的逐层推进上,也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瘸老张原本并不瘸,是年轻那会儿被王来电的曾爷爷砸瘸的,而当瘸老张发家致富了以后,顺理成章地偏袒张姓人。而作为王姓人的代表之一,王来电的爹王爱军,却试图靠诈伤骗取瘸老张的钱财。如此一来,种种不公平不道德行为都施加在瘸老张身上,这就为之后的诗性重建埋下了伏笔。是的,瘸老张原宥了这一切,并取出十万现金“随手一扔”给了王爱军,就像他跟王来电说的那样,“你崽伢子现在不懂,一个人活在世上不止要吃得好穿得好,还要有人和他说话。这田鸡也一样,你得再给它找个伴,最好把它认识的田鸡都带回去,它听到熟悉的声音心里才踏实,才会唱歌给你听。”不得不提的是它绝妙的结尾,“王来电突然转过身,腿一撩,胳膊一瘸,迎面学老头走了两步,说,瘸老张,傻瓜瘸老张……老头作势捡了块土砸过去,王来电受惊的马驹一样逃开去,老头忍不住‘嘿嘿’笑了起来。”两家可谓一笑泯恩仇,此般尽享天伦的景象,道德重建的光芒,霎时美得如同一场幻梦。
作为人类精神的劳作者,作家必须有能力恢复人类向善的意愿,必须展示人类拥有的悲悯情怀,这虽是一个道德问题,但是,“人的道德和他的智慧是相对应的。实际上,道德是人心灵中最高尚的力量,是灵魂之灵魂,而且必须扎根于所有他要描写的伟大事物的根部。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总是能看到最高贵的同情,没有门户之见,没有残忍,没有狭隘,没有愚蠢的以自我为中心。”就作家的主体精神来说,缺乏这种高尚的道德力量,不仅仅会导致叙事沉迷于人性的灰色地带而无法写出一些震撼人心的杰作,甚至会直接影响作家自身的创造力,导致叙事能力的衰退,而余一鸣显然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三
从叙事上来看,余一鸣的短篇带有强烈的话本小说特色。话本小说原本是宋代以来的小说叙事形态,它“以市民阶层为主要的拟想读者,话本小说选择杂货铺主、碾玉工人、酒店掌柜、无业游民等为表现对象。比起唐人之注重上流社会,宋人明显倾向于寻常百姓。以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作为叙事的中心,而且叙述中充满理解与同情。”余一鸣的短篇小说中,似乎都有一位隐形的说书人,那些小人物的离合悲欢,就在他抑扬顿挫的“咬文嚼字”中缓缓道来。那一抹街谈巷议的现场感,读来分外真切。譬如《我不吃活物的脸》的开头部分:“丁良才走进第三家木工板店,直截说,你别跟我玩虚招,报个一口价,老板一沉吟,报出的价格依然让他在心里跳起双脚都够不上。丁良才无奈地叹口气,报出一个价,老板谦卑而委屈地笑着,再报出一个价,几个回合下来,越来越接近理想的价位了,丁良才却失了兴致,不想和老板玩了。又不是赵本山和范伟在电视里抬价逗乐子,那两位逗的是银子,这建材店老板愚蠢到以为人人都能逗银子,让丁良才觉得这游戏没意义。”这种叙事语调,颇有一种幼时听评书的况味,凡俗而传奇,凡俗到隔壁的张三李四,而张三李四又各有各的传奇,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的,这一抛却了枝蔓,单单以故事情节来推进的模式,近乎于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用通行的白话来讲述平凡人的故事。鲜活自然,令人顿感身临其境。
与话本小说相呼应,余一鸣的短篇小说故事性极强,话本小说中跌宕起伏的情节和出人意表的结局,在其众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比如《城里的田鸡》,小说大半个篇幅都在讲述瘸老张受到的不道德甚至残忍的待遇,而当仇家王爱军跪在他面前的那刻,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他将断他一条胳膊或者腿时,他却选择了宽谅,宽谅这世代累积的恩怨,并给予对方十万块以救穷;比如《把你扁成一张画》里的林浩然,在和老板据理力争的当口,竟徒然跌进了一张画里,成了不能动的“画中人”,只能无声地对着画外的世界呐喊,永恒地呐喊;再比如,在《鸟人》中,胡森林本就是位“见不得阳光”的调查员,而当他发觉自己无意参与进了“更不阳光”的事情时,却并未视若无睹,而是选择了退出,选择了抗拒,当他抱着救赎的心情为孩子豆豆摘气球时,更加诡谲的一幕发生了,他被生生挂在了树上,整整一个晚上。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由此可见,余一鸣的短篇小说中,人物冲突的起承转合异常鲜明,出人意料的同时往往又有着极强的说服力,无疑增强了作品本身的可读性。
与此同时,余一鸣的短篇使用的是近乎“反文学性”的朴拙语言,仿若就那么囫囵个儿被作者从大地中拎出来一般,尚且散发着新鲜泥土的气息。例如《校园病人》就是这么开篇的:“从乡中学调入县中时,正是暑假,偌大的校园里见不到人影,蝉声连绵,操场上的杂草已经高得能遮人的视线,我拎着简单的行李,问传达室的大婶,值班的领导在哪里,大婶看一眼我,说跟我来。”又如《选择题》,在这方面简直更甚一步:“国庆长假回老家,头几天忙着吃喝会友,脑子里烦不了事,闲下来总觉得漏了什么,又想不出漏了什么。直到陈新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回来,这才想起来儿子他妈交给的任务,儿子读高中是放城里好,还是放老家县中好?”日记般的记述里,朴拙而不简单,恰恰彰显了一个作家对现实的高度介入,生活气息颇为浓郁。
朴拙的另一个表现是,余一鸣还大量运用了俗俚语,这些土生土长极富地方特色的语言,无疑拉近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使人由不得生出一丝暖意。这暖意是会心的暖意,是两个人咬耳朵,不足为外人道的暖意,鲜活又自然,幽默而风趣。在余一鸣短篇小说的疆域中,它极其广泛地弥散在各个角落,简直俯首即是。我们不妨来看以下几例。在《夏瓜瓤红,秋瓜瓤白》中,作者是这么讲述和尚娶亲之夜的:“和尚将门闩上,小女人就吓得哭了,一直哭,哭得和尚的大手大脚无处放,哭得墙根下听房的人们失去了兴致。和尚浑身上下就只有舌头软,可怜他舌头软也不会说一句暖人的话。小女人哭累了,和尚才抖抖索索地将女人抱了,像抱着一磕就碎的瓷瓶子,但放到床上,和尚就不自觉抱紧了。小女人凄惨地叫了一声,和尚讪讪松了手,明白蛮力用错了地方。好在夜天长,黑暗中摸着石头也能过河,和尚的手脚轻重有了分寸,终于软硬都吃在一处,咬合了,窗外突然响起了两声炮仗,震得芦苇顶落下许多灰尘。狗日的们还在哩。和尚骂了一声窗外的捣蛋鬼。后果跟被捣了蛋一样惨,和尚一下子软了。”就连和尚那赤裸的身体,都在讲冷笑话:“胸口上长着密密的一丛黑毛,一路黑下去,到肚脐眼那里喘口气,又一股劲儿纵深下去。”又如《最后的刀锋》,开篇不过寥寥数语,却妙趣横生,迅速将读者拽进故事中:“驼背老五拎着剃头篮子走在乡间小道上,不熟悉的人远远看去,会以为是走娘家的媳妇。驼背老五是剃头匠。生下来的时候爹站在外面骂娘,说破窑只能出次品,娘说再丑总比你强,拎个剃头篮子吃百家,用不着田角落里刨食。驼背老五长大就成了剃头匠,乡里不成文的规矩,手艺饭都留给带缺陷的人吃,驼子学剃头,瘸腿做篾匠,老天不绝人呢。”再如《选择题》中陈新民的那句顺口溜:“素质教育是西装领带,人前必须整齐穿戴;应试教育是贴身内裤,白天黑夜都挨身贴肉。”讥嘲之余,简直令人忍俊不禁。还有《我不吃活物的脸》中,那位“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陈律师,“民工被窝里掐死只虱子他都能闻出血腥味。”
正是借助这些独特的叙事策略,余一鸣的短篇小说强化了故事对现实的介入性,使得道德意识植根于当下柴米油盐的生活中,植根于一个个平凡人物的精神深处,而不再是作家主体的理念和标签。或者说,这种原生态的文字风貌,将原本浓郁的道德意识稀释了,仿若闲来沏一杯清茶,每一粒水分子中都充盈着淡淡的茶香,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寻。正所谓相得益彰。于无声息处,余一鸣为他笔下那些几近枯竭的人们渐次点亮盏盏心灯,灯油注满的一瞬,如入澄明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