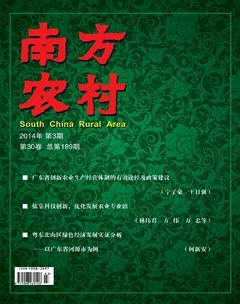农村“空心化”与社区建设困境
张红霞,方冠群
摘 要:近年来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就业,造成了农村的“空心化”。通过对湖北东北部一典型农村深入调查,发现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造成农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的主体意识弱化、传统乡村秩序被打破、村民自治缺乏主体力量、村庄关联度下降等一系列问题。这给农村发展与社区治理带来诸多困境。城市融入的重重制度障碍,使得大部分农民工并不能真正融入城市,最终一部分高龄农民工仍要回到农村。村庄精英的流失造成农村发展的困境是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关键词:空心化;农村社区;乡村秩序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4)03-0050-04
一、问题提出
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壁垒的逐渐破除,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一方面农民向城市的流动是对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突破,是中国农民摆脱土地束缚走向城市化的重要通道和推动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也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动力,满足了城市居民生活的多种需要。政府和学界更多关注的是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的影响,对于流出地的影响关注较少。毋庸置疑的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对农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农村劳动力的不断外出,可以发现农村的常住人口在逐渐减少。外出务工的大多数是学历、素质较高的,是农村的“精英”,而留在农村的大多是老年人、留守儿童。农村社会精英的过度流失造成了农村的“畸形空心化”[1]。农村“空心化”对于农村社区发展带来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农村发展的哪些方面?为了进一步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本文以湖北省双河村为个案,进行了深入调查。
本研究来自于2013年1月底至2月初在湖北省双河村的调查。之所以选择双河村作为研究对象,在于双河村外出务工的典型性。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双河村大部分青壮年都有过外出务工的经历,目前留在村里的大多数是60岁以上的老人与12岁以下的儿童,很多村民甚至举家外出务工。务工地点大多数是较远的广东、北京、上海等地。在这种情况下农田荒芜、村里公共事务无人关心。因此探讨“空心化”背景下的农村社区建设成为了本研究的焦点。
二、研究区域与研究对象
双河村地处湖北省东北部鄂豫边界,大别山脉西南段,地势以低山丘陵为主,跨淮河、长江两大流域,距省会武汉市151公里,行政上隶属大悟县,距县城3公里。双河村是一个行政村,由7个自然村组成,分别是陈家咀、汪家河、李家湾、张家岗、白庙湾、上王家湾与下王家湾,人口2561人,经济上以农业为主。由于地理资源的原因,农业资源比较匮乏,人均耕地较少;地处丘陵地带,土地耕种难以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土地耕种耗费人力很多。由于土地较少,又难以机械化,村民的种植以蔬菜为主,很多农户种植时令蔬菜,然后挑到附近的县城去卖。由于人均耕地1亩左右,耕种比较困难,收益较低,附近没有任何村办企业或工厂,很多青壮年都外出务工,留在家里种田、种地的大多数是老年人。农业资源有限,种地、种田收入较少,调查发现该村90%的年轻人都不愿意也不会种田,他们大多在初中毕业后就去外地务工了,留在家中的年轻人很少。附近的城市经济也不发达,年轻人选择务工的地区以广东最多,也有一部分在北京、上海等地。双河村青壮年外出务工的地区离家乡较远,年轻人一般1年才回乡一次,甚至更少。年轻人结婚以后,大多夫妻双方都外出务工,孩子由老人在家乡代为看管。以双河村的陈家咀为例,该自然村21个年轻人只有5个年轻人常年在家。除儿童以外,村民在家的大部分年龄均在45岁以上,而且以妇女居多。
这次调查对象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在家村民7人,村干部2人,在外务工青年3人。
三、农村“空心化”背景下农村社区建设的困境分析
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农村社区的人口结构,许多青壮劳动力常年不在家,一些农村地区常住人口大部分是老人和孩子,尤其是人多地少的湖北部分地区,这无疑给这些农村地区的社区建设带来了深刻影响
(一)“空心化”背景下村民参与集体公共事务的主体意识弱化,反应冷淡
现代治理是公民参与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管理的天然实验场。与传统治理模式中公众消极、被动参与相比,现代治理强调的是公民广泛的、直接的、能动的、更加独立的参与。治理绩效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的能力[2] 。对于农村社会来说,农业生产的基础是土地,双河村大部分青壮年的外出使原本土地紧张的情况有所改变,30%的田地处于“丢荒”状态,有一部分家庭全家在外,土地无人耕种。对于种植水稻的地区来说,水塘是稻田灌溉的根本,双河村一般是几户家庭共用一个水塘,水塘如果维持好的话,附近的稻田基本上能保持用水方便,有利于稻田的维护。据村民介绍,在上世纪70、80年代,这里的水塘每年都定期清理,一般由村里组织青壮年去做,那个时候每个水塘清澈、干净,没有杂草。近年来由于青壮年外出务工,人们对于维持水稻正常生长、种植的水塘不再重视,由于多年无人清理,水塘里淤泥堆积、杂草遍地。
在调查中发现,很多村民对于水塘的清理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这些村民年龄都偏大,他们既不愿意也没有精力干这些活。子女外出务工,在家的村民思想也有所变化,他们不知道以后孩子是否还回农村种田,对农业公共设施的投入有所顾忌,这也影响了很多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这些在家务农的人对双河村的未来是无法预知的,也不想为双河村的未来考虑什么。他们甚至有一种渴望,希望孩子在外收入高了以后完全脱离农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集体的公共利益关心很少,只要当前利益不受损失就得过且过。以致双河村的水利基础设施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也没有人去关心维修。
(二)空心化打破传统乡村秩序,基层农村“无序化”
传统农业社会是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上的“熟人社会”,村民之间彼此熟悉,沿着相同的轨迹生活,是个道义乃至行动的共同体[3]。 维持乡村秩序的大多是沿袭多年的“村规民约”,这种传统习俗与地方的村规民约,通过乡村的集体仪式与家庭教育得以代代沿袭。随着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打破了双河村沿袭多年的生存方式,年轻人不再以本地的农业生产为主,他们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生活地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代代相传的村规民约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场域,很多年轻人也不再学习、遵循传统的做法。但是现代的农村社会管理体系在中国广大的农村还没有建立起来,农村还缺乏现代性的诸多要素,大部分村民的文化水平不高,农村传统的特征并未改变。对于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村社会,传统乡村秩序对于维持中国农村的基层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改变了传统乡村秩序的沿袭路径,外出务工群体所在的城市是与传统农村截然不同的城市社会,在很多方面具有现代性的特征,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与传统的乡村社会截然不同。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务工青年的行为方式、价值理念在重新塑造,甚至在很多情况下理念、价值观出现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对于农村外出务工的群体来说,回到家乡,他们对沿袭多年的传统村规民约缺乏一致认同,把所谓新习得的一些理念带回农村,在多种不一致规范的作用下,很多人就失去了规范的约束,处于一种“失范”的状态。
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年轻人十几岁就外出务工,由于常年在外,受城市文化的熏陶,偶尔回到老家过年,也不再认同农村的一些乡土性习俗,甚至一些年轻人对一些乡土性礼仪、行为规范都缺乏起码的认知。在这些年轻人眼里,农村是“愚昧”、“落后”的,他们内心充满对城市文明的向往,回到家乡依然模仿与践行城市的生活习惯、行为规范和价值伦理。
总之,农村社会的乡土性习俗与传统道德伦理等在外出务工的背景下出现认同危机。在城市化的强势话语下,乡村文化基础上的传统乡村秩序被边缘化。在遇到一些特定的场合,村规民约失去了对农村居民的行为制约。在多元规范,甚至城乡规范不一致情况下,很多人失去了规范的引领与制约作用。旧的秩序被解构,新的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失范”、“无序”成为了空心化背景下乡村秩序的状态。
(三)农村社区自治缺乏主体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社会的基层治理采取了“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在这种治理模式下,村民委员会作为自治组织,实际上扮演了乡镇政府的“一条腿”角色,承担了大量政府任务[4]。 要实现农村基层社区的发展,必须提高村民的民主意识,实现农村社区的“自治”。但是对于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的农村社会来说,农村精英大量外流,实现村民的自治成了一句空话。
在调查中发现,现在很多村青壮年大多忙于挣钱,无暇顾及家乡的事情,在家老人、孩子根本没有能力或精力去关心村集体事务,村中事务都是由村干部独自承担。
一些学者认为,在大量农民流动的背景下, 实施日常管理的组织机构——村委会自身面临组织虚化、功能弱化、权威衰落的问题,村庄管理缺乏有效的公共权威[5]。 村庄的集体事务没有人关心,自治缺乏参与主体,导致双河村的很多发展,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的模式,村民参与很少。农村社区要获得真正的发展,无论是村民自己组织,还是政府组织村民,都需要村民积极参与、集思广益,真正作为社区的行为主体,参与到农村社区的发展中来。但是这些空心化的农村社区,缺乏参与自治的主体,缺乏合作与讨论的社会基础,农村社区发展变成了无源之水。
(四)与公共生活相关的村庄关联度降低
贺雪峰用“村庄关联”一词来表示乡村社会中的社会联系程度。村庄社会关联则是指那种具有行动能力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对村庄秩序的影响力,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所构成的行动能力,是村民在村庄内部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总称[6] 。传统村庄的社会关联以稳定的宗族关系和传统伦理为基础。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村庄是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村民生产中的关系、生活中的关系都在村庄中发生,因而村庄的社会关联度非常高[7]。 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以后,他们的生产与生活大部分是在城市中的陌生人社会,村庄不再是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在这种情况下,与村庄人的联系无论在频率还是在程度上都下降了很多。在外务工的经历也强化了他们的理性观念,他们的生存资源大多是在外获得的,随着外出务工时间的增加,越发容易使他们隔断与村庄社会的价值联系。
调查中发现,双河村很多年轻人十几岁就外出打工,与家乡的联系仅仅是因为父母在这里,他们头脑里的村庄记忆很淡。也有一部分年轻人在外的生活过得比较好,与村民人情往来很少,加强村庄记忆与社会关联的红白喜事基本上没有参与,生活圈子、社会关系基本上在双河村之外,只是在户口归属上属于双河村。由于外出务工,曾经熟悉的乡亲邻里变成了半熟悉的“陌生人”,社会交往频率急剧下降,村庄舆论对个体行为约束降低。这样下降的村庄社会关联加剧了农村社会的陌生化,正在化解着转型中的村庄共同体。
四、结论与思考
从双河村的调查可以发现,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民工潮”,使大批落后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在为流出地带来较高经济收入的同时,也给流出地农村的发展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在落后的农村,外出务工的大多是农村中学历、能力、体力等较好的精英,大批青壮年外出务工造成了农村社会的“空心化”,村民参与集体公共事务的主体意识弱化,对集体基础设施的破坏反应淡漠,维护农田基础设施的劳动力不足。随着外出务工,生活地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改变,代代相传的村规民约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场域,维持乡村秩序的村规民约被打破,乡村处于“失范”的状态,年轻人的外出也使得农村社会的自治成了一句空话,与公共生活相关的村庄关联度降低。
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大多在城市中非正规部门就业。在目前城乡二元结构下,在基于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障碍下,这些农民工一直生活在城市边缘,并不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真正融入城市。对于大部分外出务工人员来说,因为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等到他们年老体弱时可能一部分仍要回到农村。但是由于受多年外出经历的影响,这部分外出务工人员在文化认同、传统性特征方面已经与乡土社会断裂。他们为城市发展贡献了体力和精力。再回到农村,他们已不再认同乡村文化,传统的乡规民约无法约束这一群体的行为,也并不能从真正意义上积极参与当地的农村建设,从某种程度上只能进一步加速农村社区建设的困境。一些研究认为,无特殊技能的高龄农民工有出现回流趋势,这是乡村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8]。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就业促进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在中国现代化的背景下,这场大规模流动无疑是利大于弊的。但是对于流出地而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客观上抽去了农村发展的主体性力量,造成农村空心化与社区发展与治理的障碍,加剧了农村个体行为的无序化。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变迁中,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如何推进农村社会的发展,解决农村空心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学界和政府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
参考文献:
[1]周春霞.农村空心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选择[J].
南方农村,2012(3):68-73.
[2]杨蓓蕾,孙荣.新农村建设中的社区治理模式困境探究——
以H村可持续发展项目为例[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1):
190-192.
[3]贺雪峰.中国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J].
学习与探索,2007(5):12-14.
[4]许远旺,陆继锋.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变迁
[J].中国农村观察,2006(5):45-50.
[5][7]李伟.论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农村村民自治的影响[J].云
南行政学院学报,2005(2):92-94.
[6]贺雪峰.论村庄社会关联[J].中国社会科学,2002(3):
124-134.
[8]罗小龙,田冬,杨效忠.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出地乡
村社会变迁研究[J].地理科学,2012(10):1209-1213.
(责任编辑:肖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