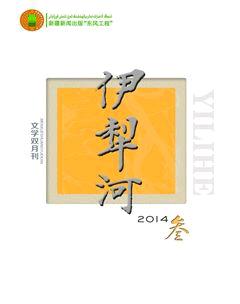箭乡之魂
鲁焰
10月10日,在闻名遐迩的“箭乡”——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来自区内外的十几位著名作家和诗人相聚在这里,参加“名家写箭乡·2013西迁圣地文学笔会”,深入发掘该县深厚的文化底蕴。
察布查尔因射艺出众,被冠以“中国箭乡”的美称,近年来,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察布查尔更是以挖掘和保护民族文化为重点,开展了一系列加强和保护民族特色文化的工作,一批重要的锡伯族特色民族文化的濒危文化遗产得到了保护。目前,“西迁节”“贝伦舞”“弓箭制作技艺”“锡伯刺绣”已经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锡伯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工程也已启动。
作家们在一周时间内,围绕该县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展开文学采风活动,锡伯民族博物院、都拉塔口岸、卡伦遗址、靖远寺、锡伯族贝伦舞、中华弓箭文化博物馆、察布查尔大渠、白石峰等,都留下了作家们的足迹。旖旎奇谲的自然风光,余味无穷的人文遗迹,浓郁的锡伯族文化韵味,无不令作家们由衷赞叹,灵感迸发,也对这片热土平添热爱。
十月之秋,察布查尔艳阳碧空,周遭散溢着一缕缕温暖、柔和的气息,一下一下地抚平心上皱褶,托举我们向上,再向上,心上的负累慢慢卸去,脚步不觉轻快起来。
其实在察布查尔,万物生发的蓬勃里,必有更为吸引人心的力量存在。
都拉塔口岸与纳旦木卡伦
我们来到这样一个有着一种别样风味的地名的口岸——都拉塔口岸,其实就是站在古丝绸之路的通道上。
在无垠的戈壁上,长着一撮撮荒草,从我国望向对方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风景没有区别。凸显生机的其实是那一溜货车,在哈萨克斯坦那一方排成了长队,等待进入中国国门,将服装、日用百货运回去。
无声的静谧里,暗藏着两国贸易的活跃景象。
都拉塔——驿站的意思。都拉塔口岸,历来是西部民间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通道。2006年起口岸对外开放。
都拉塔边防连,就驻守在这里。当年,他们住在地窝子,白天屋子里热得像蒸笼,晚上冷得墙上都结冰。广袤的芦苇滩上还有毒蛇、蚊虫出没。狂风一起,砂石乱飞。战士巡逻时,须穿从头遮蔽到手脚的防护衣,环境之恶劣可想而知。
我们走上高高的瞭望塔,拿起沉甸甸的钢盔,心里也感受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分量。端起望远镜,远望辽阔的边境线,我们对驻守在这里的子弟兵生出崇高的敬意。
是的,不管何时何地,每每站在边境瞭望塔上眺望,我的浮想也飞得很远。站在国门,对祖国的热爱与自豪感就更加强烈而清晰,祖国的温暖油然而生。
边境线上,我国军民共同戍边,守卫国门。戍边,任何时候,都会令人生出崇高感。遥想250年前,3000多名锡伯族军民从祖国的东北端出发,走过万水千山,尝遍辛苦,抵达祖国西北边疆,戍边守边,绵延几代人。骑射民族的热血精神,至今重温,依旧震撼心扉。
当我们站在纳旦木卡伦遗址前,这种感触就更加浓烈。阳光照耀下的一大片茅草,在烈风下舞动,于是一种莫名的意蕴,在周遭翻涌,是悲情,是悲壮,亦是豪迈。与草色相近的黄土断墙,呈四方状,还依稀可以揣测出这里曾经是一处坚固的堡垒,由威武勇士把守,一旦有外强入侵,只需放箭,定叫敌人有来无回。
卡伦,即哨卡。清代,在人口稀少、防务薄弱的边疆地区,是有效行使行政管理和防止外敌入侵、维护国家统一的一项重要设施,清政府调遣锡伯军民戍边伊犁,就投入驻守18处卡伦。目前,北起伊犁河,南至乌孙山北麓,尚有7处卡伦遗址。纳旦木卡伦遗址就是其中之一。
所有的卡伦都建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哨兵一守就是一个季度,一年驻守3个月,然后换防。当时的艰辛可想而知。曾经驻守卡伦的锡伯营镶白旗(孙扎齐牛录)人沃克津在《辉番卡伦来信》一文中就有描写:“……马不停蹄;人冒风尘躜行,实感步步为远……所过之处,人生地疏,忧愁之心,乃与时俱增。终日赶程,不见一相识之人,竟至口干舌燥,更不遇一知音者。”读此文,锡伯族官兵戍边卫疆的历史活动仿佛历历在目。他们为了戍边忍受凄苦孤寂的情感波澜亦令人感同身受,颇有共鸣。
卡伦历尽沧桑,是锡伯族自1764年从东北西迁到伊犁戍边屯垦的非凡历程的一个见证。
从纳旦木卡伦到都拉塔口岸,时空交错,时代变迁,而唯一不变的,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与永存。
一种崇高、神圣的情感,在这里更强烈,更深刻。
弓箭里的生命
在察布查尔,有卡伦,就有弓箭。
以往,看见弓箭,我们仅仅把它当做是一种武器。
然而,在察布查尔县中华弓箭博物馆,当我亲眼看到那些制作弓箭的用料,看到中华弓箭制作者黄浩手持弓箭专注地射向靶心时,忽然就感觉到,弓箭是有生命的。
中华弓箭,曾经从远古时期,就伴随征战与厮杀。当勇士骑一匹战马,飞驰而去,弯弓射箭,敌营大乱之时,征服的意义就从弓箭显现。在我国,最早的箭头文物出土于两万八千年前。
那时的弓箭,就是一把神器,唯有具备崇高地位者可以拥有。
在古代,弓箭的材料,极难获取,一把弓箭诞生的契机,极其稀缺。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为之。弓箭匠人的智慧与大自然的恩赐,决定了一把弓箭的成与败。
弓箭的核心部件——牛角,就标明了一种不可预知的未来。在古代,牛是重要农耕用具,维系一个部族的食粮,没有牛,就意味着随时毙命。牛,不可杀,待其寿终正寝,才可得牛角。一头牛就两个角,有了牛角,还要看运气。如果这头牛不是那么好斗,牛角在生长过程中没有伤痕或裂纹,才是弓箭可用之物。而弓箭另一必须之物——牛筋,也只能取牛背上的那一绺。
其余的材料,亦是天南海北,集合在一起,本身就不容易,何况是在古代。
做弓箭,首先还要对什么样的木材适合有一个深入研究,包括木之纹理、纤维、生长力等。纹理不对,即便同种树木也不可用。制作弓箭的木料如此之讲究,实令人唏嘘。
云木、榆木、毛竹需要在冬天准备好,春天锯水牛角,夏天铺牛筋丝,秋天再用秘制方法熬制的鱼鳔胶粘合才能完工,最后,还要多次驯弓,才能弯弓射箭。制作一把弓箭,往往需要耗费一到两年的时间。
因此,弓箭制作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生命的历程。想想看,用天南地北的材料,聚合成为一把弓箭,这里边蕴含了多少不可预知的机缘啊!
所以一张良弓太难得。而工匠的智慧,就在于如何将这些天赐机缘完美地呈现在一把弓箭上。
当我们了解了弓箭的诞生过程,会对弓箭怀有一种敬畏之心。
一个器物,一旦有了自己的灵魂,就可以说有生命了。
我看见一身英气的黄浩拉开弓箭,将一支箭专注地射出去,“噗”地一声暗响,正中靶心。“箭人合一”,这种感觉就忽然产生。
“这只是一张弓的生命,整个弓道的生命可就不同了。”黄浩说。
弓道,是什么?是弓箭中蕴藏着的做人之道,生命之道。
在中华弓箭文化博物馆,“弓之道”三个大字占据整面墙壁。
弓道可以衍生出一个人的为人准则。
远古时期就有弓箭。逐鹿之战是有文献记载中最早的弓箭之战。华夏礼射是中华文化最有魅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便是小小的扳指,都蕴藏了很深的内蕴。在古代,每个士兵都有几个扳指,不外借不离身。从弓箭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智慧。比如英国弓箭,从中显示出的民族特性——尚武的民族。
华夏是礼仪之邦,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里,修身养性恰恰蕴藏在弓道之中。中华弓道,内蕴博大,培养的是一个人高尚的品德。
中华弓箭文化里,包含的不光是技,更是魂,是道。孔子有句话,专门讲与对手要比修养,比品质,射艺之争也是君子之争。弓之道不在利而在德。物欲横流的世道其实根源上是传统文化精魂丧失。
endprint
与黄浩交谈,最令人钦佩的不仅是他对弓箭知识的领悟、弓箭技艺的精通,还有他从中华弓道领悟到的魂,让他的思想有了重量,心智变得高远。
这位28岁的年轻人,举手投足间,温良恭俭让,迥异于我们随处可见的“80后”。中华礼仪之美从他身上就体现出来,令我们感到既惊喜又遥远,生活中很少能够看到,甚至仅仅在一些影视剧中才可见一斑。他在研究推广中华弓道的同时,自己就已经不断被熏陶,被提升。
制作弓箭,推广弓箭,举办弓箭培训与比赛,都是在传播弓道文化,倡导优秀品质的自觉锤炼。
250年前,锡伯族人从东北大西迁至西北,一路佩箭而行。在察布查尔这片热土上戍边卫国、生产生活,中华弓箭文化,也由他们传承到了西域。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察布查尔,还有很多当年的弓箭。作为中华弓箭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锡伯族弓箭文化的内涵有待于不断开掘。目前察布查尔县正在形成一个文化产业,这个文化产业正在把中华弓箭文化传播到越来越远的地方。
弓之道,其意高远。在察布查尔,弓之道向我们打开了一片陌生而新奇之地,静待为人所识,所悟,所光大。
贝伦舞·萨满舞
察布查尔,人杰地灵。锡伯族人,既善于骑射,亦懂得生活。歌舞就是一大特色。
“谁给咱砸碎锁链?谁把咱救出火坑?通往幸福的阳关道谁给咱指引?天上的太阳呵,心中的明灯,毛主席呀共产党,锡伯族人民的救星。”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却是在察布查尔才知道,这其实是一首锡伯族歌曲。锡伯族人的能歌善舞在我们所到之处,都可以领略到。
贝伦舞,我们就是在一个“农家乐”小院里饱了眼福。78岁的老人全福,别看腿脚已经不利落,跳起贝伦舞却格外轻盈,一会儿扭腰,一会儿深蹲,一招一式,非常经典。六十多岁的老板娘与之对舞,轻巧如燕。农家饭做得好吃,贝伦舞也跳得极其地道,这大概只有在察布查尔才可以见到。
这是我们在爱新舍里镇看到的贝伦舞,“我把锄头用在菜园子里,我把女人的躯体交给阿哥你。”歌词直白而热辣。
锡伯族人的贝伦舞,以其欢乐的节奏迅速抓住人们的心。
贝伦舞有很多种,招妻舞、酒醉舞、走马舞、烧茶舞、拍手舞、礼仪舞等,融合了蒙古族与哈萨克族的节奏与力量。或刚勇,或妩媚,骑射民族的豪爽与细腻尽在其中。
每每听到贝伦舞的节奏,我们也会兴味盎然。贝伦舞极其容易地煽动起人们内心的欢乐。
在霍城县伊车嘎善锡伯民族乡伊车嘎善村,我们来到一户有着很大院落的人家,葡萄架上挂满了葡萄,葡萄架后边生长着绿绿的白菜、高高的玉米,更远处还有几堆玉米垛。放眼望去,黄色与绿色相映,仿佛油画一般。
我们一边吃着一串串葡萄,一边被这农家景致所倾倒。周遭散溢着收获的气息,令我们沉醉于来自乡村的愉悦。就在此刻,一场很特别的演出开始,萨满舞蹈随着铿锵的鼓乐上场。这些普普通通的农民,当他们跳起萨满舞来,却全然换了个人,那些娴熟的舞姿里,也流露了他们内心火热的情感。
舞蹈者中还真有一位萨满,她一脸和蔼,却眼神深邃,仿佛可以一眼看穿你。她告诉我,他们的服装就是从萨满教传下来的,她已经是第六代萨满了。她说,究竟是不是萨满,别人能够看出来。她打了个比方:一个小孩一直病病怏怏,直到十七岁被选为萨满,立即病好了。“当村里人来找我驱邪化病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是萨满了。”而她并不像我们印象中的萨满那么诡秘,她与我们笑谈,与我们临别拥抱,仿佛邻家的老奶奶。
萨满教在锡伯族中间一直流传。萨满教,崇尚万物有灵,将自然万物敬为山神、水神、树神等,心存敬畏。在那些神秘的表象背后,其实有着一种可贵的内涵。如若人类一直有这样一种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自然界又怎么可能沦落到如此满目疮痍之境呢?
而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舞蹈,可以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锡伯族文化的一部分。
在纳达齐牛录乡,一支农民演出队表演的锡伯族原生态萨满歌舞《神歌灵舞萨满风》,也让我们痴迷。这是在大连获得了第十二届全国中老年艺术节表演金奖、最佳创作奖及最佳编导奖的歌舞作品。表演者绝大部分都是农民,他们穿着用兽皮制作的古铜色衣裙,系着腰铃,手持刀戟神具,周身散发着一种远古气息。看他们歌舞,那种撼天地泣鬼神的力量,会让人感觉穿越了时空,心神也随着这些陌生的歌舞飘向遥远之地。那种强劲气势,激发了我们内心的一种久违情怀。
从欢快的贝伦舞,到威武的萨满舞,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锡伯族人内心世界的丰富内容。想当年,也正是这些欢乐以及神武,支撑了他们完成大西迁壮举。一个民族,若有足够强大的精神力量,就坚不可摧。
弓箭之梦
弓箭对于骑射民族锡伯族而言,已经渐行渐远了么?在和平年代里,人们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
经过DNA检测证明,锡伯族就是古代拓跋鲜卑的后裔。古代拓跋鲜卑对华夏文明产生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当他们的后裔锡伯族奉命大西迁,戍守伊犁,又对中华疆土稳固立下汗马功劳。
锡伯族素以“善骑善射”著称,史书记载锡伯族的先民:“儿能骑羊,引弓射乌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力士能贯弓,尽为甲骑。”“俗善骑射,以战死为荣,特产角端弓。”锡伯族人最初游猎于大兴安岭、松花江、嫩江流域,世代以打猎捕鱼为生。清朝乾隆时期,为稳固边疆,朝廷百里挑一,精选一千名锡伯族精兵强将,皆高大威猛,连同家属共计3000多人,跋山涉水,历尽艰险,到达新疆。点名之际,感天动地:牺牲了的勇士,妻子或者孩子义不容辞地代为报到。在新疆,这支精良部队在平叛中英勇杀敌,为国捐躯。而他们的妻子守在家里,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成为勇士们最坚实最温暖的港湾。于是直到现在,锡伯族人亦是男人雄姿英发,女人温柔贤惠。
翻开史册,在我国,弓箭在各民族历史中均有大量使用,包括匈奴的“力士贯弓”、肃慎的“楛矢石砮”、先秦的“胡服骑射”、突厥的“上赐之射”、月氏的“神骏骑射”、蒙古族的“男子三艺”、满族的“国语骑射”等。各民族的骑射文化相互交流促进,之间既有共同点,又有各自鲜明的个性,真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构成了中华弓箭文化的灿烂篇章。
在扎库齐牛录村,我们还看见了一堵厚厚的土墙,那是1828年修建的城墙,内外有壕沟,城墙下部宽达10米,上部4米宽,高3.5米,上边可以走牛马车。听说70年代还保留完整。而今,这座四方城墙却只剩下十几米……
古城墙,那是历史的一段见证,也是英雄主义精神的印迹。
察布查尔地处乌孙山与天山支脉之间的一个山谷地带,当潮湿的海洋风吹来,就给这片土地带来天赐厚泽,加之有伊犁河水横亘而过,使得这里成为新疆少有的风水宝地。居住在这里的人们,随便撒下什么种子,不需劳神费力,都能够长得郁郁葱葱。锡伯族人也像一粒种子,从东北西迁而至,落在这片沃土上,扎下根来,生息繁衍。他们也将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带到了这里。
当我站在察布查尔大渠边,眼望蓝天白云之下浩荡流淌的伊犁河水,心绪难平。已经过去200多年,这座大渠,依然给人一种宏大壮阔的感觉。站在龙口,伊犁河水就从这个龙口一分为二,一边被引入察布查尔,另一边则继续原路奔流。大渠远处,水鸟翩飞,芦苇摇荡,村落相望。这座100公里长的大渠,使当年万古荒原成为米粮之仓。
这一伟大壮举始于1802年(嘉庆七年)9月1日,即西迁38年后,锡伯族人在他们的总管图伯特的引领下,在察布查尔山口开凿渠道,南引伊犁河水。听当地人讲,当时面对如此浩大的工程,图伯特英明果断,每牛录抽100青壮年,八个牛录共800劳动力,分编成两个大队,春秋两季分期换工,轮班劳作,采取边挖渠放水、边开荒种地的办法,不但解决了渠道的试水问题,而且使劳动力的口粮得到保障。大渠修建历时七年,最终大功告成。
察布查尔大渠的修成彻底改变了西迁锡伯族人的命运。从此,伊犁河水哺育了他们以及这片土地,春生,夏长,秋收,生息繁衍,绵延流长。图伯特也因此被西迁的锡伯族人认为是开创了他们千秋大业的伟人。后人建图公祠,以示纪念,希望重振民族精神,激励子孙后代,奋发图强。
看察布查尔大渠,访图公祠,我们依然从中体会到一种英雄主义精神脉络的生发与延续。锡伯族人,正是凭借着这种精神力量,从西迁、戍边、维稳,到屯垦、安居、乐业,皆叱咤风云,有声有色。
无论是古代以渔猎为生,还是编入清“八旗”从戎,无论是百步穿杨,还是驰骋疆场,都见证了锡伯族神勇善射的英雄主义精神,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情操。
在察布查尔,每一景,每一物,都让我们看到这个民族血脉深处的精神涌动。这种精神,已成为他们灵魂深处的一种无形资产。这种精神即弓之道,弓箭文化构成锡伯族传统文化之魂,铸就锡伯民族战胜困难、顽强拼搏的精神支柱。
至今,察布查尔无愧于“箭乡”美誉。锡伯族人骑射骁勇的血液依然流淌在他们的血管里。在这里,射箭比赛国际级以上运动健将就有29位。它是中国传统弓箭和现代弓箭国家研究人才的培养基地。“弓箭制作技艺”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锡伯族弓箭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个优秀的组成部分,是中华弓箭文化的一支绚丽奇葩。
到了箭乡,你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英雄主义的气概,保家卫国的情怀,这就是箭乡之魂。
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