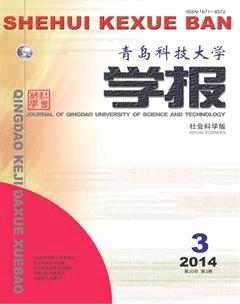“礼运大同”与“富民安人”
纪光欣+毛彬华
[摘 要]和合管理是传统社会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和合目标观是传统和合社会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其中,“礼运大同”是和合管理的社会性目标,“富民安人”是和合管理的人文性目标,二者的和合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管理思想中的和合目标的完整图景,对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实践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关键词]和合;和合管理;社会管理;社会和合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4)03-0022-05
“Liyun Datong” and “Fumin Anren”
—the harmonious target view in management thoughts of traditional society
JI Guang-xi, MAO Bin-hu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Abstract:Harmonious management is the basic spiri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 of social management, in which important content is the view of harmonious target. “Liyun Datong”is the social objective and “Fumin Anren” is humanity target. The harmony of both forms an integrated prospect of harmonious targets, which still h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practice of current social management in China.
Key words:harmony;harmonious management;social management;harmonious society
和合是客观世界的普遍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传统中国社会,无论是《尚书·尧典》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周易·乾卦》的“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礼记·礼运》的“大同”“小康”,还是孔子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老子讲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庄子阐发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墨子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上》),以至近代思想家康有为、孙中山倡导的“天下为公”,甚至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和衷共济”“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可以说,和合(和谐)的社会理想历久弥新、传承不辍,一代代思想家、志士仁人殚精竭虑、不懈求索,凝聚成了中华民族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对社会管理目标的执著追求。传统社会管理思想中的和合目标观是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心理基础和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
一、和合管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思想的精髓
中国传统文化是崇尚和合的文化,和合是一个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且内涵丰富的哲学概念,始于先秦时期,在老子、孔子、荀子、管子等各家的著述中都有着关于和、和合思想的诸多阐述,并逐渐成为儒家、道家、佛家所通用的概念,而演化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成为传统管理文化的核心理念。
就词义而言,“和”“谐”“合”单用属同义词,可以互训。古汉语中,“和”字无论是来自“龢”(《说文解字》:“龢,调也,从龠禾声”),还是来自“和”(《说文解字》:“和,相应也,从口禾声”),本义都是不同声音、音调的相应与协调,后引申为诸多要素、成分间的调和与相应。而“合”字,《说文解字》训:“合,亼口也,从亼口。”其中,“亼”为古文“集”字,意指将诸多元素采集到一起;“口”为人或容器的口形,有合拢、聚集之意。“谐”字一说来自“諧”(《玉篇》训:“谐,合也,调也”),一说来自“龤”(《说文》:“龤,乐龢也,从龠皆声);另有段玉裁训曰:“龤训龢,龢训调,调训龢。”“龤龢作諧和者,皆古今字变。”因此,明宋濂撰《篇海类编·器用类·龠部》有这样的解释:龢“今作和,又谐也,合也。”《管子》也有“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而能谐,谐故能辑”(《管子·幼官》)的说法。由此可知,“和”“谐”“合”三字义同。而“和合”①或“和谐”二字连用,强化了两个或两个以上异质因素之间的协调与融合之意,其含义本质上也是一致的,只是和合在承认差异、冲突的同时,更强调“合”,即“融突”后的整体状态或化生新事物的意蕴,所谓“合而为一”或“合二而一”,因而更具中国文化韵味。所以,张立文教授在其创立的“和合学”理论中,就把和合理解为“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诸多形相无形相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过程中诸多形相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所以和合是冲突与融合的统一体,既是融合性冲突,也是通过冲突达成融合,可简称为融突。简言之,和合就是融突[1-2]。这是对传统和合范畴内涵的深入挖掘和独特阐发。
从哲学上看,和、和合(和谐)是儒、道、墨、佛等各家各派所认同的社会组织原则,集中反映着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国语·郑语》提出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提出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确立了和、和合思想的基本走向,成为传统和合精神的经典阐释。和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认为在天、地、人中,人具有最高的地位,而在时、利、和中,和具有最高的价值;荀子也提出“和则多力”的观点:“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道家以和为事物发展的动力。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提出“德之和”“夫德,和也”(《庄子·缮性》)。道家思想中由阴、阳两个方面对立互补、动态协调而成的“太极图”成为和合思想形象而又深刻的阐释(《老子》第42章)。《易传》中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太和观念,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周易集解》卷1)。这些都表明,不同甚至对立因素的和合,才是事物顺利发展的动因,所谓“和故百物化焉”(《礼记·乐记》)。总之,既承认和尊重多样性、差异性,又协调、融合不同的事物或要素,通过宽猛相济、仁礼相谐、德法并重、执中行权,达到身心、人际、群己、天人之间的和合,是中国传统和合思想的基本精神。由于儒、道、墨、兵、阴阳等各家的抱负都不在于纯粹的学理思辨,而在于“治国安邦”“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智慧,如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指出:“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因而道家的“无为而治”、儒家的“仁者爱人”、墨家的“兼爱”“利人”、法家的“唯法为治”、兵家的“应敌而变”等,只是诸子各家开出的“药方”,各有千秋,这就使得传统和合思想具有了鲜明而自觉的政治管理或社会管理意蕴,或者说,和合管理是传统和合思想的必然走向和内在要求。
在传统社会管理思想的视野内,和合既是管理过程,也是管理目标;既是管理工具、管理方式,也是管理目标和管理的理想境界。和合管理是使管理要素、管理方式由差异、冲突到互补、协调与融合的“和合而生生”的过程,是一个形成新事物、新生命、新结构的基本方式。孔子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致中和”,孟子的“治民之产”“以德服人”,荀子的“隆礼重法”“王霸杂用”,庄子的“合异以为同”等,都是管理手段的和合。由和合管理达致管理和合,就是一个经由社会管理的和合过程和管理手段的和合运用,实现理想的社会生存和发展状态。这种理想状态就是社会管理的和合目标,就是和合社会目标—“礼运大同”与和合价值目标—“富民安人”的和合。
二、“礼运大同”:传统社会管理思想的和合社会目标
传统中国,理想的和合社会就是“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理想是《礼记·礼运》中借孔子之口而提出来的,所以常被称为“礼运大同”。原文如下: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
一般认为,《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的著作汇编,相传为西汉前期戴德、戴圣叔侄编定,东汉末年郑玄作注后流行。宋代朱熹把其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人们所熟知的“四书”,成为儒家经典。对“礼运大同”的思想倾向历来存在争议,但就其思想内容来看,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以儒家为主,融合儒、道、法、墨、阴阳等各家思想所形成的传统中国社会管理共同的理想目标[3]。先秦时期,礼崩乐坏、诸侯争霸,身处乱世又有天下情怀的儒、道、法、墨等各家先贤都表达了对社会理想目标的渴望,并提出各自的治国理政之道。如儒家的“先王之道”、道家的回归自然、墨家的“兼爱非攻”、法家的“循法而治”等。所以,“礼运大同”本身是先秦各家所憧憬的社会管理目标“不同而合”的产物。“礼运大同”的社会管理目标包含着丰富而具体的内容,涉及制度、经济、福利、用人、人际关系、道德等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是对一个理想的社会状态的全面刻画[4]。
(一)“天下为公”:礼运大同社会的总纲领
“天下为公”是大同社会的根本制度基础。儒家“托古改制”,把夏商周三代社会制度美化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孔子自己虽然没有亲自看到过、经历过(“丘未之逮也”),但是,一个“志”字(“而有志焉”)充分表达了孔子对“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的热切期盼。这种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社会理想反映的不仅是西汉初年经历社会大动荡后从统治者到老百姓对安定和谐社会秩序的渴望,而且体现着传统社会管理思想对社会目标的基本认知和人们对美好社会生活的无限向往,成为传统中国社会追求统一、安定和变革的精神动力。
(二)“选贤与能”:德才兼备的人才选拔
官吏是传统社会主要的人才,也是实际的社会管理者,儒家从“德治”“仁政”的政治理想出发,自然会主张以“贤与能”,且以贤为先的官吏选拔机制。认为只有把那些道德高尚、能力突出的人选拔到管理岗位上来,才能更好地实现大同社会各方面的目标。这里,儒家实际上把大同社会的实现寄托在那些贤能的统治者和管理者身上。诚如孟子所说的“以德行仁者王是也”(《孟子·公孙丑上》)。
(三)“货不必藏诸己”:财产公有的经济制度
这里的“货”,是指财货、财产。人们珍视财货,注意节俭,却并不据为己有,表达了财产应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有共享的社会理想。
(四)“力恶其不出于身”:人尽其能的劳动状态
人们厌恶那些不能尽职尽力劳作的行为,但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不必为己”)。这里的“力”应该包括孟子所说的身力和心力即劳力和劳心。这是说,大同社会里,人们各履其职、各尽其能,自觉地为社会奉献自己的劳动。这是一种劳动状态,也是一种社会风尚。
(五)“男有分女有归”:各安本位的社会分工
先秦儒家中,荀子是最早提出“群分论”组织观的,其中“分”就是一种社会分工结构,也是一种社会秩序和管理手段。他认为“群而无分则乱”(《荀子·富国》),农、士、商、工四个阶层的人要各安其位、各负其责,君主要“制礼义以分之”(《荀子·礼论》),才能形成合理的社会秩序。同样,大同社会里,每一个社会成员要根据性别、年龄、阶层和需要等进行适当分工,以便在社会结构中有其位置、机会和职责,形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和谐社会分工体系。
(六)“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人性关怀的福利保障
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公平的、人性化的,那些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年丧父的孩子、老而无子的人、残疾人,一切丧失劳动能力或不能自己生活的人,在大同社会里“皆有所养”,都将得到社会的供养和照顾,整个社会充满了温情和仁爱。儒家的这一理想尽管在传统社会没有实现,但在当今社会福利政策中正在逐渐成为现实。
(七)“讲信修睦”:诚实和谐的人际关系
大同社会里,与其经济、劳动、人才、分工等方面的社会制度相适应,必然存在团结友爱、诚实信用、和睦融洽的人际关系,没有战争,没有盗窃,人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谋闭不兴,盗贼不作,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们生活在安定和平、幸福和谐的社会环境中,整个社会形成了良好的道德风尚。
当然,“大同”不是无差别的均质化社会。郑玄注:“同,犹和也,平也。”“大同”实为“大和”,即各种社会要素的协调配置和人与人关系的和睦相处”,故也是“大平”,即社会制度的公正平等和社会关系的规范有序,也就是《易·乾·彖》中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万物各正性命,社会保合太和的状态就是“大同”。
“礼运大同”表达的传统中国社会所追求的公有共享、各尽其能、各安其位、公正平等、道德高尚的和合社会目标,尽管因其历史局限而难以实现,但是,其与当今中国社会正在追求的富强、民主、自由、文明、和谐社会一样,代表着不同时期的“中国梦”,共同传递着中华民族建设和谐美好社会的“正能量”。
三、“富民安人”:先秦社会管理思想的和合价值目标
“富民”“安人”是传统儒家对社会管理的价值目标的设计与追求,孔子的“德治”、孟子的“仁政”、荀子的“王制”,都是以“安人”为核心和最终归宿的。而“安人”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要“富民”。所以,“富民”与“安人”和合起来,才是对传统社会管理思想中的和合价值目标的准确概括。
孔子之前,管仲明确提出“富民”的政治主张,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也”(《管子·治国》)。即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孔子在回答冉有关于卫国的施政目标时,明确回答:“富之”(《论语·子路》)。孟子继承孔子思想,强调社会的稳定和谐,认为使百姓能过上温饱富裕的生活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前提,因为“有恒产者有恒心”。传统社会的根本是土地问题,孟子主张平分土地给民众,使民众都能养家糊口,从而才能保持统治秩序的稳定,所谓“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之而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滕文公上》)。“易其田畴,薄其赋税,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荀子提倡“上下俱富”,即国富与民富并举,但仍认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荀子·富国》)。实际上,荀子是把“富民”摆在了“富国”之前。儒家提出的“使民以时”“政在节财”“薄税敛”“惠而不费”“通工易事”等社会管理政策,都意在使统治者“制民以恒产”而富民。当然,以儒家为主的传统社会管理哲学,认为“富民”之后,需要“教之”,“教人以人伦”“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滕文公上》),认为只有使百姓懂得“仁义礼智信”,并以此规范其行为,才能最终达致“民安”的目的。孔子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对于社会管理者来说,“修己”是前提,而“安人”是目标,一切从“修己”开始,以“安人”结束。综合起来分析,“富民安人”包含着儒家“爱民、保民、富民、利民、养民、教民、安民”等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传统社会管理和合价值目标的集中体现。
(一)“富民安人”是儒家“治平”理想的最终目的
儒家思想既是一种“修己安人之学”,更是一种“安邦治国之学”。常言道:“儒言治世”,是说治国平天下乃是儒家最重要的人生理想,从先秦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均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可见一斑。《大学》所讲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修身”以上是“内圣”问题,“修身”以下则是“外王”问题。而“修身”“明德”“正己”等对社会管理者的道德要求(“内圣”)只是治平天下(“外王”)的前提或手段。内圣外王,治平为本。中国传统社会管理主要是通过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道德自觉而实现,是一种德治为主、自我管理为先、“善政”为目标的管理模式。而“治平”“外王”的理想社会状态就是“礼运大同”,儒家追求“治平”理想的最深厚的根源仍在于其民本思想,也就是为“富民安人”创造出一个安定、公平、和谐的理想社会环境,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这在存在着周期性社会动荡的传统社会里,无疑是一种非常现实的要求。
(二)“富民安人”是传统民本思想的具体表现
以民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鲜明特色,重民、贵民、安民思想一直是儒、道、墨、佛等各家各派思想的核心,其中以儒家最为典型。民本或人本思想最早是由先秦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提出的,其曰:“夫霸王之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尚书》中亦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春秋》提出“民者,君之本也”;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比喻君民关系,等等,都是对民本思想的具体阐释。而以民为本、爱人贵民的具体表现就是“富民”“教民”“安人”。孔子曰:“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荀子也指出:“不富无以养民情。”(《荀子·大略》)对社会管理者或统治者来说,唯有让百姓过上共同富足的生活,安居乐业,然后对百姓加以教化和引导,才能实现社会管理长治久安的目标。
(三)富民安人”是传统和合思想的内在要求
和合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交融意蕴,和合凸显着人的地位与价值,和合思想的核心是“人和”,即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之身心之间的共生共荣、同心合力的和谐关系。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荀子曰:“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荀子·王霸》)董仲舒亦曰:“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大于中。”(《春秋繁露》卷十四《循天之道》)这都表明,以和为贵,而和最根本的是“人和”。要达到“人和”,就必须“富民”“安人”。民富则心安,心安则人和。所以,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只有“富民安人”,方能达到人和,人和,社会才能和谐。
当然,传统民本思想主要是从君民关系、维护君主统治合法性的角度来立论的,即“富民安人”的最终目的是“使人”。孔子曰:“惠足以使人”《论语·阳货》),但其所表达的对社会管理目标的价值关切和人文关怀则是普适的。在当代的社会管理实践中,“富民安人”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就是要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安康作为社会管理的最终目标和根本价值尺度。
四、小结
目标是管理的第一个要素,管理是实现目标的工具。目标对管理的意义,就像指南针对于轮船的意义一样。管理的职责在于把组织的人才和资源集中于“做正确的事”并使之产生结果,即实现目标上来。“一个缺少全体衷心共有的目标、价值观和使命的组织,必然难成大器。”[5]无论对一个组织,还是对一个社会来说,管理都需要愿景、目标的引导与激励。先秦时期儒、道、法、墨各家以社会和合为社会管理的理想目标,探求社会管理的和合之道,成为传统和合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对后世传统中国政治管理、社会管理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传统社会管理思想的和合目标中,“礼治大同”可以看成是工具性目标,是社会性目标,表现在社会结构层面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富民安人”可以看成是价值性目标,是人文性目标,表现在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实际发展程度上。社会性目标为价值性目标的实现创造着具体的社会条件,人文性目标为社会性目标的实现确立了明确的价值导向。因此,“礼运大同”与“富民安人”的合二而一、融突和合,集中地表现着传统社会管理思想中完善的社会管理目标图景,是先秦儒家民本(仁本)思想的最终归宿。
传统社会管理的和合目标观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启示就是,无论是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还是通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更好地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都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把新的“富民安人”,即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作为根本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在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与人的参与、人的发展的和合中,选择和确定合理有效的社会治理策略。
程思远.二论世代弘扬中华传统和合文化[J].中华文化论坛,1998(1):29.
张立文.中国和合文化导论[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27.
黎红雷.儒家管理哲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301-302.
张立文.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构想[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096.
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9.
[责任编辑 祁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