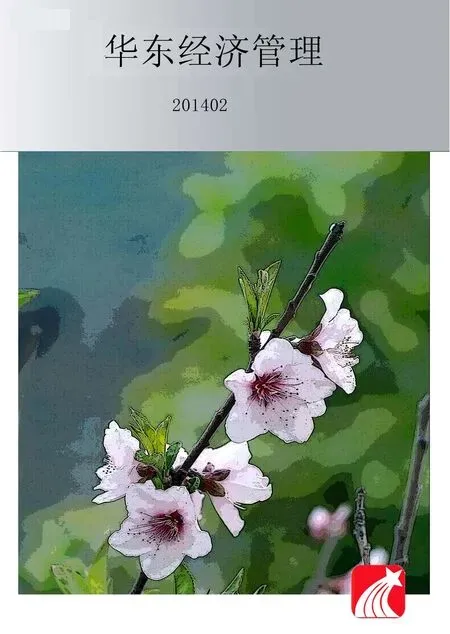储蓄和消费:群体规范对自我建构的影响
代云龙,吕 巍,曾世强
(上海交通大学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30)
一、引 言
储蓄和消费是人们日常生活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储蓄率过低而消费过高,而中国则明显相反,表现为储蓄率非常高而消费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同一国家的消费者,属于不同群体的个体也会在储蓄和消费行为上产生一定的差异,例如,中国老一辈的人就比新世代的年轻人储蓄得更多,同一个大学中属于不同社团的学生也会产生差异。本文将深入探讨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个人的储蓄和消费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了收入、性别等因素的印象,也会受到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群体规范便属于后者。当人们进行储蓄和消费活动时,会将自己的行为与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的主流行为进行比较,并最终做出选择。
然而,不同的自我建构类型的个体,其对群体的认同程度有很大差别,因而会导致对群体规范遵从程度不同。相依自我的自我概念中社会认同程度更高,会更容易受到群体规范的影响,选择与群体规范相一致的行为;独立自我的自我概念中社会认同程度较低,群体规范对独立自我的影响就不是那么显著。
所以,本文结合自我建构和社会认同理论,研究群体规范和自我建构的交互作用对人们的储蓄和消费行为的影响。本文的主要假设为:相依自我在群体规范分别表现为消费和储蓄时,其消费意愿有着显著差异;而独立自我在群体规范分别表现为储蓄和消费时,消费意愿没有显著差异。假设通过两个实验证实,第一个实验研究了感知群体规范,证实了群体规范和自我建构与个体储蓄和消费行为的相关性;第二个实验采用图表对群体规范进行操控,增强了外部效度,进一步证实了群体规范和自我建构的交互作用会对个体储蓄和消费行为产生影响。研究结果在丰富了自我建构和储蓄消费相关理论的同时,也对降低储蓄提高消费提出了新的解决思路。
二、文献综述
(一)自我建构
Markus和Kitayama[1]认为个体通过将自身置于某一参考系中进行比较,获得自我认知,而个体关于自我和他人关系的信念就被称为自我建构,也即把自己看作与他人分离还是联系的程度。Markus和Kitayama更进一步区分了东方和西方文化中的两种典型的自我建构类型,分别是独立自我和相依自我。独立自我的个体注重自身的独特性,重视那些能够表现出个人特质和偏好的个性和行为,而相依自我的个体则注重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重视他人的看法和行为,通过他人来定义自我。
对每一个个体来讲,独立自我和相依自我都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强弱有所不同。西方文化强调个体的独立性,个体在表达观点和发生行为时往往关注的是自己的看法,所以西方文化下的个体的独立自我表现更为突出。东方文化则更多地强调集体主义,强调个人应服从与集体,注重个人与他人的关系,通过他人来对自我进行定义,所以东方文化下的个体更多地表现为相依自我。
(二)社会认同和群体规范
Tajfel[2]在很早之前根据人们组间和组内行为的差异,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他认为社会认同是个体自我概念(self-conception)的一部分,它包括个体对自己作为某个(或者某些)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的认识,以及附加于这种成员身份的评价和情感方面的意义。当某一类别的成员身份变得显著时,人们主动地在重要维度上夸大不同类别个体之间的差异,而将同一类别中个体的差异最小化,并且根据类别成员共同的特征而不是个人异质的特征知觉自己和他人。之后Turner对原有的理论做了改进,提出了自我分类理论[3],自我分类理论强调把自我归入某一群体之中,个体在进行某项行为时会唤醒社会认同而不是个人认同,自我概念将主要建立在社会认同之上,那么自我就会与群体标准相一致,相关的态度、感觉、信仰和行为就会以群体的标准来定义。
但是从群体的标准跨越到群体规范仍有一点距离。尽管我们能够识别出很多种类的群体标准,但是一旦没有人与我们的看法一致,那么这种群体标准就是不可持续的。所以,群体标准是群体成员协商之后的一致意见,这种意见构成了社会现实,并不断被加强[4]。只有当处于同一群体的人在同一情境下能够共享的群体标准才能称得上是群体规范[5]。Hackma[6]认为群体规范是群体用来调整和约束群体成员行为的非正式规则,这些规则很少被写下来或者公开讨论,但是这些规则对群体成员的行为有着极大的影响。
在研究内容上,关于群体规范的大部分理论研究都将关注点集中在研究群体规范的类型和阐释群体规范的结构特征。而实证研究则集中于群体规范如何对其他社会行为产生影响,例如,学者将群体认同(group identification)和群体规范等变量引入原有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中,对吸烟[7]、回收易拉罐[8]、锻炼[9]等行为的研究证明,行为相关的参照群体的规范与个体的行为意愿是相关的,但是仅对那些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较高的人有明显的影响,如果一个人不认同自己所在的群体,那么他受到群体规范的影响就会小很多。
因此,规范是人们共享的关于思想、感觉和行为的模式,在群体中,人们的所讲和所作正好传递了与规范有关的信息。当规范决定了特定情境下的群体成员关系和个体的自我定义时,规范会对个体的意愿和行为产生较大影响。简单来说,群体规范对那些拥有较高群体认同水平的人影响更显著。
(三)储蓄消费和群体规范
群体规范对群体成员的储蓄和消费行为产生影响的前提,是与储蓄和消费行为相关的群体规范的存在。当与储蓄和消费相关的群体规范存在,群体成员才会将自己与群体的主流或者一般行为进行比较,从而受到群体规范的影响。
Duesenberry[10]提出:首先,人们对贫穷和富有的感知不依赖于收入和储蓄的绝对值,而是与参照的群体比较之后的相对值;其次,一个人的储蓄行为会部分受到群体规范和身份的影响,在消费行为上也是如此。Hsee[11]认为人们的财富的内在是无法评估的,之后在联合评估(joint evaluation)的时候才能给人带来快乐。Cynamon和Fazzari[12]认为人们在做出消费或者理财方面的决策时,会以参照群体的行为作为指导,人们会从群体中学习最大化个体效益的技巧,也会将自己的消费行为和群体行为做比较。Cynamon和Fazzari进一步将消费规范解释为个体以群体认同为基础认知到的群体的消费行为标准,并认为在研究现代消费行为时,这种规范的力量不容忽略。
从这个角度来看,储蓄和消费是有作为群体规范的理论基础的,也即储蓄和消费是一种群体规范。人们在做出储蓄和消费决策时,会以群体规范作为指导,人们会从群体中学习最大化个体效用的技巧,也会将自己的行为和所属群体进行比较。如果参照群体倾向于更多的储蓄,个人也会倾向于这么做,反之亦然。
(四)研究假设
有学者发现,储蓄和消费行为除了受到收入、社会保障、教育支出和养老方式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社会、文化等心理和行为因素的影响。例如Martineau[13]的研究表明,个人的社会地位是购买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一个人将要购买的东西与其社会地位和群体关系密切相关。
虽然影响储蓄和消费的因素很多,但是在解释不同国家或者跨文化的储蓄和消费差异时,自我建构这一理论更能发挥出效力。Tung和Baumann[14]在研究中证实,虽然与周围的白人伙伴处于同样的社会环境及制度中,澳洲及加拿大土生土长的华裔的储蓄率依然远高于白人,更加接近中国大陆居民的水平。潘黎和吕巍[15]的研究证明,在面对储蓄和消费两个互相冲突的目标时,独立自我比相依自我更倾向于选择消费目标,相依自我比独立自我更加倾向于选择储蓄目标。
在同一文化背景下,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其储蓄和消费行为也会有差异。例如,在北京国贸上班的职员和在中关村当码农的程序员有着截然不同的消费方式。这是因为群体中的个体也会受到他人的储蓄和消费行为以及对储蓄和消费行为看法的影响,也即受到群体规范的影响,而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规范。需要注意的是,前文提到的不同文化的国家在储蓄和消费上有差异,也可能有群体规范的影响在其中。
进一步观察发现,同一群体的成员的储蓄和消费行为虽然大体上相一致,但是在同一群体内部,不同自我建构的个体仍会有一定的差异。有研究者认为个人的独立自我水平和对重要的人遵从程度负相关,而相依自我水平和对重要的人的遵从程度正相关[16-17]。在大多数情况下,重要的人往往指的是个体所属的群体。由于自我建构会造成人们因为当自我概念中的社会认同更为突出,所以个体就更容易参与到与参照群体的群体规范相一致的行为中来[8-9,18]。如果自我概念中的社会认同或者说群体身份不显著,那么个体的行为就更容易与个人特质相一致,而不是群体规范,群体规范的影响有限。
因此,本研究认为相依自我在自我概念中群体认同水平较高,更注重自己的群体身份,而独立自我在自我概念中自我认同水平较高,更注重自身的个性和特质,所以相依自我比独立自我更容易受到群体规范的影响。
本研究关键假设如下:相依自我在群体规范分别表现为消费和储蓄时,其消费意愿有着显著差异,而独立自我在群体规范分别表现为储蓄和消费时,消费意愿没有显著差异。
研究由两个小实验组成,两个实验的内容和流程基本相似,均从自我建构、群体规范及储蓄和消费的行为意愿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唯一的不同在于对群体规范的测量。实验一首先进行了自我建构的操控,之后测量了被试感知到的与外出就餐这一消费行为相关的群体规范,也即测量的是感知群体规范(perceived group norm),最后测量了被试的消费意愿。需要注意的是,实验采用测量感知群体规范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证明在学生中外出就餐消费金额存在着不同的规范;二是证明这些不同的规范会对学生的行为产生影响;三是可以测量出被试所感知到的群体规范的总体情况是偏向储蓄还是消费。实验二是对实验一的补充,在研究群体规范时采用了对群体规范进行操控的方法,与实验一强调实际规范存在着差异不同,采用操控的方法是为了强调人为造成的群体规范的变化,从而证实群体规范的改变会造成被试消费行为的改变,验证群体规范对自我建构的调节作用。
三、实验一:储蓄和消费:操控自我建构×感知群体规范
(一)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2(自我建构操控:相依自我和独立自我)×2(感知群体规范:储蓄和消费)的双因素组间设计。该实验采用问卷法进行,地点为图书馆,共253名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参与了本次实验,有效问卷239份。被试中男性共有159名,比例为66.5%,女性为80名,比例为33.5%。被试平均年龄为22.09岁(SD=2.989)。
在被试填写问卷之前,研究人员会向被试详细解释研究目的和研究过程,强调问卷的填写顺序。实验由三部分组成,自我建构的操控、感知群体规范的测量和消费意愿的测量。
自我建构的操控。被试被告知阅读一段游记,这一步骤实际上是用来启动不同的自我建构。我们选用了Sui和Han[19]所采用的圈人称代词的方法,根据潘黎和吕巍[20]对文献的总结一文,该文章是发表在国际权威心理杂志上的唯一一篇使用中文材料的文章,而且圈代词的方法也是公认比较干净的一种启动材料。该材料共有2篇关于旅游的故事,每篇故事都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中全部都是与独立自我相关的词语(如“我”、“我的”),另一个版本中全部都是与相依自我相关的词语(如“我们”、“我们的”),被试被随机分配到读4个故事中的一个,并被要求圈出所有的人称代词后数出具体的个数。由于该操控方法已经被反复验证过有效性[21,19],所以实验中并未直接进行操控检验。
感知群体规范的测量。群体规范这里采用感知群体规范进行测量,被试根据自己所属的朋友或同学圈子的生活,会对所属群体的成员对外出就餐的看法和实际行为有着自己的感知,从而形成感知群体规范,然后不同的个体往往属于不同的群体,从而在感知群体规范上会产生差异,进而构成群体规范的两个维度——偏向消费和偏向储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减少消费与达成储蓄目标是一致的。感知群体规范采用4个7分题项进行测量[22,8,23-24],被试需在7分的维度上就自己的意愿进行打分,例如:“你的同学中有多少人赞同每周外出就餐一次(人均消费100元)?(1-完全没有,7-全部同学)”;“你的同学中有多少人每周会外出就餐一次(人均消费100元)?(1-完全没有,7全部同学)”等。
消费意愿的测量。采用3个7分题项对被试外出就餐的行为意愿进行测量[22,8,23-24],虽然描述上有所差别,但是简单来讲,分值越高,被试的行为意愿便越偏向消费。例如:“你期望每周外出就餐一次(人均消费100元),1-非常不期望,7-非常期望;你打算每周外出就餐一次(人均消费100元),1-完全没有这种打算,7-这种打算非常强烈”等。三个问题的均值较高表明被试的消费意愿更强,均值较低则表明了被试减少消费的意愿,反映了被试的储蓄意愿。
(二)实验结果及分析
为了检验群体规范在本实验中的调节作用,采用方差分析(ANOVA)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由于在本实验中,变量群体规范是以被试感知到的群体规范进行表征,所以在处理时需标准化,之后按值的大小分为高低两组。分析结果表明本实验中自我建构和群体规范对储蓄消费行为的影响是显著的(F=9.04,p<0.05),如图1所示。对相依自我来讲,感知群体规范分别为储蓄和消费的两组的均值之间有显著差异(M消费=4.18,M储蓄=2.72,p<0.001);对独立自我来讲,感知群体规范分别为储蓄和消费的两组的均值之间有差异,但是并不显著(M消费=3.92,M储蓄=3.59,p=0.19)。此外,我们注意到被试感知到的群体规范的均值在4分以下(M=3.54,SD=1.21),说明中国大学生这一群体所感知到的储蓄消费相关的群体规范总体上是偏向储蓄的。
分析结果表明,群体规范会对相依自我和独立自我的人产生影响。相依自我在群体规范分别表现为消费和储蓄时,其消费意愿有着显著差异,而独立自我在群体规范分别表现为储蓄和消费时,消费意愿没有显著差异,从而证明了我们的假设。

图1 群体规范对自我建构的调节作用
四、实验二:储蓄和消费:操控自我建构×操控群体规范
(一)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2(自我建构操控:相依自我和独立自我)×2(群体规范操控:储蓄和消费)的双因素组间设计。实验采用问卷法进行,地点为图书馆。共264名学生参与了本次实验,有效问卷238份。被试中男性共有160名,比例为67.2%,女性为78名,比例为32.8%。被试平均年龄为21.21岁(SD=2.307)。
在被试填写问卷之前,研究人员会向被试详细解释研究目的和研究过程,强调问卷的填写顺序。实验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自我建构的操控,群体规范的操控和消费意愿的测量。
自我建构的操控部分同实验一。
群体规范的操控和操控检验。采用过去研究中的数据理解方法[25,18]对群体规范进行操控,也即通过数据图表反映出群体规范内容,被试通过阅读图表理解其内容达到操控的目的。首先,被试会看到一系列的柱状图(如图2和图3),这些柱状图描述了大学生对外出就餐这一行为的支持程度,图表从两方面进行描述。图2描述的是储蓄规范:73%的大学生对每周外出就餐一次(人均消费100元)是不赞同的;实际上67%的大学生不会每周外出就餐一次(人均消费100元)。图3描述的是消费规范:73%的大学生对每周外出就餐一次(人均消费100元)是赞同的;实际上67%的大学生会每周外出就餐一次(人均消费100元)。

图2 群体规范的操控(储蓄规范)

图3 群体规范的操控(消费规范)
为了进一步加强操控的效果,被试需要对一系列反应外出就餐这一目标行为的观点进行总结,而这些观点被解释为来自于之前参加某一项相关实验的大学生。这些观点暗示了大部分大学生是赞同/不赞同外出就餐这一行为的,或者是否切实发生过这种行为,在阅读完这些观点之后,被试需要对这些观点用自己的一句话进行总结。
之后,被试会对图表描述的情况的真实性做出判断,作为操控检验,如果被试认为图表描述的情况不属实,那么认为操控失败。
消费意愿的测量,同实验一。
(二)实验结果及分析
为了检验群体规范在本实验中的调节作用,采用方差分析(ANOVA)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从分析结果来看,本实验中自我建构和群体规范的交互作用对储蓄消费行为的影响是显著的(F=4.93,p=0.03),如图4所示。对相依自我来讲,感知群体规范分别为储蓄和消费的两组的均值之间有显著差异(M消费=4.13,M储蓄=3.25,p<0.001);对独立自我来讲,感知群体规范分别为储蓄和消费的两组的均值之间有差异,但是并不显著(M消费=3.55,M储蓄=3.39,p=0.33)。
分析结果表明,相依自我在群体规范分别表现为消费和储蓄时,其消费意愿有着显著差异,而独立自我在群体规范分别表现为储蓄和消费时,消费意愿没有显著差异,再一次证实了我们的假设。

图4 群体规范对自我建构的调节作用
五、结果讨论与贡献
(一)研究结果讨论
本研究进一步加深了自我建构对消费者储蓄消费行为的影响的认识,并考察了群体规范作为调节变量对自我建构的影响。
第一,通过对大学生这一特定群体的研究,证明了相依自我在群体规范分别表现为消费和储蓄时,其消费意愿有着显著差异,而独立自我在群体规范分别表现为储蓄和消费时,消费意愿没有显著差异。
第二,在情境选择上,对大学生来讲,收入来源主要是父母,储蓄消费两种行为中的储蓄并不好研究,所以本研究选取了外出就餐这一行为,大学生外出就餐较频繁,自然是属于消费较为积极的类型,而不愿意频繁外出就餐,就将这笔费用节省了下来,从某种程度上说,减少消费和达到储蓄目标是一致的。
第三,本研究以两种方式验证了群体规范对自我建构在储蓄消费行为上的调节作用,实验一采用感知群体规范,实验二采用群体规范的操控,两者互为补充。
(二)研究贡献
理论上,本研究证实了群体规范在自我建构对储蓄消费行为的影响上具有调节作用,丰富了自我建构和储蓄消费理论。之前对群体规范的研究往往与个体的群体认同程度或者群体身份的显著程度联系在一起,虽然直观,但相对而言仍停留在表面。而深入挖掘群体认同的本质,发现自我建构有着更深层次的影响,相依自我往往具有更高的群体认同水平,独立自我很大程度上不会产生强烈的群体认同,所以本研究加强了对自我建构和群体规范理论上的联系。
实践上,关于自我建构对储蓄消费行为的影响已有学者做了研究,但是个体的长期自我建构是很难改变的,所以很难通过改变人们的长期自我建构来改变人们的储蓄消费行为,而群体规范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操控的。本研究讨论了群体规范对自我建构在储蓄消费行为影响上的调节作用,给如何刺激消费降低储蓄提出了新的思路,对国家制定相关工作方案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六、未来展望
本研究虽然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研究中仍存在许多不足。第一,研究选取大学生这一特定群体,收入上的不独立使得研究具有局限性,由于群体的特殊性,结论在其他特定群体中的效果有待验证;第二,研究仅测量被试的行为意愿,未考察被试的实际行为,而行为意愿和实际行为之间存在着差异,若能考察被试的实际行为,研究的可信度将会大大提高。
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第一,选取其他特定群体,特别是收入独立的成人群体,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第二,本研究以实验方式进行,研究结论在实证研究中是否仍然成立值得探讨;第三,进一步研究不同类型的群体规范,如命令式群体规范和描述性群体规范对自我建构的调节作用。
[1]Markus H R,Kitayama S.Culture and the self: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emotion,and motivation[J].Psychological Review,1991,98(2):224.
[2]Tajfel H,Billig M G,Bundy R P.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intergroup behaviour[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71,1(2):149-178.
[3]Turner J C,Hogg M A,Oakes P J,et al.Rediscovering the social group:A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M].Oxford:Basil Blackwell,1987.
[4]Hogg M A,Reid S A.Social Identity,Self-Categorization,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Group Norms[J].Communication Theory,2006,16(1):7-30.
[5]Turner J C.Social influence[M].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1991.
[6]Hackman J R.Group influences on individuals in organizations[M].Palo Alto,CA: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Press,1992.
[7]Schofffild P E,PattisonP E,Hill D J,et al.The influence of group identification on the adoption of peer group smoking norms[J].Psychology and Health,2001,16(1):1-16.
[8]Terry D J,Hogg M A,White K M.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Self-identity,social identity and group norms[J].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99,38(3):225-244.
[9]Terry D J,Hogg M A.Group norms and the attitude-behavior relationship:A role for group identification[J].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1996,22(8):776-793.
[10]Duesenberry J S.Income,saving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M].L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11]Hsee C K,Y Yang,N Li,et al.Wealth,warmth,and well-being:Whether happiness is relative or absolute depends on whether it is about money,acquisition,or consumption[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2009,46(3):396-409.
[12]Cynamon B Z,Fazzari S M.Household Debt in the Consumer Age:Source of Growth-Risk of Collapse[J].Capitalism and Society,2008,3(2):1-30.
[13]Martineau P.Social classes and spending behavior[J].the Journal of Marketing,1958,28(2):121-130.
[14]Tung R L,Baumann C.Comparing the attitudes toward money,material possessions and savings of overseas Chinese vis-à-vis Chinese in China:convergence,divergence or cross-vergence,vis-à-vis‘one size fits all’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olicies and practices[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2009,20(11):2382-2401.
[15]潘黎,吕巍,王良燕.储蓄和消费的选择:自我建构对应对目标冲突的影响[J].管理评论,2013(3):27-37.
[16]Park H S,Levine T R,Sharkey W F.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and self-construals:Understanding recycling in Hawai’i[J].Communication Studies,1998,49(3):196-208.
[17]Park H S,Levine T R.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and self-construal:Evidence from three cultures[J].Communications Monographs,1999,66(3):199-218.
[18]Smith J R,Terry D J.Attitude-behaviour consistency:the role of group norms,attitude accessibility,and mode of behavioural decision-making[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03,33(5):591-608.
[19]Sui J,Han S.Self-construal priming modulates neural substrates of self-awareness[J].Psychological Science,2007,18(10):861-866.
[20]潘黎,吕巍.从消费者行为学角度研究储蓄和消费行为的现状和评述[J].软科学,2013,27(2):132-135.
[21]Brewer M B,Gardner W.Who is this"We"?Level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self representation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6,71(1):83.
[22]Ajzen I,Fishbein M.Understanding attitudes and predicting socialbehavior[M].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80.
[23]Johnston K L,White K M.Binge-drinking:A test of the role of group norms i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J].Psychology and Health,2003,18(1):63-77.
[24]Francis J J,Eccles M P,Johnston M,et al.Constructing questionnair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J].A manual for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ers,2004(5):2-12.
[25]White K M,Hogg M A,Terry D J.Improving attitude-behavior correspondence through exposure to normative support from a salient ingroup[J].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2002,24(2):9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