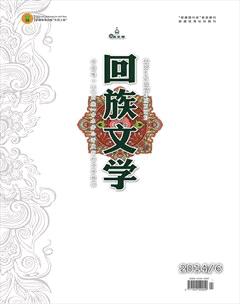头戴刺玫花的男人
马金莲

铃声悠悠响起来的时候,她知道夜里十点半到了。她从昏睡中醒来,慢慢睁开眼,眼睛不去看什么,耳朵不去听什么,心也不去想什么,就那么懒懒地睡着。脖子和枕头以最舒适的方式充分接触,头揉压着枕头,荞麦皮挤作一团发出呻吟和挣扎,索索作响,透过白洋布做的枕芯和绣花枕套传出来,直接钻进耳朵里来了。她醉心地听着。这细碎贴近的声音,像有很多亲人围着她,贴在耳根上给她说一些话。听不清在说什么,好像是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又好像并不重要,只是生活里一些常见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说话的人并不要求她听进去,只是想用这种絮叨来传达一种心情。这声音带着炕洞里玉米秸秆燃烧后的烫热和暖洋洋的味道。那些漫长炎夏中蓄积在秸秆中的阳光沉睡隐藏后,在炕洞里的燃烧中被催醒了。阳光味儿透过水泥炕板和被褥穿透出来,透过一枕芯荞麦皮散发出来,这味道就复杂了,暖烘烘的,带着一股尿骚味儿。这是从老家带来的枕头。
搬迁之前她和大家一样,将所有的被褥都拆洗了,连枕芯里的荞麦皮也用清水洗了,用筛子筛过,重新装回枕芯里带来了。队长见了还笑话大家呢,说,搬迁到大地方去,眼看着是去过好日子,还舍不得丢掉这些陈荞皮?咱山里人眼皮就是太浅了!当时她啥都没有说。邻居的一个年轻媳妇子不依了,双手搓着荞麦皮说,咋啦,带着它们咋啦,老家的味儿老家的念想,全都在这些旧家具旧物儿里头藏着呢,叫人咋舍得丢掉呢?再说川区那地方,千好万好,就是没有荞麦皮,大家都根本不种荞麦嘛!到时候枕头拿啥装?用石头沙子吗?队长被问住了,说,好好好,你这个媳妇子厉害,我不说了,你们快拆洗,看还有啥能拆洗了带走的,尽量全带上。真的搬到了这里,大家发现了当时的选择是多么正确。这里全部种玉米、油葵,就是不种荞麦。枕芯一律用粉碎后的玉米秆子装,她也装了四个新枕头,为的是万一家里来个亲戚要用到。她试着枕过,刚枕上脑壳下木木的,过一会儿里面的疙里疙瘩都明显起来,垫着后脑勺子,很不舒服。还不能动弹,稍微一动里面就窸窸窣窣乱响,吵得人心烦。
她很庆幸自己有远见,把几个荞麦皮枕头都带来了。洗过的荞麦皮洗去了尘土,但是一些原来浸透了荞皮的味道是没法完全洗净的。也许外孙子曾经骑在枕头上耍的时候直接给枕头上尿了一泡,也许女儿把口水淌在了上面。最明显的是,枕过的人都会把头油蹭在上面。还有时间的堆积,日子的点滴,不仅仅体现在她这个主人的外表容颜上和内心里,也体现在这屋子里的每一个物件上。事实上她喜欢这种味道。这是熟悉的温暖的味道。她的大半辈子都是在这种味道中度过的。这种气味渗透在她生命最底的那片布上,成为了一种本色。只有在这种味道中,她的心才是踏实的。两个女儿在城里,她去她们家住过,楼房里那种过于讲究的干净让她老是觉得手和脚不知道放哪里,怎么放才算合适,才不会显得碍眼,不给女儿添麻烦,让女婿看着顺眼。所以她住上三五天就走,回到自己这个家里的土炕上来,一颗捏着的心才能完全舒展开来。
铃声还在响。节奏很缓慢。她从这种缓慢中品出了一股不依不饶的味道。接还是不接?看样子不接是不行了,会一直响下去。会响到什么时候呢?她没有试验过。因为每次她都在这种不依不饶面前投了降,摁下那个绿色的接听键。现在,她忽然想再拖延一会儿。响声却自己歇了,出现了空白。她的眼里拥进黑暗来。外面有星星,夜色不算浓。她望着窗帘后面窗户的样子,不锈钢骨架,玻璃弥补了骨架之间的空白。她皱着眉凝望着。铃声沉睡了。夜色像一层水汽,渗透了玻璃和尼龙布窗帘,泻进来,在眼前幽幽地浮动。她伸出手,张开五指去抓。抓到了,攥紧拳头撤回来,紧紧握着。手心有点酸困了,她坚持着不往开打。
铃声又响了起来。她松一口气,缓缓展开手。手心里什么都没有,她一骨碌爬起来下炕,手机在桌子上充电呢。她一看号码,果然是那个人打来的。她没念过书,但是阿拉伯数字全部认下来了,口头算账很快。丈夫活着的时候常说,你要识文断字,肯定比一般的男人都能成,头脑灵光得很嘛。男人是半开玩笑半认真说的。手机号码都是“0”到“9”十个数字组成的。它们像一群调皮的小星星,被人调动着排队,十一个数字站在一起,就是一串手机号码。每一串号码都连通着不同地方的不同的人。现在这一串号码的尾巴上是“4”和“5”。她眼前显出一张脸,胡子包裹了下半部分,上半部分脸膛黑红。一看就是个吃了一辈子苦操了一辈子心的男人。眉目间的沟壑一道一道的。他才六十四岁,比她的丈夫大了四岁,但是丈夫就显得年轻嫩面多了。他们要是放在一起去观看,肯定像两代人。可惜没机会让他们站在一起比较了。丈夫早在三年前就口唤了。女儿是丈夫口唤后结的婚,所以这个人和她丈夫没有见过面。本来她已经要接了,一想起丈夫,忽然心里有个浪花轻轻翻了一下。她缩回手,慢慢上了炕。手机买回来的时候就是这铃声,不像唱歌,也不像鸟儿虫儿在歌唱,而是慢悠悠的一段音乐。她哪里懂得这是什么呢,刚开始听着怪不顺耳的,时间长了就适应了。音乐还在慢悠悠地唱着。她看着窗外,玻璃上的朦胧中显出两张脸,一张圆润饱满,显得笑眯眯的;一张狭长干枯,下巴上的胡子将一张脸又拉长了一些。他们都在笑,望着她笑。圆脸上的笑欢实、舒展,像一锅水开了,水花儿在一个劲儿翻涌。丈夫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当了一辈子甩手掌柜的,心宽体胖,人也显得年轻;窄脸的男人就不一样了,眉毛都显得干巴巴的,眼神闪烁,不敢直接看她,但是又忍不住要看,目光斜斜扫过来,极快地瞄一眼,又像怕羞的娃娃,赶紧收回去了。
他是什么时候对她有了心思的呢?真不好确定。女儿坐月子她去伺候了一个月,那时候他的女人正病着,他们都忙,连说话的工夫都没有。但是当她离开的时候,他送到大门口,叹一口气说,世上的女人啊,都像你一样身体好性子欢,那该多好。她走在路上才忽然回想起这句话,觉得他肯定是一辈子伺候那个病秧子女人,觉得累,所以看到健康能干的女人就忍不住眼热吧。女儿的娃娃十一个月,婆婆病逝了,女儿要上班,娃娃没人看,她就被女儿接了过去,住在女儿学校的宿舍里帮着看娃娃。乡中学离女儿婆家不远,过一段街道再上一面坡路就到了。他隔三岔五来,骑一辆破得哐里哐当乱响的自行车,来了从车把上取下一个尼龙手提袋,里面装的不是几个白面饼子就是几个油香,油香之间还夹着几片牛肉。饼子是在馒头店里买的。油香的话,那就说明他又去拱北上了。这里离拱北很近,站在女儿家的高房子台阶上能望见南边半山上的拱北,一道巨大漫长的陡山坡,里面密密麻麻分布着土堆,那下面都睡着归真的老人家和众多的朵斯提。过几天就是某一位老人家归真的日子,拱北上就要上坟过乜贴。大的话宰牛,小了就宰羊和鸡。附近的人都撵去吃油香。女儿的公公也去了。他和管事的老汉熟悉,总是能多讨要到几个油香的。他离开拱北就直接到学校来了。进了宿舍却不坐,显得很作难,站在地上呵呵笑,笑容有点傻。女儿把油香掏出来,放下几个,给他留两个。他接过口袋呵呵一笑,就告辞了。出门的脚步有些仓皇。然后自行车哐里哐当响着,他走远了。女儿渐渐地不耐烦起来,有了抱怨,说,这老汉隔几天就跑学校来,不是在图谋啥吧?嘴里说想孙女儿了,难道孙女儿就真的那么让他牵肠挂肚?女儿胳膊下夹着教案,说完之后就匆匆出去上课了。
她呆在了门口,透过玻璃看着操场上做完课间操乱纷纷往教室里拥的学生,忽然觉得心跳得有点异样。那个推着自行车一步一步仓皇离开的背影出现在眼前。他真的是想念孙女儿才一趟一趟地往来跑吗?好像是,这是最堂皇的理由。可她又觉得不是。至少不全是。她从他有些别扭的神情和动作里捕捉到了一股别有意味的目的。他不敢看她的眼睛,说话的时候只是看孙女儿,看地面,看桌子,就是不敢看站在对面的她。她直直地盯着他,发现他很少抬起头来看自己的眼睛。不是他不想看,而是不敢,那闪电一样划过去的慌乱的目光把什么都透露了。难道他一趟趟来这里和自己有关?忽然意识到这一点,他再来,她慌乱了,再也不能像过去那么从容坦然地看着他了,而是跟他一样地慌乱。女儿不在,她赶忙过去将门帘子高高搭起,说话声音也放得很大,好像心里钻进了鬼,只有这样才能把暗鬼赶出去。女儿很不耐烦了,有一次干脆给公公说,你自个儿做饭吃,这点油香你就拿回去存在冰箱里自个儿慢慢吃吧,不要给我们再送了。我和我妈都长着一双手,我们会蒸馒头烙饼子,想吃油香的话自个儿炸就是了。你还是先顾好你自个儿吧。刚说完看见娃娃手里已经拿着了一个大油香,气得抬手就狠狠地夺下来,说别油了刚穿的新外衣。娃娃望着空手哇哇大哭。女儿气哄哄抱了孩子出去了,剩下她和他。她想给他道歉,说女儿脾气不好。谁知他抢在前头,叫她不要多心,娃娃嘛年龄还小,不醒事,再过几年肯定就醒事了。说完他就走了,没有跟她告辞。之后他很少来了,来了也不进屋,连学校门都不进,就站在门口托付某个玩耍的学生娃把口袋送进来。她一看还是饼子或者油香,心里过意不去,提着口袋赶到门口,他已经走了。推着自行车快快地走,好像后面有一股看不见的大风在一个劲儿吹,让他脚步踉跄,难以慢下来。
一学期结束,她离开的时候去了他家里,作为儿女亲家总是要打个招呼的,没想到他不在家,一把铁将军把住了门。她和女儿开门走进去,一股清冷扑面而来。院子里居然有了野草,齐刷刷一层,冰草丛里夹杂着别的草。尤其一种叫灰荞的野菜,浑身举着娃娃小手掌一样的嫩叶,一片片一堆堆,给院子营造了一片一片的绿,但是透过这绿,她看到了一股凄凉。那个女人活着的时候,即便常年病着,但是家里的气氛是暖和的,活跃的,感觉这个家的主心骨是存在的。现在倒了,一切都塌架了。他明显比过去懒散了,过去一直伺候老婆,还把家里家外的活儿都没有撂下。老婆一走,他好像不爱过日子了。房台子上都长出杂草来了。当院子一棵刺玫树花期已过,只剩下满枝的叶子绿成一片。树下堆积着惨败后的花瓣,早就不是开放时候的美丽,显得脏兮兮苦巴巴的。很久没有清扫的样子。女儿抱着扫帚扫,嘴里忽然来了气,说找把铁锨剁掉去,把这种树长了个啥,又不结果子!她拦住了,毕竟是老人手里栽下的树,你一个小辈儿哪有权力随便剁呢?女儿颓丧地丢了扫帚,瞅着树忽然笑了,说,妈你不知道,花开的时候老两口就骚情得不得了,老爷子摘一串花儿,给老婆子往头上戴,把老婆子打扮得像个老妖精,两个人嘀嘀咕咕地说笑,好像年轻人一样。女儿说着笑得弯下腰去。屋子里一股灰尘味儿,案板上落着一层土。只有锅台上一个电饭锅和一个切菜板还算是干净的,有煮过饭的痕迹。女儿闻一鼻子,眉头拧起疙瘩说,又是方便面!她望望屋里,再看看屋外,心里说没有个女人,这日子终究是没法过啊。她忽然盼着女儿也能发出这样的感叹。但是女儿风风火火忙碌着,压根就没往这方面想的意思。第二天她离开了。临走都没有见他回来。
铃声叫累了,歇一会儿,第三次响了起来。咋办呢?接还是不接?她又爬起来,竖耳朵听着铃声。有那么一会儿,她的耳朵好像失聪了,耳畔一片茫茫的空白,铃声完全听不到了。眼前显出一片河面,河水静静流淌,水面上泛着无数波光。她痴呆地看着。耳边潮声退去,铃声又坚强地响起来。不接是不行了。这个男人啊,还真是倔强得很,叫人咋说呢?她懊丧地摇摇头,同时心头闪过一丝儿喜悦。说实话,她还是欢迎他这种不屈不挠纠缠的样子。这算什么呢?她真的连自己的心思都摸不透了,一方面嘴里冷静地说着拒绝他的话,另一方面,却不拒绝倾听他的诉说,然后还心里希望这样的诉说能继续下去。她不知道要是他的电话忽然有一夜中断不来了,她该咋办。她终于把手机按到了耳朵边。他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一张过早沧桑的脸在眼前清晰起来。他先说了自己今天一天的大致行踪,接着说吃了两顿饭,一顿干馍馍就白开水,另一顿泡的方便面。她静静地听着,她不喜欢打断。他说他去看了孙女儿,会跑了,满校园跑呢。又说再有三个月就是那个人的一年祭日,到时候他想宰牛念索儿。这么大的事情,锅灶上谁做呢?他说他想好了,就请她来帮忙,问她成吗。大小的事儿都交给她主持,没有人敢说啥的,他的儿子女儿他清楚,对他这个老子还是很尊抬的。她无声地咧了咧嘴,没有让笑声从嘴角溢出来。她心里有点苦苦的感觉。就要一年了,时间过得真快。那个女人的面影在眼前闪了一下,可惜眉眼是模糊的,没等她看详细点,就已经闪过去了。她想追上去喊一声,喊住了问她这几个月过得咋样,心里是不是记挂着这个家里的大小事情。唉,人活在世上,真是有很多难以割舍的东西。她的丈夫临到咽气了还瞪着眼睛望着两个女儿,嗓子眼里喑哑地喘着。女儿们被那凄厉的目光牵引,凑过去说,大,你的心思我们知道,就是我妈的养老问题,你放心,我妈不会受一点儿罪的。丈夫才在阿訇念诵清真言的动人心魄的声音里闭上了眼。
丈夫是个实诚人,一辈子待她不赖。手机里的人还在坚持说话,内容不知何时转移了,说院子里的刺玫树就要开花了,花苞儿挂了满身,再有四五天保准能开出满树的花。他的声音变得轻轻的,柔和,低沉,好像嗓子被拉宽了,下沉了,声音里有了一种浑然的铁质的东西,却不再粗粝生硬,而是透出一丝温热来,贴着心缓缓传递。我走了你咋办?你还年轻,才五十八岁,要不就往前走一步,找一个合适的嫁过去一搭过日子……丈夫在病中给她说过。她当时不说话,瞅着他笑。丈夫着急了,又提过好几次,很认真,不是在耍笑。她不着急,只是笑。最后捏着他的手,悄悄说,老东西,你放心,我这辈子就跟你一个男人。你看这满脸满手的老褶子,你叫我跟谁去,谁看得上我呢,也就是你不嫌弃罢了。现在,一个男人的声音通过电话在耳边流淌。他忽然问:你见过刺玫花开的样子吗?她一愣,想说我见过,娃娃的时节娘家后院里就有一株刺玫树,每年花开了我都坐在树下看花儿,闻着浓郁的花香看着花瓣们凋残的凋残,怒放的怒放,一茬儿一茬儿。可是她忽然改变了主意,迟疑了。因为她忽然发现自己这一刻想不起来刺玫花开的景象了。没见过吗?没见过不要紧,到时候你来就看到了,真个好看得很,我给你揪一朵戴在……声音戛然而止,像一只持续燃烧的灯忽然熄灭了。
戴在哪里呢?女人回味着最后这半句话。自然是戴在头上了。女儿不是说过嘛,公公摘了花儿给婆婆戴一头。他也要给我戴花,什么意思?像待他的女人一样地待我?想到这里她忽然心里一荡,觉得一颗心软软地瘫在地上。她很想对他说一句话,我答应你,明儿你就拾掇拾掇来领我吧,我跟你走,我们过一辈子。但是这样的话她只是心里说,嘴里不说。在心里想想可以,谁也不知道,万一说出来,那就是覆水难收了,没有退路了。他打破了她的沉默,说,你来啊,你看我这个院子多大,我一个人凄惶,你来了家就有个家的样子了。这就说得很明确了,在央求她嫁给他。她不出声,悠悠地回味着他的话。时间长了,手机烫乎乎的。她想挂掉,不忍心害他浪费话费。试了试,手指头变得发软,好像有点不舍。你这是干什么?行不行给人家一句痛快话,这么黏黏糊糊的,啥意思呢?她在心里骂自己。你啥时节变成这么黏糊的人了呢?行还是不行,痛痛快快一句话,这么不冷不热地拖着,害得人家常打电话,这个样子下去算咋回事呢?她一再骂自己。但好像有一股力量在心里撕扯着,让她犹豫,留恋,舍不得就这样断了线索,再也听不到那个日渐熟悉的声音。
丈夫口唤之后,村庄集体搬迁,她跟随大家搬离了原来的山沟,来到这川区过日子。别人都是嚷嚷着说只有两个房子太窄小了,三辈人没法儿睡觉。在她这里不是问题。对于她来说,其实是太宽敞了。这面炕的后面叠放着一些被褥。可以三五个月不去动,直到某个女子或者女婿来了留下过夜,才有机会拉开来使用一下,平时根本用不上。她的被子和枕头放在靠窗户的地方,白天叠起,晚上拉开,一天一天重复着。有一回她忽然心血来潮,将那一摞被子全拉开,铺一个褥子,上面捂一床被子。然后她看着那个被窝发呆。就像丈夫没有口唤,还活着,去寺里礼拜,然后坐在阿訇的房子里扯磨去了,所以迟迟没有回来,而她在等他回来。那一夜她醒了很久,越醒越觉得心里空,心本来是一层布包起来的,包得严严实实,随着丈夫离去的日子,一天天变得冷硬起来。但是这时候忽然发现这一层布竟然有了裂口,她伸手一摸,立即绽出了一缕缕细碎的裂口。这让她吃惊不已,不知所措,第一次发现自己心里有了一个空洞。随着丈夫离开的日子的积累,这洞一天天扩大,终于塌陷出一片深坑,黑乌乌横在她面前。她忽然抱住丈夫的枕头哭了,觉得有无限的委屈。丈夫口唤后她都没有这样伤心过。她哭着钻进丈夫的被窝,盖着丈夫的被子,铺着丈夫的褥子,鼻息里飘满了丈夫的汗腥味。她从来没有这么清醒地意识到那个人已经不在了,这一次离去再也不会回来,她就是一直等到天亮他也不回来了。她痛彻心扉地哭着。正是这时候电话响了,那是他头一回给她打电话。
他问,你到底咋想的?愿不愿意来帮忙?他还在絮絮叨叨说着什么,火车过来了,轰隆隆的声音刺穿了寂静长夜,从西边而来,碾压过这一片移民点,将晚睡的灯火和早睡的睡梦一起碾轧出模糊的呻吟。这是一趟货车。她竖着耳朵聆听,她喜欢听火车的声音。在老家的时候她没有见过火车。所以来到这里,觉得很新奇。第一时间和几个姐妹一起跑到火车道边看了看。火车道在几米之外就用铁丝网围起来了。她们不甘心,顺着轨道跑到不远处镇上的一个小站点看了看。看了也就不那么震撼了。现在她们面对火车的时候表情都很淡然,至多听到轰鸣的时候先在心里判断一下是拉人的车厢还是拉货物的车皮,然后抬头看一眼,以落实自己的判断是不是正确。她只有在夜晚的时候,会特别关注火车。不是有意关注,而是不由自主地就被火车吸引了。她没有坐过火车,不知道坐在火车上是什么感觉,火车里又是个怎样的世界。尤其客车来的时候,她总是有一点儿激动,竖起耳朵捕捉着那惊天动地的声响。车上坐了多少人,都是什么人呢,要去哪里,是一个人独自出门,还是有人陪伴?她忽然有一种冲动,想自己也拾掇一下跑出门去,到镇上的小站上火车,坐着出一趟远门。去哪里呢?先不要去想,等上了火车再说吧。重要的不是去哪里,而是有没有勇气作出这一决定。火车过来了,她忽然很焦虑,好像这条线上只有这一趟火车,不及早作决定就这样错过的话,就再也没机会了。是啊,再也没机会了。她竖起耳朵醉心地倾听着那声响。车轮摩擦着铁轨的声音,车身摩擦着空气的声音,沉寂稀薄的空气被搅和成一团,变成了热气,化成了火焰在炽热地燃烧着,呼啸着,裹挟着尘土和热浪,轰隆隆而过,向身后丢下一团热闹过后的寂寞。她像送一个亲人一样送火车远去,然后看着黑暗重新归于寂静。你不说话,不说话就是答应了吗?好啊,你答应了!你放心,饿不着你,冻不着你,不会叫你受罪的。他还在热切地表达着,说刺玫花儿真的就要开了,今年花苞儿特别多,把枝头都压弯了。她忽然眼前显出一树紫花葳蕤的景象,一句话冲口而出,开了就给头上戴几朵吧。说完她就后悔了。果然对方从这话里抓到了把柄,赶着说好啊好啊,我给你戴一头的花儿。他这句话也是冲口而出的,接着两个人同时沉默了,好像他们一不小心触及了一个共同回避的敏感区域。她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个问题,就追加一句,我的意思是花儿戴在你头上。说完她就后悔了,挨着手机的半边脸火辣辣地烧起来。强调什么呢,这一强调不是有了欲盖弥彰的意思吗。果然他揪住她话里的破绽不放,轻浅地笑了一下说,哪能给我戴呢,应该给你戴,你是女人嘛,女人戴花才好看呢。说完他笑了一下。她却忽然就恼了,觉得他这笑意有点轻浮,有点过了。她的心里莫名地有了一些气,一声不吭挂了电话。通话中断后,她却禁不住想象他在电话那端的样子,一个人躺在那个空大的院子中的上房炕上,身边空无一人,连猫儿狗儿也没有养一只。她忽然很想答应,干干脆脆给他一个准话,真的嫁过去,和他在一起搭伴过日子,两个人至少要比一个人热闹一点。
她最终还是没有吐给他一个痛快话儿,就那么一直慢腾腾地迟疑着。他的电话像夜晚穿行而过的火车,每一夜都会来,会听到他一个人在唠唠叨叨说话,在邀请她。她最终也没有一个人跑出去搭乘上火车去远方。她想的更多的是后果,冲动之后的结果。女儿的意思很明确,不希望老公公再娶,说,多老了,死灰里头还想冒烟吗?要是真找个人进门,我们两口子就不管他了,以后的养老问题他自个儿看着办。到时候连他都成问题,更不要妄想叫我们伺候他找的新人。当时女儿的话她没在意,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有震慑力,好像就是专门说给自己听的。其实她最明白,那不是说给自己的。女儿有口无心,就是个直筒子脾气。但是这让她有了顾虑。那个家里不仅仅女儿一个儿媳妇,他还有大儿子呢,还有几个女儿。虽然大家都各过各的日子,但是情况要比眼睛看到的表面复杂。他们都是一样的境况。一个人守着一个空空的家过日子,吃穿不怎么愁。平时看不到儿女们的影子,但是真的要作出一个大决定的时候,就感觉儿女其实一刻也没有离开,那些目光一直在盯着看呢。要是年轻的时候,她可能不会在意这些目光,但是已经老了啊,老了顾虑就多了,每走一步路都要把前后左右想清楚了,不光顾忌自己的脸面名声,还有后人的感受呢,更重要的也还是后人。距离那个祭日越来越近了,他的口气焦躁起来,有一次变得生硬起来,说,你到底考虑好了没有,叫我等到哪一天去呢?她想和他说说儿女对此事的看法,但是他咣当一声挂了电话,他彻底生气了。她想给他回拨过去,想了想,听着火车过去了一趟,一会儿又一趟,一夜工夫过去,不知道过去了几趟。她困了,歪在枕头上没有心情打电话了。忽然心里多心了,想终究不是自己的丈夫,不是知疼知热的人,这电话说挂就挂了,一点也不考虑这一头的人心里会不会难过。第二夜他的电话按时来了,她没有接。在那悠悠的铃声中渐渐地入了睡。第三夜电话再没有来,这一夜一共过去了六趟火车,一趟客车,其余都是货车。她朦朦胧胧地想到有一些人通过火车从一个地方去了另一个地方,有很多货物从这里搬运到了那里。火车就这样日夜不停地奔跑着,累不累,累不累呢?世界还是那个样子,日子还是原来的过法。她把几只羊赶在远处的一片滩地上吃草,然后到玉米丛里看了看,玉米叶子上起虫了,邻居说需要打药,她就去镇上买了药,回来自己背着喷雾器打药。
那个女人的祭日如期而来,如期过去。女儿说宰了牛,八千元的一头牛。她望着自己的几只开春出生的羊羔禁不住想,那头牛有多大呢,毛色是棕红的还是褐色的?牛肉她吃到了,女儿托人带了过来。女儿说,还剩余了一些牛肉,冻在冰箱里,公公说不要给亲戚邻居散了,他留着有重要用处。她听着。女儿从鼻子里嗤了一声,声音压低了,能有啥用处呢,老家伙的心思谁不清楚,正在到处寻着问寡妇呢,看来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我们当儿女的劝不住了!女儿风风火火发完牢骚就挂了电话。女儿怎么会知道母亲的心思呢?年轻人心粗,就知道忙他们自己的事情。夜里她有点感冒,头昏沉沉地疼,爬起来摸下炕找药吃,药匣子空着,没药了。她倒了点开水喝了,然后望着黑暗想心事。忽然就心事重重了,觉得从来没有这么沉重的心事,心事像荒草一样在心里密密麻麻长出一层。火车一趟一趟碾轧着村庄,就像碾轧在她的心上,她静静躺着,心里说,火车就从这身上碾过去吧,把我碾碎了也好。
第三天吧,邻居去镇上榨油,她也跟着去了。在磨坊里排着队等待的过程中,有一个老奶奶和一个老汉,两个人本来不认识,往大铁锅里倒胡麻的时候,老汉给老奶奶帮了一把,两个人攀谈上了。嘻嘻哈哈的,你一言我一语,竟然说得很投机。来榨油的人真是多,足足等了三个小时。三个小时后,老奶奶和老汉竟然打得火热,两个人彼此问了身世,问了家庭,巧的是两个人都单身,另一半不在了。老汉说要不我们一搭过。老奶奶笑得头上的一块浅紫色围巾直抖,说,要我跟你,你得给我买金货,戒指耳环项链一样不能少。老汉露出豁了三颗牙齿的褐色牙床,笑得哗哗响,说,行,一样不少。老奶奶说,那你到时候给我买个鲜亮点的外衫,成亲的时候我穿上。老汉笑得整个牙花床子都露出来了,头点得磕头虫一样,说,行行行,给你买,保证给你买,叫你打扮个老来俏。老奶奶有点顾虑,说,那不会惹人耻笑吧,骂我老了老了还骚情得很。老汉脖子一梗说,谁敢笑?谁敢说这话?看我咋收拾他!我儿子女儿的主意我来拿,你啥都不用怕,你的后人那里也不用顾虑,养老的问题也不要去愁。你是女人,哪有叫女人为这些发愁的呢?说话间清油磨出来了,老奶奶拎着塑料壶要盛油,老汉把她搡开了,老汉替了她。两个人之间已经有了一种互相疼爱的默契。油磨完了,他们肩膀并着肩膀,很亲密地出去要走了。
她一直在旁边冷眼看着。她目睹了他们由陌生到熟悉到决定走到一块儿的过程。她觉得不可思议,这也太快了吧,再说都那么大年纪了,还能这样吗?不是在耍笑吧?她十分好奇,追出去问他们,你们多大岁数了?真的准备往一搭儿走吗?老奶奶指着老汉,老脸笑成了一朵花儿,带着撒娇的口气说我六十七,他六十九,他愿意,我也愿意,两厢情愿,自然是能走到一搭儿的。她在心里惊叹了一声,都不年轻了,早就不是谈婚论嫁的年纪了。但是他们在有说有笑中离开了,走出老远了,还能听到他们在商议新婚买新衣买家具的事情。她却还有恍如做梦的疑惑,这难道是在耍笑吗?不像耍笑啊。往回走的路上,坐在邻居的农用蹦蹦车里,听着突突突的声响,她一阵一阵恍惚,那一对老人的脸不断在眼前闪烁。他们都比她大,那老汉和女儿的公公差不多。他们那么快就说到了婚嫁,还那么坦然,那么自己呢?和那个老奶奶比,自己算得上年轻人呢。脸有点烧,心有点跳。她忽然感觉自己真的不是那么老,精力还很旺盛呢。她闻到了油渣儿在袋子里发出的干燥的馨香,忽然感觉很好闻很好闻。她摸出电话,一个一个翻着看号码。她记住的号码不多,但是那一串数字是熟记在心的。她看着这串号码,透过它们看到了一张被生活折磨得布满深壑的脸。蹦蹦车颠簸着,她心里一时高一时低,高低起伏着,颠簸得她手指发软,那一串数字就没有拨出去。
这天夜里她是在一股浓烈的胡麻油的清香中爬上炕的,清油晾在一个大瓦盆里,等明天再装进桶里储存。油渣儿晾在一个尼龙袋子上,准备冬天了喂那几只怀羔的母羊。手机在桌子上充电。手机是女儿买的,图便宜买的返还话费的那种,所以带电功能很差,夜夜要充电。黑夜朦胧,窗外远处的公路上浮动着车辆的灯光。没有火车碾轧和飞驰的铁道,像一个闲暇的寡妇,沉默,无言,默默地潜伏在黑暗中。她向着手机的方向望了一次,又一次,忽然很盼望它能响起来。它终于响起来了,她怕它忽然就改变主意中断声响,爬起来扑下炕将它抓在手里。那一刻她的身影很轻盈,远不像一个近六十岁的下过几十年苦的农村女人。她摁下绿键,响亮地喂了一声。当一个声音透过耳膜传进来,她心里一呆,打电话的是女儿。女儿的声音穿越了新鲜的黑暗和漫长的路途说,我的那个为老不尊的老公公啊,他今儿把事情办了,东山里的一个寡妇,用蹦蹦车接进门的。他事先跟我们谁都没商量,不声不响就把人接来了,我这心里气不顺啊,看着就闹心……
她伸手按下了右边那个小键,不用开灯看,她知道那是红色的挂断键。女儿的声音被迫中断在黑夜深处。夜色忽然变得很浓,浓密得凝结了,一块儿一块儿的,乌云一样在眼前翻涌。她闭上眼,慢慢地让心静下来。很费劲地在眼前想象一个人,是那个人,他干瘦的脸上带着浅笑,好像有点不好意思,有点儿腼腆,一副想给她说什么的样子,但分明在顾忌什么,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她心情复杂地看了他一眼,她惊讶了,他怎么戴了一头的花儿呢?浅紫色的刺玫花儿,一朵挨着一朵,挨挨挤挤地别了一头。他的脸颊本来就红,被这鲜艳的花儿映衬,那脸颊就红彤彤一片。这个男人,终究给自己戴了一头花儿。她在心里感叹了一声。她的感叹他没有听到,因为她看见他转过身独自走了,越走越远,始终没有回头看她一眼。她想喊他等一等她,想叫他把那些花儿摘下来一些,给她别在头上。尽管他们都老了,但是花儿戴在女人头上总是要比男人好看一些的吧。可是她的喊声被另一股巨大的声响淹没了。原来火车来了,轰隆隆的声音像一首悲伤的歌谣,裹挟着巨大的风声穿透了长夜,在她的耳畔惊心动魄地响彻。
(题字、题图:李兰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