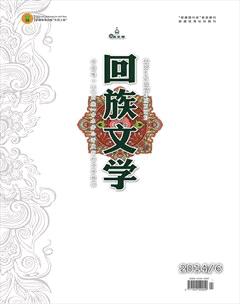故乡二章
马忠华
哇呜情结
一个周末的晚上,和妻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记不清了,大概是中央三套吧,正在播放乐器组合演奏。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身穿红色旗袍,披着长发,双手捧着一个形状如同盖碗的乐器,亭亭玉立地站在那儿,轻轻摆动着袅娜的身段,吹奏出一缕悠扬的曲子,与其他乐器发出的声音交织缠绕在一起。立刻,一种摄人心魄的感动震撼着我的全身。真奇怪,音乐听得多了,我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那不是哇呜吗?”我惊叫起来。
妻仔细一看,说:“就是哇呜。”
“嘿!没想到在电视上还能看到哇呜,并且美美地欣赏一回。”我感慨地说,“该有多少年没有听过、吹过哇呜了?大概二十多年了吧!”
“差不多了。”妻说。
于是,我们都不说话了,静静地听着这难得的哇呜演奏。我的目光,全部集中在那位姑娘和她手中的哇呜上。优美的身段,清丽的面孔,婉转幽深、绵绵不绝的哇呜声,一幅天然的美的画面。姑娘的美丽,使得哇呜更加动听;哇呜动听的乐声,使姑娘更加美丽。“人面桃花相映红”,大概就是这种意境吧!
啊!哇呜,久违的哇呜!你不经意的出现,就像窗外天空中那弯悄悄钻出云层的弯月,穿越二十年的时空,把我思念的衷肠,倾泻在那月光一样美丽的少年时代。
那时候,整天和村里一帮小孩光着脚丫疯疯癫癫地东奔西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的孩子,童年生活是丰富多彩而又无拘无束的,记忆深处最亲密的伙伴,总是那些小鸟、野草、水和泥土。连收音机也轻易见不到的我们,却能够凭着我们的聪明,从大自然中感受音乐的美妙。春天来了,折下一根柳树枝,拧动,树皮就完好地褪了下来,剪下两三寸长的一截,用嘴一吹,便发出悦耳的声音;摘一片树叶,夹在两块玻璃中间,吹奏出来的声音更好听。
但是,树皮树叶终归要枯的,这时,我们就想到了哇呜。颠着屁股跑到马场渠边,挖一捧黄泥,放在左手掌心,右手四指转动黄泥,大拇指在黄泥上面用劲往下按,便做出一个形状既像盖碗又像陀螺似的小玩意儿。尖的那头钻一个小孔,贴上芦苇秆中间的薄膜,阴干,对着那粗大的孔吹,一股浑厚的“呜呜”声便响彻天空,像牛角号一样激荡在田野间。我们就管这个好听的玩意儿叫“哇呜”。小伙伴们还比赛看谁做的哇呜既好看又好听,保存得时间长。被大家公认的好哇呜,还可以放在家里珍藏起来。
不久,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人忙了,孩子也忙了,很少有人再去玩那些“大自然的乐器”了。哇呜,也被丢弃在历史的风尘里。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各种现代化的家用电器相继出现,哇呜,更像一支孤独的飞天,被永远地遗忘在荒凉的古堡中。
1993年,我在宁夏高校民族预科部上学,校园里正流行贾平凹的《废都》。一天,在书里读到这样一段:“埙是泥捏的东西,发出的是土声地气。现代文明产生的种种新式乐器,可以演奏华丽的东西,但绝没有埙那样蕴含着的一种魔怪。上帝用泥捏人的时候,也捏了这埙,人凿七孔有了灵魂,埙凿七孔便有了神韵……”当时心里一震:这不是我儿时玩过的哇呜吗?连忙翻看平凹先生的其他相关著作以求证实。这一翻不打紧,不但证实这埙就是哇呜,而且,竟然得知,“埙是中国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吹奏乐器之一”,还认识了一位专门研究埙乐,名叫刘宽忍的音乐家。
一种复杂的感情涌上心头,有惊讶,有感动,有自豪。没想到,小时候用手捏出来的哇呜,竟然是“中国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吹奏乐器之一”,“首次发掘是在西安的半坡遗址,该遗址记载了大约七千年前繁荣的母系氏族社会的人类文明”。七千年的历史啊,七千年的灿烂文化,一个古老民族七千年的自豪与骄傲,七千年的万丈荣光,竟然由一抔黄土做证!这抔黄土,在不经意间,陪我走过了一个年代!
于是,一种强大的驱动力驱使着我,让我重新拾回孩子的心态,再一次走进哇呜的世界,走进哇呜的心灵,去阅读哇呜,去感受哇呜,去理解哇呜。在喧闹繁华的大都市里,我愿做哇呜的知己,我愿以哇呜为知己。尤其,当我了解了在这七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哇呜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条煊赫与曲折交织,光荣与艰辛陪伴的道路,我不由得想哭。我不能不沉迷于大堆哇呜的典籍里。
原始先民在长期生产劳动实践中,逐步创造出了哇呜。先民们狩猎的时候,用石头掷向猎物。由于石头上有自然形成的空腔或洞,石头划过空中,空气流穿过石上的空腔,形成了哨音。听到这哨音,灵感的火花闪过先民脑际,早期的哇呜产生了。
初期的哇呜没有音孔只有吹孔,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演奏的需求,哇呜的音孔渐渐增多了。从无音孔到有音孔,从一孔到二孔、三孔、五孔,古代已经有六孔哇呜,清代宫廷云龙哇呜即是六孔哇呜。现代则普遍流行八孔哇呜和九孔哇呜。而且,在外观上,哇呜形体的外观式样也丰富多样:唐三彩陶埙、红陶刻花埙、怪兽埙、人面埙、绘龙埙,等等。
华夏民族对土地的感情之深挚,到了顶礼膜拜的境界。这种感情,一旦体现为一种文化,便历久不衰。而这种文化的载体,也被赋予了崇高而尊贵的地位。哇呜,便理所当然地充当了这种载体。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哇呜直接由泥土制成。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典籍《尔雅》,就对哇呜作了记载。唐代郑希稷在他的《埙赋》中说:“至哉!埙之自然,以雅不潜,居中不偏,故质厚之德,圣人贵焉。”这就是说,哇呜所发出的自然而和谐之乐音,能代表典雅高贵的情绪和雍容的气度。所以仁人贤士们是十分看重这种乐器的。哇呜,自然就成了修身养性的亲密伙伴。一支悠扬婉转的哇呜乐曲走出,气质便雍容高雅,不同凡俗。
哇呜以及哇呜的演奏,体现着中国传统的儒家礼教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我国古代各思想流派中,真正重视音乐的只有儒家,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乐记》上说:“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认为古时贤明的君主就重视乐教,通过乐教来引导、节制人们的欲望,改善道德和风俗。
可是,当我们自豪于中国是个礼仪之邦,骄傲我们有着五千年光辉灿烂文化时,有几个人会想到古拙而毫不起眼的哇呜呢?
是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到了现代社会,种类繁多、品牌高档的乐器不断出现,在乐器家庭里面,哇呜多少显得有点丑陋,不奢华。在乐器店里,琳琅满目的乐器令人眼花缭乱,几万块钱的钢琴任你挑选。可是,却很少能见到哇呜。我走进平罗县城几家比较大的音像店里,想去买一张张维良的《问天》。当我问有没有埙乐方面的光盘时,那个温文尔雅的男店主尴尬地笑笑说没有;走进另一家店,那个女店主好半天都没听懂我说的“埙”是什么。我说:“也就是宁夏人说的哇呜。”女店员一听,大手一挥,不耐烦地说了声没有。我连忙尴尬地退出来,再也不好意思到其他店里去问了。我知道,问也白问。
其实,也难怪,或许在更多人耳中,哇呜的声音谈不上最好听,尤其它那一出口便是飘满天空的悠悠扬扬的、哀婉凄恻的乐音,使人听后心情总是愉快不起来。这些,都使得哇呜渐渐被人所忽视,所冷落,所遗忘,以至于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公演中几绝于耳。古老的哇呜,面临失传的危险。原本就孤独的哇呜更加孤独了。然而,哇呜不在乎,哇呜也不怕孤独。享受孤独,正合了哇呜的秉性。哇呜是用泥土捏制而成的,泥土是深沉的,沉默的,因此,泥捏的哇呜也自然是深沉的,孤独的。哇呜的孤独使哇呜始终不改它自身的高贵。
所以,哇呜毕竟会有知音的。在这个被功名利禄主宰的现代社会,也只有哇呜的知音,才能够与哇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也只有哇呜的知音,才能够与哇呜达到那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最高境界。哇呜的知音,愿意为哇呜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在茫茫人海中,那个“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人,毕竟是哇呜的知音。
“1983年,赵良山首次用埙在湖北省歌舞团《编钟乐舞》中演奏《哀郢》,乐曲虽仅仅一分钟,但那其他乐器无法替代的特殊表现力,给人耳目一新的艺术享受,轰动国内乐坛。”
“1984年,演奏大师杜次文在美国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演奏埙曲《楚歌》,这是埙乐首次登上世界舞台。动人的旋律在广场上空回响,人们吃惊于一个以土为之的乐器,竟有如此丰富动人的表现力。”
“1993年,中国第一位民族管乐硕士刘宽忍与当代作家贾平凹出版了《废都》的埙乐专辑。这次音乐家与作家的联袂,让更多的人首次通过文学作品认识了埙,了解了埙,影响颇为深远。”
“在1993年,笛箫制作大师张荣华在埙的研究与制作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功。他在前人九孔陶埙的基础上采用全新的技术,改进工艺,优选材料,进行科学配方,制出的埙在音域、音色、音量及音准等方面,均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新型工艺埙吹奏省力,外观精美,有皇家之大气,无论从视觉还是听觉上都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其音质纯正,音色优美,音域宽,音量大,可奏出完整而准确的十二平均律,且灵敏度高,在乐队中演奏可达到和谐、统一的效果。”
“1997年,张维良出了第一张埙乐的CD专辑《问天》,首次运用张荣华的低音大埙表现音乐,由此,埙的音乐文化进入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时代。”
……
我感动于一个个天才而痴情的音乐家的执着,感动于他们对哇呜的理解,感动于他们对哇呜的奉献。孤独的哇呜并不孤独,因为有了他们。
然而,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黄泥烧制的哇呜,竟然会成为我的故乡、我的回回民族的一份无上荣光!
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回族民间乐器泥哇呜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二年,出生于平罗县渠口乡的杨达伍德开发研制的泥哇呜在中国首届埙乐器展进行展示。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两个月,回族民间音乐家、器乐家杨达伍德被命名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传承人。当得知这件事,我的心,久久地沉浸在激动和自豪中。我为我的故乡平罗而骄傲,为我们回族人民而骄傲。
从此,缺乏音乐细胞、开口唱歌众人皆喝倒彩的我,就对这泥捏的哇呜,更加情有独钟,对它的痴迷,超过了任何其他乐器。一遍又一遍地欣赏这古老的埙乐,我感觉,自己和它是那样地心意相通。听着哇呜呜咽、低沉、幽涩的声音,我仿佛在聆听它如泣如诉的灵魂的诉说。
听《哀郢》,我仿佛听到了屈原在报国无门的无奈与失落下,满腔悲愤仰天呐喊。这呐喊,从楚国绵绵山脉里传出来,像一头满目凄然的老牛,呜呜地鸣叫着,响彻云霄。一时,天地回应,风雨和鸣,就连屈原脚下的汨罗江,也泛起涟涟泪花,轻声呜咽。
听张维良《驼道》,骆驼的声声仰天长啸,就像火车汽笛的鸣叫。一阵阵驼蹄踏漠的“咚咚”声,就像紧促的雨点落在鼓面上。一缕缕低婉哀怨的箫声,扯动着我的心弦。我似乎看到了平沙万里的大漠上,一个个驼队悲壮地行进在西风残照里。凄凉的内心,迷离的双眼,稳健的步伐,以及铺展在万里黄沙上的长长驼影,无不演绎着古道驼铃五百年桑田沧海忠贞不渝的坚定,演绎着它们对沙海尽头那一片绿色世界真挚而深厚的信仰。
……
我笨拙的笔,难以尽情描述我聆听哇呜时的那种感动。其实,我知道,哇呜也知道,根本用不着过多的描述,一切尽在不言中。
2014年9月份刚开学,我的女儿所在平罗县城关回民小学作出决定,为了让回族民间器乐哇呜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决定在全校开设哇呜课程。不久,一只制作精美、褐红色的泥哇呜便出现在女儿那稚嫩的小嘴上。那一刻,我几乎要落泪了。
蒲苇之乡
这是一座很小很小的村庄,整个村庄最多时候才三十几个人,而如今常住人口仅仅十一人。
这是一座偏远得有点原始古朴的小村庄,远离人烟聚集的其他大村落。这儿被家乡的父老乡亲戏称为“小台湾”,因为每当下雨,尤其是稻田灌水后,那连接外面的唯一一条土路,就被泡在水中,人几乎过不去。
然而,这里却是一个美丽的村庄。想当年,马鸿逵一眼就看上了这里,因此把这里作为马家军的军马场,专门用来牧养军马。因此,建国后这片土地就被称为“马场村”,成为全乡乃至全县都赫赫有名的粮食基地。
这里,就是我的老家——通伏乡马场村小农场。
小村受天地造化的恩宠,西边有巍巍贺兰山作天然屏障,挡住了浩瀚沙漠与奇冷寒流的东侵;东边有滔滔黄河水悠悠流过。河对面,那长长的毛乌素沙漠又为小村远远地飘起了一道淡黄色的、几乎透明的披风。在这青山长河之间,在小村庄的周围,便一马平川地形成了响彻中国的塞上江南宁夏平原。一条弧形的天然湖,是黄河改道留下的古河道,从西南方的贺兰县通义乡境内发源而来,从小村面前绕过去,向东北方向逶迤而去,最后注入了黄河。这条狭长的小湖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水草,把个湖面遮盖得严严实实,外人到此,竟然会看不出这是一条湖呢。
湖中的水草,尤以芦苇、芦草和蒲草最多,这些野生的草,曾给家乡人带来了多少收获的喜悦。每当秋末冬初,蒲草和芦苇枯萎后,父老乡亲便带着镰刀去刮蒲草,除了自家用的一部分外,其余的都远销到平罗县内外,被人们编制成了蒲草帘子,盖在温棚上面,暖暖和和地保护着千亩万亩的蔬菜温棚,为生活在大西北的人们在寒冬腊月能吃上新鲜的蔬菜做出了贡献。
最热闹的是砍芦苇。冬天,那高大纤细的芦苇,亭亭玉立地用那乳白色的茎干,竖起了一团团毛茸茸的芦穗,宛如神话传说中那些老寿星的花白胡子密密麻麻地在空中迎风飘扬,又似一片淡黄色的烟雾在弥漫。弥漫出了两千年前那首让人牵肠挂肚的诗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弥漫成了一道以芦苇为歌咏对象的蔚为大观的中国古诗词的文化长河。苇多而密,便形成了密不透风的芦苇林,我们放羊的小伙伴稍不留心,羊儿钻进芦苇林里,还一时真的难以找到呢。待到湖里面的冰冻结实了,乡亲们便赶着驴马车来到冰面上,然后从芦苇丛林的边沿开始,把方口锨的锨头平放在冰面上,用力地向芦苇林中铲了过去。只听一阵阵“咔嚓——咔嚓——”的响声,此起彼伏,交汇成一曲美妙的音乐。锨头过处,芦苇纷纷倒下,在冰面上铺开。然后,后边就有人把这些砍倒的芦苇抱成捆,用草绳捆起来,放到驴马车上拉回去。把苇穗砍去,编成苇帘子,是用来盖房子搭屋顶的绝好材料——在那个物质条件比较落后的年代,就是这些芦苇,给了父老乡亲们温暖。也有的人家不盖房子,就把芦苇卖出去,成为造纸和人造丝、人造棉等的优质原料。
大概,是芦苇林里面的温度比外面高的原因吧,苇林中的冰面比较薄,铲芦苇的人一不小心,一脚踩破冰面,半个身子就掉进水中,冻得牙齿“咯吱咯吱”地打战。如果踩破了先前别人铲过的冰面,那可就不得了了,坚硬而锐利的芦苇茬从腿肚上划过去,立刻鲜血直流,而匕首一样的芦苇茬若刺进肉中,这个人就得赶快上医院。因此,铲芦苇的工作,一般由经验丰富的人来操作,其他人只是抱、捆、拉,还要穿上厚厚的棉裤,以防掉进冰层里不至于被芦苇茬子刺伤。
记忆中的故乡,煤炭奇缺,然而,无论是寒风刺骨还是飞雪飘舞,家乡的人们从未在冬天的夜晚挨过冻。因为,那取之不尽的芦苇和蒲草,用来烧炕,烟少火苗壮,所产生的热力是那样地硬,一直到第二天太阳升起很高,炕头上还是热乎乎的。春天,这些黑色的芦苇灰和蒲草灰,又成了上等的农家肥。
春天,冰面刚刚融化,草儿也露出了又尖又细的嫩芽。我站在老家屋角向后看去,呀,那湖面上啥时候出现了一派令人心醉的绿。油油的绿呀,映衬出了一片蓝莹莹的天空和绿油油的水,仿佛一大团一大团纯绿纯绿的云,从天上飘落下来,温柔地偎依在小村的旁边。我揉眼细看,才发现那是正在吐青的芦苇。从干枯的芦苇茬的茎节旁边,钻出了无数根嫩绿的新茎,苇叶子还没有展开,紧紧地包裹在苇秆上,这使得新的苇秆像一根根锋利的绿色标枪指向蓝天。不久,苇叶展开,苇秆往上长了一大截,于是湖面上就是一大片一大片身穿绿衣的少女方队。我们几个小伙伴,扯下一小捆的芦苇叶子来喂家里的牛马羊,惹得这些畜生兴奋得一个劲地叫欢。
又过了不久,蒲草也从水底下抽出了细长细长的、薄薄的绿色带子一样的长叶子,无数根细长的绿带子在湖面上形成了一道道天然的水晶帘,在风中飘摇。就是这个绿色天然草帘,在远古的传说中,成为女娲与伏羲结合生子时的遮羞布。就这样,蒲草夹杂着芦苇、芦草以及其他各种水草,铺天盖地地长满了整个湖面,引来了难以计数的各种水鸟在湖中安家落户。一曲和谐的鸟的伴奏,鸣唱着大西北黄土地上这块难得的鸟的天堂。小时候的我,站在老家门前,张望那一湖的绿,倾听此起彼伏的鸟的歌唱,不禁悠然心醉。我多么想自己也能变成一只水鸟,穿越那密密麻麻的水草,轻翅一扇,飞到那蓝莹莹的天空下,依偎在云彩身边,让自己的身影勾勒出一幅“海鸥飞处彩云归”的美丽画卷。而我,跑到湖边,踮着脚尖从水面上抽出一根芦苇的草芯,做成咪咪子,吹奏出一声声细嫩悠长、略带颤抖的笛音来,与远远近近水鸟的歌声遥相呼应,感觉我就是一只真正快乐的小鸟了。看那亭亭玉立的芦苇,晃动着细长的腰身在为我伴舞,细细长长绿得油腻腻的叶子,不正是它们手中挥舞的绿色纱巾吗?而蒲草呢,扭动着纤细的水蛇腰,在扭秧歌。是的,在大自然中,恐怕没有哪一种植物的身材比它好了。
夏收季节到了,父老乡亲拿着镰刀,进入齐腰深的水中,刮下一捆捆蒲草,把它们晾晒在湖坡上。等到晒干了,搓拧成草绳,然后把这些草绳在水中浸泡一下,捆麦子、胡麻、玉米等。那种韧劲,一直到第二年都不会断折。
就在这时候,从蒲草茎秆中间,钻出一根根长长的、绿绿的秆芯;秆芯的上面,顶起一个个绿色的蒲草棒;蒲草棒上面,是一层嫩黄嫩黄的蒲黄。孩子们就拿上蛇皮袋,捋下这些蒲黄,经过药贩子之手,卖到制药厂,成为珍贵的药材。前几年,有一个年轻的母亲,领着儿子去捋蒲黄,没想到母子两人都被水中的杂草给缠住了双脚,最后都丧生在湖中。家乡的蒲苇湖啊,在向乡亲们无私奉献一切的同时,你怎么能忍心夺去他们宝贵的生命?
去年国庆节,正是收割水稻的农忙时刻,我回到阔别已久的老家去帮助收稻子。放眼望去,门前那条湖面上,水草已经呈现出半枯半黄的状态,但是芦苇仍然显露着旺盛的生机。浓浓密密的苇丛上方,白色的苇絮毛茸茸的,弥漫在被收割机喷吐出来的稻草灰里,凄离迷蒙,怪不得古诗说“蒹葭苍苍”呢。
我在收割过的稻田中走过去,走到湖边,看到蒲草叶子上半部分已经金黄得近乎透明,下半部却仍然带着一丝丝绿意,如一根根细长的玉带和金带。蒲草棒已经接近干枯,就像一只只小小的褐色的橄榄球,被翡翠绿的秆芯举起在半空中。芦苇呢,仍然不忘显摆它们那水草之王的高挑身材,让一团团淡黄色的芦苇穗子高高地飘扬在所有水草的上方,如神话传说中南极仙翁那冉冉飘摆的花胡子。金黄色的蒲草叶子呈细长的三角形,好像千万只蜻蜓停在那儿扇动着淡黄色的翅膀。
我折下一根蒲草秆芯,沉甸甸的,坚实而匀称,毛茸茸的蒲草棒在秆芯上面轻轻晃动,我感觉自己拿的是一把锤子。摆一摆,蒲草棒上那细碎的蒲草絮就漫天飞舞,像一阵阵的轻烟,随风飘到远方,去传宗接代安家落户。如果不小心,让这些蒲絮粘贴在你的身上,那你就别想轻易把它们弄下来。就是这笔直、坚实、匀称的蒲草秆芯,小时候,奶奶常常让我们折下来晒干,编织成草盘子,当锅盖用,也可以用来盖水缸。而在这种草盘子锅盖的蒸锅里蒸馒头,蒸出来的馒头就有一种淡淡的水草香味。那毛茸茸的蒲草棒呢,奶奶让我们捋下来填枕头,枕头软绵绵的,那种舒服劲儿,是其他的枕头絮绝对比不上的。
目光掠过湖面,我看到远处的滨河大道边的林带,在淡淡的斜阳下,朦朦胧胧,正是“平林漠漠烟如织”。
在湖中间是家乡人铺垫的土路,我走过这条土路,向滨河大道走去。看到湖边的稻田里,一片狼藉,刚刚发过的黄河大水,把这些稻子淹得东倒西歪,干枯干枯的。
宽阔的景观河里,已经被蒲草和芦草密密麻麻地遮盖起来,只露出河中间的一线水色。
我走过景观河,脚下是一条伸向黄河滩深处的土路,雪白的盐碱铺满了土路,就像一条白色的玉带穿梭在万顷金黄的稻海中。路旁的水沟里,河水已经退去,凄惨地堆满了一摊摊的死鱼。芦草和蒲草混合着其他野草,顺着水沟一直伸向远方,远远看去,就像是茂密的护堤林。苦苦菜几乎全部枯黄了,但是光秃秃的菜秆上仍然顶着一些金黄的小花,在高原空旷的黄河滩上,就像几颗孤零零的星星。小花中间,夹杂着雪白滚圆的几个絮球,像一个个蚕茧,又像是一只只白蝴蝶在苦菜枝头秋意闹。折下来一根菜茎,摇一摇,轻轻的飞絮就在空中飘舞起来,如“柳絮因风起”,一直飘到远方去传播新的生命。
极目远眺,一棵孤树把黄河滩衬托得更加辽阔空远。稻海深处,父老乡亲种植水稻所搭建的那几间临时休息的土房子,被粉刷成了白色,如远古的荒堡。我的身影,被即将落下的太阳拉得长长的,直把我拉成了一个长袖飘飘的飞天,“高原的古堡中,谁在反弹着琵琶,只等我,来去匆匆,今生的相会”,让我的心儿,悠然陶醉,与那灵秀的棵棵小草相会,与那明媚的湾湾秋水相依,相依相会在这远古的黄河滩上。
太阳贴近贺兰山沿,我该回去了。经过滨河大道,水中的落日已经变得金黄柔和,水面更加呈现出只有大西北的秋天才独有的那种亮白,鱼儿跳起,在一片金光中扩展开圈圈涟漪。蓝天白云,在景观河里倒映出一片“天光云影共徘徊”的诗意。
炊烟混合着稻草灰,还有清幽的稻香弥漫开来,树影婆娑,我的老家便如一座缥缈的海上仙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