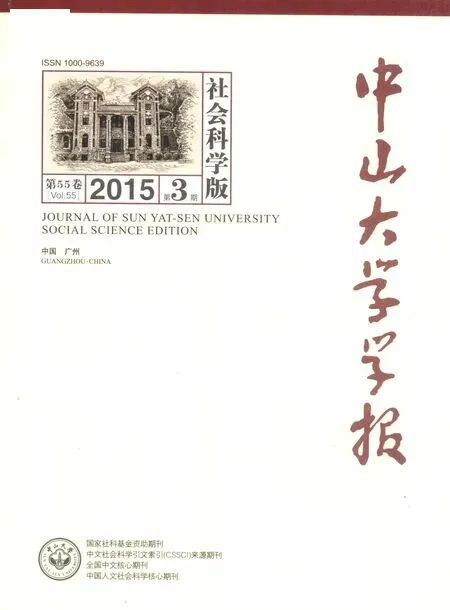“见在良知”说的核心焦点与体认维度*
张 卫 红
“见在良知”说的核心焦点与体认维度*
张 卫 红
“念念致其良知”何以可能?这不仅是聂双江、罗念庵质疑王龙溪见在良知说的起点,也是一个普遍的道德实践困境。双江、念庵立根于“未悟之因地”,而龙溪立根于“已悟之果地”,其“独知”“当下一念”“直心”“自照自察”等工夫具有非对象化体认维度。泯合对待、当下呈现、自证自知、自我圆成,这是龙溪与双江、念庵对象化思路的根本差异,也是双江、念庵无法契会龙溪思想精义之所在。通向这一境地的契机是以“信得及良知”来纯化意识,回返本真。“见在良知”所彰显的“不二”维度,将儒家心性工夫的超越性、主体性意涵发挥至极。
阳明学; 见在良知; 非对象化; 体认维度
一、见在良知之争的核心焦点
王阳明(守仁,1472—1528)高足王龙溪(畿,1498—1853)提倡的见在良知说,是最具原创性、也是中晚明思想史上争议最大的议题之一。这一争论肇始于聂双江(豹,1487—1563)、罗念庵(洪先,1504—1564)等人的质疑和批判,进而有钱绪山(德洪,1496—1574)、邹东廓(守益,1491—1562)、欧阳南野(德,1496—1554)、刘狮泉(邦采,生卒不详)等多位阳明骨干弟子加入论战,并延伸至晚明清初思想家对王学的批评。见在良知的基本内涵,如王龙溪所说:“见在良知,与圣人未尝不同,所不同者,能致与不能致耳。且如昭昭之天与广大之天,原无差别,但限于所见,故有小大之殊。”“若果信得及时,当下具足,无剩无欠,更无磨灭,人人可为尧舜。”①*以上引文分别见[明]王畿撰、吴震编校:《与狮泉刘子问答》,《王畿集》第4卷,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81页;《答吴悟斋》,《王畿集》第10卷,第251页。对此学界一般解释为良知既为存有论意义上的先天本有,又能够当下呈现于后天的经验生活中,若信得及良知,则吾人当下呈现的良知与圣人无别(区别只如昭昭之天与广大之天)②*参见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89—290页;彭国翔:《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71—72页;林月惠:《良知学的转折——聂双江罗念庵思想之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第278—279页。。盖就认同良知的先天存有义和后天活动义,双江、念庵与龙溪的理解并无二致,这也是致良知道德实践的基本前提。双方的分歧主要围绕着“当下具足”而来:一是圣愚之辨,即见在良知与圣人的良知全体同异与否的问题。双江、念庵认为吾人当下呈现的良知并不具足、圆满,只是“一端之发见而未能即复其本体”,坚持“圣愚有辨”*以上引文分别见[明]罗洪先:《(戊申)夏游记》,《念庵文集》第5卷,《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5册,第143页;《良知辨》,《念庵文集》第10卷,第200页。;龙溪则认为,当下呈现的良知与圣人的全体良知未尝不同。二是致知工夫之辨。双江、念庵认为,既然见在良知并非良知全体,且容易混同于欲根、知觉,故必须以主静、收敛之功回复先天本体;龙溪则认为当下“一念自反,即得本心”*[明]王畿撰、吴震编校:《致知议辨》,《王畿集》第6卷,第134页。。简言之,反对者的质疑概括为念庵所说:“认良知大浅,而言致良知大易。”*[明]罗洪先:《别宋阳山语》,《念庵文集》第8卷,第162页。
由于致良知工夫强调“体之于身”“体之于心”*以上引文分别见[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答徐成之·二》,《王阳明全集》第21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08页;《书石川卷 甲戌》,《王阳明全集》第8卷,第270页。的实践性,阳明学者们在各自切己的实践情境中各说各道,是造成论争未能达成一致的一个根本原因。近年的研究摆脱了以往偏重静态概念分析的解释模式,更多从阳明学的“体知”特色来解读这一问题。彭国翔通过对龙溪“先天正心”“心体立根”“一念工夫”等内涵的分析,指出见在良知说立根于先天心体,当下每一念都从良知心体发出,即心→念→心→念→心→念……这样一个不断的过程,整个意识之流便完全表现为“诚”的状态;而经验意识状态下每一个念头不免受前一念头影响,形成心→念→念→念……这样一种念念相续的情况,导致邪念、欲念形成整体意识,并遮蔽良知心体的境地*彭国翔:《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第144页。。林月惠则从实践动力的层面阐释了见在良知说最容易被人误解之处在于:龙溪以“昭昭之天即广大之天”比喻“见在良知与圣人未尝不同”,意在强调道德实践的根源性动力,即每个人心中所呈现的良知与圣人的良知一样,其“强度”都是当下具足、完全充分的;而龙溪之用意并未得到双江、念庵等人的理解,后者认为见在良知只是良知之“端绪”,并非本体,其实践动力显然不足*林月惠:《王龙溪“见在良知”释疑》,氏著:《诠释与工夫:宋明理学的超越蕲向与内在辩证》,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2年,第210—216页;另参林月惠:《阳明与阳明后学的“良知”概念——从耿宁〈论王阳明“良知”概念的演变及其双义性〉谈起》,《哲学分析》2014年第4期,第18页。。笔者从“信得及良知、于当下一念承当、时时保守此一念、一念所臻境界”几个工夫环节阐释了见在良知的具体实践内涵,指出双方各自的体证境界、问题意识、工夫入路以及由此形成的言说层面、思考方式是形成不同观点的根本原因*见张卫红:《罗念庵的生命历程与思想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305—325页。。这些讨论比明儒有更深入的推进,从不同层面阐释了见在良知的精义以及极高的工夫要求和内在严格,有助于厘清批评乃至冒用见在良知者的忽略和误解所在,同时也更能如实地理解双江、念庵等人强调涵养心体一路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尽管学界给出了见在良知之争丰富的解释,但仍有继续深究的空间:见在良知的精义在于以充足的实践动力将意念时时把持在良知心体上,也即龙溪所谓的“念念致其良知”*龙溪言:“必有事者,念念致其良知也。勿忘者,勿忘此一念之谓也。”(《念堂说》,《王畿集》第17卷,第502页)阳明也有“念念致良知”的说法。见陈荣捷:《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第222条,第300页。、“时时保守此一念”*[明]王畿撰、吴震编校:《桐川会约》,《王畿集》第2卷,第53页。按,“念念致其良知”是龙溪经常提揭的工夫教法,如云:“念念无杂,无昏无散”(《与吕沃洲》,《王畿集》第9卷,第218页),“念念不欺此良知”(《送惺台晏使君左迁序》,《王畿集》第14卷,第378页),“时时从真性流行,念念弗忘”(《册付应吉儿收受》,《王畿集》第15卷,第436页),“念念只是学圣人,觑体承当,彻首彻尾”(《书顾海阳卷》,《王畿集》第16卷,第476页)。,反对者们对此并非不能理解。念庵对龙溪说“此其为说,亦何尝不为精义”,问题是“但不知几微倏忽之际,便落见解”*以上引文均见[明]罗洪先:《答王龙溪·一》,《石莲洞罗先生文集》第8卷,明万历44年陈于廷序刊本,第11页。。做不到“念念致其良知”的确是经验生活中的常态,也是反对者们不能契会见在良知说的核心焦点。那么,“念念致其良知”何以可能?当下呈现的良知何以能够动力具足?这不仅是质疑见在良知的起点,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实践困境。此一问题,仍有待深耕。本文先从圣愚之辨的两个理解层面谈起,解析辩论双方不同的工夫起点,进而阐释见在良知所蕴含的工夫维度和思想维度及其与双江、念庵的根本差异何在,再解析龙溪何以格外重视“信得及良知”,其工夫内涵及效应为何,以期彰显见在良知说的内在特质和独特的体认维度,及其在儒家心性工夫中的意义和价值。
二、圣愚之辨的两个理解层面
“见在良知与圣人未尝不同”,这是证成见在良知说的起点,也是龙溪与反对者们争议的起点。双方对当下一念的良知与圣人全体良知的关系理解,是从各自体悟良知的实际境界出发的,但似乎都没有这一意识自觉。这一问题若从“未悟之因地”与“已悟之果地”两个工夫层面来看,又可以细分出三种解读方式,以此清晰地展现双方立论的出发点及理解歧义何在,这也是深入理解见在良知说的前提。
首先,对于未能体悟良知的一般人而言,从“未悟之因地”出发,当下一念的良知与圣人的全体良知不可完全等同。阳明即说:
圣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贤人如浮云天日,愚人如阴霾天日。虽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则一。虽昏黑夜里,亦影影见得黑白,就是日之余光未尽处。困学功夫,亦只从这点明处精察去耳。*分别见陈荣捷:《传习录详注集评》第289,221,222条,第341—342,299,300页。
相比于圣人良知的全体呈现(青天之日),一般人的良知受欲根、习心的遮蔽(阴霾天日),其“昏明不同”意味着二者良知的实现程度、实存境界是不同的。刘狮泉反驳龙溪见在良知说所用的比喻也是如此:
赤子之心,孩提之知,愚夫愚妇之知能,譬之顽矿,未经煅炼,不可名金,其视无声无臭、自然之明觉何啻千里……以见在良知为主,决无入圣之期矣。*[明]罗洪先:《甲寅夏游记》,《石莲洞罗先生文集》第12卷,第43页。
狮泉认为孩提与愚夫愚妇的良知如未经煅炼的顽矿,不可与圣人的良知(纯金)在质上等同。事实上,龙溪也承认愚夫愚妇与圣人的实存境界并不相同。他说:
自先师拈出良知教旨,学者皆知此事本来具足,无待外求。譬诸木中有火,矿中有金,无待于外烁也。然而火藏于木,非钻研则不出;金伏于矿,非锻炼则不精。良知之蔽于染习,犹夫金与火也。*[明]王畿撰、吴震编校:《南游会纪》,《王畿集》第7卷,第153页。
这里“金伏于矿”的比喻简直与刘狮泉的顽矿之喻如出一辙。以上三个比喻都表明一般人当下呈现的良知与圣人的良知虽具有本体的同一性,实存状态却是不同质、不同层的:前者是挟裹在二元对待的经验意识之流中“暂明暂灭”*阳明谓:“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则其本体虽亦时时发见,终是暂明暂灭,非其全体大用矣。”见陈荣捷:《传习录详注集评》第76条,第104页。的道德意识,后者是恒常昭灵明觉、无对待的心体。就前者而言,理欲夹缠的状况有如念庵形容的“如油入面,未易脱离”,故“一涉搀和,皆非无欲之体”*以上引文分别见[明]罗洪先:《松原志晤》,《念庵文集》第8卷,第182页;《答湛甘泉公》,《念庵文集》第2卷,第28页。。一般人与圣人良知之不同质、不同层是一实然的现实,这是反对者们立论的出发点。而在阳明、龙溪这里,虽然承认凡圣之别,但不是其立说的主要语境。基于“良知人人皆有”*分别见陈荣捷:《传习录详注集评》第289,221,222条,第341—342,299,300页。,他们将立论重心扭转到“其能辨黑白则一”、“未尝不同”上,作为吾人道德实践的入手处。
因此第二,阳明、龙溪更注重强调凡圣相同的面相。阳明“一节之知,即全体之知”*分别见陈荣捷:《传习录详注集评》第289,221,222条,第341—342,299,300页。的比喻,被龙溪用来证成见在良知说。除了“昭昭之天与广大之天原无差别”的比喻外,龙溪还以“一隙之光以为决非照临四表之光,亦所不可”、 “毫厘金即万镒金”*以上引文分别见[明]罗洪先:《甲寅夏游记》,《石莲洞罗先生文集》第12卷,第43页;《松原志晤》,《念庵文集》第8卷,第181页。比喻凡圣良知之同。这些比喻的共同点在于前者(喻一般人的良知)与后者(喻圣人良知)的关系是同质而不同量,这其实是从“已悟之果地”出发的理解和实践。对已悟良知心体的学者而言,其当下一念可透显良知心体,在质上与圣人无别,区别主要在量上的多寡,工夫便是“念念致其良知”的保任与拓展。龙溪本人走的正是这一“先天正心”的高明工夫进路:他从学阳明后,“逾年遂悟虚灵寂感、通一无二之旨”*[明]徐阶:《龙溪王先生传》,《王畿集》附录四,第823页。;天泉证道中阳明告诫龙溪“虽已得悟,不妨随时用渐修工夫”、“正好保任”*以上引文均见[明]王畿撰、吴震编校:《天泉证道纪》,《王畿集》第1卷,第2页。,也说明龙溪之功行主要是在日用常行中不断保任、扩充心体。李明辉认为:“每个人的心中直接呈现的恻隐之心即是圣人之天心(羞恶之心等亦同),在质上原无差别”,那么致良知工夫就“并非在质(纯度)上的提升,而是在量(应用范围)上的拓展”,“对原先的良知亦无所增益”*李明辉:《耿宁对良知说的诠释》,《哲学分析》2014年第4期,第47、48页。。这对已悟良知心体的学者而言是不错的。
然而龙溪的立论显然要有针对大多数未悟学者的适用性,故“见在良知与圣人未尝不同”的第三种解读方式在于:“未尝不同”的双重否定句式意在承认二者差别的前提下重点强调二者趋同的面相,人人本具的当下一念良知尽管有被遮蔽的可能,仍然与圣人的良知出于同一本体。因此阳明说“困学功夫,亦只从这点明处精察去耳”,龙溪面对双江指责其说为“悟后解缚”语时也说:“舍此更无从入之路、可变之几,固非以为妙悟而妄意自信,亦未尝谓非中人以下所能及也。”因为,这是吾人当下只能且必须依循的道德实践之依靠,“不信见在,又将何所用力耶?”*以上引文分别见[明]王畿撰、吴震编校:《致知议辨》,《王畿集》第6卷,第134页;《与罗念庵》,《王畿集》第10卷,第238页。龙溪的用意在于,以人人本具的当下一念良知为依据而唤醒、证成本体,以此提撕学者立志成圣的实践动力。这是念庵、双江等人不能善会的。
总之,解读见在良知说具有“未悟之因地”与“已悟之果地”两个工夫层面,这也是双江、念庵与龙溪工夫路径的不同起点。王龙溪所主的见在良知说走立根于心体的高明一路,这在龙溪提揭的“独知”“当下一念”“直心”“自照自察”等工夫体认要点中得以极尽发挥。
三、独知、当下一念、直心自照
瑞士现象学家耿宁借用唯识学的自证分和现象学的原意识来解释良知,认为良知是与心之所发之“意”同时现存且必然现存的“自知”*[瑞士]耿宁:《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17页。。笔者认为,经由良知自证分的阐释角度凸显了“良知之当下自证自知”的体认维度,良知本体(心体)是一泯合对待、无分别的清净识体,只可当下直观呈现,不可对象化地求取*参见张卫红:《良知与自证分》,《“商务印书馆学术论坛——耿宁〈人生第一等事〉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05—113页。。而在阳明后学中,王龙溪对于这一体认维度和思想维度最为敏感,发挥得最为充分。先看龙溪对良知本体的界定。龙溪与阳明一样,也称良知为“独知”,表述更为详细:
《易》曰“乾知大始”,乾知即良知,乃浑沌初开第一窍,为万物之始,不与万物作对,故谓之“独”。以其自知,故谓之“独知”。
夫独知者,非念动而后知也,乃是先天灵窍,不因念有,不随念迁,不与万物作对。*以上引文分别见[明]王畿撰、吴震编校:《致知议略》,《王畿集》第6卷,第131页;《答王鲤湖》,《王畿集》第10卷,第264页。
朱子对《周易·系辞》之“乾知大始”的解释是:“知者管也,乾管却大始,大始即物生之始。”又言“此‘知’字训‘管’字,不当解作‘知见’之‘知’”*以上引文均见[宋]朱熹撰、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74卷,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1686页。,“知犹主也,乾主始物”*[宋]朱熹:《原本周易本义》第7卷,《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册,第680页。,意谓“乾”主管万物资生之始。龙溪并不满意朱子的解释:“《本义》训‘知’为‘主’,反使圣人吃紧明白话头含糊昏缓,无入手处。只一‘知’字且无下落,致知工夫将复何所属耶?”*[明]王畿撰、吴震编校:《答季彭山龙镜书》,《王畿集》第9卷,第213页。故阳明、龙溪等心学家们都将创生并承载天地万物的本原直接敛归精神主体,如阳明所说:“知天地之化育,心体原是如此。乾知大始,心体亦原是如此。”*[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答友人问 丙戌》,《王阳明全集》第6卷,第210页。此外,江右王门学者王塘南也说:“易曰‘乾知大始’,此知即天之明命,是谓性体,非以此知彼之谓也。”见[明]黄宗羲:《明儒学案》第20卷,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76页。阳明、龙溪都将“乾知”视为一词,此“知”即“良知”。“乾知”作为创生并承载万物的本原,非念动而后知,不随念迁,不与万物作对。“本是无声无息,本无所知识,本是无所粘带拣择,本是彻上彻下”*[明]王畿撰、吴震编校:《答洪觉山》,《王畿集》第10卷,第262页。,表明它是能所二元对待之前、先于名言概念的“独一”,以其非对象化的自我证知,故云“独知”。龙溪将这一观照、呈现万物的身体据点称为“先天灵窍”“圆明一窍”:“鸢鱼活泼浑常事,都入圆明一窍中。”*[明]王畿撰、吴震编校:《天游次马师山韵二首》,《王畿集》第18卷,第554页。陈立胜认为:理学家之“窍”超越了医家定位于具体脏腑的身体(实体)含义,是承载天地万物的“心窍”,因其“虚”“无”“通”的性质,天地万物才能在此呈现*参见陈立胜:《身体之为“窍”:宋明儒学中的身体本体论建构》,氏著:《“身体”与“诠释”——宋明儒学论集》,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第65—66页。。龙溪对于“独知”原本具有超越性、非对象性特质的领会是极为敏锐的:“谓独知即是天理,则可;谓独知之中必用天理,为若二物,则不可。此等处,差若毫厘,谬实千里,不可不早觉而明辨者也。”*[明]王畿撰、吴震编校:《答洪觉山》,《王畿集》第10卷,第262页。我们可以说“独知自身就是天理”,不能说“独知发用为天理(一物)”,若是则独知与天理便是“二物”。未经意识分别的“独知”只能直观显现,稍一把捉,便落入“二物”的对待求取方式。龙溪对此中的毫厘之辨是十分自觉且明晰的。
如是,“独知”便超越了时间意识*对象化思维与时间意识相关联,“胡塞尔对时间化概念的规定中至少包含着对象极和自我极两个方面的含义。”见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532页。。龙溪言“良知本来具足,本无生死,吾人将意识承受,正是无始以来生死之本”*[明]王畿撰、吴震编校:《与存斋徐子问答》,《王畿集》第6卷,第145页。,即是此意。其具体呈现形式,只在“当下一念”。在究竟意义上,这“当下”(现在)不是与“过去”“未来”相对、使时间得以延绵的一个因素——在对象化的意识活动中,“现在”是构成过去、现在、未来时间之流的对待之相,念念迁流,刹那生灭,心识总在不断地了别对境、产生意念,又不断被新的意念所取代、淹没,故常人当下一念的良知在经验意识之流中随时可能被取代或遮蔽,很难做到“念念致良知”。龙溪称:“千古圣学只有当下一念。”*[明]王畿撰、吴震编校:《书查子警卷》,《王畿集》第16卷,第478页。此“当下”的内涵由特定的“一念”所规定。先看龙溪言“念”的不同语境:
念者心之用也。念有二义:今心为念,是为见在心,所谓正念也;二心为念,是为将迎心,所谓邪念也。正与邪,本体之明,未尝不知,所谓良知也。*[明]王畿撰、吴震编校:《念堂说》,《王畿集》第17卷,第501—502页。
龙溪指出了两种“念”:一是从良知心体显现之念,这是吾人在具体的伦理情境中当下显现的道德意识,称为“见在心”“正念”;二是被欲根习气所遮蔽的意念,因其偏离了本心之初动而产生了私意、将迎等分别计较,故谓之“二心”“将迎心”“邪念”。龙溪有时又将两者区分为“本念”与“欲念”*见[明]王畿《留都会纪》:“吾人之学,不曾从源头判断得一番本念与欲念,未免夹带过去。此等处,良知未尝不明。”《王畿集》第4卷,第90页。。严格说来,龙溪所说的“当下一念”与第一种“正念”仍有区别。因为正念与邪念属于具体的对象化意识,当下一念良知则是超越正邪意念、并能够辨别正邪是非的“本体之明”。 “当下一念”与第一种“正念”之不同在于,前者是心体将动之初的“几微”,谓之“一念独知”“一念之微”“最初一念”“一念灵明”,“从混沌立根基”*以上引文分别见[明]王畿撰、吴震编校:《新安福田山房六邑会籍》,《王畿集》第2卷,第51页;《闻讲书院会语》,《王畿集》第1卷,第6页;《南雍诸友鸡鸣凭虚阁会语》,《王畿集》第5卷,第112页;《龙南山居会语》,《王畿集》第7卷,第167页。,是“本心寂然之灵枢,非可以意识承领而得也”*[明]王畿撰、吴震编校:《答李渐庵》,《王畿集》第11卷,第272页。。这表明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有善恶等对待内容的“念头”,而是未有相见二分对待、未成是非善恶分别之前的心体之念。在这个意义上,龙溪说:
念者心之用,所谓见在心也。缘起境集,此念常寂,未尝有也,有则滞矣;缘息境空,此念常惺,未尝无也,无则槁矣。
一念者无念也,即念而离念也。故君子之学,以无念为宗。*以上引文分别见[明]王畿撰、吴震编校:《别曾见台漫语摘略》,《王畿集》第16卷,第464页;《趋庭谩语付应斌儿》,《王畿集》第15卷,第440页。
这也是龙溪无中生有、体用相即思想的立基处。“当下一念”是心体萌动之初(几微),尚未形成具体的意识(念头),“无念”“离念”指向绝待之心体,此“一念”是心体非对象化的自证自知。故由此一念而体现的“当下”,就不是物理意义的刹那生灭的时间,“当下一念”是心体“显现在前”的现量境。这一体认维度深细难明,龙溪常言“心之精微,口不能宣”,言“藏密”“密体”*以上引文分别见[明]王畿撰、吴震编校:《自讼长语示儿辈》,《王畿集》第15卷,第427页;《藏密轩说》,《王畿集》第17卷,第496页;《与沈宗颜》,《王畿集》第12卷,第330页。,均指其为常人难以体会的精妙隐微的心识层面。而常人能够把握的往往是心体之发动已经完成、有具体内容的“正念”,它在经验意识之流中常与欲念、邪念挟裹在一起,时时有被遮蔽的危险。
以上“当下一念”与“正念”可对应于龙溪、念庵对见在良知不同理解,耿宁对此有清晰的区分:“(龙溪的)‘一念’应当被理解为‘精神的本己本质’在现时意识中的一个真实显露,而不能理解为一个思想的短暂瞬间。”“罗洪先在这里将王畿的‘这一个意念(一念)’理解为一个瞬间意识。”*[瑞士]耿宁:《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第699、918页。因此,念庵指责龙溪“以一念之明为极则,以一觉之顷为实际,不亦过于卤莽乎”*[明]罗洪先:《(戊申)夏游记》,《念庵文集》第5卷,第143页。,实未能契合龙溪所说的“一念”。当然龙溪并没有明确区分两种“一念”之不同。究其原因,一则古人没有清晰界定概念的意识;二则就践履工夫而言,“正念”正是回溯到“一念之微”的契机。
以此,龙溪之“当下一念自反”可理解为:“当下”与“一念”超越了二元对待的分别意识和相应的时间相,由此“一念”显现为心体自身并为自身所证知。龙溪说“吾人本心自证自悟,自有天则”*[明]王畿撰、吴震编校:《赵麟阳赠言》,《王畿集》第16卷,第447页。,就包含有心体自证自知的维度。同时,“当下一念”还包含有“随时”“即时”回返心体之义。故“师门所传学旨至易至简,当下具足,一念自反,即得本心,可以超凡入圣”*[明]王畿撰、吴震编校:《与莫廷韩》,《王畿集》第12卷,第335页。指示的工夫形态是:直接、随时回返并显现心体,无须渐进的意识层次和时间历程。此即龙溪所说“自证自悟,直下承当”*[明]王畿撰、吴震编校:《答王敬所》,《王畿集》第11卷,第278页。,也即阳明在天泉证道中所说“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即本体便是工夫,易简直截,更无剩欠,顿悟之学也”*[明]王畿撰、吴震编校:《天泉证道纪》,《王畿集》第1卷,第2页。。
一念自反后,如何做“时时保守此一念”的工夫?龙溪与其他阳明学者工夫实践的共同性在于,工夫内容无外乎涵养本体与改正习心的正负两面之功。但龙溪始终保持对良知本体“自证自知”维度的敏锐性,工夫始终是一非对象性、非经验性的证知活动。相应地,工夫内容体现为心体当下的“直心以动”与“自照自察”。龙溪谓“吾人为学只是一个直心,直心之谓德,无亿度处、无凑泊处、无转换处、无污染处……先师信手拈出良知两字,无思无为,以直而动,乃性命之枢,精一之宗传也”*[明]王畿撰、吴震编校:《直说示周子顺之》,《王畿集》第17卷,第497—498页。,“直心以动,全体超然,不以一毫意识参次其间”*[明]王畿撰、吴震编校:《赵麟阳赠言》,《王畿集》第16卷,第446—447页。,始终保持意念在二元分别之前的“直心”状态,如是“绵密保任,久久行持”*[明]王畿撰、吴震编校:《与吴中淮》,《王畿集》第12卷,第310页。。此外,龙溪常言照察工夫,他将阳明所说“良知常觉常照”*陈荣捷:《传习录详注集评》,第171条,第245页。之功极尽发挥。《水西精舍会语》载:
一友问:“应物了,即一返照,何如?”(龙溪)曰:“是多一照也。当其应时,真机之发即照,何更索照?照而不随,何待于返?”*[明]王畿撰、吴震编校:《水西精舍会语》,《王畿集》第3卷,第64页。
龙溪意谓,心体应物时并没有一个对象化的“索照”过程:先产生一个随境波动的意念,再由第二个意念觉察第一个意念,那已经不是原本的心体返照了。原本的返照是在一念发动的将动未动之初,当下即发即照,照而不随,非念动而后照。耿宁也认为“一念自反”不是一种对象性反思,“而是暗示一种集中关注、一种对自身还在现时进行之中的意识或体验的内化和深化”*[瑞士]耿宁:《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下册,第702页。。如是,“其几只在一念发动处,自照自察,一毫瞒他不得”,“只从一念入微处讨生死,全体精神,打并归一,看他起处,看他落处,精专凝定,不复知有其他”,“一念惺惺,冷然自照”,“寂照含虚,无二无杂”*以上引文分别见[明]王畿撰、吴震编校:《与吴中淮》,《王畿集》第12卷,第310页;《答李渐庵》,《王畿集》第11卷,第271页;《答刘抑亭》,《王畿集》第11卷,第298页;《答刘凝斋》,《王畿集》第11卷,第273页。,心体当下的自照自察,始终保持着观照对境之绝待无倚的超越维度。这也保证了意念稍有偏离心体时,便“才动即觉,才觉即化”,即龙溪称道颜子的“不远复”之功:“人知未尝复行为难,不知未尝不知为尤难。颜子心如明镜止水,纤尘微波,才动即觉,才觉即化,不待远而后复,所谓庶几也。”*[明]王畿撰、吴震编校:《与阳和张子问答》,《王畿集》第5卷,第124页。它要求心体对意念时刻保持观照,哪怕有纤尘微波之偏离,也能随时照察并当下融归心体,不待偏离甚远而后复。如是,才能“时时保守此一念”。“未尝不知为尤难”体现的是心体如明镜止水般清澈、绝待的高深观照工夫。
正因龙溪之功始终不落二元对待的经验意识层面,他才说“无工夫中真工夫”、 “无修证中真修证”*以上引文分别见[明]王畿撰、吴震编校:《与存斋徐子问答》,《王畿集》第6卷,第146页;《答吴悟斋》,《王畿集》第10卷,第248页。,并对任何经验性的认知、对象化的把捉保持警惕,“凑泊”“安排”“拣择”都是落入对待、执著的用功误区:“一念灵明,洞彻千古,一切世情习气,原自凑泊不上”,“才涉安排,即为憧憧”,“凡在名目上拣择、形迹上支撑、功能上凑泊,而非盎然以出者,皆有所为而然也”*以上引文分别见[明]王畿撰、吴震编校:《与萧来凤》,《王畿集》第12卷,第326页;《答李渐庵》,《王畿集》第11卷,第272页;《与胡栢泉》,《王畿集》第10卷,第265页。。反对者批评见在良知无须工夫或工夫太易,实是不能契会这一体认维度所致。
四、双方体认维度之别
在阳明学者的工夫实践中,“致良知须以悟得良知本体为前提……阳明后学的‘致良知’谈论,乃以如何‘悟良知本体’为本质性的关键工夫”*林月惠:《阳明与阳明后学的“良知”概念——从耿宁〈论王阳明“良知”概念的演变及其双义性〉谈起》,《哲学分析》2014年第4期,第12页。。诚然,双江、念庵与龙溪一样强调立根于心体用功,但其工夫起点却是从未悟之因地层面展开的:“故知善知恶之知,随出随泯,特一时之发见焉耳。一时之发见,未可尽指为本体。则自然之明觉固当反求其根源。”*[明]罗洪先:《甲寅夏游记》,《石莲洞罗先生文集》第12卷,第36页。故须“从见在寻源头”——这显然是认识者把握一个认识对象的二元识度——因苦于“当下一念”在经验意识中随时会被遮蔽,故预设良知为某个对象性的存在,从而将当下一念的良知向上翻转为超越层不为分别意识所扰动的“寂体”来求取。对于双江、念庵所预设的形上未发寂体,龙溪批评其“以寂为外、以感为内,而于内外之间别有一片地界可安顿也”,“别有一个虚明不动之体以为主宰”;对于双江、念庵所主归寂、专内以涵养未发心体的工夫路数,龙溪批评其“别求未发之时,故谓之茫昧支离”*以上引文分别见[明]王畿撰、吴震编校:《致知议辨》,《王畿集》第6卷,第134、136、140页。。从其反复强调的“别有”“别求”字眼可知,龙溪所批评的是一种“二见”的认知和实践方式。他在对念庵主静说的批评中言之甚详:
若曰吾惟于此处收敛握固,便有枢可执,认以为致知之实,未免犹落内外二见……然才有执著,终成管带。只此管带便是放矢之因。比之流转驰逐虽有不同,其为未得究竟法,则一而已……骊龙护珠,终有珠在。以手持物,终日握固。会有放时,不捉执而自固,乃忘于手者也。惟无可忘而忘,故不待存而存,此可以自悟矣!*[明]王畿撰、吴震编校:《答罗念庵》,《王畿集》第10卷,第234页。
“收敛握固”“有枢可执”“以手持物”“终成管带”都指向有把捉的对象化体认方式,龙溪谓之“二见”。相比于“无可忘而忘,不待存而存”的究竟无为境界,无论是执著求取还是放任驰逐都不脱对象性之维度。这一点,念庵随着践履工夫的深入也渐渐意识到了。他晚年超出了主静归寂说,转为主张收摄保聚说,并在家乡主持丈田的活动中以收摄保聚之功打通动静。龙溪在肯定念庵工夫“得手”的同时,仍谓“略存一毫知解……略着一些影子,尚须有针线可商量处”*[明]钱德洪:《答论年谱书(六)》,《王阳明全集》第37卷,第1374页。,“终是有收有制之功,非究竟无为之旨也”*[明]王畿撰、吴震编校:《松原晤语》,《王畿集》第2卷,第42页。。这“略存”“略着”的小问题在于,此时念庵虽悟得心体,但在本体层面仍未化掉“有收有制”的对象化把捉痕迹,距离究竟无为的良知化境尚有一间未达。也只有到龙溪这般明澈无待的工夫境地,才能如此纤尘毕照,看到念庵之工夫仍有未脱“二见”的痕迹在。故龙溪反复申说的“忘却分别二见”“不落动静二见”“忘得能所二见”“不坠有无二见”*以上引文分别见[明]王畿撰、吴震编校:《与狮泉刘子问答》,《王畿集》第4卷,第81页;《与刘凝斋》,《王畿集》第11卷,第274页;《书见罗卷兼赠思默》,《王畿集》第16卷,第475页;《答王敬所》,《王畿集》第11卷,第277页。,无不指向泯去对待、心体直显的原初意识。
同时,龙溪十分清楚他与双江、念庵体认方法之差异症结,正在于后者尚未契会良知本体及其独特的体认维度。其谓:
但以为近来讲学之弊,看得良知太浅,说得致良知功夫太易。良知万古不息,吾特顺之而已。其有所存照,有所修持,皆病其为未悟良知本体。*[明]王畿撰、吴震编校:《别曾见台漫语摘略》,《王畿集》第16卷,第464页。
龙溪自知“当下一念自反”是高明一路。故当耿天台问“当下亦有未认处否”时,龙溪答:“当下亦难识,非上根不能。”*[明]王畿撰、吴震编校:《留都会纪》,《王畿集》第4卷,第89页。又说一念工夫乃“中人以上境界,非一蹴所能至”。然而,“不论钝根利器,皆须如此行持,此万古人心之本体”*以上引文分别见[明]王畿撰、吴震编校:《趋庭谩语付应斌儿》,《王畿集》第15卷,第440页;《答万履庵》,《王畿集》第9卷,第217页。。龙溪在指点刘狮泉用功方法时也说:“兄但忘却分别二见,功夫自然归一。”*[明]王畿撰、吴震编校:《与狮泉刘子问答》,《王畿集》第4卷,第81页。本体法尔如是,故对于未悟本体的学者而言也须建立“不二”的思想和行持维度。因为在龙溪看来,从二元对待的经验意识返归“独知”之体的工夫途径,不可能是同质同层的渐进过程。其谓:
但其间煞有机窍。若不得其机、不入其窍,虽终日检点矜持,只成义袭之学。且如司马君实平生无妄语,心事可质神明,名重四夷,岂非世间豪杰之士?但一念入微未得稳贴,每疚于心,时常念个中字,未免又为中所缠缚,其拟《玄》作《潜虚》,亦是系心之法,以其未得机窍也……若悟得时,中不待念,虚不待潜,反身而求,无不具足。*[明]王畿撰、吴震编校:《与潘水帘》,《王畿集》第9卷,第219页。
即便司马光已至“平生无妄语,心事可质神明”的道德造诣,工夫仍不脱“系心”“检点矜持”的对象化把捉,未能于一念入微处当下返归心体。而在龙溪看来,一念回返心体的“机窍”,就是他反复申说的“信得及良知”。
五、如何“信得及良知”
就精神活动而言,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价值信念,“信”都是开启并实践它的首要条件。从字源上看,《说文解字》将“信”与“诚”互训;“诚”者,“敬也”(《广雅》);“纯也,无伪也,真实也”(《增韵》)。《尚书·太甲》言:“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左传》释云:“言鬼神不系一人,能诚信者则享其祀。”在古典语境中,“诚”“信”唤起的是真切纯一、无伪无杂的心灵力量,甚至可以超越经验世界,开启天道,沟通鬼神。与一般宗教的对象化信仰崇拜所不同的是,阳明学者对良知的信仰,已将信仰对象(天理、良知)内化到精神主体之中,与精神主体合一。如本文开头所引的龙溪之言,若信得及时,良知当下具足,人人可为尧舜。故“信得及”并非一种对象化的信仰,而是对于良知人人本具、本无污坏的自我肯信、自我认同。此“自我认同”同时指向“依良知而行”的“行动抉择”,故良知发用的实践动力是当下具足,不必外求*见林月惠:《王龙溪“见在良知”释疑》,前揭书,第192页。。龙溪对此言之甚详:
若信得及时,全体精神收摄来,只在此一处用,针针见血,丝丝入理,神感神应,机常在我……一切嗜好,自然夹带不上;一切意见,自然搀搭不入。
于此信得及、悟得彻,直上直下,不起诸妄。*以上引文分别见[明]王畿撰、吴震编校:《与唐荆川》,《王畿集》第10卷,第267页;《直说示周子顺之》,《王畿集》第17卷,第498页。
由“信得及良知”而带动起大雄猛气象和念念纯一无杂的定力,才能“全体精神收摄来”,才可冲破欲根习心的遮蔽、经验意识的束缚当下返归心体;才能“直下归根承受”“时时从良知上照察”*以上引文分别见[明]王畿撰、吴震编校:《答邹东廓》,《王畿集》第9卷,第201页;《金波晤言》,《王畿集》第3卷,第65页。,直下契入心体自证自知的维度。故龙溪与人论学时,每语“诸君果信得良知及时”*[明]王畿撰、吴震编校:《闻讲书院会语》,《王畿集》第1卷,第6页。,又以学不得力的原因为“信心不及”:
吾人学问未能一了百当,只是信心不及,终日意象纷纷,头出头没,有何了期?
若不信得这些子,只在二见上凑泊支持:下苦工时,便是有安排;讨见成时,便成无忌惮,未免堕落两边。其为未得应手,则一而已。*以上引文分别见[明]王畿撰、吴震编校:《三山丽泽录》,《王畿集》第1卷,第10页;《答赵尚莘》,《王畿集》第9卷,第226页。
“信不及良知”意味着缺乏充足的道德实践动力,无法从“意象纷纷,头出头没”的经验意识湍流超脱出来,也就无法超越二元对待的经验认知模式,要么执著于强力刻意的安排把捉,要么沉沦于大撒把式的肆无忌惮,总是堕入对待之见,未能“应手”。故王龙溪评价念庵说“此方今第一人也,奈于当下良知尚信不及耳”*[明]耿定向:《观生记》,《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0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36页。,深憾念庵未能契会良知的体认维度。故当龙溪自豪地说“师门致良知三字,人孰不闻,惟我信得及”*[明]王畿撰、吴震编校:《遗言付应斌应吉儿》,《王畿集》第15卷,第442页。时,实大有深意在。《中庸》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信得及”是以至深至纯的精神力量化除一切对待,以“诚之”而合于“诚”,直显天道,自我圆成。龙溪所谓“自信之真机”*[明]王畿撰、吴震编校:《答胡石川》,《王畿集》第9卷,第209页。,也是由人返天、由对待返归绝待之“真机”。
“信得及良知”的道德行动力所至达的深度与纯度,固然为一般人难以企及;其自我肯信、自我圆成的体认维度,固然难以契会;但在龙溪看来,顿悟良知的大门并非就此为中下根器的学者关闭,因为“道力业力,本无定在,相胜之机,存乎一念,觉与不觉耳”。其出脱之机,说到底还是在于能否由当下一念提起自信本心的觉性。如是,“吾人只是挨门就臼,挨来挨去,忽然得个着落,便是小歇脚”,此后“信心渐深,功行渐熟,遇境不动,微动即觉,不为所碍,方见有所得力处。久久惯习,触处逢源,方见无可用力处”*以上引文分别见[明]王畿撰、吴震编校:《答李渐庵》,《王畿集》第11卷,第271页;《留都会纪》,《王畿集》第4卷,第89页;《与张含宇》,《王畿集》第12卷,第307页。。说到底,渐修之路一样要不断地以“信得及”之力来提撕、觉醒良知。广义而言,“信得及良知”可以说是致良知教的共法,同样为其他阳明学者重视*如念庵也说:“学问争差,只在疑信。才承当,便能信。才退缩,便作疑。”([明]罗洪先:《与萧云皋》,《念庵文集》第3卷,第64页)邹东廓云:“今若信吾至善真体,原是帝衷,则种种习气,不肯勇除,直是获罪上帝,无可躲闪。”([明]邹守益撰、董平编校:《简刘晴川》,《邹守益集》第12卷,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590页)。龙溪则将其升格为致良知教最重要的工夫口诀和法门,彰显了最充足的道德实践动力和最强烈的道德主体性。
六、结 语
“念念致其良知”何以可能?王龙溪与聂双江、罗念庵等反对者们的分歧焦点何在?在学界以往的解释中,就心学内部而言,可从双方工夫路径之顿与渐、功行程度之熟与生、自然与勉然等方面诠释*龙溪在评价念庵的收摄保聚说时,即以“自然”“勉然”两种工夫形态暗喻他与念庵路径的差别:“(良知)乃其天机之神应,原无俟于收摄保聚而后有,此圣学之脉也。虽尧舜之生知安行,其焦劳怨慕,未尝不加困勉之功,但自然分数多,故谓之生知安行。愚夫愚妇,其感触神应,亦是生知安行之本体,但勉然分数多,故谓之困知勉行。及其知之成功,一也。”见《致知难易解》,《王畿集》第8卷,第191—192页。;在思想方法上,也往往析之以一元论与二元论思维模式的差异*参见彭国翔:《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第330—343页。。就心学外部而言,与见在良知说渊源最深的当属禅宗的顿悟法门。“信得及”“直下承当”“本来具足”“无念为宗”等工夫要旨,几与顿悟禅法在形式上等同*如《圆悟禅师心要》(弘学等整理:《圆悟克勤禅师——碧言录·心要·语录》,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言:“直下不起一念,脱体承当”(卷上《示升禅人》,第267页),“佛祖以禅道设教,唯务明心达本。况人人具足,各各圆成……若是宿昔蕴大根利智,便能于脚跟直下承当,不从他得”(卷下《示吴教授》,第331页),“放得下,信得及,活泼泼,无窠臼,廓然及得净尽,承当担荷”(卷下《示从大师》,第301页),“深根固蒂,信得及,了得彻,虚寂灵明,不动不变为基址”(卷下《示鲁叟》,第316页),“彻底信得及,直下把得住,始可印证”(卷上《示隆知藏》,第231页)。。本文从见在良知的非对象化体认维度入手,则龙溪与双江、念庵在工夫体认和思想方法的根本差异得以更为清晰地彰显:良知本体是非对象性、自证自知的“独知”,只可直观地呈现,不可对象化地求取。它显现于“当下一念”,这“当下”不是与过去、未来相对待的时间之流里的“现在”,这“一念”也不是经验意识之流中的“一个念头”,而是未有相见二分对待、未成是非善恶分别之前的“心体之念”。“当下一念自反”即心体直接显现在前的现量境。它的运动方式是无对待的“直心以动”,它感应万物的方式是泯合能所的“自照自察”,即便受外境扰动而有所偏离本体,也能才动即觉,不远而复。而通向这一境地的契机便是“信得及良知”,以精诚专一之信力纯化意识,化去对待,回返本真。如是,“念念致其良知”之“其”即是良知自身或意识自体,“念念致其良知”是意识自体的自信、自知、自证、自反、自主、自照、自察。龙溪在“当下一念”中,将意识自体之泯合能所、自我圆成的体认维度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一体认维度化去了对象化的认知与求取,故云“本来易简”*[明]王畿撰、吴震编校:《滁阳会语》,《王畿集》第2卷,第35页。。儒家心性体认的“不二”维度可远绍孟子所主的“仁义行”,王龙溪则是对这一体认维度最为敏锐、陈义最高、也最精微的阳明学者。他不像一般儒者那样在为善去恶的意识活动中用功,而是直接从先天心体立根,超越了能所对待的经验意识活动阶段,转识成知,直显本体:“良知之与知识,其端甚微,其辨甚精,非夫豪杰之士,超然于二见之外,能转识为知者,何足以与此?”龙溪甚至宣称:“二见纷纭而圣学始亡,道之不明于世,有自来矣!”*以上引文分别见[明]王畿撰、吴震编校:《水西同志会籍》,《王畿集》第2卷,第37页;《答茅治卿》,《王畿集》第9卷,第229页。而心体自知自证所彰显的“不二”维度,意味着人性原本就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精神恒久在当下能动地显现并创造,“变动周流,不为典要,日应万变而心常寂然。无善无不善,是为至善;无常无无常,是为真常;无迷无悟,是为彻悟。此吾儒不二之密旨,千圣绝学也”*[明]王畿撰、吴震编校:《不二斋说》,《王畿集》第17卷,第493页。。儒家心性工夫的超越性*耿宁也认为,良知本体是一个超越的概念、宗教概念。见[瑞士]耿宁著、肖德生译:《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贵阳会议之结语》,《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24—25页。、主体性意涵在此发挥至极,至高意义的为己之学可以在这样的视野中呈现。
【责任编辑:杨海文;责任校对:杨海文,许玉兰】
2014—11—1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思想、讲学与乡族实践——邹东廓与江右王学的开展”(11YJA720038)
张卫红,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广州510275)。
B248.2
A
1000-9639(2015)03-01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