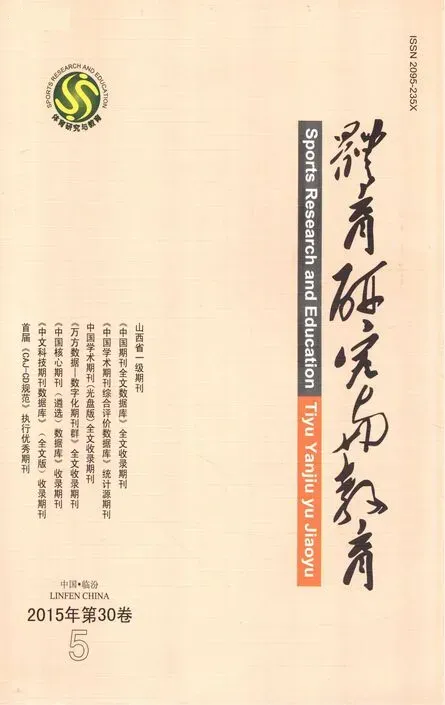文化生态视野下苗族吹枪的活态传承
周彦山
1955年,克罗伯的学生、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朱利安·H·斯图尔德(1902一1972)在其《文化变迁的理论》中首次提出“文化生态学”概念,并倡导成立了专门的学科。斯图尔德[1]的文化生态学——即对特定人类文化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认为文化与其生态环境是不可分离的,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在斯氏看来,相似的自然环境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文化适应了相异的自然环境而造就了世界不同的文化形态,自然环境适应的概念构成了斯氏文化生态学的基础。斯图尔德的这种理论为认识文化与环境的关系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但斯氏并没有跳出自然环境决定论的巢窠,他的“特殊进化论”[2]关注的也仅是环境对文化造成的影响,无法解决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多重复合关系。而事实文化的产生、发展、变迁不仅仅只限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还与社会环境以及周边民族文化相关连。之后斯图尔德的学生萨林斯[2](Marshall Sahlins)在继承斯图尔德和怀特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新进化论”,“生境”的概念。他突破了斯图尔德所指的环境仅指自然环境的局限,把环境的概念拓展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生境);不仅重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作用,也重视文化对环境的能动作用。随后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将生态学的系统论植入文化生态学研究领域,使文化生态形成自己独立的系统。文化生态学迅速在全球各领域广泛传播。
我国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文化生态学。冯天瑜[3]认为相互交往的文化群体以从事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及其他文化活动为背景和条件,文化生态本身又能构成一种文化成分;方李莉[4]认为,人类所创造的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各种文化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甚至类似食物链的文化链;邓先瑞[5]认为,人类与其生活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网络体,人类创造的文化是与其生存空间的环境及其变化相依相伴;司马云杰[6]认为,“文化生态学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来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的规律的一种学说;魏美仙[7]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成和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环境。这一特定的环境综合了该种文化生成发展所必需的一切要素,它就是该种文化的生态。虽然目前国内对文化生态概念的表述存在差异,但都强调文化与环境的相互影响与制约。关于文化生态的体系划分目前在学界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冯天瑜[3]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包括工具、技术、生产方式等)与“社会制度环境”三层论和司马云杰[6]的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经济体制、社会组织和价值观四层论。熊春林[8]在综合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文化生态学的研究,不应只停留在学理层面上,更应运用于解决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中。
21世纪以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领域开始植入文化生态学理念,研究成果有三类:其一,是将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和方法作用于个案的研究。如万义对苗族鼓舞、侗族舞春牛、土家族烧龙习俗的研究。此研究将个案文化生态体系进行划分,从“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和心态文化层”[9]四维分系统考察个案的文化生态变迁;其二,是将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和方法作用于整个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研究,主要探究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如王俊奇依据地域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分为三大类型,即“高原地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亚热带地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三江地域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10],并对民族体育文化形成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其三,是将文化生态学视角和方法作用于整个体育学科,研究构建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如龚建林[11]将文化生态系统分为“体育项目、象征符号、乡土情结、历史传承、文化认同、社会组织、体育环境”七个要素。其主要贡献在于将文化哲学的原理与方法融入文化生态研究领域。不足之处是忽略了体育技术对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性。
然而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由技术的、社会的和观念的三个子系统构成,技术系统是决定其余两者的基础,技术发展是一般进化的内在动因[12]”。技术系统构成了文化系统的基石,体育技术构成了体育文化的基础和关键。例如篮球的运球、传球、投篮、抢篮板等技术是整个篮球文化的基础。美国篮球文化的塑造和全球化传播即是以篮球技术的宣传为先锋,观众在观赏体育技术的基础上,更深入地了解了篮球文化;技术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文化进化的走向。对于大众而言,欲了解某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第一步先要了解它的基本技术,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了解它的内在文化。而基本技术本身决定了普通大众对于该项目的基本认识,是决定是否进一步探究和参与实践的关键,也是实现活态传承的关键。
1 对民运会赛场上吹枪技术的质疑
体育技术是影响体育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体育技术是指人们改变或控制运动训练、竞赛及体育科研管理等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身体精神环境)的手段、规则或者活动。它包含物性技术和软性技术两个方面:物性技术指先进科学技术应用于体育场馆、器材、运动服装等外部条件的建设及其改善的手段,还指现代生物技术在体育训练、比赛中的应用;软性技术主要指各项体育规则的制订和不断完善的手段[13]。吹枪在从原生态走向民运会赛场的过程中,其技术曾受到发掘者的改动,主要在器材等物性技术和竞赛规则等软性技术两个方面进行了改革。
原生态苗族吹枪流行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董干镇的马林村、马崩村、麻栗堡村以及相毗邻的越南社会主义国家的铳干地区,是当地苗族喜爱的一项民间运动项目,传承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1985年至1990年国家民委组织民族民间传统体育开展挖掘、整理工作,发动各基层单位深入乡村挖掘、抢救散落在各地乡野、民间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遗产。1988年由麻栗坡县民族事务委员会、体育运动委员会深入马林村挖掘、整理此项目;1992年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第六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吹枪列为比赛项目。全州8县派队员参加了吹枪角逐;1998年云南省第六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吹枪列为比赛项目。全省各州市、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派运动员参加吹枪角逐。自1998年起,云南各州市运动会均把吹枪列入各地州少数民族运动会比赛项目。在民运会的强力推动下,吹枪由马林、马崩、麻栗堡村片区的民族民间运动摇身成为全省范围的民运会竞技项目。
1.1 泥丸改成钢针,增加了危险系数,不利于普及
吹枪比赛有立姿和跪姿两种姿势,比赛中运动员在10分钟以内,将10颗箭矢吹射到固定靶上,依据环数的高低来角逐胜负。男子射程距离15米,女子射程距离10米;箭靶高度,立姿1.3米,跪姿1.1米;环靶直径从10环至3环依次为0.03米、0.06米、0.091米、0.122米、0.152米、0.182米、0.214米、0.251米[14]。云南省民运会在1998年至2006年期间沿用民间的吹枪器材——即由泥土做的子弹,用长1.20米的竹子做成枪管。后来因为在吹射过程中无法避免泥土子弹与口腔直接接触,在考虑卫生问题的情况下,2006年云南省第8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吹枪子弹改造成赵氏弓弩M60A×2型。吹枪[14]限用赵氏弓弩吹箭系列M60A×2型,不得自行改装和增加附加物,吹枪全长1.275米,枪管内直径0.01米,使用的针箭由长0.08米,直径0.002米的钢针镶嵌直径0.01米的塑料尾翼制成。在比赛过程中运动员将长0.08米的钢针子弹在10米开外吹射到直径0.03米的靶环上,依据靶环高低来判定胜负。泥丸改成钢针之后,最大的优点在于锋利的钢针针头容易插在靶环上,便宜裁判计分,但是钢针制作的子弹增加了吹枪的危险系数,吹射到人和动物关键部位,容易致残,以致于欲购买吹枪器材必须出具正规机构单位证明方能购买,不利于大众普及。
1.2 规则本身决定了赛场上观众不得拍照、不得欢呼
吹枪规则规定“立姿身体站立,两手前后握住枪管,枪身不得接触身体其他部位,跪姿一腿屈膝、脚掌着地,另一腿弯曲、膝盖和前脚掌或脚尖着地,成三角支撑,臀部可坐在膝盖着地的后腿上,两手前后握枪,枪不得接触身体其他部位”[14]。在吹枪比赛时,运动员要在宽1.2米、长2.5米的射击区内保持规定姿势吹射固定数量的子弹到固定的靶环上。虽然过程中允许站立或坐下休息,但是吹枪与步枪,射弩等射击项目不一样,是依靠人体呼吸肌吹气发力。在紧张的赛场氛围下,运动员任何身体体位的改变、视觉、听觉上的冲击、心理的微妙变化都会导致人体心跳速度改变,进而影响呼吸深度与频率。而呼吸深度与频率一旦改变,吹气发力力度大小就会随之变化,使子弹抛物线发生改变,最终影响比赛成绩。所以,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吹枪运动员都需要屏息静气,高度集中注意力,把自己调整为一个极度平稳安静的状态。由于吹枪比赛对赛场光线和声音分贝的要求很高,所以相关部门规定,在吹枪比赛过程中不准任何人在运动员视线范围内拍照、开闪光灯,观众不得在队员吹射得好成绩的时候鼓掌叫好。从这个角度说,依据目前技术体系建立的吹枪文化,其内部因素是排斥吹枪项目本身的群众基础、妨碍吹枪的现代化传播的。

图1民运会赛场上吹枪立姿比赛
1.3 民运会赛场吹枪技术有悖民间传统
2010年苗族吹枪被列为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命名马林苗族村民罗洪明为传承人。在2013年12月9日——12月月13日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他代表家乡代表队——麻栗坡县代表队参加吹枪的角逐。在比赛过程中,他向技术代表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苗族吹枪比赛也应该像射弩一样,分传统跟现代两种比赛方式。我们现在比赛的吹枪已经丧失了我们的民族性。建议比赛设立传统吹枪和现代吹枪两种比赛形式,不然我们当地农民都不用现代枪,现代枪不像我们的祖辈留下的传统枪。”虽然当时技术代表并没有正面回应传承人的诉求,但民间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传承者及当地群众不认可现代吹枪的技术改革,恐怕是不争的事实。笔者曾在2010年11月,2011年12月,2012年12月到马林村做田野调研,对吹枪传承人做过3次访谈;文山州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后,笔者又直接采访了罗洪明和麻栗坡具吹枪队队员王兴忠、罗启光、罗洪芬、侯兴丽、王兴丽等人。从他们的反映中深入了解到吹枪传承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一方面,我们得承认现代技术对吹枪的改革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这种改革有悖于民间传统,使吹枪传承出现了危机。

图2传承人罗洪明展示民族民间吹枪
2 民族民间吹枪是苗族适应生境的产物
从社会学角度讲,人是同时具备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双重属性的。无论生物的人还是社会的人都受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周边民族文化的影响与制约。从人的生物属性角度来看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为适应关系。与其他生物相比,人类无论大脑有多发达,四肢有多健全,其生息繁衍过程同样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然界永恒的法则;作为文化的人、技术的人、社会的人,其所创造的文明,要与自然环境之间表现出高度的适应性。与此同时,人类创造的文明又赋予人类适应自然以能动性,使人类在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认识自然,把握事物发展规律,进而利用自然,推动文明向前发展。
2.1 适应所处自然环境
作为生物的人,吹枪是当地村民宣泄烦闷情绪的手段。马林村、马崩村、麻栗堡村地处滇东南岩溶高原南部边缘斜坡地带,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形。由于地面被大量裸露的石灰岩覆盖,人们将石灰岩之间的空地开垦作土地(称为石头旮旯地),当地人在旮旯地上耕种玉米、高粱、蔬菜、豆类、红薯等粮食作物维持生计。因为大量裸露的石灰岩妨碍牛耕的运作,这里大半部分的土地不能使用犁——牛耕技术来耕种,只能依靠锄头——人工来耕种;同时大量裸露的石灰岩还严重妨碍当地交通运输的发展,种子、农家肥、化肥的输入与土地产出的输出全部得依靠人力;除此之外村民的日常生活的一些必需品如柴火、饲养家畜所需的大量草料的采集和运输也要依靠人工。相对于临县较好的自然条件,在相同的生产技术水平下,生产出相同能量的农作物、饲养出相同比值的家畜需要付出更多的人力,消耗更多的体能。加之马林村、马崩村、麻栗堡村这一片区域,到冬月、腊月、正月期间,便终日被大雾笼罩,气温持续在8℃以下。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繁重的劳作,人们自然会产生强烈的烦闷情绪。为了缓解这种压力,村民就在社会活动中寻求释放。而吹枪技术中的深吸气、屏息、呼气发力等技术动作本身对舒缓人体压力、宣泄烦闷情绪有独特的功能,因之久而久之就成为当地村民喜爱的一种有效宣泄的手段。
2.2 适应自身狩猎文化
作为文化的人、社会的人,传承古老的狩猎的文化,主动适应环境是马林村苗族村民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滇东南一带的苗族自称蒙,其祖先源于古代的东夷部落。“《说文·通训定声》曰:“夷,东方之人也,好战,好猎。”故字从大持弓会意,是典型的猎人形象。族源神话也是反映先民生活的重要途径,“后羿射日”就客观地体现了东夷部落射猎的风习[15]。我国历史上由东向西曾发生过5次民族大迁徙。清康熙、雍正年间,政府对贵州境内的三苗地区施行“改土归流”政策,导致贵州的苗族向云南各地区迁徙,文山(滇东南)一带的苗族就主要是从黔西南兴义等地迁来的。有关资料证实,文山麻栗坡县董干镇地区的苗族于清雍正年间就已陆续迁徙至此。“董干镇村委会龙保寨有一冢熊氏苗族坟,碑文记载其人死于清雍正年间,从贵州迁徙到此地落籍[16]。”苗族古老的狩猎文化,在民族迁徙过程中薪火相传,振古如兹。《民国邱北县志》(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邱北县)第二册《种人》中记载:“苗族,好猎善用强弩”;《马关县志》(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卷二记载:“苗族,好猎猛兽,善用火铳,发则多中,制药付弩,中则立死[17]”。古老的狩猎文化赋予滇东南苗族主动适应环境的能动性,他们发明了“支”和“打”两种狩猎方式。“支”是指利用事先设计好的陷阱等待猎物落入圈套的狩猎方式,主要工具有夹板、刷竿、铁锚、连扣;“打”则是直接利用武器打击猎物的狩猎方式,主要工具有弓箭、弩、吹枪、火铳等。然而历史上不具备狩猎文化特征却又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壮族则形成了以“那”文化为特征的壮族文化,唱“坡牙”山歌,敲铜鼓,舞牛头,跳手巾舞,演绎着颇具地方特色的稻作文化,与苗族狩猎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充分说明了吹枪的产生是苗族古老的狩猎文化对于自然环境的能动性结果。
3 适应的技术原理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由技术、社会和观念的三个子系统构成,技术系统是决定其余两者的基础,技术发展则是一般进化的内在动因[12]”。文化能否进步,最主要的是对能量的开发、利用与控制能力,能量之间的投入与产出转换比例关系取决于人类的适应程度和适应技术水平的高低。
滇东西苗族狩猎的“支”和“打”两种形式,从能量的投入与产出比例看“支”是能量输入最小的一种狩猎方式,但是往往从自然界捕获的能量也少;而“打”的方式从自然界捕获能量的速度较快,但自身投入的能量就较多。解放前当地人打野猪、麂子等大型哺乳猎物通常用弩和火铳,需要多人合作完成,其弩箭的选材、制作,火铳器材、火药、枪沙的购买使得投入端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使用弩、火铳等高能耗的器材打鸣禽等小型鸟类,能量的投入与产出比例悬殊,当地人并不能接受,因而需要构建一种针对鸣禽类的低能耗“打”的技术来弥补狩猎体系的空缺。在当地冬月、腊月、正月的大雾天气环境下,鸣禽类往往成群结队的往人类生火的地方靠近(当地人称,牲畜与人类一样,冬天也需要烤火)。人们不再为寻找猎物而四处奔波,大自然已经准备好现成的猎物,只需要通过一种“打”的方式便能将其捕获。相传“打”刚开始是使用通花杆(中华旌节花)做枪管,以适合枪管大小的树籽做子弹,做成“通花枪”,以此来“打”鸣禽类动物。后来由于通花枪管的笔直程度以及子弹与枪管之间的闭合度不够完善,常造成人体能量的浪费,投入与产出比例并不令人满意。
通花枪技术的不完善是推动吹枪文化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在漫长的探索过程中,当地人发现当地生长着的一种直径约0.015米的薄竹的单节竹节很适合做枪管。这种竹节最长长度可达1.2—1.3米,竹高10米有余。经过不断尝试最终薄竹管取代了通花杆做枪管(通花杆的笔直长度和内部光滑度无法与薄竹媲美),同时将子弹也改造成可就地取材的泥丸。泥丸的优点在于可根据枪管大小自行制作,这比树籽儿等子弹,人工无法根据枪管大小来调节,无疑有诸多优势,况且用树籽需要等到成熟季节,上树采摘等行为消耗的能量也增加狩猎能量的投入。在选用这种竹子时,人们注意了所选薄竹的长度和内径的大小要符合人体肺活量水平,经过实践证明长度在1.1米到1.2米之间的吹枪枪管,配上直径0.015米的球形泥丸子弹最符合当地成人的肺活量水平。过长、过大则肺活量无法有效驱动子弹。过短、过小则人体潜能无法有效释放。而竹子天然生长形成的锥形枪管更适合聚合枪管内壁与子弹之间的气体压力,具有伸缩性的粘合泥丸与锥形枪管二者合二为一,实现了在狩猎时将人体输入的能量高效地转化为打击猎物的动能的目的。当地有经验的村民可谓弹无虚发,1小时可捕获10多只猎物。这种狩猎技术对能量的投入与产出比列而言,可谓成效卓著。吹枪本身的发明填补了苗族狩猎文化体系里关于“打”鸣禽等小型动物的空缺,是其狩猎文化体系里的重要一环。
4 走向衰落的原因及活态传承重建
任何事物都是充满矛盾的发展过程,吹枪同样是一个在无序和有序之间不断发生着变动的动态文化体系。尽管当地人在与自然环境的斗争和适应过程中,也曾使吹枪保持了较长时期稳定的活态传承,但近20年来科技、经济的快速发展,却逐渐使它走向衰落,陷入即将失传的危机之中。
4.1 衰落的原因
最近二三十年里,村里修通了公路,村落与外界的联系开始变得快捷、通畅。汽车运来了大批的化肥、高产的杂交种子和高效杀虫剂。新兴的化肥和杂交种子配上杀虫剂能使原来的土地亩产增长3到4倍。生产力的快捷发展不仅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出大山,流向城市,而且也打破了原先建立起来的有序的吹枪活态传承体系。村民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接受了城市生活的现代元素,原来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吹枪成了挂在墙上的摆设。而新生代的孩子们,初中毕业后如果不继续上学就会跟随父母、亲戚外出打工,这使得他们再没有了接触吹枪、使用吹枪的机会,吹枪走向衰落也就在所难免。
吹枪走向衰落,还有一个内在原因,即系统内部的矛盾运动。在当地的狩猎文化体系里,吹枪狩猎的对象主要是鸣禽等小型鸟类,随着经济发展,物质条件的丰裕,人们不再需要通过捕获鸣禽等小型动物以满足生存需要,同时,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加强及相关保护的法律法规陆续颁布实施,狩猎也日益淡出人们的视野。吹枪虽然还有其存在的自然环境,但是却没有了其社会环境。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如果不将其文化精髓提炼出来,使其服务于教育,并与旅游适度结合,失传恐怕只是时间问题。
4.2 活态传承重建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府颁布了“废刀令”。在这种柔道丧失传承的社会背景下,日本柔道之父嘉纳治五郎不但没有迎合社会风气歧视柔术,反而主动学习各类柔术,并在担任校长期间将柔道从道馆引入学校,最终使其走向了奥运会赛场。嘉纳治五郎“从对青少年教育的目的出发,以东方的柔术为基础,将传统柔术里那种残酷的生死决斗形式加以革新,使之成为具有西方文化游戏性质和教育性质的胜负竞赛的对抗形式,促使青少年在练习过程中达到锻炼体魄和培养意志的双重教育目的[18]”。可以说柔道最终能成为“一项全世界流行的体育运动”,嘉纳治五郎功不可没[19]。而对于在相似背景下改良中国武术的马良而言,其改良效果却与嘉纳治五郎对柔道的改革相差甚远。马良“是在参照德式兵操的编排与练习方法[20]”的基础上改良中国武术,使其作用于部队训练。这种做法在近代“土洋体育之争”中引发的争议不断,最终新武术没能得到延续和发展。前人的经历告诉我们,学校才是民族传统体育改良的主战场,改良过程需遵循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规律,需介入现代教育理念。
学生应德、智、体全面发展,学校体育应让学生在愉快、轻松的课堂氛围中锻炼身体、宣泄不良情绪、磨练心理素质、学会相互合作。吹枪项目本身在原生态中就在宣泄不良情绪、增强肺活量、发展手指感觉神经末梢、锻炼心理素质等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因而它具备在学校中进行推广的条件。学校在对吹枪进行改良的过程中需注意与现代教育理念相对接,摒弃民运会赛场上静态枯燥的吹枪规则,发挥学生在创编游戏规则和改良器材方面的主体性和自由权;教师要注意从中引导、择优改善,努力拓展其生存空间。
4.2.1在体育教学中创编吹枪游戏民运会赛场上的吹枪静态打靶单调而乏味,学生体验之后“三分钟热”现象明显。其实在狩猎实践中,狩猎者和猎物也是不可能长时间停留在原地的。假想猎禽瞬间会有短暂的停顿,那么狩猎者是必须不断的移动身体,调整角度以寻求射击的最佳位置,因为距离猎物越近,命中率越高,射击难度系数越低。因此在忠于原始文化的背景下,教师在创编吹枪课堂游戏中,射击之前可设立训练身体素质的障碍,让游戏者通过跑、跳、爬等形式穿越障碍物之后到达射击区;射击区也要划分出不同的射击距离,由远及近赋予不同的分值;靶位上则可设立不同体积大小的气球,依据体积大小赋予不同的分值。最后根据射击距离得分加中靶得分的总和为一人一次射击得分,按规定时间内小组总得分高低来判定胜负。该游戏适合课堂分组游戏教学,其优点集策略性、健身性、娱乐性为一体,使分组对抗赛即失紧张又欢愉。

图3创新吹枪游戏规则、分组闯关射击气球比赛
4.2.2改良民运会吹枪子弹,创编新型吹枪竞赛规则民运会吹枪的子弹用长0.08米的钢针镶嵌直径0.01米的塑料尾翼制成。钢针的最大优点在于可以很容易就插在靶环上,方便裁判计分,这是泥丸不能做到的,但同时其危险系数的增加阻碍了吹枪的传播与发展。如果将泥丸改造成面粉制造的弹丸,既可以不污染口腔又能保持吹枪的原始状态,同时搓捏子弹的过程还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手指感觉神经末梢。而“猎物”则可改变为人,在游戏规则中可规定子弹只能打人体的躯干部位。游戏时双方不停的跑动、跳跃、转身、射击、躲避,不仅可以增加其对抗性、观赏性,还可以营造更好的比赛气氛。观众使劲吆喝,运动员随意发挥,这样的吹枪游戏符合青少年身心发展特征,能有效提高射击的准确性、灵活性和反应能力。实践证明,参加这样的吹枪游戏,在校大学生上场对抗3分钟之后心率可达到145分以上,面部有明显的流汗,呼吸深而急促。此项目的娱乐性较强,授课学生表示面粉制造的子弹打在身上的疼痛在安全范围以内。
将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开发不同的健身、娱乐方法结合起来,是保护它的重要途径。具体到吹枪而言,一方面继承前人留下来的吹枪历史文化,另一方面,以现代教育理念和方法改选它,将它引进大学体育课堂,既可以丰富体育教学、锻炼青少年体质,增强体育课的趣味性,又不乏民族特征,不失为一种一举多得的好办法。

图改良子弹之后的“打人”比赛和自制子弹
5 结论
原始吹枪技术的形成是其文化持有者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产物,它与自然环境休戚与共,与狩猎文化一脉相承,已形成动态有序的传承体系。但在近二三十年中,吹枪所面临的人群和村落社会环境均发生了变化,其技术的适应性受到挑战,活态传承遭到破坏。面对当前困境,实现吹枪活态传承的关键在于新型技术的创建,以现代理念、技术的介入使其适应新兴的社会环境,实现活态传承。
[1] (美)威廉·A·哈维兰著,瞿铁鹏,张玉译.文化人类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2] 罗康隆.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3]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国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 方李莉.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10~113.
[5] 邓先瑞.试论文化生态及其研究意义[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93~97.
[6]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7] 魏美仙.文化生态:民族文化传承研究的一个视角[J]. 学术探索, 2002(4):106~109.
[8] 熊春林.国内文化生态研究述评[J].生态经济,2010(3):153~155.
[9] 万义.苗族鼓舞文化生态变迁的人类学研究———湘西德夯的田野调查报告[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0(11):595~699.
[10] 王俊奇.我国少数民族体育形成的地理环境因素[J].体育科学研究,2004(6):39~42.
[11] 龚建林.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结构与特性[J].体育学刊2011(7):40~44.
[12] (美)托马斯·哈定,著,韩建军,等译.文化与进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13] 张克勤.哲学视域下的体育技术浅释[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1(1):32~34.
[14]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省体育局.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竞赛和表演规则及裁判法[Z].昆明:云南省人大办公厅印刷厂,2010.
[15] 曾玉华.我国东夷氏族集团体育文化的流变及影响[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11):1482~1484.
[16] 麻栗坡民族事务委员会.麻栗坡民族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
[17] 熊玉有.苗族文化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
[18] 余建华.嘉纳治五郎与日本柔道的发展[J].体育文化导刊,2004(7):60~61.
[19] 邓正龙.教育体系下日本柔道的现代改革历程——兼论嘉纳治五郎的重要贡献[J].体育学刊,2013(3)115~118.
[20] 马廉祯.马良与近代中国武术改良运动[J].回族研究,2012(1):37~44.
[21] 杨海晨.论体育人类学研究范式中的田野调查关系[J].体育科学,2012(2):8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