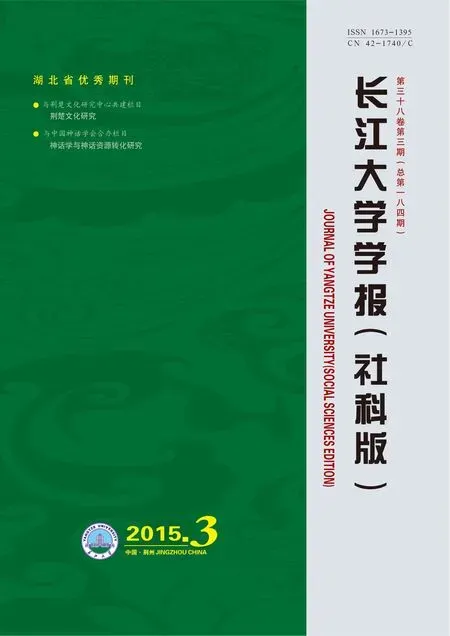超越族裔性
——华裔美国文学母题内涵演变探究
吴俊韦朝晖
(1.广西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2.钦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西 钦州 535000)
超越族裔性
——华裔美国文学母题内涵演变探究
吴俊1韦朝晖2
(1.广西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2.钦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西 钦州 535000)
20世纪90年代以降,华裔美国作家打破美国主流社会强加在华裔美国人身上的刻板形象,力图展示真实的自我,同时通过超越文学作品母题的族裔性,表达了对于种族之间和谐共处的诉求,及其实现的可能性。他们的作品,体现出具有包容品格的族际性。其具体表现为:超越族裔性,走向融合性;能够满足多种族群审美期待的人物塑造。
华裔美国文学;母题;族裔性;超越
关于华裔美国文学作品母题的变迁历程,笔者参照程爱民的研究[1],将其分为三个时段:早期阶段(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40年代)、本土化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超越族裔性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降)。笔者曾就华裔美国文学母题变迁第一及第二时段,做过相应的分析,拙文《历史视角下早期华裔美国文学作品母题内涵考察》,重在分析母题早期阶段的流变[2];拙文《华裔美国文学作品母题“本土化”进程之历史研究》,则重在考察母题的本土化进程[3]。为使华裔美国文学作品母题的变迁研究,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系列研究,本文拟就华裔美国文学母题超越族裔性的情况,做相关探讨。
一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几代华裔美国人的努力,在与其他族裔的交往过程中,华裔美国人终于以其吃苦耐劳、朴实坦诚的优秀品质,慢慢地赢得了其他种族人群的信任和认可。种族之间的冲突,已不再成为华裔美国人与其他种族人群人际关系的主要特征,取而代之的,是各个种族人群之间寻求共处之道。得益于此,华裔美国人的处境,较之以前大为改观,其对于身份的诉求,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多地讲求族裔性,就意味着画地为牢,反而会让本来已经获得的身份认同,走向自我销蚀。华裔美国人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其思考就不再停留在如何进行自我防御上,而是将超越族裔性,作为其主动思考和努力攻克的课题。华裔美国作家应势而出,重新评估了其之前所一直强调的文学中的族裔性问题,因为“族裔性作为族裔文学的根本属性是一种‘差异’符号,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具有双重影响。它可以促进族裔文学的接受,也可以导致族裔文学的独白。美国华裔文学在美国的接受是伴随着‘族裔性’减弱而进行的”[4]。顺应发展潮流的华裔美国作家们站了出来,为华裔美国人代言,表达了自己对于族裔之间友好相处的渴望。当然,他们也非常清醒,没有对抗,并不意味着自己长期以来被别人所强加于自身的负面形象就消失殆尽,种种潜藏于他族人群,尤其是主流人群意识中的刻板形象,依然阴魂不散,无形地制约着华裔美国人,阻碍着他们各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要与他族建立起平等和谐的关系,就要消除别人对自己形成的那种刻板印象,将真实的自我展现在人们面前,让人们不再带着隐形的有色眼镜观察自己,而是平等对待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超越族裔性。于是,华裔作家们开始将笔触探入这个领域,旨在改变别人的刻板印象,还原真实的自我。
二
20世纪90年代以降,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进一步发展,中国成为世界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国际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并且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缓和,促使了中国内地新移民的不断涌入美国。这一时期,到达美国的华人大多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学创作,不仅冲破了美国主流文学长期以来施加给华裔美国人的刻板形象,即认为华人就是一些只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奸诈和愚蠢是他们的本质;并且也冲破了华裔美国作家们在创作中所塑造的新的刻板形象,例如华裔美国人在美国文化中的他者形象、中美文化冲突、寻找和保持华裔属性等。这一时期其作品的母题,更多的是在多元文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不同文化间的共存,以及更多地关注人类社会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实现了跨越族裔性的转变。谭恩美后期的创作,任碧莲到雷祖威等的创作,都体现了这一转变。
谭恩美早期的作品,都是通过描写母女间的冲突与和解,来探讨中美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其重要母题主要是探寻华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但在《拯救溺水鱼》里,她一改其写作风格,通过描写几个代表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美国白人,在旅途中所反映出来的情趣和思维模式,打破了美国白人强加给华裔美国人的刻板形象,重塑了华裔美国人的英雄形象。此外,这部作品在内容、背景或人物的选择上,都体现出多样性特征。这些改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作者的创作主题发生了从寻找文化身份到突破族裔性的转变。陆薇认为,后殖民理论先驱弗朗兹·法侬,率先在精神分析意义上研究了刻板化形象,之后,巴巴指出:刻板化形象并不仅仅是对成为某种歧视的替罪羊的虚假形象的刻画,它是一种远比这更为含混的反射和内射,是带有隐喻和转喻性质策略的文本,是错位、负罪和挑衅,是带上官方和虚幻的面具,再将其撕裂的文本。[5](P84)由此可见,在华裔美国人身上曾经依附的挥之不去的刻板形象,是长期以来美国主流霸权文化和媒体共谋的结果,华裔美国人因此被无辜地固定成两类:“粗野的族群和阴险恶棍、不可同化的异族和白人的奴仆。”[6]在美国排华浪潮期间,美国主流舆论认为华人是“黄祸”,认为成千上万的华人移民到美国,便意味着将有成千上万的白人会因此失去工作而丧失生存的机会,最终将导致美国的灭亡。相形之下,华裔美国女性则被美国主流舆论刻板化成白人男性的玩物:
按照亚裔美国学者彦·勒·埃斯皮若塔斯的研究,华裔女性被刻画成两类,一类是“莲花”型,即娇小可爱,温柔顺从,渴望被白人男性拥有,拯救,即便是遭遗弃也无怨无悔的“亚洲娃娃”;另一类则是“龙女”,即阴险、邪恶、足智多谋、身手矫健、智勇双全的女魔王,同时也是具有白人男性多方抵抗的性诱惑力的魔女。[5](P97)
刻板化形象是美国霸权主义在不同时代对华人压迫的体现。虽然种族歧视时代已经过去,族裔时代已经到来,但这种压迫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存在着。“是人们借助于生物学概念对人群进行分类,并把一些想象性因素附加在某些弱势群体身上,从而形成了对某一特定群体的固定化看法。它和历史、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密切相连。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受西方中心论的支配,白人种族对这些特征进行强化,并使这种差异观念合法化,使其渗透到社会文本、历史文本、文学文本之中,使之无意识化,使非白人在意识深处不知不觉中实现自我卑劣化,自我憎恨化,从而使白种人自我高贵化。”[7]通过运用文学创作来证明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刻板形象固定化的虚伪性,从而打破华人的刻板化形象,便成为美国华裔作家们面临的主要任务。在美国的主流文学中,白人男性具有其他种族无法比拟的优越性,白人男性总是以崇高的人格魅力、文明的传播者和世界保护者等形象出现。为了颠覆这种形象,重塑华人的真实形象,谭恩美在《拯救溺水鱼》中,第一次运用与美国主流话语相同的笔法,解构了美国主流文学中白人男性的形象。这一努力,既解构了美国白人一直引以为豪的白人种族优越论,同时也解构了华裔的刻板化形象。此外,作者在书中塑造了三个华裔女性形象:一个是近乎全知全能的陈碧碧;一个是受过良好教育,有高尚的职业,能够自立的朱玛琳;一个是性格独立自主的埃斯米。白人主流社会一直流传着华人没有英雄、历史和神话的固定舆论,而这些优秀的女性形象,无疑对这一舆论进行了较为有力的冲击,并重构了华裔英雄形象。
任碧莲是继谭恩美之后,又一个备受瞩目的华裔美国文学作家。其作品所涉及的母题,有移民、文化异同、异族之间的紧张关系等。淡化族裔身份,是其作品的主要特征。在其作品中,主人公的身份是变动的,是可以自由转换的,因此,其美国梦已不同于以往华裔作家所追求的那种通过美国白人承认才能实现的美国梦,而是一个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各族人群各个文明之间共存共荣的梦想。其作品题材也是关于第一、二代华裔美国人的移民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已经有所改变。任碧莲突破了以往作家的叙事模式,不再像他们那样,将中国传统文化神话化、历史化,不再致力于描写中美文化之间的冲突,也不再执着于华裔美国人本真身份的探究。在她的笔下,移民母题再也不局限于华裔美国人的故事讲述中,而是延伸到其他族裔世界里。其作品一改其他美国华裔作家作品对单一族裔性的关注,而构建起更为多样化的族裔性。其作品中,不仅有我们所熟悉的华裔美国人,也有犹太裔美国人、非洲裔美国人等,并且这些人都能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和谐共处。比如,在《谁是爱尔兰人》和《爱妾》中,其两个家庭成员均由不同族裔所组成,他们之间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与价值观,也会有矛盾,但最后他们还是可以和谐相处。《谁是爱尔兰人》中的老祖母,在和女儿女婿发生争执被赶出家后,被自己一直鄙夷的女婿的母亲爱尔兰人收留。正因为如此,她的思想观念开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她摒弃前嫌,和爱尔兰亲家友好共处。由她们组合而成的家庭是特殊的,因为她们的种族身份是不同的,并且也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是她们却相亲相爱地生活在了一起。这个故事的结局,生动地体现了作者追求和谐共存的母题。在《爱妾》中,任碧莲也延续了这种家庭模式。在成员身份复杂多样的家庭里,血缘、种族和身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成员用彼此的爱,化解了彼此之间的矛盾,故而他们能够和睦相处。从这些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任碧莲的创作,已经打破了以往华裔作家固有的那种叙事模式。在作品中,她有意地淡化了华裔移民的种族特性,通过描述这些典型的美国社会家庭模式,这些来自于不同种族的家庭成员之间互助互爱,和谐相处的情形,借此表达了她期望建立一个和谐多元文化社会的期望。
一方面,族裔性是某个少数族裔的根本特性,是他们向主流社会发声,以求身份合法性的有力依据,失却这个特性,便意味着少数族裔什么都不是。为此,美国华裔作家最初的发力点,便是在其作品中凸显族裔性。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其所体现的社会文化价值,已为历史所承认。但另一方面,族裔性毕竟是个封闭性概念,如果不顾已然发生改变的社会实际,在作品中一味过分地强调族裔性,就会在不知不觉间,使自己陷入文化孤立的境地,有遭致冲突再来的危险。长此以往,族裔性反而会成为自我消亡的掘墓人,不利于少数族裔的生存和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部分美国华裔作家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顺应历史的要求,以开阔的视野,理性的胸怀,在其作品中,超越过往专属母国文化涵义的母题,赋予了其新的延伸意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谭恩美和任碧莲等为代表的美国华裔作家,敢于善于与时俱进,超越自我,故而成功地赋予了其作品中的族裔性母题新的普遍化的含义。
[1]程爱民.论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阶段和主题内容[J].外国语,2003(6).
[2]吴俊.历史视角下早期华裔美国文学作品母题内涵考察[J].百色学院学报,2015(1).
[3]吴俊.华裔美国文学作品母题“本土化”进程之历史研究[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4]刘增美.族裔性对美国华裔文学接受的影响[J].山东外语教学,2014(3).
[5]陆薇.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安晓宇.东方主义与美国社会中的华人刻板形象[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2(3).
[7]唐利平.《华女阿五》:两种族裔属性斗争的文化政治学[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Surpassing Ethnicity——On the Changes of the Motif Connotation of American Chinese Literature
WuJun1WeiZhaohui2
(1.CollegeofForeignLanguages,GuangxiTeachersEducationUniversity,NanNing530001;2.CollegeofForeignLanguages,QinzhouUniversity,QinZhou535000)
Since the 1990s,American-Chinese writers have been attempting to break the stereotype of Chinese imposed by American mainstream and to show the true self instead.They have also been expressing their appeals of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races and its possibilities of realization.Their works reveal inter-ethnicity,focusing on the ethnic fusion instead of the ethnicity,figuring new characters who can meet the multiracial aesthetic expectations.
American Chinese Literature;motif;ethnicity;surpassing
2014-12-21
广西2013年度哲社规划课题(13BWW003)
吴俊(1973—),男,广西桂平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华裔美国文学研究。
I106.4
A
1673-1395 (2015)03-002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