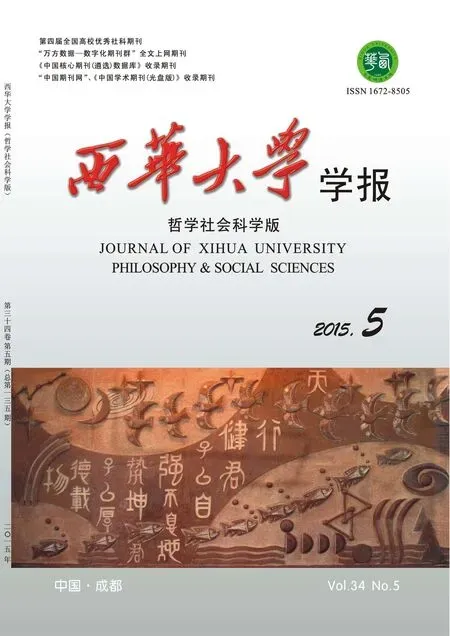抗战时期难民迁徙与“内迁文化”的形成
王春英 吴会蓉
(1.四川省行政学院 四川成都 610072;2.西华大学人文学院 四川成都 610039)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专栏·
抗战时期难民迁徙与“内迁文化”的形成
王春英1吴会蓉2
(1.四川省行政学院四川成都610072;2.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39)
抗战时期难民数量之大、涉及范围之广、难民的生存境遇之惨,胜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的难民现象,“紊乱、惊惶、骚乱”可谓是抗战时期逃难民众的基本写照。即使在如此悲惨的境状下,广大的难民尤其是其中的内迁文化人士仍以坚强的毅力从事着文化建设,传播着先进的思想与观念,推动着后方文化事业的发展,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内迁文化”。
抗战时期;人口移动;难民群体;内迁文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造成中国逃难流亡人口数以千万计,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抗战时期难民数量之大、涉及范围之广、难民的生存境遇之惨,胜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的难民现象,“紊乱、惊惶、骚乱”可谓是抗战时期逃难民众的基本写照。但在这巨大灾难面前,广大的难民尤其是其中的内迁文化人士仍不屈不挠地、以坚强的毅力从事着文化建设,传播着先进的思想与观念,推动着后方文化事业的发展,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独具特色的“内迁文化”。
一、日本侵华战争引发大规模难民迁徙,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
战时的难民与平时的难民不同,平时的难民多是因水灾、旱灾、荒灾、蝗灾而成为难民或灾民,战时的难民由战争造成,其遭遇之惨、生活之苦,更非平时的难民可比。抗战时期的难民生存境遇之惨胜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的难民。其自行谋取生活者,过着极贫苦之个人生活与家庭生活;其由公家出资收容于一处者,过着极贫困之集团生活。
1.迁徙难民的基本情况
抗战时期流徙人口来自四面八方,北方以河南、河北、山东各省的难民为多,南方则以湖北、湖南、江苏、安徽诸省为盛,湖北难民尤为多些。总的来看,以来自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河南、江西等处于正面战场省区的难民最多。至抗战胜利前夕,仅安徽全省境内全部沦陷者15县,部分沦陷者24县,完整未沦陷者共23县,总计沦陷区面积约为6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41%。战乱和自然灾害造成安徽出现260多万难民,其中数十万难民流亡载道,日本的侵华战争是造成中国人口迁移的最主要因素[1]。
抗战时期逃难迁徙民众原来所从事的职业多种多样,有贫亦有富。据振济委员会统计室对重庆市难民的抽样调查显示,至1938年9月10日止其所登记收容的363名难民中,原来有职业者105人,分别为“农业5人、工业8人、商业33人、交通运输1人、自由职业43人、公务11人、从事服务业5人”①。自1938年11月起至1939年9月底止,经水陆两路过万县的难民共26000人,在有业者中,“城市小商人占50%、工学两界占15%、农人仅占2%~3%”②。可见,难民群体中有企业家、工商业者、小手工业者、公务员、教师、学生、农民、工人、渔民、海员等等,其中商人、小手工业者占最大比例,而农民因依赖土地,大多近躲而不愿远逃,故在逃难后方群体中所占比例不大。
难民的受教育程度也多种多样。据非常时期救济委员会汉口支会于1938年1月31日为止所登记的资料来看,在31000余名(未含8岁以下儿童)难民中,“因为都来自江浙一带,所以教育程度相当的可以。据调查所得,受过中等教育以上的占5%,受过中等教育的占15%,受过初等教育的占2.5%,受过普通识字教育的占22.5%,未受教育的占20%。失学的学生占25%,失业的学生占10%”[2]48。
到抗战后期,重庆市当局对难民收容情况的调查资料显示:“住在(重庆)南岸这几个收容所的难民,一般说来,过去都是过着中等水准的生活,大多数人都是识字能够提笔写信的,他们的职业过去做过小学教师、公务员、办事员、秘书、书记之类。有这类能力的人,在收容所里占70%以上。”[3]可见,知识分子包括大中小学教师、青年学生、自由职业者等,在难民群体中确实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2.难民流离转徙,境况悲惨
抗战时期的人口迁徙,是人们为了避开战祸、避难求生而被迫踏上的漫漫流亡之路,其并非有组织、有计划的人口迁移,亦不同于社会上其他如经商行贩、侠客游民、游方和尚等人的流动形式。它随着战争的产生、存在、消亡与抗战相始终,其迁徙漫无目标,流动时间特长,具有很强的无序性。
众多的黎民百姓被战争逼离家园,沦为难民,踏上流徙之路。因战争影响而流徙出来的民众形成庞大的流亡队伍,一群群“逃难的人,有老的、小的、男的、女的、贫的、富的、瞎子、残废,还有几个正在病着的”③,有的从前是衣冠楚楚的佳公子而今变成囊无寸金、衣单被薄的落难者;有的以前是名闺秀女今亦潦落穷途,街头卖唱。
抗战时期逃难群体背井离乡,往往行居不定、困顿流离。民众逃难,大多只能依靠自己的双脚,沿途乞食而辗转流徙,只有少数比较富裕者才有能力借助交通工具逃亡。所以,当时逃亡群体中常有人感叹说:“能够逃抵重庆的人,这是很不容易的。至少,他们还能够解决交通问题和旅费问题。”④
如在吴淞口被日军封锁后,作家沙汀与一批内地和东北同事“为了避免敌机轰炸,是深夜离开上海的”,他们“乘沪杭路的火车先到嘉兴,然后再换车奔赴南京”,“在嘉兴换车时吃了不少苦头,并且为搬运行李引起同志间的误会”,“其实,那份失落的行李,是被临时雇用的搬运夫趁火打劫了”[4]。
战时保育院保育生黄金轩述道:
大家一路上因遭日机空袭,又受饥饿与疾病折磨,再加上背井离乡后对惨遭日本鬼子杀害的亲人的哀思及幸存的亲人的怀念,真把这些流浪儿拖得狼狈不堪。好不容易于5月中旬赶到当时的陪都重庆,又为躲避敌机日夜不停的狂轰滥炸,即换乘木船溯嘉陵江而上,至北碚附近之白庙子上岸,在川北运煤小铁路线上的水岚垭站暂住下来,等待后来进行分配。此时已入初夏,天气渐热,我们一个个蓬头垢面,身上虱子成串,气味难闻,瘦弱得活像一只只毛猴。我们没有固定的住所,那些闲着的乌黑的运煤小车厢、铁斗车和居民的屋檐下,竟成了我们的“临时宿舍”。每天不定时地拿出两顿稀饭,大群“小饿鬼”一拥而上挤抢起来,体弱者则常因挤不进圈儿只好唱“卧(饿)龙冈”了。在短短的几天里,饥饿与疾病就接连夺走了十几个小伙伴孱弱的生命,死神仍继续威胁着其他人。[5]
由于交通运输事业落后,逃难迁徙民众前途茫茫:“水道吧没有船,陆路吧缺乏车(商船和客船难民哪里有份挤上)!”[6]因此,“沿途的难民,三百一群五百一队,总有二十多里长。多半的难民,是一手提着箱,一手携着篮,背上又负着一袋米或是一包被,而且还带着一群的老少”⑤在惶乱中奔逃。每到一地,只要能活下去,就暂时停顿下来,稍稍喘口气。而一旦战事来临,每个人都紧张起来,急忙“收拾了自己两手可以携带的东西,呼男唤女,扶老携小”⑥,又开始排山倒海似地逃往异地,真是“前头不断泻出后面也不断流入”[7],形成了“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流亡画面。
在抗战时期流徙群体中,就知识说,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有目不识丁者;从年龄看,能够远离家乡的,毕竟是壮年者居多数,老少次之;从逃难的情形说,有从炮火中孑然一身出来的,也有携带相当的资财,事前逃出来的;就遭难的情况看,有家屋荡然的,有情况不明的,也有田庐无恙的。但是,“贫富都是人,都是逃难,虽然逃的方式有轮船、火车和‘开步走’的不同,逃的目的在苟延生命,实无二致”[2]59 ,[8]。在生命受到战争威胁的严酷形势下,流动人群手忙脚乱、六神无主,辗转迁徙奔向大西北、大西南和其它安全区域。
二、面对灾难,不屈不挠的内迁民众,尤其是其中的文化人士仍积极从事着文化建设,由此形成独有的“内迁文化”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但面对灾难,广大的难民尤其是其中的内迁文化人士没有屈服、没有消沉,他们仍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在大后方积极从事着文化建设,传播着先进的思想与观念,推动着后方文化事业的发展,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内迁文化”,造就了以四川为重点区域的后方抗战文化中心。
1.大量文化人士迁移内地与文化的传播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相继陷落以后,东线、西线与北线各个战区逐渐扩大,战区人口大规模西迁,除党政军界的以外,其中以商人、企业家、医生、工程师、教师、自由职业者、技术工人等居多,换言之,受教育程度越高者迁移的比例越高。
后方各省的人口多了,尤其是学生多了。在昆明,有云南大学、西南联大、中正医学院、中山大学、同济大学、华中大学、中法大学、地质调查所、北平图书馆、北平研究院等科研院校先后迁入。当时有人评价说:“这里已经有些像从前的故都,成了大学区了。”[9]
各地知识分子由前方集中地奔向武汉,转赴川湘,好似潮水一般地涌入内地[10]。据作家沙汀回忆,“单是从北京、上海疏散到成都的知名人士,如朱光潜、马宗融、毛一波、何其芳、卞之琳等就有30人左右”,“由于大批文化人聚集成都,本地原有的文艺工作者也更加活跃了。这突出地反映在《新民报》、《新新新闻》、《华西报》的副刊上。单独出版的文艺报刊,也发行了好几种。其中最突出的是何其芳、卞之琳诸位自费出版的《工作》,抗战前以《画梦录》蜚声文坛的作者文风大变,竟然发表了‘成都呀,让我把你摇醒吧!’这样激动人心的诗作”[4]109-110。
内迁文化人士为后方带来先进科学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思想,推动了后方文化事业的发展。西南一切文物制度等在抗战时期皆已为人所重视,一班学者都深入内地探讨西南文化之渊源与发展,人类学家则采取各人种之异同之材料,其余一切社会现象,都已为一班社会学者所重视。
张伯苓于1937年在重庆建立的南开中学“保持了天津前驱者的高水平和传统”[11],成为抗战时期西南的一个重要教育机构。吴宓曾发出感叹说:
昔人以滇南为瘴疠蛮荒,今则绝非是。此地但无烽警,便是桃园。长年气候温和,如春秋。花木终岁盛开,红紫交加。树木皆长大,不凋不黄。……苟能国难平息,生活安定,在此亦可乐不思蜀矣![12]
同时,中国的文化传播事业在后方也有所发展。1928年8月1日,国民党中央电台在南京正式播音。抗日战争爆发后,广播事业在战争中受到了摧残,1938年3月国民党中央电台在重庆恢复播音,1940年1月15日增设短波国际电台,负责国家宣传。据不完整资料统计,整个抗战期间仅在四川出版的各类报纸就有近200种,刊物1600种。其中,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型报刊,集中在重庆和成都两大城市,中小型报刊多分布在四川省内其他广大地区。抗战时期的西南都市,多被称“真正成了学术的中心”[9]。
2.“内迁文化”的兴起与后方抗战文化中心的形成
“内迁文化”,是指中国抗战时期广大内迁文化人在西南区域里创造的一种以他们为主体的、带有鲜明时代和区域色彩的抗战文化[13]。日本全面侵华后,中国东部甚至中部大部分地区相继沦陷,日寇铁蹄所至肆意摧残中国文化,迫使东部、中部沦陷区的大量高等院校和文化机构、设施、团体及大批文化名人纷纷内迁西移,由此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中国文化重心西移[14]。
内迁的难民群体中不少人是来自先进文化区域江浙一带的文化人士,他们“充当各省各种教育的教师,或任联保主任保长等职”,还有不少难民是“被占领区域内各种工厂的工友”,他们被“安插于内地新设立的工厂里面工作”[2]43,内迁难民对提高内地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难民在流亡过程中或定居流入地之后,一方面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辛苦劳作,参与当地的建设;另一方面在与其他人的接触中,或向当地人的学习中,也传播原籍的文化习俗,起到了促进两地文化交流的作用。尤其是内迁西移的广大难民群体中有为数众多的进步文化人,他们很快融入移入地,与当地文化人共同努力奋斗,以各种文化形式为抗战奔走呼号,并以坚强的毅力在西部地区开展大量新的文化建设。
抗战时期大量人口的西移,促进了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等后方省区文化事业的繁荣,重庆、成都、桂林、昆明、贵阳等大都市的变化尤其突出,后方出现了抗战文化中心。
自“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首都南京危如累卵,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以继续抗战,并最终于1940年9月正式确定重庆为“陪都”。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使四川战时地位转换。政府机关、工厂、学生与难民大量迁入,加之在日机的不断轰炸下新难民的成批出现,给重庆及至全川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随着战线由东南沿海和华北地区不断地向西部、内地推移,“后方”的概念不断收缩,直至主要包括川、滇、黔等西南省份。西迁难民基本上都选择了向川渝进发的道路,于是抗战时期庞大的苦难人流陆续向重庆、成都等四川大中城市及附近县区聚集。大量西迁难民落脚川省,造就了以四川为重点区域的后方抗战文化中心,为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了特殊的色彩。
3.“内迁文化”对内地文化的影响
抗战时期的人口西迁,使得后方地区人们的衣食住行及娱乐活动等生活习俗出现了趋洋尚奢的风气——在后方城市里,饭店、旅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生意兴隆;“挂外省牌子汽车”日益增多,人力车价普遍加洋⑦……;而重庆、成都等城市的妇女们“烫发涂脂,奇装高跟出入于消费影戏,徘徊于大马路之上”。老舍先生说道:“由上海南京及大城镇里逃来的小姐太太们,他们都不但不自己擦脂涂红,她们还这样说:‘哎呀,真奇怪,我们来了,四川人也学会修饰了,也会穿高跟涂口红了!’”[15]这些地域风俗之变化,大多与政府的推动密切相关,如国民政府曾在川省大中城市多次组织开展“清洁运动”,使后方都市居民形成了定期大扫除、清洁运动周、清洁大检查等良好习惯。
近代中国人,其“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男子剪辫和女子放足”,这个变化“看似形体上的现象,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现象”[16]。抗战时期妇女群体面对残酷战争灾难,在政府鼓励下“毅然决然地取下裹脚布”参加抗战,无论在战区还是后方,这都带来了无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自十六岁到三十岁的妇女,是一个最广大的数量,同时也是一支最坚强的力量。过去她们虽然裹着小脚,在太平时代仍能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但自抗战以来,她们已经尝够了小脚的痛苦。敌人来了,跑不动,为了不愿供敌寇蹂躏,只得投井自尽。这些惨痛的事实,使她们觉悟到封建制度害人之甚。另一方面,政府当局看到这种情形,也迫令三十岁以下的妇女一律放足,再加上妇女抗日救国会所组织的放足委员会,加以多方的宣传、鼓励,她们毅然决然地取下裹脚布,让束缚了多年的脚开始享受自由,并且还坚决地参加了妇女抗日救国会,一面加紧学习,一面负起抗战救亡工作。⑧
抗战时期历经苦难的流徙群体,尽管对故乡魂牵梦萦,但其“心灵已经流离太久,故园静谧的模样已是模糊不清”[17],不少西迁难民转化成为后方省份当地移民,战后重庆、成都及兰州、西安等城市的人口都增加了50%以上,其中有很大的比例是流徙而来的难民人口[18]。
抗战时期大规模的难民群体迁移后方,其中包括政府官员、工商人士、科研人员、文化工作者等高文化素质难民的迁入,对西南后方区域的工业、农业、金融、交通运输等各行各业的发展,起到了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尤其是促使一些原先十分落后的区域得到了初步开发。但大规模的战时人口移动,同时也给后方地区带来了严重的人口压力及一些社会问题,如传播疾病、增加治安隐患、加重后方民众的负担,甚至导致一些地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等,因此,抗战时期难民人口移动,亦如张爱玲的“文明”沉思——“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却是无所不包的[19]。即使战时后方城市的繁荣很短暂,“归心似箭的难民重返家园匆匆离去了,迁来的工厂或整个搬回了沿海或抽走了资金”,但抗战时期大规模逃难人群“孕育出新的文化因子”所带来的影响并不会因此而消失。
注释:
①见中央日报,1938-10-03(3)。
②见中央日报,1939-09-27(2)。
③见新华日报,1938-03-15(4)。
④见新华日报,1945-02-04(2)。
⑤见新华日报,1938-03-15(4)。
⑥见中央日报,1939-04-24(3)。
⑦见中央日报,1939-01-04(5)。
⑧见妇女生活,1939,7(2):3—4。
[1]张根福.战祸、自然灾害与难民迁移——抗战时期安徽省个案研究[J].民国档案,2004(4):105.
[2]叶溯中,等.伤兵问题与难民问题[M].上海:独立出版社,1938.
[3]救济难民要切实[N].新华日报,1945-02-04(2).
[4]沙汀.我在抗战后方琐忆[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08.
[5]官祥,黄自贵.教育家赵君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218.
[6]企程.江边的流民团[J].新华日报,1938-07-27(3).
[7]吉凯.难民[N].新华日报,1938-03-15(4).
[8]管雪齐.难民出路的设计[J].奋斗,1938(6)-(7).
[9]林照.昆明印象[N].中央日报,1939-03-13(6).
[10]范任宇.怎样以难民群体里的知识分子来配合抗战工作[J].难民周刊,1938(4):1.
[11][美]包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M]//沈自敏,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北京:中华书局,1979:103.
[12]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1936—1938)(第6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331.
[13]黄药眠.和范长江、陈同生在一起的日子[J].新闻研究资料,1979(1).
[14]唐正芒.中国西部抗战文化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11.
[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冯玉祥日记[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563.
[16]严昌洪.晚清民国时期社会风俗的变迁[M]//周积明,宋德金.中国社会史论(下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536.
[17]王树增.解放战争(1946年8月~1948年8月)(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35.
[18]孙艳魁.试论抗日战争时期难民西迁的社会影响[J].广东社会科学,1994(5):108.
[19][美]李欧梵著.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毛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03.
[责任编辑燕朝西]
Refugee Migr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Immigration Culture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WANG Chun-ying1WU Hui-rong2
(1.SichuanAdministrationCollege,Chengdu,Sichuan, 610072,China;2.CollegeofHumanities,XihuaU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39,China)
The refugees were unprecedented in terms of its number, range and sadness of plight in the record of the refugee history. “Disorder, panic and harassment” were the basic reflection of the displaced people. Even under such a miserable condition, the vast number of refugees, especially the inland literal people, with strong will, were still engaged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spreading the advanced thoughts and view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undertakings. As a result, the unique “inland-moving culture” came into being.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migration; refugee groups; inland-moving culture
2015-04-13
王春英(1962—),女,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K265
A
1672-8505(2015)05-0005-05
——聚焦各国难民儿童生存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