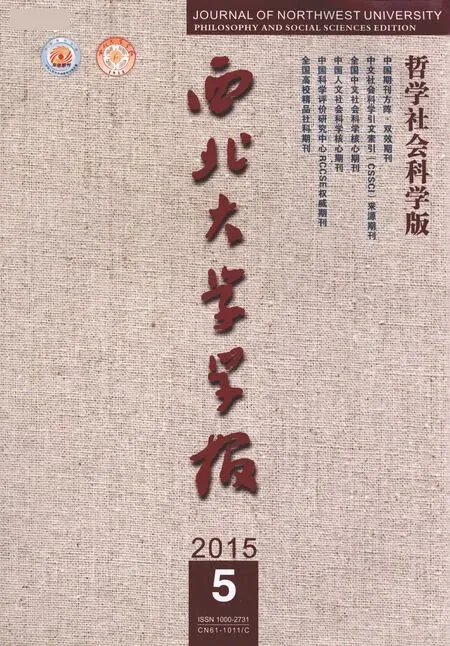当前中国美学界围绕意象问题的争论之我见
李祥林(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成都 610064)
当前中国美学界围绕意象问题的争论之我见
李祥林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围绕“美是意象”的观点,当下国内美学界见仁见智引发争论。从主张者和批评者言论看,双方争论焦点与其说是在如何理解何为意象,毋宁说是在如何理解何为美。回眸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建国后两次美学热潮都是围绕“美是什么”展开的,但争来争去,终无定论,形成的只有诸说并存局面,国内美学界实际上也放弃了在此话题上争论谁是谁非而把目光投向了美学研究更广阔领域。今天围绕意象问题的讨论,没有必要把精力再耗费到当年那种对美的解答谁是谁非之争上,而应看到,从本土寻求话语资源的“美在意象”“美是意象”说的提出,乃是当下学界对创建本土特色的中国美学体系的积极回应和努力。这种回应和努力,对于把中国美学研究向纵深推进才是真正重要并值得关注的。
关键词:美;意象;当代美学;中国话语
“意象”一词,对于文论界、美学界不陌生。当前中国美学领域,围绕“美是意象”的观点,人们见仁见智引发一场学术争论,成为行中人士关注的热点之一。由这场争论所触动和引发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下面就此谈谈己见,以供学界朋友参考。
一
先看看争论双方的言论。主张“美即意象”者说:“审美意象就是审美活动中所产生的‘意中之象’……其中的‘意’,是主观的情意,也不同程度地融汇着主体的理解;其中的‘象’,是情意体验到的物象,和主观借助于想象力所创构的虚象交融为一。意与象合,便生成了审美活动的成果———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意象。”[1](P208)又说:“审美活动就是意象创构的活动,审美活动的过程就是意象创构的过程。意象的创构不仅仅属于艺术作品的创造,整个审美活动都是一种意象创构的活动。美就是主体在审美过程中情景交融所创构的意象,它是在审美活动过程中动态地生成的,体现了主体的能动创造。在客观的物象、事象及其背景的基础上,主体通过主体的感知、动情的愉悦和想象力等能动创构诸方面创构审美意象。”[2]批评“美即意象”者说:“首先,‘美是意象’的观点混淆了美与美的对象、美的观念之间的界限。如果说对‘审美意象’创构过程的分析是朱志荣理论体系中的特征论部分的话,那么‘美是意象’便属于本体论范畴。……实际上,‘美’是一种抽象的价值存在,而‘意象’无论是观念层面的还是物质层面的都只能算作美的对象,两者一个属于抽象一个属于具体,决不是一回事,但朱先生却将两者混为一谈。其实对美与美的对象以及美的观念的区分,早在古希腊柏拉图那里便已经有所体现,在《大希庇阿斯》篇中柏拉图分析了‘什么是美’和‘什么东西是美的’这样两个有联系但又绝不可混淆的命题,‘美本身’和‘美的事物’分别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同时,诸如‘恰当为美’‘有益为美’‘快感为美’等认识属于美的观念,这与‘美本身’也不是一回事。尽管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像柏拉图一样进行如此抽丝剥茧式的哲学思辨,但亦不能忽视最基本的哲学常识。所以,朱先生‘美是意象’的命题是存在明显的不严密性的。”①韩伟《美是意象吗?———与朱志荣教授商榷》,《学术月刊》,2015年第6期。前者主张“美是意象”,实际上是就美的本质提出一种解答;后者批评“美是意象”,认为意象仅是美的现象而非美的本质。不难看出,双方争论的焦点与其说是在如何理解什么是意象,毋宁说是在如何理解什么是美。也就是说,“美即意象”主张者提出美可以这样理解,“美即意象”批评者认为美不可以这样理解。对此争论,该如何看待?
“美是什么?”此问题涉及美的本质,可谓是老话重提。回眸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建国初期和20世纪80年代两次美学热潮都是围绕此中心话题展开的。这个问题,是在哲学界“唯物论”和“唯心论”之争的大背景下,将美是什么的问题置放到是物质还是精神的哲学层面加以讨论的。当年,学人们兴致勃勃地围绕“美的本质”问题纷纷撰文著书、立说开派并投入激烈论战,造成了美学研究在中国空前热烈的景象,那局面迄今让行中人士怀念不已。梳理彼时诸家观点,大致可分几大派系:美是客观的,美是主观的,美是主客观统一的。主张美是客观的,认为美是物质世界的客观属性,是可以脱离人类这个审美主体而存在的,不能说没有人类就没有大自然的美;主张美是主观的,认为美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主观产物,离开人类以及人类社会,纯粹的大自然无所谓美不美;主张美是主客观统一的,则试图在自然与人类、物质与精神之间寻求协调,认为美只能产生于二者的结合中。诸家观点,各据其理,各说各话,彼此就美在物还是在心抑或在心物之间争议不休,但最终谁也未能说服谁。因为,美的本质究竟何在,不同的论者各有不同的推理系统,但任何一家观点都仅仅是带臆测性的一家推论而已,谁也拿不出能让对方哑口无言的铁证,自然就谁也说服不了谁。况且,对美是什么的终极性解答究竟该从何出发,既然诸家理论自逻辑起点上就分道扬镳,又各自依据不同的理论来相互辩驳和争议,那么,由于彼此之间原本缺乏共同对话基础,其各说各话式论争的结果如何也就可想而知。看看上述引起争议的“美即意象”论,从“意”即“情意”而“象”即“物象”这基本界定看,大致可将其划归美是主客观统一说。对此,持论者本人亦承认:“几十年来,我们很多美学学者,都深受朱光潜先生的影响,一直在接着朱光潜说。尤其是近30多年来,很多学者实际上继承和发展了朱光潜先生的主客观统一说。我认为,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说实际上已经包含了‘美即意象’的命题,具体说来就是,审美活动是意象的创构活动。”总之,“美即意象,包含着客观的物象及其背景以及主观的情趣两个方面,经由主体的心灵通过想象的创造加以融合,是主客观统一的产物”[3]。
二
回顾当代中国美学历程,结合当下中国美学研究现状,由此来看围绕“美是意象”的争论,我觉得有些状况需要梳理和反思。首先,眼下这场争论,有无必要把双方论战焦点再拽回到美的本质界定之争上?熟悉新中国成立后两次美学争论的人都知道,主张美是客观论者可以指责美是主观论者有见人不见物之嫌,主张美是主观论者可以指责美是客观论者有见物不见人之嫌,该二派也可以一致指责美是主客观统一论者有混淆心、物之嫌;同样,主张美是主客观统一者也可以指责前二派有见物不见人或见人不见物之嫌。如果我们把21世纪中国美学界眼下这场争论仍拽回到此,就会发现,这争论恐怕顶多只能算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美学两次热潮关于美的本质论战的翻版或继续而已;若真是这样,其对中国美学研究的当下推进意义究竟还会有多大,则值得打问号了。众所周知,关于美的本质问题尽管在20世纪国内两次美学热潮中争论得不亦乐乎,文章写了许多,书也出版不少,但争来争去终无结果,最后人们不得不承认各家美论有各家的道理,也不得不像前人一样发出“美是难的”这美学史上很早就有的感叹。争论之后,感叹之后,反思之后,国内美学界开始调整自我,把研究目光从“形而上”的玄思逐渐转向审美心理、审美文化、审美器物、日常生活、多民族文化等等,以致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继有“审美文化研究”“审美人类学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少数民族美学研究”等进入公众视野。不得不承认,当年国内美学界实际上是放弃了从纯粹“形而上”的哲学层面对美的本质的争论,把对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悬搁起来了(尽管这个问题从学理上讲不能彻底弃之不顾),因为“美是难的”。人们意识到,至少我们现有的知识水平和悟解能力还不足以彻底解答这个终极性的美的哲学问题,与其在此老话题上长久你争我吵纠缠不休而原地踏步,还不如把精力放到美学其他更广阔领域去做更具实效性的研究,用当下的话来说,使美学研究在“接地气”中激发与时代、社会、生活贴近的活力。明白这点,我想,眼下这次关于“美是意象”讨论,争论双方的用意大概都不是想回到过去那让人头疼却不得其解的美的本质问题之争上吧?若真是认定必须返回到这个点上,那么,我个人觉得,即使是在今天所谓高科技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继续追究和争论在这个古老的美的哲学问题上谁是谁非,恐怕依然不敢奢望会有更多结果。因为,走过来的道路从实践提醒我们,“美是难的”……
这次讨论,如果双方确实都无意回到上述原地踏步式争吵上去,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可不可以用“意象”概念作为阐释美的观点?我认为可以。既然美是难的,对美的阐释也就不妨是开放性系统,各种观点只求自圆其说,彼此便可并立,相互也不必争吵。以此观之,作为一家之言,主张“美是意象”者提出这观点其实没什么值得诟病的。古今中外,关于美是什么,各家各派说法多多,从“美是理念”到“美是典型”,从“美是自然”到“美是形式”,从“美是和谐”到“美是自由的显现”再到“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凡此种种,可谓“条条道路通罗马”,各有自家的贡献。正如有人希望从自然物质中分析出美,也正如有人希望从人的活动探求美,主张“美是意象”者提出从“意”与“象”的结合中把握美,这作为一家之言的关键不在于要顺从美的客观论必须说美在物或顺从美的主观论必须说美在心,而在于只须在论者自己设定的“意”与“象”之间进行逻辑自足的阐述就行了。在这里,“美是意象”说作为一家之言成立与否,关键在于其作为美的主客观统一说的内部逻辑阐述是否自足,而不在于跳开其固有的主客观统一立场而站在其他立场(或美的主观论,或美的客观论)去评议之褒贬之。也就是说,关于“美是意象”话题的讨论,似乎也宜放在与之相同或相近的逻辑语境中为好,否则,又难免陷入昔日诸家争论美时彼此缺乏共同对话基础的那种状况,表面上斗嘴激烈而实际上各说各话,难以形成真正的交锋,自然也就无助于学科及学术的推进。换言之,与其站在跟“美是意象”(美是主客观统一)截然不同的话语基础(美是客观的,美是主观的)上去非议这种观点,诟病这种观点不符合批评者的话语立场,倒不如试着置身对方话语基础(美是主客观统一)去论析用“意象”释美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备有效性,后者也许更有实际的、现实的意义。当然,对于提出和主张“美是意象”者来说,最重要的是逻辑自足的观点表达和理论阐释,而如何在自有立场上将这套话语逻辑表述得更严密、更充分也更圆融,同样是需要不断思考、梳理、琢磨的。
三
当下研究者提出“意象”阐释美学问题的学术意义又何在呢?人们对“美即意象”说有种种批评,但在我看来,提出“美即意象”者有一良苦用意被重视不够,这就是努力用本土话语来解答美学问题。熟悉文学史者知道,西方意象派(imagism)诗歌崛起于20世纪初,其美学之根除了中世纪欧洲哲学和柏格森美学外,正是以重视意象创造的中国古代诗歌为其精神渊源之一。当年敏泽撰写《中国古典意象论》一文[4],认为“意象”是源于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反对视之为西方输入的舶来品,几番辨析后,他指出舶来之说实为“历史的误会”。作为对古典文论用力甚深的专家,他之所言,不无道理。尽管西文“image”通常被译为“意象”,但实际上,“西方美学的‘image’,与中国传统美学之意象,实有内涵的重大区别”[5](P234),后者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尽管二者在某些地方有相通。也就是说,“意象”在中国本是由来古老且极富民族特色的范畴,推重意象形态的艺术是中华美学的优良传统。作为定型术语,“意象”在汉代王充《论衡·乱龙》已见。作为美学概念,“意象”直接用于文论始见于《文心雕龙·神思》。重意象创构的美学思潮在中华艺术史上脉流不断,唐、宋、元、明、清乃至近代,以“意象”论艺者代不乏人。意象美学智慧的萌芽,又可上溯“儒道两家之统宗”(熊十力语)的《易》。尽管中国古代美学主要是从艺术创造和审美来言说“意象”,但并非说不可用此范畴解说“美”。如前所述,“美是什么”迄无定论,持主客观统一说的研究者提出以“意象”来解释美,其作为一家之言未尝不可。须知,中国美学意象论的奥妙,原本就在“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物我融合的意象创构论中,人这能动主体的作用尤其重要,借用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公式,“意象”创造不是“S—R”的结果,而是“S—AT—R”的产物,是既向外摄取自然物象又向内得诸主体心灵的产物。主张“美即意象”者,一方面是想从主客二元对立的区分中超脱出来,一方面更是希望从中国传统美学中寻求美的本质解答的话语资源。这种观点,犹如当年美学领域出现的“美即自由”“美即典型”“美即和谐”等等一样,也是自成一格的。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其从“意象”切入解读美是什么,主要还是希望以中国话语和中国方式来解答美学史上这一“哥德巴赫猜想”。也就是说,这位美学研究者是在朝着中国话语的美学体系大厦建立的方向努力。这种努力,从他的《中国艺术哲学》《中国审美理论》等书之定名上可以看出,从他对商周美学思想、华夏审美意识的追踪可以看出。至于“美是意象”观的张扬,不过是他多年这种学术努力的体现之一。
援“意象”释美,论者又引出叶朗的“美在意象”说。的确,叶先生在其《美学原理》中写道:“‘美’在哪里呢?中国传统美学的回答是:‘美’在意象”[6](P55)。这位美学家强调,以意象释美乃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回答”。叶先生的《美学原理》问世于2009年,他以及当代中国美学研究者对意象问题的关注不始于此。先看学界的集体成果,1995年问世的《中国美学范畴辞典》在“美论”部分收入“意象”,词条开篇释曰:“中国古代美学的基本范畴之一。‘意’即审美者的心意,‘象’即形象、物象。前者无形,后者有形。‘意象’即心意与物象的统一,无形与有形的统一;即意中之象,或含象之意。意象在中国古代美学中具有审美本体的意义,地位大致相当于现代美学中的‘形象’,是文艺所要创造和描绘的基本审美对象。”当然,该书没有把“意象”跟“形象”全然等同,且看词条末尾:“意象在中国古代美学、文艺学中的地位虽略近于现代美学、文艺学中的形象,实与形象大有差别。它侧重于意,而不是侧重象,带有明显的主体性。它产生于审美者的心灵,而不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意象与形象的这种地位近似而内含不同的情况,突出反映了中国古代美学从主体出发,即从审美主体的心意出发,又追求主体融入客体、心意融入物象的民族特征”。纵观《中国美学范畴辞典》对意象这个本土美学范畴的界说,其强调话语有二:一,“意象既然是审美者的心意、情意与形象的统一,则意象就不是客观存在,也不是对客观存在的物象的摹仿,而是审美者的心灵创造……意象实质上是审美者的情感、心意的物象化、形象化”;二,“意象在中国古代美学中具有审美本体的意义,它就是美,就是文艺作品的意蕴美”[7](P72-75)。《中国美学范畴辞典》对“意象”的阐释文字占了三个页码的篇幅,显然是把它作为重点词条设置的。这部辞典对“意象”的解说,时而指“美”(全称意义上的),时而指“文艺作品的美”(单称意义上的),似乎行文矛盾,但仔细琢磨,又不尽然,因为如前所述,对“美是什么”的学术解答不必拘囿在某家某派某说,只要自我逻辑圆融,可以“条条道路通罗马”。而根据重视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中国传统文化观,意象说认为文艺作品作为“心灵创造物”,其美实为情与物、意与象交汇融合的产物。再看学者的独立成果,在当代中国美学界,汪裕雄是对意象专题进行系统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以其多年之力撰写出意象研究三书①汪裕雄的意象研究三书,20世纪以来陆续出版,分别是《审美意象学》(1993)、《意象探源》(1996)和《艺境无涯》(2002)。2013年10月,人民出版社将此三书重刊,称“这三部著作,具有清晰的内在逻辑关系”,说著者是“对20世纪以来中国美学作出贡献的重要学者之一”(编者的话)。。无论从审美心理深层结构对意象的动力学研究,还是从中华本土哲学、历史角度对意象的文化学探源,乃至结合意象与意境对传统生命美学内涵的发掘,汪先生学力深厚的研究成果都令人刮目相看。如今,主张者循此理路,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由此进而去理解整个美及美的对象,倡言“美在意象”或“美即意象”,试图以本土话语对此众说纷纭的美学问题给出一种中国式的解答,有何不可呢?
汪裕雄在《意象探源》引论中尝言:“作者在研习中国传统美学时,久有一种感觉,即近代以来,许多中国学人持西方逻辑理性传统以参照中国古代文化,多少忽略了中国文化的独特之点。”[5](P1)当年,这位学者的意象研究三书,在中西比较视野中对“中国文化的独特品貌”和“中国文化的历史脉络”用力尤其多且深,正是有感而发之作。纵观国内学界,随着学术反思步步深入,力图从本土发掘术语、概念、观点、理论资源来建构中国美学体系,如今呼声甚高。比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论界、美学界对“失语症”的学术反思步步深入,出现了国内学人对“西方话语”霸权的质疑和对“中国话语”创建的热切呼唤。中国美学研究也在“返回家园”的战略选择中重新自我定位,不断寻求新的发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的大旗下,立足本土本民族,构造“有中国特色的美学”成为学术自觉。重写本土美学史,构建名副其实的中国美学大厦,成为当务之急。在此背景下,如今中国美学研究正发生着多方面的视点转移,正如我在若干文章中曾述及的②有关论述,请参阅李祥林《多民族·小传统·形而下———对中国美学研究视野拓展的再思考》,载《百色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多民族视野中的彝族诗学与中国文论》,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性别、民族、中国文艺批评》,载《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2期。。譬如,瞧瞧当今兴起的“审美人类学”研究、“审美文化史”研究、“多民族美学”研究乃至“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当不难看出中国美学领域在发生从“形而上”到“形而下”、从“中心化”到“边缘性”的学术转向。在这种从“上”到“下”的目光挪移中,在这种从“中心”到“边缘”的视域拓展中,步入21世纪的中国美学不断寻求新的学术生长点。又以汉族以外少数民族诗学和美学研究为例,“重建中国话语”成为当下中国美学界、文化界乃至方方面面的共识,人们逐渐认识到,它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对外”也就是如何处理好中国与外国、东方和西方的关系问题。从内部看,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多民族的血缘维系着中华大家庭,多民族文化相激相荡的交流融合历史地铸就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格局,中华美学的全部丰富性和完整性惟有在其他各民族美学与汉民族美学的多元互补中体现出来,而在此多元互补中也蕴含着今日中国美学体系建设可汲取和借鉴的思想资源。再以区别于“形而上”之文字的器物为例,即使暂且不说在文字产生前的种种考古遗迹和实物,在多民族共居的中国,好些族群原本有语言无文字,他们的审美心理、审美意识、审美观念往往凝结在他们丰富多彩的“形而下”的物质文化遗产中。即使是在有文字的族群当中,就审美意识的积淀和体现而言,非文字性的器物(如服饰、建筑、用具、食物等)作为人类文化的创造物,也从方方面面弥补着书面化文本所提供信息的不足……总之,要建设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美学体系,离不开对本土文化方方面面的观照,离不开对中国本土资源的发掘和借鉴,而当下国内美学界借助“意象”诠释“美”,无疑正实践着此。
目前,围绕“美是意象”话题的论争在本土美学界展开,其最终走向及结果如何,不好预测。希望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参与这场讨论,以真诚的思考贡献自己真正有新意的研究成果,从而把这场讨论真正引向深入。在此,重要的是与其说是论争结果不如说是论争过程,因为这场学术论争过程中所反映出的当下中国美学界人士在努力推进学术研究方面的积极姿态和进取精神才是一门学科最需要的,对于这种姿态和精神我们理应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
参考文献:
[1]朱志荣.中国审美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朱志荣.论审美意象的创构[J].学术月刊,2014,(5).
[3]朱志荣.也论朱光潜先生的“美是主客观统一”说———兼论黄应全先生的相关评价[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
[4]敏泽.中国古典意象论[J].文艺研究,1983,(3).
[5]汪裕雄.意象探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6]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7]成复旺.中国美学范畴辞典[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赵琴]
【文学研究】
Think About the Current Chinese aesthetics' Debate Over Imagery Sichuan University,Institute of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LI Xiang-lin
(Institute for Non-orthodox Chinese Culture,Sich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China)
Abstract:The current domestic aesthetics scholars have no consistent view around " Beauty is imagery ".Looking from the advocates and critics of speech,dispute focus is not so much on how to grasp the imagery,rather in how to understand what is beauty.Looking back at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esthetics,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state,two aesthetic boom are built around what is "beauty",but there is no unified view.Only many theories exist side by side,domestic aesthetic community actually gives up the debate on the topic and pays attention to a broader field of aesthetics.Around the discussion of imagery today,there is no need to concentrate on solutions of what is "beauty"."Beauty in imagery"or"Beauty is imagery" is put forward from local discourse resources.The present academic circles have positive response and strive to create the Chinese aesthetic system of local features.These responses and efforts which make Chinese aesthetic research to advance in depth are really important and worthy of attention.
Key words:beauty; imagery; contemporary Chinese aesthetics; Chinese discourse
作者简介:李祥林,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教授,从事文学人类学、文艺美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04-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5-05-007
中图分类号:I01
——论交响乐组曲《草原意象》的意象美